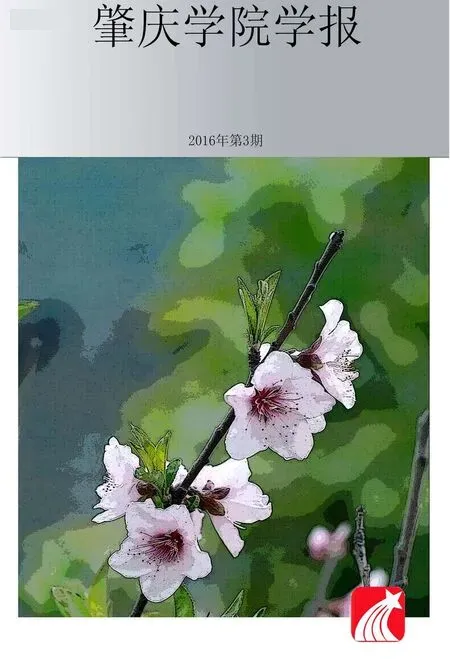日常·去蔽·戏中戏
——《即墨侯》的历史叙事
2016-02-15陈少萍
陈少萍
(肇庆学院 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日常·去蔽·戏中戏
——《即墨侯》的历史叙事
陈少萍
(肇庆学院 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即墨侯》中郭家绵延几代人的家族历史与民国至解放后的岭南大历史,并置在作家个人化的书写里,以小见大,传达作家对历史的想象和理解;作家调动了各种写作手法,郭家狗的全知视角、变换的叙述时态、旁人回忆、作者插叙等,使被叙述的事件呈现出立体多维的形态,着力还原被遮蔽的历史和生存故事;“戏中戏”的诵读方式则给庸常的和平年代注入一股厚重的历史感,使端砚文化与制砚人的家族传统再次成为支撑整部作品的精神内核。
《即墨侯》;历史叙事;宏大;日常;去蔽;戏中戏
钟道宇把对端砚近乎宗教式的热爱和虔诚融进一段宏大的历史书写中,在端砚温润细腻的质地里研磨出郭家一代代人的生命歌哭。作家似乎努力在日常生活和博大的历史之间舒展开一份最具个人情怀的诗性想象,为我们努力重构一段民国历史的记忆。在文本的叙述话语中,我们感受到这种努力的真诚。
一、历史叙事的宏大与日常
作品以史诗的姿态瞭望民国以来的岭南肇庆,并把时间坐标定格在解放后的肇庆新貌。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这里的历史既是关于政治的、战争的、革命的大历史,又是郭家人关于气脉的、风度的、精魂的家族历史。无论何种历史叙事,它们都是作家对规范化理性历史整体的一种图解,着力用文本虚构的话语寻找民国以降的历史真相,并在郭家人身上积淀着厚重沉实的历史气息,使“大”的历史书写和“小”的家族变迁在文本话语中找到一种共存的关系。
这一写作意图通过狗的全知视角完美地体现出来。魔幻的轮回不死,超验的前生今世,拟人化的讲述口吻,把叙述的时空极度膨胀,在纵横杂沓的人事变幻中,从容而富有安全感地把握历史与人生。由郭家老侯爷、郭端正、郭树生、郭木桥……这基于亲情血脉和家族精魂的链条,在郭家狗的轮回转世中得以延续,这其中,整合了作家对民国时期大历史的个人化叙事。同时,狗的忠诚品质,使得叙述角度具备了客观实诚的特点。它重在尽可能地用参与的眼光记录着郭家上下几代人的生命轨迹,同时也烛照着影响人物命运的时代;它从不对人物命运沉浮进行先知般的预言,也不予罹难的时代妄下道德评判。因此,狗的全知叙述角度,不仅赋予作品历史叙事宏大的史诗品质,还使得在叙述话语重构中的历史获得某种意义上的真实品格。犹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诗比历史更具有历史的普遍意义”[1]。借助小说虚构的语言文字,人们可以把握经过独特解释的历史。
郭树生为孙中山刻砚的家族秘密,反衬的却是孙先生“天下为公”起共和终帝制的博爱理念;郭树生夜上鼎湖山的忐忑拘谨,映照的是孙中山平易近人的慈悲胸怀和运筹帷幄的革命气度;疍家母女平静相依的日常生活和质朴温润的山水情缘,牵出袁世凯复辟和反袁运动,再窥见肇军总司令李耀汉的仕途跌宕;伴随着郭树生与翠莲的生死爱恋,我们领会了桂系林虎军长的魄力和柔情,更感受到桂军与肇军混战的凄凉岁月;罗彩云对郭天赐的痴心等待和舍身取义,背后却是刘副官的阴险毒辣和变节投诚;郭家玉和陈老师的志同道合,给抗日战争泼上了最浓墨的色彩……不一而足。郭家人日常的生活温度,融化着历史的理性和恢弘,它们都在作家的诠释中获得了独特的意义。
二、历史叙事的遮蔽和去蔽
如果说,规范化的正史是史学家话语权力的结果,它记载了历史清晰的真相,把历史的多种可能性阐释成唯一的必然;那么,个人化的历史叙述在讲述时也获得了某种话语权力,它体现了作家理解和想象中的历史形态。如何在话语权力对历史真相的遮蔽中,拨开迷雾,给予历史更多的可能性,或从更全面的视角去考察,这是一种两难的叙述。
我们不难发现,作家灵活地运用各种叙述方法不断地在给历史去蔽。它首先体现在,狗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不同视角分别切入叙述。当郭树生终于完成那方“天下为公砚”之后,郭家狗卧在郭府冰凉的青石台阶上回忆,由此补写进一段郭端正如何成为即墨侯的历史,这是现在视角对过去时态的补充;“一双晃来晃去的手”,引发了狗对因制作“百鸟归巢砚”而使郭端正惹祸被砍下右手的灾难的反思;“夜上鼎湖山”的最后部分,郭家狗补叙飞水潭对鼎湖山发展旅游事业的意义以及粤语和普通话的国语之争的事实,等等,所运用的是狗的未来视角对现在时态的切入叙事。这种时态的灵活转换,让历史被遮蔽的某些部分逐渐显示出更全面的形态。
其次,借用他人,往往是亲历者的讲述、补叙。郭天赐对黎仲实生前基本情况、伟大功绩的回忆,使其真实的形象渐渐浮出历史地表;郭木桥老人对作家钟道宇讲述“千金猴王砚”的历史,并道出与黎仲实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是珍藏的相片,无不从各方面充实了黎仲实作为同盟会创会会员和辛亥革命志士的血肉形象;还有作家钟道宇对狗讲述砚的历史、砚的收藏,从另一个角度丰满了郭家端砚技艺传人的家族精魂和砚文化精粹。这种借亲历者的讲述方式,在为历史去蔽的同时,也为历史奠定了真实可信的基础。
再次,便是作家作为小说第一叙述者的写作技法:插叙。历史的纵横与盘根错节,无法在有限的小说篇幅中得以淋漓铺展,于是,插叙便成了虽然传统却有效的方法。肇庆西江的大水灾、高要惨案、肇庆四会至广州的“四海轮”沉船溺亡事件、四会县政府驻县国民军联合拘捕麻风病患者、日军进犯肇庆城,等等。作为一部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文化历史小说,地域特色不仅仅体现在端砚这一文化符号身上,还体现在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历史变迁、自然灾难、人间祸害上。在此意义上,作家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因为有了肇庆这一实体及生于斯长于斯的肇庆人民而显得更为生动和真切。
三、“戏中戏”的个人化历史想象
如果说小说上半部是从历史的纵向进行叙述的话,那么下半部则是在横向现实层面上的书写。如何在现实中描写出历史感,使得整部作品不至于头重脚轻,这不仅是一种写作策略,更是历史在现实中的无尽延伸。
在这里,作家用了“戏中戏”的手法。第一层“戏”意在呈现作家钟道宇与妻子无聊的日常生活。一种精神上无共鸣、心灵上不相通的平面家庭生活,与郭树生和翠莲超越生死的爱情,与郭家玉和陈老师拥有共同生活理念和革命情怀的爱恋,甚至是刘副军长对罗彩云的强盗式抢掠霸占等相比,显得更加苍白而无力、平庸而琐碎。在这种意义上,第一层戏的深意在于反衬对比,两个时代、两段历史、两种生活并置形成巨大的反差,让读者有种失重的落差感。然而,正当我们倍感无聊的时候,作家巧妙地引入第二层“戏”,它体现在作家在狗面前所进行的朗读。使得这部以端砚为题材和审美对象的小说,不仅再一次充满了历史感,也让小说前后部分有了一个较完整和一致的文化主题。作家钟道宇的《千金猴王砚》,以最具个人气息的想象,构建了汪兆铭和陈璧君乱世中相遇相知的故事,并表达了作者一种全新的理解。同盟会时期的汪兆铭,在《民报》上写大量反清文章的汪洋恣肆、做革命演讲的汹涌澎湃、转战日本秘密复刊《民报》的坚定信念,甚至策划银锭桥上埋炸药暗杀摄政王载沣的惊天动地、对陈璧君的优柔寡断、锒铛入狱的慷慨悲歌……在第一层“戏”的平面碎片里,慢慢浸染出历史的厚重感。历史有其终极的真相和意义,却永远没有一个我们能确定的具体真相,后现代思想家伊阿布·哈桑说,“历史是一张可以被多次刮去字迹的羊皮纸”[2],它既存在于历史资料中,也存在于主体的不断追求之中,每个人都拥有对历史真实至高无上的想象权利。而汪兆铭和陈璧君的历史,体现的正是作家用个人的方式对历史终极意义的求索——时代、际遇、自身性格等是如何影响着汪兆铭由文人而政客,由爱国而卖国的人心变异。
《持守——岳飞砚的前世与今生》的诵读,则将历史往纵深方向推进。由一方砚串连起岳飞、谢枋得、文天祥三位爱国将领舍身成仁的英雄气概,为保卫南宋王朝抵抗金军、蒙古军的惨烈血腥,凝聚成“不磷不缁、持坚守白”的民族气节。作家在这些浩然正气的爱国英雄身上,有着自己鲜明的道德倾向,于是,一段保卫大宋王朝的历史便以作家想象的形式诗意地铺展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戏中戏”以端砚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而整部小说第一人称视角的郭家狗与读者却一起成了第三方听众,这种叙述视角的变换和互相阐释,也为作品历史感的沉淀起了积极的作用。
关于郭家狗来世做人与来世做狗的悬念,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考空间,它将永远在人世的变迁与轮回中,让每一个今天最终成为历史。
郭家绵延几代人的家族历史与民国至解放后的岭南大历史,在作家的想象中成为一种个人化的历史叙事,作家用郭家狗的全知视角、变换的叙述时态、旁人回忆、作者插叙等写作手法,努力为历史和生存的故事去蔽。当历史演变成平庸无聊的现实时,“戏中戏”的诵读方式则为其注入了一股厚重的历史感,使端砚文化与制砚人的家族传统再次成为支撑整部作品的精神内核。
[1]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18.
[2]伊阿布·哈桑.后现代主义概念初探[M]//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23-125.
O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Ji Mo Hou
CHEN Shaop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Guangdong 526061,China)
Ji Mo Houintertwines the continuous history of generations of Family Guo with the long history of South Guangdong from the time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until the time after PRC was established.The result is a very personalized book,which reflects Family Guo's life as a microcosm of the immerse history taking place around them,and in turn demonstrates the writer's imagina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the history.The writer uses various writing techniques,such as Jiagou Guo's omniscient perspective,switching narrative tenses,memories from bystanders and interposed narration from the writer,etc.This type of narrative creates a multi-dimension view of the events,and restores the depth of the hidden history,joy and tragedy found in their life stories.The book unfolds a“play within a play”,injects a rich appreciation of cultural and traditional life in ordinary and peaceful times,and enables the culture of Duan inkstone and the family tradition of inkstone makers to be the spiritual core of the entire book again.
Ji Mo Hou;historical narration,immerse;daily life;off-cover;play within a play
I207.425
A
1009-8445(2016)03-0012-03
(责任编辑:卢妙清)
2015-10-12
陈少萍(1978-),女,广东潮州人,肇庆学院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