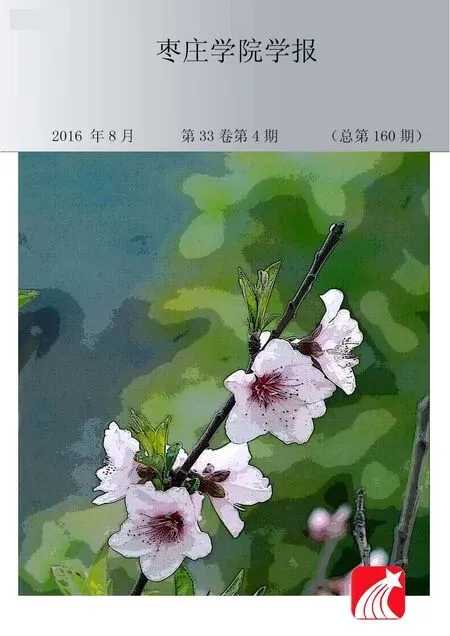从《论语》对鲁国违礼现象的批评看孔子“礼”的观念
2016-02-15胡其伟
胡其伟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从《论语》对鲁国违礼现象的批评看孔子“礼”的观念
胡其伟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摘要]《论语》广泛地记载了孔子和其弟子的言行,其中孔子对鲁国违礼现象的批评语录有若干条,虽不多但引起了古今许多学者的争论,值得注意。这些批评有的是针对当时的士大夫,有的则针对鲁国公室。针对这些批评进行研究,可以看到春秋时期鲁国礼制的逐渐崩坏,也能从另一方面理解孔子礼的观念。
[关键词]《论语》;违礼;批评;观念①
《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其核心在对于“仁”和“礼”的相关看法。而这些观点则散见于孔子对于礼和仁的阐述以及对当时礼节的评论之中,尤其是孔子对违礼现象的批评,蕴含了丰富的孔子有关“礼”的观念。
一、鲁礼的本源
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周初分封,其长子伯禽代周公就封鲁国,成为鲁国第一任国君。周公殁后,成王鉴于周公之勋劳,“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1](P1522),“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2](P842)。鲁国除了有周公庙,还有文王庙,可知,鲁国所享有的天子之礼,限于祭祀周公、文王之时使用,这部分天子礼乐与正常情况下享有的诸侯士大夫等礼仪构成了鲁礼体系。
自宋代以来,对于鲁国是否能享有天子礼乐分为三种观点。马端临等认为,天子礼乐虽是成王所赐,但鲁和伯禽不当受。清代学者崔述则引用“八佾舞于庭”和管氏“反坫”反推此举是鲁国自行僭越。顾栋高则认为,鲁国确享有天子礼乐,但有所降杀。[3](P22~24)
实际上,从种种迹象看来,鲁国确有享用天子礼乐的资格。《礼记》的记载不必说,除了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以外,还切实记载了鲁君郊祭时的威仪——“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韣;旗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2](P843)。《左传》中还记载了定公四年,卫国子鱼追述西周武王、成王时的分封,在讲到鲁国时说到“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明德……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4](P1536~1537)。对比康叔、唐叔的分封,鲁国的独特性可谓是绝无仅有。除了相同的分领殷民族氏、大路之外,鲁国还有“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这类天子才有资格享有的玉器良弓,甚至派遣了成套的官员,赐予了典籍、官司、彝器,周王室给予鲁国的待遇确实不同于其他诸侯。吴季札、韩宣子等使臣聘问鲁国,鲁国为其遍演群乐,仿佛如今都能看到乐舞恢弘盛大的场面,通晓并遍演群乐也是天子才能有的权力。因此,鲁国兼有四代之服、器、官,成为儒家学者心目中除王室外王礼之所在。
《左传》多次记载他国攻打鲁国,却难寻鲁国有天子礼乐是违礼的端倪。无论是闵公四年鲁国因“犹秉周礼”而保全,还是之后对鲁的征伐,都没有哪国家以鲁国不应有天子礼乐为借口,可见,任何一个邦国,都对鲁国秉持周礼是认可的。更何况,周公确实具有能够配得上天子礼乐的德行。武王克商之际,周公便立下过赫赫军功。在灭商之后,“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1](P1515)。在武王去世后,“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5](P516)。实际上就是安抚王室,率军东征平定三监之乱,使周的统治区域真正的扩展到东方沿海,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继承武王的事业,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分封,稳定了周初的统治秩序。礼乐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形成,使西周走上正轨,从而影响了后世的中国。《礼记·礼运》中孔子也称赞周公“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2](P583),其认为周公谨守礼节,比肩禹至成王这些后王,同时也肯定了成王是一代明主,否则在文献中也应当有孔子对成王重赐鲁不满,而传世典籍则未见。
从上述所引史料所见,鲁国拥有天子礼乐是毋庸置疑的。《左传》就有多次鲁人祭天祭祖的记录。但笔者认为,如果鲁国真的拥有所有的天子礼乐,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无论是《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称颂周公之德[4](P1227),还是《礼记》、《史记》中叙述成王赐给鲁国祭祀周公时享有天子礼乐,尊崇的对象都是周公,也就能明确鲁国所享有使用天子礼乐的权限仅限于祭祀周公及文王、天地山川,祭祀除周公之外的历代鲁公则不能使用天子之礼。而且,孔子对周王的称颂更多地局限于文王、武王和成王、康王,而康王之后的各王统治期间已经“王道不显”。之后的周王不作为,他们在违背礼的情况下将天子礼乐“滥赐”给鲁国,鲁国拥有除周初正常受赐以外一部分天子之礼也就不言自明了,“滥赐”所得之礼本身就是不符合周礼的原则。不耀德而观兵的穆王,烹杀齐哀公的夷王,违背宗法干涉鲁政、丧南国之师的宣王,以及伤周道的幽王厉王都可能“滥赐”之。再者,《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家驹就明言鲁公“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6](P524)是僭越,很有可能在祭祀历代鲁公时,也正是僭用天子之礼。
二、孔子对鲁国违礼现象的批评
在西周中后期,就已经出现了礼制被破坏现象。周宣王凭喜好指定鲁国君位的继承,给鲁国造成了内乱;周幽王废申后和宜臼而立褒姒和伯服,违背了西周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继承规则。到春秋时期,下犯上者有之,臣弑君者有之。孔子对鲁国现实的指责,实际上也是对整个西周末年和春秋现状的不满。
(一)士大夫对礼的僭越和破坏
孔子的批评,最大的一部分集中在对士大夫,尤其是对鲁国三桓的僭越和破坏礼制的批评。
1.大夫僭天子
乐舞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乐舞配合周礼,共同起到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作用。“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7](P192)是《论语》最先所见的评论,季氏八佾舞于庭也是大夫违礼的典型代表,孔子对此发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慨。按周制,乐舞的阵势以天子为最大。天子八佾,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7](P191~196)如果鲁国祭祀周公、文王,采用八佾之舞倒还符合礼制标准,但如果是祭祀其他先公就难以解释了。作为大夫的季氏,是不允许使用八佾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正记载了季平子招去跳万舞的人,使得对襄公的祭祀无法进行。[4](P1462)很有可能孔子对此批评是针对于此,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亦持此观点。[8](P23)
大夫强,公室卑,三桓在举行家祭也不遵循礼制。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7](P197)三家在家祭后撤去祭品礼器时歌《雍》乐,《雍》乐是天子撤祭时所用,鲁国有时也可使用,作为大夫就无权享有了。按照《雍》诗的内容,天子祭祀,助祭的是诸侯,庄严肃穆。显然是是天子的特权,三桓作为大夫僭用《雍》乐,不合周礼。
2.大夫僭诸侯
以三桓为首的大夫既然不对天子的特权有所顾忌,对公室的特权自然也更不在话下。《八佾》篇云: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7](P210)旅(也做祣,或者胪)祭山川则是鲁公的的特权。季氏旅于泰山,行诸侯之事而非诸侯之尊,孔子言泰山之神不如林放,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作为大夫的季氏旅祭泰山是不够格的。
当然,三桓还搜刮有术。季氏所聚敛得比鲁始祖周公还富有。周公富在德,而同为其后的季氏不念先祖的德行,贫困民众,甚至孔子之徒子路也助长季氏的横征暴敛,孔子自然愤然说道:“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7](P999)
春秋时期,以下犯上屡见不鲜,《论语》记载的是陈成子弑杀齐简公的案例,孔子建议鲁公出兵讨伐,鲁公竟然说“告夫三子(三桓)”[7](P1293)。可见,鲁公的权势衰落到甚至连军队的控制权都难以掌控的尴尬境地,昭公出奔也就可想而知了。无怪乎孔子感叹鲁国现状的“无道”: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7](P1465)更不需奇怪的是季氏在问政的时候,孔子也会借题规劝“子帅以正”[7](P1117)、“苟子之不欲”[7](P1119)。
在孔子所生活的鲁国,他所见的贵族僭越肯定不仅仅是展现在《论语》中的这些。从春秋之初开始,整个社会秩序趋向混乱,周天子权威一落千丈,频频有王师与诸侯国交战的事例。更何况“犹秉周礼”的鲁国公室衰弱,大夫掌权。在春秋时期的鲁国,贵族阶层权力欲望的扩大和公室想要保住其独特的权威,势必产生冲突,而这些冲突的表现正是大夫的僭越和他们对礼的破坏,甚至因此产生武装冲突,一旦维护旧有等级秩序的礼制破坏,公室权力下移,有权势的士大夫阶层就可以趁机把持国家权柄。
(二)公室对礼本身的破坏
鲁礼的破坏,不仅仅是外部势力——大夫阶层尤其是三桓——有意无意违背的结果,还是公室本身的不自觉甚至是破坏。公室带头不遵守礼,为秩序的崩塌推波助澜。《春秋》之始就揭示了这一点。隐公的上位很大程度上由于太子的年幼,使得他有问鼎君位代为摄政的契机。然而在隐公五年,隐公不顾大夫的劝阻跑到棠地去看捕鱼这种低下的职业,这与周礼等差有序相悖。在“考仲子之宫”时,他严格上说只是摄政的身份,也并非仲子的嫡子,本不该由他来主持。且如上文所言,祭祀仲子是不能够使用八佾的,《左传》以其笔调特意地形容隐公初次正确地遵从周礼用了六羽,实际上就是在讥讽鲁国当时甚至在很长的时间内可能就一直在用八佾祭祀先公。“初”、“始”字之褒贬可见一斑。
在《论语》中,除了违背“同姓不婚”原则的昭公外,其他例子并不多,但也不是无迹可寻。《八佾》一章有记载,“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7](P228)历来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孔子认为鲁国僭越天子之礼而不想观看。仅从语法上容易发现,这样解释极为不妥,灌以后不想看,那么灌和灌之前呢?上文也提到,鲁国是拥有天子之礼的,若是祭祀周公等正常情况下时,这句话如此解读就极易出现误解。既然是灌之后不想再看,那么是灌之后出现了什么状况导致孔子不想看呢?笔者发现,也许在最初编撰《论语》这部书时,章节的内容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八佾》这一章节更多的介绍了孔子对当时违礼现象的批评;在《乡党》这一整个章节,几乎都是讲孔子亲身践行礼仪的各个方面。而正是《八佾》这一章的最后一句,笔者发现正能接在“不欲观之”之后,不但内容的相关性甚为匹配,而且在语义衔接上比《论语》中其他章节任何一句都更加合适——“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7](P299)那就可解释了,孔子作为周礼的继承者,不仅仅认为礼是外在的约束,还应该成为每个人内心的自我意识,而且祭祀丧葬承载了“慎终追远”、“报本反始”这一孝道的基本表现,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主祭者,身居高位却不宽厚,主持祭礼却不恭敬,有丧事却不感到由衷的哀伤,孔子恐怕是看不下去的。对于类似的言论,还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7](P238~240)“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7](P1557)孔子认为,做一件事情不能仅仅去操作死板的流程走过场,尤其是孝道方面。孝敬父母除了基本的物质关怀,最重要的是对父母最真诚的爱,包括祭神的时候就要像神灵真的在面前一样由内心产生敬畏,所谓的玉帛和钟鼓,都是表现礼的方式,而更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认同。
三、孔子礼的观念
孔子对周礼的评价很高,认为周礼吸取了夏商二代的精华,郁郁乎文哉,正是他一生的追求。夏代的精华是质朴而接近人情,孔子称赞夏祖大禹是个无可挑剔的伟大人物,“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7](P735~736)正是艰苦朴素的真实写照,孔子也坚定地站在了质朴一边、孝道一边。而“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2](P1311),孔子认为质很重要,文也不能缺,他和弟子选择了“文犹质也,质犹文也”[7](P1088),做一个表里都懂礼守礼的君子。
周代的礼,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代的特色。朱凤瀚先生在《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中说到,基于政治因素和克商后新的形势,周人对商人的上帝的观念有所继承和发展,增添了道德色彩,成为约束贵族的行为准则。[9](P20)《礼记·礼运》中明言,礼本源于原始的饮食习惯和对死者、先人的纪念以及神秘莫测自然的崇拜。经过夏商二代的充实,到了周代,经由周初的“制礼作乐”,形成系统的礼乐制度。周人对礼乐的系统化、程序化,剔除了较为原始的宗教色彩,增添了政治、伦理的因素,用以维系血缘宗族和等级秩序,形容为“尊尊亲亲”。李泽厚先生将其概述为“它是在周初确定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其特征是将以祭神为核心的原始礼仪,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统化、拓展化,成为一整套习惯统治法规”[10](P8~10),是相当贴切的。
孔子自诩周代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发扬者,是丝毫不过分的,无论在鲁国担任中下级官职,还是周游列国期间,都切实地践行着应有的礼仪,以至于在被匡人围困之时,依然不改初衷,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7](P762)
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学者认为孔子是一个固守周礼而不变通的人,其实孔子对于周代礼乐文明,既有所保留,又有所革新。其中最主要的,无外乎两点。
一是对三代以来宗教观也就是对天和鬼神的敬畏认识。由于社会生产水平和知识水平的局限,当时始终不能正确认识自然及其规律。在春秋时代,虽然对天和天命观保持仰望,孔子也说“天生德于予”[7](P623)、“获罪于天,无所祷也”[7](P246)。但是春秋时期,王道不显,周室德衰,诸侯争霸,曾经膺受天命的周王室也没落到偏居一隅,那些传颂的先祖神灵,在世俗受到危难的时候也没有顾及他们的子孙后代。随着情形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人们质疑天命鬼神。不仅仅在《诗经》中有“昊天不佣,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11](P661),“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11](P683)等对昊天上帝的抱怨之辞,就是在《论语》中,也有孔子否定子路祈祷有用所说的“丘之祷久矣”[7](P655)、“敬鬼神而远之”[7](P520)。天命不显,这些言行事实上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对社会动荡、秩序混乱的呼号和孔子对一生向往的周礼复兴艰难的无奈和喟叹。从孔子对违礼现象的批评来看,孔子在内心是认识到社会现象的并承认的,与其说他“知其不可而为之”,更不如说他是在内心坚守它就像人们坚守梦想一样,这无可厚非。
二是对周礼的认识和实践的提升。首先,孔子认为,礼是人生存的必备条件,把礼提升到“得之则生,弗得则死”[2](P585)的高度。周礼汇集前代的精华,尽善尽美,应由始至终遵循。其次,礼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能有所损益,“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7](P749),民之所欲,为政者从之。再者,每次进太庙的时候总是要问一问,并非孔子刻意不知礼不守礼,因为对礼本身孜孜不倦的态度,也是礼的表现。周室东迁以来,对有配天之德、昊天上帝的祭祀并不多见,鲁国本身对郊禘之礼的举行或许也并不中规中矩甚至本身就有违礼制,且礼乐崩坏的春秋时期,人们所遵循的礼更多只是礼的外在仪轨,已失去对礼的内在精神的自觉认同和自我提升。孔子或真的对禘礼不甚明了,直言不知,所以对各种细节都要问一问;或对他期望已久的鲁国现实大失所望。而在他的心里,真正懂得这些礼仪的人,一定是像文、武、周公那样的懂得治国的至德之人。可以说,掌握礼的前提是要对礼虔诚向往,不断追求,身体力行地正确完整地认识礼。不仅仅如此,正如上文所说,最重要的是个人内在自我修养的提升,即个体对“礼”这一规范的自觉认同和自我境界的提升。譬如在丧事和祭祀的时候,要正心诚意,就如先人神灵真的降临面前而毕恭毕敬,否则,玉帛和钟鼓都齐备,但内心却没做到敬畏怀念,也不符合礼的原则;在碰到有丧事的人,一定也会表现出悲伤的神色,“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7](P582)。这也是孔子推己及人的原则,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亦是“仁”的理念的体现,[12](P40)孟子所言为“恻隐之心”。
可见,孔子对礼,并不是原模原样的继承,他看到了社会现实,看到了士大夫、公室对礼的僭越和破坏,他坚持周礼,又在原有周礼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化、世俗化的整理。他倡导的礼,是贴近生活的礼,所以我们在《论语》中所见的孔子,既有他理想中的追求,又有切实的有血有肉的一面,两者并不矛盾。如今我们很多人也一样,在理想和现实有矛盾冲突的时候,有时选择坚守内心,有时选择屈服现实。
四、结语
通过对鲁国礼乐本源的分析,我们知道,鲁国在周初确实被赐予了使用天子礼乐的资格,虽然并不是享有全部天子之礼,但在历史上确确实实举行了一些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的仪节。孔子对违礼现象的批评,并非是因为鲁国在周初继承一定的的礼乐体系时没有资格,而是时光的流转之中,无论是康王后历代周王的滥赐,还是鲁国公室、卿大夫阶层或多或少冲击鲁国的礼乐体系,都是不符合礼的表现。“周礼尽在鲁矣”[4](P1227)本身的形容没有错误,当时的社会,能在一国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持周礼,舍鲁国其谁?只不过遗憾的是,鲁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非礼僭越,违背周礼的情况难以枚举。孔子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他也感慨“周公其衰矣”[2](P597~598)、“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7](P569),他既做了对理想的坚持,也根据现实做了一定的折衷和调整。孔子的礼,是理论化却又接近世俗的,他认为,人贵为有礼。实践礼的前提是正确、完整地认识礼,在自己身体力行的同时强调推己及人,由家到国,再到天下。而重点是发自内心地尊崇礼,礼质朴崇敬的内涵比各种具体的仪式都更加重要。这也正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时,要由最基本的孝发展到礼再到最高的仁。这些坚持、折衷和发展,很大程度上都在儒家的典籍中有所体现,而《论语》以丰富的对话和举止保存了下来,让我们看到孔子和弟子生活中的一面,也看到了这字里行间所蕴含着的孔子的礼乐观念。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王青.礼乐文化嬗变中的鲁国祭祀[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5.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黄怀信,周海生,孔德立.论语汇校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8]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朱凤瀚.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J].中国社会科学,1993,(4).
[10]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8.
[11][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2]王灿.言语之外的孔子形象——以《论语·乡党篇》为中心[J].枣庄学院学报,2009,(4).
[责任编辑:张昌林]
[收稿日期]①2016-05-26
[作者简介]胡其伟(1992-),男,浙江丽水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5级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77(2016)04-0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