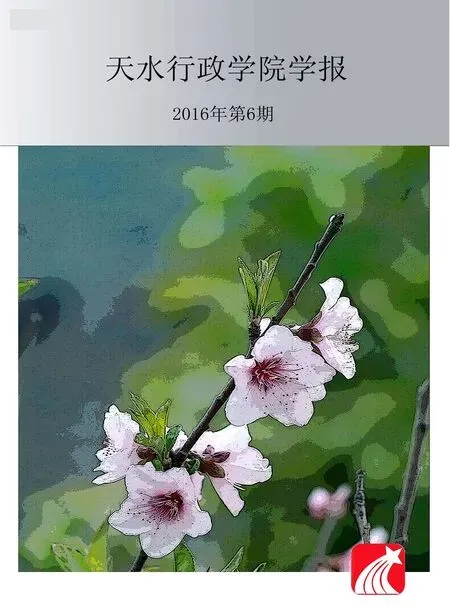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
2016-02-13吴玉姣
吴玉姣
(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
吴玉姣
(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领悟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一般属性,认清其专有特色本质,有助于对其内涵的正确解析;把握西方法治话语体系应用于中国法治的弊病,熟知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本土优势,认准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法治话语体系的融合趋向,有利于深刻体会构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必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推进需要以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自觉构建为基础,同时也要求在树立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自信后使之自立、自强。以此为前提,有必要主动推进法治体系建设、深入挖掘传统法学理论、仔细推敲司法实践案例、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法治特色。
中国;法治体系;法治话语体系
“一个没有独立学术话语体系的学科,势必在学术上失去说话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从而最后导致失去生存的空间。”[1]李龙教授以此论证构建中国法学学术话语体系的紧迫性。同样,构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也有其重要意义与现实需要。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还一度被视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意味着我们正面临一项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我国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向全世界诠释,以成功塑造“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形象,撼动西方法律帝国主义,打破其法治话语霸权。因而,探寻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刻不容缓。
一、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内涵
“话语”原指“一段大于句子的连续语言。”[2]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人们交往需求而产生的话语,逐渐演变为力量的象征。在话语理论方面造诣颇深的法国哲学家福柯对“话语”一词见解精辟,他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3]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与法治话语体系在逻辑上成种属关系,因而领悟中国法治话语体系同于法治话语体系的属性,认清其专有的特色本质,以正确解析其内涵,是构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首要环节。
首先,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作为法治话语体系的下位概念,同样反映了法治话语体系的一般属性。“法治体系”是集描述性和规范性为一体的概念,包括“保障人权、制约公权、促进公正、维护稳定、推动发展等价值内涵”[4]。概言之,法治话语体系可认为是对权力话语进行制约、对权利话语进行弘扬的体系。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一般属性体现为:一方面,几千年传统礼教和生活习惯,使得中国人们对权力无上敬畏,这种权威崇拜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当今的权力滥用。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被提上日程,这是对权力话语进行限制的开端。另一方面,自19世纪西学东渐后,权利概念被引进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经过五四运动的启蒙也日渐觉醒,尤其是2004“人权入宪”开启了保障人民权利的新纪元。而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以法治保障人权的宏伟纲领”[5],将人权保障措施进一步细化。在全面保障人权已然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任务之时,开放权利话语成为大势所趋。
其次,“限制公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法治最本质的属性,在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中当然应有所体现。然而,中国法治话语体系又根植于中国法治,其必然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影响,显露出专有的特色本质。如《中国法律的形状》[6]一文曾将中国法律系统的社会结构概括为“内圆外方”、运作方式描绘为“三位一体”、价值观冲突表述为“二元对立”、文化核心认定为“法政合一”,相应地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也反映上述特征。以中国法律系统“内圆外方”的社会结构为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于2011年建立,预示着我国法治“有法可依”的局面形成。这是我国现阶段法律系统社会结构的“外方”表现之一,而作为中国法治体系表征的话语体系必然也离不开这一框架的限制。另外,受“以和为贵”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法律往往注重协调而淡化规则,进而形成了法律系统“内圆”的社会结构。这也就催生了“案结事了、定分止争、胜败皆服”[7]等一套独具特色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当然,“外方”的法律系统不可避免地与法律实践有些脱节,“内圆”的法律系统也因法律的灵活运用给了权力可乘之机。中国法治体系存在的这些缺陷导致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相应地有“远离实践、注重权力”之嫌,在今后的完善过程中需着重改进。
二、中国法治话语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一)西方法治话语体系应用于中国法治的弊病
西方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对于中国法治的积极作用,我们不应忘怀。然而西方帝国主义日渐显现的通过法治进行殖民的负面样态,我们也应有所警惕。鉴于此部分的论证视角,笔者仅描述西方法治话语体系应用于中国法治的弊病,以此说明有必要打破西方法治话语的霸权地位,具体分为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西方法治理论本身不完备。“自由主义法治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公开推崇并向后起法治国家推行的法治形态,大致可以代表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主流法治意识形态。”[8]然而,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给西方民众和当代中国人刻画的是一个超级理想的乌托邦似的法治图景。首先,作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构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其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实践的假想。其次,“社会变化,从典型意义上讲,要比法律变化快。”[9]由此可见,作为社会生活调节工具的法律有其局限。再次,法律的普遍性使得个案正义有时得不到考虑,法律的强制性忽视了现实中必要的妥协。因而,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便往往以实质正义的不能实现为代价,将程序正义推向制高点。在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缺陷明显的情况下,渗透其中的西方法治话语体系必然也不够完善。
中西方“法”的差异。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观点,法的本质可归结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二是,“法的内容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10]。西方的“法”体现资产阶级意志,其内容由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而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意志与物质生活条件与西方国家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中西方的“法”存在本质差异。此外,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都视为“法的精神”。诚然,道德文化、历史传统等都会对“法”产生一定影响。就这些方面而言,中西方的“法”也有着根本性区别。如西方传统文化主张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注重契约自由与个人平等;中国传统文化则以儒家思想为主,试图追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就使得以“法”为前提的法治话语体系,在西方更注重个人自由,在中国更侧重以和为贵,于是也便决定了西方法治话语体系不能应用于中国法治的局限。
(二)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本土优势
符合中国实际。针对“法治”经世致用的特征,各国也必然发展出专有的法治话语体系。如为“方便人民参与审判、便利审判回应民意”而存在的陪审制度在各国的表现形式就不尽一样。仅在东亚国家中,就存在日本的裁判员制度、韩国的国民参与审判制度、台湾地区的公民观审制度,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等泾渭分明的形态。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指与法官有着同等权利的人民陪审员参加法院审判的制度。围绕其产生的系列配套措施如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的范围、任职的条件、经费保障等都与中国社会现状紧密相联,而中国法治“镜像”的话语体系也必然要与中国实际相符。另外,见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的法治话语体系身负着顺应中国现实法治的使命,这是西方法治话语所不能胜任的。仍以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为例,为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人民陪审员制度也在进行相应的完善。2015年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的10个省(区、市)中各挑选5个法院开展改革试点工作。这一法治的新举措必然会带来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变更。
具有中国特色。“任何法治建设都必须面对不同的国情。”[11]参与中国法治建设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也必然具有中国特色。如,具有上达民情民意功能的“信访”,在我国古代各朝各代都有应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传统制度得以继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行信访法律体系形成了以国务院、各省市自治区的《信访条例》为主的基本框架。虽然,现有信访制度的部分功能已异化——“信访不信法”、“弃法转访”、“以访压法”等问题频繁出现,但这一独具特色的制度仍具有重要意义。“对民众来说,它承载着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的诉求与祈盼;对社会而言,它是化解纠纷和救济权利主要途径;对政府来说,更希望它起到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12]随着2014年《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的通过,信访制度在中国大地上仍将继续发光发热,这也就表明了相关法治话语依然存续且需要进行完善。较之几乎缺失信访制度内容的西方法治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优势显著。
体现中国法治的发展规律。1997年“依法治国”被视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1999年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被确定,2012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得到了战略性部署,这些无疑反映了在我国法治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其见证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也因之而具有愈加丰富的内容。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法学界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和解读西方的法治理论和实践。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的法治理论与中国实际问题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开始走入法学家的视眼。从言必称西方到法治本土化研究热潮的兴起,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也越来越多地提及法治及其本土化。深受我国法治发展规律的影响,西方法治话语体系的作用被逐渐淡化,中国法治话语体系慢慢开始得到关注。
(三)中西法治话语体系的融合趋向
在法律国际化和法律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法系与各国之间的沟通得以加强,在相互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的范围愈加广泛、程度也愈加深刻。如在司法案件呈井喷式爆发的当下,低效率、高成本以及处理结果较为单一的诉讼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非诉形式的司法救济程序应运而生。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人们开始寻求以非诉渠道解决纠纷。另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各个国家的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也在缩减。如,注重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开始意识到制定法的优点,正有意识地制定各种法律;而注重制定法的大陆法系也觉察到判例法对于法律统一的作用,以我国为例最高法院就屡次颁布指导性案例。“法律趋同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法律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也是各国适应国际化和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13]相应地,中西法治话语体系也呈现出融合的趋向。
三、构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措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推进需要以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自觉构建为基础,同时也要求在树立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自信后使之自立、自强。以此为前提,有必要主动推进法治体系建设、深入挖掘传统法学理论、仔细推敲司法实践案例、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法治特色。这是也构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必由路径。
(一)主动推进法治体系建设,催促中国法治话语体系自觉构建
“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同一程度超过人们的任何想像。”[14]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这一理念的落实必须通过中国法治语言,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主动与及时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催促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自觉构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已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等五个体系。在基本目标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后一步工作当然是努力让这美好的愿景尽快实现。
(二)深入挖掘传统法学理论,树立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自信
“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西方话语对中国法学渐有从‘影响’转变为‘宰制’之虞。”[15]法学家们对西方法治的全盘介绍无可厚非,然而发展至“言必称希腊”就有点过于极端。诚然,中国古代的“法治”与现代“法治”含义并不全然相同,但我国传统法学理论蕴含了丰富的现代“法治”理念。这无疑为树立起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自信提供了条件。
首先,作为第一批引入西方法治话语体系的大思想家梁启超,其从晚清时期起就率先探究我国法家思想,其从法家的经典著作中研读出了“法治”精神,并将管子认定为世界上解析“法治主义”的先行者。另外,其著有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管子传》、《先秦政治思想史》等大作,对于后世学者研究法家“法治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程燎原教授赞誉称“就法家‘法治’思想的研究而言《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乃首出的大著,《管子传》为精妙的续作,《先秦政治思想史》则是繁茁的终篇。”[16]而继梁启超之后,又涌现了汤学智、麦孟华等一大批以西方法治话语体系为标杆阐释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学者。其次,道家、儒家、墨家等思想派别也反映出或多或少的当代法治思想。如墨家主张在刑法上“赏当贤,罚当暴,不杀无辜,不失有罪”的思想就是当代刑法上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再次,从《中外法学名著指要》一书收录的作品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著作在法治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不乏深邃的法治思想,我们应有法治自信。当我们引用西方法治话语体系时应该斟酌中国古代是否也应有此类似的精神,进而以此构建我国法治话语体系。
当然,判辨古代传统法治精神的最终目的是将其改正后为当代法治建设服务。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我们要建设现代的政治,一面要采用法家根本精神,一面对于他的方法条理加以修正才好。”[17]
(三)仔细推敲司法实践案例,培养自立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
按照伯克利学派将法分为“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回应型法”的三个阶段的观点可知,我国正处在“回应型法”阶段。这就要求我国法治能更加关注社会生活,探求更加适合中国实践的法治建设,这也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目标的外部环境。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虽然也可对比研究西方法治进而取长补短,但主要还需立足于中国本土与中国当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独立性的要求。而为更好地发挥中国法治话语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也必然培养其自立特征。
司法实践案例浓缩反映了一国法治的本质,法治理论也只有落实到本国司法实践案例中才具有意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以中国司法实践案例为指导,另外也只有将法治建设至于中国本土司法实践案例中进行检验才能保证其不偏颇。然而熊谋林老师在《三十年中国法学研究方法回顾——基于中外顶级法学期刊引证文献的统计比较(2001—2011)》一文中经过统计得出对于司法实践案例的研究现状是“中国学者不仅对司法案例关心不够,在此前提下还更加偏向于研究外国的案例”。这一实证研究与“法学研究脱离实践的抱怨声在法律实务界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18]的控诉如出一辙。中国司法案例的研究在法治建设中并不受重视的现状提醒我们,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仔细推敲每一个司法实践案例。一方面,从中国司法实践案例中总结法治理论的缺漏进而明确法治建设的完善方向;另一方面,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案例的研究察觉法治理论的异化方面,进而找准法治建设的途径。当然,在建立独具特色的中国法治体系的同时,自然也就培育了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自立性。
(四)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法治特色,塑造自强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区别,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法也有很大差异。张文显教授在《我的学术研究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进程同步》访谈一文中就曾以“新型”为界,将资本主义法与社会主义法进行区分——“资本主义法是权利本位法,社会主义法是新型的权利本位法”。汪习根教授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一文从法学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政党与法治的关系、国家权力的分配运行与监督机制、对人权的保障等四方面论述了资本主义法治与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不同。在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量级代表,其法治的繁荣昌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意义非凡。因而,注重研究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构建自强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对于世界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
此外,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法治特色在另一层面上也意味着注重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虽然同属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我国的法治与苏联以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也不尽相同。如我国治理体系的一整套制度就由“以中国共产党党章为统领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统领的党和国家的政策制度体系、以宪法为统领的法律体系及由法律体系构建起来的法律制度体系”[19]三个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我国还根据具体情形创建了独具特色的制度,如“一国两制”制度。这是我国成功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具体实践,并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实行社会主义法治,香港实行以英美法系为主的资本主义法治,澳门实行以大陆法系为主的资本主义法治,这是我国当今法治的特殊格局。当然,这一法治格局也面临着不少挑战。面对这一法治制度创举,应循序渐进地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目标。不仅如此,塑造一套自强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从而通过话语的掌握进而达到权力的把控,使得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顺利进行,这一工作也极为必要。
[1]李龙.论当代中国法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J].法律科学,2012,(3).
[2]戴维·克里斯特尔等.现代语言学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11.
[3]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59.
[4]张文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纲领——对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认知与解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1).
[5]李君如.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全面保障人权[J].人权,2015,(1).
[6]刘思达.中国法律的形状[J].中外法学,2014(4).
[7]谭世贵,李建波.论司法和谐及其实现[J].时代法学,2007,(4).
[8]顾培东.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J].法学研究,2012,(3).
[9](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人学出版社,2004.419.
[10]张文显等.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80—81.
[11]陈金钊.法治遭遇“中国”的变异及其修复[J].扬州大学学报,2013,(1).
[12]吴华钦.从信访的三次高峰看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J].法学评论,2015,(2).
[13]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与前沿[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47.
[14](德)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2.
[15]支振锋.西方话语与中国法理—法学研究中的鬼话、童话与神话[J].法律科学,2013,(6).
[16]程燎原.洋货”观照下的“故物”——中国近代论评法家‘法治”思想的路向与歧见[J].现代法学,2011,(3).
[17]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12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8]周少华.法学研究方法:书斋里的法学[M].北京: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3).
[19]张文显.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5).
Reaching on Redesigning the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of Law
WUYu-jiao
(Law School,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Comprehend the attribute to the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of law,recognize its nature characteristic,it is help to properly interpret its connotation.Grasp the disadvantage of western discourse system of law,familiar with the advantages of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of law,and known as the trend of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egal discourse system,it is helpful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necessity of redesigning the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of law.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of law need to be consciousness,self-confidence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Based on this premise,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system construction,to dig the traditional legal theory,careful scrutiny of the judicial practice cases,pay attention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China;legal system;discourse system of law
D920.0
A
1009-6566(2016)06-0075-05
2016-10-23
吴玉姣(1991—),女,湖南娄底人,湘潭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