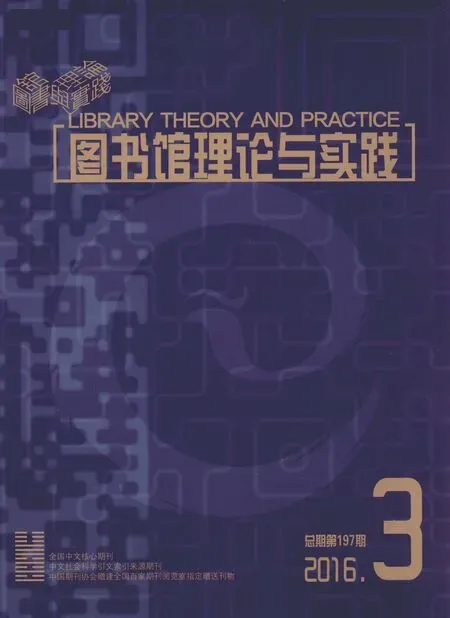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发微
2016-02-12云南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
阳 清(云南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发微
阳清(云南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
摘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是迄今为止研究《隋志》的最为详尽之作,书首“叙录”部分巧为佳构,可谓引导读者学习和考察《隋志》的最佳资料。姚氏《叙录》采用辑录体式,辅以按语来解释、说明以及评论,藉此表达撰者观点和见解,其中针对《隋志》种种学术疑案的处理,足以解惑发蒙,启迪后学。本文拟结合《考证》及其书尾“后序”,阐发《叙录》的微妙之处,为读者更好地利用《隋志》以及姚氏《考证》创造条件。
关键词: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
史志目录因为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往往深受学者重视。唐前史志目录,唯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两种存世。如果说,《汉志》是东汉前赋文献的集大成者;那么,《隋志》“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1]908其著录图书“最为宏富”,“自周秦六国、汉魏六朝迄于隋唐之际,上下千余年,网罗十几代,古人制作之遗,胥在乎是”,[2]其研究价值更为突出。有清以来,为《隋志》考补疏证者达十家之多,章学诚、章宗源、汪之昌、姚振宗、张鹏一、李正奋等学者都有著作传世,其中,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则是迄今为止研究《隋志》最为详尽之作。
姚振宗是清代享誉盛名的目录学家,撰有《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汉书艺文志拾补》《汉书艺文志条理》《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考证》等目录学著作七种。《清史稿·文苑》对他大加赞誉:“目录之学,卓然大宗。论者谓足绍二章之传”。[3]著名学者陈训慈亦认为其学问应在章学诚、章宗源之上,“虽不知名于当时,信足矜式于百世”。[4]姚氏有感于《隋志》“文略,非考证不明”,而近时“为目录考证者,往往以搜缉佚文为事,余皆不甚措意”,“不于一书之本末源流推寻端绪,徒沾沾于佚文之有无以究心焉”,故而试图“补苴章氏之残缺不完”,①书名《隋书经籍志考证》(以下简称《考证》),体例却与章氏同题著作有异。据新编序例,此书“凡撰人爵里、著书指归,但有可以考见之处,靡不条举而疏通证明之,务使一书源委大概可见,而佚文有无多寡之数,亦约略可稽”,可谓尽得古人所长,卓然自成一家。
姚振宗《考证》乃鸿篇巨制,全书凡五十二卷。最值得称道的是,该书“方之集注,实事求是;譬彼叙录,具体而微”,其学术内涵极为深厚。为了彰显其学术内涵,书首“叙录”部分巧为佳构,洋洋洒洒万余言,内容上包蕴万端,次序上有条不紊,是引导读者学习和考察《隋志》的最佳资料。本文拟阐释和发明书首《叙录》,为后学更好地利用《隋志》以及姚氏《考证》创造条件。
从结构看,姚氏《叙录》前后包括叙四部源流、叙本志撰人、叙本志体制、叙诸家评论、叙章氏《考证》等五项内容,另附新编序例以及又记,总体上与原书《后序》前后呼应,相得益彰,符合古代目录学著作的一贯思路,藉此让《隋志》的学术内涵得以展露无遗。考其体例,姚氏《考证》采用了历代目录学著作中较为常见的辑录体式,亦即针对某种文献,首先辑录他人评论或相关资料,并且保持所辑资料的客观性,继而辅以按语形式来表明撰者的观点和见解。此书《叙录》亦然,其中“叙四部源流”辑录资料八则,按语四则;“叙本志撰人”辑录资料六则,按语二则;“叙本志体制”辑录资料七则,按语八则;“叙诸家评论”辑录资料三十四则,按语二十三则;“叙章氏《考证》”辑录资料五则,按语二则;总计辑录资料六十则,按语三十九则。辑录与按语交互成文,浑然一体,不仅博采众长,集辑而述,而且持论公允,自出机杼,于条纹缕析之中见其学识和修为。最为典型的例证是,《序录》“叙四部源流”先是征引晋王隐《晋书》、梁阮孝绪《七录叙目》以及《隋志总序》,梳理从郑默《中经》到荀勗《新簿》的目录学传承,继而以按语说明四部之体发端于郑氏,而论定于荀氏;接着征引齐臧荣绪《晋书》、梁阮孝绪《七录叙目》及其所附《古今书最》《隋志总序》等,梳理从荀勗《新簿》到李充《晋元帝书目》的目录学轨迹,继而用按语解释李氏以经史子集提纲,已更正荀氏四部乙丙之序;接着征引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指出目录学中的“七分法”始于刘歆《七略》,“四分法”则始于荀勗《新簿》,继而以按语肯定此说;接着征引清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指出“四分法”真正定型于李氏《书目》,隋唐以来史志大率使用李充部署,继而以按语评论:“晁《志》言四部本末固善矣,而钱氏发前人所未发,尤为精覈。”这里,借助八则资料,辅以按语四则,姚氏非常清晰地梳理了唐前四部源流的真实情况。更有甚者,《叙录》在辑录相关资料之际,还针对不常见者标明出处,让研究者有迹可循,实为难能可贵。
辑录体目录学著作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这种著述较为常见的弊病,表现为使用前人材料贪多务得,以致游离于主题之外,由此结构松散,内容空洞,章法紊乱如丝;抑或又因为受前人牵制、时代束缚以及个人学力不足等,相关按语流于主观臆断,难以真正地解决学术问题。姚氏《叙录》在辑录相关资料之际,不滥用前贤研究成果,亦不妄加揣测和品评,其繁简自然,顺势而行,一切依据现存或者古人遗留至今的学术问题来展开研究,旨在为读者更好地认识和考察《隋志》提供便利。因此,《叙录》“叙本志撰人”、“叙本志体制”、“叙章氏《考证》”与“叙四部源流”比重相当,其“叙诸家评论”则内容三倍于前者。在目录学视野中提要钩玄之际,姚氏《叙录》一方面展示出自己的心得体会,试图提出并解决有关《隋志》的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则直面某种具体问题,或阐发、或补苴、或存疑甚而干脆流于失考,其中针对《隋志》学术疑案的处理,诚足以解惑发蒙,启迪后学。
第一,关于《隋志》的撰者。姚氏《叙录》“叙本志撰人”旨在探讨这一比较棘手的学术问题。通过考察唐李延寿《南北史叙传》及《上南北史表》、后晋刘昫《旧唐书·令狐德棻附传》、唐刘知几《史通·正史篇》、宋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文献资料,可见《隋志》撰者涉及褚遂良、李延寿、敬播、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令狐德棻、颜师古、孔颖达、赵志弘、魏征、长孙无忌等十二位,几令读者无所适从。姚氏《叙录》在分析上述资料的基础上,认为“大抵是志初修于李延寿、敬播,有网罗汇聚之功;删订于魏郑公,有披荆剪棘之实。撰人可考见者,凡三人,旧本题魏征等撰,征实可信也”。这一结论主要依据《南北史叙传》《上南北史表》《四库提要》等,至于其他九人为何被排除在《隋志》撰者之外,姚氏按语并未详言。真实的情况是,《隋志》撰者牵涉到领修者、分题者、初修者、删订者、上进者等多类责任人以及诸多相关环节,而本志究竟由何人执笔、个中细节如何,仍然值得学者进一步讨论。
第二,关于《隋志》的图书分类。姚氏《叙录》“叙本志体制”主要探讨这一学术问题。通过检读《隋志》总序、四部分序、道佛篇序等,人们已略知该志著录文献的部、类以及卷数。《叙录》主要使用按语,抑又结合《唐六典》,以说明《隋志》四部五十五小类与大小序四十八篇的分布情况,并具体解释各部小类的称名及其文化内涵。《叙录》还附及道藏、佛藏的小类称名,同时指明其与隋代道、佛专科目录的时代关联。更为重要的是,《叙录》征引《旧唐书经籍志序》,指出毋煚《群书四录》、《隋志》小序皆取法于《汉志》旧例,《群书四录》分类则依据《隋志》,又补充认为《隋志》分类多用《七录》旧例,其事类著之于《六典》,成为当代法程,遂而影响及毋煚《群书四录》,由此从体制角度出发,一方面阐明《汉志》对《隋志》《群书四录》的深远意义,另一方面梳理从《七录》到《隋志》乃至《六典》《群书四录》的目录学线索,充分展示出了其学术张力。与此相关,姚氏《叙录》“叙诸家评论”亦曾从不同角度去评价《隋志》的分类,下文拟将论及。
第三,关于《隋志》的文献归类。文献归类实与图书分类休戚相关。毕竟,文献归类亦即图书分类的间接体现。图书分类则是文献归类的前提条件,图书分类有失妥当,必然会影响到某些文献无所措置。结合图书分类,姚氏《叙录》“叙诸家评论”多次涉及文献归类这一学术问题。历代学者对《隋志》的文献归类褒贬不一。持赞赏态度者,譬如郑樵《通志·校雠略》认为,《隋志》著录“丧服”一类,乃《仪礼》中析出文献,因其终成一家之书,故于《仪礼》后自成一类,如此“可以见先后之次,可以见因革之宜,而无所紊滥”。[5]835郑氏又以“春秋三传”与《国语》的先后次序为例,认为“《隋志》每于一书而有数种,学者虽不标别,然亦有次第”,“可以次求类”。[5]835无独有偶,《四库提要》亦认为:《隋志》“凡于全经之内专说一篇者”,“皆与说全经者通叙先后,俾条贯易明”。[6]732上述二家,肯定《隋志》在经部礼类、春秋类的文献分类以及归置上恰如其分,实即赞赏《隋志》善于处理析出文献与母体文献之间的关系。姚氏赞成此说,同时指出这种优点根源于《汉志》,取法于《七录》。持批评态度者,譬如刘知几《史通·因习篇》指出,《隋志》“霸史”类止取东晋一世十六家,可谓义例未安。郑樵《通志·校雠略》指出,“《隋志》所类,无不当理,然亦有错收者”,譬如“谥法三部已见经解类矣,而《汝南君谥议》又见仪注”。[5]834宋高似孙《子略》认为《隋志》流于淆杂,乏诠汇之工。明焦竑《隋经籍志纠繆》亦指出《隋志》中不少文献的归类出现了失误。抑又,《四库提要》认为,《隋志》“实录”类列诸杂史,义类未妥。《四库提要》还指出,《隋志》归类失误,表现为“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6]981上述种种批评,往往结合例证来说明问题。姚氏《叙录》一方面根据例证逐一核实,或肯定之,或辩驳之,或评判之,另一方面则检读《隋志》全文,或查核是否存在着例外的情况,或补充其他有效的例证。譬如针对《史通》所言,姚氏《叙录》经过查核,认为《隋志》“霸史”类实不止东晋十六家之书,故而刘知几所言欠妥。又如针对郑樵之论,姚氏《叙录》指出《隋志》并无经解一类,而《通志》举例《汝南君谥议》亦误,今检读本志“仪注”类,其著录乃《汝南君讳议》,当是《魏晋谥议》之误。又如焦竑《隋经籍志纠繆》使用例证亦多失误,姚氏不仅逐一辩驳,而且征引章学诚《校雠通义》,批驳其“不知古人类例”,“大抵以《通志·艺文略》为不传之秘,皆虚浮无当”。更为难得的是,通过研究,姚氏还认为《隋志》杂传、地理二类编次无法,实因拘泥于二家之书,足见其考据之严谨。要之,紧密结合图书分类,姚氏《叙录》对于《隋志》的文献归类问题进行探讨,客观上拓展了学术空间。
第四,关于《隋志》的文献重出。文献重出实与图书分类、文献归类以及析出文献直接关联,姚氏《叙录》“叙诸家评论”亦有论及,其形式多样,原因复杂,不一而足。郑樵《通志·校雠略》指出,《隋志》“缘分类不考,故亦有重复者”,其中同一种文献于两类之中重出,“实由分类不明,是致差互”;同一种文献于一类之中重出,则是“不校勘之过也”。[5]834无独有偶,钱大昕《隋书考异》亦强调,《隋志》中有一书而重出者,亦即一书同时出现于两类之中,也有一书两收于同类者,后者乃史臣粗疏之失。姚氏《叙录》认为《隋志》的重出文献甚多,而前述郑氏、钱氏所列,尚有遗漏。此外,该志附注“梁有亡书,往往见于他类著录,亡而不亡”,不失为另一种文献重出。姚氏按语又征引宋傅崧卿《夏小正戴氏传》序,指出:“隋悬重赏,以求逸书,进书者多离析篇目,以邀赏帛”,《隋志》中有某篇从某书析出而著录者,有某书分为二三部书著录抑且卷数各异者,有某书与原序分别著录者,甚至有某书别出为另一部书著录者等等,“若此者,虽或由本志从诸家书目节节抄入,亦未始非当时离析篇目之所致”。这里,针对《隋志》文献重出现象的可能性分析,足以开导蒙昧,发人深省。笔者以为,关于文献重出问题的原因探讨,除上述学者所论,还可能归诸于《隋志》的撰者及其不同分工。《隋志》著录工作非一人、一时、一地所能完成,这或许是造成文献重出的原因之一,至于某书出现于两类之中,还可能缘于该书确实难以分类,故而分属两类皆可。至此,关于《隋志》文献重出问题的探讨,不失为一种极具创新性的学术话题,值得后学进一步思索。
第五,关于《隋志》的文献遗漏。清人钱大昕《隋书考异》指出,《隋志》漏收文献较多,某些唐前实际存在的文献,本志既不载录,抑且不在亡书之数。钱氏通过考察部分古注和正史,得见《隋志》经部遗漏若干典籍,通过系统考察正史列传,得见《隋志》史部、子部、集部同样遗漏了不少典籍。钱氏《十驾斋养新录》又认为,《隋志》之所以遗漏了部分经籍,或因王、阮并未著录。要之,《隋志》著录文献难辞挂漏之咎。姚氏《叙录》认为《考异》在列举例证方面偶有失误,而“本志所录据隋人见存书目,非一一见其书而著之也”,故以漏收。《叙录》还研究得出,《隋志》所谓见存者,或据隋人见存官私书目,或据唐初人见存书目;《隋志》收录唐初近时人著述,或亦见隋人书目,或由史官别自采入;考之南北五史,钱氏所列《隋志》四部的遗漏文献,尚可补充其它例证。针对《养新录》所言,姚氏《叙录》依据《唐志》《宋志》以及《玉海·艺文》展开考察,发现《隋志》遗漏经籍著闻者尤多,至于其它小录、短书遗漏者,更是难以统计;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献并非梁、隋书目所遗,足见该志草率了事。要之,姚氏《叙录》关于《隋志》文献遗漏问题的思考和探究,同样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
第六,关于《隋志》的文献附注。结合其分类体系,姚氏《叙录》“叙诸家评论”同样涉及这一学术问题。郑樵《通志·校雠略》指出:“《隋志》于他类,只注人姓名,不注义说,可以睹类而知义也。如史家一类,正史、编年各随朝代。易明,不言自显。至于杂史,容有错杂其间,故为之注释,其易知者则否。惟霸史一类,纷纷如也,故一一具注,盖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槩之论。”[5]835又曰:“古之编书以人类书,何尝以书类人哉?人则于书之下注姓名耳。《唐志》一例削注,一例大书,遂以书类人”,“以人寘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若用《隋志》例,以其人之姓名著注于其下,无有不安之理”。[5]835这里赞扬《隋志》附注繁简各异,有当注义说者,有不当注义说者,有一一具注者;而与《新唐志》相比,《隋志》附注以人类书,其取舍之间伦贯有序,尽显章法。姚氏《叙录》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叙录》接着征引《四库提要》,肯定《汉志》“本刘歆《七略》而作,班固已有自注”,《隋志》则“参考《七录》,互注存佚,亦沿其例”,后有“《唐书》于作者姓名不见纪传者,尚间有注文,以资考核”,由此彰显出史志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抑又,清钱大昕《隋书考异》认为,《隋志》附注所云梁者,乃阮孝绪《七录》著录文献。姚氏对此不以为然,《叙录》辅以按语指出:“《志》中所注称梁武帝、简文帝、梁元帝之谥,必非《七录》本文,自是后人追改。他如朱异、萧子显、陶弘景、何胤、刘敲、刘潜诸家,皆并时之人,或卒于阮氏之后,而《志》皆附载其书,亦曰‘梁有’。以《七录序目》纵横家验之,知其采宋、齐、梁、陈四代书目,而亦注‘梁有’。以《五代史志》讬始于梁也,不尽是《七录》也”,又自注云:“春秋三传类中尚存有‘宋有’一条”,“大抵宋、齐书目所有者,梁代诸家书目无不有之,故概以‘梁有’括之也”。如此辩驳,证据确凿,擘肌分理,既令人信服,亦引人入胜。
第七,关于《隋志》的综合评价。前述已部分论及历代学者对《隋志》的褒贬,这里仅从宏观上讨论。唐人对《隋志》持苛刻态度者,莫过于史学家刘知几。《史通·书志》云:“近世有著《隋书》者,乃广包众作,勒成一志,骋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车而重轨,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其理有不安,多从沿革”,“详求厥义,未见其可”,“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7]清人朱彝尊对此不以为然,其《经义考·著录篇》充分肯定《隋志》具有不可否认的目录学价值,至于《史通》谤讪之,实乃见解褊狭。《四库提要》同样强调:“子元之意,惟以褒贬为宗,余事皆视为枝赘。故《表历》《书志》两篇,于班、马以来之旧例,一一排斥,多欲删除,尤乖古法。”[6]751姚氏《叙录》赞同清儒所言,他认为“刘氏于《艺文》一体,未尝详究其体用,故其言如此”。相比之下,四库馆臣对《隋志》的总体评价较为公允。《四库提要》指出,该志虽“编次无法,述经学源流,每多舛误”,然“后汉以后之艺文,惟藉是以考见源流,辨别真伪,亦不以小疵为病”,[6]409可谓不刊之论。
第八,关于《隋志》的其他问题。譬如依据《隋书·牛弘传》,姚氏看到所谓经籍“年踰千载,数遭五厄”[1]1299之论,直接影响到《隋志》的总序,至于牛氏《开皇四年四部书目》,亦成为《隋志》蓝本之一。又如依据《四库提要》所言,《隋志》始有杂史之目,义取其兼包众体,宏括殊名;“杂史”类著作或专抄一史,或合抄众史,影响到后世相关文献。姚氏指出,《隋志》“杂史”类皆抄撮旧史之属,实即后世史抄之源。《四库提要》还认为,《隋志》“地理”类有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以总名者,不失为我国丛书之祖。《提要》还论及《隋志》霸史、楚辞、别集、佛、道等诸多部类文献及其相关学术问题。姚氏《叙录》均有征引和阐发,为后人研究《隋志》拓展了视野。
此外,《叙录》“叙章氏《考证》”主要讨论章宗源及其同题著作。据孙星衍《章宗源传》,章氏曾“辑录唐、宋以来亡佚古书盈数笈”,“其已辑各书,编次成帙,皆为之叙,通知作者体例曲折,词旨明畅”,“撰《隋书经籍志》及杂文若干卷”。[8]另据孙星衍《古史考序》,章氏“好辑佚书,欲依《隋书经籍志》目为之考证,所辑书满十余笈”,遗书后为“中书叶君继雯所得”,[9]波及孙氏者甚少。另据严可均《铁桥漫稿·书<北堂书钞>原本后》,章氏佚书辑本汇聚于孙星衍者甚多,因其最终未付剞劂,后多散佚。对此,姚振宗如此疏理:“章氏辑本后皆归于叶氏、孙氏。叶氏未见传刻,孙氏则有谯周《古史考》,在《平津馆丛书》”,“或谓历城马国翰玉函山房所刻经、史、子三部辑本皆章氏之书”,疑得之于叶氏,从章氏史部考证看,其辑佚文献特多,惜未见其它传本,集部或未尝措手,后有严氏集其大成。抑又,据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记载章宗源族裔章广文所言,章氏“著述甚富,殁后多零落,有《隋书经籍志考证》,最详核”,海昌钱警石已云“全书未见,若史部考证则有之”,此书“《隋志》所载今佚者,必详载体例及诸家评论”,“史部为《太平御览》目录所引隋以前书,凡《经籍志》未载者,悉取以补之”,又旁摭诸种类书、政书佚文,“隋以前乙部,殆无遗珠矣”。[10]姚氏继而指出,章宗源《考证》后由崇文书局刊入丛书,其书“先后次第,自起居注以下皆不从本志。篇中部居,亦复有所移易”,其书极意规仿王伯厚《汉志考证》,“其于著录之书,不求甚备,而篇叙之文反有所考;于撰人始末,不必甚悉,而传注类书所引诸佚文,则独致其详”,“本意因辑书而为是志,皆从辑本中约略录出”。通过辑录相关资料,辅以按语,姚氏《叙录》较为详细地考证了章氏同题著作的学术渊源、目录学特征、流传始末等,为读者更好地评价和使用清代《隋书》补志创造了有利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姚氏《考证》书尾附录《后序》,恰与书首《叙录》互为表里,相互补充。《后序》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谈本志缘起事理及四部纯驳之大略,二是谈新撰《考证》未尽之例之大略,三是谈新撰《考证》推寻事理得所藉手之大略。其中第一部分指出:《隋志》所谓“今据见存”相关书目不止一家;附注“梁有”亦不限《七录》一家;文献重出还可能缘于撰者但见书目,不见本书,因疑为别本,故不妨互见;诸如此类,同样给研究者以重要启发。此外,《后序》针对《隋志》的评论,诸如:“注文不与本文相维系,率意比附,于撰人时代每多离合失次,章法亦未能尽善,其于《七录》所载之书,亦多有删弃”,“统观大致,经、集两部为优,史、子两部瑕不掩瑜。大抵长篇累牍,记载繁富,夹杂于见存、《七录》者,皆未能范我驰驱,首尾一贯。类例不熟,故分隶不清,动为他家书目所束缚,而迁就依违,茫无把握”,等等,因其与书首《叙录》相关评论略显不同,由此恰到好处地补充论证,可谓客观而公允,同样是品评《隋志》不可多得的重要言论。
要之,姚振宗《考证》可谓《隋书》的最佳补志。姚氏《后序》第二部分曾自评该书:“多心得之言,为前人所未发,亦有驳前人旧说之未安者。一书之中,凡本事可考及命意所在者,靡不著于篇。其或疑信参半,亦姑过而存之。撰人始末,必求其详尽。取裁安处之间,几经审慎而始定;订正疑异之处,数易稿草而后成。力摒繁冗不切之言,务存简要核实之语。节引诸书甚多,情况不一,而佚文有无多寡之数,亦于此可见。唯恐不出于人,不得已而始谋诸己。大抵四部之中,可考见者十之八九,其不可知者,多无足重轻之书。此书不能详稽远揽,然弥缝阙失,积累饾饤,意则自信其不浮。篇中失考之处,每不能自已。”如此评述,实乃坦诚而公正。非但如此,书首《叙录》大量辑录了前人有关《隋志》研究的重要资料,抑又使用按语或解释、或说明、或评论相关学术问题,足以泽被后学,乃至成为学习和研究《隋志》的最佳导读,彰显出非凡的学术意义。
[参考文献]
[1](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M]//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5049.
[3](清)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398.
[4](清)陈训慈.山阴姚海槎先生小传[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3(2).
[5](宋)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7](唐)刘知几.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1-62.
[8](清)孙星衍.五松园文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21.
[9](清)章宗源.古史考[M].兰陵孙氏藏版《平津馆丛书》刻本。
[10](清)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3:52-53.
Subtlety of Sui Shu Zhi Reseach Description
Yang Qing
Abstract:Sui Shu Zhi Reseach, written by Yao Zhenzong, is the most detailed work among the research on Sui Zhi, and its description is well-structured and comprehensive and is honored as the best material guiding the readers to study Sui Zhi. The description has fully expressed the author's point of view with a compiling style and comments as explanation, notes and commentaries, which provides guidance and disabuse for other leaners in study. This article expounds on the subtlety of Sui Shu Zhi Research description to make a reference for other research.
Keywords:Yao Zhenzong;Sui Shu Zhi Reseach;Description
[收稿日期]2015-08-13[责任编辑]李海燕
[作者简介]阳清(1979-),男,湖南衡阳人,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文献。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唐宋类书小说文献学研究”(项目编号:2014Z039)的研究成果之一。①本文引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均参考中华书局1955年版《二十五史补编》排印本,后文不注。
中图分类号:G256.4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5-8214(2016)03-01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