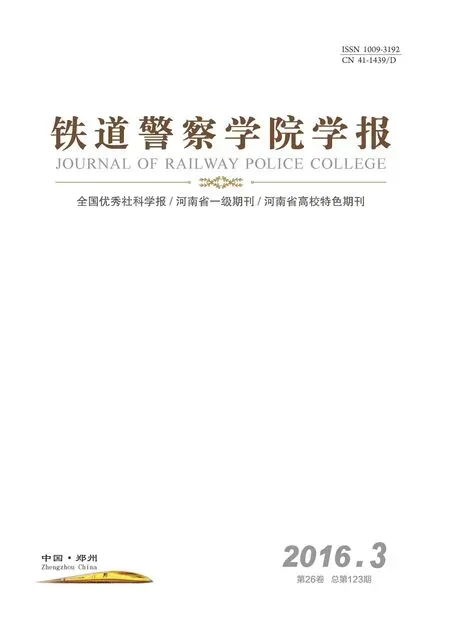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处置中警察权运行问题研究
2016-02-12李金锋周文峰
李金锋,周文峰
(重庆警察学院 治安系,重庆401331)
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处置中警察权运行问题研究
李金锋,周文峰
(重庆警察学院 治安系,重庆401331)
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具有不确定性、自发性、缺乏组织性等特点,容易诱发治安问题。为切实提升安保工作效能,公安机关必须面对并解决安保工作中警察权运行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完善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法规,明确警察权介入和人权保护衡量标准,加快推进治安治理步伐,以达到有效处置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的目的。
警察权;公安管理;群众聚集活动
一、警察权权属分析
“警察权是指国家依法授予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警察机关以及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职能所必需的各种权力,包括履行警察刑事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所运用的一切权力的总称,亦即警察职权”。在我国,警察权配置太广,十余种机构都拥有警察权。就目前而言,警察权系统通常包括以下四部分:一是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二是《人民警察法》规定的除公安机关之外的四大警种,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警察、监狱人民警察、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三是专门机关的人民警察,如:铁道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交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民航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林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海关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四是武装警察部队,如:内卫部队、黄金部队、水电部队、交通部队、森林部队、边防部队、消防部队、警卫部队。
警察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层面的警察权是指法律规定的所有合法主体所拥有的警察权,狭义层面的警察权仅仅指公安机关所拥有的警察权。
警察权具有六方面特征:法定性、强制性、单方面性、易扩张性、广泛性和不可处分性。法定性是指警察权的实施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不得超越警务职能和法律规范,法无授权皆禁止。强制性是指警察权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在实施过程中,权力作用对象有服从义务。单方面性是指警察权是单方面行为而非双方合意行为,其实施不需要征得相对人的同意,不以相对人的意愿为实施必要条件。易扩张性是指警察权如果不加制约,很容易延伸自身的权力边界。广泛性是指警察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相对于其他权力而言更为广泛。不可处分性是指非经法定程序,警察权不得被自由转让,警察机关不得自由放弃职权。
公安机关的权力是警察权的典型代表,狭义的警察权仅指公安机关的权力,本文所指向的警察权即是这种狭义层面的警察权。公安机关的权力同样具有上述六方面特征,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任何情况下行使警察权都应该遵循这六方面特征的要求,包括在大型群众性活动安保工作中。公安机关的警察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治安管理方面的权力、刑事诉讼方面的权力、武装方面的权力和紧急状态处置方面的权力。
二、警察权介入限度界定
若无违法犯罪,警察权存在的必要性将为零。现代法层面上的警察权是公民呼吁政府制造的结果,因此,警察权介入是外来的而非天生的,警察权的介入也必须有一定的限度。笔者认为,根据危害可能性,警察权的介入限度是逐步升高的,总体来讲,警察权的介入可以分为四个限度。
一是最低限度——警察权的闲置。警察权的闲置所针对的对象具有无明显危害潜在性,即不仅不具有明显的危害性,同时危害潜在性也不明显,如普通公民、人群聚集密度低的场所、危险性低的物品等。对于这些无明显危害潜在性的对象,警察权的介入性极低,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警察权被闲置了,但这不代表警察权在这个时空段消失了。根据公安两大客体可以相互转化的规律,在主客观条件影响下,公安第二客体也可能转化为第一客体,即合法公民会转变为违法犯罪人员。为有效预防违法犯罪的发生,警察权必然要通过一定形式证明其合法存在性,如安全知识讲座、警情通报、违法犯罪后果教育等。二是低级限度——警察权的显现。警察权的显现所针对的对象具有明显的危害潜在性,即虽不具有明显的危害性,但其危害潜在性已经可以被察觉或推测,如可能透露违法犯罪信息的重点人物、人群聚集的场所、极易滋生违法犯罪的行业、具有危险性的物品等。对于这些有明显危害潜在性的对象,公安机关必须使用警察权,防止其危害由潜在性变成显示性。三是中级限度——警察权的初级证明。警察权的初级证明是指从表面上来看,公安机关通过警察权的运行证明自己对维护社会秩序是有益的。警察权的初级证明所针对主要是明显的浅度危害行为——违法行为。将公安机关处置违法行为时使用警察权界定为初级证明,主要是因为相对于犯罪行为来讲,违法行为的危害性要低得多;另外,社会大众一般会将处置违法、侦查犯罪行为作为公安机关存在意义的“标签”,而且公众对公安机关处置违法行为的关注度要低于侦查犯罪行为。四是最高限度——警察权的自我实现。警察权的自我实现是指从表面上来看,公安机关通过警察权的运行证明自己的价值完全得以实现。警察权的自我实现所针对的主要是明显的深度危害行为——犯罪行为。将公安机关侦查犯罪行为时使用警察权界定为自我实现,主要因为犯罪是各国共同界定的公安机关打击的对象,犯罪的严重程度要高于违法行为。而且,相对于违法行为来讲,公众更加关注侦查犯罪行为,会直接将侦查犯罪的情况等同于公安机关价值的实现程度。
在明确警察权介入限度的情况下,在不同限度范围内,警察权的干预强度应有比例要求。对于初级限度,公安机关所行使的警察权干预强度不应超过劝说、教育等非执法类警察权;对于低级限度,公安机关所行使的警察权干预强度不应超过治安行政处置权、治安行政管理权、交通管制权、现场管制权等非核心警察权;对于中级限度,公安机关所行使的警察权干预强度不应超过治安案件调查权、治安行政处罚权、治安行政强制权、警械使用权等行政性核心警察权;对于最高限度,公安机关所行使的警察权干预强度不应超过立案权、侦查权、刑事执行权、武器使用权等刑事核心警察权。本文主要讨论的警察权属于第二限度,警察权的干预强度也应符合相对应的比例要求。
三、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中警察权介入的三种困境
大型群众聚集活动分为三类:一是组织型,即政府组织实施的大型聚集活动;二是申请型,即社会组织申请举行的大型聚集活动;三是自发型,即群众自发组织的聚集活动。在这三类群众大型聚集活动当中,组织型和申请型都有明确的举办者,举办者都会事先告知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可以先期进行预判并采取针对性警务措施,能够有效避免安全(案)事件的发生。但是,大型群众自发型聚集活动因具有自发性、不确定性、缺乏组织性等特点,极易诱发或促使安全(案)事件的发生。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的安保工作不仅考验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能力和水平,同时也考验警察权使用的合法性问题。目前,警察权在安保工作介入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困境。
(一)公安机关权力使用与权力依据的不对称性
权力的运行需要法律来制约,而制约权力的法律必须能够保证权力运行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尽可能简洁、有效,否则权力运行容易规避客观存在的法律。公安机关在处置大型群众自发性活动过程中必然要使用警察权,而所使用警察权的法律法规来源却比较分散且不明确,无形中给公安机关赋予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裁量权被行使时至少在形式上容易给人造成违法或滥用的主观印象。大型群众活动中警察权实施的主要依据是《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但是该条例仅对大型群众活动中安保管理主体、公安机关的安全许可职责、违法处罚等内容进行了较为笼统的规定,并未就安保工作的具体开展、公安机关警察权使用范围、其他参与主体的管理权限等内容进行规定。而且公安部和国务院法制办在关于大型群众性活动的释义中明确规定,群众自发性活动不适用《大型群体性活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5条对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者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8条对扰乱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违法行为进行了规定。研读上述条款可知,该规定只适用于大型群众性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不包括大型群众自发性活动的情形”[1]。其实,上述规定只是明确了大型群众自发性活动中若出现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可以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处罚,也就是为公安机关处置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关键问题在于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安保工作并不只是考验公安机关处置违法犯罪问题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违法犯罪行为发生之前,公安机关维护现场秩序所使用的警察权的合法性来源问题。《人民警察法》第15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为预防和制止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可以在一定的区域和时间,限制人员、车辆的通行或者停留,必要时可以实行交通管制”。但是,公安机关在处置大型群众自发性活动中所使用的警察权并不单单是交通管制权。《人民警察法》第17条规定公安机关“经上级公安机关和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突发事件,可以根据情况实行现场管制”。不过,大型群众自发性活动不能界定为实质意义上的突发事件,而且,根据该条规定,如果大型群众自发性活动没有演变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突发事件,公安机关就不能使用现场管制权,而实际生活中,公安机关在大型群众自发性活动中一般都会使用现场管制权。根据法无授权皆禁止的原则,如果没有法律依据而使用警察权,或者说没有达到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条件便使用警察权,就是违法行为或者说是权力滥用行为。如果被处置的公民提出了相关行政诉讼,则公安机关将面临法律上的不利局面。
(二)警察权介入与公民权保护的冲突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当中,违法犯罪是先于警察权而产生。当原始的警察权产生后,权力主体掌握在社会大众手中,所实行的警务形式是自发性警务,无所谓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冲突问题。但当社会自身无法有效预控犯罪,以及国家认识到违法犯罪也在某种程度上危害到国家安全的时候,警察权就潜移默化地转移到国家政权手中,此时社会上就形成了三个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系统:社会系统、违法犯罪系统和警察系统。而警察系统一旦独立形成,就自然拥有了自身的独立利益,因为警察权天生具有易扩张性。警察权的使用目的虽在于保护公民权这一终极利益,但也含有显示自我存在、保护自身利益的某种成分。无论如何,从一定意义上来看,警察权与公民权是成反比关系,即警察权越大,公民权越小。这一定律同样适用于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中警察权的运行。在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中,公安机关主动使用警察权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出现违法犯罪、治安事故、群体性事件等治安问题,但公安机关的行为必然干预了法律没有禁止的公民合法权利,公安机关使用的警察权的强制性越严重,侵犯公民权的力度也就越大。如果公安机关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最大程度地抹杀公民自发性聚集的合法权利,则此时的警察权无疑严重违背了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最初目的,因此要时刻警惕警察权无视约束而向各类行政权蔓延扩大的可怕后果。但如果公安机关为了保护公民自发性聚集的合法权益而闲置或者吝惜警察权的使用,一旦发生诸如上海外滩踩踏的事件,导致群众伤亡发生,又怎么能说是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呢?因此,如何在警察权的运行与公民权的保护之间保持理性平衡,是公安机关在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中行使警察权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三)社会参与主体权力配置的法律规制缺位
大型活动安保工作其实就是治安工作社会治理的过程。违法犯罪来源于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部门当中,公安机关只是社会主体之一,公安机关不能从源头上完全预防违法犯罪,公安机关的预防功能具有有限性。为有效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社会治安主体必须由狭义向广义转变,即由公安机关单一维护型向社会主体参与维护型转变,公安机关必须协同社会力量来共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社会治安主体的转变,凸显了治安治理在治安工作中的应用。治安治理是社会治理中的一种。参考治理的含义以及治理的突出特点,结合治安工作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治安治理是指公安机关协同非政府力量,采取合作、协商、合作等手段,共同解决治安问题,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治安治理有五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多元治理主体包含公安机关,二是多种治理措施中包含强制性手段,三是治理的对象主要是治安现象中的治安问题,四是提供的产品性质是公共服务,五是治理的目标是维护治安秩序。作为警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安保工作同样具有这五个方面特征,其中之一便是参与安保执勤的主体具有同样性,包括公安机关、警校学生、保安、政府各部门等。公安机关处置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符合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而警校学生等社会主体只拥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防御性权力,并无法律层面上的执法权。社会主体参与处置,无非基于地方党委和行政机构的行政命令,并无法律法规规定或明确的委托要求,处置过程中所使用的相关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有待商榷。
四、安保工作中警察权规范化运行路径选择
(一)完善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法规
虽然目前下位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不够完善,公安机关还可以根据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相关规定开展安保工作,但毕竟公安机关开展安保工作的主要依据是《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而且相关上位法规定比较零散、不成系统。因此,从短期发展阶段而言,应尽快完善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法规。一是要从国家层面完善《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将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纳入管理范畴,同时就安保工作具体开展中公安机关警察权的使用范围、种类和性质进行明确。二是在《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尚未完善时,地方政府可以就如何细化落实条例进行规定,如重庆市政府制定了《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就安保工作中公安机关的权力运行进行了细化,为处置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法规依据,在全国属于首创。三是针对社会主体参与安保工作,应通过下发文件等形式进行委托授权,对于社会主体参与权大小、参与的深度与形式等内容进行明确规定。
(二)明确警察权介入和人权保护权益衡量标准
笔者认为,从法理层面考虑,在平衡警察权介入和公民权保护冲突方面,最为重要的是要确定一个衡量标准。而要制定该衡量标准,就必须从公安工作的价值目标上着手,因为价值目标是一切公安工作的最终指向。大体来讲,公安工作的价值目标有七个部分:公正、秩序、效率、和谐、稳定、安全、人权。传统的警察权在价值目标考量上,秩序的价值顺序要优先于人权。现代意义上的警察权在价值目标考量上,人权价值目标的重要性越发突出。在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安保工作中,公安机关处置工作所体现的价值目标主要也是秩序和人权两个方面。那么,二者之中哪一个的价值顺序优先?笔者认为,秩序价值目标应该优先于人权,但衡量标准应该界定为秩序优先、兼顾人权。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当前法治化发展水平尤其是公安法治化发展水平仍然带有浓厚的秩序色彩,这在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安保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得以体现。二是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安保工作不同于单个的违法处置和犯罪侦查活动,因为违法处置和犯罪侦查活动的对象都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明确性,而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安保工作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无法进行可量化的人权保护,而且理论上的人权保护纯应然性无法带来现实可操作性。三是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安保工作属于警察权介入的第二限度,公安机关不能超限度使用警察权,应在保持底线不被突破的基础上,尽量保护公民参与自发性聚集活动的合法权益。那么,在明确衡量标准的前提下,最关键的是社会治安秩序包括的范围很广,公安机关的现有力量不可能确保在大型群众自发性处置活动中不发生任何危害治安秩序的行为,所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之底线应该被量化、被界定。笔者认为,基于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的特点,在开展处置工作过程中,公安机关只要能确保不发生特定性的危害多数人生命健康安全的事件或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就基本达到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底线目标,而盗窃、诽谤等任何时空都可能发生的普遍性的危害治安秩序行为不应该被界定为该种情况下的底线目标。
(三)加快推进社会主体治理能力建设
从长期来看,面对有限的警力和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为确保有效预防和精确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由社会主体参与或承担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安保工作等非核心警务工作是必由之路,也就是说,走治安治理模式是未来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安保工作的必然趋势。治安治理模式的核心在于公安机关将权力分流给社会参与主体,其意图是使社会参与主体能够发挥比政府更有效的治理作用,最终目的是达到善治。这种分流必须满足一个前提,即社会参与主体有能力承担安保工作,换句话说,社会参与主体必须适格。其实,若全由社会主体来承担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的安保工作,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确保社会主体具备符合目标需求的治理能力;第二步是通过修改法律法规,将安保工作涉及的相关警察权有限度地转移给社会主体。其中,第一步完成是第二步开展的前提,如果社会参与主体本身无法承担治理的重任,那么政府将治理责任和权力移交给它们,等于是要被治理对象承担治理失败、利益受损的风险,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做法。因此,有部分学者建议当前可将大型活动安保工作交由保安公司来负责实施。但是,由于受保安公司管理水平不一、地方行政力量干预、法律规范的制约等诸多因素影响[2],保安公司的治理能力有限,并未达到适格要求,由保安公司来负责大型活动安保工作的提法过于超前,不符合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或者说,在现阶段不具有可操作性。但是,既然已经存在政府市场“双失灵”的问题,社会就必须介入到治理中,这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发展趋势。因此,对于大型群众性自发聚集活动治安治理工作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培育社会参与主体治理能力,积极推动法律规范的修缮以赋予社会主体治理权力。只有社会参与主体具备适格的权责能力,安保工作才能真正由公安机关转移到社会主体手中,这或许不仅仅是大型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安保工作需要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治安治理、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都应该关注的问题。
[1]周文峰.大型群众自发性活动安全管理问题与对策[J].公安研究,2015(4):73-76.
[2]胡永正.当前保安服务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J].公安学刊,2006(2):41-42.
责任编辑:时娜
The Operation of Police Power in Handling Large Unmeditated Aggregations of Mass
Li Jinfeng&Zhou Wenfeng
(Chongqing Police College,Chongqing 401331,China)
Largeunmediatedaggregationsofmassareuncertain,unmediatedandbeinglackof organization,thus they are likely to cause public disorder.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ecurity work,police agencies must face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police power.The effect disposal of large mass aggregations can be gained through improving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bout the security of aggregations,clarifying the standard for the intervention of police power and human protection,and accelerating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order.
police power;police management;mass aggregation
D631
A
1009-3192(2016)03-0056-05
2016-03-09
李金锋,男,安徽阜阳人,重庆警察学院治安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安学基础理论;周文峰,男,云南潞西人,重庆警察学院副调研员,国家一级安全防范设计评估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安全。
本文为重庆市决策咨询与管理创新计划项目“大型聚集活动风险评估机制研究”(cstc2015jccxA00002)、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型群众自发聚集活动安全管理研究”(15SKG211)、重庆市公安局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大型聚集活动风险评估与安全管理研究”(R2015-1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