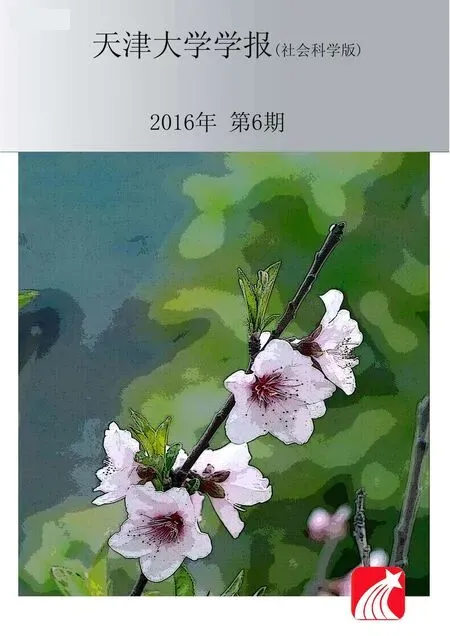电影叙述者的非人称性问题
2016-02-10黄灿
黄 灿
(1.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2.长沙学院中文与影视传播系, 长沙 410022)
电影叙述者的非人称性问题
黄 灿1,2
(1.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2.长沙学院中文与影视传播系, 长沙 410022)
与小说不同,电影叙述者的身份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叙述者的身份与叙述方式密切相连,电影讲述与展示相融合的表现方式使电影无需小说中单一的、人格化的叙述者作为中介,因而电影叙述者呈现出非人称性特征。因为电影创作和表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电影叙述是由一个复合的机制完成的,这一机制代替了人格化的叙述者身份。
电影叙述者; 非人称性; 叙述机制
叙述者是伴随着小说的兴起而诞生并成熟的概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论何种小说叙事,都是通过语言这一中介“想象性”地呈现的。作者将虚构的作品形诸于文字,通过这一中介,读者虚构性地还原作品。这一模式(虚构——中介——虚构)的非直接性使叙述者成为小说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这一概念,作者和读者的虚构得以在热奈特所言“语式”(即讲述故事的方式)的层面互相靠近。尽管无法完全复现,但读者通过叙述者,得以发现在这种间接性的虚构讲述中,世界是如何展开的,人物是如何行动和感知的。与戏剧、电影这些更具直观性的艺术相比,小说是不能直接呈现的。这一特性为许多叙述工具和功能的衍生带来了生长的空间。特别是,在一种科学主义的思潮下,人们希望对小说进行更具科学性、更精确的分析和判断。于是,叙述者成为经典叙事学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并自然而然地与小说绑定在一起。
然而随着叙事学的发展,人们对其他媒介下艺术形式的叙事性关注与日俱增。对于像戏剧、电影这样的传统媒介表演艺术而言,其叙事性是否存在?能否用经典叙事学进行分析?其叙述功能与小说叙述有何异同?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对于计算机游戏、超文本、博客等新媒介表现形式,其叙述如何突破传统的情节模式,叙述者对于其交互性的本质特色有何影响,也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注意。
一、讲述与展示:决定叙述者形态的前提
对于叙述者问题的探讨应该从不同媒介艺术的呈现方式开始。小说是一种讲述(telling)性的艺术,戏剧是一种展示(showing)性的艺术,而电影更复杂一些,是介于展示和讲述之间的艺术。展示与讲述是区别叙事艺术的重要标志,其划分的标准在于叙述事件的“在场”与“不在场”。当受众与叙述事件同处于一个时空,这是一种展示的艺术,而反之,叙述事件与观众处于不同的时空,需要通过虚构和想象建立某种在场的幻觉,则属于一种讲述的艺术。对于展示艺术而言,叙事聚焦是可见的、确定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演员、舞台、场景的安排与布置。而对于讲述艺术而言,便只能通过想象性的方式还原场景。在英加登看来,对应于现实存在的空间,文学作品中的空间是一种现实的“再现空间”,这一再现空间并不等同于现实存在的空间。
如果我们认识了再现客体的特殊本质——理解了它的内容——我们就会知道,它虽然是一种类型的现实客体,但它并没有“扎根”在现实世界中,它自己也没有处在一个现实的时空中,这就是说,它完全没有脱离意识主体行动对它的引导。[1]
这一没有脱离意识主体的再现空间,其聚焦方式不是直呈的,而是要经过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这一中介作用经由读者进行“解码”时,显然是人言人殊的。经典叙事学对于叙述者的研究,包括热奈特的叙述聚焦三分法和弗里德曼对叙述视点的八分法,都只能在文本“整体”层面告诉我们,故事是叙述者如何讲述的,讲述的视角怎样,叙述者视角与声音的关系如何。但这样的划分并不能让我们真正完全把握再现空间,很大一部分空白,需要我们用想象自行填补。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其他媒介叙事与小说叙事进行比较时,会发现他们是优劣互现的。戏剧、电影等艺术形式直观、鲜明 、聚焦相对简单。而小说叙事模糊、多义、聚焦复杂。与书写和舞台表演不同,电影是一种更复杂的叙事学对象,因为影片来源于书写和舞台的叙事潜力的组合。从讲述和展示的角度来看,电影是一种较之小说戏剧更具复合性的呈现方式。观众观看的是一种明确的视觉画面,但已经不是“纯粹”的现场表演,而是经过了拍摄、剪辑等一系列后期制作,呈现出明显的叙事性特征。安德烈·戈德罗(André Gaudreault)经过考证,确认到1902年,大多数影片是只有一个镜头的。1903年开始摄制多个镜头影片,1910年以后,电影艺术家才真正划分场面,根据蒙太奇进行拍摄。[2]单镜头电影更多依赖场面调度,而当多镜头电影产生,镜头与镜头开始互相组合时,一种电影的“叙事语法”开始产生,镜头作为叙事单位,使电影呈现出一种更接近小说叙事的特质。正是这种复合性的呈现特质,让电影的聚焦研究变得更加复杂和丰富。
叙事问题的理论支撑点是叙述者,因为在经典叙事学看来,任何叙述活动都是由叙述者完成的。但是在展示性活动的媒介叙事中,比如戏剧、电影或者电视,拟人化的叙述者形象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至少来自3个方面。一方面,小说中文本叙述者虽然大部分时候是隐身的,但可以让人感觉到存在,因为他行使着中介的功能。小说的读者可以感觉到小说是被一个文本叙述者讲述的。而在展示性艺术中,这一中介功能减弱或者消失了,那么这些艺术还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文本叙述者”呢?就像戏剧那样,台上的人物进行真实的、活灵活现的演出,如何说服观众,这背后有一个统一的“叙述者”存在吗?他是谁?他存在于何处? 他的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如何呈现?这些问题便显得急迫而难以解决起来。
一方面,在小说叙述中,人物叙述者叙述时,是可以控制叙述视角的。因为读者只能循着人物叙述者的叙述声音去想象和还原画面。余华的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开头用人物的话语牢牢控制画面。
我看到了自己,一个受惊的孩子睁大恐惧的眼睛,他的脸形在黑暗里模糊不清……紧随而来的另一个记忆,是几只白色的羊羔从河边青草上走过来。[3]
画面高度聚焦在人物的话语中,或者说,人物的话语实质上就是画面的提供者,这是小说叙事中常见的现象。这种统一(当然,也有例外)在展示性媒介艺术中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人物开口说话,但观众的聚焦不会因此而有太大的变化,因为舞台、人物、道具和背景都是实存的,不会因为人物的语言而产生任何变化。那么,人物开口说话,是否还具有聚焦功能?人物叙述者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这一问题,也必须加以考虑。
另一方面,由于画面的实存而非源于中介的想象,画外音这一叙述者与画面会产生多样的关系。如果说展示性艺术人物叙述者的存在方式让人存疑的话,那么画外音提供的就是一个明确的叙述者形象——有一个声音在确定无疑地“叙述”,但这一叙述行为仍然会与画面产生张力。也就是说,即便画外音提供了一个确定的叙述者,这一叙述者仍然与画面处于各自独立的状态。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画外音一直化身为成年马小军,并以一种第一人称回顾视角进行讲述。这一画外音在大部分时候都与画面贴合,但在一些关键性的情节中,画外音会对画面进行纠正。众人在老莫餐厅聚餐,马小军和刘忆苦因为争风吃醋打起来,马小军用碎酒瓶捅刘忆苦,却出现了对方安然无恙的非现实画面,这时候画外音停止了画面。
千万别相信这个,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勇敢过,这样壮烈过。我不断发誓要老老实实讲故事,可是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干扰就有多大。我悲哀地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记忆总是被我的情感改头换面,并随之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头脑混乱,真伪难辨。
显然,这种画外音叙述者的声音和画面同步呈现,又互相抵触的情形在小说中是很难出现的,在电影中却成为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段。其原因正是在于讲述性艺术中,画面是由语言中介提供的,而展示性艺术中画面却是确定性的。
二、电影叙述者:对一个复杂概念的追溯
最早涉及电影叙述者问题的是阿尔伯特·拉费(Albert Laffay)。他在1964年出版的《电影逻辑》一书中提出:“任何影片的组织都建立在位于银幕外的一个潜在的语言中心上。”[4]拉费在书中提出“大影像师”这一概念,“大影像师”用来表示操作画面的机制,指一个不可见的叙述策源地,不是指一个具体的人或人物,而是“隐形于每一部影片背后的潜在在场。”[4]81
若以小说叙事学的术语来看,拉费此处所言大影像师对应的应是文本叙述者,而非人物叙述者。如前所述,因为去除了中介性,文本叙述者在电影中是隐身的,难以找到踪迹,这也让很多电影研究者不承认人格化的电影“文本叙述者”存在。有必要赘言加以说明的是,电影叙述者理论和电影作者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于小说来说,作者通常只有一个,把作者作为文本外的实体性存在,叙述者作为文本内的概念性存在,隐含作者作为连接这两者的桥梁,便成为一个虽无奈,但也颇为精巧的设计。但对于电影来说,情况就完全不是如此。首先,电影的作者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早在1913年,德国就诞生了“作者电影”(Autorenfilm)一词。这一术语联系着关于作者身份的认知。德国的电影剧本作者认为,他们不仅对脚本拥有著作权,而且也是电影本身的作者。而在法国,作者的概念(auteur)出现于1920年代,这一术语认为电影导演才是电影的作者[5]。到1950年代,电影手册派发展了作者的观念,将其与场面调度的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根据他们的观点,导演的作用不只鲜明地体现在剧本中,也可以体现于影片的拍摄本身。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英国《电影》(Movie)杂志再次发起了关于作者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作者被视为可以制造意义的诸多结构之一,以此解决关于电影作者的浪漫美学态度。《电影手册》也批评关于作者身份的浪漫主义观念,作者从作品的中心变成了支撑电影文本的众多结构之一。与之同样重要的结构,还有制片厂(studio)和明星(stars)。后结构主义将所有相关话语都看做是被纳入文本或内在于文本的。而符号学引入了文本主体的理论,也就是说,主题位置内在于文本过程之中,包括所有观众的主体和作者的主体,他们都是意义的生产者。换言之,电影作者此时成了电影构建出来的形象。及至精神分析介入电影理论,作者问题开始越来越深入地与主体问题纠缠起来[5]48-55。
抛开这些哲学性思辨,仅从技术和体制上考量,作者也是一个颇费思量的复合性概念。一部电影的完成,需要有剧本,剧本作者创作构成电影创作的第一个步骤(若改编自小说,还涉及到原著作者)。在拍摄阶段,演员和布景、道具等工作人员共同完成“现场的演出”,由一位或几位摄影师对这一演出进行可重复的摄制。而摄影师的拍摄工作,既有自己的创作在里面,也受分镜头剧本的指引。这个分镜头剧本有可能是导演自行制作的,也有可能是分镜师完成的。导演会对整个电影制作环节进行管理和监控,但导演的权力也受制片人、明星演员和剪辑师的制约(尤其在好莱坞体系内)。当我们说到电影的作者的时候,我们与其说是言及某个单独个体,毋宁说是片尾字幕打出的名单的团队,和这一团队背后的体制(不同体制下,制片人承担的角色及对电影摄制担负的任务就不相同)。
因此,在电影中,“作者”本身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哲学层面都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晦暗不明,这里面既有哲学思潮发展带来的结果,也有电影本身技术、体制特点造成的结果。但不管怎样,要想清楚地界定电影的“作者”是困难的。那么,隐含作者这一在小说叙事中本就充满争议的概念,在电影叙事中就变得更不可索解,甚至可以说,电影的隐含作者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由于作者和隐含作者变得面目模糊,也因为电影本身取消了其中介性,电影的文本叙述者也成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
波德维尔对此有过专门的分析,他认为,在电影中,如果人物讲述故事,那就是人物叙述者,比如《爱人谋杀》(Murder My Sweet)中的马洛(Marlowe);如果是一个故事世界之外的人进行叙述,比如《朱尔和吉姆》(Jules and Jim)中描述叙述世界的画外音,《轮舞》(La ronde)里在血与肉中向观众说话的游戏主持者,这些电影就保持着一个清晰的、非角色化的叙述者。波德维尔认为,这些人格化的叙述者一直稳定地沉潜在电影的叙述过程中而没有创造什么。他更关心的是那些含蓄的“非人格化叙述者,“即便没有声音和形体出现在叙述的轨迹里,我们还能说电影有一位叙述者吗?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超越整个叙事,为之找出一个作为叙事源头的实体存在吗?”[6]波德维尔认为小说叙事与电影叙事是不一样的,文学理论为小说叙事寻找一位叙述者是合理的,但我们观看电影的时候很少会注意到电影是被一位像人一样的实体讲述的[6]62。对此,西摩·查特曼也对电影叙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小说的叙述者讲述整个故事,是整个阅读活动的中介。即使度过大段的对话或关于人物思想的直接或间接的引语,我们仍然假定存在着一个叙述者。但是在电影里,叙述者的存在只是在他说话时才能被感觉到。叙述性的视觉形象与声音形象的合力支配着观众,使他们觉得事情就发生在眼前。……在电影里,直接地耳闻目睹着‘事件本身’,使观众忘记了讲述那些事件的某种外部的声音。[7]
三、非人称性:电影叙述者的核心问题
不妨以此为例,管中窥豹,分析电影叙事学对经典叙事学“批判性继承”。电影叙事学者对于叙事学的基本框架是继承的。波德维尔在书中也沿用了叙述者(narrator)/作者(author)这一经典对立概念。其他电影叙事研究者包括西摩·查特曼、安德烈·戈德罗、弗朗索瓦·若斯特等人,也都在经典叙事学的框架下展开电影叙事的讨论。但这一继承经过媒介叙事,尤其是讲述/展示之区别的过滤后,发生了很多变化,创造了一些新的叙事观念。比如电影中是否存在未明确现身的文本叙述者就存在着争议。媒介叙事的区别让电影叙事理论从一开始就关注具体问题,而无意从整体上袭用某种大而化之的“普遍叙事语法”。当然,这种直接性和推测性的理论建树亦带有感受性强的特点。波德维尔认为:“在观影的过程中,我们很少会注意到故事是被一位像人一样的实体讲述的。”这种经验性的判断更像结构主义叙事学产生之前小说理论家下断语的方式。试比较麦茨对观影方式的另一种看法。
在电影院里,影片虚构和观众人格决定了情感的参与,这种参与可以变得非常活跃,于是,“知觉移情”就在一闪即逝的艺术激情的短暂时刻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主体对于影片情况自身的意识开始有点朦胧和滑动不定,尽管这种滑动(只是滑动的开始)在一般情况下从未被推至极端。[8]
显然,麦茨的观点是一种超越了一般经验的观照。当我们同样地尝试“超越”观影经验来看待电影中的叙述者时,我们必须自问一个问题:电影叙述者真的不存在吗?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电影给观众提供的虽然是一种貌似真实的影像,但这种影像毕竟不是真实的。电影呈现的每一个镜头都可能是经过复杂的场面调度、精心筛选和剪辑,并以一种“有意味”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种“有意味”的方式区别于我们自然撷取的画面,呈现出一种被控制被操纵的效果。当我们穿透影像的幻象,审慎地面对这一事实时,我们必须回答是“谁”或是“什么”提供了这些影像。无论波德维尔或是查特曼,还是其他秉持此论的学者,他们在否定电影的文本叙述者时,都只是陈述观众好像“忘记”了电影是被“叙述”的,而无法回答电影有没有、该不该有叙述者的问题。
俄罗斯导演列夫·库里肖夫(Lev Kuleshov)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从一部电影中选出演员伊万·莫兹金一个没有表情的面部特写,并将这一镜头和三个具有不同意味的镜头连接(一个汤碗、一口棺材和一个孩子),结果莫兹金没有表情的脸在实验者看来分别表现为饥饿、悲痛和父爱。库里肖夫实验既揭示了观影过程中的幻象,又指明剪辑这一过程具有的“叙述”功能。对于这一功能,爱森斯坦表达得更明确。
蒙太奇不仅是造成效果的手段。而首先是一种“说话”的手段,表达思想的手段,即通过独特的电影语言、独特的电影语法而表达思想的手段。[9]
对剪辑的思考使电影从一种拟真的影像变成了语言,麦茨的电影语言理论即是由此而来。在麦茨看来,任何讯息如果不断反复,并且包含某些变化,都会成为某种“句法的章程”,电影中这些主流中的变化像语句那样被反复使用之后,变成了一种电影专门使用的语言系统,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10]。对于电影语言和语法的探究使我们可以超越经验的层面,捕捉影像背后的秘密,既然电影是一种语言,那么存在一位使用这种语言的叙述者也便是合情合理了。
很多理论家关注并试图解决这一矛盾:电影“看上去”没有叙述者,但电影“应该”有一位叙述者。这其中,瑞安和伯戈因提出的无人称叙述者便为两者架起了桥梁。
瑞安是从文学叙事开始提出这一概念的。正如前文所说,文学叙事中存在一些接近于戏剧的展示性叙述,在这些叙述中,事件好像是自己发生和呈现的,而没有一个拟人的叙述者,典型的代表就是海明威和格里耶隐匿叙述者的小说。瑞安认为,叙述者并非一定要具有拟人的身份,也并不需要心理学的内容,“它”更接近于某种功能性的存在。
叙事者的概念是一切故事的逻辑必需,但是它在非人称叙事的情况下,没有心理学的基础。这就意味着,非人称叙事的读解者没有必要试图回答“谁在说话?”这个问题。[11]
显然,这是叙事学的后辈对经典叙事学“遗产”的一种回应。众所周知,热奈特对于“谁在说”和“谁在看”的区分标记了聚焦研究的一个重要时代。这一区分同时也将拟人化的叙事者推向了顶峰。非人称叙述者的提出,既是对传统的反思,也是发展。这一发展在电影聚焦研究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推动,伯戈因认为,与人称叙述者“报道”虚构世界相比,非人称叙述者行使的是“创造”虚构世界的功能,因而人称叙述者可以撒谎,但非人称叙述者是永远真实的。
戈德罗和若斯特将这一问题导向了更为复杂的阶段,他们认为,对于小说来说,文本叙述者和人物叙述者叙述使用的材质是一样的,“一个词语的叙述者用词语讲述另一个词语的叙述者用词语所讲述之事,因而存在材料的同质性。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叙述代理导致第一叙述者几乎完全隐迹”[12]。而对于电影叙述来说,因为电影混合多种表现材料,自身也不是单一性的,因而可以提出一种模式,即把电影的叙述者看作是一种机制而非人格化的、单一的叙述者。这一机制负责统合所有的影片表现材料,组织安排叙述策略。他们援引安德烈·加尔迪对于“影片陈述者”职责的划分,将其分为图像的责任人、言语的责任人和音乐的责任人[12]72。这样,电影叙述者从“去人格化”的解构走上了建构的道路。
对于电影叙述者这一“最让人生畏”的问题(伯戈因语),非人称叙述者的提出是一个阶段性的小结,而不是结束。可以看到,文学和电影叙事都遇到了非人称叙述的问题,但因为媒介的区别,两者却同中有异。文学语言的中介性让拟人化叙述者这一隐喻天然具有可接受性,因而在文学叙事学发展过程中,这一命题并未得到太大的重视。但在电影叙事中,面对无中介呈现的影像,非人称叙述者的问题就变得至为重要起来。对于文学叙事而言,将文本叙述者想象成拟人的或非人称的,其实区别并不大,反而拟人的叙述者更符合读者对于“运用语言中介讲述故事”这一想象。但在电影叙事中,叙述者非人格化就成为必不可少的选择,既因为电影的作者是一个构成复杂的概念,也因为电影的展示性远远大于讲述性。因而建立一个去人格化的、功能性的叙述框架,就成为必然了。
[1] 罗曼·英加登.论文学作品[M].张振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222.
[2] 安德烈·戈德罗.从文学到影片:叙事体系[M].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6.
[3] 余 华.在细雨中呼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5.
[4] Albert L.LogiqueDuCinema[M].Paris: Masson, 1964:80.
[5] 苏珊·海沃德.电影研究关键词[M].邹 赞,孙 柏,李玥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13:48.
[6] David B.NarrationintheFictionFilm[M].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61-62.
[7] 西摩·查特曼.用声音叙述的电影的新动向[G]//戴卫·赫尔曼.马海良,译.新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19.
[8] 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M].王志敏,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9] 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M].徐 建,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
[10] 克里斯蒂安·梅茨.电影的意义[M].刘森尧,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8.
[11] 罗·伯戈因.电影的叙事者:非人称叙事的逻辑学和语用学[J].世界电影,1991(3):9.
[12] 安德烈·戈德罗,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M].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5.
Impersonality of the Film Narrator
Huang Can1,2
(1.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2.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Communication of Movie and Television,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22, China)
Compared to fiction, the identity of the film narrator has been in a huge controversy since it features impersonality.The identity of narrator is closely interlinked with the way of narrative while film telling is well integrated with showing, all of which contributes to impersonality, marking a big difference from the fiction that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single and personified narrator as an intermediary.Owing to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film making as well as performance, film narrating is fulfilled by a composite mechanism, namely narrative mechanism, which functions as the personified teller of fiction in the narrative of film.
film narrator; impersonality; narrative mechanism
2016-01-17.
黄 灿(1980— ),男,博士,讲师.
黄 灿, huangcan0910@sina.com.
I05
A
1008-4339(2016)06-55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