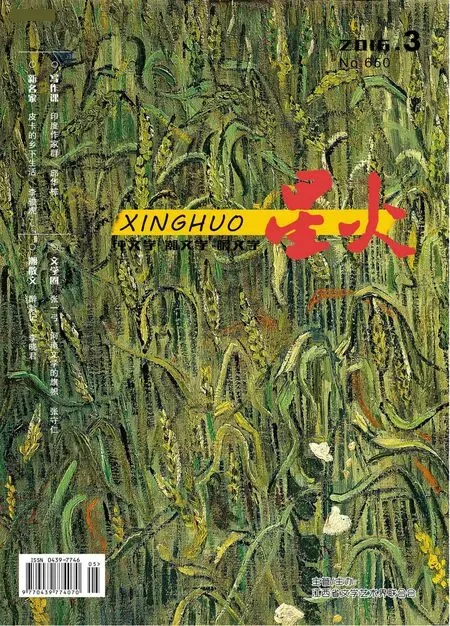身体里的兽
2016-02-06○蔡瑛
○蔡 瑛
身体里的兽
○蔡 瑛

蔡瑛,江西鄱阳人,江西省作协会员。有散文作品见于《创作评谭》《美文》等刊。著有散文集《幸福温度》。
肿瘤,这只猛兽是从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蹿到我面前的。在这之前,它只是一个有些灰暗的名词,像远在北京的霾,又像是衣服外面沾的一点污泥,隔着空间与皮肉,基本不具备关注度与杀伤力。在这一天,它成了我心上的一头兽。
我曾经与它激昂决战,但终是败下阵来,心力交瘁。这只兽,从此在我身体里安营扎寨,像个处心积虑的小人,静待着某个时刻蹦出来,揭穿属于我的一切温暖美好的假象。它有着不同的面目,本领非凡,虎视眈眈,干扰我原有的秩序与常态。我们互相揣测,互相对峙,我和它,像两只红了眼的兽。有一天,我照镜子,发现我消瘦了,我原本圆润上扬的脸部线条,呈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松懈疲软的趋势。它在镜子里静静地与我对视,我仿佛越过数年的光阴,看到了自己垂暮的老态。
我知道,这是它的杰作。
1
我清晰地记得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清晨,就像记着一个可疑的誓言。
那一天注定不是一个寻常的日子。那是周一。我们在乡下过了周末,一大早要赶回县城,儿子要上学,我要上班。上车前我突然发现我落下了我的手表,结婚十周年的礼物,一块瑞士梅花,我唯一的奢侈物。我匆匆折回头,房间里它可能存在的地方,抽屉,床头柜,洗手间,枕头底下,全没有。我完全不记得我把它落在哪里,记忆里一片空白。时间不容耽搁,我慌慌张张地上车,一路惴惴不安,心像没有依托的钟摆,空荡荡地悬在那。半路上,母亲突然来电话。记忆中,我从来没有在早上七点多钟接到过母亲的电话。然而这并不能代表什么。母亲说,上班了吧,我和爸来鄱阳了,你爸胃痛,带他来人民医院看下。母亲的语调很寻常。莫名的,心头的钟摆陡然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声比一声令人慌乱。父亲从来没有上医院看过病,除了单位组织的体检。极少的头痛脑热,父亲几乎连诊所都不愿去。我那个最注重养生,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风雨无阻地坚持长跑与泡脚的父亲,居然来人民医院看病。我感觉有点不好。我说,妈,我现在在回城的路上,等会去医院陪你们。妈说,不用陪了,你上你的班,一点小病,我陪你爸看看就行。挂了电话,我怔在那里,随即打电话给在县城的老二。爸来人民医院看病,你怎么都没有去陪?我的语气里有着莫须有的急促与质问。我又不知道,我这就去。老二嘟哝着回我。挂了电话,坐在那里,心里有些发慌。丈夫在旁边模糊不清地说着什么,让人觉得聒噪。乡下的路,一个弯道接着一个弯道,像一个饶舌的妇人,把一段话说得弯弯绕绕晦涩又冗长。我靠在椅背上,觉得有些虚弱。
那天早晨,像一个出错的程序,孩子要迟到,最珍贵的手表不见了,父亲突然身体欠安。可是,我不知道,那其实是我生命里最珍贵的时段。那个时候,一切都还安好。我默默地看着时间往前走,拉不住它。
这是一个初夏的早晨。我们的车迎着薄薄的阳光与一片澄蓝的天空,却兀自开进了一片让人窒息的阴霾。
2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手机与电脑的搜索格里都只有一个词,晚期肝癌。它触目惊心地反复出现,像一种顽固的病毒。我一遍又一遍地搜索着与这个词相关的一切文字资料,它的起源,它的症状,它的走向。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灰色,一团一团的灰像陈年发霉的棉絮一层又一层地向我压来。那鬼魅一样的x光片,从上海最权威的肿瘤医院飞到深圳最大的中医院,所有的医生都是面无表情的死刑宣布者。我们对医生咆哮哭泣,像胡搅蛮缠却没有能力的孩子。在真相面前,泪水与愤怒,都无比轻飘。
我不相信事情没有转机。晚期肝癌,这是个什么鬼,我相信我能把它大卸八块,洞穿它,肢解它,消灭它。我像个过滤器一样自动地过滤掉一切的灰色,牢牢地锁住那一星半点的希望之光。我相信奇迹。怎么可能,我的父亲。
父亲一直未知。我们像保护婴儿一样保护着父亲。父亲配合着我们的一切,我们的隐瞒,我们的安排,我们的药方,我们的食谱。那个曾经严厉要强的父亲像个单纯的温顺的孩子,信任与依赖着我们。没有了任何手术的机会,我们把希望寄予食谱与中药,想通过中药与饮食来重新建立一个体内环境,一个肿瘤细胞不能生存且自行灭亡的环境。我用各种途径寻找一切专门与肝癌作对的食物,像一个资深营养师一样严苛地安排着父亲的食谱。书上称碱性物质能对抗癌细胞,只要体内形成碱性环境,癌细胞便无法生存。我们让所有父亲爱吃的油炸辛辣、动物性食品等酸性食物从父亲的饮食中彻底消失,每天数种碱性蔬菜水果轮番上阵,搭配一些强碱性的海藻与豆类,红薯、大枣、芦笋等抗癌佳品更是每日必备。这些五彩缤纷的食物像是我们埋伏在父亲身体里的勇士,我们都相信它们一定会不辱使命,将父亲的癌细胞一一刺穿。
有一次,母亲为几个孩子炸了花生米,父亲一直好香脆的食物,尤爱油炸花生米。熟悉的香味从餐桌漫开,父亲惯性地伸出筷子,在伸进嘴里之前,父亲顿了一下,犹疑地看向我。看着我的父亲像一个殷切等待的孩子。我心里一酸,却摇了头。那不是花生米,那明明就是滋长癌细胞的恐怖分子。父亲憨笑一声,将嘴边的花生米放回碗里。我分明听到父亲的喉咙发出了一声叹息。
我们都仿佛成了抗癌专家,欲将所有的抗癌奇方一网打尽。妹妹从微信里看到一条关于柠檬水抗癌的消息,我们买来柠檬,切成薄片,像哄孩子一样哄着最厌酸的父亲一口一口皱眉喝下,那柠檬水真是漂亮,它们通过父亲的喉咙发出最美妙的声响,像一朵花开的声音。各种信息里都声称,中药或许能创造一种奇迹。我们都深信不移。然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太多的药方像一个纵横交错的路口让我们无法抉择,我们不知道哪个路口通往重生,而哪个路口或许就直接走向了死亡。每一次,那一包包形状香味各异的草药拿在手里,我都想入口一一尝验,生怕送入父亲腹中的是致命的毒药。那是一段耳目失聪的日子,我们一次次强打起精神,准备去创造一个奇迹,像穷途末路的传销者,面对天花乱坠毫无逻辑的谎言,自欺欺人地强迫自己去相信。我们后来通过网络查找到省里最有名的肝癌中医专家,便去省城彻夜排号,我坐在那个名中医面前,像个小粉丝一样激动得语无伦次。我说,还好我们找到了你,还好我们找到了你。仿佛他就是能终结死亡咒语的神。
我把父亲病情的真相锁定在我们姐妹几个当中,所有的亲戚,甚至母亲都瞒得死死的。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我只知道我不能让父亲精神崩溃,不能让他可能出现的消极状态导致病情的恶化。谁愿意面对自己走向死亡的真相,死亡,是一切的终结,是灰烬。希望,才是良药,是火苗。就算是假象,病人也会死死地拽住它,选择相信。我不知道父亲对于自己的病情到底知道多少,对于我精心编制的假象到底相信多少。他从来没有追问,没有提起过与死亡半点相关的话。他也许真的相信了,也许,只是配合我们相信了。也许,他只是因为回避,而选择了相信。在安排父亲去省城面诊的时候,我和妹妹们像特工一样,事先安排好所有的环节与细节,不容许残酷的真相以任何可能性泄露到父亲面前。每一次去省城拿药,我都一遍又一遍检查药方与药盒,不留有任何有肿瘤肝癌的字样。有一次,由妹妹去拿药,我忘了交待,一盒写有适用于肝癌字样的药盒送到了母亲面前。母亲打来电话,哭泣着追问。我用了半个下午的时间,发挥出连我自己都讶异的思维与口才,再一次骗过了母亲。放下电话,我感觉自己全身瘫软,手脚冰凉。窗外的阳光漫不经心地照进来,没心没肺似的晃人眼。我突然觉得身边的世界完全不一样了。我锁上办公室的门,一个人呆呆地站着,拿起手机,我想打一个电话,我翻着通迅录,一个又一个名字,仿佛没有一个和我有什么关联。一切的存在与温情,都是假象。丈夫突然来电话,询问我下班的时间,晚餐吃什么。我对着手机神经质地号叫,你就知道吃什么,就你吃得下,我就知道这不是你的父亲,我就知道你根本不在乎,我就知道你完全不能体会我的感受,什么夫妻同心,什么有难同当,你就是个别人!我扔下手机,终于,号啕大哭起来。
3
是的,我们都一厢情愿地想象,只要父亲保持良好的心态与状态,只要我们密不透风地为他重建一个理想的环境,所谓的肿瘤,只是身体里一个可以与生命共存的肿块。然而,父亲还是渐渐消瘦了。癌细胞早就渗进了他的血液,正一点一点在他身体的每一处蔓延。父亲肝部的肿瘤越来越硬了,连胸也鼓胀了起来。母亲说,怎么感觉你的胸肿大了?父亲笑着,伸了伸臂膀,什么肿大,那是胸肌。每一次看到父亲笑,我的心都会发颤。有一次,父亲露出腹部,跟我说,妹仂,这里越来越硬了,你摸摸看。我伸手过去,父亲的腹部像藏着一块硕大而炙热的铁块,一份灼痛与恐惧从我的手掌漫向全身。我无从感知那铁块塞在父亲的身体里是什么感觉,我更不能把那铁块从父亲的身体里取出来。我虚弱地告诉父亲,肝硬化当然就是硬的。我感到越来越无力,只想逃离。我告诉自己,这一定是场持久战,我要先自我修复,我要喘息。我没有向单位告假去珍惜每天的陪伴,而是跟母亲说好周末回来便仓惶地逃回了城里。我若无其事地上班,同事们像往常一样说笑,男人们吹着牛皮,女人们说着服装,父亲的绝症像是昨日的一个噩梦。只是,我走不出那个噩梦。我做不了任何事,手机里,电脑里,意识里,全是肝癌晚期四个字。我觉得我也成了一个肝癌晚期的病人。我给父亲打电话,爸,还好吧。好着呢,能吃能睡,放心。每一次,父亲朗朗的笑声从手机里传来,像复读机一样。
当死亡借着至亲之人的躯体宣告着向我走来时,我才发现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软弱者。在父亲面前,我像个无师自通的演员,轻松地说笑,胡扯一个又一个肝硬化治愈的病例,叮嘱他的吃与睡。然而,脸一转向他处,泪水便挣扎着无声奔涌,像可耻的叛徒。我是父亲的长女,是他一直以来都寄予期望与信任的长女,是五个孩子里说话处事都最有分量的长姐。这是一个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却与生俱来的事实。在我三十余年顺风顺水的生活里,父亲突如其来的肿瘤,像一场浩劫。我感觉那块沉重而炙热的铁块从父亲的身体里转移到了我的身体,我拖着它,孤身走在一片雾霾里。
那好像是我和父亲共处的最后一个周末。我回家,父亲正在院子里给花除草。黄昏,院子里有淡淡的花香,微风带着初秋的清凉。父亲弯腰拾掇花草的身影像一个童话。我嗔怪他,爸,说了要多休养,你总闲不住。父亲说,都是手脚功夫,等我病好了,我要重新规划生活做好计划。我呆呆地看着他的身影,像一个母亲痴痴看自己的孩子。我说,爸,给你照张相吧。父亲搬来小凳子,端坐在花草前,像个小学生。镜头前,我的六十二岁的父亲明显老了,他穿着白色的棉汗衫,两鬓斑白。他坐在那里,因为消瘦而显得弱小,他努力地笑,却仍然笑得那么无力。那个黄昏,我仿佛看到父亲渐渐融入到夕阳里,变成那些晚霞,一点一点散去光芒,一点一点隐没在即将到来的黑夜里。
我的父亲,他有理由相信他还可以重新规划他的生活,他错过了太多他想要的日子,这一路的辛酸与隐忍,纠葛与桎梏,如今,人到花甲,万事顺意,他的人生要重新启航。生病期间,他在日记本里写下一段话:“心态平和,生活规律,有所追求,无须强求,喜欢劳动,心地善良,待人宽厚,助人为乐,家庭和睦,子女孝顺。日行八千步,夜眠八小时。”像是一段对他的生命迟来的爱的告白。
4
当我直面肝癌这个问题时,才知道,癌症已经无处不在。它绝不是远在北京的霾,更不仅仅是沾在衣服外的泥点子。它与我们息息相关,是每一片天空里隐形的霾,是我们身体里的某一根毛发,某一个细胞,某一根经脉,是我们的每一个不成眠的夜,每一次贪欢的杯,每一种纠葛的念。
癌症(恶性肿瘤),已经成为除心脑血管外的人类死亡的首位因素。关于癌症的数据报告越来越让人震撼与揪心,中国每年有两百多万人死于癌症,癌症的发病呈低龄化趋势。癌症其实是一种千丝万缕的慢性病。癌症的发生发展是关乎着我们的环境因素(物理、化学、生物等致癌因素),机体因素(遗传、神经、免疫、内分泌、代谢等),以及微环境多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专家指出,百分之八十的癌症来自于我们所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含吸烟)和所吃的食物。更细一点划分,癌症的生发百分之三十与吸烟有关(吸烟不仅与肺癌有关,很多其他癌症也与之有关)。百分之三十五与饮食有关(如一些富含亚硝胺的腌制食品与胃癌、食管癌有关,过食霉变花生玉米因富含曲霉毒素而易得肝癌,高脂肪饮食可能与大肠癌、乳癌有关,盐过多促胃癌,饮食纤维素少可能易患大肠癌)。百分之十与感染有关。百分之二十五与生活习惯有关。更有专家直言,我们的饮食作息习惯就是癌症的源头。而生活方式比任何因素更为重要。
父亲,他的肿瘤是什么时候埋下的呢?也许具体到是某些混进父亲身体里的霉变的花生米,是那每日两餐雷打不动的烧酒,也许是内心里的那一个又一个的结,它们蛰伏在身体里,找不到出口,慢慢地,腐化溃烂,郁结成团,终是变成了一个再也无法剔除的恶性肿瘤。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癌细胞,就像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欲念。它是每个人身体里的一头兽。只是,有的与身体和解,安居乐业。有的,在考验与束缚中性情大变,生了恶念。父亲身体里的那头兽,是如何从了恶,或许,只有父亲才知道,或许,父亲自己也不知道。所谓的生活方式,是一张错综复杂的人生版图,有着太多自己情愿或不情愿的底色,关乎命运,关乎性情,关乎虚妄与执念。
二○一三年秋,我参加了一个葬礼。我的一个中专寝室姐妹死于直肠癌晚期。得知她病情是一个星期前,我们计划着周末去看她,却接到她的死讯,直奔殡仪馆。我至今都后悔在那样的地方去见她最后一面。我想,她一定也不愿意。她是一个灵动活泼到让很多人失色的女孩,而最后,她躺在殡仪馆的一个冰棺里,像一个老太太一样穿着夸张的寿服,双颊深凹,牙齿突出,小腹像座小山一样可疑地隆起。她性格外向,家世良好,在我的记忆里关于她的一切都是一片明媚,她的人生理应鲜花盛开果实芬芳,怎么就沾上了直肠癌这个丑恶的魑魅?
参加完葬礼回来,我总感觉我是做了一场荒诞的噩梦,我无法相信那个古灵精怪的女孩成了那具我所看到的面目全非的僵硬躯体。我在QQ里找到她,打开她的空间日志。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好像时间被我按了倒带键,她从冰棺里爬起来,扯掉那腐朽的假面与寿服,走到我跟前对我娓娓述说。那些文字,像一个个电影画面,展示着我记忆与想象之外的晦涩与寒凉,像窗外瑟瑟的秋雨。十年的光阴,像一列跑偏的火车。她的婚姻,她的梦想,或者还有其他一些东西,都偏离她的意念混沌地靠错了站。她淡淡地诉说,借着我记忆里的那张灵动鲜活的脸,像在说别人的故事。那些明明暗暗的线交错成一张网,她困在其中,一张明媚的脸,像一个空洞的假面。唯一和校园里那个女孩扯上关系的,是十年后她依然是个贪吃到偏执的女孩。那个中专时便鄙视我们的多愁善感诗情画意,立志只做一个简单而快乐的吃货的她,仍然保留着偏激的饮食习惯,口味奇重,只爱辛辣烤炸,不下厨房,不喜蔬菜,常年在肯德基这样的西餐厅里对付。在胃疼到痉挛时仍然去吃酸辣鱼,大呼过瘾后,却在卫生间里痛到一身冷汗而昏倒。她就像个执拗而叛逆的孩子,放纵与宠溺着她的胃,好像只有在食物里,才可以找到她要的简单与刺激。她把那薄薄的肉身当成信念坚定的地下党,任其经受各种严刑拷打。她不知道,它已然叛变。我记起葬礼时她那中年得女的白发老爹,拉着我们的手,一遍又一遍地说,孩子们,你们,还有你们的孩子要管住自己的嘴,切切管住自己的嘴!祸从嘴出,病从嘴入啊!那颤抖而苍老的声音,像是上帝的谶语。
一切,皆有源头。所谓因果,所谓轮回,谁都无法逆转。
5
父亲的那一天,来得很快。快到猝不及防。那天早晨,母亲打电话来说父亲开始感觉痛。我清楚地知道,痛意味着什么。我像一个害怕看鬼片又忍不住在捂住双眼的手指缝里心惊胆颤地偷看魔鬼的小孩一样,在无数次地煎熬与恐惧中去查询过晚期肝癌临死前的各种症状。而痛,是其中之一。还有比痛更可怕的,比如,呕血,昏迷,癫狂。
痛,无休止的痛,越来越无法忍受的痛,将要击破一切谎言,彻底击垮那个心心念念着要重新规划生活的父亲。我要终止,或者舒缓父亲的痛。我去中医院找一个信赖的中医老师,我说,您一定要帮我,我要开止痛的中药,要止痛,但不能伤害我父亲的身体。那个头发花白面色红润的老中医看着我,用一种温水般的语调对我说,妹仂,不要急,你看起来气色很差,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保重自己的身体。人生啊,会有很多意外,扛一扛,都会过去。我自己的父亲,五十二岁,死于肺癌。那个时候,我比你还年轻。万事由命,别太上心。那个老中医,大概和父亲差不多的年龄吧。他和父亲一样叫我妹仂。我特别想上前抱一抱他。
我准备了止痛的中药,又托熟人买到了晚期癌症阶梯式止痛三步曲中的曲马多,以及吗啡。只要止住痛,父亲还可以照常吃喝,还可以熬过一段日子,而我,要时刻陪在他的身边,和他聊聊我们共有的工商事业,我们共同爱好的文学。还有我的孩子,他要承欢外祖父的膝下,听外公讲讲他无法想象的从前的故事。
两天不见,父亲的样子竟然全变了。他虚弱地坐在椅子上,母亲搀扶着他。那个屋子,空荡寂冷,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晦暗的潮湿。父亲抬头看我,用一双我完全不熟悉的仿佛蒙上了一层灰的眼睛,他说,妹仂,你来了,别担心,没什么大事。那双眼睛轻易地击溃了我五十多天精心伪装的坚强,我心慌意乱地躲进厨房煎药。药罐不知什么时候拿在手里,哐咚一声,掉在台面上,一块瓦片在罐沿的裂痕中挣扎着,终是掉落,摔在摊开的浓褐色的药汁里,像一个倒在血泊中的决绝的勇士。全是他妈的谎言!我突然想狠狠地骂粗话,诅咒一切该诅咒的。然而,我还是把药端给父亲,他接过来喝了两口,停下来喘气,他说,妹仂,我实在喝不下去了,我可以不喝吗?我说,爸,你怎么跟孩子似的,全喝下去,喝下去就不痛了。父亲再次相信了我,他端起碗,仿佛用尽全力喝完了他生命中最后一碗药。
那头兽彻底在父亲身体里爆发了。中药,曲马多,甚至吗啡,全都止不了痛。没有任何东西能止住父亲的痛。我曾经在网络上详细了解过吗啡的作用,它是癌症止痛的神药,任何的痛只要经过它,一个小时内必然止住。只是它有上瘾的副作用,有的晚期癌症患者靠它能维持一年半载。它曾经是我心里的最后一张护命符。我等待着有一天它像鸦片一样让父亲上瘾。上瘾,简直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病症。可是,这个疼痛的终结者,这个止痛界的神话,没有止住父亲的痛。我不知道连吗啡都止不了的痛是怎样一种痛,我仿佛看到父亲体内的一切正在那块炙热的铁块下一点一点焦黑熔化。我的父亲蜷在床上,在疼痛的抽搐里折腾着更换姿势,一次比一次无力。我,这个巨大的谎言,杵在父亲的床头,像一摊卑微而无望的烂泥。时间仿佛停滞。我看见我的父亲用颤抖的身体抱住他的妻子,说,我可能不能陪你白头到老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对母亲的告白。也是唯一一次父亲说的,与死有关的话。
6
父亲走了,我却停在了那里。一切都像出了错。
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痛感被麻痹,像一个精神病患者,在一些记忆的死胡同里打转。我摇头阻止了父亲递到唇边的花生米。我在父亲临死之前还要他喝下了难以下咽的苦药。我要父亲每天去吃那些所谓的能打败癌细胞他却不爱的蔬菜水果。我在父亲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临阵逃脱。我反复纠缠在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细枝末节里,像一个糊里糊涂让狗屁不通的烂片匆促上映了的导演。
我想起那个深圳中医院主治医生的话,太晚了,不用再开药,所有的治疗都没有了任何意义,也就两个月的时间了,该吃吃该喝喝,多陪陪他,别去折腾。我们悲愤地打断他,斥责着他的无良与无情。在亲人的生命面前,我们都像没有理智的偏执狂与幻想家,一个良心医生的真话被所谓的亲情与道义淹没了。有太多的晚期癌症患者,置身于白色恐怖的医院里,死于不必要的手术台前。有太多的晚期癌症患者,承受着多次化疗放疗等现代医学的二度摧残,在他们最宝贵的生命时段里,萎缩与脱落的又岂是肌体与头发?过度的治疗,就像过度的环境开发,在缤纷的假象背后,往往是无法复还的加速毁灭。
对于人类无法攻克的癌症,尤其是癌症晚期,最需要的,不是无谓的救治,而是维护生命主体最后的自由与尊严。
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告诉父亲真相,我一厢情愿地剥夺了他的知情权,或者也给他的人生带去了难以弥补的遗憾以及我们永远缺失的答案。在那最后的五十天里,他也许可以更坦荡自由,也许可以更坚强理性。我不知道,在那五十天里,我的父亲到底在想些什么?他对于他的人生对于我们还有些什么愿望与交待?我追不回那些时光,拉不回父亲,更无法解读生命的真相。我停在那里,走不回去,也走不出去,像一头无法突围的困兽。
后来,我发现我心里的那头兽没了,它钻进了我的身体深处,埋伏了起来。它不动声色,我却能时时感知它的存在与它的窥视。我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规规矩矩,按时作息,每天散步,躲避社交与饭局,不看书不写字,关注起空气质量,食物来源,抗拒任何违背自然与土地的一切假象。我变成了一个战战兢兢的卑微的求生者,把所谓的梦想与精神搁置起来,只关注与生命息息相关的鸡毛蒜皮。看到有人嗜烟好酒,便想用那个老中医一样的温水般的语调劝诫他。听到某人得癌症离世,那头兽便如惊弓之鸟,在我的身体里翻江倒海。我去体检,却在取化验单的时候如临大敌,生怕自己就是下一个要被枪决的死刑犯。我在父亲离去的后遗症里,像一个暮气沉沉贪生怕死的老人。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指甲似乎长得比别人要快,我悲哀地意识到,我身体里的癌细胞也会比别人长得快。任我怎么努力,我都跑不过它,这只兽。像父亲一样。他坚持了数十年的长跑,却依然被它死死拽住。我也逃脱不了。
这世上,又有谁能敌过这潜伏在身体与时间里的狰狞而冷血的兽。
7
父亲的七七,我回家接母亲。父亲立在棂前和从前一样对着我笑。我站在院子里,久久挪不开步,像一个大病未愈的病人。屋前一个老寡妇,坐在后门口抽烟,看着我没心没肺地笑起来,你爸以后可以和我家死鬼一起凑脚子摸麻将了,他们也有伴了。活人不知死人,死人不知活人,终究,都要往那条路上去。那个女人,死过两任丈夫,二十年前,前一个丈夫死于肺癌,半年前,后一个丈夫死于肝癌。这个看尽生命无常的女人坐在那里,吞云吐雾,嘻笑轻言,像个云淡风轻的戏子,也像个洞穿一切的智者。
我被时间渐渐拉回了日常生活。我仍然每天都会想起父亲,有时会流泪,更多的,是怀念他的笑。我发现父亲所有留下来的影像,都是他的笑。仿佛笑,是他唯一的遗言。我把一张我和父亲的合影装上框放在我书房的桌上,在旁边放上一盆文竹。父亲最喜欢绿色。那是黄昏,晚霞从天边渐暗下来,田间小路上,我挽着父亲的臂膀。父亲往前迈着步子,稳健,从容。看不到一点病态。渐暗的景致里,唯有父亲脸上的笑,像镶着一道光。笑容散开处,绿意葱郁,余辉笼罩。每一次坐在书桌前看书或写字,抬眼,便看到父亲。看到他无处不在的笑。我想起著名女作家杨绛老人在百岁那年写的一段话:“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是的,每一个人都终会“回家”。所有的生命都要落下帷幕,最终归于寂无,归于永生。对于活着这件事,父亲,用他的笑容作了最好的总结。我于是相信,在“回家”的路上,父亲,正如那一天的步子,稳健,从容。
年底回乡,突然听闻屋前的老寡妇一星期前死了,和她那个前任死鬼丈夫一样,是肺癌。那个女人在临死前对旁人说,那两个死鬼,没跟他们享过什么福,倒是把这瘟病传给了我。他们这是急急地召着我去做伴啊。第一次,在死亡面前我竟没有感觉到悲凉。
清明节那天,我坐在父亲的坟前。满山的映山红又开放了,一丛一丛,热烈奔放,像不朽的希望。我看到我年轻的父亲牵着他小小的长女,对着这座青山跟她讲她的爷爷,以及他爷爷的故事。青山仍在,父亲也仍在。我发现我和父亲仍是可以交流的,他懂我,我也终于懂了他。我突然想起他在生病期间写的那段话,“心态平和,生活规律,有所追求,无须强求,喜欢劳动,心地善良,待人宽厚,助人为乐,家庭和睦,子女孝顺。日行八千步,夜眠八小时”。我这才知道,这不是他对于生命迟来的告白,是他对生命的自我解读与终极理想,更是他对我们这些孩子——他的血脉传承所有的愿望与交待。父亲何等明达,他用他的方式安放了他心里的最后一个结。
离父亲不远,并立着两座坟。是老寡妇和她的后任男人。另一处,一座小山丘里,住着她的前任男人。她的个头瘦小的儿子带着他的孩子在认真地祭拜,三座坟墓前香火缭绕,那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将手里的映山红逐一插在坟前,一张红扑扑的脸,像眼前的春天。
我站在一片绿意里,感觉身体里的那只兽蜷起身子,像一只猫一样,露出意兴阑珊的睡意。四周一片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