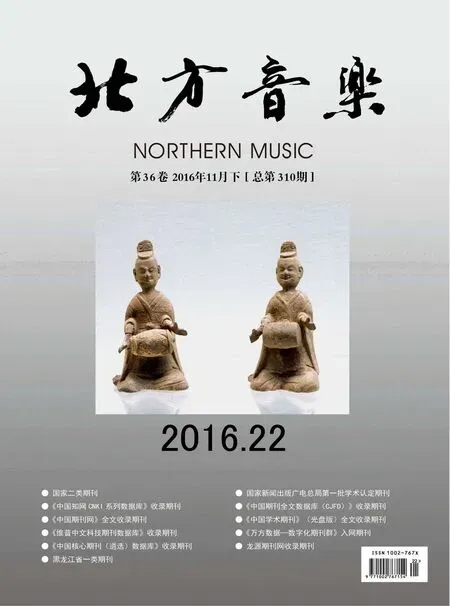“怪力乱神”——商代乐文化探究
2016-02-04王云龙
王云龙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重庆 404100)
“怪力乱神”——商代乐文化探究
王云龙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重庆 404100)
在商王盘庚迁殷之后,政局日趋稳定,使得商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空前成就,创造出青铜时代辉煌灿烂的文化。在统治环节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又被国之大事所需要的祭祀活动,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伴随着祭祀活动而出现的乐文化日益兴盛,成为我国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时期。本文就以此时期乐文化为研究对象,从乐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殷商时代的乐舞文化,以及殷商时代的乐的“巫”性等方面进行探析。
殷商;音 乐;乐文化
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因为商王盘庚将王都迁往“殷”(今河南省安阳市),所以后世将之称为殷、殷商。商人创造出青铜时代辉煌灿烂的文化,亦即以青铜器艺术为中心,包括文字、天文、历法,以及音乐、舞蹈、诗歌等在内的殷商文化。
一、乐文化与殷商时代精神
殷商时期,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个很特别的时期。不同于周文化的“文质彬彬”,商文化具有粗犷、稚气和原始的野性之美。在这个时代的美学里,我们看到了尊神事鬼、夸扬暴力以及崇尚武功,可以说这是一个“怪力乱神”的时代。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在其著作《美的历程》中,将最能代表商代美学精神的青铜器之美,称为“狞厉的美”,他在读解饕餮纹饰的时候说道:“……这种种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反而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好些饕餮纹饰也是如此。它们仍有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李泽厚认为,在人类向文明社会迈进的漫长历程中,不是只有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其间必定有战争和死亡,必须经历血与火的野蛮年代。而狞厉的青铜器艺术,正是这个时代精神的最好体现。
而这个时代的音乐,必定和他的青铜器艺术一样向我们昭示着他的时代精神。殷商时代的乐文化,正是在殷商时代特定精神氛围中形成的,深深的印刻着奴隶制的血腥历史和阶级的烙印。
比如在商代著名的祭歌《商颂》里,许多地方在炫耀着一种“武功”思想,表现出一种崇尚暴力的野蛮的文化意识。在这些祭歌里歌颂和夸耀武丁、武汤等英雄们的征服大业,体现了一种采用暴力和征服的手段向文明时代跨进的历史力量,更体现着青铜时代独特的审美理想和时代精神。
二、殷商时代的乐舞
据文献记载,商代的乐舞主要内容为歌颂最高的统治者,形制比较严格,并以祭祀为主要的目的,带有浓烈的政治意义和神秘性。
殷商时代乐的发展状况,从 “甲骨卜辞中关于商代乐舞的记录”,可以看到明确的记载:《濩》是颂扬汤灭夏而作,通过卜辞的描述,后也用来祭祀先祖;《商》据《礼记》载,是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重要乐舞;商代的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人类的生产活动还是主要依靠自然的力量,气候依然主要影响着人们的劳作;例如祈雨作为殷商最重大的祭祀活动之一,便是不可或缺的,有乐器演奏、专门的乐舞表演等。这些通过乐舞作为主要形式的祭祀活动,都是人们寄希望于神灵,并以乐舞来朝拜或者是以神化来祈福予自身力量,规模十分宏大。
(一)“桑林之舞”
殷商时代,脱离了母系氏族社会,进而转向对祖先和帝王的崇拜与依靠。这原始的宗教信仰,是依靠上天的力量去平衡自然条件,商人寄希望于神灵,以实现“神意”来取代“民意”。
殷商时期的乐舞多用于祭祀之时,其代表作为“桑林之舞”。据史料记载,“桑林之舞”是由一个由巫师领舞,动作狂放、衣着袒露的舞蹈。仲春之月,青年男女相聚一起,跳着以求偶为目标的浪漫舞蹈,这也是求雨祭典内容的一部分。而甲骨文中的“舞”字与“巫”字很相像,“降神离不开舞蹈”,可以看出,巫师的任务就是率领众人起舞,于祭祀礼仪中祭祀神灵。
据载,“桑林之舞”主要用于祈雨仪式。它的目的是通过祈雨来求得神灵的庇护,借以打动上天的眷恋与同情。《礼记·乐记》记载:“桑田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描绘了桑林之舞的浪漫、放荡不羁。从殷商的后代宋来讲,其子民继承了殷人游牧生活的习性。在他们看来,殷商的巫师文化强调虔诚的宗教意识,乐舞中狂热的舞蹈者,是在虔诚的祭祀宗教活动中忘记了自我,奉献其中;而在周人眼中,其为不加节制地纵情歌舞;而这对宗教的崇拜纯洁虔诚而圣洁,在宋人眼中视为脱尘的仪式。
(二)“东夷部祭祀乐舞”
据史料载,商代乐舞的内容主要有祭祀神灵与歌颂先王的丰功伟绩两大类。而商朝盛行的祭祀乐舞——“东夷部祭祀乐舞”却已经难以考究。不过从甲骨文的卜辞以及后人诗歌中,可以看出一些历史痕迹。据《诗经·商颂·那》描述其祭祀乐舞:有鼓、镛、磬、管等乐器。其表演之时,“渊渊、简简”等象声词。这些可以反映出祭祀仪式过程中,众人高歌,并伴有乐器齐奏的宏大效果。而商人于祭祀仪式中特别崇拜音乐,在供给神灵祭品之前,便开始高歌音乐,钟鼓齐鸣,待奏响过之后,祭品才被迎接。巫师们用响彻心底的乐的艺术奉献给神灵,同时也用最虔诚的心以传播天地之间。商代的乐舞不同于夏朝时的野蛮与血腥,在“呯呯呜呜”的声中不断表演——“以勇武为美”。
(三)“大聚乐戏于沙丘”
殷纣王虽为商代的亡国之君,但其在先秦的艺术领域,却开一代之先河。据载,商代后期,他聚集了联盟各方国的乐舞(因只能来源东夷部族),“大聚乐戏于沙丘”,可见商纣王对于各方乐舞的集大成。其“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便为后人所不耻。如果详实考究,可发现商代属奴隶制社会,原始的母系氏族公社里的裸体舞蹈对商代的乐舞有一定的影响,同时酒肉的奢华体现了社会财富的一定积累。而这种在我们现在看来疯狂的举动,可以理解为氏族社会的末期,权利者疯狂的占有欲望、一种近乎生命原始本能欲望的冲动。彻夜的饮酒,肉林与酒池,凸显了早期人类原始本能欲望的冲动。这时期的乐舞,与人们生存的基本欲望紧密相连。周朝的先民评价其殷商乐舞创作,原本追求净化心灵的感官享受,再到通过乐舞祭祀神灵以求庇护;商王朝晚期各方面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乐舞创作并没有结合现实,反倒成了靡靡之音。商纣王在艺术领域里虽为一代先驱,却跃进了一步,离开了其东夷部族祭祀乐舞庄重、严肃等一贯主张,使自己葬身于历史的悲剧之中。
三、殷商乐文化的“巫”性
殷商时期的乐舞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美学及社会价值。对于“文化”一词,有学者解释为“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文化的文明与理性的成熟在前进道路中,并非一帆风顺,常会遇到一定的曲折,殷商时期的乐,便在坎坷中艰难前进。殷商时期崇尚多神论,并推断巫术的出现可能要早于宗教,因巫术试图借助魔法的力量使自然界服务于人的意志。夏时期,在国家层面上已经出现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地神的仪式。殷商时期的神有如下特点:殷人崇尚的是多神组成的一个神灵王国,有上下统一的秩序构成的特点;神的首领是由自然界与人们最密切关系的职能神转化而来,具有涵盖多神的具有较大作用的物神转化而来,即农业之神;另一类为祖先神灵,尚不能确定其宗教地位,但是可能是最高神与世俗人们的媒介,不能确定其是否为卜辞中的“帝”;祖先神灵与帝都分有善恶两方面,具有“酒神的精气神”。同时有学者提出“神人以和”的审美观点,指出这种审美理念,实际上是巫术的宗教理念和乐舞的一种结合,这种信仰内在的逻辑即崇拜祖先,崇拜山川河流等自然,他们通过特定的乐舞,祭祀神灵,把自然界以及祖先赋予神化、人格化,是一种自然的精神寄托,同时也是亲近自然,力求得到平衡。殷商时期人们更多的“追求情感的统一而不是逻辑的规则”。原始宗教的初始,象征政治、道德的诗乐便与艺术审美的诗乐产生矛盾,而礼乐的宗教性与王权性,改变了早先巫术宗教的成分,更多地加入了理性成分。周朝后,“神人以和”历史性的演变为“礼乐之和”。
总之,这一时期的文化背后也反应出了它代表的精神内涵,从文化角度上去看殷商时期的乐文化,更能体现民族性的精神特点;而殷商时期的宗教,主要以巫术为代表,理性与伦理不断往复,社会道德秩序并不强;“神人以和”这具备“酒神型精神特质”的殷商先民,具有图腾与信仰的浪漫民族,用狂热的乐舞,大量的祭祀与崇拜,塑造了殷商文化独有的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