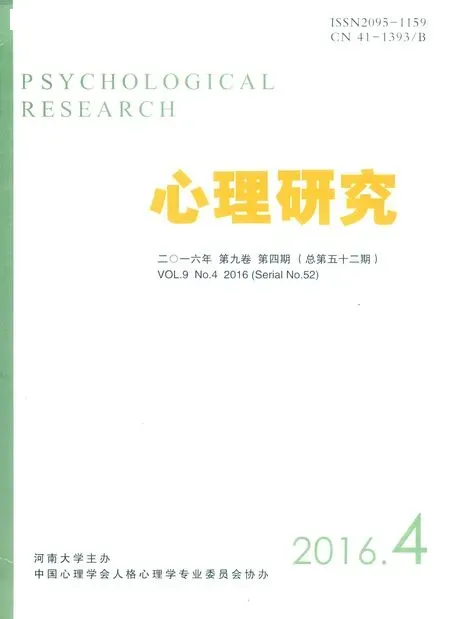重返意识经验世界
——评《神经现象学: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哲学进路》
2016-02-04殷融
殷融
(潍坊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潍坊 261061)
重返意识经验世界
——评《神经现象学: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哲学进路》
殷融
(潍坊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潍坊 261061)
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感,感受到自己是一种意识的统一体。然而,组成我们人体的基本元素与宇宙其他物质其实并没有本质不同,都要遵循同样的物理与化学定律。那么微观分子结构是如何让我们产生意识感受的?上世纪70年代,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涉足意识研究领域。基于唯物论与物理主义的传统认知科学认为,人类的主观意识经验是可以还原为客观生理结构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明晰大脑的物理状态及其神经机制,就能对应地揭示意识感受。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科学家对人类的大脑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我们如今已可以对人类很多复杂社会行为进行生理辨识,例如,5-羟色胺水平低会导致暴力行为,后叶催产素则是人们做好事的生物基础。然而,认知科学在“大脑如何产生意识”这一基本性问题上却出现了“解释的鸿沟”。虽然科学家发现了越来越多类意识感受的神经相关物 (如多巴胺产生兴奋、内啡肽产生愉悦),但是这些相关物也无法说明客观的生理变化如何导致了主观意识体验的出现。意识究竟是如何生成的?产生于大脑何处?又以何种方式显现?这一系列关于意识的疑问成为了认知科学研究领域的重大谜题。事实上,由于意识经验不能被拆解为各种感觉活动或神经机制的机械组合,因此,认知神经科学所秉持的客观研究法可能根本无法对意识的本质进行考察,认知科学家亟需吸取其他学科的力量。
在意识研究问题上,现象学天生具有与认知神经科学联姻的优势。一方面,由胡塞尔、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等人开创的经典现象学论证了意识经验具有主观性、整体性与不可还原性,这种对意识特征的描述恰巧对应了当代认知科学在意识研究方面遇到的难题。另一方面,现象学在意识经验的探索上有许多独特的方法论(比如悬搁、本质直观与现象学描述),这些方法可以帮助神经科学研究澄清概念、提出理论假设与阐释数据。因此,现象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合作有望为解决意识之谜提供新的出路。近十几年来,西方认知科学领域就诞生了这样一场融合了现象学与神经科学的神经现象学研究运动。其中,智利著名科学家瓦雷拉于1996年发表了《神经现象学:一种应对意识困难问题的方法论救治》一文,明确界定神经现象学的目的与立场、内涵与方法。此后,这一新的研究方向吸引了一批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的目光,学者们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神经现象学的理论与实验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尝试将现象学的还原、内省和沉思训练等第一人称方法与认知神经科学的第三人称方法相结合,以此探索人类的主观意识经验。然而,较之国外神经现象学研究的如火如荼,当前国内对于该领域的关注则存在明显不足,中文学术期刊极少刊载关于神经现象学的介绍或研究,相关著作更是绝难一见,对于神经现象学的全面引入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科研工作。
令人欣喜的是,陈巍博士著述的《神经现象学: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哲学进路》一书受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全额重点资助项目资助,即将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终于填补了国内在该研究领域上的空白。本书以50余万字的巨幅,对神经现象学运动进行系统地阐释与建构。世界著名脑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唐孝威院士与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朱菁教授联袂作序推荐,相信无论是哲学、心理学还是认知科学的学者都能从中获益。
本书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其中开篇部分(第1、2章)主要厘清了现象学运动的范畴与边界,追溯了神经现象学诞生的背景。该部分首先特别解释了为什么神经现象学是“一场运动”而不是“一门学科”,并强调神经现象学并不欲将现象学全盘自然化,而是要在认知科学对意识经验的研究中借鉴现象学的理论、概念与方法,正因如此,神经现象学具有问题导向的特征,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具体的研究领域。之后,陈巍博士从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等角度出发,对神经现象学内部做出了狭义神经现象学与广义神经现象学的区分,并辨析了两者各自的特点。在考察神经现象学的缘起背景时,本书则分别聚焦于西方现象学哲学及认知科学两大学科的演进进路,一方面回顾了经典现象学及现象学自然化运动的发展轨迹,阐述了这二者的主要理论内涵及其对神经现象学的启示;另一方面则梳理了当代认知科学在生命观、心智观及意识观等维度的发展与变革,特别强调了认知科学在意识研究问题上遇到的困境,由此区分出了西方现象学与当代认知科学这两股源流在神经现象学兴起中的作用,并表明了开展神经现象学研究的必要性与必然性。通过这一部分,读者可以对神经现象学运动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比较充分的了解。
本书第二部分(第3章)则系统论述了神经现象学的理论内涵,包括神经现象学的本体论立场、认识论立场与方法论立场。在本体论上,神经现象学坚持意识经验的主观性、整体性与不可还原性,认为意识经验是有机体的身体与外界环境复杂互动过程中涌现生成的。这一立场揭示了生命体或活体在心智中的基础作用,并强调了心智、身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前风行于认知科学领域的具身认知研究思潮就是这一立场的源流及具体体现。在认识论上,神经现象学遵循胡塞尔、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立场,尝试消解经验主义与理智主义所预设的那种认识活动与认识对象的二元对立,力图建立一种“中道认识论”。以经验主义与理智主义为代表的二元论在过去几个世纪内一直统治着认识论领域,认知科学受其影响在不自觉中也全盘接受了那种“非此(经验主义)即彼(理智主义)”的立场。神经现象学则拒斥二元论的妥协论调,试图在消除笛卡尔主义主客两分的前提下来重新认识心智的本质。在方法论上,神经现象学主张将第一人称方法与第三人称方法相结合。神经现象学一方面沿袭了现象学在探索意识经验时所采用的第一人称方法,并对其加以改进,以期获得更加精确与丰富的第一人称数据。另一方面,神经现象学也认可神经科学在探索意识经验时所采用的第三人称方法论,同时建议将其与第一人称方法论有效地结合起来。研究者可以将现象学方法“前载”于实证研究,使用从现象学分析中发展的洞见来建构实验假设、设计实验方案及训练被试,也可以将现象学方法“后载”于实证研究,为神经科学的实验发现寻找第一人称方法上的解释。神经现象学围绕意识经验问题,从生命与心智现象出发提出了中道认识论,又将其认识论主张融入到具体的意识经验研究之中,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有效贯通,显示出强大的解释力。本部分涉及到大量现象学、认知科学及神经动力学理论,陈巍博士在介绍时不纠缠概念,不刻意含混晦涩的术语,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清晰的神经现象学理论地图。
本书第三部分介绍了神经现象学的研究实例。陈巍博士按照研究对象(主体水平与交互主体水平)与研究领域(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不同将这些研究分为四类:主体水平上的意识研究、主体水平上的意识经验障碍研究、交互主体水平上的意识经验研究及交互主体水平上的意识经验障碍研究。其中,主体水平上的意识研究具体包括视知觉、内时间意识、自我觉知、自主感与拥有感等问题;主体水平上的意识经验障碍研究主要包括癫痫与幻肢的解释与治疗;交互主体水平上的意识经验主要涉及人类的“读心”机制,具体包括镜像神经元系统、动作识别、意图共鸣、共情、语言理解等问题;交互主体水平上意识经验障碍的神经现象学研究则主要涉及自闭症的成因与干预。这些研究贯彻了神经现象学的方法论原则,涵盖了现象学理论与实验证据之间的双向建构,既有严谨的自然科学实证支持,又渗透了深邃的现象学思辨,这进一步论证了神经现象学在化解意识经验及读心问题上的效力,同时也显示了神经现象学强大的应用价值及实用主义取向。通过这些实例,读者可以对神经现象学的具体研究领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此外这些实例也有助于深化读者对神经现象学理论体系的理解。
由这三大部分可以看出,本书的主体内容是对神经现象学概貌与基本框架的描述,但这并不仅是一项简单的介绍工作。由于神经现象学涉及多个学科及多个研究领域,因此神经现象学运动内部是一幅鸟集鳞萃、头绪繁杂的研究景象,初次接触神经现象学的研究者难免会有如坠五里雾中之感。而本书则对神经现象学的这一罅隙做了重要的梳理工作。从理论层面看,西方学者其实较少对神经现象学的整体理论基础进行论证,即便是这一运动最初的领导者瓦雷拉也只是设想了其宏观的学科框架。而陈巍博士则通过对诸多学者的观点进行分析,尝试提炼了神经现象学的理论内涵(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立场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具体研究层面看,虽然当前神经现象学研究与日俱增,但这些研究并没有被纳入一个完整的类型体系,陈巍博士提出的划分方式则有效地将分布在不同领域内、针对不同对象的零散研究有序地联系起来,最大可能地保留了同类研究的一致性与异类研究的差异性。这些工作为神经现象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科根基。此外,陈巍博士在书中对某些具体领域也提出了一些有原创性的理论,如读心的双重机制观、具身交互主体性、自闭症的原初交互主体性障碍理论等。这些观点将充实神经现象学的实体理论,有助于其未来学科体系与元理论的建构。
除梳理介绍之外,本书在结尾部分还对神经现象学运动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分析。陈巍博士以完全中立的视角,既肯定了神经现象学的学术价值,也指出了其局限之处。近年来,神经现象学的繁荣蓬勃彰显了其坚韧的跨学科张力与旺盛的生命力,但与此同时,该研究进路在学界也面临越来越多的争议。陈巍博士敏锐地捕捉到了神经现象学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了一一剖析。例如,从认识论角度看,神经现象学关于心智活动的“具身—生成观”常遭人诟病,尽管已有很多研究都证明身体可以影响人们的认知活动,但这并不等同于可以认定身体直接构成了认知活动本身。从方法论角度看,虽然一些神经现象学家提出了如何对现象学还原方法进行改进的设想,但这些方案在当前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此外,神经现象学所主张的将第一人称方法与第三人称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手段在具体操作上也存在着极大的难度。在实践中,无论是将现象学还原“前载”还是“后载”于神经科学实验,都很难在现象学数据与神经科学数据之间形成真正的、持续的互惠约束。因此,仅就目前研究进展来看,神经现象学还难以成为一剂破解意识之谜的灵丹妙药。
针对这些困境,本书为神经现象学运动未来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具体的研究展望。特别是在研究方法问题上,陈巍博士指出,未来的神经现象学研究需要积极吸纳最新的精密技术,利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与弥散张量成像等技术破解大尺度脑神经集群联动活动,探索意识经验的神经机制。与此同时,研究者也需要对第一人称方法的使用进行明晰的界定,如,究竟哪些研究主题更适宜于将研究者本人或被试作为现象学还原的实施者?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现象学的立场解释实验数据?如何进行明确的现象学还原训练?通过这些持续的努力,才能使神经现象学在方法论上的优势真正得以体现。
当然,作为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本书还遗留下了形而上学层面的意识困难问题,有关自然化的交互主体性纲领的建构也有待进一步地完善。不过,瑕不掩瑜,本书不仅为国内研究者了解神经现象学提供了可靠的导引,也为神经现象学运动未来的走向搭建了一副清晰的路线图,相信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中得到很多的学术启迪!
潍坊学院博士基金赞助项目(2015BS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13YJC720015)
殷融,男,讲师,博士。Email:yorkns@s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