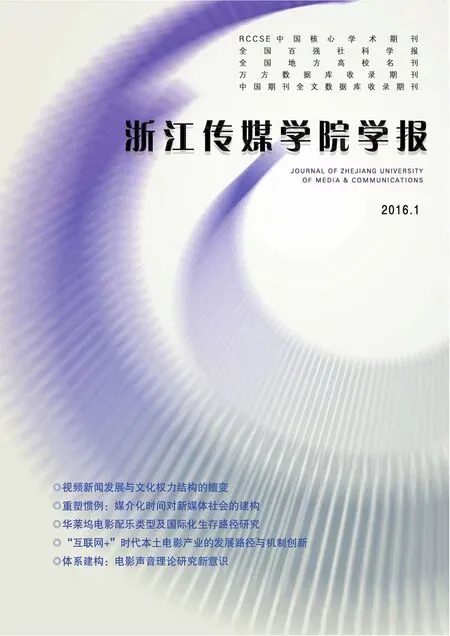“老片新映”:一种文化现象的审视
2016-02-04包磊
包 磊
“老片新映”:一种文化现象的审视
包磊
摘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老片新映”在网络与报纸中激起诸多的关注,却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和应有的探讨。文章以“老片新映”为关照角度,通过文化现象层面的扫描与电影发展史视域下的梳理,借助卢卡契的“意识形态的总体性”理论与杰姆逊“怀旧电影”的概说,阐释作为产业化运作过程中的商品,电影如何追踪与回应当下中国电影观众的审美文化心理。在此基础上,结合麦茨的电影机构的精神分析学说,从电影产业运作的总体性视界解释谁是“老片新映”的受益者;最终探究这种文化现象助力于重建中国电影美学传统的可能性。
关键词:“老片新映”;怀旧电影;产业化运作;美学传统
2014年10月24日,经社交网站上发起“还星爷当年的一张电影票”等活动之后,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系列终在20周年纪念时以修复版的形式再现于影院,用3000万的票房成绩完成了“‘回锅肉电影’的一次华丽转身”。随后,走进电影院的观众发现越来越多老片的身影:2015年1月8日,王家卫的心血之作《一代宗师》经重新剪辑后以3D的制式重见观众;同月15日,周星驰的另一经典巨制《功夫》也在10周年纪念之际以3D的版本“重见天日”;稍后,2月13日的情人节档期,陈可辛导演的华语片爱情经典《甜蜜蜜》经过修复音轨、提升至4K画质后二次上映;就连内地“贺岁片之首”也耐不住寂寞,《甲方乙方》和《不见不散》在2月6日以“买一赠一”的捆绑方式出现。这连串老片的持续上映一时间成为网络空间和平面媒体热烈讨论的话题,以致这类影片被比作“回锅肉电影”,甚至上升为一种电影文化现象。然而,这一文化现象却未能引起理论界的注目与探讨。
其实,将这类影片归为“回锅肉电影”并不恰切,毕竟回锅肉在回锅之前并不能称为爽口润肺的珍馐佳肴,但这些老片在此次上映之前已被公认为华语电影的经典之作。若将其称作“老片重映”或也是现象层面的曲解,毕竟这些老片是标榜3D、IMAX、4K画质、修复音轨等的重新剪辑的二次创作。从影像本体上来说,它们已经是对于原有影音素材与叙事理念的升华和超越。因此,对这一文化现象给定“老片新映”的概说似乎更为合理。但这种“老片新映”为何在此时集中呈现?它对应着怎样的中国电影文化现实?在产业机制与美学观念的互动中,它们又如何影响中国电影的未来走向?
一、现象溯源:“老片新映”的文化心理
从电影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老片新映”在中外电影中都有出现。1956年,伴随着“双百方针”所带动的社会文化意识的开放,一批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民族化经典之作曾在解禁后修复上映,“如《桃李劫》、《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创作者从本土上找到革命现实主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1]在“文革”结束后,“十七年”生产的633部影片的绝大部分也曾解禁开画。[2]如今,“老片新映”更常见于各大电影节,类似于“向经典致敬”的非竞赛单元(比如2015年4月16日—23日举办的第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就设有“评委会主席作品回顾”、“大师回顾”、“经典修复”、“获奖集萃”、“系列饕餮”、“多国风情”等多个单元展映老旧影片)。与国内“老片新映”的现象同步,美国本土出现“2014年,《阿甘正传》为纪念上映20周年以IMAX版本重映,《捉鬼敢死队》上映30周年纪念重映,《电锯惊魂》上映10周年重映”。[3]只是,上述这些现象与此番中国本土市场的“老片新映”现象的具体历史与文化语境确有不同。
就现实而言,对此番“老片新映”现象产生刺激的直接来源,是2012年《泰坦尼克号3D》在内地上映斩获的近10亿巨额票房,让所有的中国电影人既垂涎又兴奋。因此,寻找适当的经典影片借助科技的手段重新剪辑上映继而获得可观的收益,似已成为一条水到渠成的规范模式和达成路径。但正如现象学所示,“我们在开端的时候不能把任何认识当作认识,否则我们就不具有可能的、或者说同一的,充满意义的目的”。[4]细审内地“老片新映”现象,除了上述处于表层机制的商品因素之外,其内在的深层结构才是引人深思之处,即作为产业化运作活动中的商品——电影是如何追踪与回应当下中国大众审美文化心理的。
卢卡契认为,“一个观念是否是真理,取决于其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总体性的能力”[5],“‘整体性’在它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中是可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实际上组成了一个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内地的“老片新映”的文化现象,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它是意识形态的总体性效果的互文本:当前的人们停下来稍作沉寂,重新审视这陌生的现实和已消逝的美好过往。孤独而又焦虑的个体在回首往昔时,被社会现实带入怀旧的时代,而“老片新映”所对应的恰恰就是杰姆逊阐释的“怀旧电影”的文化现实。
“怀旧电影却并非历史影片,倒有点像时髦的戏剧,选择某一个人们所怀念的历史阶段,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然后再现30年代的各种时尚风貌”。[6]审视当下的华莱坞电影,怀旧风潮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弥漫影坛,并且明显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形式与风格:其一,校园怀恋与青春记忆的题材类型已经成了创作的显见形式。在2011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取得超高票房和良好口碑的示范效应下,《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同桌的你》、《匆匆那年》、《万物生长》等影片相继上映。它们都将共同的记忆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在校园爱恋的统照下讲述青春与成长的文化母题,用怀旧电影的形式引发一代人的情感与精神共鸣;其二,“老片新映”所对应的不仅是怀旧电影的概念,更是怀旧电影的超越。就怀念的历史阶段和影像叙事来讲,这些电影本身已是典型的怀旧影片:《大话西游》系列在时空穿梭中瞻顾五百年爱恋的前后两端,《甜蜜蜜》的叙事辗转于1986—1996年的大陆、香港、台湾和美国纽约,《功夫》将时空架构在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低层社区,《一代宗师》更是退守到上世纪中叶的香港武侠江湖。而利用“老片新映”的形式,将影片重新加工后,作用于刚刚获得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叠加经验的内地观众,更是怀旧中的怀旧。“怀旧电影的特点,就在于他们对过去某一种欣赏口味方面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非历史的,这种影片需要的是消费关于过去某一阶段的形象,而并不能告诉我们历史是怎样发展的”。[6](227)对比这些新映的老片,无论是《大话西游》系列、《甜蜜蜜》、《一代宗师》对于逝去的美好留恋、感伤和刻骨铭心的爱情的缱绻眷恋,还是《功夫》、《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对于庸碌人生中梦想达成的希图渴求,无不吐露出对于过去某个特定时代的双重怀旧。对应中国社会急速成长又怅然若失的总体文化现实,这种双重怀旧的经典影片也在同构着身处其中的观众审美心理。
上述老片之所以能够新映,除了怀旧电影的精神特质外,作为“被结构的多义体”,它们同样指涉着观众对那个被抽空了的现实的指认方式和想象性满足,如同缺席的在场和在场的缺席一样。不论是《大话西游》系列还是《功夫》的新映,它们都是周星驰新片缺席内地2014年度电影的已然存在——前者显现着对2013年《西游降魔篇》票房佳绩的移情作用,而后者则是3D技术与周星驰神话持续又必要的文化衍生品。《甲方乙方》与《不见不散》明显针对《私人定制》和《非诚勿扰》的“炒冷饭”式创作的回应。事实上,这两部影片的新映,和冯小刚本人并无任何关联,它只是精于运作的华夏影业公司对于观众感念此前冯氏喜剧带来的纯粹娱乐的及时把握。从前的平民冯小刚如今已变身为商人权贵,其电影的精神架构也从对于达成共识的平民意识的追认变成对普通人的颐使气指与刻薄嘲讽。而《一代宗师3D》和《甜蜜蜜》修复版则属于对当时爱情情节剧热潮的回应。当《致青春》、《匆匆那年》、《同桌的你》等纷纷以在场的方式熟练地复制有关青春和爱情的伤感模式时,它们的回归则可显示出另类模式的在场,只是缺席的永远都是过去。
由此,新映的老片在产业化的运作机制中,获得了观众自觉感知的经验层面的认同,完成了影片本体与观众审美心理层面上的文化重估和价值同构。
二、博弈:谁是“老片新映”的受益者
处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实境之中,“老片新映”的直接目的当然是投观众所好,借经典之名、以商业化的运作方式获取可观的票房收益。但由于老片的产生时间相对久远,其制片方与版权所有者几经变更,修复上映后票房收益的分配也存在各方的博弈。比如,《功夫3D》在上映时,版权所有者哥伦比亚公司宣称导演周星驰可以获得17.5%的票房分账比例,但事实证明,《功夫3D》的上映跟周星驰没有任何关系。而《大话西游》系列原是周星驰的彩星电影公司和西安电影制片厂共同摄制,但由于当年该片票房遭遇滑铁卢,直接导致了彩星公司的破产和香港版权的转售。[7]几经周折之后,这次《大话西游》系列的制片方已是大陆版权的所有者华夏影业公司。类似的情况也出现于其他几部新映的老片之中。那么,抛却这样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商业诉求,表象之下,谁才是影片的受益者?
“电影机构不单是电影工业,它还是一种内化于‘习惯于电影的观众’之中并使它们适应电影消费的精神机器。第二机构,即观众的元心理学的社会规则,第三机器则是电影批评、电影观念……电影机构的目的和效果,就是为了建立一种使观众自动光顾影院的机制”。[8]麦茨的这一理论在从电影精神分析的意念出发阐释电影机制构成的同时,也为电影工业的持续运转提供了总体性的视野。依此分析,新映老片的受益者大体包括作为外部电影机器的版权所有者、影片本身与导演,内部电影机器的观众,以及第三机器的电影观念。
就比较几部新映老片的票房收益与制作成本来看,几乎每部影片的新映,制片方都能获得可观的收益。与制作一部新片不同,这些老片基本上只是经过转制为3D/IMAX/4K/修复音轨后的重新剪辑。在国内,即便花费最大的3D转制技术,其成本也仅为600万,除此之外的成本可忽略不计(他们并不需要高昂的前期拍摄和制作费用,而宣发更多的是凭借痴情影迷的口碑营销)。这样看来,《大话西游》系列新映所获的2500万票房依分账比例,片方大有利润可图;《甜蜜蜜》修复版1194万的票房也让陈可辛再次破费的200万得以收回。《一代宗师3D》所贡献的6534万票房更让制片方博纳影业收获颇丰。如此,“老片新映”也为电影资本的持续再生产创造了优厚的前提。
但同样也应看到,如果对这些新映老片的票房成绩作一横向比较,即便是上述经典,其票房收益也有较大的差异。相比《一代宗师3D》534万的高额票房,十周年纪念版的《功夫3D》仅收获2543.2万的票房。《一代宗师3D》画质上虽不能媲美欧美的精良制作,但凭借重新剪辑后流畅的叙事结构也为影片徒增几分感动。而《功夫》的新映却因3D效果的差强人意和所谓重新剪辑的子虚乌有,不能让仅有的走进影院的影迷“足够陌生”,最终贻害的正是自己的商业利润。此中得失,令当下电影人与后来者警醒、反思。
而就作为经典的原文本与影片导演来说,他们同样也受益于新映的老片。因为“即便是经典,其存在方式也应当是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伴随着历史的行进和人类认识的深化,其具体作品中的确已被印证的受制于产生条件的那些僵化的形式和内容,是可以被改编乃至被解构的”。[9]通过技术手段的再造使影片超越了影像本体的存在获得崭新的技术程式和呈现意义,在经典的流动中给人以“意向性的体验”,在自我反思与拯救的心理投射中坚守精神的家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就是“老片新映”的基本价值所在。作为该片的导演,即便是没有直接参与票房的分账,新映的老片也在提示着他们缺席的在场,当观众感念于经典的再造之时,无形之中会对其将要上映的影片产生期待视野。
相对而言,观看这些新映老片的观众,最主要的还是曾有过初次观看经验的80后群体。他们之中,年龄较长者已从青年逼近中年,而年龄较小者也已到了结婚育子的新阶段。这一群体也是当下中国最具怀旧情结的“焦虑一代”:在度过无忧无虑与回身是梦的童年之后,他们大同小异的成长都被置放在急剧转型的社会阵痛之中。当他们凭借着一无所有的励志勇气与无知无畏的年少轻狂,肆无忌惮地冲撞于触手所及的规则和体制,终归头破血流之后,环顾四周,却无人能够捧出真心抚慰他们伤痕累累的内心深处。在苦闷、迷茫、于无声处哭泣之后,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特征和找寻信仰的价值坐标,正是进行自我救赎和回到精神家园的无奈选择。“电影作品与观众心理的关系是一种隐喻和换喻的关系,就是说,两者具有同一形式,电影作品是观众心理结构的倒影式摹本”。[8](9)这批新映的老片在平行时空中暗合这代人的心路历程,并以怀旧电影的形式投射出梦想与现实的距离。80后观众以此在电影院中再造白日梦,重新寻找生活下去的勇气。因此,观众也是“老片新映”的受益群体。
既然新映的老片对于制片群体、创作群体、受众群体来说都是有益的,那么,对于其所对应的产业化生产的投资、制片和发行来说,也都是有益的,这样就为其持续的再生产创造了条件,由此带来电影观念的革新。“老片新映”实际上已经证明急剧扩张的中国电影产业本身充满着多样性与丰富形式,代表着电影产业化进程中华莱坞电影生产与创作的另一种可能。
三、未来之路:重建中国电影美学传统的可能性
不可否认,这些新映的老片都是当代中国电影商业化进程中的经典之作,其本身的艺术理念、商业成就经过了消费文化和市场经济的检视能够重新上映,也说明其自身美学价值的充分被肯定。回顾历史,我们也能看到,即便是在中国电影黄金时期的三四十年代,《姊妹花》、《渔光曲》、《假凤虚凰》、《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也是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流传下来的经典,*这四部影片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史上,有记载的有过票房佳绩的影片:“(《姊妹花》)于1934年2月13日公映后,盛况空前,创造了在同一家影院(上海新光大戏院)连映60多天的惊人纪录”;“《渔光曲》公映……并出现了连映84天的卖座奇迹”——引自陆弘石.中国电影史1905-1949[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69-70.“《假凤虚凰》(在文华公司)商业上最成功,仅影院之首大光明电影院一地,观众就达16.5万人次,是该影院1947年的票房冠军,也是战后最卖座的华莱坞片之一”;“而《一江春水向东流》则创造了华莱坞片卖座的最高记录,从1947年10月到1948年1月,连映3个多月,观众达712874人次”。转引自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19-125.这些影片在当时与好莱坞电影的竞争丝毫不亚于现在。*据统计:1933年,华莱坞片84部,进口故事片431部,其中美国片有355部,占进口片数量的82%;1934年,华莱坞片86部,进口故事片407部,其中美国片345部,占进口数量的85%;1936年,华莱坞片43部,进口故事片367部,其中美国片328部,占进口数量的89%。美国电影以每年占进口片80%以上的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电影的放映市场,甚至决定着影院业的生计”。转引自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79.以此来比照,“老片新映”似在开辟重建中国电影美学传统的可能性之路。而在当下电影产业中,更应该诞生兼具商业价值与美学表达的经典作品。
但目前中国电影产业的最大症结就在于仅顾电影的资本收益所致的电影审美维度的缺失。当代西方美学在古典体系的三面坍塌之后,美的本质虽然趋于消散,但毕竟还在通过电影等艺术形式重建离散的审美心理。相比之下,中国社群受制于市侩气十足的“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完成对于美的本质的探寻;而在社会剧烈转型中,传统与现代的撕裂又在本体论的层面上消解着主体的审美心理。于是,处身其中的艺术必然失去了原有的中心结构与逻辑范式,趋于深度模式与历史意识的消解、虚无和平面化。表现在电影领域,就是综艺电影的出现。原本,《小时代》系列的无休止呈现,已经意味着虚拟的公共空间对于社会实体的更大程度的入侵以及对真实的人的存在状态的深度介入。而《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等综艺电影给观众所带来的仅是快感而非美感,“快感是审美的途径,美感才是审美的目的。须知,当观众过度的视听感官生理上快感得到满足之时,伴随而至的便是精神上责任感和反思能力的衰弱”,“失度的视听快感消解着精神意象的追求,无节制的刺激造成感性审美的失调”[9](315)。电影人应对与解决这场剧烈的精神危机的方式,将关系到中国电影的未来走向。
从中国电影历史形成的民族风格来看,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奠基时期,从来都是在商业电影的体制机制下,依循“儒道互补”的美学传统,在感性娱乐的基础上建构伦理教化观念、生发意味与况味。“中国古代美学对审美和艺术社会性的认识得力于儒家,对艺术本体特征的认识得力于道家。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起着抵制和克服道家虚无消极精神的作用,道家热烈向往自由的精神起着动摇和突破束缚个性的儒家礼法的作用”。[10]反映在电影传统中,中国电影既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传统、忧患意识与批判情怀的积极入世精神,同样也呈现出关心个体生命的实现、表现人生况味和心灵平静的出世情怀。
而《大话西游》系列、《功夫3D》、《一代宗师3D》、《甜蜜蜜》修复版等的上映都在致力于讲述一个感动人心的好故事,同时,又启迪着人对生存境遇的思考和对自由追求的探询。通过流动的美的画面获得身心两方面的愉悦,是电影所应追求的效果。给人以人生、历史的启迪,触动心灵的深层,让人在银幕前感悟到‘形而上’的某种‘意味’和‘况味’,也许是电影的境界。[10](100)这也同样印证宗白华先生所论艺术应“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11]以求达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四、结语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老片新映”从文化心理上追踪与回应了现时代中国电影观众的审美文化心理,并植根于电影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它不仅呈现出产业化生产中电影创作的新维度,表明扩张中的国内电影市场的无限可能性,也启示电影人应正视喧嚣与欲望带来的躁动和不安,在致敬经典、寻求创新中反思当下,在承继传统中重建中国电影的美学体系,直面未来。
参考文献:
[1]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1965)[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143.
[2]丁亚平.中国当代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17-18.
[3]李玉斌.老片重映,您会不会去捧场[EB/OL].www.http://times.clzg.cn/html/2015-01/22/content_481372.htm,2015-01-22.
[4][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M].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8.
[5][匈]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M].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
[6][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27.
[7]贵圈.经典老片如何再次走上大银幕[EB/OL].http://www.52rkl.cn/guiquan/1029454Q2014.html,2014-10-29.
[8][法]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M].王志敏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8.
[9]仲呈祥.审美之旅——仲呈祥文艺评论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215.
[10]史可扬.影视美学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2.
[1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0.
〔责任编辑:华晓红〕
中图分类号:J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6)01-0089-05
作者简介:包磊,男,电影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北京朝阳,10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