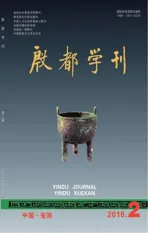婚姻内女性意识的衍化
——《手机》文本新释
2016-02-02陈国元
陈国元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婚姻内女性意识的衍化
——《手机》文本新释
陈国元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
刘震云的《手机》在通讯工具的统摄下以女性名字结构全篇。除伍月外,严朱氏等人均为婚姻中的女性。从表象观之,作品中“说话”的主体是男性,但其实作者言述的是说话方式与女性的关系。女性是现代性通讯工具发展下的受伤者、成长者、成熟者,最终成为过激者,在婚姻中的话语权随传话方式的改进被逼无奈地获具了充分乃至畸变的展现。因此本文以“说话”为媒介,以“手机”时代的于文娟和沈雪为中心,探讨了婚姻中女性意识的语言沿革方式,及它与现代性的联系。
刘震云;《手机》;女性意识
刘震云是名重视“说话”的作家,《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显豁地以“说话”为主题。《手机》的母题也是“说话”,但作者却将“手机”——结构全篇第二部分的通讯工具作为标题,势必包蕴更为内在的深邃思想。作品的文本时间应是第三章——人工传话、第一章——电话、第二章——手机,但若将“手机”置于第三章,“说话”的力度显然羸弱了。这种结构“标志着刘震云……把现实纳入历史的视野中的一种纵横向的观察,历史是渐渐淡出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隆起,就像山脉的高耸,它的渐渐隐没在地平线下的部分正是与‘历史’的相交点”[1](P379)。为凸显现实,作者重新安置了叙事时间。作为历史变迁到现实的物质代言,“手机”为通话工具的第二章被置于山峰部分。历史终归是人创造的,“手机”仅是服务于人的工具。在现实和历史的交错中,小说《手机》刻画的婚姻中的女性——于文娟、沈雪如同通讯方式的变革一样是发生质变最显豁的人群,因此也被置于最显赫的构架中。
整部小说三章均以女性名字命名,代表三个不同的通讯时代。女性与“说话”本应在《手机》中获具天然联系。但是“说话”的主体在作品中是男性,从开篇“严守一他爹不爱说话”[2](P4),到第二章严守一借助“手机”实施言语欺骗,再到第三章为传话给严白孩呼唤其回家成亲,“说话”的主角均为男性。从表象观之,女性成了被男性用“说话”牵动的附属品。但事实上,《手机》里婚姻中男性主体的说话方式并没有明晰的变化。虽然祖父、父辈未像严守一一样借用工具遮掩婚外情,笔者认为这仅是由于条件尚不具备而已,从第一章吕桂花带给少年严守一们的性幻想,到第二章严守一风花雪月般的浪漫史,再到第三章严白孩三兄弟争先恐后娶媳妇的积极性,男性在性别意识中未发生质变。而是婚姻中的女性在由通讯设备变化导致的男性的压力下表现出性格衍化,甚至最终形成裂变。
一、严朱氏:人工传话时代的“默片”
在严朱氏时代,女性对结婚对象没有表达权。她的第一个夫家虽是朱家主动提出断亲,却是严朱氏的叔叔因侄女受到虐待而主动的,是男性长辈保护孩子的行为。这种行为需要得到另一个男人的准许才能实现,所以“然后要了一纸休书,与杨家断了亲”[2](P237)。因此严朱氏可以先准备许配给严青孩,也可以最后嫁给严白孩。作品第三章虽以“严朱氏”命名,但她本人在婚姻中却是一场默片电影,没有丝毫自主权,相反“说话”的声音全然来自婆家:
严老有便知老朱有意。回来与老婆商量,老婆却有些犹豫:
“那妮儿我前年赶集时见过,见人不会说话,一头黄毛,不知道是不是傻。”
又说:
“再说她脚恁大,又不是白薯,无法用刀再削回去。”
又说:
“再说又是寡妇,像尿罐一样,别人都用过了 。”[2](P238)
这一段是以长辈女人的观点审视儿媳的选择标准,婆婆的立场全然置于男性衡量女性的审美准则之上。同时,严老有和老婆商量娶儿媳也是虚伪的,他的心中早已拟定好主意,与其说是商量,不如说是公布。
严老有照老婆脸上啐了一口:
“不爱说话怎么了?话能顶个球用!我话说了一辈子,不还是给人扛活?”
又说:
“脚大怎么了?脚大能干活。你倒脚小,连个尿盆都端不起。”
又说:
“寡妇怎么了?寡妇经过事,说话知道
深浅,不像你,一张嘴就是个二百五。”[2](P238)
严老有才是一个“经过事”的男人,能够打破传统眼界,按照务实的标准挑选儿媳。在男人做主的时代,严朱氏满足了严老有的眼光,因此在没有任何语言的前提下,顺利组建了婚姻。可见,在农业社会,妇女没有女性意识,即使有也难以实现,婚姻和爱情意识更无从谈起。如同阎连科在《坚硬如水》中刻画的程桂枝一样,为了“生娃儿”夫妻间便应直奔主题,任何多余的爱抚都被视为流氓行径。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女性意识在吕桂花时期有所觉醒。
二、吕桂花:电话时代的“情话”
历史进行到吕桂花时代,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同样作为经历过男性的女人,严朱氏因为有过正规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改嫁的过程中显得光明正大,而“跟镇上管广播的小郑睡过觉”[2](P11)的吕桂花则困难重重:“听说吕桂花要嫁过来,全村人都反对。连不大说话的严守一他爹,都气得涨红了脸,朝门框上啐了一口浓痰:‘我靠,那是破鞋!’”[2](P12)。幸运的是,作为当事人的牛三斤见了吕桂花之后坚持己见,成全了这场婚姻。与严朱氏不同,吕桂花出场后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谁到镇上打过电话?跟我到镇上邮局去一趟”[2](P13),于是有了乘汽车四十里打一个电话出场,仅仅传递了一句话——“最近你还回来吗”[2](P24)。原本夫妻间的私事,在电话时代被矿工们传唱成一首歌。
吕桂花是1960年代的先锋女性,不顾忌道德准则任凭情感流动,甚至忽略理性与有家室的小郑纠缠不清。可以说,如果在发达的手机时代,她或许就是伍月一样交际花似的人物。与伍月不同的是,她置身于婚姻并得到幸福。在婚姻的呵护下,觊觎她的男性只能束缚欲望。虽然长时间与丈夫身居两地,但是她并没有处心积虑的怀疑丈夫是否对她有不忠的行为,而是更多言说思念。在婚姻中,吕桂花勇于袒露自我意识,虽然最终成就了一个笑话,但充分体现了女性的表达欲。排除吕桂花婚前的道德性错误,婚姻中的她较之严朱氏成熟了很大一步。她借用“电话”这一工具,以语言作为成长标志,自己也成为历史沿革的招牌。她不仅属于自我,更代表一代女性在婚姻中如何通过“说话”讲述自我意识。因此“电话”仅是婚姻中女性成长表现借助的外在工具,女人内在的话语权才是真正在婚姻中发生变化的产物。
三、从于文娟到沈雪:手机时代的“手雷”
到了“手机”时代,于文娟——婆婆喜欢的传统型贤妻良母成了沟通严朱氏、吕桂花与沈雪在婚姻中锐变的过渡地带。严守一“找她是因为喜欢她不爱说话,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还有脸上浅浅的笑容”[2](P40)。然而在消费、传媒时代,夫妻间的沟通不能像东西的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中那样得到实现了,况且东西的小说之所以没有语言是生理条件所限的被逼无奈。于文娟和严守一的生活在结婚十年后因无话可说而变得新鲜感消失殆尽。这种无语感从很大程度上源于严守一在现代性生活中的疲倦,因为于文娟本来就是沉默寡言的人,而她喜欢严守一的地方在于后者与之互补——“说话逗”[2](P40)。作为名流,严守一“在电视上天天演自己,在生活中就不愿再演了”[2](P47),并最终影响了夫妻间情感沟通。现代生活是他们婚姻死亡的罪魁祸首。然而严守一并不能心甘情愿在静默的冷宫中独善其身,多次出现婚外情,与之交往最缠绵的是伍月。与伍月在一起最“解渴”的原因是“在整个过程中,伍月嘴里都在说着世界上最脏最乱的话。严守一被她勾的,也把心底最隐秘最脏最乱平时从无说过的话都说了出来。……严守一第一次知道了脏话的作用,它还能使人脱胎换骨和使心灵得到净化”[2](P57)。从精神分析层次看,伍月适合严守一是顺理成章的。吕桂花是少年严守一的性启蒙者,她“眼是细眼,像小羊,半睁半闭,老蒙着,但偶尔睁开,……十二岁的严守一,魂儿就被她勾了去”[2](P12);而伍月,“最勾人的是她的两只细眼,老蒙着,半睁半闭;偶尔睁开,看你一眼,就将你的魂勾了去”[2](P55)。虽然在弗洛伊德的视域内,童年经验被定义为五岁以内的体验,但通过刘震云的描写,俨然严守一的少年经验成为影响他潜意识的择偶标准。“潜意识藏有我们童年的大略记忆……它还包括我们自己感觉得到的秘密、怨恨、爱以及某些强烈而原始的热情和欲望。”[3](P22~23)伍月是严守一对少年时代吕桂花的认同。虽然严守一依照传统标准与于文娟结为连理,但贤良淑德的于文娟明显无法满足严守一释怀压抑的方式,因此成为婚姻中的受伤者。暴露婚外情的导火索是具有时效性的“手机”。在人工传话和初有电话的年代,严守一自圆其说的谎言无法被轻而易举地戳穿,但在“手机”时代却变得破绽百出。在极端激愤下,于文娟脱胎换骨般发生锐变,她:
推开严守一,突然爆发了,嘴像机关枪,乱豆一样说了一阵:
“严守一,我刚才已经算过了,我跟你已经十年零三个月了,我嫁你的时候二十六岁,现在已经三十六岁了,……我说你这么多年跟我没话,原来你早就在外边有人了,你跟我没话你可以告诉我,没想到你一直在和别人说话,你乱搞女人我不生气,可你和别人一条心时你这是在乱搞我你知道吗?我一想到你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还不知怎么说我呢……”
因为于文娟在生活中说话从来都是慢条斯理,没说话先笑,现在突然改变了语速,把严守一吓懵在那里。
虽然于文娟并没有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中静珍和静宜的口才,但由于原本静寂寡言的性格,使这段话的震慑力绝不次于雷霆万钧。如果说“手机会变成手雷”[2](P104~105),此刻的于文娟就是手雷爆炸。荣格认为:“妇女在精神上被丈夫抑制,丈夫在感情上被妻子控制,……我们将其描述为‘被控制’者和‘控制者’难题”[4](P190),“控制者”,即丈夫在中年的时候,由于人格上分裂的天性:
心中对统一和完整感的盼望就越持续。……他开始意识自己是在寻求完满,追求自己一直缺乏的满足和完整感。对被控制的一方来说,这只是证实了她一直为之痛苦的不安全感;她发现显然属于自己的房间里居然住着其他不受欢迎的客人。她对安全感的渴望落空了,失望感促使她退向自我。只有在绝望和强烈的行为之下,她才可能成功地令伴侣让步屈服,并迫使对方承认他对完整性的渴望只是孩子气或病态的幻想。[4](P191)
在作品中,严守一比意识幻想走得更远,在有话无法说的压力下,因为寻觅到可以让他痛快淋漓讲脏话的人,所以屡次身体出轨。这成为于文娟难以容忍并最终逼迫她做出以离婚为强烈反抗的举动。的确,“于文娟是传统的,也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她的冷漠与坚强表征了现代女子与男性争取平等的家庭地位的意识与决心”[5](P346)。
可以说,于文娟在婚姻的自我保卫战中表现得刚刚好,既通情达理又捍卫自己在婚姻中的地位,是理智与情感的综合体。她的独立意识和果敢性格避免了自己在婚姻中继续受伤。因此,女性意识在于文娟身上表现的是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是机关枪似的、连篇累牍般的“说话”。她在婚姻内充分表达自我意愿,拥有独立意识而拒绝背叛,敢于在受到伤害后坚决说“不”。
在婚姻中最终全然走向性格裂变的不是于文娟,而是沈雪。因为她是严守一选择的第二个结婚对象并已与之同居,所以我们粗略地将之归为婚姻中的女性。沈雪出场时是以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冷美人女教师姿态现身的,一个缺乏社会经验并钟爱行为艺术和实验话剧的较为简单的女孩。她吸引严守一的地方在于“她一张口就傻不愣登,句句让人好笑”[2](P80)。弗洛伊德认为追求“享乐原则”是人潜意识诉求的“最高指南”。沈雪的快乐天使形象无疑对男性有磁力。所以严守一试图与之经营婚姻,但这并不能绝对抑制他再次燃起婚外情。同时由于于文娟出人意外地生了一个男孩儿,严守一对沈雪的谎言比对于文娟的有过之而不及。纯稚的沈雪最初对严守一的谎言深信不疑,然而她毕竟不是《红楼梦》中的傻大姐,阴差阳错地阅读了伍月发给严守一具有暧昧性的短信后,沈雪对严守一的信任底线崩溃了,以致最后变得尖酸刻薄、蛮不讲理。本来她是从事文明职业的教育者,最终却化作了不讲理的泼妇,乃至于无法相信严守一诉说的真情。当严守一说“我实话给你说”时,沈雪像抓住证据一样回应道:“你现在才给我说实话,那你以前跟我说的都是假话吗”[2](P147)。她变得和费墨的老婆李燕一样对严守一的生活产生了任性地联想。费墨的婚外情却使沈雪产生了对严守一连珠炮似的攻击:
“……你把照片和存折放到费墨那里,让人家怎么看我?”
……
“我说的还不是照片和存折的事,我说的是,昨天你为什么替费墨撒谎?”
……
“我说的也不是你替费墨撒谎的事,我问你,昨天在火车站,你为什么关机?”
……
“你单是昨天晚上没开机吗?你有好几天都关着机,要么就是不在服务区,你干什么去 了 ?”[2](P192~193)
原本因为“说话”可以给严守一带来幸福感的沈雪被逼成了曹禺的《雷雨》中繁漪式的凌厉的女人,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阁楼上的疯女人”式的人。火柴燃烧时伴着她的怒火,火柴熄灭时扑灭的是她的理智。单纯的沈雪成了歇斯底里的泼妇。
婚姻中的沈雪不是成熟,而是因思想过激而不可理喻。沈雪和于文娟一样均为毁坏婚姻的执行者。从表面看来,直接原因是男性在婚姻中的不忠行为,导火索是“手机”揭发了谎言。然而是否就应操持女权主义的利剑将男性视为婚姻中的刽子手呢?导致女性在婚姻中衍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结语
看似一本正经,甚至不时劝说严守一保守婚姻道德的费墨在出轨被捉之后说:“还是农业社会好哇。……那个时候,一切都靠走路。上京赶考,几年不归,回来你说什么都是成立的。……现在……近,太近,近得人喘不过气来!”费墨所谓的农业社会的优点似乎是因为时间慢下来所以成全了谎言,从另一侧面理解则是现代生活中,夫妻之间需要独立的空间和相对的距离感,不要彼此作对方全知全能的上帝。但这并不能说明从农业社会到消费时代男性比女性所需的空间更大,或许因为男性比女性参与社会的可能性更大,“说话”的机会更多所致。于文娟可以因为嫌弃手机脏而拒绝使用,但是严守一离开手机一天便未能及时接到奶奶病重的噩耗。因此,不能像剖析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一样认为是污浊的男性导致婚姻中女性性格裂变的原因之一。在农业社会,恰如严守一在主持节目时被采访的大爷坦白在谈恋爱时只说过一次谎一样,谎言并非集体无意识般独属于男性,而是男性更多参与现代生活并迫不得已产生难以释怀的畸变,在新鲜感全然泯灭之后,在“手机”时代为婚姻带来预警信号。因此,《手机》内婚姻中女性意识的衍化过程是现代性引发的性格裂变。
或许刘震云并非有以《手机》为媒介捍卫女权的意识,但在文本中渗透着以婚姻中女性意识变迁为中心的现代性变革。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女性随着历史的现代化变革拥有了更宽泛的婚姻表达权却最终失去了婚姻?能与严守一始终如胶似漆的俨然是伍月,距离和偷来的自由似乎让男女关系更加如沐春风,因此现代性时代婚姻中的夫妻间如何把握交往的距离和尺度?这似乎是另一个学科研究的话题。
[1]郭宝亮.文化诗学视野中的新时期小说[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2]刘震云.手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3][美]约瑟夫·洛斯奈著.郑泰安译.精神分析入门——150个问题的解说与释疑[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
[4][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陈俊松,程心,胡文辉译.人格的发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
[5]黄怀平.三种存在方式的共现——电影《手机》的女性主义文学阐释[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1).
[责任编辑:舟舵]
I206
A
1001-0238(2016)02-0085-04
2016-03-02
陈国元(1984-),女,黑龙江省绥化市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