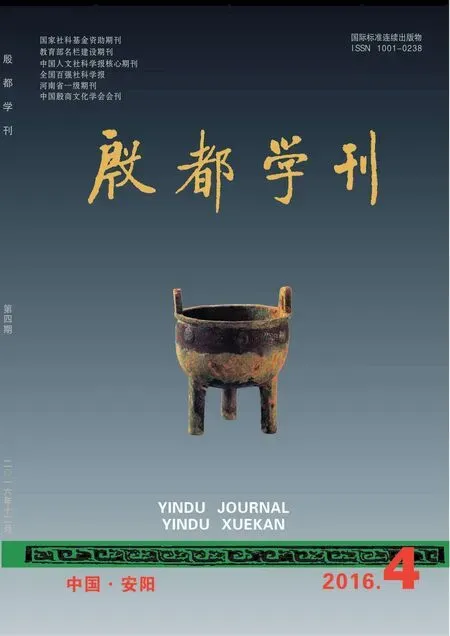《西厢记》中的“X-儿”形式考察
2016-02-02史翠玲
史翠玲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西厢记》中的“X-儿”形式考察
史翠玲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X-儿”是汉语中一个重要的语言现象,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其中对不同历史时期“X-儿”形式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西厢记》中“X-儿”形式共出现404次,出现频次高,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时“X-儿”形式的运用状况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
《西厢记》; “X-儿”形式
一、引言
“X-儿”形式虽然产生时间不是很长,但却是汉语中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因此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以往的研究中,前人在讨论“X-儿”的语言性质时,由于关注点不同,对儿缀、儿尾、儿化等术语的含义及其关系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为方便讨论,笔者认同曹跃香[1]、李巧兰[2]等人的做法,从形式入手,将其统称为“X-儿”现象。
以往对“X-儿”现象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且普、方、古三个角度均有涉及,但总体来说,共时观察多,历时研究少。然而共时平面的“X-儿”现象是不同历史阶段发展演变的结果,只有对各个历史时期“X-儿”形式的使用面貌进行全面考察,才能对其发展史有更为清楚的了解,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现代汉语共时平面中的“X-儿”现象。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有人在做。学者们借助对历史语料如变文、佛经、话本、杂剧、小说等的考察,剖析“X-儿”形式在某个或某几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面貌,并在此基础上,梳理该形式发展演变的线索。
杂剧代表着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反映近代汉语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了解当时语言运用情况的重要窗口。作为元代杂剧的代表作,《西厢记》是值得关注的一部重要作品。然而,笔者发现虽然学界对该作品开展过许多方面的研究,但针对其语言使用状况所做的研究却不多,针对某种语言现象进行细致研究的更是少见,其中对“X-儿”现象进行全面、深入讨论的文章笔者还没有看到。
本文对《西厢记》中的“X-儿”形式进行了穷尽性考察。据统计,该形式共出现404次,使用频次高,且表现形式丰富,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笔者认为对其进行分析,可以管窥当时“X-儿”形式的发展面貌,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多可供参考的资料。
二、本文的理论依据
前人在探讨“X-儿”形式中“儿”的性质时,使用的术语略有区别。王力[3]、高名凯[4]、吕叔湘[5]称之为词尾(或后加成分)。竺家宁[6]将“儿”后缀与“儿”词尾等同看待。在现代汉语中普遍将其称之为“儿化”。由此可见,对“儿缀”、“儿尾”、“儿化”这些术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笔者认为,要对语料中“儿”的具体使用情况进行判定,首先要明确“儿”的性质,理清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
“儿”的语言性质历来是争论的一个焦点。前人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儿”是不是语素;第二,“儿”是什么性质的语素。影响比较大的观点有三种:
第一,“儿”是后缀语素。支持者有赵元任[7]、朱德熙[8]、竺家宁[6]、邵敬敏[9]等。这是现在最通行的观点。
第二,语音节律说。李立成认为“‘儿化’纯粹是一种语音节律现象”[10],因此不能将其看作唯一的不成音节的构词后缀语素。葛本仪[11]也认为“儿化”只是一个音节中发生的音变,不能将其作为独立的后缀语素看待。
第三,两性说。该说法不但承认了“儿”的语素地位,而且将“X-儿”中的“儿”分成了两种:构词成分和构形成分。高名凯[4]提出应将“白面儿”、“劲儿”中的“儿”与“轻轻儿”、“脸盆儿”中的“儿”区分开来,因为前者加上“儿”后词汇意义发生了变化,而后者并没有构造新词。
刘雪春[12]赞同高名凯的说法,认为儿化在词中起两种作用:第一,构成新词;第二,增加或改变原词的附加意义。在此基础上,她提出,“儿化实际上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语素,一个是后缀,一个是词尾。”[12:15]其中“儿缀”可以构成新词,也可以表示附加性的词汇意义,而“儿尾”只改变词的附加意义。因为“儿”也记录词根“儿”,如“健儿”、“男儿”等词中的“儿”,所以她进一步指出,“儿”记录了词根、词缀、词尾三种不同的语素。
笔者认为要全面了解某一时期“儿”的使用情况,应将文本中出现的所有“X-儿”结构纳入考察范围,其中不仅应包括刘雪春区分出的“儿缀”和“儿尾”,也应包括她顺带提及的词根语素“儿”。目前笔者所看到的文章在分析语料时将这三者,尤其是具有构词作用的“儿缀”和具有构形作用的“儿尾”混同在了一起,将二者统一称为“儿缀”。这样的处理办法相对来说更容易操作,因为只要将具有实在的词汇意义的词根语素“儿”区分出去就可以了,但笔者认同高、刘二人的说法,认为在“X-儿”结构中,作为构词成分的“儿”和作为构形成分的“儿”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对其加以区分。
本文在分析《西厢记》中的“X-儿”结构时,将其中的“儿”分为词根语素、词缀语素、词尾语素三类,尝试分别对其进行考察。当然,这首先要涉及到分类标准的问题。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提取作为“词根语素”的“儿”相对而言更为容易,因为与“儿缀”和“儿尾”相比,它具有实在的词汇意义,而后两者主要附加在词根词素上,意义相对空灵。
确定“儿缀”和“儿尾”的区分标准时,笔者结合了刘雪春[12]和葛本仪[13]的观点:第一,“儿缀”与其所依附的词根语素构成新词,而“儿尾”只改变词的语法意义或增加其附带的色彩意义,不产生新词;第二,“儿缀”所依附的词根语素可以是可成词语素,也可以是只能用于构词的非词语素,而“儿尾”所依附的词根语素变化前都是词;第三,如果“儿”在其他音节后自成音节,可作后缀语素看待;第四,“儿缀”与其所依附的词根语素的组合具有封闭性,故词典会收录,而“儿尾”与其所依附的词根语素的组合具有开放性,无法一一列举。
三、《西厢记》中“X-儿”形式考察
笔者对《西厢记》中的“X-儿”形式进行了穷尽性考察,统计结果显示,该形式共出现404次,其中部分词语如“简帖儿”、“孩儿”等重现率达一二十次。“儿”的使用不仅丰富了《西厢记》语言的表现力,对其进行分析,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X-儿”这一语言现象的使用面貌。
(一)词根语素“儿”
词根语素通常也称词根。它具有实在的词汇意义,是组成新词的主要部分,同时也是新词词汇意义的主要承担者。“儿”的本义是“小儿”。王力(2011)指出,凡是没有脱离“小儿”这一实在意义的都不能称为“词尾”。王力所说的“词尾”即“词缀”。
《西厢记》中“X-儿”形式中有一部分“儿”仍具有词根语素的性质,是整个“X-儿”结构的意义承担者。
1.保留本义,表示“年幼的人、小孩子”
(1)因俺孩儿父丧未满,未得成合。
(2)先夫弃世之后,老身与女孩儿扶柩至博陵安葬。
(3)因丧事,幼女孤儿,将欲从军死。
《说文解字》对“儿”的释义为“孺子也。从儿,象小儿头囟未合。” 也就是说,“儿”的本义是“小孩子”,如“婴儿”、“儿童”中的“儿”。上面三条语料中“儿”都具有实在的词汇意义,指小孩子。这些词中“儿”的词义并未发生虚化,构成新词时是意义的承担者,因此属于词根语素。
2.指“年轻的人”,多指青年男子
(1)今者回来,本待做亲,有夫人的侄儿郑恒,来夫人行说道你兄弟在卫尚书家作赘了。
(2)时乖不遂男儿愿。
以上两条语料中,“儿”使用的虽非本义,但语义并没有虚化。它作为中心语,与前面的词根语素“侄”、“男”组成了偏正式复合词,并受其修饰。
3.表示某类人
他出家儿慈悲为本,方便为门。
“出家儿”义为“出家人”。“出家”是用来修饰“儿”的,“儿”在这里的意思是“……的人”,具有实在意义。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出家儿”指的是剧中的长老法本。红娘对他给予男女主角的帮助进行了肯定,所以该称呼应无鄙视义,但“儿”的引申义具有“小”义,用“出家儿”称呼一个寺院长老,并不够尊重,是一种很口语的说法。
(二)词缀语素“儿”
1.人名/表人名词+“儿”
(1)从到京师,思量心旦夕如是,向心头横躺着俺那莺儿。
(2)稔色人儿,可意冤家,怕人知道,看时节泪眼偷瞧。
一般认为“儿”作为词缀,起初用于指小字或小名。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今天。语料(1)中“莺+儿”组成了用于人名的专有名词,“儿”应视为词缀。语料(2)中“儿”附着在词根语素“人”后,构成新词,用于称呼情人,因此也应视为词缀。
2.动植物名词+“儿”
(1)劳攘了一宵,月儿沉,钟儿响,鸡儿叫。
(2)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
(3)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得媚。
以上语料中,“儿”附着在表示有生命的事物的名词之后,但同时并不指这类事物的初生者,因此,“儿”应当视为词缀。
3.人体部位名词+“儿”
(1)他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
(2)想着他眉儿浅浅描,脸儿淡淡妆。
(3)我知他乍相逢记不真娇模样,我则索手抵着牙儿慢慢的想。
除以上语料外,文中另有“手儿”、“脚儿”、“腿儿”等词语。这些词中的“儿”已经脱离了本义,且无所谓初生与否,具有明显的词缀性质。
4.无生命体名词+“儿”
(1)老妇人手执着棍儿摩挲看,粗麻线怎透得针关。
(2)门儿外,帘儿前,将小脚那。
(3)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搵帮重重迭迭的泪。
“棍儿”、“门儿”、“车儿”、“衫儿”等词都属于无生命体,无所谓初生非初生,且自成音节,因此笔者将其归入了“儿缀”。
5.抽象名词+“儿”
(1)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得步香尘底样儿浅。
(2)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扭捏着身子儿百般做作,来往向人前卖弄俊俏。
(3)你看我姐姐,在我行也使这般道儿。
“样儿”、“像儿”、“性儿”、“道儿”分别义为“样子”、“容貌姿态”和“诡计”,也就是说“儿”与其所附着的词根语素共同构成了新词,因此属于构词成分。
6.自然现象名词+“儿”
(1)月儿,你团圆呵,咱却怎生?
(2)风淅淅雨丝丝,雨儿零,风儿细,梦回时,多少伤心事。
“儿”附着在“月”、“雨”、“风”等表示自然现象的名词后,自成音节,故本文将其归入了后缀语素。
除附着在各类名词后以外,“儿”作为构词成分还可以跟在以下词类后:第一,“动词+儿”,如“画儿”、“遭儿”等;第二,“形容词+儿”,如“庞儿”,第三,“数量词+儿”,如“一点儿”、“半星儿”、“两口儿”等。
另有一例较难归类,单列于此。“好教我去住无因,进退无门,可着俺那埚儿里人急偎亲?”此处“那埚儿”、“那埚儿里”同义,指“哪儿”、“哪里”。作者在古籍库中查到该说法最早产生于关汉卿的《陈母教子》。“儿”在该词中是作为构词语素存在的,并非可有可无的成分,因此属于词缀语素。
(三)词尾语素“儿”
1.指人
(1)一个小厮儿,唤做欢郎。
(2)痛煞煞伤别,急煎煎好梦儿应难舍;冷清清的咨嗟,娇嘀嘀玉人儿何处也!
“小厮”一词义为“未成年的男性仆从”,“玉人”在此处则是对所爱者的爱称。“儿”只是改变了这两个词的附加意义,为其增添了小称或爱称色彩,因此属于构形成分。
2.动植物名词+“儿”
(1)休教那淫词儿污了龙蛇手,藕丝儿缚定鲲鹏翅,黄莺儿夺了鸿鹄志。
(2)夫人怕女孩儿春心荡,怪黄莺儿作对,怨粉蝶儿成双。
(3)放时节须索用心思,休教藤刺儿抓住绵丝。
“藕丝儿”、“黄莺儿”、“粉蝶儿”、“藤刺儿”等中的“儿”并非构词形态,因为它们并未因后加“儿”而产生新词,加“儿尾”前后的两个形式只是同一个词的两个变体。
3.人体部位名词+“儿”
(1)今日多情人一见了有情娘,着小生心儿里早痒痒。迤逗得肠荒,断送得眼乱,引惹得心忙。
(2)且休题眼角儿留情处,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
(3)拂拭了罗衣上粉香浮涴,只将指尖儿轻轻的贴了钿窝。
《西厢记》中表身体部位的词语后附儿尾的情况很多,除了语料中的用例以外,还有“心坎儿”、“身躯儿”、“眼睛儿”、“眼皮儿”、“耳朵儿”、“口儿”、“手掌儿”、“指头儿”、“柳腰儿”、“脚尖儿”等。毫无疑问,“身躯”、“眼角”等词语与“儿”搭配在一起后,词汇意义并未发生改变,只增添了亲切、随意的色彩,使文章用词更为通俗、自然,具有生活气息,因此“儿”是构形语素。
4.无生命体名词+“儿”
(1)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儿前面。
(2)我将这纽扣儿松,把搂带儿解;兰麝散幽斋。
(3)将简帖儿拈,把妆盒儿按,开拆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
“栊门”、“纽扣”、“简帖”等词语后附“儿”时没有产生新词,变化后的形式只增加了随意、口语等色彩意义,因此“儿”属于构形语素。
5.抽象名词+“儿”
(1)业身躯虽是立在回廊,魂灵儿已在他行。
(2)把似你休倚着栊门儿待月,依着韵脚儿联诗,侧着耳朵儿听琴。
(3)他……腰如嫩柳,俊的是庞儿,俏的是心,体态温柔,性格儿沉。
“魂灵”、“韵脚”、“性格”等词后的“儿”可加可不加,加与不加的区别只在于色彩意义稍有不同,基本词义没有发生改变,因此“儿”也是构形成分。
除以上几类名词外,表自然现象的名词后也有加儿尾的情况,如“夜凉苔径滑,露珠儿湿透了凌波袜”中的“露珠儿”。
词尾语素“儿”除了跟在名词后以外,还常见于数量词和动词后,具体用例如下:
6.数量词+“儿”
(1)大人家举止端详,全没那半点儿轻狂。
(2)孩儿有一计,想来只是我与贼汉为妻,庶可免一家儿性命。
(3)凭着你灭寇功,举将能,两般儿功效如红定。
7.动词+“儿”
(1)老夫人转关儿没定夺,哑谜儿怎猜破;黑阁落甜话儿将人和,请将来着人不快活。
(2)我则道拂花笺打稿儿,原来他染霜毫不构思。
(3)至如你不脱解和衣儿更怕甚?
上述语料中,“儿”均为构形语素。此外,“儿”也有后附于副词、形容词的现象,如“争些儿”、“悄声儿”等。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西厢记》中,“儿”尾也有后附于后缀“子”的现象,如“扭捏着身子儿百般做作,来往向人前卖弄俊俏”、“打扮的身子儿乍,准备着云雨金巫峡”中的“身子儿”。“身子”是一个词,据笔者考察,在同一时期,相同的意思也可以用“身儿”这一说法。此处,“儿”后附于“身子”之后,不自成音节,于词汇意义并无改变,且含义更为虚化。
四、《西厢记》中“X-儿”的使用情况分析
《西厢记》是元杂剧的代表作品,语言属于近代汉语。据前人研究,当时“儿”的使用范围已经很广了,加之作者王实甫是北方人,因此文本中“X-儿”形式出现的频次比较高。
数量上,《西厢记》中“X-儿”形式共出现404例,其中有词根语素“儿”29例,词缀语素“儿”168例,词尾语素“儿”207例。
从表现内容上看,“X-儿”中的“X”涉及人、动植物、人体部位、常见物质、抽象事物、动作、状态等多个方面。此外,《西厢记》中还出现了双词缀现象,“儿”可以后附于词缀“子”后。
从与词类的具体组合情况上来看,词尾语素“儿”的组合范围更广一些,除了可以与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搭配外,还可以与副词和词缀“子”搭配,而且,它与数量词的组合能力明显强于词缀语素“儿”。
通过考察,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西厢记》中“儿”仍有本义用法,表“小儿”义,如“孩儿”、“女孩儿”,但也有引申用法,如“男儿”、“侄儿”、“出家儿”等。在这些表人名词中,“儿”仍有实在意义,属于词根语素。
第二,“X-儿”形式可以用以指称动植物,如“马儿”、“猫儿”、“鸡儿”、“黄莺儿”、“粉蝶儿”、“树儿”、“花儿”、“藤刺儿”、“柳叶儿”等。一般认为动植物后的附加语素“儿”是由表示鸟兽虫类初生者的“儿”发展而来的,有表示“幼小”、“形体小”等含义。但从例词中可以看出,《西厢记》中的附加语素“儿”不仅可用于指称形体小的动植物,如“鸡儿”、“柳叶儿”等,也可以用于指称“马儿”、“树儿”等形体大的动植物。这是“儿”语义虚化的表现。
第三,《西厢记》中附加语素“儿”广泛用于人体部位名词和无生命体名词之后,使用范围很广,如“眉儿”、“袜儿”、“车儿”、“泪珠儿”等。在这些结构中,“儿”的“指小”意味仍然比较常见,如“袜儿”、“针儿”、“泪珠儿”等,但同时,“儿”也可用以附加于形体较大的名词,如“车儿”、“房儿”、“墙儿”等。这也是“儿”的语义发生虚化的一个表现。
第四,“儿”可后附于抽象名词、数量短语,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如“模样儿”、“性格儿”、“一团儿”、“两遭儿”等。
总的来说,《西厢记》中“儿”的主要用法已经不是指人,“X-儿”形式的使用范围很广,表达的意义也很宽泛,其中大部分“儿”的意义已经明显虚化,与之相伴而行的是,“儿”的语音已经发生变化,对前字音节的依附性变强,不少已经失去了独立音节,形成儿化韵,如“身子儿”等。
[1]曹跃香.儿化、儿尾和儿缀等术语在不同平面上之转换使用——兼论“X儿”的规范问题[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101-104.
[2]李巧兰.河北方言中的“X-儿”形式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2007.
[3]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 2011.265-268.
[4]高名凯.汉语语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03-105.
[5]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11-12.
[6]竺家宁.中古汉语的“儿”后缀[J].中国语文,2005,4:346-353.
[7]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80-81.
[8]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0-31.
[9]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第二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17-118.
[10]李立成.“儿化”性质新探[J].杭州大学学报,1994,24(3):108-115.
[11]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54-56.
[12]刘雪春.儿化的语言性质[J].语言文字应用,2003,3:15-19.
[13]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71-108.
[责任编辑:邦显]
2016-08-19
史翠玲(1985-),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H146
A
1001-0238(2016)04-009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