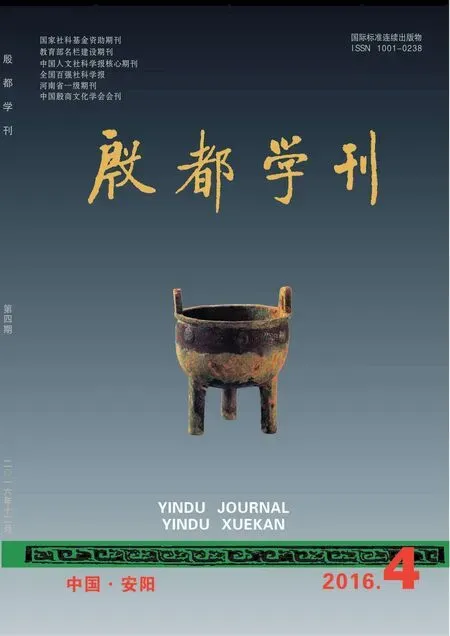叙事策略与文化意蕴——论《红高粱家族》《北极村童话》《风景》的儿童视角
2017-01-06史新玉
史新玉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叙事策略与文化意蕴
——论《红高粱家族》《北极村童话》《风景》的儿童视角
史新玉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20世纪80年代的儿童视角小说创作空前繁荣。本文主要通过对儿童视角小说的内部研究,分析比较其叙事特征,并从文化诗学的角度揭示儿童视角叙事方式所具有的独特的文本内涵。
儿童视角;叙事学;文化诗学
对于一部成熟的文学作品来说,创作形式是一个重要因素。不论是读者还是批评者,如果不了解文本形式的奥秘,便无法与作家进行对话。就小说而言,其主题往往需要通过某种形式展现出来。小说的原型并不多,故事本身没有多少故事,母题更是屈指可数,然而作家创作出的小说作品却不计其数且各有千秋,这源于作家“讲故事”的功力。如何讲故事,谁来讲故事,常常是小说创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使同一个故事,每个作家讲出来的都不大一样,这是因为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独特创作形式,故事通过作家对语言的运用、对修辞手法的运用,或通过叙事结构、视角以及时间的变化呈现出来。其中,叙事视角对于揭示文本的内涵起着无法忽视的作用。
米克·巴尔在其《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明确指出:“叙述者是叙述本文分析中最中心的概念。叙述者的身份,这一身份在本文中的表现程度和方式,以及隐含的选择,赋予了本文以特征”。[1]一个小孩讲故事,与一个女性、一个老人或一个病人讲故事是不一样的,有的叙述者,即小说当中讲故事的人,当他的身份是一个小孩时,那么整部作品观察世界的方式就变了。
一
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以儿童作为叙述者的不在少数,采用儿童视角作为叙事策略的作品并非个例,从鲁迅的《怀旧》(1911年),到萧红的《呼兰河传》(1941年),一直到新时期,儿童视角越来越受到小说创作者的青睐。20世纪80年代前后,这类小说的创作相对集中,先锋文学代表作家莫言、苏童和余华,新写实小说作家方方以及东北女作家迟子建等均对儿童视角小说进行了创作实践。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1986年)、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1986年)和方方的《风景》(1987年),以及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1991年)等。随着数量的增多,儿童视角小说进入了文学批评者的视野。目前,学界多从概念的界定、创作发生、发展历程、作品意义等方面对儿童视角小说作品进行分析。
对创作发生的研究,学界一方面从创作论的角度研究作家运用儿童视角进行小说创作的深层心理因素,进一步探讨对此类小说进行创作的行为发生机制,从作家的心理活动出发,以荣格的“原型”理论作为切入点,认为“儿童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它普遍地存在于人类心灵之中”[2],儿童原型会以各种形式体现在每个人身上,这种与所有人共存的“内在小孩”随时可能因为某种因素被唤醒,此时,作家往往通过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儿童形象来宣泄强烈的情感,从而保持心境的平和。另一方面,多数学者考虑到了作家童年经验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正如《北极村童话》的作者迟子建所言:“北极村是我的出生地,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于是我在写《北极村童话》时充满了幻想,完全没有感觉是在写小说,而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如饥似渴地追忆那种短暂的梦幻般的童年生活”。[3]此外,有学者提到作家所处时代也对小说创作有着重要影响,认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作家对乡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从小在乡村长大,对现代化的蔓延和城市化的发展有着与生俱来的排斥感。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远离都市,回归乡野”这种意识的影响下,中国文坛诞生了一批优秀的儿童视角小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另外,也有学者谈到作家的精神归根与儿童视角小说创作的内在联系,认为“当代儿童视角小说的创作者们之所以能够用童年和童心来牵动我们的情思,是因为复归儿童,复归精神之根是人类共有的心理情结”。[4]笔者认为,上述几方面都可以归结为作家心理因素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也有人从性别角度入手,探讨当代男性作家创作的儿童视角小说。在一篇硕士论文《当代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儿童视角——以莫言、苏童、余华为例》中,作者主要考察了莫言、苏童、余华等作家的童年成长经历和早期阅读体验对其儿童视角小说创作的直接影响,进一步剖析作品所蕴含的意义及深层题旨,并通过解析具体文本,肯定作家们在儿童视角小说创作中对儿童的真切关注。笔者认为,从性别角度出发分析同一类小说作品是可取的,但是作者研究得并不够深入,缺乏将男性作家的儿童视角小说创作与女性作家作对照的环节,没有找到这三位男作家的创作不同于女性作家创作之处,以及与其他男性作家儿童视角小说创作的共性特征,所以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多数学者梳理了儿童视角小说的发展历程,从纵向角度分析其历时演变。王黎君将儿童视角小说起源问题追溯较早,他从历史的角度谈起,认为在晚清时期,现代儿童观已初步形成,“直接开启了五四时期现代儿童观的建构过程”[5],并从对西方的译介、第一人称的普及等方面分析了儿童视角小说诞生的时代背景。
二
简单地讲,小说创作过程就是作家讲故事的过程,而儿童视角小说就是作家讲的儿童眼睛里的故事。儿童视角小说并非固定单一的叙事策略,如果将这个点放大可以发现,作家的性别不同,身份不同,或者同一作家的创作时间不同、内容所反映的时代不同以及儿童身份的不同等因素,造成了每一部儿童视角小说之间的千差万别。本文中,笔者将通过对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以及方方的《风景》进行分析比较,并揭示小说创作中儿童视角这一叙事策略所包含的文化意蕴。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写的是长大后的“我”对父亲孩童时期所经历的事情的回忆,是用大人的口吻写成的童年回忆录,且故事中提到的绝大部分情节“我”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由于故事发生的时态全部为“过去式”,故事的内容与儿童,也就是童年时的父亲有关,故事发生的场景也是儿时,所以整部作品的叙事视角依然是儿童。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多以儿童视角作为叙述角度,《北极村童话》就是其典型的儿童视角小说之一。小说采用第一人称,以小女孩“迎灯”的眼眸看世界,写出了苏联老奶奶等故乡人的淳朴善良,以及与动物“傻子狗”之间发生的快乐的事情。方方的《风景》则以一个亡婴的视角观察其一家人艰苦辛酸的生活。
米克·巴尔指出:“在叙述文本中可以找到两种类型的讲述者:一类在素材中扮演角色,一类不扮演。这种区别即使在叙述者与行为者合而为一(例如在叙述中以第一人称讲述)时依然存在”。[1]也就是说,视角不等于口吻,叙述人不等于见证者。上述三部作品的儿童视角之间各有差别,从 “儿童”的身份来看,《红高粱家族》中的叙事者并非儿童,未在“素材”中扮演某种角色,更不是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整个情节的讲述是大人的思维,作家莫言以成年人的口吻讲述“我”父亲小时候的见闻,并以“我”爷爷和“我”奶奶作为核心角色, 在这里,笔者尝试着将隐含的叙事者变为显性的叙事者:
①(我)我爷爷余司令走到墙角后,立定,猛一个急转身,父亲看到他的胳膊平举,眼睛黑得出红光。勃朗宁枪口吐出一缕白烟。父亲头上一声巨响,酒盅炸成碎片。一块小瓷片掉在父亲的脖子上,父亲什么也没说。
②(余司令)我走到墙角后,立定,猛一个急转身,胳膊平举,眼睛黑得出红光。勃朗宁枪口吐出一缕白烟。我儿子豆官头上一声巨响,酒盅炸成碎片。一块小瓷片掉在他的脖子上,他什么也没说。
③(豆官)我父亲走到墙角后,立定,猛一个急转身,我看到他的胳膊平举,眼睛黑得出红光。勃朗宁枪口吐出一缕白烟。我头上一声巨响,酒盅炸成碎片。一块小瓷片掉在我的脖子上,我什么也没说。[6]
可以看出,①③句运用的都是儿童视角,但①句是通过未经历句中所述场面的“我”讲述的,是“我”对我父亲(大人)讲的故事的转述,而③句的“我”,即小说中“我”父亲是句中所述场面的亲身经历者;②③句的叙述者均为故事的亲历者,但是句子②的叙述者是成人,而非儿童视角。由此可见,句子①“通过‘我’无所顾忌胆大妄为的无知叙述,我们看到了‘我爷爷’不仅是英勇无畏的抗日英雄,更是一个杀人越货的土匪”。[5]哲学家大卫.K.刘易斯说过:“在故事世界里,讲故事行为就是实话道出讲述者所知之事的行为,而且(在这个故事世界之内)故事是作为已知事实来讲述的”。[7]《北极村童话》与《风景》中,迟子建和方方都将小说叙述者与行为者结合成同一个人物,《北极村童话》中的小女孩“迎灯”更像小孩,整部小说运用了传统意义上的儿童视角;《风景》与前两者相比,差异较大,作家方方在采用儿童视角的基础上,对叙述视角做了进一步的“陌生化”处理,以一个死者幽灵来观照世界,独具个性。
不过,小说叙述者与情节中的行为者并不一定等同于“隐含作者”,方方的《风景》更像是隐含叙事者与显性叙事者融为一体的。小说中的“我”是一个亡灵,被父亲埋于窗下,永远和家人在一起,“我”宁静地看着哥哥姐姐们生活与成长,见证了这个家庭及这个世界的阴暗和荒谬。作者将死者幽灵这个身份作为叙述者,因为并不真正存在于这个现实世界,本身带有了一种虚幻,因此这个视角变得无限广阔,能看到常人所不能见,“一个人物叙述者通常声言它在细述关于其自身的真情实况。它可以自称在写它的自传,即便其素材明显地难以置信、荒诞、不合情理,甚至是超自然的。”[1]
为了较为清晰地比较这三部作品的儿童视角,笔者绘制表1如下:

表1
三
佛克马明确指出:“文学必须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文学再也不是一个隐蔽的、‘律的’领地了,文学研究的对象也不能仅局限于文学文本”。[8]作家采取何种形式对故事进行言说,以及形式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本的文化内涵。从文化诗学的角度讲,迟子建笔下的儿童视角所看到的是美好的事物,如人性的善和美;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呈现的是一种复杂性,体现的批判性更多;方方的《风景》则更倾向于对底层生活状态的关注与揭示。这种差别往往与作家的身份有关,不同的作家身份,其文本所呈现的价值和意义也不尽相同。
方方是一位新写实小说家,作为“最早尝试将视角伸人历史深处、力图在较为广阔的时代风云变换中叙述家族历史、命运沉浮的作家”,[9]她在《风景》中以类似于人像展览的方式书写了一系列生活底层人物,李杭春将该小说的题目“风景”进一步解释为“中国‘小人物’风景”,[10]以一个死去的婴儿的眼睛观察世界,从空间、地域文化的角度展现底层人民生存状态和命运沉浮,旨在揭示社会真相,“在‘八十年代的视野’中对历史进行了重新的择取、剪辑和排列组合,并从这种‘历史’筛选中展开与八十年代的广阔对话”。[10]“死婴”这个特殊的视角赋予了文本特别的含义,不论现实多么惨淡,“我”都安详地睡在家的窗台下,即使”我“看到了世间的不公与黑暗,也依然没有任何情绪起伏,“我”只是冷静地叙述目之所见,这种“被死者复写的世界”散发着阴冷与绝望的气息。
纵观迟子建的小说创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作品均采用儿童视角,她说:“童年视角使我觉得,清新、天真、朴素的文学气息能够像晨雾一样自如地弥漫,当太阳把它们照散的一瞬间,它们已经自成气候”。[11]她的作品基本上走在现实主义框架当中,在其代表作《北极村童话》中,作者以小女孩“迎灯”作为故事的见证者,并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为读者展现了中国的“北极”漠河的风光以及充满乡土气息的民俗,“与迟子建同时代出现的作家作品中,大多数人倾向于对生活黑暗面,人性罪恶面的揭示,文学作品中弥漫着压抑、窒息的气氛。对社会生活失望、人情淡漠、人性畸形、变态的描写铺满读者的视线。迟子建带着皑皑白雪的清透、辽阔林海的壮丽、散发着原始的芳香走进了人们的视线”。[12]与迟子建同时代的作家莫言、方方、余华等,他们的作品色彩属于“灰色系”,迟子建的则属于“彩色系”,与莫言的先锋小说以及方方的新写实小说相比,迟子建的小说更注重对真善美的赞美,在她的笔下,北极村的村民淳朴、善良,整部作品弥漫着诗般的气息。
莫言的《红高粱》具有复调意味,同时也是陌生化、狂欢化小说作品的典型。作家“回归民间,向传统和本土借鉴叙述资源,去表现“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凸显“藏污纳垢的形态”。[13]莫言通过儿童视角的运用,借着独特的声音和腔调,更好地利用了童年乡土生活带给他的广阔的创作素材和资源。
[1][荷]米克·巴尔著,谭君强译.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
[2]李琰.当代儿童视角小说创作研究[D].苏州大学,2010,(5).
[3]迟子建,周景雷.文学的第三地(文学对话录).当代作家评论,2006,(4).
[4]吴丽丽.当代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儿童视角——以莫言、苏童、余华为例[D].安徽大学,2014.4.
[5]王黎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儿童视角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7.7.
[6]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11.
[7][美]赫尔曼主编,马海良译.新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
[8]王宁.关于文学史、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者诸问题——访著名学者佛克马教授[A].比较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C].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9]张小刚,王莹莹.在“名”与“实”之间——重释《风景》兼及“新写实小说”的“起源性”问题[J].长城,2010,(5):15.
[10]李杭春.中国“小人物”风景——方方《风景》读法一种[J].小说评论,1989,(1).
[11]梁爱民.聆听天籁 感悟童心——迟子建小说的儿童叙事视角[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7).
[12]于慧.缤纷灿烂的精神家园——迟子建小说创作中的儿童视角研究[J].东北师范大学,2008,(4).
[13]夏兆林.“真”与“深”的表达诉求——论莫言小说中的儿童视角[J].曲阜师范大学,2013,(4).
[责任编辑:舟舵]
2016-07-14
史新玉(1993—),女,山西阳泉人,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
A
1001-0238(2016)04-007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