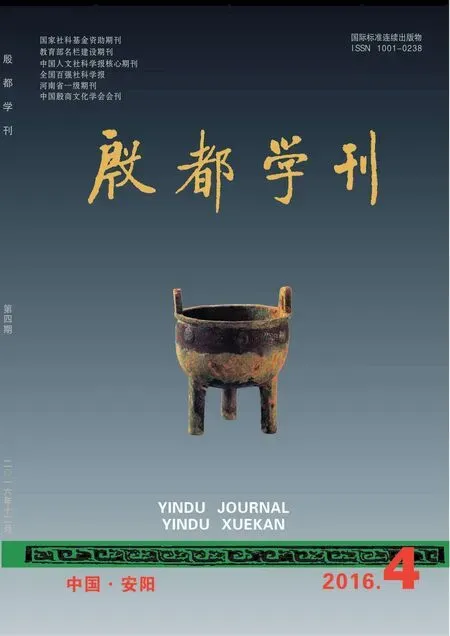明代大禹记忆及其文化意蕴
2016-02-02徐进
徐 进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明代大禹记忆及其文化意蕴
徐 进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大禹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神话人物之一,上承五帝,下启三代,地位特殊,而大禹传说更是经久不衰,深入人心,自成体系,并逐渐“历史化”“政治化”“人格化”。明人对于大禹有着特殊的历史记忆。在明代,大禹祭祀备受重视,典祭制度空前完善,帝王登基,必遣使告祭。然而,历史记忆并非单纯关乎过去,它更是现实需求的反应。明人借鉴大禹治水之法,治理水患具有明显成效,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功能,且大禹精神被明人重塑深化。大禹记忆透视出了明代社会情境、文化意蕴、政治境况的某些侧面,是另外一种历史事实。
明代;大禹记忆;文化意蕴;禹祭
大禹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神话人物之一,上承五帝,下启三代,地位特殊,而大禹传说更是经久不衰,深入人心,自成体系,并逐渐“历史化”“政治化”“人格化”。秦汉以来,中国士人都深信大禹及其事迹是真实存在,近代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对大禹及其事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举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大禹纯属神话虚构,从而掀起了学术界的一场争论。但因大禹传说中“历史”与“神话”杂糅在一起,加之时代久远,物证缺失,难以定论,至今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文欲跳出大禹研究的本体论方向,拟从历史认识论角度,追溯明代大禹记忆及其文化意蕴,通过大禹记忆透视其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及其精神的现实重构。
一、大禹祭祀: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
在中国历史上,自五代、两宋至元,中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方面,深受汉族文明的浸润,逐渐汉化。另一方面,对汉族文化也产生一定冲击,一度出现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直至明朝建立,汉族才重掌大一统国家政权。建国后,重建和深化汉族文化无疑至关重要,强化大禹记忆是其措施之一。大禹被视为是中国首个王朝——夏朝的开国之君,功勋卓著,而其治水事迹,更是为世人敬仰,成为汉民族的精神典范和情感根基,而大禹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一部分,成为汉族文化的重要基石。明人对大禹的历史记忆,深受此社会文化的影响。王明珂认为:“若我们将对历史的探求当作是一种‘回忆过去’的理性活动,此种‘回忆’常常难以脱离社会文化的影响。”[1](P137)明人对大禹特殊的历史记忆无疑强化了汉族群体的民族文化认同,而这种历史记忆主要通过大禹祭祀这一仪式得到体现和强化。
大禹祭祀历史悠久,其中明朝的禹祭制度最为完备,祭祀典礼空前隆重。明代官方禹祭有两种形式,一是立殿庙祭,一是会稽陵祭。明朝建国之初,即建帝王庙,自伏羲至元世祖,凡17帝,居正殿五室,其中夏禹与商汤、周文王同居西一室。[2](P1501)洪武七年(1374年),太祖躬祀,有大禹祝文为“夏禹王勤俭家邦,平治水土,天锡九畴,彝伦攸叙”[2](P1604),并规定每年春秋仲月,按时祭祀,永为典制。由此可见,明代帝王对大禹记忆是夏王朝的立国始祖身份,与汉高祖、隋文帝等居同等地位,彻底将大禹“政治化”“人格化”。
禹葬会稽,屡见史籍,如《史记》《墨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越绝书》《论衡》《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水经注》《宋书》等,是否为史实,暂抛开不论,但能够肯定的是后人常在此举行祭禹活动。自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亲自“上会稽,祭大禹”[3]后,历代帝王都重视大禹祭祀,或亲往祭禹,或遣官告祭。至明代,皇帝登基,必遣使告祭,形成制度。大禹祭祀分为告祭和致祭两种形式,皇帝登基特遣专官称告祭,皇帝遣使传制称致祭。洪武四年(1371年),太祖遣臣告祭,补《登极祭文》。九年(1376年),太祖朱元璋规定“凡遇登极,遣官告祭”[4]。此后历朝皇帝基本遵循这一祖制,新帝登基,必遣官祭禹。有明一代,凡17位皇帝,其中11位皇帝登基之时都遣官祭禹,颁布《登极祭文》,具体有太祖、宣宗、英宗(正统、天顺)、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除此,天顺至嘉靖年间,皇帝遣使致祭凡14次,时间分别是天顺三年八月十二日、天顺六年八月十二日、成化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弘治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弘治十七年八月十八日、正德八年八月二十日、正德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嘉靖七年九月七日、嘉靖十九年八月一日、嘉靖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嘉靖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嘉靖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嘉靖三十七年九月十一日。[5]此外,还规定大禹陵庙五百步内禁人樵采,设陵户二人看守,每三年遣道士以香帛致祭,每年春秋仲月遣地方官祭禹庙。如按此制,明代大禹的官方祭祀次数甚为繁多,但多不见诸史料。由此,祭禹典制空前完善,足见明代帝王对大禹祭祀颇为重视,从而强化了对大禹的历史记忆,传承了大禹文化。
大禹庙陵除有祭祀功能外,还承载着文化功能。明代文人雅士除游历名山大川,禹庙也是其游历之所,而其所到之处通常会留下诗作,称“禹庙诗”,如茶陵诗派代表人物李东阳、“前七子派”重要诗人郑善夫、周祚、马明衡、汪应轸、陈鹤、季本、杨慎(杨廷和之子)、陈耀文等9人都曾留有《禹庙诗》,其中郑善夫还撰有《禹穴记》,对大禹研究颇为深入,是明代研究大禹的重要人物。以上9人是明代文人士大夫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对大禹的纪念活动推动了对大禹集体记忆的存续,也彰显了明代文臣士人群体对大禹的文化认同。
此外,明代民众也会定期或不定期到禹庙祭拜。古史记载禹生于石纽,当地人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每年在这一日“熏修祼享”[6]。明代禹庙遍及全国,有记录者包括浙江、山西、湖广、河南、江苏、四川、陕西、南直隶、北直隶等,其中部分禹庙因年久失修而坍圮,明代重修了部分禹庙。正统八年(1443年),重修山西潞州大禹庙;正德十年(1515年),重建山西夏县大禹庙;嘉靖十三年(1534年),新建白毛山阴大禹庙;嘉靖二年(1523年),知府南大古修会稽禹陵,嘉靖二十年(1541年),知府张明道重修。除了禹庙外,还有以大禹命名的菲饮泉、栢泉寺、禹井等等。
总之,明人正是通过对大禹的祭祀和纪念活动等仪式而被记忆、重塑和传承,通过仪式表达个体和群体对大禹的情感寄托,也体现出汉民族对大禹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触及到了文化内核和情感根基,强化了对以大禹为典范的民族文化认同,而这种认同既体现情感依附,也包含政治色彩。
二、大禹治水:历史真实与社会治理
大禹治水是大禹传说的重要内容,其过程的历史真实性虽值得商榷,但洪水灾害、治水经验则是历史记忆的真实。历史记忆并非单纯关乎过去,它更是现实需求的反应。“历史与记忆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并非所有的事件都留存在记忆中,而是根据其社会重要性的逻辑被记忆”[7]。首先选择将大禹和治水相连,足见治水在历史记忆中的社会重要性。这也充分说明了明人对大禹的历史记忆是有其现实缘由的。
有明一代,水灾频发。邓云特先生统计明代共发生水灾196次,为当时灾害中最多者。[8]鞠明库先生统计明代277年中共有水灾1875次,[9]二人统计结果差别较大,但都一致认为明代水灾发生次数居各种灾害之首。水患关乎国计民生,关乎南北漕运,关乎北方经济。因此,治理水患是明王朝面临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明人追溯历史记述,将大禹治水视为信史,且作为治水必遵之典范。邵宝在《治河论上》中记有:“万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法禹可乎?”“时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10]由此足见,明代对大禹治水推崇之高。
大禹治水的对象是黄河中下游的水患,“禹治水之功,莫大于河”[11](P1458)。在明代,黄河水患频发,明人在治理黄河水患时多借鉴大禹治水之法,即重疏导。明初大儒宋濂有言:“自禹之后,无水患者七百七十余年。此无他,河之流分,而其势自平也。”[11](P12-13)他认为大禹将黄河水势分流,改堵为疏,是治水成功的首要因素。明代治水名臣徐有贞提出了著名的治水三策,分别是置造水门、开分水河、挑深运河,这三种治水策略都旨在疏导水流,最终成功治理了7年未治愈的黄河水患。他认为疏导黄河水势是大禹治水成功的主要原因,“昔禹凿龙门,辟伊阙,无非为疏导计”[12],并借鉴了这一治水之法,成功治理了水患。他也因治水有功,升为左副都御使。总理河道工部尚书潘季驯是明代治理黄河水患的水利专家,先后四次出任总理河道都御使,治水经验极其丰富,他在总结经验时首先强调“水性不可拂”,其中他也提到“禹治水曰:疏瀹决排,亦第去其壅塞耳”[13](P4599),可见潘季驯的治水经验也借鉴了大禹治水的方法。此外,明代各地治理水患大都采取疏导之法,虽无明言都是效仿大禹治水之方,但毋庸置疑,大禹的疏导之法对于明代治理水患具有重要影响。
总之,明人总结大禹治水成功的关键就是顺从水性,疏导水流,平缓水势。若违逆水性,“虽神禹,亦难底绩”[13](P835)。大禹治水传说为明代治理水患提供了有益经验,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使得大禹治水传说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功能表面看似是明人对大禹进行集体追忆的结果,实则是因治理水患的现实需要而有意选择记忆的结果,一方面,强化了明人的大禹记忆,另一方面,也赋予了大禹传说的历史真实性。
三、大禹精神:历史放大与现实重构
大禹作为神话传说人物,其是否真实存在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记忆探求背后隐藏的社会情境、文化意蕴和政治境况。大禹精神已渗透进汉族文化的骨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范和中华民族的情感根基。究其原因可发现,大禹精神与儒家文化高度契合,如大禹的仁德爱民、勤奋节俭、忠君孝父、公而忘私等,无不与儒家文化相符合。大禹精神和儒家文化分别作为汉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共同信仰,二者已相融一体,这也是历代汉王朝的帝王国君推崇大禹、祭祀大禹的根本缘由。在明代,统治者根据现实需要将大禹精神进行了重构深化。
1.大禹的勤俭精神。史书记载:“禹之为人也,克勤克俭”[14]。明前期,尤其是洪、永时期,皇帝尚能勤政,常以圣王为榜样,不仅崇尚大禹之勤俭,且以身作则,并以此教育皇太子。朱元璋即位后,深知治理天下不易,勤勉政事,丝毫不敢怠惰,并以大禹“惜寸阴”[2](P1882)的精神自勉。成祖朱棣在《皇太子圣学心法》一书的序言中写到:“须臾暂息,则非勤励,大禹勤劳,功覆天下”[15](P1209)。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礼部左侍郎胡濙上言十事,其中包括勤庶政,务节俭,并都以“大禹之克勤”、“禹之菲饮食,恶衣服”[16]为例,内阁首辅胡广更是称赞朱棣“勤俭如大禹”[15](P1329),虽为溢美之词,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朱棣勤政节俭之品质。宣德元年(1426年),宣宗因宫室的蔬菜供应过于繁多,劳民伤财,从而“三分减二”[17](P383),并以大禹“恶衣菲食”为例。至明中后期,皇帝大多荒淫怠政,有识之臣则以大禹之勤俭影射皇帝之荒淫,劝告皇帝勤政节俭。如隆庆二年(1568年),张居正上言穆宗:“仰惟皇上即位以来,凡诸斋醮土木淫侈之费,悉行停革。虽大禹之克勤克俭,不是过矣。然臣窃以为矫枉者必过,其正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节省,恐不能救也。”[18]他表面是赞扬穆宗停革淫侈之费,实则是影射皇帝依旧奢侈荒淫,劝告其要崇尚节俭。嘉靖十八年(1539年),南京礼部尚书霍韬、吏部郎中邹守益赠与年幼的皇太子一本图画书,共有十三幅图画,其中一幅则以大禹“菲饮食,恶衣服”为例,教育太子能够节俭。[19]由上,明人习惯将大禹之勤俭精神与皇帝相联系,或皇帝以此要求自己,或廷臣以此影射皇帝之荒淫,告诫其要勤俭。
2.大禹的民本思想。《尚书》载有夏禹祖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0],因《尚书》成书时间和作者已不可考,故此言是否为大禹所说,值得商榷。但窥其内容,与儒家思想高度契合,其出自儒家之手或许更为可信。不管史实如何,大禹的民本思想成为明人的历史记忆则是客观存在,这种记忆不仅是对大禹民本思想的原始再现,更是根据现实需要的重构再造。明代灾蠲关乎国计民生,且制度较为成熟,发生灾害后,一般由地方官员将灾情上报中央,说服皇帝蠲免赋税,在陈辞中多会援引大禹的民本思想,劝说皇帝“惟以生民为忧”[21],蠲免赋税,发粮赈济受灾民众。此外,还将大禹的民本思想列入《御制帝训》一书序言的《仁民篇》中:“禹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夫食则思民稼穑之艰,衣则思民蚕桑之劳,饱则思民之饥,暖则思民之寒。赋敛以时,役调有节,宽厚以容之,简静以休之,俾农工商贾,各力于生业,水旱疾疫,皆为之赈恤,无失所之。忧有生遂之乐,则民心永安,而天命永固矣。”[17](P936)除此,明人还将大禹之忠孝比拟君臣关系,将大禹“虚己求言”[22]劝诫皇帝虚怀纳谏,将大禹之“亲师慕学”[23]劝告皇帝经筵讲学之重要,将大禹精神根据统治需要进行了现实重构和历史放大,一方面,丰富和深化了大禹精神,另一方面,对于皇帝善政、国家统治不无裨益。
综上,分析大禹记忆的目标不在于考证厘清大禹事迹,而在于透视记忆背后的个人情感、社会情境和文化意蕴。祭祀作为历史记忆的仪式表现方式,明代大禹祭祀制度的完备和帝王对大禹祭祀的重视程度,可窥探出明朝统治者对于大禹特殊的情感寄托。明朝作为汉族大一统王朝,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倒看,明朝是最后一个汉族政权王朝。正看,明朝是在经历五代、两宋至元代长达300多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汉民族再次实现国家大一统的王朝。虽然,异族文明逐渐被“汉化”,但汉族文化也受到一定冲击,甚至一度出现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而大禹建立的夏朝向来被视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是汉族文明的开端,这或许是明朝统治者推崇大禹,重视大禹祭祀的根本缘由,试图通过强化大禹记忆,丰富大禹文化,从而增强汉族文化认同。另外,明代水灾频发,明人对大禹治水之法的探求,使得大禹记忆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功能。循此,明人对大禹精神的现实重构,不仅丰富了大禹文化,深化了大禹精神,而且对于国家统治和皇帝善政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总之,虽然大禹记忆无关乎大禹史实的真实考证,但却能够透视明代的社会情境、文化意蕴、政治境况,可谓是另外一种历史事实。
[1]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
[2](明)夏元吉等.明太祖实录 [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1962.
[3](汉)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59:260.
[4](明)张元忭.(万历)会稽县志 [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526.
[5]沈建中.大禹陵志 [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5:80-81.
[6](明)曹学佺.蜀中广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1册) [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141.
[7]蓝达居.历史人类学简论[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8]邓云特.中国救荒史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30.
[9]鞠明库.灾害与明代政治 [D].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18.
[10](明)黄 训.名臣经济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4册) [M].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470.
[11](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 [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明)孙继宗等.明英宗实录 [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1962:5362.
[13](明)张惟贤等.明神宗实录 [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1962.
[14](宋)黄伦.尚书精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册) [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452.
[15](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 [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1962.
[16](明)杨士奇等.明仁宗实录 [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1962:122.
[17](明)杨溥等.明宣宗实录 [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1962.
[18](明)张居正等.明穆宗实录 [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1962:636.
[19](明)徐阶等.明世宗实录 [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1962:4703.
[20]尚书 [M].北京:线装书局,2007:52.
[21](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 [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1962:1798.
[22](明)薛应旂.宪章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2册)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51.
[23](明)李东阳等.明孝宗实录 [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1962:289.
[责任编辑:郭昱]
2016-08-27
徐进(1988-),河南临颍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史。
K248
A
1001-0238(2016)04-003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