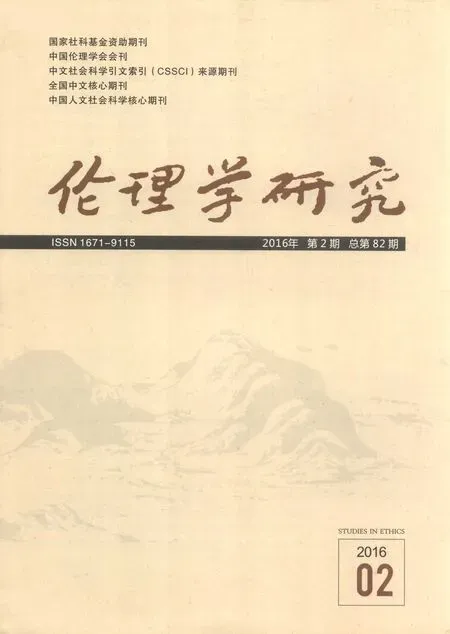人权伦理研究的新维度
——第五届人权与伦理学论坛综述
2016-02-02裴彧
裴彧
人权伦理研究的新维度
——第五届人权与伦理学论坛综述
裴彧
2015年10月23-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与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五次人权与伦理学论坛在广西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广西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林业大学、贵州大学、深圳大学、湖南科技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宁夏大学以及广西区委党校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着“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人权、人性与价值观”、“人权与中西方传统尊严观”、“人权与科技增强”、“人权与人机互联”、“人权与国际伦理”等广泛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各家高论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专注于概念辨析,借鉴于传统文化,热心于热点问题,以及放眼于未来世界。
一、概念辨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甘绍平区分了人权理论中的“个体自主的权利”和“集体自决的权利”。而人权理论要对个体人权和集体人权两者都予以承认,这是因为集体人权中有一项“集体自决权”“无法回溯为个人权利”,例如通过投票而定下来的集体的自我决定无法回溯为任何个体的自我决定。甘教授进而指出“集体自决权最重要的载体是国家,而以国家为载体的自决权被称为主权”。他承认国家主权所承载的集体决定权不能回溯到个体人权,但是立刻又提醒道“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主权自然而然就等同于集体自决权”,因为国家主权要想得到人权理论的支持,就“不(能)与个体权利发生对立与冲突”而是要“为个体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如果说甘教授所倡导的“普遍”的人权跟“抽象”有脱不掉的关系,必须抽掉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况才能“普遍”地适用于“世界”,那么重“普世-抽象”而轻“国情-具体”的观点立即受到中国人民大学龚群的批判性反思。龚教授提醒我们注意汉娜·阿伦特的悲观论调:“把人宣布为自身权利的根据,这种抽象的人权观有落空的危险”,所以“当法国《人权宣言》把人们从传统的神学、习俗的保护下解放出来之时,一种抽象的人的观点并没有提供一个人权保护的支点,实际上是把人们抛入到一种除了民族国家政府之外而没有传统力量保护的无助境地”,这样一来实际上“国情-具体”的政权反而成了“普世-抽象”的人权的“保护人”了。甘教授高扬普遍人权的“应然”,龚教授提醒具体人权的“实然”,二者和而不同的声音还在本次会议的其他论文中找到回音。针对甘教授对人权的基础性地位的肯定,你可能会问,如果人权是主权等伦理概念的基础,那什么又是人权的基础呢?广西大学卢永欣的回答是:“一切权利和政治理想的探寻,都应以感性自由为根基。”他援引费尔巴哈对感性直观的追问,论述感性是“哲学的起点”,而感性自由则是“人之生存根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拓展了的感性中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权利、真理和‘人’。”虽然卢副教授确认了人权的源头是感性自由,不过仅仅说出感性自由还难以确定人权的具体内容究竟有哪些,而这些人权内容又由什么概念对其辩护?对此南京师范大学的高兆明回答道:人权的基础是尊严,“缺失尊严的人权缺失坚实基础。”换言之,可以用尊严概念来为人权进行辩护。
二、借鉴传统
广西大学的杨通进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文化运动对权利观念的认知和建构存在许多偏差。这些偏差使得许多现代中国对权利(特别是人权)的认知、认同和建构一波三折,也延缓了中国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速度。”余波所及,自五四以至如今,许多人仍然没有能够“跳出陈独秀们、胡适们的局限”,这些局限包括:(1)把权利当作西方特有、东方不必有的东西加以拒斥,而不知道权利实为现代特有、古代必不有的概念,但凡想要迈入现代化的社会都必须接受权利观念的洗礼;(2)没能坚持权利的个体主义本质,导致人权和表示群体的“民权”、“国家的权利”相混淆;(3)把权利当作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而工具是可以视情况而舍弃的,这一误解导致权利丧失了其基础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孙春晨“基于儒家仁爱伦理”找到了两条“人权实现路径”:一条是“建立在伦理关系之上的人权实现路径”,另一条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人权实现路径”。众所周知,儒家伦理重“关系”轻“个体”,重“义务”轻“权利”,似乎与强调个体权利的人权概念格格不入,但是一旦把概念投放到实践中去,或许就会像孙研究员所发现的那样,“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人权概念……都是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这就容易导向一种高度抽象的人权理论,为了展示人的权利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就必须抽掉人的具体规定性”,而“儒家仁爱伦理将人视为处在一定伦理关系中的个体……(因此)个人权利的实现有赖于一定的社会伦理关系的支撑。”此乃建立在伦理关系上的人权的实现路径。孙研究员所指出的两条路中,第一条道路同样涉及到了人权的“抽象-普遍性”的优点和缺点的问题,与甘教授与龚教授的讨论遥相呼应。湖南师范大学的王泽应接过孙研究员的接力棒,继续发掘儒家思想对人权问题的启发,如果说孙研究员是用望远镜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儒家思想,那么王教授就是用显微镜从微观上见微知著,挑出王夫之的尊严论展开详细“解剖”。他总结道:“王夫之的尊严理论以人性尊严为始基,以人道尊严为重点,以人格尊严为旨归……在尊重天道自然的同时凸显出‘依人建极’的人本主义色彩,并对人的身心形神予以关照……形成一种价值整合与价值导向辩证统一的尊严理论”,并推荐大家关注王夫之“身心合一、理欲合一、性命合一的独特智慧”。除了儒家思想以外,与会者还介绍了道家思想对人权问题的启发,以及从中外历史对比的角度发现了人权与身体权的中外不同的关系轨迹。
三、热点探讨
本次论坛上运用人权概念分析现实的论文多达为六个方面: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生育权。在高科技对于传统生育方式的冲击这个问题上,西南大学的任丑教授指出,关于生殖技术所带来的道德悖论(对父辈的生育权的满足和对晚辈的命运自我决定权的干涉),伦理学“不应当囿于这样的道德悖论而裹足不前”。伦理学不是为了阻止历史潮流前进,而是为了把潮流引导向安全的方向。任教授进而提出了伦理学应该提请人们注意三个方面的责任:“人类实存律令赋予生殖技术的责任”、“生殖技术自身蕴含的责任”以及“生殖技术应用的责任”。承担起了这三方面的责任,就有望发挥生殖技术造福人类的一面,弱化其威胁尊严的一面。同样是探讨生育权的问题,深圳大学的李隼副教授利用基本人权的概念构筑起了“生育伦理的逻辑起点”。由于生育权“被国际社会广泛确认为一种基本人权”,因此基本人权也就成为了“所有生育伦理主张的根本出发点”。无论是鼓励人口增长还是限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都不能罔顾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理论判定”,一方面,生育政策的制定“可以尽量从现实社会发展情况的分析中获得一定的理据支持”,但是另一方面这类政策却“必须满足严格的程序正义的要求,并保持一定的慎重和敬畏的态度。”文化方面,复旦大学的张娅以通俗文学的一位热门作家卫慧的身体写作为标靶,澄清了真正的女权主义是什么的问题:“自我身体和欲望的开放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只有平等的人格价值和权利才是女权主义的应有之义。”政治方面,宁夏大学的尹强提醒我们警惕“少数民族文化的道德本性以及其中足以让我们警惕的冲突形式”,从而有益于我们“共同承担起在少数民族发展中应当承担的责任。”经济方面,贵州师范大学的欧阳辉纯比较了“人的价值”和“经济发展”二者的重要性,得出的结论是“人的发展具有优先性,人的价值是民营经济发展的起点,也是其发展的终点”。国际关系方面,宝鸡文理学院的王曦璐提出了“国际关系领域中人权问题的本质是主权与人权何者优先”的论断,并把国际关系人权困境的文化因素诊断为“人权的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这一诊断书与本文前述的“普世-抽象”与“国情-具体”之争遥相辉映,而王曦璐用国际关系中的人权困境这个比较具体的论题支持了普世的、平等的人权原则,不过必须加上限制条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文化”所达成的“共识”的人权原则;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发展着”的人权原则。
四、关注未来
清华大学的卢风借审视现代科技所面临的问题来检验人权概念。他认为装备了高科技的现代性“不断激励”人们“扮演上帝”,然而这却“是现代性的迷信”,将会使人类“在种种‘自作孽’式的科技创新中走向毁灭”。那么人权的概念能不能预防科技的危险呢?卢教授认为“人权原则——无法约束扮演上帝的人们”,究其原因,一是人权原则高扬人类自身,拒斥上帝、命运,于是生命不再是来自神圣的赐予,生命本身也就丧失了神圣性,这就再也难以阻止科技对生命的肆意改造(例如人工生育和基因工程);另一方面,人权关乎个人自主,而自主需要能力作为支撑,能力又需要科技的保障,因此科技会受到支持人权的思想家的青睐,因此很难指望这些倾心于科技的思想家对于科技的危险保持警惕。中山大学的翟振明探讨了人机互联与人权的关系,提出“在网络化的虚拟现实和物联网整合之后,我们原有的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的基本概念会变得失效”,而这些基本概念一旦失效,“对人权问题之讨论和界定也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为此我们需要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一个责任主体的双重身份的关系,即在道德和法律层面的单个责任主体,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却各有一个角色;隐私和隐匿的关系,即既保障隐私权,又有效防止“隐身”的网民在赛博空间制造事端;物理伤害和心理伤害的关系;人工物和自然物的关系,即虚拟世界的“自然景观”也都是用户创建的“人工物”,那么如何处理人工物和自然物的界限,进而如何修正“财产占有”的概念就成为一个问题;人身和财产的关系;以及意图和后果的关系。大连理工大学的王国豫指出,由于“纳米材料生物效应的不确定性”,从事与纳米材料相关研发、生产、包装、搬运、运输等工作的从业人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健康与安全风险。所以纳米技术“可能造成对从业人员的基本人权的侵犯”,为此“应该对纳米技术进行‘有罪推定’”,包括在管理方面将纳米材料视为有毒化学物资,在信息方面告知工人相关材料的风险,以及在机制方面建立纳米材料职业安全风险预防机制。种种措施都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相关从业人员的基本人权。
总之,这次论坛各方学者所发出的声音可谓“广而不散”,围绕人权的“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核心问题,从理论、现实、过去、现在的多种角度展开了对话与交流。与会者高度认同研究人权伦理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认为缺乏人权问题的研讨,就无法实现现代伦理学中的道德奠基与道德论证问题,无法辨析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也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伦理学界以及中国社会价值观念整体的巨大变迁。
(裴 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