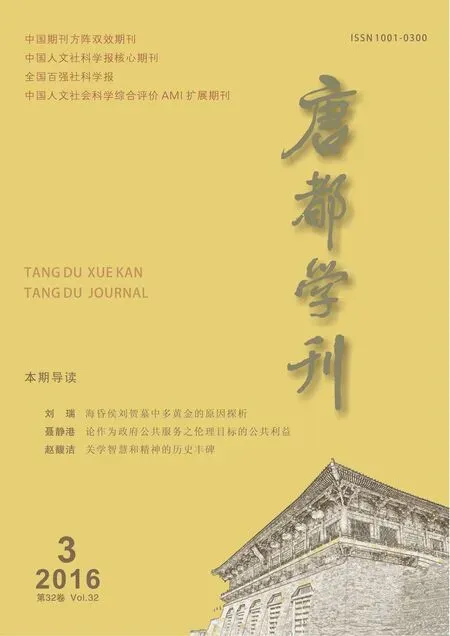中共中央化解西安事变困局的策略与经验研究
2016-02-02吴永
吴 永
(陕西省委党校 中共党史教研部,西安 710061)
【历史文化研究】
中共中央化解西安事变困局的策略与经验研究
吴 永
(陕西省委党校 中共党史教研部,西安 710061)
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兵谏”形式发生的西安事变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国内矛盾,造成时局困舛。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分析各种利弊的基础上,从大局出发,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正确把握中日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采用多种策略,最终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由此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
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事件,特别是在中共党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与作用。通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不仅摆脱了政治上孤立和内战中被动的困境,而且为促成全国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也因此成为国内时局转换的枢纽和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点。毋庸置疑,在日本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代背景下,以兵谏形式突发的西安事变本身具有双重的社会效应——或促成内战结束(积极效应),或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消极效应),而后者在事变中的演化趋势则更为明显。因此,如何消弭事变的消极效应,是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所在。本文试从社会危机处理的视角对西安事变加以考察,重点梳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化解西安事变困局中所采取的策略和经验。
一、西安事变引发的国内困局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本意是要“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以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但因事发仓促,谋虑不周,不料竟造成时局困舛动荡,孕育了更大的社会危机。
(一)国内时局动荡多舛
西安事变发端于国共内战关键之际。在红军长征进入陕北后,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一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以结束其所谓的“戡乱时期”。西安事变前,迫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红军“东征”中途折返,“西征”连连失利,战略突围十分困难。但中共在统一战线方面却获得了重大突破,与张学良、杨虎城方面秘密达成了“内部停战”的协议。正因如此,国共两党在西北得以形成暂时的战略均衡态势。而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特别是蒋介石的被拘禁和扣押,则完全打破了上述均势,顿时引起了时局紧张和更大规模的内战危险。
在如何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国民党南京政府最高层分化为主和和主战两派。主战派(时称“讨伐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戴季陶、居正、吴稚晖、朱培德、叶楚伧、何应钦等军政要人;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主战派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为严重危害了民国的利益与权威,为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给予严厉处罚[2]117。主和派则认为,武力讨伐不仅将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而且也将会导致陕西无辜民众遭受战争创伤,因此,“为国家计”,必须“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2]30。宋美龄明确表示:“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3]故坚决反对武力讨伐。但在国民党军队内部,胡宗南、刘峙、薛岳等高级将领纷纷要求武力讨伐。多数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表示“须以极速极大的军事力量,克服西安。”[4]在主战派的推动下,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下达了军事讨伐张学良的命令,声称此举是“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护国本”[5]。随后,国民党军队迅速向西安周边集结,并动用空军轰炸了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而张杨方面,为防不测,早已在临潼至潼关沿线部署了重兵把守。双方可谓是“剑拔弩张”。
西安事变的这一结果,不仅置张学良、杨虎城于危险境地,而且也给中国共产党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中国共产党虽然肯定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具有正义性,但也认为,由于西安事变采取了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6]127。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内战危险,中共也迅速地在西安周边地区集结部队,作出了军事部署,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中央军。
时局变化如此之速,内战危险如此之大,可以说是民国以来所罕见。
(二)社会各界为之哗然
首先,教育界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进行了强烈谴责和抗议。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传达北平后,震动了整个学界,几乎人人都为蒋的安全担忧[7]。西安事变发动的第二天,南京的各大院校和学术团体纷纷通电全国,谴责张杨:“当国家统一之际,绥乱将平之时,竟乃包藏祸心,劫持统帅,摇乱国本”[8]。罗家伦、吴贻芳、陈裕光等教育界名流更是指责张学良、杨虎城的扣蒋行为是“亡国之举”[2]447-448,随后,蒋梦麟、梅贻琦等北平各大学校长致电张学良,奉劝张学良悬崖勒马。他们强调,蒋介石身为国家统帅,责任重大,如遇不测,整个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如果张学良仍然执迷不悟,图一己之私,以抗战为名,觊觎国家,或“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9]。上海各大学校长如翁之龙、黎照寰、刘湛恩等也纷纷致电谴责张学良,认为西安事变系“动摇国本,助长敌焰之举动”,在国难严重之今日,“实在令人痛心和愤慨”[2]449。就连朱自清、闻一多等民主人士也把西安事变视为破坏国家统一的逆举,认为“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希望国民政府迅速予以讨伐[10]。
与此同时,文化界的一些名流也对西安事变表达了不满。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一向对蒋介石并没有多少好感的胡适致电张学良,公开为蒋说话,谓“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他告诫张学良:“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11]即使连张学良十分敬重的朋友、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也是感到“莫不痛心”,希望中国不要重蹈西班牙内战的覆辙[12]。
教育界、文化界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在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际,国人对于国内各党派、各阶级团结抗日的渴盼。尽管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政权的独裁专制统治不得人心,但就当时的国情来看,国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并且在国内建设方面也有一些积极的表现。特别是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方面,蒋介石政权还是给予了文化教育一定的优惠政策,重用了一大批文人和学者,在政治上更是极力拉拢知识分子。这对于那些一向主张社会改良、充满理想主义和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来说,是颇具诱惑力的。也正因如此,在没有完全了解事件真相之前,以兵变形式发生的西安事变才引起他们的震惊、恐惧和不满。而就西安事变本身来说,处置不当,确实有陷国家和民族于内战的危险。
(三)前苏联对事变表达强烈不满
在国际上,前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举足轻重。张杨发动兵变,本望得到前苏联的支持和肯定。但事与愿违,西安事变不仅没有得到前苏联的任何声援,而且还直接导致了前苏联对中共的不满和批评。
“九·一八”后,日本占据东北,对中苏两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尽管前前苏联对日本侵华实行“不干涉”政策,但出于牵制日本的考虑,中苏两国在1932年底宣布复交。随着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在欧洲的崛起,共产国际七大把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前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适时提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但与此同时,前苏联为避战自保,对日仍然进行着妥协性外交,以求早日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在希冀利用“国联”制裁日本的企图破产后,也希望利用与前苏联交好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刺激英美对自己的扶助;二是政治解决共产党。在此背景下,国民党开始与前苏联秘密接触,商谈军事互助协定及相关援华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一战和二战期间,苏俄(联)援华政策明显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积极推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促成中国民族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一方面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甚至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以求得对日妥协,为苏俄(联)赢得阻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喘息”机会。而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则完全打乱了前苏联的计划。前苏联尤其担心西安事变会导致国民党与日本的妥协,陷前苏联于中日的夹攻之中。
因此,当西安事变发生后,前苏联的第一反应就是震惊和愤怒。西安事变后,前苏联《真理报》《消息报》迅速澄清与该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并称西安事变为“西安叛变”。与此同时,前苏联外交部在召见国民党驻苏大使蒋廷黻时亦表明:前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之间没有与事件相关的实质性关系[2]534。当得知中共党内有杀蒋的呼声后,斯大林在质问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时,对这一主张表示了极大的愤怒。随后,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斯大林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进行了严厉指责,认为“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同时主张,在政府改组方面,“由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最杰出活动家来改组政府”,并且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13]。在得到斯大林的授意后,前苏联驻华使馆也发表声明,阐述了中立的立场,撇清了与西安事变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2]535。
前苏联的上述作为明显带有向国民党示好和打压张杨及中国共产党的倾向,目的是避免国民党与日本的妥协。对此,斯诺评价道:“斯大林想救出蒋介石,是由于怕没有蒋介石,国民党将军们会一怒之下转而与日本人联合,成立反苏同盟。”[14]作为共产国际的盟友,前苏联的这一立场和态度显然置中共于十分尴尬和被动的局面。尽管前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定下了基调,但划清与中共、张学良的界限,无疑会使中共和张学良在国际上陷入被孤立的危险境地。
二、中共应对西安事变的策略
在应对和处理西安事变中,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审时度势,积极采取各种策略,努力消弭事变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一)肯定西安事变的作用,旗帜鲜明地支持张杨
客观地说,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治上对国民党分化的结果,对化解蒋介石的军事“剿共”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作为西安事变的策划者,张学良、杨虎城显然对事件的应对处置事先缺乏全面系统的谋划,因而在事件发生后显得一筹莫展。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任何贸然行动,都有可能使事件变得更加复杂。为此,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支持张杨的爱国壮举,肯定了西安事变的进步作用。
在接到西安事变这一突发事件的电报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作出相应部署。一方面,指示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引导社会各界进行舆论宣传,揭露蒋介石对日妥协和对内独裁专制的行径,争取国民党内主和派和民主派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以备不测,联合张杨在军事上作出严密部署[15]621。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专门就西安事变问题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广泛分析各种利弊因素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事件的发生总体对中国共产党是有利的,使党打破了长期以来被蒋介石控制的被动局面。同时,鉴于事件的突发,中国共产党还缺乏全面的准备,因而毛泽东提出,除了要在军事方面做好准备外,重要的是在政治上要取得主动,争取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组织上和行动上与党保持一致,稳定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抗日工作。为此,他建议要做好张学良、杨虎城的思想工作,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
为了稳住张学良、杨虎城,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12月13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再电张学良,就西安事变后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作了相应部署,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张杨的义举,同时拟派周恩来去西安与张杨共同商讨解决当前面临的棘手问题。12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杨,双方就西安事变后的行动方针进行了磋商,明确告知中共方面将积极配合张杨,确保西安的安全。中革军委主席团也于同日向红军发出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指示红军做好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以确保目前西北地区的巩固与联合[15]622-644。
中共在道义和政治、军事上的及时援助,让张杨既摆脱了孤立无援的困境,也在极度紧张中保持了克制与冷静,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二)转变对蒋介石的策略,坚持和平解决事变
如何处置蒋介石,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单从共产党一边来看,蒋介石反共罪行累累,杀之并不足惜。的确,在得到蒋介石被拘禁的消息后,党内“杀蒋”的呼声很高,包括王明、张国焘、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人也积极主张“杀蒋”。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统帅和南京政府军政首脑,不独在国民党内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当时整个国家中的地位和声望亦无人可及。特别是在中日民族矛盾节节攀升的背景下,杀蒋将不可避免导致国内局势的混乱。前文所述社会舆论强烈谴责西安事变即是一有力佐证,故党内“杀蒋”主张甫一提出便遭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反对。毛泽东认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15]626张闻天也指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不仅如此,张闻天还明确反对把蒋介石交由人民公审[16]。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定下了准确的基调。
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对张杨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东北军内部同样存在“杀蒋”与“保蒋”的争议。就张杨二人而言,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也不完全一致。从“东北改旗易帜”“中东路事件”到“中原大战”等重大问题的处置上看,张学良始终是与蒋介石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即使对“九·一八”后抗战问题的处理,张、蒋二人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大致也是一致的(关于这一点,张学良在晚年回忆中明确表示,东北问题,主要责任在他[17])。因而,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用意是力促蒋介石抗日,而不是惩罚蒋介石。但杨虎城既非蒋介石的嫡系,也非张、蒋二人的结拜关系,他最大的担心就是释蒋之后可能引起蒋介石对他本人以及十七路军的报复,故力主惩蒋。以周恩来为主的中共代表团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认为对蒋介石的处置应当谨慎,既不能逞一时之快而杀蒋,否则会引发更大的时局混乱;也不能因保蒋而迅速释蒋,否则西安事变达不到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因此,在会见张学良和杨虎城时,周恩来明确表达了中共关于“促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不仅如此,如果蒋介石愿意抗日,中国共产党还将拥护其为抗战领袖[18]336-337。这与张学良的立场可谓不谋而合。针对杨虎城的担心,周恩来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申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将有利于推动全民族的抗战,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战,有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蒋介石是不敢随意妄为的。经过周恩来坦诚布公的解释分析,消除了杨虎城内心的疑虑和不安。他表示:“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19]
中共与张杨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上所达成的一致立场,不仅消除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分歧,而且也进一步巩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础。
(三)利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团结主和派,分化主战派
尽管国民党内部分化为主战派和主和派,但其时,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区别主要是针对西安事变本身的处置方式不同,两者并不涉及对国共两党关系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处置。而这恰恰是西安事变需要妥善解决的两大善后问题。因此,不管是主战派的决议还是主和派的决议得以通过,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安事变。但国民党内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分歧与斗争,则为中国共产党介入其中提供了历史契机。
由于国民党内部以及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内部在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而事件又特别紧急,因此相持双方急需一个合适的第三方介入。从张杨等方面的角度来说,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唯一对事件解决较为适宜的第三方;从国民党主和派方面来说,尽管他们不愿意共产党的介入,但在“主战派”明显占优势的情况下,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也只能希望中共能说服张杨,以联合张杨抵制主战派,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就给中国共产党与“主和派”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契机,使原本与事件没多大关联的中国共产党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事件的核心。中国共产党能否得到国民党“主和派”方面的认可,关键在于中共的立场和态度对蒋介石是否有利。对此,周恩来经过多方了解,探清了国民党各方对待蒋介石以及事变的态度,特别是蒋介石的态度在事变后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初始的强硬逐渐转向调和和期盼获得自由。周恩来将这一重要情况以及国民党内部一些重要人士的意见及时电告中央[18]342。蒋介石态度的转变无疑对事件的和平解决以及为中国共产党联合主和派提供了重要条件。
中共中央在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由于对西安和全国的情况比以前更清楚了,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如何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也就比上一次会议更为明确。毛泽东分析认为,西安事变将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前途,即“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15]626。为了积极争取光明的一面,毛泽东明确表示要旗帜鲜明地支持以张杨等为代表的抗战派,尽可能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早日结束内战,促成时局向抗日的转变。中共中央在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提出了具体解决西安事变的四项方针,明确把团结国民党左派,分化“主战派”作为处理西安事变的主要策略[6]128。随后,中共中央将会议精神电告周恩来,指示中共代表团要做好国民党中间派的工作。
在正确分析和判断时局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了充分的信心。这种信心是建立在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各派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国民党内部本来就派系林立,矛盾重重,特别是亲日派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较深。尽管蒋介石对日长期实行妥协退让政策,但毕竟与亲日派的投降主张有着本质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对蒋介石的诱降政策迟迟不能奏效的根本原因。因而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不仅担心张杨和中共会置自己于死地,而且更担心亲日派会投降卖国,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此背景下,唯有接受中共和张杨的抗日主张,才是唯一可以获生的选择。而蒋介石态度的转变恰恰印证了中共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上形成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独特策略,即联合张杨,团结主和派,斗争主战派,力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策略着实抓住了国民党的命脉,促使各方最终接受了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
(四)积极争取国民党内重要人士的支持与配合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事件本身,并非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只有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能真正达到国、共和张杨多方共赢的目标。为此,借助西安事变,从国民党内部寻求支持与配合,共同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大成功策略。
在12月1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有利于内战结束的力量做了分析,明确指出,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即“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15]628。为了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12月21日,毛泽东通过潘汉年转告南京方面,为避免亲日派借助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南京及国民党各地“左”派当务之急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左”派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共同促进国内和平:“(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15]631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要他派人去董钊、樊松甫、王耀武、胡宗南等处,告以何应钦、何承浚等亲日派实欲置蒋于死地之阴谋,愿与谈判恢复蒋自由之条件。
在得到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周恩来在会见宋子文派来的代表郭增恺时明确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态度。周恩来告诉郭增恺:这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出贡献。并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20]83。郭增恺向宋子文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宋子文喜出望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十分赞赏。国共双方正式谈判启动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六项主张”也得到了宋子文个人的肯定。中共的真诚态度赢得了蒋方的认可。在谈判中,宋美龄明确赞成停止内战,表示:“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21]。在周恩来的劝说下,蒋介石最终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协议[15]622。
在中共的努力之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化解。不仅如此,西安事变还为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围绕抗日统一战线,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空前活跃,为中国抗战政治资源得以整合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政治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处理西安事变的经验
综观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经验,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从大局出发,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正确把握主要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就西安事变后的国内矛盾来说,不仅有国共两党、两军之间的矛盾以及蒋介石集团与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的矛盾,还有蒋介石集团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内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矛盾。尽管从表面上看,张杨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是引发西安事变的直接原因,但真正的根源性矛盾却是中日民族矛盾。“九一八”后,尤其是1935年“华北危机”全面爆发后,当日本的侵略已经严重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时,没有什么能比维护民族独立更为重要的了,此时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积极协调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抗日救国。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却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勇于内战,怯于外战,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整个国家的民族利益诉求,极大地损害了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从而使社会大众普遍对国民党政权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可以说,正是由于蒋介石集团的罔顾时势和倒行逆施,才最终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对此,就连台湾史家王健民都表示:“西安事变之主要导因当然为日本之侵略”[20]84。而中国共产党尚在长征途中即已敏锐地发现了国内局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在《八一宣言》中高扬抗日救国的旗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呼号。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更是从民族存亡大局出发,在正确分析国内各种矛盾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突出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此一来,张杨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其他矛盾在中日民族矛盾面前,无不变成了居于从属地位的非主要矛盾,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就顺理成章。
第二,保持克制与冷静,明辨利害,准确定位事件的性质。西安事变是作为极为复杂的突发事件发生的。对这一事件性质的定位是否准确,将直接关系到事件能否得到妥善解决。而就当时的国内、国际主流反应来看,多数是对西安事变持反对和批判态度的,而且国民党多数认为该事件是中共“煽惑”的结果,尤其是在全国社会各界纷纷声讨张杨的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要对西安事变立即作出客观的评价是有很大难度的。一则中共确实没有参与西安事变的谋划,二则张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并没有公开化,贸然作出不当结论,不仅会置张杨和东北军、西北军于尴尬和危险的处境,使得事件变得更加复杂,而且也会使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和国内舆论上处于被孤立的困境之中;再则,张杨在发动西安事变后,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将发动事变的真实动机告诉中共方面,让中共难以揣测张杨是否真正着眼于联共抗日。因此,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虽然站在抗日救亡大局的高度,充分肯定了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认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但仍然冷静地指出:“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15]627-628不轻易发言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事件的复杂化。当年在中东路事件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曾因草率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置本党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在西安事变这一决定国内政治走向的关键问题上,如果稍有差错,就可能酿成千古大错。故中共中央不轻易发言,是深刻吸取历史教训走向成熟的体现。
尽管中共中央没有就西安事变的性质轻易言论,但对西安事变中的大是大非问题还是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的。如中共中央以红军诸将领的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公开表示:“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6]139把西安事变定性为国民党内部爱国将领的抗日义举。这样做,既肯定了张杨的爱国壮举,又为张杨留了后路。在处理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中共方面始终保持着克制与冷静,直至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其宣传方针的指示中仍然强调:“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6]123-124。1937年3月1日,当史沫特莱问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时,毛泽东再次强调:“‘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之后,宁陕对立,于是又有人说:共产党把西安造成马德里。这也完全不合事实”*陕西档案馆存,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毛泽东与史沫特莱谈话),1937-03-01,油印本。。显然,置身于事件之外,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既有利于使事件性质简单化,有利于保护张杨,也更有利于团结国民党的大多数,同时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光明磊落,为日后领导抗战树立了正面形象。
第三,做好处理事件的两种预案,在争取政治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同时做好应对内战的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西安事变是在蒋介石集团武力“剿共”的背景下以兵谏形式出现的,并且国民党内部在对西安事变的处理上又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此种情况极易引发大规模内战。对此,中共中央科学分析了西安事变可能导致的两个前途,从而确立站在张杨方面的基本立场,果断采取政治的和军事的两手准备,全力争取和平解决,以实现兵谏的目的。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表明立场,力主事件攸关各方顾全大局,从民族利益出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鉴于当时国民党部分部队开始向西安集结,为配合张学良、杨虎城应对中央军进攻西安,中共中央果断地作出相应的军事部署,在军事上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以确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前途。谈判之初,中共中央即明确指示:做好充分军事应对,“准备万一放弃西安时不至仓卒(猝)误事”。当和平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凡事向好坏两面着想,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面”。和谈已经接近尾声时,中共中央仍不忘告诫:“决不动摇以西安为中心持久作战、奋斗到底之决心”[15]630。这足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经过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长达10年的反“围剿”斗争的实践,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逐渐走向了成熟。而事实也证明,如果没有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严阵以待,仅仅通过政治谈判,蒋介石集团也不会接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谈判条件。
第四,遵循矛盾冲突的社会弹性原则,坚持原则的一致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任一社会形态,其政治系统内部的矛盾冲突,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矛盾冲突,政治系统通过社会系统而与自然系统的矛盾冲突,都有相应的弹性限度,超过这一限度,本来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矛盾冲突,就会转化为对社会发展的破坏。这就是矛盾冲突的社会弹性原则。而社会弹性原则所遵循和维护的,就是社会发展在矛盾激荡中的有序和协调。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形势异常复杂,解决不好,可能会激化各种社会矛盾,甚至还会掀起更大规模的内战,阻滞和延缓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在事变的和平解决中遵循了社会弹性原则,从实际出发,考虑现实条件的客观可能性,在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原则下,灵活采用各种策略,力争事物朝着有利于各方的方向发展。面对扣蒋形成的僵局,中共一方面对张杨的行为给予肯定,另一方面也表示出担忧,积极进行多方斡旋,极力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面对蒋介石只答应口头承诺拒不签字的情况,中共代表因势利导,表明政治立场,反复陈述抗日民族大义,借以消除蒋介石的后顾之忧;面对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尽管中共为张学良鸣不平,但并不以释放张学良为国共合作先决条件,公开宣称属其内部问题,但同时希望蒋介石作为一党领袖不要食其前言。如此,在西安事变中的各种矛盾的发展在临近或达到其弹性限度的临界阈值的时候,通过各方利益的调整而得以平稳解决。
[1] 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辑[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1055.
[2] 秦孝仪.西安事变史料:上册[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
[3]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DB/OL].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xasbwsg0101.html.
[4] 杨天石.海外访史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422.
[5] 罗元铮.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46-1947.
[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 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M].封长虹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141.
[8] 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N].申报,1936-12-14.
[9] 平教育界纷电张学良(劝以民族危机为念)[N].大公报,1936-12-16.
[10]全国声讨叛逆一致拥护政府(各界通电痛斥张学良)[N].大公报,1936-12-17.
[11]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513.
[12]黄德昭,王秦.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04.
[13]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M].马细普,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9-50.
[14]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M].党英凡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14.
[15]逄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6]张闻天文集(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200-201.
[17]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115.
[18]金冲及.周恩来传(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9]张树军,等.毛泽东之路[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101.
[20]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21]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三编(延安时期)[M].台北:中文图书供应社,1975:81.
[责任编辑 贾马燕]
On the Strategy and Experience for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Xi’an Incident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WU Yong
(TeachingandResearchDepartmentofHistoryofCPC,ShaanxiProvincialPartySchoolofCPC,Xi’an710061,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nsifying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Xi’an Incident actually intensified the internal conflicts by the forced remonstration, resulting in the predicament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fter the Xi’an Incident,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y analyzing the variou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rom the angle of the whole situation, conformed to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development, properly grasped the major contrad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dopted different strategies, and finally settled the Xi’an Incident in a peaceful way. Its peaceful settlement symbolized the political maturity of CCP.
Xi’an Incident; CCP; KMT; national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K264.8
A
1001-0300(2016)03-0084-08
2016-02-28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困局的历史经验研究”(12XDJ008)的阶段性成果
吴永,男,安徽蚌埠人,陕西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历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政党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