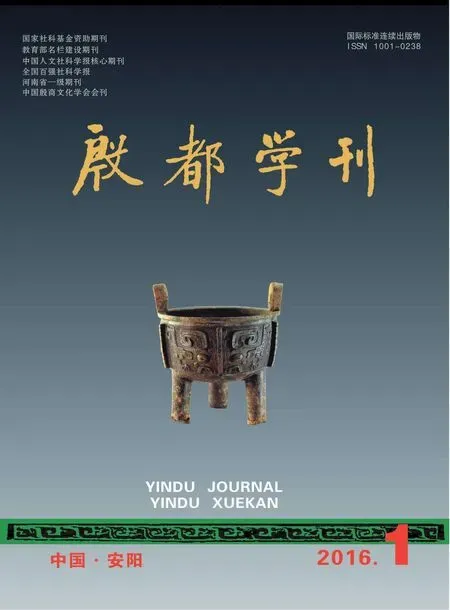安史之乱时期的墓志年号与河洛士人心态初探
2016-02-02王苑
王 苑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安史之乱时期的墓志年号与河洛士人心态初探
王苑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关于唐代安史之乱的史料文献,如宋人著录的《玄宗实录》、《肃宗实录》、《明皇幸蜀记》、《唐历》、《蓟门纪乱》、《河洛春秋》、《西斋记》、《天宝遗事》、《天宝乱离西幸记》、《汾阳家传》等十余种,时至今日,大多已经亡佚,或仅存残篇断简。并且,现存的正史记载,如新旧《唐书》、《通鉴》,其所记安史之乱中的一些情况,也颇有冲突抵牾之处,其中对叛军所记尤其如此。依据现有史料已难以对此断其正误。尽管如此,现存的唐人石刻资料中尚留有一些这一时期的材料。以此证史,我们可对安史之乱中的一些问题作具体分析,并亦可从中考稽探求此一战乱时期的胜败形势及士人心态的嬗变。
关键词:安史之乱;墓志;年号;士人心态
由《资治通鉴》所列看,关于安史之乱资料在宋尚有《玄宗实录》、《肃宗实录》、《明皇幸蜀记》、《唐历》、《蓟门纪乱》、《河洛春秋》、《西斋记》、《天宝遗事》、《天宝乱离西幸记》、《汾阳家传》等十余种。但是,这些书现在大多已经亡佚,或仅存残篇断简。但现有的正史新旧《唐书》、《通鉴》所记安史之乱中的一些情况,也颇有冲突抵牾之处,其中对叛军所记尤其如此。依据现有史料已难以对此断其正误。由上所见,现存的唐人石刻资料中尚留有一些这一时期的材料。以此证史,我们可对安史之乱中的一些问题作具体分析。
一、叛军的年号
安史之乱前后不足七年,却有四人称君。其年号也换了多次。史家对此的记载有些不一致。诸史皆记安禄山占东京后建燕园,年号是“圣武”。但对安禄山之后的事记载则有出入。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安庆绪是否有改元“载初”一事;二是其在相州改元是用什么年号。此事在宋已有分歧。现借助石刻资料,可定其是非。
《新唐书·逆臣传》叙及安庆绪篡弑安禄山之后,曰:“既袭伪位,改载初元年。”[1](P6421)但《旧唐书》与《通鉴》记此事时均未提及“改元载初”之事。现存这一时期的洛阳地区的墓志,在这一年,基本上是采用“圣初二年”纪年。其中有二月的《呼延府君夫人张氏墓志》,《贺兰公及夫豆卢氏墓志》,五月的《任金墓志》、八月的《曹公及夫人康氏墓志》、十月的《王清墓志》等。[2](P1721-1765)[3](P666-668)这些墓志在时间上前后相连。它表明这一年叛军控制区域仍是用安禄山年号。所谓改元载初一事并不存在。那么,安庆绪为什么没有按照惯例改元?《旧唐书·安庆绪传》称:安庆绪诸人弑安禄山之后,“因掘床下深数尺为坑,以氊罽包其尸埋之。又无哭泣之仪。庄即宣言于外,言禄山传位于晋王庆绪,尊禄山为太上皇。”[4](P5371)“严庄、高尚立为伪主。庆绪素懦弱,言词无序,庄恐众不伏。不令见人。”[4](P5372)安庆绪篡弑并取代其父实为一次政治内讧,名实皆为不正而不可告人。对此,他们当然不愿宣扬,其不改年号可能即是为此。“载初”是武后时期所用的一个年号,《新唐书》中不知是据何记载叛军改元一事。由上述墓志所用年号可见,叛军并无此年号。司马光《通鉴》不取《新唐书》之说,也有其依据,可能更符合史实。
《新唐书》在叙及安庆绪退守邺城时,曰:“以相州为成安府,太守为尹,改元天和。”[1](P6422)然而《通鉴》却言:“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元天成。”[5](P7042)《通鉴考异》对此有辨析,其曰:“《唐历》曰改元天和,《蓟门纪乱》曰改至成,与实录年号不同。《纪年通谱》两存之。实从《实录》。”[5](P7042)现存出土的《燕故□府君墓志铭》,其中有言:“继亲张氏,享年四十有三,天成年□□卒于家。”[2](P1475)而作于大历年间的《大唐故辛府君墓志铭并序》曰:“伪云天成二年七月十六日终于私第。”[2](P1762)这两方墓志都出现了“天成”年号,这是最可信的实证,它说明《通鉴》中的“天成”之说可信。《新唐书》《唐历》的“天和”说,《蓟门纪乱》的“至成”说,皆不足信。《通鉴》取于玄宗、肃宗《实录》,这些材料说明本书史实更可靠。然而,《蓟门纪乱》也有可与墓志相印证处。如《通鉴》于唐肃宗乾元二年引《蓟门纪乱》曰:“思明既杀乌孙恩,不称国家正朔,亦不受庆绪指麾,境内但称其某月而已。”这一点,在这一时期的墓志里也有反映。如《大燕赠赞大夫段公夫人河内郡君温城常氏墓志铭并序》曰:“享年八十四,以七月廿一日终于蓟县礼□□之私第。以其年十一月廿一日□殡于燕京城南□礼也。”[2](P1720)铭额称“大燕”,而文中不提年号,这与《蓟门纪乱》所说正是相符的。
二、唐军收复洛阳的时间
在安史之乱期间,中原一代存在着两个政权。这一时期的墓志也因葬地与葬时的不同,使用的年号也不一样。战争期间,壁垒分明,极少会在一方的控制区内使用对立方的年号。因此,墓志上的年号是与双方对某一地区的控制权联系在一起的。其时东京两度易手,我们可依据墓志材料具体说明双方进驻洛阳的时间。
《通鉴考异》对唐军收复东京的时间作了辨析,曰:“《实录》云:‘(至德二年十月)庚申(十六日),庆绪走,其夜至东都苑,帅其众党奔河北。壬戌(十八日),元帅广平王破贼于陕西,八日收洛阳’。《年代纪》:‘十月己未(十五日)破贼于新唐,辛酉(十七日),庆绪奔河北,壬戌(十八日),广平王入东京。’《新纪》:戊申(四日)贼败新唐,克陕郡。壬子(八日)复东京。按陕、洛之间几百里,《汾阳传》、《新纪》太早,今从《年代纪》、《幸蜀纪》。”[5](P7040-7041)诸家所记唐军收复东京的时间略有不同,其中《新唐书·肃宗纪》所记与《通鉴》所记,出入颇大,其说取于《汾阳传》,现存《安禄山事迹》亦与此同。其曰:“十月六日,又收东都。”[6](P42)它们所说的唐军收复东京的时间,都早于《通鉴》十日。
《通鉴》所据是《实录》,由其时所存的二方墓志,看此说比较可信。一为《王清墓志》,有云:“以圣武二年九月廿四日反(返)真于观虚室……以其年十(月)六日葬于洛阳之北石槽也。”[3](P668)其二为《长孙夫人阴堂文》,曰:“未及归京师,权安厝于大茔北十五步之原礼也。葬用圣武二年十月十七日。”[2](P1719)这两方墓志作者在十月六日与十月十七日仍用圣武年号,可见,唐军收复东京不会早于十月十七日。《实录》可信,而《新唐书·肃宗纪》、《安禄山事迹》所叙皆不可靠。《通鉴》取《实录》,可谓精审。
三、在叛军二占东京期间士人心态的差异
战乱中,叛军两度攻占东京,安军与史军的实力不同,其与唐军的力量对比,前后也不一样,而当时人们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同。这由当时的墓志中实用的年号,也可看出这一情况。
安军反叛之初,尚有高尚、严庄等士人参与,并接受了一批降官。唐军在洛阳一带是全面溃败,故而容易造成一种改朝换代的势头。如现存的《陈牟少墓志》中有云:“(夫人李氏)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八日寝疾弥留,终于东京铜马拖里第,享年七十二。无何,会燕朝革命,天宝十五载正月一日改为圣武元年,兹年五月十三日迁葬就府君早穴合葬。”[2](P1725)足见,其时人们正以改朝换代的观念看待这一事实。叛军第二次占据东京,时间从乾元元年(758)九月庚寅(二十七日)至宝应元年(762)十月乙亥(三十日)。但唐军这次不是战败溃退,而是有策略的撤退。《通鉴》云:“(李光弼)遂移牒留守韦陟使帅东京官属西入关。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帅吏民出城避贼,空其城,光弼帅军士运油铁诸物,诣河阳为守备。”[5](P7082-7083)唐军一直存于洛阳周围,史军控制的范围比安军首次攻占东京时自然要小。同时,经过这一次波折之后,士人们对唐室也恢复了一定的希望。这一时期,洛阳一带的墓志也以用叛军年号为主。如有:顺天元年十一月的《刘君及夫人邓氏合葬墓志》、顺天元年十二月的《李庭训及夫人崔上直合葬墓志》、显圣元年六月的《司马望墓志》、显圣二年七月的《孙君墓志》。但是,即使是在洛阳一带,仍有用唐室年号的。如《张备夫人李三娘墓志》曰:“上元元年十一月七日终于河南南县安全里……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合葬于□勒之山左也。”[3](P682)史思明虽已于上元元年闰四月正式进入洛阳,但其实力多被牵制在河阳与李光弼对阵,对地方的控制还力不从心。此家墓地在河南县安全里,近在洛阳城外,故仍能用唐室年号。这反映了其时人们仍心存唐室,并不想承认史思明政权。
杜甫《悲陈陶》言:“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杜甫是在叛军占领长安时写下此诗的。当时,唐军大败,叛军气焰正炽,而杜甫看到城中百姓人心仍对唐王室存有希望。在唐军收复两京之后,百姓就应对唐朝廷更有信心了。这种人心向背的问题,我们今日也可以由石刻文献中得到更真切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五代)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王守雪]
中图分类号:I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16)01-0066-03
[作者简介]王苑(1989—),女,山东济南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与文论。
[收稿日期]2015-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