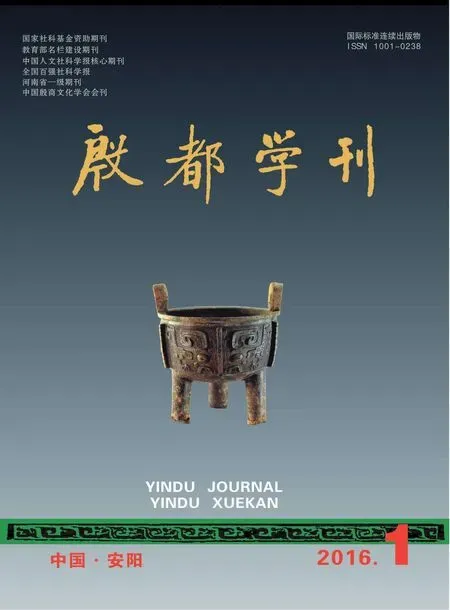杨亿《汉武》唱和组诗新探
2016-02-02陈梦熊
陈梦熊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杨亿《汉武》唱和组诗新探
陈梦熊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杨亿等人所作《汉武》唱和诗是针对真宗朝“西祀”、“东封”和“祥瑞”频降的现实政治有感而发,绝非单纯意义的“以学问为诗”。传统认识中对杨亿及其“西昆派”的认识有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有必要加以厘清。以真宗封禅泰山的真实动机、真宗皇帝与杨亿的微妙关系,以及真宗朝士人文人对杨亿的界定和他们对待“西祀”、“东封”的态度,将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杨亿等人寄寓在《西昆酬唱集》中《汉武》唱和组诗的真实情感。
关键词:杨亿;《汉武》唱和组诗;讽喻
引言
《西昆酬唱集》本为杨亿等馆阁臣僚编纂《册府元龟》之余应酬唱和之作,其中一组《汉武》唱和诗,后人多有争议。《瀛奎律髓汇评》卷三引纪昀评:“此便欲真逼义山。”又《汉武四首》之二,方回评:“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没”一句为“言兴亡之运,理所必有,虽汉武帝之力矩心劳,终亦无如此之何也。”[1](P127)即是认为此组唱和诗乃有感而发,是讽喻宋真宗。王仲荦《西昆酬唱集注》就指出此诗是:“馆臣之为诗讥讽汉武,实即欲以谏帝并止其东封也。”[2](P42)此说当否,值得商榷。巩本栋教授即认为:“论者或以为是谏真宗信王钦若之说,造为祥瑞,东封泰山。其实,宋真宗东封泰山要在作此诗两年之后,很难相信诸位馆臣当时已有此先进之明。”[3](P166)而罗争鸣先生更是据巩本栋教授的观点和自己考证,认为此组诗歌“是杨亿等秘阁文人在编修《历代君臣事迹》时,在披览典籍、分类部居、采摭铨择之际对历史典故的感怀之作,也是对传统题材的再抒写,不必作‘过分诠释’。”[4](P26)两种观点似各有其合理之处,却又难以令人完全信服。二派的观点何以由此矛盾,关键在于后者缺乏从历史维度审视问题的意识,非但没有从真宗朝的历史背景入手考察杨亿对待宋真宗西祀东封的态度,也忽略了杨亿与真宗的微妙关系,从而没有准确把握到真宗朝士大夫群体走向分化的趋势,也就无法从社会背景的角度去解读《汉武》组诗。
本文将从真宗封禅泰山的真实动机、真宗皇帝和杨亿的微妙关系,以及真宗朝士人文人对杨亿的界定和他们对待“西祀”、“东封”的态度,对《汉武》组诗给出合理的解释。
一、借古讽今是“《汉武》组诗”的本质
围绕着《汉武》组诗的争论形成了两派观点,矛盾的焦点在于此组咏史诗是否为讽喻宋真宗封禅泰山而作。以此问题为原点,双方各自拿出了自己的证据。认定其为讽喻诗者指出:“此诗有说讥武帝求仙,徒费心力,用兵不胜其骄,而于人才之地不加意也。”[1](P127)否定其为讽喻诗者虽表述各有不同,观点基本一致:巩本栋教授从杨亿等人作《汉武》组诗早于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封禅,不可能预见未发生之事,是从逻辑层面否定了其作为讽喻诗的合法性;罗争鸣先生则认为这不过是后人的过度诠释,《汉武》组诗是宋人“以学问为诗”的掉书袋式行为的具体表现,是从宋人作诗方式进行理解的产物。
笔者并不能认同二位先生的观点。所谓“咏史诗”究竟是单纯的炫耀学识,或者是“寄寓深意”需要我们加以辨析。人们讨论某一时期的历史、或者是点评某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可避免地带入当下语境的思考。“真实的情形往往是,对未来的估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应回忆哪些历史,凸显哪一部分过去,强调什么样的一场,突出何种传统。所以,任何所谓的‘回顾’、‘检讨’,几乎都是有立场,有预设的。历史不是自我呈现的,而是被叙述的。”[5](P165)杨亿等人汇集于馆阁中编纂的《册府元龟》原名《历代名臣事迹》,其编纂目的绝非一般意义的类书集成,而是要为帝王治理天下服务。身兼此等重任肯定让杨亿等人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倍加小心,也不免在编选“祖宗故事”、“历代事迹”的同时融入他们对真宗朝现实的思考。
真宗朝最大的现实在两点:其一是“澶渊之盟”,其二是“神道设教”。二者相互渗透,前者是源头,后者则是延伸。巩本栋教授以真宗封禅在《汉武》组诗两年之后作为否定的证据,是将《汉武》组诗理解为真宗封禅泰山的实录,未免有一一坐实之嫌。历史的真相是,封禅绝非真宗皇帝一时兴起,而是他本人和部分朝臣共同努力、悉心营造的结果。真宗朝是赵宋王朝从“得天下”到“治天下”的转折点,“作为有宋建国以来生长于承平之世的第一代帝王,他一方面缺乏太祖、太宗般把握政治局势的能力,一方面又急切于建树个人的形象和统治权威。”[6](P298)他需要寻找一种方式凸显自己的地位,使自己能够成为与太祖、太宗并列的圣君。
契丹既受盟,寇准以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钦若忌准,欲倾之,从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帝愀然曰:“为之奈何?”钦若度帝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惮旦,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以圣意喻之,宜无不可。”乘间为旦言,旦黾勉而从。[7](P1329)
正是在王钦若的提醒之下,真宗皇帝意识到“澶渊之盟”是对“天子”崇高地位的沉重打击,就更加急迫地要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以及寻找自己统治下的赵宋天下已迈入“太平盛世”的各种证据——天降祥瑞和西祀、东封则成为最有简便易行的选择。“澶渊之盟”是真宗朝政治生态发展的转折点,它直接促成了“天书”、“西祀东封”等事件的发生。我们不仅可以在正史中可以找到真宗皇帝和王钦若的对话,也能在宋人的笔记中发现类似的记载。司马光《涑水记闻》中就写到:“王冀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莱公于真宗,真宗曰:‘然则如何可以洗此耻?’冀公曰:‘今国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闻之,庶几不敢轻中国’。”[8](P120)两段记述大致相同,后者多出了“引天命以自重”的表述。此一句道出了真宗封禅的真实目的。在“镇服海外、夸示外国”的外衣下,真宗皇帝和他的臣僚们为了洗脱“澶渊之盟”的耻辱开始了一次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融合着证明赵宋政权合法性和粉饰太平于一炉。非但帝王将相无法置身其外,即便是曾经明确表示反对符瑞的寇准,也在遥远的雷州献上了“祥瑞”,这是真宗朝最大的现实之一。面对此种情景,士大夫阶层不可能提前毫无觉察。他们或是主动投身于其中、或是持观望态度,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只是在自己的心中和笔下表达自己对这场“造神运动”的态度,杨亿的态度表明他是不支持宋真宗亲自发动的造神运动。正如邓小南教授所言:“面对接踵而来的天书、封禅诸事,他们不得不选择自己的立场。登基已近十年的真宗,不仅凭借其帝王身份,也依凭其统治经验,在听信于王钦若、丁谓等人的同时,笼络住以王旦为首的国家行政班子,容忍了或明或暗的抵制与批评,也利用了大批不能淡忘于进身之途的文人。”[9](P322-323)
关于杨亿的态度,我们可以从他为真宗起草的封禅诏书被修改一事中见出端倪。他奉命起草的封禅诏书有一句“不求神仙,不为奢侈”,被真宗皇帝下令改为“朕之是行,昭答玄贶;匪求仙以邀福,期报本而洁诚。”*李焘《续修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所谓“不求神仙,不为奢侈”是采用为尊者讳的表述方式,委婉地掩盖了真宗封禅的真实目的。真宗默许之下的修改强调“匪求仙以邀福,期报本而洁诚”,表面的意思是说自己的行为是酬答上天所赐的祥瑞,并非是“粉饰太平”。对比之下,我们发现:杨亿的封禅诏书是试图为真宗封禅的真实目的“装点门面”,其反对封禅的态度不言而喻;而真宗授意的修改则直接暴露了内心最真实的想法。由此可见,杨亿对真宗“封禅”的真实动机可谓洞若观火,接下来将要发生的西祀东封就不是无法预计的未来,而是必将发生的“事实”。因此,他在唱酬之余借由汉武故事讽喻真宗也在情理之中。
所谓“神道设教”则是真宗朝另一不可回避的重大事件,它直接表明了真宗对待封禅的态度,以及他向臣民解释为何要“西祀”、“东封”的动机。《周易·观卦彖辞》即有“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孔颖达疏曰:“此明圣人用此天之神道以观设教而天下服矣。天既不言而行,不为而成,圣人法则天之神道,本身自行,善垂化于人,不假言语教戒,不须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观化服从,故云‘天下服矣’。”*《周易正义》卷三《观卦》载王弼注.“神道设教”本是儒家为圣人设定的教化之道,由于圣人能够掌握自然万物的运行法则,为了能够教化民众、使其理解自然、遵从自然,选择以“神道设教”的方式在普通人与自然之间搭建起信息沟通的桥梁。宋儒对于“神道设教”有着更为实际的理解,他们没有阐发汉儒“应天感人”的学说,而是将其与宋代社会的现实联系在一起,更加强调统治者对民众的教化。司马光认为:“君人者能隆内杀外,勤本略末,德洁诚著,物皆信之,然后可以不为而成,不言而化,恭己南面,颙然而已:所谓‘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也。”可见宋代士大夫们并不否认“神道设教”的合法性,而是多了一些现实的考量,“天道”的神圣性也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
如果将汉代的祥瑞、天命理解为臣子在帝王暗示、默许下的操作,真宗皇帝则是亲自登台,参与到“神道设教”的具体操作中。在大中祥符五年,他本人曾亲作《祥瑞论》颁发给臣僚。此书今已不可见,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大旨以明王虽有丕祥,常用祇畏,中人一睹善应,即自侈大。圣贤思以防邪,故《春秋》不书其事;然神祇降监,亦以扬祖宗之烈,当钦承而宣布之。若恃休期以自肆,固宜戒也。”将“神祇降监”的“天书”、“祥瑞”阐发为“扬祖宗之烈”不能不说是真宗皇帝的发明,既是为了转移“澶渊之盟”带给自己的耻辱感,也是维护赵宋政权唯一性、合法性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但在当时并非没有人质疑所谓“天书”,《曲洧旧闻》记载:“祥符中天书降,有旨云:‘可示晁逈。’逈云:‘臣读世间书,识字有数,岂能识天上书?’”[11](P88)
综上所论,以真宗一朝的社会现实而言,杨亿等人面对天书、符瑞频降的景象,内心没有任何想法是不可能的。但臣下的身份又决定了他不能采取太过直露的方式去表达个人意见,借吟咏历史为载体的《汉武》组诗是他们表达讽喻之志的最佳方式。
二、《汉武》组诗的历史背景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当代学界对杨亿及其《西昆酬唱集》的传统认识。尽管很多人对于杨亿及其编纂的《西昆酬唱集》多持否定态度,或认为“西昆体带有浓厚的贵族趣味”;或视其为馆阁臣僚的唱和之词,与社会现实无涉。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说他们写诗的目的是‘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写出的诗,其题材范围必然是比较狭隘的。”[11](P30)学术界也有其他的声音,曾枣庄先生在《怎样读〈西昆酬唱集〉》一文中指出:“大中祥符元年(1008),王钦若等迎合真宗意旨,伪造天书,议封泰山。杨亿不以为然,被命草东封诏,他以‘不求神仙,不为奢侈’之语规讽真宗。”学界不同的声音提醒我们,对待杨亿及其《西昆酬唱集》应持谨慎态度。
就杨亿的道德品质而言,在当时得到了士大夫的普遍认可,欧阳修就有“性特刚劲寡合”的评语,苏轼也赞其为“忠清鲠亮之士”。这提醒我们并不能将杨亿仅仅视为润色鸿业的“文学侍从”,在他的身上体现着宋代士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而乐”的高贵品质。
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诰杨亿尝草答辽人书,云“邻壤交欢”,帝自注其侧,作“朽壤”、“鼠壤”、“粪壤”等字,亿遽改为“邻境”。明日,引唐故事,学士草制有所改为不称职,亟求罢,帝慰谕之。它日,谓辅臣曰:“杨亿真有气性,不通商量。”及议册皇后,帝欲得亿草制,使丁谓谕旨,亿难之。谓曰:“勉为此,不忧不富贵。”亿曰:“如此富贵,亦非所愿也。”乃命它学士草制。(孔平仲《谈苑》)
杨亿的品性不仅表现在人格层面,也落到现实政治操作层面。在写给辽国的国书中,他所用的文辞本为外交常用辞令,却令真宗感到不悦。根本原因是宋辽两国的关系绝非“交欢”,而是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杨亿触及到真宗脆弱的心理防线,有其迂腐的一面。但在围绕是否着册立刘娥为皇后的原则性问题上,杨亿没有屈从于真宗,反倒给出“如此福贵,亦非所愿”的答复,展现了士大夫的气节。综合考察上述两个方面,我们基本可以描绘出杨亿的历史面貌——他的身上兼具儒家文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也掺杂了不知权变的迂腐。
以诗作为例,杨亿将《受诏修书述怀三十韵》置于《西昆酬唱集》之首,诗中有“危心惟毅棘,直道忍蓬藤”之语,颇有身居高位者谨言慎行之感,正体现了杨亿为宦的谨慎,而非阿谀者嘴脸。“与宋初馆阁宰辅大臣徐兹、李防、李至、吕端等五代旧臣和宋朝宰辅相比,与真宗朝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抛弃原则依附皇权的馆阁词臣相比,杨亿作为西昆体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具有自觉的独立于皇权的人格意识,在他身上体现出有宋一代士人典型的气质人品。”[12](P6)笔者认为,视杨亿及《西昆酬唱集》为贵族文人唱和之作的观点弱化了它的精神内涵和审美境界。方智范先生就曾指出,将馆阁文人视为宫廷诗的主力是不错的,但不能据此认定他们的诗作都是贵族趣味,而是需要慎加甄别。对于杨亿的认识同样是如此。
厘清杨亿与真宗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对于理解《汉武》组诗的真实含义十分重要。
蓬莱银阕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溥金掌费朝餐。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李庆甲汇编校点 :《瀛奎律髓汇评》卷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7 页.
上面是杨亿所做《汉武》诗,充分体现了西昆派诗人高超的写作技巧和丰赡的学术素养,展现出鲜明的馆阁文学色彩。罗争鸣先生根据诗中大量引用典故的写作技法,并参考其他几位唱和者的《汉武》诗,指出“杨亿、刘筠、刘骘等人的《汉武》诗,主题并无多少创意,仍是感慨神仙虚幻、汉武妄求而不得的人生悲剧,进而表现惯常的讽喻之旨。就风格来说,这七首诗大掉书袋,用典繁密,不熟悉《孝武本纪》、《武帝纪》、《汉武故事》、《博物志》等原典,几乎不能全然了解。”[4](P27)似乎是要彻底否定杨亿等人写作此组唱和诗的讽谏意味。他还援引杨亿所做《大宋天贶殿碑》,认为此文详细记述了“天书”发现的经过,从而证明杨亿并未明确反对真宗封禅。事实上,这种官样文章对于词臣出生的杨亿而言,不过是官场的形式而已,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内心真实的想法。至于“八年八月庚寅,知汝州杨亿言,粟一本至四十穗。”[13](P3609)就更是无以作为例证,为官者久离枢要,为谋求仕进、或求得更好的境遇向皇帝献上祥瑞是自古以来官场中就很常见的事情。将其作为理解诗歌的例证,甚至是延伸为判断某人品格高下的证据,就很难保证不陷入理解的误区。
杨亿等人所作《汉武》组诗的确有堆砌辞藻之嫌,但真正的用意却不是炫耀学识,更多是追求“下以诗讽上”的现实目的。罗盛鸣先生曾指出杨亿并不反对真宗封禅,就宋人所著《儒林公议》的记载来看,事实并非如此。书中记载:“杨亿虽以辞艺进,然理识清直,不为利变。……朝廷议封禅,亿谓不若爱民息用为本。复为邪佞所排,眷宠浸衰矣。”《儒林公议》为田况所著,其人为仁宗天圣八年进士,著者官至枢密使,其书对太祖至仁宗朝野之事多有记载。根据此书所记,杨亿在朝廷讨论封禅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意见,认为“不若爱民息用为本”。根据书中记载,杨亿对于“朝廷议封禅”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并直接导致失宠于真宗。
问题讨论至此,我们不禁会产生如此的疑惑:为何杨亿的言行存在不一致之处?究竟何种面貌才是最真实的杨亿?
这种现象在中国传统文人的身上并不罕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情况。一方面,他们将自己作为圣人的弟子,希望逢遇明君、实现“得君之助”的梦想,从而完成“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臣下的身份和僚属的地位使得他们只能仰人鼻息,在不断揣测圣意的宦海沉浮中度日。二者的紧张关系塑造了士大夫阶层微妙的心态:当他们憧憬着宏图大志时就会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的诗句;而当他们陷入人生迷茫时,又会写下“古来圣贤皆寂寞”的叹息。当诗歌不再作为外交辞令时,诗人们往往是将其作为疗治心灵创伤的药剂。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去幻想,只有那些愿望难以满足的人才去幻想。幻想的动力是尚未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14](P2)对于杨亿而言,修齐治平的人生愿景早已被真宗“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的追求所摧毁。于是,寄居于“昆山之西”、“藏玉之室”的生活就是他最理想的选择。但他却无法超脱于“西祀”、“东封”的现实政治,转而以诗为讽喻的工具诉说自我对现实的看法。一组《汉武》唱和诗讲述的故事看似是典故的炫耀、辞藻的堆砌,实际却是对现实最直接的控诉。诗中所谓“神仙”事并非是指汉武帝求仙访药的史实,而是直指真宗导演的种种闹剧背后“引天命以自重”的真实目的。
杨亿以《汉武》诗讽喻真宗并非他个人行为,我们可以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寻觅到相同题材的诗作。以崔遵度和杨亿《属疾》诗为例:
李白羹初美,相如渴渐疗。八砖非性懒,三昧减心忧。笔苑多批风,词锋胜解牛。
旧山疑鹤怨,畏日想云愁。广内劳挥翰,通中羡枕流。使星方屡降,客辖未容投。
好奏倪宽议,何须庄舄讴。朝衣熏歇不,侍史待仙洲。
此诗多用典故,带有浓厚的“西昆体”色彩。崔遵度所用“倪宽事”语出《汉书》,是劝喻杨亿顺从真宗心意——即附和封禅事。可见当时士人对真宗封禅的认识是清醒的,而他们对杨亿反对封禅的态度也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将《汉武》唱和组诗认定为讽喻真宗西祀东封当无疑义。
[参考文献]
[1]李庆甲汇编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上[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27.
[2]王仲荦注.西昆酬唱集注·卷上[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1.
[3]巩本栋.关于唱和诗词研究的几个问题[J].江海学刊,2006,(3):166.
[4]罗争鸣.<汉武>唱和诗述议——兼论<西昆酬唱集>的缘起与特征[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26,27.
[5]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J].历史研究,2004,(1):165.
[6]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J].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298.
[7]脱脱.宋史·王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8.1329.
[8]司马光.涑水见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9.120.
[9]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322—323.
[10]朱弁.曲洧旧闻[M].北京:中华书局.2002,88.
[1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0.
[12]方智范.杨亿及其西昆体再认识[J].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6):6.
[13]王应麟.玉海[M].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3609.
[14]胡经之,伍蠡甫.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读·下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
[责任编辑:王守雪]
中图分类号:I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16)01-0069-05
[作者简介]陈梦熊(1984—),男,湖北恩施人,西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收稿日期]2015-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