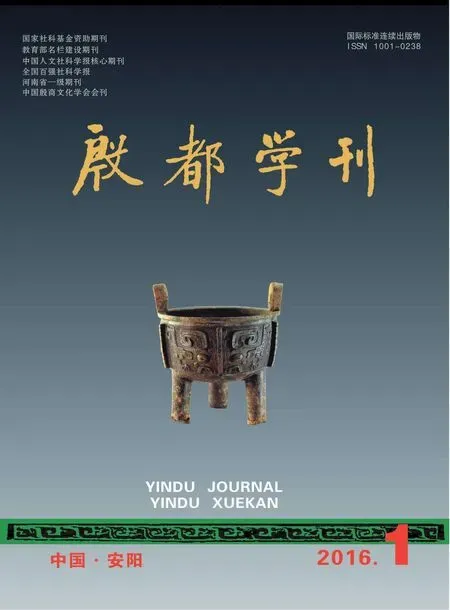从商周都邑看早期城市功能的发展
2016-02-02惠夕平
惠夕平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从商周都邑看早期城市功能的发展
惠夕平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城市与国家起源、文明起源息息相关。城市功能是城市存在的本质特征,商周城市是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构成要素都可以在商周城市中找到渊源。本文从人口积聚、防御、政治和社会、智慧和知识、祭祀和礼制、手工业生产、经济和市场等几个方面讨论了商周城市的功能及其特色。
关键词:城市功能;商周;都邑
近世以来特别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经过系统调查和发掘的商周都邑聚落已达十数处。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聚落考古研究方法的普遍推广应用和考古学新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周都邑布局形态日趋清晰,在补充和丰富文献记载之不足的同时,也为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重要资料。许多学者对中国古代早期城市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如主辅都制度、城郭制度、两城制、三城制等,取得了丰硕成果,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传统的都邑研究以城市形态探讨为多。城市形态是透视城市功能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现代城市形态主要是对城市物质肌理、塑造城市各种形式的人以及社会经济和自然过程的研究。[1]考古和历史学中的古代城市形态研究,主要着眼于城市空间布局和城市物质形态的研究,前者着重考察古代城市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如宫殿宗庙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平民居住区在城市内外的分布、组合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状况;后者着重考察构成城市组成部分的形态、结构和功能。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并不是单纯的前后承继关系,同样,在都邑形态和功能研究上,单线进化的思维亦不可取。应当承认,不同地区、不同背景下的城市发展存在着区域差别,至少在早期城市诞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这种区域差别即已经开始显现,在不同的景观背景下,不同族群发展了各具特色的城市聚落形态,这也造就了世界不同地区早期城市功能的多样化。本文拟结合相关资料对考古所见的商周都邑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国内外学者对早期城市功能的定义和研究
城市功能是城市存在的本质特征,是城市系统对外部环境的作用和秩序,不同地区、不同背景下的城市具备不同的功能。在芒福德的著作中,他将城市活动划分为两个相互区别的方面:一个是一般的人类功能,它是普遍存在的,只是有时被城市的构造所强化和丰富了;另一个是城市的特有功能,是城市的历史渊源及其独特的符合结构的产物。[2]福克斯和特里格等学者将其定义为“处于一个城市中心的各项活动和机构”。[3]对于史密斯来说,城市功能是其探讨的城市化进程的四个维度之一,它与城市形态、城市生活、城市含义等共同构成了功能视角下的城市定义的主要内容。在其文章中,史密斯将超出自身所在地方“在一个区域内影响人群的行为和机构”称为城市功能;[4]布兰顿在他的文章里对早期城市功能的多样性进行了讨论,如祭祀中心与酋邦、市场体系与早期城市等,他还对中国早期城市的市场体系进行了关注。[5]类似的研究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虽然布局和功能分区研究较多,但与国外学者注重早期城市功能多样性研究相比,国内的同类研究相对较少。相关研究大多围绕行政管理功能和防御功能等问题展开,与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相关的王权探讨较多,围绕交换、市场、手工业等角度的探讨较少。这一方面源自于中国考古学的文化历史定位,也与早期学科的发展和交流相关。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等相关理论和方法的介入较少,类似的研究便开展较少。随着考古学跨学科趋势的日益发展和更多新技术的介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在逐渐拓展。
二、 考古所见的商周都邑性聚落及其功能发展
在《城市革命》一文中,柴尔德提出了早期城市的10个特征要素,分别是:比之前聚落既广且密的人口和城市规模;不同于村落的人口结构和功能;剩余产品的集中;纪念性公共建筑;脱离生产的统治阶层的存在;文字和科学的发明;代数、几何等其它科学的精密化发展;集中社会剩余产品供养的其它人员的出现;经常性的长途“贸易”,以交换本地没有的原料;专职工匠的存在。[6]虽然柴尔德所提出的这十条标准被一些学者认为带有种族中心主义的色彩,其关于农业和剩余产品推动城市产生的观点也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我们还是可以借鉴其中的一些探讨来考察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特色。
目前,考古所见的商周都邑聚落主要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殷墟、丰京、镐京、成周(洛邑)、东周王城以及为数众多的列国都城如郑韩故城、齐都临淄、晋都新田、赵都邯郸、鲁国故城等等。下文将从人口积聚、防御、政治和社会、智慧和知识、祭祀和礼制、手工业生产、经济和市场等几个方面对商周都邑建设所体现出的城市功能进行探讨。
1.人口积聚
如同柴尔德所提出的,城市革命在人口统计学上会有反映,最早的城市代表了一批拥有前所未有数量人口的聚落单位。[7]因此,城市最基本的功能便是承载人口。这与《说文解字》“城,所以盛民也”相一致。在新时期时代晚期以来的考古学研究中,人口逐渐集中的现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早在新时期时代晚期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人口向中心聚落的集中便已经出现,与这一过程紧密相联的,便是次级聚落规模的缩小和中心聚落规模的膨胀。[8]这一过程,也正与中国早期城市的产生密切相关。在中原地区这一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尤其是都邑性聚落的膨胀更是滚雪球般地迅速发展。龙山晚期的新砦古城寨、王城岗与新砦分别只有17万平方米、30万平方米和100万平方米,二里头则首次达到了创纪录的300万平方米,郑州商城和殷墟的面积则分别达到了1300万和2600万平方米。大量的城市及城市外围人口的存在是维持早期城市发展的基础力量。都邑的膨胀和人口的吸引必然导致周边人口的减少,一些学者因之将商周视为“城市国家”,如侯外庐先生由“邦”“封”“城”“国”入手对商周社会的探讨,[9]以及学者宫崎市定等人所推想的中国古代的“都市国家论”[10]等,可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状况。
2.防御
与人口的积聚相密切联系的便是早期城市的防御功能。一般说来,防御是城市聚落尤其是周围施以围壕和高大城墙的城市的另一重要功能。《谷梁传·隐公七年》“城为保民为之也”也正是这个意思。包括自然地形地貌、河渠水道、人工建筑、城市布局和聚落体系等构成了早期城市防御文化的重要内容。防御功能已有学者研究较多,此处不再赘述。[11]
3.政治与社会
在早期城市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将管理职能视作城市中心的基本职能。政治角度是探讨早期城市功能的重要着眼点,一些学者将早期都邑视作早期王权的物化形式。[12]具体到中国青铜时代的商周时期,更具有自己的特色。商周都邑发展与王权的发展和礼制变迁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夏商周王权是早期邦国君权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的王权行使在王权国家的范围内,它不但支配着本邦,也支配着其他属邦。[13]与新石器时代等早期城市的发展相比,商周时期的都邑变迁清晰体现出了王权的加强和异化。一方面,相对封闭且独立的宫城的出现和成熟,显示出这一时期王权在行政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在二里岗时期,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核心的王朝都邑及其周边地区的一系列同时期城址如垣曲商城、焦作府城、盘龙城等构成了一套整齐划一、等级严密的城市聚落体系。这一时期城市的空前发展延续了二里头遗址以来的都邑布局和规划思想,但又与前期有明显区别。根据学者的研究,作为首次出现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首都,二里头遗址开始出现了面积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大型围垣作坊区和纵横交错的城市主干道,[14]但尚未发现象征礼仪等级和封闭性的完备城郭存在,目前的发现仅仅出现于郑州地区——大师姑、望京楼等二里头文化夯土城墙的出现既与地处中原的重要位置有关,也与历史渊源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在二里头二三期之际文化交流碰撞区域先后出现的一系列夯土城墙城邑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王权的竞争和加剧。随之而来的二里岗都邑建设从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显示出空前的向心力和文化统一性,表明这一时期以军事殖民为后盾的王权扩张达到了第一次顶峰。这一时期王权的强化不仅仅表现在区域角度,即使在都邑的内部,“宫城——内城——外城”等封闭性明显、等级清晰的三城制的可能存在和出现,[15]昭示了这一时期至高无上的王权和秩序的确立。到了晚商西周时期,族邑特征明显的都城建设成为发展的主流,尤其是前者,族群架构下的城市和国家体制一目了然。[16]西周晚期开始,中央王权开始受到挑战,与此相适应,都邑的布局开始出现显著变化。代表这一变化的便是两城制的出现。“两城制”的概念最早由徐苹芳先生提出,[17]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宫城—郭城的布局模式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反映了这一时期王权的异化和发展。当然,这不仅仅与王权的异化相关,也同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有密切关系。
4.智慧和知识
自诞生以来,中国古代早期城市就一直是知识和智慧的承载者,居住于其中的贵族阶层垄断了文字体系和知识的解释与传播,这从文字符号的发现和流转可以看出。早期的文字或刻画符号大多发现于中心性聚落遗址,莒县陵阳河、双墩、丁公、高邮、陶寺等等概莫能外。进入青铜时代以后,随着早期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文字被进一步垄断。商代前期的文字主要发现于南关外、商城、小双桥、台西等遗址,后期的文字材料主要见于殷墟,尽管都城以外的地区也偶见文字材料,但数量极少。殷周甲骨文主要发现于都城,记录和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从甲骨材料的加工、制作,贞人的占卜和甲骨的刻写等方面来看,文字牢牢地掌控在社会上层的贵族手中,成为社会上层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这一时期的都邑城市也就理所当然地承担了知识承载和传承的使命。
实际上,作为知识和知识的承载者,早期城市的这一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文字体系上。都邑城市的规划也反映了早期的宇宙观和信仰体系。[18]早期宇宙观对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早期农业民族而言,掌握天象规律并进而敬授民时却往往成为最原始的权力来源”,[1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早期城市本身即是当时知识和信仰的体现者。
5.宗庙祭祀
在考古和人类学家的研究中,一些早期城市即是由史前时期的祭祀遗址发展而来,之后宗庙祭祀逐渐与行政管理职能相结合。商周都邑中留下了大量的宗庙祭祀遗迹,且都位于都邑的核心位置。“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突出表现,祭祀和礼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文献记载的这一内容把城市与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连接者二者之间的纽带则是对宗庙先君之主的祭祀。应当指出的,商周时期统治者的祭祀,并不仅仅代表着其个人,而是代表其治下的所有民众而举行的国家祭祀。这样,宗庙的建立和祭祀活动的开展就成为商周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王权统治者也因此自然而然地获得了维系其统治的权力。
6.手工业生产
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重要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便控制在中心聚落内,这也是后世所流行的朝贡体系的最初内容之一,通过控制重要手工艺品的生产、分配和流通,早期国家的统治者们不断强化其权力。到了青铜时代,通过周边方国的供纳和中央政府的册封和赏赐,夏商周时期中国早期朝贡体系已经基本成形。作为青铜时代发展巅峰的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生产和铸造一直控制在都城中。自二里头文化后期开始,青铜礼器已经逐渐开始取代传统的陶器和玉器成为新的社会地位的代表。统治者严格控制青铜冶炼技术并掌握着再分配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不同的等级和爵位制度。二里岗时期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发现了大规模的青铜冶铸作坊,并且这种传统一直贯穿于商周时期的整个过程。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冶铸作坊被严格限制在都邑内部并建立了围垣,以便加强控制。有学者认为,这表明二里头时代聚落内部社会层级间的区隔得到强化。[14](P62)到了二里岗时期,郑州商城内的冶铸作坊虽然没有设置于具有高大城垣的内城之中,但仍然置于都城内部的专门区域。青铜冶铸作坊、骨器制作作坊、陶器生产作坊等成为商周时期都邑城市中的主要手工业门类,显示出其在城市中的重要地位。
7.经济和市场
早期城市的经济功能目前讨论较少,尽管一些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将交换或贸易视作早期城市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至少在东周之前的城市中目前尚未见到与“市”明确相关的材料,这并不能排除城市功能讨论中交换和贸易因素的存在,但由于考古材料的限制,相关研究的难度比较大。商和西周早中期的诸多都城遗址中均未发现明确的交换或贸易场所存在。在文献记载中,东周时期似乎已经开始了依照不同职业安排城市居民区域的实践,如《管子》所记载的“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公贾近市”,《国语》所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等。这或许反映了当时学者对城市区划的理想展望,但都邑考古实践中已经发现了明确的“市”之存在,如秦雍城中发现的“市”。“市”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80米,南北宽约160米,四周是厚1.5-2米的夯土夯土围墙基址,四面墙的中部各有一座“市”门。[20]其它战国都城中也有一些类似遗迹的发现,学者多有讨论,此处不再赘述。[21]
三、结语
城市与国家起源、文明起源息息相关。传统上对早期城市的政治和军事防御等功能讨论较多,但实际上一座城市往往担承着多方面的功能。城市一方面是特定社会机构活动的中心,同时,这些机构又通过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换把各地区连接在一起。充分发掘传统的政治和军事防御之外的功能,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机制、发展及自身特色具有重要的意义。商周都邑功能的发展,经历了由王权主导下的政治军事功能为主、容纳社会大多数人口和垄断重要手工业生产和知识传播,发展到后期的经济和交换日益突出、古典王权由发展成熟而逐渐走向式微,从而为中古时代社会变迁和成熟城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张蕾.国外城市形态学研究及其启示[J].人文地理,2010,(3):90-95.
[2]刘易斯·芒福德,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101.
[3]Fox R G. Urban anthropology : cities in their cultural settings[M]. Prentice-Hall, 1977;B Trigger Determinants of urban growth in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In Man, Settlements and Urbanism, Ucko, P. J., R. Tringham & G. W. Dimbleby (eds), 575-99. London: Duckworth.Trigger, B. (1972).
[4]Smith M E. Form and Meaning in the Earliest Cities: A New Approach to Ancient Urban Planning[J]. Journal of Planning History, 2007, 6(1):3-47.
[5]理查德·布兰顿,李宏艳(译).人类考古学视角下的城市起源[J].都市文化研究.2006,(2).
[6]戈登·柴尔德,陈洪波(译).城市革命[A].戈登·柴尔德著,安志敏、安家瑶(译).考古学导论[M] .上海: 三联书店,2008:89-101:;原文见Childe V G. The Urban Revolution[J]. Town Planning Review, 1950, 21(1):3-21.
[7]Childe V G. The Urban Revolution[J]. Town Planning Review, 1950, 21(1):3-21.
[8]中美日照地区联合考古队.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考古调查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Underhill A P, Feinman G M, Nicholas L M, et al. Changes in Regional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the Dvelopment of Complex Societies in Southeastern Shandong, China[J].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008, 27(1):1-29.
[9]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M].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
[10]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A].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C].北京:中华书局,1993 (3).
[11]张国硕.中原先秦城市防御文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2]董琦.论早期都邑[J].文物,2006,(6).
[13]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王权形成论纲[J].中原文化研究,2013,(6):5-17.
[14]许宏.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J].文物,2013,(10):61-71.
[15]刘庆祝.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研究[J].考古学报,2006,(3).
[16]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J].中原文物,1995,(3):84-93.
[17]徐苹芳.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A].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C]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5;又徐苹芳.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几个问题[A].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卷)[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6.
[18]Wheatley P.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M]. Aldine Pub. Co, 1971.
[19]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2 .
[20]王兆麟,卜云彤.秦古雍城发现市场和街道遗址[N].人民时报,1986-5-21.
[21]刘敦愿.春秋时期齐国故城的复原与城市布局[J].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郭昱]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16)01-0029-04
[作者简介]惠夕平(1979—),男,博士,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先秦考古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