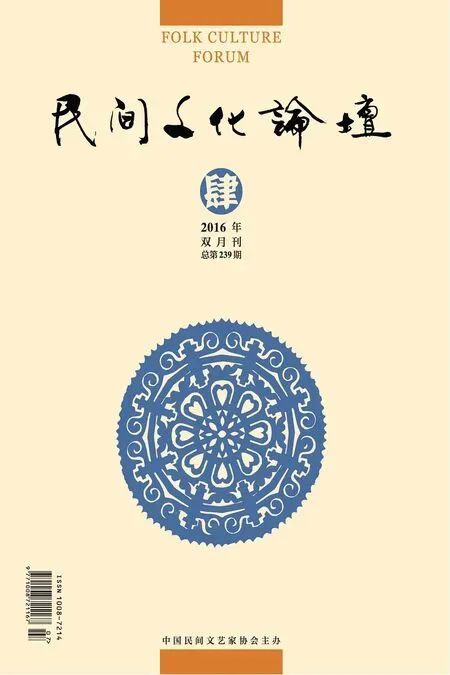四川博物院藏11幅格萨尔唐卡画的初步研究—关于绘制时间问题
2016-02-02李连荣
李连荣
四川博物院藏11幅格萨尔唐卡画的初步研究—关于绘制时间问题
李连荣
关于《格萨尔》史诗的“连环画”(或故事画)由来已久。但是比较完整全面地用绘画展示《格萨尔》史诗的“全部内容”,还是要数本文介绍的四川博物院所藏11幅格萨尔唐卡画。在本文中,笔者主要通过分析此套故事画的故事内容,探讨了它的绘制时间、地点等问题。笔者认为,这套故事画绘制的时间,最早应该不会超过16世纪,也即它是绘于清代的一套故事画。更确切一点说,它最早绘制的时间应该是18世纪左右,最晚也不会晚于19世纪晚期。绘制地点应该位于昌都至康定的某个地区。明正土司有可能是此套绘画的主持人或资助者。
《格萨尔》;唐卡画;四川博物院;康定
一、引言
最近由四川博物院、四川大学博物馆科研规划与研发创新中心编著的《格萨尔唐卡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3月)一书,比较细致地公布和介绍了四川博物院(以下简称“川博”)所藏11幅格萨尔唐卡画的分解图像及题录(或题记)全文。其中,还附录了一幅《格萨尔及三十大将》唐卡画及石泰安等人的相关研究文章。笔者认为,这11幅唐卡画的公布在《格萨尔》学界是一件重大事件。尽管这11幅唐卡画于1958年①Rolf A.Stein, Peintures tibétaines de la vie de Gesar, Ars Asiatique, V, 4, 1958,pp.243—271.中英文译稿可参见,石泰安:《格萨尔画传》,刘瑞云译,Rolf A.Stein, Tibetan Paintings of the life of Gesar, Arthur Makeon Trans.,《格萨尔唐卡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9—227页。、1988年②王平贞:《四川省博物馆藏〈格萨尔王传〉唐卡的初步研究》,《格萨尔研究集刊(3)》,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418—434页。、2004年③陈志学、周爱明:《稀世珍宝〈格萨尔〉唐卡》,《中国西藏》,2004年1期,第36—39页。公开发表并做了相关研究。但相对于此次公布来说,以往的公布情形就相形见绌了。以下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11幅唐卡画的绘制时间与地点稍作解读,以求方家指正。
以《格萨尔》史诗为题材的“连环画”(或故事画)由来已久。据说8-9世纪在拉萨建立的旧木如寺(རྨེ་རུ་དགོན་རྙིང་བ།),是为纪念格萨尔大王之骁将霍尔辛巴梅茹孜而建立的,晚近就有人拍摄到了其新寺院中题记为“辛巴梅茹孜”的壁画④སྨིན་དབུས་པོ་དང་པདྨ་བཞད་པ་གཉིས་ཀྱིས།ལྷ་སའི་རྨེ་རུ་དགོན་པ་དང་ཤན་པ་རྨེ་རུ་རྩེར་འབྲེལ་བ་ཡོད་མེད་ལས་འཕྲོས་པའི་དཔྱད་གཞི།གླིང་གེ་སར་རིག་གནས་དྲ་བ་ནས།http://www. gesar8.com/article/word.aspx?id=728。遥想当年,若当时的寺院完整保存至今,我们就可以欣赏到其中所绘的精彩故事和栩栩如生的众英雄们了。当然16-17世纪以后,西藏绘画中选取《格萨尔》史诗作为题材,绘成故事画,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比如我们知道17-18世纪罗布林卡中所绘的《赛马篇》《北方降魔篇》等故事⑤ཡེ་ཤེས་དབང་མོས།བདུད་ལེའུ།ལྷ་ས།ལྷ་སར།བོད་ལྗོ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ན་ཁང་།༡༩༩༡ལོའི་ཟླ༩བ།དཔེ་སྐྲུན་གསལ་བཤད།།。但是比较完整全面地用绘画展示《格萨尔》史诗的“全部内容”,还是要数本文介绍的四川博物院所藏11幅格萨尔唐卡画。此外,我们还曾看到过相关《格萨尔》史诗的不少故事画,比如白玛次仁等国外学者也曾公布和研究过几组故事画①Pema tsering. Historische, epische und ikonographische Aspekte des glin ge-sar nach Tibetischen Quellen, In Die mongolischen Epen: Bezüge, Sinndeutung und Überlieferung (Ein Symposium), ed. by Walther Heissig.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1979,pp.158-189.(中文见《民族文学译丛》第二集史燕生译稿,中译文缺图片。)。
除去这类故事味道很浓的绘画,在西藏历史上还出现过许多以《格萨尔》史诗中的个别英雄为题材的单幅英雄画,如上面提到的英雄辛巴梅茹孜的画。其中,尤以格萨尔大王的形象为盛多。这类绘画,我们一般称为“格萨尔王骑征像”,它的特点是以格萨尔大王为核心人物创作的类似“佛、菩萨、护法神”等的唐卡画。由于类似于佛画,因此,现在所见此类绘画多与英雄崇拜和信仰的关系比较密切。比如,比较典型的代表是德格印经院的大小雕版画②小雕版画可参见拙著《格萨尔学刍论》,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52页。大雕版画可参见中共德格县委•德格县人民政府编:《香巴拉神殿——德格》,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7页。等。事实上,此类绘画从起源上看,起初有可能是用作讲故事的道具③关于这个看法,已经有众多学者指出过,比如石泰安:《西藏史诗与艺人研究》,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6页。。也即它可能也是一幅故事画,正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四川博物院所藏的11幅中第6幅图画一样。至今,这类绘画还随着时代发展,展现出了各种面貌④李连荣:《格萨尔学刍论》,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40—57页。。由于与本文关系不近,在此不赘。
正如上面提到,本文中关心的重点并不是绘画,而是故事。因此以下根据这套系列连环画所讲述的《格萨尔》故事(史诗内容)特点,来考察其绘制时间与地点等问题。
二、“题记”的解读与补充
首先我们来指出一些“题记”解读方面的问题。当然,此次能够全面详细地公布每条题记和分解图画,是对学界的最大贡献。但笔者认为也有一些瑕疵存在,这里根据笔者浅见,略做表述。
(一)据笔者统计,整套绘画的全部题记约820条。其中有两条遗漏:即第9幅20-2中的ཆོས་འབུམ་ལྕགས་པར་ཁུར་ཚུལ་(曲奔⑤现行本中称为 ཆོས་སྒྲོན།即音为“曲珍”。背负铁样的情景)和第11幅16中的འཛམ་གླིང་རྒྱལ་པོ་ལྷའི༼ལྷ་ཡུལ༽་གཤེགས་ཚུལ་(世界大王去往天界的情景)。
(二)一些题记的解释估计有误,比如第11幅中的《地狱篇》,笔者认为应该是《地狱救母》而非解读者所谓的《地狱救妻》。依照《格萨尔》史诗的传承特点来看,第一,作为康区类型的《格萨尔》史诗,基本上不会讲述《地狱救妻》的故事,很显然这是“安多型”《格萨尔》的特征之一;第二,从所列“题记”可以推断,讲述的就是“救母”情节而非“救妻”情节(比如题记12中出现འགོག་ཟ།即果萨[格萨尔之母],其内容可与木刻版《地狱救母》故事对照,在此不赘)。另外如第9幅中的一条“题记”(23)ཚ་ཞང་ཁྲོ་ཐུང་གཉིས་ཤ་བ་བརྔ༼རྔོན༽ས་ནས་རྒྱ་ཡིག་པོ་ཏི་གསེར་མགོ་ལོན་ཚུལ་(嚓香、晁同二人在打猎的地方,得到金边梵文经卷的情景),很显然这里得到的是“汉文的金头书信”而非“金边梵文经卷”,这个情节见于《汉岭传奇篇》故事的开头部分,汉公主通过射箭(或托飞鸟)带信给格萨尔的情节,正是以上两位得到了书信,而且晁同在向格萨尔汇报此事时还隐瞒了自己私藏书信上的凭证“金头”之事。
(三)题记中“错字”纠正。本书题记解读者依据对《格萨尔》史诗的熟悉和良好的藏文功底,非常正确地解读和纠正了题记中的许多错别字,这是非常可贵的贡献。这从石泰安对“题记”内容解读的比较中,就可以看到本书著者的成绩。很显然石泰安及其给他提供帮助的藏族人,没有做到这样精细。但是,在这里本书著者也受到了时代和方言或多或少的影响,有些纠正字词错误方面表现出了犹豫不决的情景,有时候本书著者也打上了问号,比如第4幅题记2-7中ཇོ་རུའི༼རུས༽བོད་དགོངས་པ༼དགོན་པ༽ལ་ལུག་འགྱེད་ཚུལ་(觉如给藏地寺院?分配绵羊)。笔者认为,此处不应该把དགོངས་པ(思考)纠正为དགོན་པ(寺院),而应该是སྒང་པ(高原)。这从1661年完成于康区江达县波罗寺的整理本《分大食财宗》和1723年完成于拉萨的整理本《霍岭大战》中就能见到བོད་སྒང་པ(高原西藏、高原吐蕃、高原藏人),这是《格萨尔》史诗抄本中一个非常频繁的词组。特别是前者,为我们解读康区流传的《格萨尔》抄本和康区方言读音的正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例如康方言读音特点之一,ang音读作ong音,如khang读作khong)。这样一来,第3幅题记2-7中的བོད་དགོད་བ༼དགོན་པ༽ཤེལ་འགྱེད་མཛད་ས་(给高原藏地分配水晶的地方),第5幅题记1-2中的 ཇོ་སྐྱིད་ཀྱི་༼ཀྱིས༽བོད་དགོང༼དགོན༽པ་གསེར་འགྱེད་མཛད་ཚུལ་(觉吉为高原藏地分发金子的情景)等等都可以纠正为སྒང་པ(高原)了。
总之,“题记”的解读是以《格萨尔》史诗故事为基础的,《格萨尔》史诗本身的传承由于时代、方言区、记录者的文字水平等的差异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差别。比如第10幅图中的一条“题记”(12-2)ཚ་ཞང་གི་ས༼གིས༽མདའ་ཚད་ཚུལ་(嚓香发箭圈地的情景),解读者将其放置在了故事结束部分,而笔者认为是否可以译为“嚓香(丹玛)表演射箭技艺”,将故事内容放置在比试阶段更为合适呢?
三、关于绘画时间与地点
关于这套唐卡画是什么时候创作的,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如有说明代,有说清代等①李连荣:《格萨尔学刍论》,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42页。。笔者认为,它最早不会超过16世纪。除了从画风上大家已经确认的那样,作为噶玛噶智画风的这套系列绘画,不可能超越它的画风产生的历史。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噶玛噶智画派成立的时间为16世纪②康•格桑益希:《噶玛噶孜画派唐卡艺术的与文化审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59页。,因此它也不会超越这个时间段存在。此外,笔者从这套绘画的故事内容方面,也可以推导出上述时间,主要证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证据之一:鸟铳(枪)
鸟铳或鸟枪传入中国最早的时间是明朝。一般认为是1495年或1542年(即明朝弘治和嘉靖年间)两种说法。来源地为噜密(据说位于小亚细亚半岛或土耳其,16-17世纪以其火绳枪(arquebus)出名,曾出口至阿拉伯、也门和印度,备受欢迎③Robert Elgood. Firearms of the Islamic World: in the Tareq Rajab Museum, Kuwait,London: I.B.Tauris,1995.pp.37—40.)和日本两地④阎素娥:《关于明代鸟铳的来源问题》,《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第104—105页。。作为介于印度和中原内地之间的西藏,何时和何地传入这种武器,虽暂无法考察,但最早也应该不会超过16世纪。从一些文献记载来看,18世纪以后,这种武器已经在藏区比较普遍流行了,而且得到了上层人士与一般民众的大力欢迎。
不管怎样,可以确信的一点是,正如从这套《格萨尔》故事画所绘一部《征服西宁鸟铳宗》中获取这种武器宝库的说法来看,这的确在现实生活中曾成为了藏区部落头人们所倚重或炫耀的重要武器。而且,自明朝以来西宁在藏文献中被称作“嘉西宁”(即汉西宁),由此可见,“鸟铳”传入西藏文化中,似乎更多来源于汉文化这条通道。若从清朝1648年设立鸟枪兵情况来看,从这条通道传入西藏的时间大约也不会早于17世纪。事实上,清军重视装备这种武器始于18世纪①毛宪民:《清代火枪述略》,《满族研究》,2005年第4期,第48、49页。。在西藏大量使用这种武器,也可能始于清军平定郭尔喀之后,也即18世纪晚期。从以上内容可以推断,这套“连环画”最早也不会早于16世纪。
(二)证据之二:བུ་སྡུག(布杜)名称及其他
这套连环画中占很大篇幅的是《格萨尔》史诗中的一部《霍岭大战》,也可以说这也是这套连环画的“核心部分”。事实上,在整部《格萨尔》史诗中,《霍岭大战》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故事核心”。由此,《霍岭大战》对于《格萨尔》艺人、画师和民众来说,在其心中所占的分量可见一斑。
我们知道,1723年经མདོ་མཁར་ཞབས་དྲུང་ཚེ་རིང་དབང་རྒྱལ(多卡瓦)②关于1722-1723年《霍岭大战》的整理者问题,可参见拙文《试论〈格萨尔〉史诗的几种发展形态》,曼秀•仁青道吉、王艳主编:《〈格萨尔〉学刊(2012年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第287—298页。组织众多艺人整理完成《霍岭大战》之后,这个“整理本”(以下称“多卡瓦整理本”)迅速成为此部史诗的范本,而且传遍了整个藏区,甚至成为学者们的学习典范③17、18世纪以来,拉萨贵族中阅读《格萨尔》史诗成了一种学习传统“诗学”的方法。可参见 མདོ་མཁར་བ་ཚེ་རིང་དབང་རྒྱལ་གྱིས་བརྩམས།བཀའ་བློན་རྟོགས་བརྗོད།[M]ཁྲེང་ཏུའུ་རུ།སི་ཁྲིན་དཔེ་སྐྲུན་ཁང་།༡༩༨༡ལོའི་ཟླ༡༠པ།།丹津班珠尔著、汤池安译:《多仁班智达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和艺人创作《格萨尔》史诗的“底本”④可以说很多《格萨尔》史诗分部本是基于它的风格、特色乃至故事结构上创作出来的。。将这套系列绘画中的《霍岭大战》与多卡瓦整理本的故事情节进行比对,可以发现,整个故事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其中最具典型的问题,就在于称作བུ་སྡུག(音为“布杜”)一个人物。“布杜”一词含义有二,意之一为“爱子”(从亲友方),意之二为“可怜儿”(从仇视方)。这个人物是格萨尔单枪匹马来到霍尔国之后的关键变化身形之一,正是通过此化身,格萨尔成了霍尔铁匠部落的养子,融入了霍尔国的内部社会。但在多卡瓦整理本中他的名字不叫བུ་སྡུག“布杜”,而叫ཐང་རྙེད(音为“唐聂”,意为“在草滩上找到的”)。不论他处,就这一点可以断定,此部绘画依据的“底本”是多卡瓦整理本之前或者同时并行于世的一个手抄本。
而且从《格萨尔》史诗的抄本与艺人说唱传统来看,布杜一词尽管在文字上有多种写法,但确切的拼写法更可能是扎巴艺人说唱本中的“布杜噶布”(བུ་ཏོག་དཀར་པོ།)⑤གྲགས་པས།ལྷ་གླིང་གབ་རྩེ་དགུ་སྐོར།[M]པེ་ཅིན་དུ།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༡༩༩༨ལོ་ཟླ༤།ཤོག་གྲངས༨པ།。这是格萨尔在天界时或幼年时使用的名字之一。其含义可能是“白色肉髻或肉坨”。其中དཀར་པོ།“噶布”意为白色,乃“善、美好”的修饰词,བུ་ཏོག“布杜”意为肉髻或肉坨(圆髻),这是其真正含义。事实上此词真正的源头应该是ལྷ་བུ་དམ་པ་ཏོག་དཀར།的缩写,译为“天神之子白髻圣人”,此为释迦牟尼佛在兜率天界的名字。由此可见,此部史诗发展到佛教文化阶段,格萨尔被称为千佛化现等等,也就比较合理自然了。
但从格萨尔的诞生故事来看,特别是较早期英雄的神奇诞生故事,比如白马藏族中传承的《格萨尔》中可以看到,英雄最初诞生为一个“肉坨或肉蛋”(俗称肚子,藏语གྲོད་པུ།,音为“卓布”①有些地区藏语方言中,使用了གྲོད་པུ།(音为卓布)一词来指“肉坨”含义。གྲོད་པུ།特指牛羊的胃脏或反刍器官,牧民用来装酥油。民和本《格萨尔》中就是将此“肉坨”(卓布)用箭划开后,从中蹦出了天神之子(Prof.Ts.Damdinsuren ed.,Tibetan version of Gesar Saga Chapter I-III, Ulan Bator: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ciences and education of Mongolia,1961.p.22.)。格萨尔幼年时的另一名字ཇོ་རུ།(音为觉如)一词,或许也可能与གྲོད་པུ།有关,在安多口语中གྲོད་པུ།可读作གྱོད་བུ།(音为觉吾)这与ཇོ་རུ།(音为觉如)音近。关于ཇོ་རུ།的含义,有多种说法。但它也可能具有“肉蛋”的含义。比如甘南本中说,格萨尔初生如一岁孩童模样,母亲将其用哈达与绸衣卷裹起来,在母亲怀中就如抱着一个ཇོ་རུ།一样,因此母亲取名为ཇོ་རུ།。可见这里的ཇོ་རུ།指的应该是“肉蛋”一类的东西( ཀྲུང་གོའི་སྤྱི་ཚོགས་ཚན་རིག་ཁང་གི་མི་རིགས་གྲངས་ཉུང་གི་རྩོམ་རིག་བརྟག་དཔྱད་ཁང་དང་ཀན་ལྷོ་བོད་རིགས་རང་སྐྱོང་ཁུལ་རྩོམ་རིག་ལྷན་ཚོགས་གཉིས་ཀྱིས།གླིང་སེང་ཆེན་རྒྱལ་པོ་སྐུ་འཁྲུངས་པའི་ལོ་རྒྱུས།[M]གཙོད་དུ།ཀན་ལྷོ་བོད་རིགས་རང་སྐྱོང་ཁུལ་རྩོམ་རིག་ལྷན་ཚོགས།༡༩༨༣ལོ་ཡིན་པ་འདྲ།ཤོག་གྲངས༡༥པ།།།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与甘南藏族自治州文联编印:《诞生史》,1983年?,第15页)。当然ཇོ་རུ།也与被称作佛或尊者的ཇོ་བོ།(音为觉吾)音近。从语言近似上解释、衍生故事新义,达到地方、文化认同的目的,也是建构故事、传说的特点之一。),被抛弃在野外受到野兽的“守护”②这也可从中国古代传说周朝祖先“弃”诞生后被弃之于野的故事中见到相同母题。参见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1页。,划开肉坨后诞生了英雄及其天神兄妹等③邱雷生、蒲向明主编:《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26页。。因此,“肉坨”或者“带包衣的孩子”(或者称作“蛋卵”④有些《格萨尔》艺人自称自己诞生时被包裹在卵壳中,如果洛艺人昂仁的自述。)更可能是此词最初的含义。或许这也是早期社会中对于初生儿的称呼。这种将初生儿称作“肉坨”(或者“圆蛋”)概念及所采取的诞生仪式,其历史可能非常悠久,而且传承比较广泛。格萨尔也成了其中一个鲜明例子。此外,此词的另一种文字书写方式,即现在通行的བུ་སྡུག一词,具有了特殊的含义,转变成了“爱子”或“可怜儿”。尤其是“可怜儿”一意,比较符合格萨尔幼年的低贱身份。因此,也得到了广泛应用,甚至成了其真正名字。其词的另一种写法,就是贵德分章本和民和本中提到的 སྡུག་ཕྲུག(音为“杜楚”,意为可怜儿)⑤Prof.Ts.Damdinsuren ed.,Tibetan version of Gesar Saga Chapter I-III, Ulan Bator: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ciences and education of Mongolia,1961.p.23.(此书正文为藏文)一词。这之后,理所当然地བུ་སྡུག与ཇོ་རུ།也可以连接起来了,即བུ་སྡུག成了ཇོ་རུ།的修饰词,译为“可爱的觉如或爱子觉如”。
此外,在这套绘画的《霍岭大战》中,还讲到了一个重要情节,即岭国英雄སེང་སྟག་ཨ་དོམ།(音为“森达阿董”)之死及其死后化为了狼的身形⑥四川博物院、四川大学博物馆科研规划与研发创新中心:《格萨尔唐卡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7页。。这是比较罕见的一个情节。不论是多卡瓦整理本,还是其他通行抄本中,在此处担当这个角色的应该是岭国英雄ཨ་ནུ་གཟིག་འཕེན།(音为“阿奴斯潘”)。因此,也可确定此《霍岭大战》并非为多卡瓦整理本。
(三)关于“赛马称王图”
作为一种旁证资料,我们来看此套绘画所提供的第6幅《世界雄狮大王》的主尊像。它几乎与17世纪的一幅“格萨尔骑征像(即战神形象)”一模一样,这就是炉霍画家 རྣམ་མཁའ་རྒྱན(朗卡杰,1610-1690)所绘《赛马称王》画①甘孜州文化体育和广播影视局、甘孜州文化馆编:《康巴唐卡画名人作品选》,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26页。此外,2012年笔者参加四川省文化厅等机构主办的“格萨尔故里行”调研活动,得赠此幅唐卡的模本小型画一幅,上面记有“四川甘孜炉霍县唐卡艺术协会赠《赛马称王》”等字样。。这两幅画像中的格萨尔王的形象、姿态、手持物、坐骑和13威尔玛战神等,基本上是一致的。唯一较大的差别在于:马首的朝向和相应造成的手的位置出现了差异。至于马首朝向问题,笔者也曾做过揣测②李连荣:《格萨尔学刍论》,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53—56页。,这可能与藏族的民间信仰和佛教思想有关,藏族民间认为向上(向西)③向上即是向西的概念在苯教中有鲜明的反应,显然后来佛教也采用了这种观念。为善好,围绕圣物向右旋转为佛教信仰。鉴于这样的想法,后来典型的“骑征像”中马首定型为向左(即向西)得到了普遍认可,比如德格印经院的大小雕版为代表的一大批收藏于各大寺院中的格萨尔战神形象既是如此。本书中所附川大博物馆所藏“骑征像”(即《格萨尔及三十大将》)显然也是这种想法的反映。但在此套绘画的第6幅中马首朝右,我们只能理解为“天神下凡”的含义了(即天神从上方天界下凡。在藏族民间文化传统中,有时将表示天界的“上方”概念与表示西方的“上方”概念混用,如上部印度与下部中原之说。因此在此表示了天神从西方来的概念,这也可从格萨尔大王马前“侍从”面向西方敬献礼物中来理解此种含义)④在后期的画家中一般固定为马首向左。不过20世纪80年代初,四川几位画家所绘“骑征像”中马首不但朝右而且双前蹄腾空;另之后色达画家拉孟所绘“骑征像”中马首也是朝右。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传统的回归”吧。。关于马首向左的画法得到后来画家的认可,这也可从11幅格萨尔唐卡画中所绘各故事内容的分解画面,基本围绕主尊画像向右旋转的布局中得到了印证——即这显然受到了藏传佛教“右旋”概念的影响。
此外,还有两点相似处在于这两幅绘画中均没有出现13威尔玛战神中的“双鱼”形象⑤关于格萨尔王的13威尔玛(藏文为ཝེར་མ།)战神形象(关于威尔玛与战神的关系,也有不同说法。早期两者各司其职,比如此套系列绘画第8幅主尊画为九大战神或者一些抄本中提到的“战神念达玛布(གཉན་སྟག་དམར་པོ།)”,而威尔玛指人形身材动物头颅的一组保护神。但到后来一般将二者连用在一起了),有多种说法,而且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发生着变化。笔者简略地将其分为两组,一类是“双鱼组”,有“双鱼”、风马中的四神兽、四种鸟类等为主的一组,约有15种动物;一类是“鲁组”,有“鲁”(蛇或龙)、两种鸟类以及普通动物为主的一组,约有13种动物。很显然,前者是居•弥旁等学者认定后出现的形制,后者则可能来自史诗本身或更早时期。双鱼原本是八祥瑞之一,进入格萨尔之威尔玛系列可能用来代指龙族。另外也可能显示了用佛教文化中的“龙”来取代苯教文化中“鲁”(蛇或龙)的含义。和格萨尔胸前所系为金锁而非护心镜,这两点也是后期此类绘画中的重要标志。当然两幅画毕竟可能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细处不同之处还有不少,比如格萨尔的铠甲、幡矛旗的形制、“侍从”英雄的形象以及格萨尔之脸色(白色即天神脸色,而非史诗中所述的董氏族紫色或赭色)、战马的野驴色(而非枣骝色或赤兔色)等。另外,关于格萨尔将手置于耳旁的含义,一般有两种解释,即倾听天神预言或者对臣属唱歌宣教。前者可从众多分解图画中找到类似例证,后者则可从米拉日巴等瑜伽修行者的图画中找到相似示意。
由此,笔者认为,“格萨尔骑征像”最早应该是从“赛马称王图”发展而来的。它最初的功能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从“侍从”人员和30员大将的保留与否可见一斑。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称王图”已经完全变成了“骑征像(即战神形象)”了。由以上情况推知,这套系列画有可能吸收了17世纪的这幅画的某些特点,也就是说它的绘画时间有可能晚于17世纪。
(四)关于绘画“底本”
我们已经知道,《格萨尔》艺人或绘画者在进行创作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之前,必须具备一个故事草本。但是二者之间也有所不同,艺人根据自己掌握的众多故事情节作为“草本”搭建完整的故事;而绘画者的草本则需要更加周密详细,这可称之为“底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可以从画师创作的过程中必需要根据一个抄本或刻印本作为“底本”进行创作,可以断定这一点。作为一个旁证,我们来看2007年完成的“《格萨尔》千幅唐卡画”以及2013年完成的“《格萨尔》精选本”插画的绘制过程,可窥见绘制《格萨尔》史诗故事的一斑。从画师选定《格萨尔》底本,然后再选择“经典的故事情节”进行构图,到最后落笔成画①甘孜州岭•格萨尔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格萨尔王传•千幅唐卡》,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第128页。གནམ་ལྷ་བཀྲ་ཤིས་ཀྱིས།བོད་ཀྱི་ཐང་གའི་མཛེས་རྩལ་ལས་འཕྲོས་ཏེ་གླིང་སྒྲུང་གི་བར་བཅུག་རི་མོའི་སྐོར་མདོ་ཙམ་གླེང་བ།《格萨尔研究集刊(6)》,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561—583页。。这一系列过程,对画师来说,尽管人物形象上有选择的自由,但绝对不会凭空构想和创作“故事”。比如从此套故事画中的《岭国形成篇》至《赛马篇》可见,更多采用了甘南地区发现的手抄本《诞生史》的内容②ཀྲུང་གོའི་སྤྱི་ཚོགས་ཚན་རིག་ཁང་གི་མི་རིགས་གྲངས་ཉུང་གི་རྩོམ་རིག་བརྟག་དཔྱད་ཁང་དང་ཀན་ལྷོ་བོད་རིགས་རང་སྐྱོང་ཁུལ་རྩོམ་རིག་ལྷན་ཚོགས་གཉིས་ཀྱིས།གླིང་སེང་ཆེན་རྒྱལ་པོ་སྐུ་འཁྲུངས་པའི་ལོ་རྒྱུས།[M]གཙོད་དུ།ཀན་ལྷོ་བོད་རིགས་རང་སྐྱོང་ཁུལ་རྩོམ་རིག་ལྷན་ཚོགས།༡༩༨༣ལོ་ཡིན་པ་འདྲ།།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与甘南藏族自治州文联编印:《诞生史》,1983年?。。《汉岭传奇》可能采用了昌都地区发现的抄本③རྒྱ་གླིང་།[M]ལྷ་སར།བོད་ལྗོ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ན་ཁང་།༡༩༨༤ལོའི་ཟླ་༢པ།,《地狱救母》则与江达县瓦拉寺木刻本非常近似④དམྱལ་གླིང་རྫོགས་པ་ཆེན་པོ།[M]ཁྲེང་ཏུའུ་རུ།སི་ཁྲོ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༡༩༨༦ལོའི་ཟླ་༤བ།。
因此,通过这种观点,我们来看这套系列故事画时,除了能够证明其画师是根据某一个特定的“底本”进行创作的这件事之外,它还证明了这套系列绘画依据的抄本肯定早于1723年的整理本或者或和它接近的一个时期。因为要绘制一套系列绘画,必定要搜罗大量的、“信得过”的“抄本”作为“底本”。如果1723年本已经出现,画师不会不采用这位经著名作家整理的权威本子。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这套绘画最晚也可能创作于1723年前后。当然,从这套绘画保存得如此完好和色彩如此鲜亮方面来看,除了唐卡本身具有能够长久保存的特色以外,单就从临摹角度来说,如果这套绘画是临摹本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确信这套临摹画的“唐卡画底本”最早也肯定创作于18世纪左右。
(五)关于故事系统
从整套绘画所描述的故事类型来看,无疑它属于18大宗中的康区型。但从其所属“故事系统”也即从整理者与艺人的“偏好”、《格萨尔》“知识”及整理、编校“完整故事”的观念来看,这套绘画所描绘的《格萨尔》故事系统更接近于居•米庞等整理的德格林葱本(19-20世纪)与蒙文北京木刻本(1716年木刻⑤Prof.Ts.Damdinsuren ed.,Tibetan version of Gesar Saga Chapter I-III, Ulan Bator: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ciences and education of Mongolia, 1961.p.12.)。也就是说,这套绘画也有可能依据这个时期的《格萨尔》手抄本绘制的,即绘制于18-20世纪之间。关于这套绘画的故事系统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另著文作更进一步的阐述。
(六)关于绘制地点
关于此套绘画绘制的地点,许多学者指出可能绘于康定(因为此套绘画的拥有者明正土司就居于此处⑥参看本书中所附石泰安的论文,他指出本套绘画的拥有者为明正土司甲联升。石泰安:《格萨尔画传》,刘瑞云译,Rolf A.Stein, Tibetan Paintings of the life of Gesar, Arthur Makeon Trans., 《格萨尔唐卡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9页。)。但是笔者依据《格萨尔》史诗的传承特点及噶玛噶智画派形成、发展的特点判断,这套绘画可能的绘画地点或许是比康定更靠西部的地区①依据任新建考证,被称为嘉拉甲波的明正土司管辖的范围包括了康定以西的“鱼通河、大渡河西部、泸定县”等处的广阔木雅地区。由于与木坪土司的亲属关系,也曾管理过康定以东的宝兴县等地。由此可见,其管辖范围位于康区的汉藏文化的连接地带。参见任新建:《康巴历史与文化》,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第119—133页。,炉霍、德格甚至更靠西的昌都也许是这套绘画创作的地点。从噶玛噶智画派兴起的特点来看,昌都更可能是它的创作地点,因为它更靠近噶玛噶智派兴起的地区。
从《格萨尔》史诗的故事系统的发展来看,昌都地区(包括玉树在内)在18世纪以前已经成了康区《格萨尔》史诗的传承中心。但是18世纪以后,随着德格土司的兴起以及德格印经院的建成,康区文化中心开始转移到了德格。受到当地文化人士与上层人士的关心,康区格萨尔的传承中心也转移到了德格甚至更远的东部与北部地区。因此,在这一地区内产生这套绘画可能比较合理。也即,此套绘画创作的地点有可能在于昌都至康定的某个地区,比如炉霍也符合这些条件。
四、小结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证据,笔者认为这套故事画绘制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16世纪,也即它是绘于清代的一套故事画。如果我们确信此套绘画并未选取多卡瓦整理本《霍岭大战》作为“底本”,而且也未囿于居•米庞等整理《天界》《诞生》与《赛马》,那么可以更确切一点说,它最早绘制的时间应该是18世纪左右,最晚也不会晚于19世纪晚期。或者我们可以说,此套《格萨尔》史诗的故事画,最早于18世纪左右在昌都至康定的某个地区,在一位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权力且爱好《格萨尔》史诗的土司或者活佛的主持、资助下完成的,明正土司也符合以上这些条件。因此,我们暂且将其确定为18世纪的《格萨尔》唐卡画,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责任编辑:丁红美]
J2“214”
A
1008-7214(2016)04-0081-08
李连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