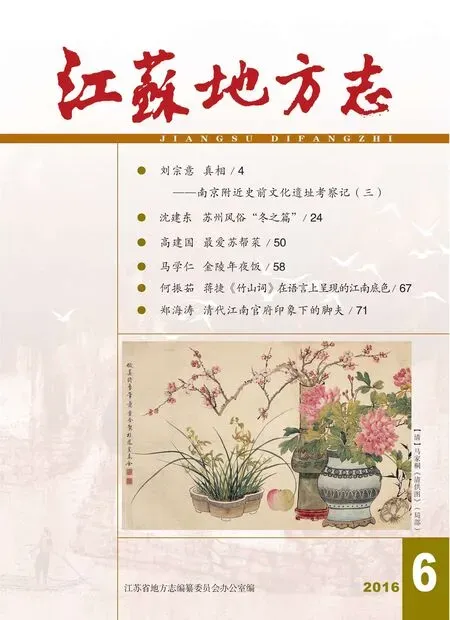长牵路
2016-02-02◎陈益
◎ 陈 益
长牵路
◎ 陈 益
长牵路
黄昏时分,当潮水一般的游客从古镇退去时,我也准备回城了。尽管心里明白,这时候的周庄才是本质意义上的周庄。不说南湖的星月和后港街上的灯火,光是澄虚道院内的那株琼花,在暮色中开放得如银盏般地耀眼,便足以让人久久驻足。
很快,我乘坐的汽车就来到了澄湖南岸的长牵路。只有本地人才听说这个流传了不知多少年的名字,想起它当年牵路长长的模样。如今这里已经极少见到风帆,牵船更是早已绝迹。挂在人们嘴上的地名,只是对历史的一种祭奠。湖边,一条宽阔的公路平坦如砥。路边,田畈里的油菜花金黄一片,几乎将人的眼睛都要灼通。麦苗则绿得很浓,像是泼翻了绿色的油彩。可惜没有紫云英了,如果加上暗红色,色彩的对比将更加强烈。
上次是在立冬季节走过长牵路。湖畔丝毫不见萧瑟之意,晚秋收敛了生命的蓬勃冲动,将全部的希望蕴藏在植物的根茎和果实中,以静待来年,它就显得分外庄重。路边的那些树木,摇曳着浓郁乌亮的叶片,绿得很有层次。偶尔有几片落叶飘下,让我想起一位俄罗斯作家的比喻:“秋天是踏着车来的,它带着薄薄的霜花闪光的红叶”。
此刻,春天的湖面上笼罩着淡淡的暮蔼,模糊了天水相接的边缘。阳光消逝了,可蓝天依然高远而明朗,芦丛围拥中的湖水便显得分外澄澈。近湖,密集的网箱留下纵横交错的青灰色线条。它们如五线谱,让平静的湖面显出了韵律。
如果在早晨,那颜色确实像纯度很高的宝石,毫无瑕疵,诱人目不转睛地凝视。在水环境日益严重的今天,能见到如此明净的湖光水色,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人们深深懂得湖泊对于保护生态平衡的特殊作用,对它倍加珍爱,千方百计地让它保持原生态。尽管澄湖的庄鸡、野鸭、翠鸟,已廖若晨星。
澄湖,亦称沉湖。它原本不是湖,而是一座古老而繁华的城市。《太平广记》载:“该地古为陈县(或云陈州)而名陈湖”。原来,这个名叫陈州的城市堪称苏州的姐妹城,能与苏州媲美。但由于地壳陷落,它一下子变成了湖。《吴县志》上也有记载,说湖畔的津浦庙中,有一口明代弘光元年所铸的钟,钟上镌有唐代天宝六年春天“地陷成湖”的字样。近年来经考古证实,它“地陷成湖”的时间,不是地方志上所说的唐天宝六年,而是南宋乾道年间,整整误差了四百多年。
澄湖总是呈柔美之态。尤其在雨天,明镜似的湖面被雨点击起密密麻麻的水泡,犹如一匹被揉皱了的巨幅灰绸,在风中铺展。一道一道弧形的水带,不知是风吹成的,还是船尾拉出的,带着晶亮的丝绸质感,煞是动人。每年七八月份的台风季节,湖上的浪涛像无数白毛牯牛你追我赶,让帆船和湖鸥都失去踪影。但这只是湖的一时任性,而不是它的天性。谅是苏东坡,在湖边也不会留下“浪淘尽千古风流”的绝唱的。
我在长牵路上思索着时序和季节的意义。
不仅仅是大自然的轮回,也不仅仅是生命的节律,许多看似重复的事物,它的内涵在演进中已悄然变化。“天地革而四时成”,我们怎能只从字面上来理解?
长白荡
只有长久生活在水乡的人们,才能说出湖、荡、潭、泖的区别。长白荡,位于古镇锦溪和周庄之间,是一个中等规模的湖泊,光从名字看,就能想象那浩淼伸展的形态。
在江南,水是带来灵秀之气,且又绵延不息的缘由。临水人家、垂柳依依的河岸、粉墙黛瓦蠡窗、水阁亭榭、橹声欸乃的船只、浩渺的烟波……这一切构成了素淡古朴的民俗画卷。人置身其间,仿佛走进了恬淡自在的纯净世界。然而,假如在夏秋台风季节,湖上的浪涛像无数白毛牯牛疯狂追逐,足以让帆船和湖鸥都失去踪影。
我有过一次暗夜船行的经历,至今难忘。
那是好多年前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们完成了在古镇周庄的施工任务,匆匆返城。七八个人驾着一艘小轮船,在霏霏细雨间驶入长白荡。夜幕如一顶湿漉漉的网罩,遮掩了整个湖荡,四周乌沉沉的一片,船儿仿佛掉进了偌大的墨缸,不知所向。没有月色星光,连远处岸边的灯火也不见半点光晕。伸手不见五指,这句话丝毫也不夸张。
司机在驾驶座上坐不住了,弓起身子,眼睛紧贴挡风玻璃,费力地探寻前方,可是什么也看不见。找不到任何参照物,船头的射灯分外微弱,在茫茫湖面上只照见飘忽的雨丝,几乎没有作用。马达单调的哒哒声响,更令人心头不安。在湖上行驶了个把小时却发现,我们的小轮船转了一个圈子,似乎仍然在原处。如果说刚从湖汊驶入时,他是凭着经验,轻舟熟路,现在却有些慌张了。
夜,携着风雨走向深沉。
白天施工,大家都挺劳累。此刻,又有饥渴与困倦袭来。然而谁的心里都不敢松弛,纷纷焦灼地推测着,议论着,试图找到航向。但什么努力都不奏效。我不由想起,有一次雨夜独自在泥泞的田埂行路,四周也是漆黑一团。踉跄中摸到口袋里的一盒火柴,摇了摇,似乎还剩几根。于是摸索到一个稻草堆,抽出几根稻草,将最后一根火柴点燃,终于辨出方向……此刻,我们连长白荡中渔民的网围都无法辨认。
失去了光亮,才会体味光亮的可贵。
时间在无情地流逝,汽油快不够了。司机流露烦躁的神色,忍不住嘀咕道。我们的领队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了几句。他比我们年长几岁,脾性沉稳,遇事不慌不忙,又有长期外出施工的经验。我明白,他肯定能指挥小轮船驶出暗夜……
这次难忘的夜行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也充分领略了长白荡的多面善变的风姿。
苏州塘
在一个城市生活了很多年,仍有从未涉足之处,哪怕近在咫尺。
那天早晨,我行走在娄江边,无意间发现了一堵残垣。花岗岩、青石和红砖堆砌成的墙体,留有一扇木窗。墙粉斑驳,青苔漫漶,一块任随岁月侵蚀的蓝色搪瓷路牌镶嵌其上,依稀可见“苏州塘”三字。丝瓜的藤蔓擎着黄花从后侧爬上顶端,绿叶在阳光下透亮。
苏州塘,似是一个被遗忘的街区。
街面狭窄而又潮湿,行人与自行车在电线杆下小心翼翼地交会。灰暗的建筑物,大多铺设机制瓦屋顶。考究些的墙面则敷设马赛克。天井里的绳索上晾晒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天沟边,一个赤膊小伙子神情肃穆,独自思量什么。女人们围着自来水龙头洗涤,一片叽叽喳喳。我打量着几个小院,青瓦粉墙,覆满了爬墙虎。仅从郁郁葱葱的老树,就不难推测它存世的年月。一个从院子里走出的老妪告诉我,从懂事起就住在这里了,如今已八十岁,眼看四周的高楼大厦一幢幢起来,很盼望搬迁。前几年墙上出现了醒目的“拆”字,还画上一个圈,然而迟迟没动静。
我在小街上来回走了一圈。南端,有花岗石河埠伸向娄江;北端,是车来车往的马路。临街,善于经营的人辟出店面,张贴了“电脑维修,手机贴膜”“烫染造型”“首饰翻新”等等广告,也有人办起了自助洗衣房,狭窄的空间里摆放着五六台洗衣机。街口是露天摊点,售卖煎饼馒头、卤汁熟食或蔬菜水果。最热闹是在傍晚,许多在附近商贸城打工的人,会过来享受陕西凉皮和河南烩面之类。他们的口音南腔北调。
与整个城市的生活节奏相比,这个从未被汽车轮子碾过的街区,至少迟缓了二十年。
一位石姓老人在街边和我随意攀谈。他也有八十岁了,手里拿着钢丝钳,似乎是要去修理什么。他说,他们家祖籍苏北兴化,从父辈开始居住在这里。那时周围都是农田,只有几处草房,人们以耕作为生。渐渐地房屋才多起来。他有三个儿女,他们或买土地办工厂,或拥有打桩机,早就搬出去了,只有老俩口还住这里。家里多余的房子,出租给外地人,租金补贴生活,也算不错。
在饱经沧桑的“苏州塘”小街,他丝毫也不显苍老。
古老的娄江,是太湖入海的三条通道之一,出苏州娄门,迤逦而东。依据它所流经的区域,人们分别称之为苏州塘、昆山塘、太仓塘。娄江从刘家港注入东海,那是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起锚之地。
我知道,娄江最初是在叶荷河那儿拐弯朝北,经至和塘往东,流向太仓的。至和塘,纪念着宋代至和年间一次成功的水利工程。四十年前,娄江又有一次大规模拓浚,走向也改变了。我有机会参与了几个月,住在工地上,风里来雨里去。不知怎么竟没有到过苏州塘。犹如娄江,我们称颂为母亲河,对它却知晓甚少。在水路主宰一切时,它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我不敢肯定三宝太监郑和的宝船是否在苏州打造,但大明永乐年间那些精美绝伦的丝绸、陶瓷、苎布、茶叶、铜器,无疑是经由苏州塘运往刘家港的。来自海外的“明月之珠,雅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同样也溯江而上,转道苏州,运往京城。
苏州塘,在数百年间见过很多世面。或许,曾有很多肤色黧黑、衣着怪异的外国使臣从这里经过,以欣悦纳罕的目光打量过岸边的景色。今天,娄江沿岸的人们仍然将玉米称作番麦,将甘薯称作番芋。
郑和下西洋,是一次政治性的海外贸易活动。它极大地刺激了娄江沿岸的手工业、农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不难想象,昔日娄江的繁华足以与苏州七里山塘媲美。可惜没有哪个画家能像徐扬一样,留下一幅《盛世滋生图》。如今,空寂的江面上风帆早已消失。偶尔可见摩托艇和拖驳驶过,划出长长的波痕。当夕阳西坠,白色的江鸥轻盈地掠过水面,才让人感慨岁月的飞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