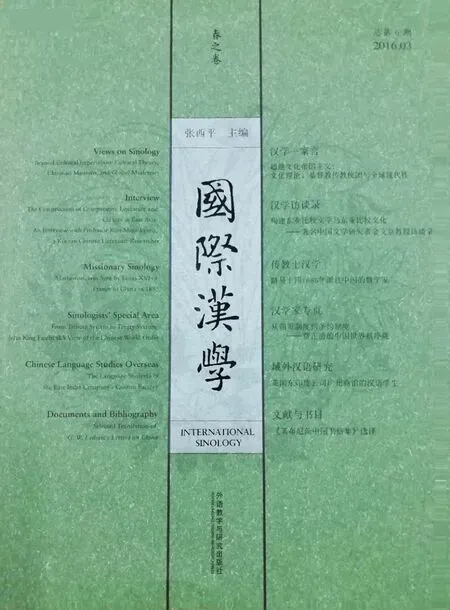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汉语学生*
2016-02-01
刘美华 杨慧玲 译
译者按:本文发表于1938年,原文“The Language Stude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Factory,”刊登在Journal North China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8, Vol.69, pp.46-81。作者苏珊·里德·斯蒂夫勒(Susan Reed Stifler)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伦敦会等机构的原始文献,进行了长期梳理,才汇集成文。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7世纪初就与中国有商业往来,长期以来,由于缺乏中文翻译人才,在贸易交往和政治交涉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翻译对公司的意义重大。然而,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语言封禁政策,他们无法在与中国官府交涉中争取利益,尤其是两次使华团的失败让他们意识到培养汉语翻译人才的重要性。在广州商馆关闭前的30年,东印度公司在培养汉语人才方面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1810年至1831年间,公司共培养了19位汉语人才,不仅为阿美士德使华团提供了译员,还一度使用汉语与中国官府书信往来,而不再完全依赖“语言通事”,甚至培养出德庇时这样中文造诣颇深的汉学家。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广州商馆,处理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关系和事务,而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汉语人才在不同时期的起伏变化,亦是中英关系史的一个投影。本文发表后成为研究这一时期中英关系史、翻译史的重要文章,也是21世纪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这篇文章如今在国际学术期刊过刊网以及国外馆藏期刊中都不易找到,其扎实的英国档案文献基础使得它时隔数十年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一、18世纪
自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与中国贸易以来,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英国人对中国人的语言几乎一无所知,这是中英关系史上的异常现象之一。但更为奇怪的是,1793年当第一个英国使团出使北京时,使团中唯一能够使用汉语的欧洲人竟是一位12岁的少年。觐见乾隆皇帝之时,这位少年不仅能听懂皇帝的问题,他的对答更是让年迈的皇帝龙颜大悦。为此,乾隆帝赏赐给这位英国少年一个绣有五爪金龙的黄色丝绸荷包,作为认可他成就的礼物,这件礼物后来成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博物馆收藏的珍品。伦敦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图书馆的墙上挂着一小幅画像,画中少年—五官精致、面部带有贵族气质,而且鼻子比一般人要长,这就是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访华使团的见习生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①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印度事务部的乔治·莱纳多·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之子,1798年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书记(writer),1816年升至商馆大班,同年随阿美士德勋爵(William Pitt Amherst,1773—1857)出使京城。返回英国后出任国会议员多年,踊跃地参与关于中国和印度事务的辩论。他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法学博士,并于1823年协助创办英国皇家亚洲学会,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D.N.B.)., LIV,114;参见G.T.Staunton, 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Public Life of Sir George Staunton (London, 1856).的摹像。
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过去了,英国没有一所大学将汉语课程纳入教学大纲:开设汉语学习的私立学校也都以失败告终,能坚持学习汉语的学生也是凤毛麟角。1820年,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在书中如是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学习汉语人数如此之少,这被解释为汉语本身缺乏吸引力,因为不管是从中国非同寻常的政府性质,或是从汉语复杂的结构来说,为了鼓励人们勤奋地去探索它,似乎只需知道‘怎么回事’就够了。”德庇时意识到这些信息当然是从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职员那里获得的。“然而,不管是想象还是汉语确如所说那么困难,抑或二者兼有,事实上都阻碍了汉语的学习,除此之外,”他还意味深长地补充道,“中国人自己也有意制造外国汉语学习者的障碍。”①J.F.Davis, Chinese Novel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 to which are added Proverbs and Moral Maxims (London, 1822), 1.另一位19世纪初的作家评论说:“如果不向人们展示出快捷致富的前景和好处,没有其他国家在引进一个新的学科或拓展旧学科时遇到如此大的困难。”②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hereafter JRAS): II, 9.“On the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Oriental Literature,” by W.C.Taylor.
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职员的看法不完全属实:泼冷水和冷漠的态度都是1780年之后才出现的,18世纪初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英国人并非都是如此,至少有人能掌握汉语,只是需要一些时间而已。坎宁安(James Cunningham)就明确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曾以东印度公司医生的名义被派到舟山,在1702年写了一篇舟山岛的文章。坎宁安在提及“内陆城镇”时这样说,“等我会些许汉语,我想到一些城镇去。”③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14 vols.(London, 1809), IV, 694.“Abstract of two letters from Mr.James Cunningham F.R.S….”事实上,汉语要比坎宁安预料的难得多,但有证据表明,通过在澳门对汉语的接触,早期在广州的英国商人中偶尔有对汉语感兴趣的。大英博物馆早期馆藏中有中文版《四福音书》(又名《福音合参》)和《新约圣经》的不完全译本,这一抄本源自罗马天主教传教士1740年前在广州的译本。④手稿描述:“先是中文版的《四福音书》,接着是《新约圣经》中《使徒行传》第一章到《希伯来书》末尾,耶稣会士译。”扉页上有一条注:“《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草稿(Evangelia quatuor Sinice Mss.)”。此抄本奉霍治逊(John Hodgson,又译贺特臣)之命抄录于1737—1738年,霍治逊认为此手稿细致、准确,于1739年9月呈赠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长史路连(Hans Sloane)。广州同样也是把中国小说译成英语或葡萄牙语的地方,据说译稿是由东印度公司职员约在1719年完成的。⑤Han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A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which are added, I.The Argument or Story of a Chinese Play.II.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and III.Fragments of Chinese Poetry. In four volumes with notes.(London, 1761) 斯当东认为这是由 “一位名为James Wilkinson的先生”所翻译。由Dromore主教Thomas Percy博士编辑出版。另见J.F.Davis, Chinese Novels, 4; G.T.Staunton, Memoir of 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Bart. (London, 1823), 383.Letter of Earl Macartney to George Thomas Staunton, Nov.1800.
这一译作在译者去世后发表(1761),发表后的十年间,英国人对中国事物的普遍兴趣一如既往,既具18世纪的时代特征,同样也显露出对汉语的猎奇之心。⑥例如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2 vols.(London, 1762).“A Dissertation on th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of the Chinese,” I, No.1; Critical Review, June, 1762, reviewing J.T.Needham, De inscriptione quadam Aegyptiaca (Rome, 1761);The Chinese Traveller, 2 vols.(London, 1775), I, pp.240-255, pp.256-267.当时有一种假设,汉语的书写方式源于埃及,这是英国皇家学会讨论的问题,讨论的结果就是英国皇家学会写给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一系列征求信息的询问信件。英国皇家学会提出这些询问信可经由广州商馆转给北京的耶稣会士,与此同时,他们还想为伦敦的学会图书馆购置一批书籍:“一两部有汉语语音和汉字、汉字后有释义的好字典;其他一些重要的汉语书籍,无论是否有注解,能得到的都要。”1765年,广州商馆把挑选好的4卷本的《诗经》、6卷本的《说文解字》和两部分别为26卷和14卷的字典运往伦敦。①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5 vol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1929), V, 117-118; J.F.Davis, The Chinese, 2 vols.(London, 1836), I, p.250; Asiatic Researches, II, pp.371-372;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XII, pp.685-691."Extract from the Journals of the Royal Society, June 23, 1768, respecting a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Society by a Member of the house of Jesuits at Peking in China.By Charles Morton, M.D." In eighty years the Royal Society had forgotten the “Observations and Conjecture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Made by R.H,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III, pp.285-291.数学家胡克(Robert Hook)经过悉心观察,搜罗到一部中文字典、一本年鉴以及其他一些书籍,胡克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凭借他出类拔萃的才智推知对汉字本质更为准确的知识,远超过过去一个多世纪许多学者们朦胧的认识。
显而易见,这一请求引起了广州商馆的重视并得到明智的处理。回顾此前30年广州商馆的汉语学习,可以让我们对这一现象有更清晰的认识。在这一时期,东印度公司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
1760年以前,中国并未禁止欧洲人学习汉语,汉语学习之所以无人问津,都是拜广州那些所谓的“语言通事”所赐,广州港口如今已是国际贸易的中心。这些“通事”说的是“支离破碎的洋泾浜英语”,这种洋泾浜英语取代了早期国际贸易中使用的洋泾浜葡语,通事们作为口译人员是垄断性的,他们收取高额的服务费用。当遇到超出他们的词汇量以及语言水平的事情,就有必要雇用居住在澳门通晓汉语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由于这些人都无意扩大英国的利益,广州商馆中如有通晓汉语的职员可能会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带来最大化利益。
然而,跨出具有里程碑意义一步的不是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也不是广州商馆管理委员会,而是“诺曼顿号”(Normanton)的船长里格比(Rigby),他在1736年把一个当时还不为人知的少年洪任辉(James Flint)带到了广州,目的很明确:让少年留在中国学习汉语。这个少年似乎学习勤奋并取得了相当进展,大约在第三年年末时,里格比遭遇海难失踪。里格比去世时洪任辉在印度,回到广州后,洪任辉向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委员会求助,“如果你们乐意为我在这里的居留提供一些资助,给予我留在广州学习阅读汉语和书写汉语的机会,我定会努力掌握汉语官话和当地人普遍使用的语言”。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对洪任辉的事早有耳闻,因此热情地向广州商馆推荐他。一笔钱(150两白银)立即被拨给洪任辉使用,而且雇用他做东印度公司职员。经过四年的学习,洪任辉的官话掌握得相当好,但并未成为官方译员,直到英国海军司令晏臣(Anson)环游世界途经广州时,洪任辉的才华才得以施展。在海军司令与两广总督会面的盛大场合,以及晏臣拜访会见其他中国官员时,洪任辉的表现“甚得海军司令的欢心,他表现突出,翻译精准,一切都在掌控中,让其他中国通事望尘莫及。”次年(1744),公司大班与“粤海关监督”(Hoppo)会晤,洪任辉再次担任口译。他取得的成绩传到了英国,1746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在广州贸易季给予洪任辉特殊指令,任命他“做管理委员会的通事,并在需要时协助处理公司事务,在居留期内必须住在商馆内……并准每船给他90两白银。”他很快就成为被认可的译员。1747年9月6日有一条记录:“公司来了位地位显赫的中国官员……洪任辉替我们与他交流。”又一条:“我们通过洪任辉说服他到“诺福克号”(Norfolk)甲板室进行会谈”。他们希望洪任辉与粤海关监督甚至总督的定期对话能够取代语言通事或行商们间接而不尽如人意的接触,希望此种方式作为令人满意的贸易的根基,或许能取消他们在广州贸易中遇到的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与日俱增的种种限制。但是1753年,一纸由洪任辉起草、中国人执笔书写的诉状被呈递给粤海关后,“代写诉状的中国人被下令收押”。没有中国抄写员的帮助,洪任辉的诉状有时让人看不懂。尽管困难和令人失望的事接踵而至,他仍然坚持学习汉语,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担任重要的角色。②Richard Walter, Anso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London, 1928), p.381, 384; Morse, Chronicles, I, pp.276-277, 287, V, p.1, 6, 9,11, 12; E .J .C.MSS, Factory Records, China (1741—1755), p.152, 184, 186, 197, 200, 206, 207.一条1754年7月5日的记录写道:“正如我们所知,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一名中国通事的诚信,我们派了洪任辉先生到粤海关府衙……他回来后肯定了通事此前传达的话。”
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洪任辉未能成为东印度公司永久职员并非公司的错误。1753年,董事会选派贝文(Bevan)和巴顿(Barton)两名青年来华学习汉语,费用由东印度公司支付。洪任辉为他们推荐了老师,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之后,巴顿的名字在东印度公司名录上销声匿迹,而贝文担任公司的正式译员20多年。①Morse, Chronicles, I, pp.296-297, II, p.51, 55, 61, 209, V, 27, 76.The entry of 14 Feb.1756 states, “他(贝文)汉语学习进步飞快,举止行为得体,为公司效几年犬马之劳不成问题。”
“洪任辉事件”结束了他在公司的职业生涯,也迫使贝文消极无为,影响了东印度公司派遣更多译员来华,这是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史上不能忽略的一个篇章。广州的贸易环境日益恶化,导致英国人试图北上寻找此前到访过的北方贸易港口。于是,1755年哈里森(Samuel Harrison)、菲茨休(Thomas Fitzhugh)乘坐“贺得勒斯伯爵号”(Earl of Holderness)北上,由洪任辉担任翻译。这一行人与宁波官员商谈甚欢,商谈后哈里森呈递了一份有19条条款的禀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然而,早在“贺得勒斯伯爵号”回到澳门前,广州商馆已为此表面的胜利付出代价。定期教导年轻的贝文和巴顿数月的中国教师被叫到南海县衙,且被告知不宜继续留在商馆。记载了县衙与这位中国教师密谈的记录接着评论说:“南海官员毫无道理地宣称,我们英国人学习汉语会增加县衙的诉讼和麻烦,这样的罪名肯定会落在中国教师的身上,他还说,利用掌握的汉语所作的错误行为及在宁波的成功,显然,没有洪任辉的协助绝不可能做到。”②Morse, Chronicles, I, p.297, V, p.21, pp.25-26, p.27.后来两次北上宁波(1756年、1757年),洪任辉和贝文都参与了,证明广州的官员尽他们所能地阻止在其他口岸开拓贸易。③Ibid., V, pp.49-53, p.68, p.75; G.L.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2 vols.(London, 1797), I, 416.
1757年中国皇帝谕旨肯定了广州行商的特权,严格限制广州一口通商,这一年,当“翁斯洛号”(Onslow)抵达宁波时,谕旨已经生效。此谕旨是18世纪中国对外国人与日俱增的限制措施的顶峰之举。④Earl II.Pritchard, Anglo-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Urbana, Illinois, 1929), chap.VII.中国排外情绪由来已久而且越来越强烈。在中国人看来,这起事件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这些英国船北上直接依赖于洪任辉的语言能力。
无视这条谕旨,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管理委员会在1759年为争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决定再次尝试。他们让贝文留守广州,派洪任辉赴宁波,向官府呈递申诉不满和像以往那样请求在北方港口通商的请愿书。⑤E.I.C.MSS, China 20 (1782—1815), Extracts from Diaries, 20 May 1759.如果在宁波失败,洪任辉将继续去京师告御状。虽然洪任辉始终没能进入京城,但通过贿赂官员,他把状纸递到了朝廷。他被从天津由内陆河道遣送返回广州,这位第一个穿越中国旅行的英国公民,被监禁了两年半后被迫离境。1762年年底洪任辉回到英国,再也没能重返中国,东印度公司也不能获得扭转性的谕旨。⑥Morse, Chronicles, I, pp.301-305, IV, pp.313-320, V, p.80, 81, pp.83-84, pp.88-89, pp104-105; E.I.C.MSS, China 20 (1782—1815), Extracts from Diaries, 25 Dec.1759, 30 Oct.1761 ; Gentleman’s Magazine, Aug.1835."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by T.Fisher.洪任辉在马戛尔尼使华前不久离世。G.L.Staunton, Embassy, I, 38.德庇时认为东印度公司对于“担当如此艰巨的、无私的甚至危险的任务”的洪任辉并未给予他应得的认可或回报。Davis, The Chinese, I, 42.另外一件事对英商来说又是一个打击,被指控代洪任辉写诉状的中国人被处死了。不仅如此,官府还开始明令禁止中国人替外国人写呈词的做法。⑦Morse, Chronicles, V, 84; J.R.Morrison,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Canton, 1834), 47.伍德(Francis Wood)1758—1761年间供职于管理会,但不是公司正式的汉语学生。1761年夏心智失常,遂于当年冬天被送回家。 E.I.C.MSS, Factory Records, Diaries (1761-1769).15 Dec.1761; Morse, Chronicles, V, 76, 99.
中国人被禁止担任抄写员或教授外国人汉语,洪任辉被驱逐出境,贝文受到了制约,广州商馆在接下来的30年里尤其困难,随着贸易量的增加,广州商馆的处境更加艰难。1773年贝文返回英国,曾一度重返广州,但1780年年底最终离开了中国。从1780年往后几乎长达20年的时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中没有中文译员。①E.I.C.MSS, China 20 (1782-1815), Extracts from Diaries, 9 Nov.1767; Morse, Chronicles, V, 165, II, 61.1780年3月22日记录:粤海关监督在府衙接见了贝文先生和拉佩尔先生,“和他单独谈了两个时辰……通事协助商人只是形式;实际上是由贝文在与之对谈。” Ibid., II, 55.
贝文职业生涯结束的那一年,广州商馆特选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产生,继承了先前的管理委员会成为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管理机构,首任特选委员会大班人选在广州商馆的传统中意义非凡。特选委员会的第一位大班是菲茨休,他和洪任辉两次北上;第二位是贝文;第三位是小拉佩尔(Matthew Raper Jr.)。虽然菲茨休和小拉佩尔从未像贝文那样正式做过汉语学生,但他们对汉语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认为学习汉语要远比为东印度公司物色一名译员更加重要。他们以图书馆中文藏书为荣,那些中文藏书还有中文字典,都是他们收集并带到英国的,他们还成为在英国学习汉语的赞助者。他们对语言问题的见解使他们受雇于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当讨论卡思卡特(Cathcart)和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计划时,语言问题更加重要。②Ibid., II, 39, 51; E.I.C.MSS, China 20 (1782-1815).“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柯伯先生(Cobb)画的有关中国和使团的速写……1792”; Antonio Montucci, the Characteristic Meri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London, 1801), 8; Monthly Magazine, April 1804.No.113.
随着这三位的离开,东印度公司的旧传统似乎也消失殆尽了。与中国官员直接对话成为天方夜谭,而中国通事的洋泾浜英语不得不成为交往的常规方式。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通事们还不如行商的英语好,有些行商掌握了不同于“洋泾浜”、很地道的英语。③Morse, Chronicles, II, 61.行商完全有能力胜任英商和官府对话的中介—至少在这个时期—但是英商觉得中国行商不能作为中立的译者而予以信赖。④G.L.Staunton, Embassy, II, 566, 567, 577; Davis, The Chinese, III, 199.东印度公司没有让低级书记员学习汉语的鼓励措施,公开跟中国教师学习汉语也不可能。
这一时期东印度公司的完全屈从不仅让中国以外的人不能理解,甚至公司内部也有人不理解。1790年的一份关于广州商馆和对华贸易的总报告(应该是在印度完成的)里有这样的批评:“我们的公司……公开宣称:作为东印度公司代理人,任何对汉语或对清政府的知识都会表现为偏见或行为不当;这是毫无远见的谬论,为的是避免将他们卷入与中国政府官员的纷争中。”⑤E.I.C.MSS, China 20 (1782-1815), March 1790.
在那些不幸的事件中,诸如1784年的“休斯夫人号”(Lady Hughes)事件就很有必要寻求其他西方人的帮助。这一时期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供职的两位,一位是丹麦行的第二大班莫尔(Morier),他有些汉语知识;另一位是法国译员加尔贝(Galber)。⑥Ibid."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unfortunate accident which happened at Whampoa.24 Nov.1784."加尔贝据说是“唯一掌握中国官话和方言的欧洲人”,他被选作1788年出师不利的卡思卡特使团的翻译,在卡思卡特病逝后放弃了使命。⑦Morse, Chronicles, II, 166."Instructions to the Cathcart Embassy"; E.I.C.MSS, China 20 (1782-1815)."Document concerning Proposed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 following the Cathcart Expedition"; H.Cord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Paris,1920), III, 380.卡思卡特病逝后没有多久,加尔贝也离世了,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遭受了严重损失。在筹备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时,特选委员会没能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推荐任何一名具有中文翻译能力的人。⑧G.L.Staunton, Embassy, I, 38.
二、马戛尔尼访华使团
马戛尔尼勋爵把寻找中文译员的任务委派给他的副使莱纳多·斯当东爵士,⑨乔治·莱纳多•斯当东(1737—1801), 供职于东、西印度公司多年后,被选派随同马戛尔尼勋爵使团访华,被误认为是第一个出使北京的英国公使。1787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790年获牛津大学法学博士。D.N.B., LIV, 113.斯当东转求欧洲,结果令人失望。自从耶稣会受到压制以及随后被解散,打破了欧洲大陆悠久的博学汉语传统,在巴黎也一无所获。耶稣会的在华传教事务虽然由遣使会(Lazarists)接管,但是斯当东发现在遣使会总堂(Maison de Saint Lazare)竟没有人曾到过中国。巴黎外方传教会(Maison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有一个人曾经到过中国,但他回法国已经有20多年了,汉语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并且无论如何也不愿去那个遥远的国度了”。在英国众多的教授欧陆语言的教师中,有一个名叫蒙图奇(Antonio Montucci,1762—1829)①蒙图奇,意大利锡耶纳人,研习英语和其他使用中的语言,1789年在史塔福郡的韦奇伍德新学校教授意大利语。他一边用傅尔蒙(Etiénne Fourmont,1683—1745)的书学习汉语,一边教授别人,直到1804年离开英国返回欧洲,说服普鲁士国王为他的计划提供资助。他最后的著作完成于德累斯顿(Dresden)和罗马。见Montucci, The Characteristic Meri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2; Larousse, Dictionaire, XI, p.530.的意大利人,他受雇于史塔福郡(Staffordshire)的著名陶瓷世家乔舒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韦奇伍德家的陶瓷被选为敬献中国皇帝的礼物。蒙图奇曾经学过汉语,虽然仅是初学者而且是自学的,他对此全力以赴,并对筹备中的英国访华使团抱有浓厚的兴趣。被引荐给斯当东后,他引荐斯当东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罗马传信部天主教大学联系。在英国部长威廉·汉密尔顿爵士(Sir William Hamilton) 的帮助下,找到了两名接受传道训练的中国人。一个叫周保罗(Paul Ko or Padre Cho),他是较好的学者,但“反应迟钝、呆头呆脑、顽固不化”,跟随英国访华使团到中国后离开了使团;另一位李(Lee)先生善始善终,陪伴英国访华团走完漫漫旅程,直到使团从京城返回澳门后离开。因为李是“中国鞑靼人”,样貌和一般汉人不太相像,穿英国军装,佩戴军刀和绶带,用英语称其为“李先生(Mr.Plumb)”,常常被当作欧洲人进出。在英国使团遇到很多困难和小麻烦时,他真正为使团效过力。②Helen H.Robbins, 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London, 1908), p.245, 322, pp.391-392; Aeneas Anderson,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New York, 1795), p.64, 123, 132, 155, 160, 161, 166, 190, 201; G.L.Staunton, Embassy, I, p.388,II, pp.40-41, p.593; G.T.Staunton, Memoir of G.L.Staunton, pp.48-49; John Barrow, An Autobiographical Memoir (London,1847), p.50; Montucci, the Characteristic Meri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6.李在完成任务后离开使团,尽管很多人劝他回英国,可派到英国西部的修道院去,他直到1802年还与马戛尔尼通信。关于他对英国访华使团的贡献,所有的记录者都予以热情的肯定,其中有人评价说:“我能够给予他的赞扬无论怎样都不够。”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London,1804), 410.然而,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4)引用前耶稣会士梁栋材(Joseph de Grammont,1736—1812)的话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没有高水平的译员是马戛尔尼访华失败的最重要原因。Cordier, Histoire Générate.III, 81.梁栋材的观点见Robbins, 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pp.461-462.
在穿越大西洋和印度洋长达数月的航行中,英国使团中的一些人兴致勃勃地要跟这两位译员学习汉语,尤其是他们中的科学家巴罗(John Barrow,1764—1848)。③巴罗,科学家和数学家,马戛尔尼使团的审计官,在北京负责照管英国使团送给中国皇帝的礼品。后来在好望角还做过马戛尔尼勋爵的私人秘书,研究并写了关于南非地理的文章。他还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1835年被授予准男爵的荣誉称号。D.N.B., III, p.305; G.L.Staunton, Embassy, II, p.319; G.T.Staunton, Memoirs, pp.8-9.在斯当东的引荐下,巴罗得到了马戛尔尼勋爵的赏识,并与小斯当东④国内学界父亲的常用译名为斯当东,儿子为小斯当东。小斯当东跟随父亲第一次出访中国时,年仅12岁。—译者注一见如故,这个使团里聪明的见习童生的学习热情也感染了巴罗。小斯当东的德国教师赫脱南(Hüttner)⑤赫脱南(John Christian Hüttner, 1766—1847),莱比锡大学的古典研究学者,1791—1797年被莱纳多•斯当东邀请到英国担任小斯当东的家庭教师。他多年在英国外交部担任译员。G.T.Staunton, Memoirs, 5, pp.201-202; Allpemcine Deutsche Biographic, XIII, p.480.也有兴趣学习,然而,英国使团中仅巴罗和小斯当东初具汉语能力。在航行即将结束之际,小斯当东已经“跟随一位脾气非常坏的老师在断断续续的课程里”学会写工整的汉字并能略说汉语。⑥Robbins, 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p.177, n.1;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p.176, n.当他们的船队抵达中国北部海岸,在中国皇帝的特派官员面前,巴罗和小斯当东的汉语水平受到了考验,小斯当东的父亲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学习汉语的其中一个是成年人,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孜孜不倦地学习,但却尴尬地发现当中国官员跟他讲话时,他几乎完全听不懂,而他的中文发音同样让中国官员难以听懂;另一个是位少年,他肯定没有成年人那么刻苦,但他感觉敏锐,口齿更加灵活,结果证明他已经算是一个较好的译员了。”①G.L.Staunton, Embassy, I, p.489.
马戛尔尼勋爵接到的指示中称,除了那不勒斯的两名中国人之外,“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传教士,或其他不受国籍或偏见影响的有识之士”都可以为英国使团服务。②Morse, Chronicles, II, p.236.罗马传信部在澳门的两位传教士汉拿(Hanna)神父和拉弥尔特(Lamiet)神父,本想借机到北京谋个数学家或天文学家的职位,英国使团允许他们搭船北上是考虑到他们或许可以充当翻译,但因为中国只允许英国使团正式成员上岸,两位神父未能如愿,因此只能返回澳门。③Robins, 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p.245, 260.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努力号”(Endeavour)把一位会说西班牙语的中国青年送到英国使团协助翻译,但是他不能做译员,据莱纳多•斯当东说,因为当中国朝廷官员在场时,他战战兢兢的,以至于把英国特使的普通言语译成了中国式的难以想象的谦卑言词。④G.L.Staunton, Embassy, I, 396-397, p.451, II, p.14.
李先生和小斯当东因此成为英国使团仅有的译员,直到英国使团到达京城,遇到了皇帝身边效力的一群天主教传教士。法国海诺特人(Hainault)罗广祥(Nicholas Raux),巴黎遣使会会士,因为他说法语,便于和英国大使做简单沟通,因此使团在京期间都由他陪同。⑤Robbins, 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p.275, 282.据马戛尔尼描述,此人“又高又胖,举止谈吐从容,出口成章,懂汉语和满语,似乎十分满足现状”。意大利人德天赐(Adéodat Deodato),罗马传信部神父,经常为他们担任译员。但无论是这两位,还是其他传教士,都未被允许随英国使团前往热河,因此,所有最重要的觐见都由李先生和小斯当东做翻译。中国文人熟悉朝廷风格,英使文书最后定稿的译本至关重要,然而,30年前曾协助洪任辉书写呈词的广东人刘亚扁的结局众人皆知,中国文人无人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⑥Ibid., p.284;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p.72; Anderson,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p.160; G.L.Staunton, Embassy,II, p.234.1811年当北京驱逐传教士时,德天赐和另外三名传教士来到广州,在那里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座上宾,他们的翻译得到认可,直到他们准备好前往马尼拉。Peter Auber, China (London, 1834), pp.229-230; Morse,Chronicles, III, p.164; K.S.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1929), 177.据莱纳多·斯当东在他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ccount of the Embassy)记述,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之下,最好的方法是“英语文书先由赫脱南翻译成拉丁文,再由英使中不懂英语的中译员把拉丁文译成汉语。中译员用普通中国人的口语把拉丁语翻译出来,再由其他译员用合适的书面语转写下来。最后由见习童生立即把译稿工整地誊抄一遍,应中国译员的请求,原译稿要当着他的面销毁。⑦G.L.Staunton, Embassy, 11, pp.136-143.这位少年抄写的中文文书‘如此整齐和流畅,让众人感到震惊’。”⑧Barrow, Travels in China, p.176, n.
从接受使命之初,马戛尔尼勋爵就理解这一点:与清政府打交道最根本的困难在于语言问题,以这种可笑的辗转翻译交流,更凸显了语言问题。他觉得如果“能与(在广州的)总督建立常规往来,通过用汉语与他充分的交流来克服困难”,积怨很可能就此永久化解。因此,在马戛尔尼离开中国前向两广总督提交的请求中,他再次恳请“允许中国人教导英国商人汉语,汉语知识有助于英商更好地遵从中国的法律和海关程序。”⑨G.L.Staunton, Embassy, I, 239, II, pp.566-567; Auber, China, p.198; Morse, Chronicles, II, p.253.殷勤款待英国使团的两广总督给英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既然他听到两广总督给予了口头允诺,广州商馆可以向他传递信息,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事情会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乐观地相信这一请求能够实现。①Robbins, 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p.353, p.355, pp.364-365.
三、英国访华使团影响
在英国访华使团还没有扬帆回国前,广州商馆特选委员会在乐观的英使建议下,采取行动落实汉语学习的事情,好不容易找到一位中国人愿意在贸易季结束后教他们汉语。在澳门,中国教师拒绝出入东印度公司的住所,即使住得很近,也要求他的学生在别处见面,而且至多接收三名学生。在众多有意愿学习汉语的书记员中,特选委员会选择了特拉佛(Benjamin Travers)、帕特尔(Thomas Charles Pattle)和刺佛(John William Roberts)。特拉佛的职业生涯并不长,在帕特尔和刺佛的努力下,广州商馆一度恢复了昔日的汉语传统。②G.L.Staunton, Embassy, II, p.581; Morse, Chronicles, II, p.209.
虽然清政府很快下令禁止马戛尔尼勋爵提出的将汉语学习合法化的请求,禁止外国人向官方通事或买办之外的人学习汉语,③J.R.Morrison, Chinese Commercial Guild, p.48; Davis, The Chinese, III, p.199.但是广州有了一丝新转机,小斯当东与英国使团一起回到英国后,继续学习汉语。1798年,小斯当东的天赋被东印度公司认可,他是到广州商馆做书记员的最佳人选。④G.T.Staunton, Memoir of 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p.365; E.I.C.MSS, China, Court’s Letters, IV, (1796—1799), 29 March 1799.
通常这类职位都是由与东印度公司有关系的家族年轻成员来担任,所以当小斯当东1800年1月份到任时遭到一些人的嫉妒,但是很快就消除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由于小斯当东能够不受中国行商的干扰直接与两广总督交涉,因此,以往让商馆困扰不已的许多事情在他的协助下,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1800年“朴维顿事件”(Providence affair),由于小斯当东不懂中国法律,他怀疑两广总督故意误导英国商人,于是,他找到了一版完整的法律条文并把它部分译成英语。1810年,英文版《大清律例》(Ta-Tsing-Leulee)正式出版,这是首次连同案例直接译成英语的书,虽然此前该书早已人人皆知。⑤G.T.Staunton, Memoirs, p.17, 27, 28, pp.44-51; G.T.Staunton, Memoir of 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p.56, 381, 383; Morse,Chronicles, II, p.327, p.368;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pp.419-420.次年,小斯当东因父亲去世返回英国,在他回英国的两年里,广州商馆终于完全意识到他的重要性。⑥Morse, Chronicles, II, p.369.
继承了准男爵爵位的乔治·托马斯·斯当东于1802年初回到了英国,他发现汉语在蒙图奇和哈盖尔(Joseph George Hager,1759—1819)⑦哈盖尔,出生于意大利米兰一个日耳曼商人家庭。他在伦敦的工作受到法国拿破仑的关注,1802年拿破仑将其召到巴黎。1809年他回到意大利的帕维亚(Pavia)任东方语言教席(不包括汉语)。Biographie Universelle, XVIII, p.338;Classical Journal, June, 1810.间的竞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哈盖尔是德裔意大利人,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汉学家,曾接受阿拉伯语的训练,到伦敦后不久于1801年出版了他的《边划译》(An Explanation of the Elementary Characters of the Chinese),此书一经出版便受到一致好评,现在他正在准备编辑汉英词典。⑧Critical Review, Apr., June, 1801; Monthly Magazine, Aug., 1801.蒙图奇在英国居住时间要久一些,对汉语了解也要略胜一筹,他认为哈盖尔是半路出家的外来户,他的成功来自于“让真正有学识的君子敬而远之的厚颜无耻,他甚至在斯当东不在的时候在伦敦沽名钓誉”。⑨Montucci, Letters to the Editor of the Universal Magazine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cluding Strictures on Dr.Hager’s two works,and the Reviewers’ Opinions concerning them ...(London, 1804), p.24.他在《中国语言的特征》(Characteristic Meri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01)一书中尖锐地抨击哈盖尔作品的同时,也给出了自己对这一长期工作的规划。⑩Montucci, Proposals for an elementary work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London, 1801).在小斯当东回英国之前,《文献评论》(Critical Review)杂志就已成为主要阵地。①Critical Review, Feb., 1802.蒙图奇曾帮助东印度公司把莱纳多•斯当东介绍给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这为他立下一功。蒙图奇与周保罗有很好的交情,当那些那不勒斯来的中国籍传教士在伦敦逗留期间,他曾被这些中国传教士们推荐翻译英国皇室给中国皇帝的信件。借此,他自称是“英国皇室和东印度公司的临时译者”。他还获得了菲茨休和拉佩尔的私人赞助,他们的汉语词典供蒙图奇使用。②蒙图奇列出了他曾在英国看到的六部汉语词典。其中两部为菲茨休和拉佩尔从中国带回的,这两部词典是替英国皇家学会从广州购买的,一部是蒙图奇私人收藏,另一部原为罗马传信部所有,后被周保罗带到了英国。Montucci, The Characteristic Meri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8; Monthly Magazine, April, 1804.No.113.他想要修订拉佩尔词典(Raper dictionary)英译本的计划,直到1804年哈盖尔放弃在英国寻求赞助离开英国后,才开始实施。
巴罗对蒙图奇这一计划非常关注,因为他想在英国学习汉语,或许他代表的是小斯当东的想法。“如果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明文规定,所有赴中国出任书记员的人选必须认识500或1000个汉字,我敢说,胜任这一职位的人屈指可数(不超过20个),而这一职位的薪金又非常丰厚,像目前这种通过家族关系内定职缺的情况就不大可能发生了。”巴罗列举了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推动印度梵语研究时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自己不重视,完全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别人的掌握之中,那么,我们就活该忍受我们所抱怨的敲诈勒索。”③Barrow, Travels in China, pp.417-418.德庇时描述巴罗是“一个真正研究中国并了解中国的人”。Davis, The Chinese, I, p.77.在他们的呼吁尚未得到结果前,蒙图奇和小斯当东就离开了英国,学习汉语的兴致也如昙花一现。广州商馆再次召唤小斯当东,中国给这位未来的汉学家提供了比伦敦更好的机遇。
在小斯当东回到英国的时间里,他处理了父亲的遗产,与老朋友巴罗一起讨论改善与中国关系的计划。除了讨论语言问题外,他们积极主张再次派遣英国使节访华。这一主张在1804—1805年被提上日程,基于之前的经验他们提出很多建议,巴罗认为小斯当东在中国任职期间是英国派遣第二个使团的最佳时机,出使费用相对第一次也会有所减少,并且可以利用这位“才华横溢、做事谨慎、理智同时性情温顺”还会汉语的英国人。他相信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势在必行。④与此次出使中国有关的文件可参见E.I.C.MSS , China 20 (1782—1815).这段引文来自一个叫“J.B.”的人写的“备忘录”中。巴罗接着说:“无论如何,给中国皇帝的信附拉丁译文,然后随其自然,都似乎是非常不妥当和不礼貌的做法。这些信件无一例外地被交到了法国和葡萄牙传教士手中,他们带着挫败我们的目的,不止一次地在翻译时扭曲原意,让我们的计划失败,使他们国家受益。”
1804年年底小斯当东回到广州,他发现在他休假期间,广州商馆另聘了西班牙奥斯丁会的罗德里格(Rodriguez)神父做翻译。罗德里格神父在内陆和北京传教多年后,再次回到沿海地区。虽然罗德里格神父为广州商馆翻译一事先是遭到葡萄牙人、后来又遭到中国人的强烈反对,罗德里格神父在接下来的五年依然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在广州和澳门做翻译和教学,而且特选委员会也给他丰厚的薪金。他被认为是“当地最懂汉语的外国人”,⑤1808年11月1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给他父亲的信,L.M.S.MSS, China (1805—1820).不久他身边聚集了一群渴望学汉语的欧洲人。在公司被快速提拔并成为特选委员会成员(1806年)的刺佛和帕特尔,由于公务繁忙无暇顾及汉语学习,但是在新来的人中,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1780—1874)⑥皮尔逊把疫苗接种介绍到中国,并写过一本关于疫苗的小册子,后由小斯当东翻译成汉语。 J.R.A.S., IV, xiv; K.C.Wang and L.T.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Tientsin, n.d.), p.143; Chinese Repository, II, 36 ft.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误把这一小册子的贡献归功于伦敦同名的George Pearson博士。D.N.B., LIV, p.115.和茶叶检验员波尔(Samuel Ball)⑦波尔任东印度公司茶叶检查员多年,1806年他的朋友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写信为他推荐了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Charles Lamb, Letters, edited by Alfred Ainger, 2 vols.(London, 1904), I, p.289.波尔于1832年回到英国,当时曼宁把自己收藏的珍贵的汉语书籍赠送给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图书馆,波尔承担了给曼宁藏品编目的工作。 J.R.A.S.,VIII, p.xi; Quarterly Review, XLIII, p.153.波尔著有:Observations on the Expediency of Opening a Second Port in China (Macao,1817) 和An Account of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Tea in China (London, 1848).抽时间和这位新老师学习汉语。在小斯当东第一次离开广州商馆期间(1808—1810),罗德里格为公司做了最后一次翻译,他在小斯当东来中国前一年被驱逐出境了。①Davis, The Chinese, I, 60; Morse, Chronicles, II, 409, III, 72; R.Morrison’s Journal, 5 Jan., 6 Oct.1808; Morrison to the L.M.S.,13 May 1814.L.M.S.MSS, China (1805—1820); Select Committee to the Court of Directors, Secret Letter, 1 Mar., 1809.在伦敦会的手稿材料中,有一份马礼逊和他学生的通信的抄件,也抄给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和广州商馆。引自L.M.S.MSS,E.I.C.Transcript.为了帮助他的汉语学生,罗德里格神父用拉丁文编纂了一部汉语语法书。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浩如烟海的文件中,有一本用英语注释的罗德里格语法书手稿,他的一个学生将之完成并呈交给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以备“公司使用”。②“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xpressed by the Letters that are commonly used in Europe.From the Latin of F.John-Anthony Rodriguez, A Spaniard, of the order of St.Augustin.Who had been Missionary,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in the interior Parts of China.”John Geddes,一位与广州商馆毫无关系的商人将之译成了英文,送给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Mr.Dundas,其中称罗德里格神父是“一位极具智慧和灵敏的人”,有“相当高水平的汉语”。John Geddes 翻译语法书的目的是为那些无需学习汉字而只学口语的人准备工具书,发音是南京音,“这个音被认为是最好的、最普遍的” “此外南京话都能听得懂。任何南京话说得好的人,只要年龄不是太大,如果他在其他省份而且必须说当地语言时,他能很快适应其他省份的发音”。
在刺佛担任特选委员会主席期间,广州商馆里又掀起一股学习汉语的潮流,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图书馆的建立意义非凡。公司职员的个人书籍收藏于1806年以前就已悄然开始,但是人们愈发感觉到,如果有一个供大家开放使用的图书馆,既可以避免重复收藏,也可以物尽其用。捐款和赠书奠定了广州商馆图书馆的根基,订购图书使图书馆继续发展。刺佛提供了一间和商馆餐厅毗邻的大房间用来放置图书,以便大家用餐前聚集,并委任皮尔逊为图书馆馆长。这些藏书被保管并且在广州商馆贸易季都在运营,这无疑为在中国的一小群欧洲人带来了极大的福祉。广州商馆解体时,图书馆也散落了,当时有以英语、法语和汉语为主的图书4000余册。③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藏书目录,由马礼逊和德庇时编写,1832年出版,共列了1600种图书,分六个类别:1.神学,法律,哲学;2.传记,历史,游记;3.艺术,科学,商业,政治;4.古典文献,古董,翻译,语文学;5.诗,戏剧,小说;6.杂撰。Chinese Repository, IV, p.96.See also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Morrison, D.D.by his widow (London,1839), I, p.215; Davis, The Chinese, II, p.253; William C.Hunter,The Fan Kwei at Canton(《广州番鬼录》)(London,1882年),p.31.德庇时将一份手抄目录当作礼物赠给了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图书馆。
四、托马斯·曼宁和马礼逊
小斯当东第二次离开商馆的那段时间(1808—1810),东印度公司翻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并不是柔瑞国(Father Rodriguez)神父。1807年1月,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1772—1840)④托马斯·曼宁,哲学家、数学家、探险家,是第一位进入西藏到达拉萨的英国人 (1811)。据说他通晓15门语言,曾被认为是欧洲第一位汉语学者。因为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有一篇著名文章《论烤猪》(A Dissertation unpon Roast Pig)提到他,他与兰姆的私人友情妇孺皆知。曼宁的个人藏书、书籍和手稿全部赠予了英国皇家亚洲学会。D.N.B.XXXV1, pp.71-72; J.R.A.S., VI, vi; Lamb, Essays of Elia (London, 1903), p.164; T.Manning, Journey to Lhasa,in Clements R.Markham, 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London, 1876), p.280.曼宁从未留下任何重要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他的朋友们对此颇为失望。R.Morrison to the L.M.S.,21 Mar.1817.—L.M.S.China (1805—1820); Staunton to R.Morrison, 10 Apr., 1818; Morrison, Memoirs, I, 5152; G.T.Staunton, Miscellaneous Notices, p.407; Chinese Repository, IV, p.149.意外地来到了澳门,曼宁—英国剑桥大学高材生,35岁左右,强烈的好奇心让他开始研习汉语。在大学时代,他就已经对亚洲语言热情高涨,他认为亚洲语言“通过比拟或许能够佐证他关于希腊语介词和虚词的观点”。1801年,曼宁前往巴黎,跟随哈盖尔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学习,《亚眠和约》(Peace of Amiens)失效后,他被迫终止了学业。哈盖尔的赞助人拿破仑给他一本特殊通行证,他才得以离开法国回到英国,他原本希望能够继续学业,不幸的是,他回到伦敦时正值小斯当东和蒙图奇将要离开伦敦,正如曼宁自述:“和我想象的相去甚远,在英国根本没有丝毫提高自己汉语水平的机会”,于是,他决定去中国。带着能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谋作外科医生的想法,曼宁开始学习医学。这期间他此前的想法已经变了,他的视野也开阔了,他对整个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决定转而研究中国的“社会与哲学”。①“A moral view of China; its manners; the actual degree of happiness the people enjoy; their sentiments and opinions, so far as they influence life; their literature, their history; the cause of their stability and vast population; their minor arts and contrivances;what there might be in China worthy to serve as a model for imitation, and what to serve as a beacon to avoid.” T.Manning,Journey to Lhasa, p.280.在英国皇家学会的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的推荐之下(约瑟夫·班克斯曾承认他钦佩曼宁的才华),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聘用了曼宁,曼宁告别了他充满幻想、幽默风趣的好朋友查尔斯·兰姆,踏上了中国之旅。由于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曾坦言曼宁提出将赴华学习汉语,广州商馆特选委员会对曼宁的到来颇为困惑,但他严格自律,并没有做任何让东印度公司不快的事,这让广州商馆感到宽慰。“虽然我们认为他成功的希望很渺茫”,特选委员会说,“从他的知识储备和性情来看,他其他方面的成就可能要比他对公务的贡献大得多。”②班克斯爵士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的信, May 1806.Auber, China, pp.218-220; Lamb, Letters, I, p.196, 242, 279, 297;Morse, Chronicles, III, pp.71-72.曼宁到达中国的时间是1807年1月,不是马士(H.B.Morse)记载的1808年。
曼宁的计划是要在北京朝廷谋一份天文学家兼医生的职位。他于1807年11月向两广总督正式提出申请,并于翌年再次申请。只是他来华的时机不好。1805年的反夷事件导致清政府颁布禁教令,并驱逐在京的外国天主教传教士。③Latourette,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p.175-176.极为失望的曼宁带着新的希望前往交趾支那,但是依然没有成功,④当时在广州的一个人说,尽管他已经成为法籍马里•约达(M.Dayot,越南名:阮文智)先生前往安南国英国使团的成员,甚至都不被允许在顺化上岸。“一位在安南的法国人告诉安南国王,说曼宁是一位科学家,一个好人,安南国王答道‘或许吧,但他是英国人。’”Morrison’s Journal, 14 Jan., 4 July 1808; R.Morrison to Hardcastle, 4 Dec., 1809.L.M.S.MSS, China (1805—1820).于是曼宁返回广州,此时正值1808年斯当东回英国,曼宁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他在广州继续研习汉语,偶尔做些翻译,1810年初前往孟加拉和西藏地区。此时,罗德里格神父已经离开澳门,斯当东尚未从英国回来,幸好有一位年轻的英国新教传教士,广州商馆才没有再次陷入没有译员的困境。这位新教传教士于1807年初秋抵达澳门,在短短的时间内,他的汉语水平取得了惊人的进步。⑤Morrison’s Journal, 21 June 1809.L.M.S.MSS, China (1805—1820); Morse, Chronicles, III, p.72, 103.马士注意到曼宁汉译英的译文“非常糟,简直无法辨识,除非用英语思维略能理解,破坏了中文原意。”
1805年,当马礼逊被伦敦会选中作为赴中国传教的第一人时,他在英国学习汉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⑥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对伦敦会的答复 (London, 1806), 第212页。蒙图奇和哈盖尔去了欧洲大陆,小斯当东刚刚返回中国,曼宁虽然还在伦敦,但他仅是个汉语初学者,况且正忙于他的医学研究,这是他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谋得一官半职的筹码。伦敦会图书馆自诩有一份“汉语”主祷文的手稿,但很快就被初学汉语数周的年轻的马礼逊识破。⑦手稿背面写着“汉语祈祷文。Cozeén.[sic.] G Burder带来,1802年6月2日由肖蒙(Chaumont)先生抄写,原件近期从中国京城寄出。汉字从上至下、从右到左阅读。” L.M.S.MSS, China (1805-1820); Morrison to Burder, 27 Dec.1805.Ibid.那位阿贝•肖蒙(Abbé Chaumont)先生,一位在亚洲生活多年的罗马传教士,将北京主教Monsr.Do Govea的拉丁文著作译成了法文,书名为 Relation de l’Etablissement du Christianiame dans le royanne de Corée (London, 1800)。伦敦人普遍认为阿贝•肖蒙先生懂汉语,但是证据显示,他汉语书面语的知识有限。Rev.William Moseley,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London, 1842), 23, 69.关于大英博物馆藏汉译手稿的内容和价值,当时曾咨询过肖蒙、小斯当东、蒙图奇。Ibid., p.54, 56, 58, 61, 75, 77.
1805年8月至12月,马礼逊三次接触汉语为他的学习奠定了基础。他抄写了一部大英博物馆馆藏的四福音书手稿,发现了两部英国皇家学会图书馆收藏的词典,并结识了容三德(Yang Sam Tak)。这位来自广州的中国青年为了经商而热切地渴望学习英语,在英国威尔逊船长(Henry Wilson)的帮助下来到了伦敦。如何安顿容三德成为威尔逊船长的一大难题,由于威尔逊有着很强的福音派倾向,他克拉珀姆区福音派(Clapham Sect)的朋友和亨利·索顿(Henry Thornton)、廷茅斯勋爵(Teignmouth)等人注意到了容三德。克拉珀姆派为扎查(Zachary)从塞拉利昂①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2 vols.(Philadelphia, 1841), II, pp.317-318.(Sierra Leone,即狮子山国,在非洲西部)带来的一群年轻的非洲人建了一所宗教学校,年轻的中国人容三德被送到了这所学校。容三德发自内心地厌恶黑人,他与这个学校格格不入,因此他欣然接受了马礼逊的邀请,搬进了马礼逊在大英博物馆附近菲茨罗伊广场匹特街14号的住处,尽其所能全力帮助马礼逊学习汉语。容三德算不上是一位称职的老师,虽然他会读、会写并且懂一些官话,但他在这位年轻的传教士尚未做好去中国的准备之前,就返回了中国。但在容三德的帮助下,马礼逊已经成功地抄录了大英博物馆的手稿,并带着这份抄本去广州协助他完成了《圣经》的汉译。②Moseley,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82-87; “1803年与一位现在克拉珀姆的中国人容三德的谈话记录 ,”L.M.S.MSS, China (1805—1820).
前往中国传教的极不确定性和它的传奇性使得英国福音派人士对汉语学习极为关注,福音派人士集思广益对学习汉语提出了许多建议。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格兰特(Charles Grant)是此行的热心支持者,但他相信由于汉语的特质,《圣经》永远不会被译成中文。③Moseley, op.cit., p.19.英国商馆第二级内科医生麦肯(Dr.McKinnon)告诉伦敦会的朋友,在澳门可以学到“也许不是很地道的”汉语官话。他认为虽然中国可能不会对传教士敞开大门,但是对科学家或有一技之长的人,如钟表匠和懂医药的人则另当别论。④Hollingsworth to Burder, 14 Oct., 1805.L.M.S.MSS, China (1805—1820).威尔逊船长认为只要找到合适的人,在广州学习汉语并非难事;但是在中国居留必须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准许,他认为,假如去中国的人是位牧师,只要东印度公司任命他为广州商馆牧师,就能留在中国。威尔逊船长进而建议小斯当东或许能够在学习汉语方面提供帮助。⑤R.Morrison to Robert Cowrie, 12 Sept., 1806; Same to George Burder, 25 Sept., 1806.L.M.S.MSS, China (1805—1820).
麦肯医生所倡导的让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用科学辅助传教的方式,让伦敦会投入了资金用以购买“一个小型精密仪器从事各种自然科学实验”,然而,马礼逊却完全不适应这种方式。“如果扪心自问”,他说“我更愿意从今天开始将我毕生精力用在研究《圣经》的原始语言和汉语学习上”⑥R.Morrison to Hardcastle, 1806, Ibid..。事实上,在马礼逊登船而曼宁抵达广州的那个月,他在使用科学仪器一事上并无任何闪失,而曼宁在北京谋职的热切希望遭到了冷淡的拒绝。
清政府对待除外国商人以外的来华人员的态度,英国东印度公司非常明了,即使是董事会中福音派的成员也迟疑是否要推动马礼逊的事情,尤其在他们感觉到许多英国董事会成员普遍反对传教的态度后。虽然格兰特和帕里(Edward Parry)非常同情马礼逊,但是格兰特还是敦促马礼逊以威尔士亲王岛 (即槟榔屿)作为汉语学习的驻地。在那里马礼逊既不会与清政府有任何冲突,又可以学习汉语和马来语,一举两得。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格兰特诚挚地促请马礼逊接受此建议并给他在槟城的朋友写介绍信。⑦Charles Grant to Hardcastle, 17 Nov.1806, Ibid..无论是马礼逊还是伦敦会都拒绝接受这种折中的妥协,找到不依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到达东方是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因此,马礼逊取道美国纽约搭乘一条美国船前往目的地。在抵达广州后的几个星期,他住在美国洋行,平时也被当成是美国公民。
马礼逊在利用英国皇家学会的词典时,结识了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爵士,得到了一封班克斯爵士写给英国广州商馆小斯当东爵士的引荐信。这一季的特选委员会对马礼逊也很有利:由剌佛任主席,帕特尔位居其次,他们是在马戛尔尼出使后从初级书记员中被选中学习汉语的三个人的其中两位。不仅如此,剌佛作为特选委员会主席,早就热切地鼓励广州商馆雇员追求知识的兴趣,尤其提倡学习汉语。小斯当东从澳门给马礼逊写了一封友好的信,强调了其中的困难,转告他剌佛已决定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马礼逊到达广州商馆六个星期后,小斯当东也到了商馆,他一到商馆就把这位年轻的传教士引荐给特选委员会主席剌佛。剌佛对马礼逊非常友善,还立即为马礼逊提供图书馆的便利,并邀他到广州商馆用餐。①G.T.Staunton, Memoirs, p.36; Morse, Chronicles, III, p.54; Morrison, Memoirs, I, p.162.这是小斯当东和马礼逊终生深厚友谊的开端,也是马礼逊和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结下不解之缘的开始。季末,小斯当东第二次休假回英国,启程前,他看着马礼逊舒适地在一家“闲置的法国洋行”安顿下来,并把自己的官话老师介绍给他。②R.Morrison’s Journal, Feb., 1808.L.M.S.MSS, China (1805—1820).
除了小斯当东外,马礼逊起初并没有和商馆其他更重要的成员有密切来往。图书馆馆长兼外科医生皮尔逊先生和茶叶检验员波尔与马礼逊一样痴迷于汉语学习,志同道合的三个人很快共享书籍和学习计划。③“皮尔逊先生把我还没有抄完的手稿词典留给我,真是太好了”。R.Morrison’s Journal, 15 Mar., 1808.L.M.S.MSS, China(1805—1820).“澳门的波尔先生送给我一部西班牙语写的汉语语法书”,Ibid., 22 Apr., 1808.到1808年春,马礼逊已经充分掌握了汉语口语,中国人能听懂他说的广东话和汉语官话,他迫不及待地实施他的第一项伟大计划,编写一部英汉、汉英词典。④R.Morrison to Hardcastle, 29 May, 1808.L.M.S.MSS, China (1805—1820).彼此熟悉后,马礼逊在与皮尔逊的谈话中透露了这一计划。皮尔逊医生立即和广州商馆高层人士提起马礼逊的计划,得到一致赞同。马礼逊这段时期的几篇日志非常重要。1808年4月11日:“特选委员会的益花臣(John Fullerton Elphinstone)先生从澳门寄给我他的手抄汉语词典,并衷心祝愿我实现我的目标,他认为这将使每一个和中国有联系的人受益。”
1808年5月23日:“皮尔逊医生来信说剌佛先生赞同我编一部汉语词典的设想,并愿意在费用方面予以帮助,他认为东印度公司也不会反对。此外,这两位先生都很乐意施以援助,但是他们自身的处境也很微妙,英方有令不允许他们插手此事。皮尔逊医生催促我前往澳门,希望澳门葡萄牙政府或天主教会不要干涉我的计划。”
1808年5月25日,以下是波尔传来的喜讯:“对我计划感兴趣的先生们想方设法让我在澳门安顿下来,为我提供住处和一些桌椅,我可以在那儿住到9月份。剌佛先生(有必要不让公众知道这些人的名字)说不能安排我住在商馆内。”
1808年6月4日:“恰逢英王寿辰,在剌佛家用了早餐,东印度公司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
1808年6月8日:“皮尔逊先生和剌佛先生来访。皮尔逊先生的一席话至关重要,对我编纂字典大有裨益。”
1808年6月10日:“剌佛再次造访,小坐片刻。他第一次提到了解我在学习汉语并打算编纂一部词典。当我说已经有几位先生给了我一些词典和书时,他表示会在职权范围内尽其所能为我提供帮助。”
1808年6月11日:“皮尔逊先生到访,剌佛先生正式委托他传达,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暂且把我安顿在澳门或广州商馆,以便我继续编纂工作。此外,待将来词典编成之日,他也定会鼎力协助出版事宜。”
就这样,马礼逊作为东印度公司的编外人员领到了一份津贴,直到次年冬季,他被任命为广州商馆的正式译员。在这期间,马礼逊继续一边学习汉语,一边致力于词典编纂,同时还要指导波尔和一个叫莫顿(William Morton)⑤莫顿几乎还是个孩子。他身体欠佳,第二年因健康原因被迫放弃了学习汉语。他的姐姐在1809年冬与马礼逊结了婚。Morrison, Memoirs, I, p.246.的年轻人学习汉语,莫顿及家人暂居澳门,马礼逊希望他可以做他的长期助手。⑥R.Morrison’s Journal,1808年6月13、27日;7月8日。L.M.S.MSS, China (1805—1820).
值得一提的是,在马礼逊早期学习汉语期间,他几乎没有得到欧洲对汉语有研究人士的指导。此外,他的中国教师们也是差强人意。他在伦敦认识的容三德,一心想着经商,对他关心的事业不感兴趣。①Ibid., 2月7、23日;1808年3月22—23日。“容三德很乐意帮我,但是反对以我最需要的方式帮我—那就是用汉语交流。” R.Morrison to Hardeastle, 10 Dec.1809.L.M.S.MSS, China(1805—1820).小斯当东的汉语官话老师云官明(Abel Yen)是广州教区的天主教徒,对新教并不了解。此人系山西人氏,从小被教会收留并接受教会教育。他官话标准,但是对汉语经典的了解不及拉丁语多。事实上,他对汉语经典几乎一无所知。②Morrison, Memoirs, I, 163, 167; R.Morrison’s Journal,1808 年 3 月 10、11 日。马礼逊亟需一位能用汉语写文章的人,1808年春,蔡轩(Low Heen)最早任此职,马礼逊说他“是对我帮助最大的助手”。③R.Morrison’s Journal,1808 年 3 月 15 日。因为云官明不愿离开广州,于是桂有霓(Kwei Une)取而代之陪同马礼逊前往澳门,他们6月初动身,整个夏季都陪同马礼逊。马礼逊此时写道:“我的助手现在不错,只要能够维持现状,毫无疑问我会受益匪浅。”④“我现在一共有四个助手。蔡轩负责抄写和教授方言。桂有霓也负责抄写,同时教授官话。蔡轲(Afo)负责采购等等。阿定(Ating)负责掌勺……容三德负责除桂有霓之外其他人之间的和睦相处。”R.Morrison’s Journal,1808年3月21日。L.M.S.MSS, China (1808—1820).
五、马礼逊任职于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第一次因公务求助于马礼逊是在1808年10月,当时由于与中方的语言障碍导致商馆人员全部从广州撤离。⑤英军海军少将度路利(William O’Brien Drury,?-1811)1808年9月21日率领远征军在澳门登陆,随后又有一支孟加拉来的分队加入。中国人及澳门葡萄牙人极力反对,10月停止贸易,11月下旬度路利撤军后,12月初贸易恢复。曾为度路利少将担任翻译的罗德里格一度被捕,由于罗德里格受到中国人和在华葡萄牙人的憎恶,英国人帮他离开中国并给予了一万元奖励。剌佛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怪罪而被撤职,两广总督吴熊光也遭到降级的处置。—译者注此时,马礼逊在给帕特尔的信中说,他不愿意参与政治事件。⑥R.Morrison’s Journal,1808 年 10 月 15、30 日.L.M.S.MSS, China (1808—1820).1809年2月,东印度公司正式任命马礼逊为译员,年薪500英镑(合2000中国银元),还允诺马礼逊此前提出的安排莫顿做他的助手。⑦Alexander Pearson to R.Mortises, 19 Feb., 1809., L.M.S.MSS, Correspondence with Fisher; Morse, Chronicles, III, p.72.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在1808年2月任命小斯当东为广州商馆译员,在他作为货主的常规薪金之外,另增加年薪500英镑。当这一任命到达时,小斯当东离开了中国,于是在他1810年返回中国后开始执行。1809年4月4日,这位译员接到了委员会大班交给他的第一份翻译任务。此时的马礼逊和他的新娘—莫顿的姐姐愉快地生活在澳门,跟随葛先生(Ko-sienseng)研读“四书”。葛先生是一位老学究,取代桂有霓做马礼逊的官话老师,同时也指导马礼逊夫人和莫顿的汉语学习,还监管蔡轩的抄写工作。⑧R.Morrison to Hardcastle, 4 Apr., p.1809.L.M.S.MSS, China (1805—1820).据说葛先生的祖父是朝廷命官,“他性情温顺又有亲和力,……毕生投身于教书事业。”⑨R.Morrison’s Journal, 22 Dec., p.1812.L.M.S.MSS, China (1805—1820).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的固定收入让他摆脱了经济上的窘迫,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投身于汉语学习。1809年秋,他返回广州商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按常规在贸易季节与东印度公司其他雇员一起常驻广州商馆。但是,1810年2月1日,他和他的家人还在澳门时,发生了一起紧急事件,⑩1810年1月16日,一位叫黄阿胜的中国人在商馆附近被杀,中方认定凶手是英国“皇家夏绿蒂号”(Royal Charlotte)的水手。因英方不能向中方交出凶手,亦不认可中方的证据,贸易暂停。—译者注“羚羊号”(Antilope)奉命将他带回广州。2月10日:“在与广州府和南海县的重要会晤中,马礼逊担任译员。”⑪Morse, Chronicles, III, pp.103, 120.自此,马礼逊对广州商馆襄助极大。
剌佛当时任广州商馆主席,他认为任命马礼逊为公司译员远比临时聘用罗德里格神父或曼宁意义重大。他希望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能有一个固定的、永久的职位,并希望广州商馆能够培养汉语人才。这意味着要即刻从年轻的书记员中招募汉语学习者。随后,三位书记员立即投身到了剌佛的计划中,同意从1810年夏天开始跟随马礼逊学习汉语。选中的人分别是:图恩(Francis Toone)、部楼顿(William Plowden)和伯赞克特(William Bosanquet),比尔先生(Mr.Beale)为临时加入,他是澳门一家“Letter of Credit House”的成员,①此人可能是麦尼克行(Magniac and Company)的比尔(Thomas Beale),任普鲁士大班的英国商人。参见Morse,Chronicles, III, p.176.还有一位荷兰年轻人,他不久前刚从海盗手中死里逃生,他当时得到商馆主席剌佛的护佑,于翌年冬天便随剌佛一起离开中国。这就是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第一个汉语班的阵容。皮尔逊医生经常跟他们在一起学习,翌年春,部楼顿因病返回英国,米勒(Charles Millet)加入进来。②R.Morrison to Hardcastle, 25 Feb.1810; same to same, 7 Jan.1811.L.M.S.MSS, China (1805—1820) ; Morse, Chronicles, III,p.133, 178.此后,受雇于公司的雇员无一例外都投入到汉语学习中。
随着1810年秋天英国船只的到来,剌佛商馆主席一职被解除,由波朗(Henry Browne)接任,但是和波朗一起到中国的还有小斯当东。在小斯当东和曼宁不在广州期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接受了特选委员会聘用马礼逊的建议,但是现在宣布称:“斯当东准男爵既已返回中国……东印度公司有理由不再继续聘用马礼逊先生……东印度公司对马礼逊薪金的发放也即刻终止。”③Court of Directors to Canton, 18 Apr.1810.L.M.S.MSS, E.I.C.Transcript.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剌佛解职并没有给特选委员会的政策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加之小斯当东积极支持马礼逊的事业,波朗很快被说服了。特选委员继续聘用马礼逊并支付他工薪。④R.Morrison to Hardeastle, 4 Feb.1811.L.M.S.MSS, China (1805—1820); Morse, Chronicles, III, pp.134-145.“几位低级职员(为了提高自己)最近开始在马礼逊的指导下学习汉语。对此,我们认为马礼逊的服务始终非常重要,因而提请聘他做教师,在广州商馆职员中推广迫切需要的汉语知识。”Select Committee to the Court of Directors, 31 Jan.1811.L.M.S.MSS,E.I.C.Transcript.马礼逊此前夏天开始教授汉语的事情,让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同意接受马礼逊作语言教师,因为董事会知道委员会支持保留马礼逊教员一职,并且同意在恢复小斯当东译员职位的情况下继续支付马礼逊薪金。此外,小斯当东因为疏于汉语学习已久,此时对公司的事务感觉有压力,“其他事务和气候的原因”让他在汉语学习方面力不从心,他开始越来越依赖于马礼逊的帮助。⑤G.T.Staunton to John Barrow, 16 July, 1811.E.I.C.MSS, China 20 (1782—1815).翌年当他返回英国时,译员一职的薪金即刻转给马礼逊,马礼逊年薪累计1000英镑,与低级外科医生的收入相当。⑥Morse, Chronicles, III, p.165.在马礼逊回到英国的两年(1824—1826) ,他每年有500英镑收入。1830年,马礼逊的薪金涨到1300英镑,与高级外科医生相当。那时,特选委员会建议董事会为马礼逊增加退休金,遭到了董事会的拒绝。Ibid., IV, 223: China Consultations, 28 Dec.1820.L.M.S.MSS, E.I.C.Transcript.1814年小斯当东再次踏上中国土地之时,已担任特选委员会委员的他拒绝担任译员。马礼逊的地位从此稳固,他的未来有了保障。⑦R.Morrison to Hardcastle, 7 Dec.1814.L.M.S.MSS, China (1805—1820).
伦敦会对其传教士并没有稳固的经费支持,可以想象,早期传教士们或多或少要靠自己解决经济问题。伦敦会在给马礼逊的指示信中建议他,可以教授英语或各种科学,以全部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的经济压力。⑧Instructions to R.Morrison, 20 Jan.1807.L.M.S.MSS, China (1805—1820).接受东印度公司的固定薪水,使马礼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边渴望摆脱经济上的困窘,一边又想潜心研究,而且他对政治上的勾心斗角毫无兴趣。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掌握汉语,马礼逊认识到稳定收入的工作和汉语学习有一定关系,这样的益处更大。“您希望我能够自给自足”,他写道,“我希望这是最少分散我精力的方式”。⑨R.Morrison to Hardcastle, 25 Feb.1810, Ibid..同时,广州商馆大班的行为让马礼逊意识到,为英国商馆效力会让自己成为清政府的眼中钉、中国商人的肉中刺。“剌佛先生果然有先见之明”,马礼逊写道,“他极力隐瞒我在商馆任职这一事实,直到我能够不依靠中国助手独立工作;六个月之后我参与广州商馆与清政府的会晤,我在商馆任职才为人所知。”这样一来,他原本可以愉快地辞去职务,但是他意识到:“如果我不在商馆任职,他们就无法容忍我在中国居留。”①Same to same, 7 Jan.1811, Ibid..一度非常担心重蹈洪任辉和罗德里格神父的覆辙,他曾经在帮商馆翻译拟定文件时要求特选委员会保证,他无需对文件内容负责,只负责翻译抄写。②Secret Consultations, 11 Oct.1814.L.M.S.MSS, E.I.C.Transcript; Morse, Chronicles, III, 210-211.“在东印度公司里,人人皆知他是第一个能够用汉语起草可以被中国当局同意接受的公文的人,而他准备并且提交的第一份公文,以前被当作是一位有学问中国人的成果,中国官府用了各种方法查找公文作者,准备以违背中国法律、辅助外国人、叛国罪将其治罪。”Asiatic Journal, March 1835."Memoir of Morrison," by T.Fisher.
整整25个春秋,马礼逊为商馆立下的汗马功劳并非一直都得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肯定,他们很不情愿并极为勉强地接受特选委员会对马礼逊的任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之所以会持这种态度,是因为担心马礼逊的传教活动影响他们与清政府的关系,尤其是1811年清廷颁布反对传教士的禁令以后。如果马礼逊采取其他方式,他能否登陆并得到特选委员会朋友的保护值得怀疑。1813年,伦敦会派第二位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③米怜在马六甲建立了伦敦会的传教据点,编有《印中搜支》(The Indo-Chinese Gleaner,1817—1822),并在马礼逊的帮助下创办了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他学习汉语非常勤奋,在《印中搜支》上发表了很多重要的汉语著作的译文。 D.N.B., XXXVIII, p.9; Robert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Rev.William Milne (Malacca, 1824).来中国,在澳门登岸的当天他就被中国当局驱逐,马礼逊没能帮助米怜获得商馆的准许留在广州学习汉语。米怜在英国广州商馆呆了一个月,和特选委员会现任秘书图恩住在一起,但他的传教方式完全与马礼逊心无旁骛地学习汉语不同,他积极主张以向中国人散发宗教读物的方式传教。④Latourette,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178;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Rev.William Milne, pp.44-45.1815年,广州商馆特选委员会接到伦敦指示,立即解雇马礼逊并终止商馆与教会的任何合作。如果马礼逊想继续留在广州,必须以“美国人的身份”留下。广州商馆当年10月开会讨论董事会1815年1月6日的这一指示。特选委员会沉着地“决定在没有接到进一步的命令前,延迟执行这一指示”,并请马礼逊对此做出详细的解释。⑤Court of Directors to Canton, 6 Jan., 1815; Select Committee to Robert Morrison, Secret Consultations, 12, 14 Oct., 1815.L.M.S.MSS, E.I.C.Transcript.马礼逊针对这一谴责,声明自己并不属于“天主教”(清政府在颁布的禁令中对罗马教廷的称呼),也没有散发宗教书籍。在为争取继续聘用马礼逊而给董事会的申诉中,委员会主席益花臣和小斯当东爵士据理力争,最终他们的目的达到了。⑥R.Morrison to the Select Committee, 14 Oct., 1815.特选委员会的立场和观点值得引录:1815年10月12日,广州(商馆)秘密协商: 我们不得不考虑,解聘马礼逊会给公司在华贸易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和不便……因此我们决定暂缓执行董事会的决议。我们试图说服董事会对印刷、出版和分发汉语版《圣经》以便用基督教义来教化当地人这一问题的看法,同样,我们也会注意英国政府关于干涉其他国家包括像中国政府这样似乎并不重视宗教的国家的宗教信仰的政策。如若马礼逊先生此举是为了传教而引起我们或中国朝廷的注意,那么我们应该当机立断劝阻他,如果他任意妄为,我们只好即刻解聘他,并不再保护他。马礼逊在公司的广州商馆居住期间,不太可能瞒着我们公开进行传教或是其他的行动;在澳门居住期间,有当地的葡萄牙教会监督。至于出版中文《圣经》译本,虽然不是马礼逊告诉我们的,我们当然知晓此事。然而,出版和散发宗教小册,我们很怀疑,在这里经商的人经常见面,从未听人说过此事,也从未听说过其他地方有。我们相信这件事,充其量就是马礼逊把一部分《圣经》译成了中文,并印了一些中文《圣经》供他自己使用;或许也给了他熟悉的人一些印本。中国人式的礼貌不会让人拒绝接受作者的赠书,但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否有人会读这些书,或者书的内容会给人留下任何印象。至于向中国人传教(被理解为利用他的影响劝诱中国人公开承认基督教信仰,因此引起中国政府对他和那些入教者的注意),我们不相信马礼逊已经有或者可能有任何一个教徒,如果他有这样做的企图,不可能躲过我们和中国官府的注意。马礼逊偶尔赠送他翻译的《圣经》,只是努力让人们对基督教有些好感,而且这样的行为非常有限,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得知,大范围向中国人散布《圣经》的是一位居住在爪哇、名叫米怜的传教士,中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如果派遣马礼逊的伦敦会这样说,我们必须声明那都是胡说,毫无根据。以我们观察,如果马礼逊引起了中国官府的注意或者他为宣传宗教观点的行为引发了怨言,我们完全有责任制止这样的举动,并且立即终止马礼逊与公司广州商馆的关系;假如中国官府要求他离开中国,我们决不包庇,并支持这样行动。Select Committee to the Court of Directors.Secret Letter.3 Dec.1815.L.M.S.MSS, E.I.C.Transcript.细读了他们的陈述后,董事会同意特选委员会的请示并准许了他们的行为。①Court of Directors to Canton, 10 July 1810, Ibid..
当时,这些通信让人更加意识到马礼逊任汉语教师的重要性。1810年夏学汉语的三个人,是有了特选委员会大班剌佛的推荐才开始的,他们完全是自愿的。夏季休假的几个月,澳门的气候根本不适合学习。天气凉爽一些的时候,商馆在广州公司的业务占用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1813年底,马礼逊认为这样的汉语学习收效甚微,于是他制订了以下详细计划。“给汉语学生设立一个独立的部门。选拔两人并免于工作任务……这两位学生中水平较高的那个需要充当译员助理,并开始熟悉官府书信中常见的文体和措辞。”必须稳定地雇佣母语教师,但是鉴于他们出入商馆不甚安全,他们应该和学生同住并得到合理的报酬。当年特选委员会的委员有:益花臣、帕特尔和小斯当东,他们都支持马礼逊这一计划并向董事会提议。董事会批准了这一申请,并同意支付中国教师300或400中国银元的薪水,此外,“对于立志掌握汉语的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只要事务允许,可以免除工作专心学习。”②Morse, Chronicles, III, p.205, pp.209-210; Morrison to the Select Committee, Secret Consultations, 15 Mar., 1814; Select Committee to the Court of Directors.Secret Letter, 18 Jan., 1815.关于马礼逊向董事会开设汉语班的建议,特选委员会对此很感兴趣,他们说明了学习语言环境的新变化,并分析了这些新变化背后的原因。近年来,汉语老师不像以前那么难找了。一方面,相关人士想尽办法阻止当地教师帮助我们学习汉语,我们无法完全摆脱那些昔日为行商头目的商人。他们似乎有一套带有妒意的针对外国人的侵犯的规章制度,商人们使尽浑身解数想让我们明白朝廷官员的权力是不可逾越的。另一方面,由于害怕有人向官差告密,没有中国人甘愿冒险来我们的广州商馆教外国人汉语。在近年来所发生的更严重的事件中,不管是涉及一个中国人被英国人杀害一事,还是1818年占据澳门时,商人们已经认识到,我们与朝廷官员的直接沟通可以让他们避免很多麻烦和责任。关于这一点,有必要提及做多年行商头目、脾性自由的卢茂官(Mowqua),但或许是因为大权在握才导致如此多行商都依赖他行事。基于近年来的这种状况,找人来商馆教汉语要相对容易一些,广州的几位先生已经找到了汉语教师,但是他们的汉语学习经常因工作事务而中断。本地教师进入商馆仍然冒着一定风险,若是被官兵们抓到,会被盘问来访欧洲人的动机。本地教师似乎只有住在商馆内才免受这等风险,因为我们仍然保持和高级官员们的约法,即便是受到商人的唆使,他们的下级也不会把矛头指向我们。Canton Secret Consultation, 15 Mar., 1814., L.M.S.MSS, E.I.C.Transcript.虽然东印度公司即便是特选委员会都没有全盘接受马礼逊的整套方案—没有给他派译员助理,但至少他的教学计划得以实施了。③1822年特选委员会主席咸臣 ( J.B.Urmston)为广州商馆的汉语学习制订的计划包含了此计划的重要特点。此时,特选委员会面临马礼逊暂时缺席、缺乏汉语人才带来的问题。咸臣1822年计划书与马礼逊1814年计划书的措辞非常相似。Canton Secret Consultations, 18 Mar.1822, Ibid..
同时,董事会还批准给汉语学生每人每年100英镑的补助。董事会还承诺,如若学生语言能力足以胜任翻译的工作,除正常薪水之外,将有额外的奖金,如果是书记员,那么就会有300英镑,大班则是500英镑,但是“如果在其他大班和书记员中有人同样可以胜任特选委员会委员”的情况下,汉语学生一旦荣升特选委员会委员,意味着放弃这部分收入。这些汉语学生只有熟练掌握汉语,并定期把自己翻译汉语的作品寄到伦敦,才可以得到这份特别的补助。①Court of Directors to Canton, 5 Apr.1816, paragraph 3, 5, 8, 7, 8, 9.Ibid.. 后来的文件中包含董事会的若干条说明:只有定期提交译作以证明他们汉语水平和热情的学生才可以获得此津贴。See for example Court of Directors to Canton.Separate Letter, 13 Apr.1831, paragraph 39, 40, Ibid..至此,用于汉语学习的时间和资金都到位了。
先后于1812年和1813年抵达广州的三位初级书记员:班纳曼(James Bannerman)、马治平(Charles Marjoribanks)和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②德庇时,东印度公司官员之子,在广州商馆脱颖而出。他是最后一届特选委员会主席,1834年和律劳卑(Napier)一同被任命为驻华商务总监。任香港总督期间(1844—1848)创建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此分会在他离任后解体。1848年离任后定居英国的他对中国和中文的兴趣有增无减,出版若干关于中国的专著,在牛津大学设立汉语奖学金并于1876年成为法学博士。D.N.B.Supplement, II, p.118.,以及于1814年抵达的丹尼尔(James F.N.Daniel),都决定学习汉语试试运气。德庇时很快脱颖而出,随后便被免除工作专心学习中文。至1814年11月,可以和小斯当东很好地进行汉语对话了,并干劲十足地继续学习,“他的上进心着实令人佩服”。当年12月,德庇时着手翻译第一份官方文书,1815年1月,他交上了他翻译的《三与楼》(San-Yu-Low,或The Three Dedicated Chambers),2月,他已经把一部中国剧本译成英文。③Morse, Chronicles, III, 191, 209, 251; Canton Separate Proceedings, 12 Nov.1814; Select Committee to the Court of Directors,16 Jan., 23 Feb., 1816.L.M.S.MSS, E.I.C.Transcript. 这一时期马礼逊和他的汉语学生的优秀作品如下:Horae sinicae,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by Robert Morrison (London, 1812); 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 Notes.Canton, China.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at 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By P.P.Thorns 1815; San-Yu-Low: or the Three Dedicated Rooms. A Tale,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J.F.Davis, Esq., of the Honourable Company's China Establishment.Canton, China.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at 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P.P.Thorns.1815.1817年,德庇时、伯赞克特和图恩被认为有资格获得译员补助金,在这三位获得补助的汉语学生中,其中有一位是于1810年夏参加马礼逊第一期汉语学习班的。1816年,图恩和德庇时作为低级译员参加了阿美士德(Amherst)使华团,在他们离开广州商馆期间,伯赞克特成为了商馆的正式译员,“虽然他还没有他们那么优秀”。④Morse, Chronicles, III, p.307; Canton Consolations, 15 Jan., 1817; Select Committee to the Court of Directors, 19 Jan., 1817.L.M.S.MSS, E.I.C.Transcript.
六、广州商馆汉语学习班的最后几年
无论阿美士德使华团所取得的成效多么不尽如人意,都不能归罪于缺少专业的译员。有位居使团第三号人物的小斯当东,马礼逊以广州商馆正式译员身份加入使团,且有图恩和德庇时做助理译员,皮尔逊为口译译员兼外科医生。1816年春,广州商馆筹划英国使团计划之时,曼宁立即从印度赶回期望能为使团尽一己之力,为了能够加入使团,他甚至愿意放弃他钟爱的长胡子和飘逸的长袍,因为阿美士德勋爵并不赞同他的装扮。报酬方面:曼宁2000银元,图恩、德庇时、皮尔逊和马礼逊各1000银元。⑤Morse, Chronicles, III, p.259; G.T.Staunton, Miscellaneous Notices, 409; G.T.Staunton, Notes o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Embassy in 1816 (London, 1824), 8-9; Select Committee to the Court of Directors, 19 Jan., 1817.L.M.S.MSS, E.I.C.Transcript.“有幸见到景仰已久的曼宁先生。他蓄有一把长胡子,俨然一名中国人。”William Milne to the L.M.S., 16 Jun., 1813.L.M.S.MSS, China (1805—1820).仅就语言沟通能力而言,身为两次使团成员的小斯当东比谁都清楚,阿美士德访华使团的语言优势比1792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不可同日而语。⑥G.T.Staunton, Notes on the British Embassy in 1818, p.206; Court of Directors to Canton.Secret Letter, 12 Mar., 1817,paragraph 7, 8.L.M.S.MSS, E.I.C.Transcript.
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目的之一与语言有直接关系。1814年,在广州的英国人发现由于与美国的战争,在华英国人的处境日趋艰难,其中最急迫的是他们失去了跟随中国教师学习汉语后、商馆自己翻译并用中文呈交文书的特权。这时的两广总督坚持不再接受广州商馆的中文文书,按照惯例,商馆如有所请,往来书信用英语书写、由行商译成汉语呈交。①Davis, The Chinese, I, p.73; Auber, China, 248; Morse, Chronicles, III, p.219; Select Committee to the Court of Directors, 1 Oct.,1814.L.M.S.MSS, E.I.C.Transcript.小斯当东于1814年开始与总督谈判,争取到多项特权:其中一项特权是允许英国人用中文给朝廷高官写文书,但是,如告知英国大使访华时须附英语原本。②Morse, Chronicles, Ⅲ, p.222, Corrected Report of Speeches of Sir George Staunton (London, 1833), p.88.A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text is in J.R.Morrison,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48 ff.小斯当东在与中国官府的谈判中得罪了广州当局,因此他在中国朝廷中变得声名狼藉。他曾多次被指控,甚至面临被驱逐的威胁。广州商馆的事情迫使他们积极促成第二个访华使团出使北京。③Morse, Chronicles, Ⅲ, p.222; R.Morrison to the L.M.S., 2 Mar., 1815.L.M.S.MSS, China (1806—1820); Henry Ellis,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2 vo1s.(London, 1818), I, pp.63-81.其中一个目的便是“寻求英国广州商馆和北京衙门或北京管理机构之间有通畅的沟通渠道,无论是由在华英国人口头交流,还是用汉语书面奏陈”;另外一个目的是争取用汉语书写给地方或朝廷的文书的权利。④Morse, Chronicles, Ⅲ, p.286.
就其出使的主要目的而言,此次出使可谓一事无成。但是对于阿美士德一行来说,此次出使的教育作用是一大收获。经由陆路从广州赶至京城,据小斯当东观察,一路上大家学会了很多实用的、竟然连店主都能听得懂的汉语口语。小斯当东发现,这样的学习与在广州的语言学习相比有趣得多了,在广州每天都听到“支离破碎的或洋泾浜英语……这种通用的交流工具……足以进行贸易和沟通”。⑤G.T.Staunton, Notes on the British Embassy in 1816, 232.第二次访使华团结束后,小斯当东随即返回英国,放弃了他的汉学研究。“我的汉学研究至此结束,从我回到欧洲的那一刻起……便永不再继续了。我在这个国家从未有过闲暇、途径和条件继续我对中国学问的研究。” G.T.Staunton, Memoirs, p.101.然而,他还是热情地资助汉语学习并大力向英国人介绍汉学。
使团访华结束后,广州英国人学习汉语一事被提上日程。自1818年,东印度公司就开始赞助马礼逊编纂词典的工作。1814年,印工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as)携带一台印刷机来华,随即印刷工作便开始了。就在印刷工作在澳门进行之时,商馆忽然发现因雇佣华工制作字模受到了中国当局的制止。在向两广总督申诉的同时,特选委员会也提出了学习汉语的事,总督口头答应了,之后以书面形式答复,“称从未干涉欧洲人学习汉语”,但是为外国人制作汉字字模是违背中国法律的行为。⑥Select Committee to the Court of Directors, 7 Mar., 1817, paragraph 22, 23, 24; Same to same, 26 Mar., 1817, paragraph 51.L.M.S.MSS, E.I.C.Transcript; R.Morrison to the L.M.S., 21 Mar., 1817.L.M.S.MSS, China (1805—1820); 24; Same to same, 26 Mar.,1817, paragraph 51.L.M.S.MSS, China (1805—1820); Morse, Chronicles, III, pp.178, 209, 240, 251, IV, p.98.商馆处于这种情况下,一年半后的报告中说“可喜的是,中国人不再阻止商馆聘请中国人到商馆教授汉语了。”⑦Select Committee to the Court of Directors.Secret Letter, 2 Dec., 1818, paragraph 22.L.M.S.MSS, E.I.C.Transcript.
自此以后,除非特殊情况,商馆职员定期向中国教师学习汉语,根据1814年达成的协议,商馆与朝廷的往来书信都用中文书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项协议偶然也会派上用场,在1830年大事件发生之前,商馆还算顺利。1825年,总督向行商发布命令,认可只允许英国人用汉语与朝廷书信往来。⑧Morse, Chronicles, IV, pp.112-113.1830年之后事件不断,1834年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被取消后,这些问题便遗留给英国政府。⑨J.R.Morrison,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pp.52-53; Davis, The Chinese, I, p.94; Morse, Chronicles, IV, p.321.
自阿美士德访华至商馆撤离广州,东印度公司记录有11位书记员抵达广州后便投入汉语学习。加上之前和马礼逊学习的8位,1810年至1831年间共有19位公司职员成为汉语学生。①以下是广州商馆书记员作汉语学生的名单: (1810—1830)姓名 入班时间 (大概) 待遇伯赞克特 1805图恩 1805 1817, £100部楼顿 1807米勒 1810班纳曼 1812 1817, £100马治平 1812德庇时 1813 1817, £100; 1825, $2083; 1827, $417; 1828, £100丹尼尔 1814 1830,£100史密斯 1815 1825, £100; 1826, £100; 1827, $417; 1828, £100; 1830, £100杰克逊 1815 1828, £100; 1830, £100英格利斯 1822 1825, £100霍希尔(John G.[or B.] Thornhill) 1824林赛 1824 1828, £100; 1830, £100克拉克 1825 1826, £100; 1827, $417; 1828, £100; 1830, £100文肖(Henry Thomas Ravenshaw) 1825莫里斯 1828 1830, £100坎贝尔(James William H.Campbell) 1829亚历山大(Henry Robert Alexander) 1829查尔斯(Charles Frederick Young) 1830他们的水平参差不齐。德庇时无疑是所有学生中出类拔萃的那一个,1824年至1826年在马礼逊回英国期间,德庇时代替马礼逊在商馆做译员。德庇时在英国听说马礼逊想离开广州,他意识到广州商馆将陷入困境,便主动提出要回到中国。②Morse, Chronicles, IV, p.110; Court of Directors to Canton, 2 Apr., 1823, paragraph 22.L.M.S.MSS, E.LC.Transcript; R.Morrison to Hankey and Burder, l0 Nov., 1823.L.M.S.MSS, Morrison Paperns. 德庇时入职年薪为500英镑。1822年马礼逊如是记载:“负责这里事务的公司职员们越来越认识到懂汉语的重要性:我们被切断了所有与中国助手的联系;若不具备英汉互译的能力,我们在与行商们的语言沟通中很可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行商们是与政府打交道的中介,他们翻译时常胡说八道毫无顾忌。商馆里懂汉语的职员都不在,在这个时候,我若是就这么丢下商馆不管也太不厚道了。”(R.Morrison to Hankey, 15 Feb.1822, Ibid..) 在任的特选委员会主席咸臣,警醒大家因马礼逊不在所导致的事态的严重性。他指出没能给马礼逊配助手、让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汉语学习中是不明智的,还说“如果汉语人才对于商馆至关重要,那么仅仅是出于爱好、新鲜或是业余休闲来学习汉语,是不可能满足公司对汉语人才的需要的。” (Canton Secret Consultations, 18 Mar., 1822.L.M.S.MSS, E.I.C.Transcript.)除了德庇时外,图恩和班纳曼以及其他七位学生曾经荣获100英镑的学生补助。他们是:丹尼尔、史密斯(T.C.Smith)、杰克逊(John Jackson)、英格利斯(R.H.Inglis)、林赛(H.H.Lindsay,又化名“胡夏米”)、克拉克(H.M.Clarke)和莫里斯(F.J.Morris)。③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广州商馆被取缔之后在中国逗留一段时间。克拉克是留守广州处理公司事物的两名职员之一,他直到1839年才离开中国。 亨特(Hunter):《广州番鬼录》(The Fan Kwei at Canton),第32页。他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6卷,第486页上发表一篇关于英国和尼泊尔战争的文章。林赛加入了1832年马治平派遣的考察活动,著有: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in the Ship "Lord Amherst"(London,1833),Letter to the Right Honorable Viscount Palmerston o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3rd ed., London, 1838)。1837年以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委员身份留在中国。《中国丛报》,第5卷, 第507页。英格利斯是这一学会的第一任财务主管,同时也是《中国丛报》第4卷和第5卷的忠实赞助者。公司档案有商馆最后几年对这些汉语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1827年,史密斯为特选委员会立下汗马功劳。马礼逊对他评价甚高,表扬他“中国文学造诣颇高”而且是“最可靠并最有价值的一类”。④Court of Directors to Canton, Secret Letter, 10 Apr., 1827; Select Committee to the Court of Directors.Separate Letter, 28 Dec.,1830, paragraph 65.L.M.S.MSS, E.I.C.Transcript.至于克拉克、杰克逊和林赛,特选委员会在1830年的报告中指出:“他们的中文流利,翻译精准”。①Ibid., paragraph 64.克拉克还曾学习广东方言,马礼逊评价他“方言学习取得相当大的进步”。②Select Committee to the Court of Directors, Secret Letter, 18 Nov., 1828, paragraph 49, 126.Ibid..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第三部分完成于这一时期,这一工作吸引了这些年轻的书记员们。R.Morrison to Fisher, 23 Feb., 1829.L.M.S.MSS, Correspondence with Fisher.委员会对林赛很是赏识,1831年委员会认为,如果需要,林赛完全可以胜任译员一职。③Select Committee to the Court of Directors, 15 Nov., 1831, paragraph 75. L.M.S.MSS, E.I.C.Transcript; J.B.Urmston,Observations on the China Trade (London, 1833), p.97.克拉克被认为是马礼逊最有可能的接班人。④R.Morrison to Fisher, 23 Oct., 1833.L.M.S.MSS, Correspondence with Fisher.
1826年,马礼逊在英国休假两年后重返中国,随后的五年是商馆汉语学习的黄金时期。马礼逊早期的几个汉语学生都先后从书记员荣升为大班,从大班跻身特选委员会委员,他们毫无例外都得益于汉语学习,虽然他们的学习热情因人而异。1810年至1820年间,图恩、部楼顿、米勒、马治平、班纳曼、丹尼尔、德庇时、史密斯和近年来身居特选委员会的杰克逊,都先后出现在马礼逊语言班的名单上。因此,这段时期能够始终保持两名书记员参加汉语学习也不足为奇。1828—1829年,部楼顿任特选委员会主席的这两年,分别有五位、六位汉语学生拿到补助金,这段时间的汉语学习达到了顶峰。⑤Morse, Chronicles, IV, p.165; Court of Directors to Canton.Separate Letter, 31 Mar., 1830, paragraph 108.L.M.S.MSS, E.I.C.Transcript. 1829年的五个人是:德庇时、史密斯、杰克逊 (大班)、林赛、克拉克 (书记员)。德庇时次年不在中国,随后由丹尼尔和莫里斯替补上。当时的情况从马治平身上可见一斑,出于对马礼逊的赞赏,他不仅支持马礼逊在商馆教授汉语,而且还积极支持这位长者的每项工作。
马治平任特选委员会主席期间,特选委员会起草“有关增加投入以鼓励更多商馆职员学习汉语……的提议”,据说,“此事日渐被重视起来,鉴于之前会汉语的职员在贸易沟通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而新的行商几乎不具备良好的英文,此事被提上议程”(商馆培养的汉语译员明显扭转了上个世纪商馆的困境)。特选委员会建议增加汉语学生的补助金,还建议启用一个全新的、引人注目的项目,那便是在英国建立一个东印度公司的汉语学校,广州商馆可以从学校招募雇员,这和巴罗(John Barrow, 1764—1848)早在1804年提出的计划如出一辙。但是这两条请求均未被采纳。⑥Select Committee to the Count of Directors.Separate Letter, 30 Mar.1830, paragraph 168, 169, 170; Court of Directors to Canton, 13 Apr., 1831, paragraph 37, Ibid..
对东印度公司垄断地位的不确定性影响了这一项目的申请,不管董事会如何裁决,不管东印度公司将来何去何从,广州的职员已经认定了学习汉语的重要性。⑦“贸易季结束后,委员会主席对初级书记员学习汉语一事给予特别指示,告知他们根据当时的指示,学习汉语将是今后他们工作中必要和基本的组成部分。” Select Committee to the Count of Directors.Separate Letter, 28 Dec., 1830, paragraph 64, 65, Ibid..现在有德庇时、丹尼尔和史密斯支持马治平,马治平本人对汉语学习的一贯立场和商馆同僚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对汉语学习价值的认可,使1830年的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并且估做出决定:每一位初级书记员一到广州就应该立即开始汉语学习。假如董事会能在英国开设汉语学校抑或更早看到汉语学习的益处,情况将更为乐观,但这一请求未被批准,身在广州的汉学家们已经准备好补救措施了。为了让更多雇员学习汉语,他们搬出了英国印度事务部的条例,让董事会决定汉语水平是否应作为晋升特选委员会的标准之一。⑧Select Committee to the Count of Directors, 15 Nov., 1831, paragraph 74, 77, Ibid..根据这一决定,1829年和1830年新来的三名雇员立即投身汉语学习之中,董事会看到雇员中有9人在汉语学习名单之上,不得不建议不能因为学习汉语而耽误日常工作,多数人应该在“工作之余”学习汉语。①Same to same, 28 Jan., 1832, paragraph 30 contains a copy of the official order of Charles Marjoribanks, Presiden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Messrs.Ravenshaw, Campbell, Alexander and Young; Same to same, 10 April 1832, paragraph 60, Ibid..
1831年之后广州商馆的前途未卜和混乱局面以及1834年广州商馆的被取缔,结束了这些值得赞许的努力。马礼逊目睹东印度公司最后一名职员离开中国,对自己未卜前途的担忧远不如对解散汉语班的惋惜之情来得深刻。律劳卑勋爵到任后,委任他为英国政府译员,担任此职仅仅几周的时间,夏末,马礼逊去世了。②“我是位不同寻常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年薪1300英镑,没有其他任何津贴用于雇佣人、付房租或是其他事情。但是,我会穿上缀有英国皇家领扣的副领事服!”Morrison, Memoirs, II, p.523.接替他职位的不是他在东印度公司培养的汉语学生,而是他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③马儒翰,自幼跟随父亲学习汉语并在马六甲(Malacca)进修。1830年在广州担任英商翻译,年薪1200中国银元。英国割占香港,他是理事会的委员之一,直至离世,他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逝世是英国的一大损失。D.N.B., XXXIX,p.111.,马儒翰生于澳门,自幼对汉语耳濡目染。
显然,汉语学习对于东印度公司来说举足轻重,忽视汉语在一定程度上对广州商馆不利。自18世纪下半叶后期开始,他们尝试维持培养英国译员的策略,并雇佣这些英国人在广州商馆工作,然而却受到中国人的猜忌和帝国傲慢的阻碍。担任广州商馆翻译工作的第一个英国汉学家当属小斯当东,他临危受命,挽救公司于危难之中,也为马礼逊铺平了通往商馆之路,而马礼逊以独特的身份兼学者、汉语教师和译员为一身在广州商馆服务长达25年。自1808年开始,剌佛就将马礼逊置于东印度公司的护翼之下,到广州商馆被取缔之前,马治平和德庇时都最大程度支持汉语学习,每届特选委员会的目的都非常明确并不断加强,虽然常常与董事会狭隘的观点产生分歧,最终还是会在商榷后如愿以偿。随着广州商馆被撤销和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贸易的终结,事实上也摧毁了大英帝国最早关于汉语研究学校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