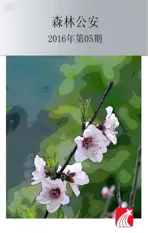破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对象之探究
2016-02-01薛培王军
薛培 王军
破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对象之探究
薛培王军
2002年《刑法修正案(四)》对1997年《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进行了修改,将“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修改为“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并增加了“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扩大了刑法保护范围,加大了刑法打击力度,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对象确定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及其制品。
然而,自刑法修订以来,有关破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的执法、司法实践与立法本意相去甚远,效果尚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并非破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数量不多,而是现有的法律规定对破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对象界定不明,给执法、司法带来了困难。对此,笔者拟对破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对象的认定进行探讨,包括对现有法律规定、司法实践进行梳理和分析,结合对野生植物的认定进行理论和实践的研究,针对法律规定、司法实践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困难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现有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一)法律规定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为“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2月11日)第一条规定: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珍贵树木”,包括由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树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2008年6月25日)第七十条“本条和本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的‘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包括由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树木或者其他植物”。根据以上司法解释可见,“珍贵树木”包含3类:1.由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2.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其内又包含:(1)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2)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所限制出口的野生植物,目前我国参加的限制进出口野生植物的国际公约有《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该公约附录一、二所列对象为本罪对象;(3)未定名或者新发现并有重要价值的野生植物;3.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树木。相应的,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为3类中除珍贵树木以外的所列物种,即国家重点保护的草本、菌类等植物。以下将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对应简称为一类、二类、三类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二)司法实践认定
根据上述规定,对于一类、二类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而言,只要符合规定,无论是人工种植还是野生植物,均是刑法所保护的对象,实施破坏行为即涉嫌构成犯罪。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经有关部门确认的古树名木数量相对有限,而目前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保护植物名录也未正式公布,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第三类保护植物就成了执法的主要对象。这不仅是因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所列物种是我国迄今为止集大成的,最具权威性的植物保护名录,更是由于根据名录按图索骥,执行起来方便明确。第三类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因为在现实中最为多见且争议最大,由此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这也是笔者试图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二、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认定存在的认识分歧及执法困境
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植物,目前已公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虽然扩大了保护范围,但是在执法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及困难。
(一)关于第三类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认定问题
1.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是否必须为野生植物。关于第三类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是否必须为野生植物,理论和司法实践都极不统一。理论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司法解释规定了第三类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是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植物,自然必须为野生植物,即只有既满足物种是名录所列物种,又满足野生植物的条件,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受刑法保护;虽列入名录中,但并非野生植物而为人工种植的,不在刑法保护范围之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第三类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是指列入名录中的植物,而不论是否为野生植物皆可成为刑法所保护的对象。其理由是:一是从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来理解,国家保护植物是保护物种不灭亡,主要通过保护物种的数量来实现。当前,国家鼓励人工培养和种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主要是鼓励其行为的公益性,对于该行为的商业性尚属空白项。在国家没有出台关于人工培养和种植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如何进行商业利用的管理规定之前,人工培养和种植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及其制品应该纳入本罪的犯罪对象。二是《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是一部确定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权责的行政法规,其保护范围限制为原生地天然生长的野生植物是理所当然的,但该条例对于植物制品尚无违法性限制。如果用这样一部行政法规来限定基本法律《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的犯罪对象,是不符合法理的。法定罪不是行政违法的升级,不能将行政违法作为犯罪的必然要件。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保护范围早已突破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范围,并且无论是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原生地天然生长”的限制。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完全可以理解为对物种的不区分生长来源的保护。
相应地,各地司法实践也都体现了理论存在的这两种观点的差异,有些地方,如云南、贵州等地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来源并不加以区分,只要是列入名录中的植物,均为刑法保护之对象,对相应的犯罪均加以打击。而有些地方,如福建,则持谨慎态度,该省高级人民法院林业审判庭、省人民检察院林业检察处、省森林公安局《全省法院林业审判工作会议综述》(2001年6月18日)中明确: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关问题:1.第一条中明确了“珍贵树木”的范围。野生植物中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为珍贵树木。人工种植的树木凡符合该条规定“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即可视为珍贵树木。该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龙岩市人民检察院《龙岩市林业刑事案件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2004年4月23日)也明确:一、会议对下列问题达成了共识:13、人工栽培、种植的植物是不是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犯罪对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36号《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侵犯对象已作了明确规定,一是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野生植物;二是符合该条规定“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人工种植的树木。因此,只有符合上述第二点规定的人工种植的植物,才能成为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犯罪对象。可见,福建省不仅严格限制对于属于名录中的植物还需要确认是否属于野生植物,而且对于虽经鉴定或经验判断应属于野生植物而当事人提出有过人工培育行为的,采取疑罪从无的做法,不予认定为野生植物,将其排除在犯罪对象范围之外。
2.野生植物的定义尚不明确。我们暂且将第三类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是否需要限定为野生植物的问题搁置,假设需要野生植物这一限定,而关于野生植物的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也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理论上,野生动植物是指那些生存在天然自由状态下,或者来源于天然自由状态下,虽经多代人工驯养或者培植但尚未产生明显进化变异的各种植物。通俗地讲,野生动植物包括家畜、家禽、家鱼、家养宠物、农作物、蔬菜、瓜果、栽培花卉等以外的所有动植物。”这种定义貌似严谨,却仍无法很好地划清野生与非野生的界线。有学者提出,野生植物的定义应当从区分基本概念出发,《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应属权威性较高的文件,公约中,就将人工培植定义为“由种子、插条、分株、愈伤组织或其他植物组织、孢子等在控制条件下生长的活体植株,控制环境条件的形式包括耕作、施肥、除草、灌溉或诸如盆植、整床等苗圃作业或防备恶劣气候的方式”,包括了大多数人工措施。而不符合上述关于人工栽培定义的植物即被视作野生来源的植物。即野生植物包含了人工培育的野生植物及野生来源的野生植物。
而中国目前较为权威的定义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条例所保护的野生植物,是指原生地天然生长的珍贵植物和原生地天然生长并具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文化价值的濒危、稀有植物。”即野生植物应当是“原生地天然生长”。而对于“原生地”“天然生长”的概念,尚无具体的规定。对于“原生地”的理解,目前较为科学统一的认识是,“原生地植物”与“外来物种、外侵物种”相对应区分,可见,被移植植物只要没有跨出该物种的原生区域,仍然具备“原生地”条件。对于“天然生长”,有人理解为是排除了人工干预的纯天然的生长。笔者不同意该观点,“天然生长”是一个相对概念,应理解为人的活动,包括对植物的轻微干预,只要不足以改变某植物的原始种质属性,仍视其为“天然生长”,而不是指无人工痕迹的自生自灭状态。因为植物很少有绝对纯天然生长,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总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植物的生长。因此,如果对某野生植物实施了病虫害防治、保护性培育或抢救性移植等行为,并不意味着改变了植物的野生属性,只要没有实施足以改变其某种质属性的行为,如嫁接等,仍然认为其是天然生长。问题关键是对于“人工干预的程度”以及“是否改变物种的野生属性”,仍需进一步统一认识。
(二)基于不同认识产生的执法窘境
上述分歧之所以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是因为无论基于上述何种认识,在执法、司法实践中都存在问题,法律的实施陷入困境,法律效果难以有效发挥,保护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目的难以实现。
1.若无须限定野生植物,则打击范围过宽。认为对于第三类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无须限定野生植物,只要是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植物,均应受到刑法保护。根据这一观点,对于执法、司法来说,当然是简单易行了,但是无形中扩大了打击范围。国家鼓励人工培养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就是希望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扩大保护物种的数量,避免物种濒危、灭绝。而如果对保护物种无论来源一律予以打击,无形中影响了该政策的推行。虽说国家鼓励人工培养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主要是鼓励其行为的公益性,但是对于培育者来说,在培育过程中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如果抑制其商业行为,无疑抑制了人工培植行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与保护珍贵、濒危物种的目的背道而驰。
2.若限定野生植物条件,根据不同理解会产生差异。一是基于国际公约的理解,打击范围过宽。根据上述《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定义,野生植物包含了人工培育的野生植物及野生来源的野生植物,非野生植物是除此以外的其他植物。问题是,如何区分人工培育、野生来源,又如何区分培育的方式是极其困难的。根据植物人工培育的情况看,由于人工培育历史短,技术也不纯熟,符合国际公约人工培育的定义的少。因此,上百年的古树,基本上都属于野生植物的范畴,应当予以刑法保护。且虽经培育的珍贵树木、植物,除非符合公约中人工培育的定义的植物,即利用种子、插条、分株、愈伤组织或其他植物组织、孢子等在控制条件下长成,也应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应给予刑法保护。也就是说,查处到涉嫌的植物及制品,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这也是有些地方不对野生属性加以鉴定辨别的依据。但此种情况带来的问题就是打击范围过大,导致的结果是,人工养护行为或追求商业利益的种养行为也可能涉嫌犯罪,在另一个角度上看,抑制了保护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活动。二是根据《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理解,打击面过窄。目前,基于《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对野生植物的理解,关键在于对原生地天然生长的认定。而关于原生地天然生长的鉴定一般采用两种做法,一是鉴定人员根据植物的生长环境、林相分布来认定。对于此种方法,主要针对生长于相对野外的环境,如山林中人迹罕至而植物已形成天然群落分布的植物,鉴定的结果具有较高的确信力。而对于诸如门前屋后,河边村前的生长较为单一的植物来说,有些尽管年代久远,鉴定人员难以得出“原生地天然生长”的鉴定意见。办案执法人员只能采取对知情人员进行走访调查,间接印证是否属于天然生长,主观随意性较大,此种结果是办案人员自己就存在内心不确信。一旦当事人辩称系其家族成员播种或有对其进行管理培育,办案执法人员就显得底气不足。并且,对于植物活体或死体而言,这种鉴定方法还有一定可行的空间,但对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来说,上述鉴定方法就失去了其效用。对于植物制品而言,其生长属性属于不可鉴定因素。特别是来源不明的制品,一旦嫌疑人主张该制品是人工种植植物加工而成,本着控方举证的原则,执法办案人员就要一筹莫展了。即,此种做法实际上将所有来源不明的植物制品排除在保护范围内,不能有效打击犯罪,法律因此变成了一纸空文。
三、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建议及对策
(一)从法律上明确对象范围
对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对象,无论在理论上争议有多大,对于法律而言,特别是作为惩治手段最严厉的刑法,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不可不明,过宽就放纵了犯罪,损害了司法权威;过严则有可能损害当事人的权益。因此,笔者认为,迫切需要从法律上明确刑法保护对象。即需要在法律层面上对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犯罪对象进行严格限定,通过配套的司法解释,阐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对象是否限定为野生植物,何为野生植物,对于常见的人工养护行为应当如何认定,以及对于涉及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应当如何认定等问题。
关于第三类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笔者认为,应当限定为野生植物。理由是,为保护珍贵、濒危植物,我们应当鼓励对珍贵植物的人工保护,以确保物种数量,起到防止物种濒危、灭绝的危险。但对于野生植物的理解,应当依照国际公约关于野生植物的理解。即,并非经人工干预的种植行为都认定为人工培育。一般说来,通过播种、插条、分株等方式培植后,还需要人工控制其生长环境,即有较大的人工干预程度。对于房前屋后的树木,人工干预其生长程度较大,可以将此类植物排除在保护范围。而对于成长于村落外围的植物,典型如村口树,由于其生长环境为非人工控制环境,因此虽与人类活动联系较为密切,仍应列入刑法保护的范围。但对于从野外移植到自家庭院种植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由于先前移植行为本身属于破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行为,具有可罚性,并且移植行为并不能改变该植株的野生特性,因此应当列入刑法保护范围。而对于人工栽培的植物来说,符合人工培育条件的植物应当排除在刑法保护范围之外。
(二)从行政上加强保护管理
虽然我们希望法律规定越明确细致越好,但是作为基本法,刑法规定应当相对稳定,这就决定了刑法无法将所有的情况一一罗列,这就难免产生疏漏。因此需要辅之行政手段加强保护管理,才能应对多变的实践变化。
根据现有的司法解释,对于古树名木及国家禁止、限制进出口的植物来说,无论是人工的、还是野生的,均属于刑法保护对象。目前的问题是,经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确定的古树名木数量极其有限,而报批程序又极其烦琐,导致许多可以列为古树名木进行保护的植物没有及时被列入,得不到有效保护。笔者建议,有必要扩大对古树名木的保护。各地定期对需要列入古树名木的植物进行报批,或者改变报批方式、简化报批程序,即有关部门公布古树名木的报批条件,凡是符合条件的树木可申报为古树名木。虽然司法解释规定只有省级以上有关部门确定的古树名木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但地方部门可以对地方保护的重点植物完善保护措施。例如,地方部门对地方确定的古树名木进行挂牌管理,从很大程度上能对破坏古树名木的不法分子起到震慑作用。对于国家禁止、限制进出口的植物也应当进一步明确,如定期公布国家禁止、限制进出口植物名录,方便行政执法,使此类植物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此外,对于人工培养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行为,相关部门应当出台管理规定加强管理,防止不法分子利用人工培养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政策行破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之举。
(三)从司法上调整举证责任
刑事案件中一般遵循控方举证原则,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原则。有学者提出,本着证明责任平等、均衡的原则,对于破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而言,法律没有明确要求证明对象是否野生,控方可以不承担该项证明责任。被告如果提出对象不是野生的而且可以成为非罪的理由,那么,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就应该由被告自己承担证明责任。非法采伐、毁坏人工培育的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不构成本罪,其举证责任应是行为人自己。行为人不能证明采伐、毁坏的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是人工培育的,则可视为是天然的。对于从司法上适当调整举证责任的主张,笔者同意这一观点,但认为举证的理由和依据还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无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是否限定为野生植物,对于野生属性的认定其实无须过多证明。理由是,野生植物分为野生来源的野生植物和人工培育的野生植物,要改变植物的野生属性,需要人工干预达到改变其质属性的程度,如嫁接出新品种,种植后其花、枝、叶发生变化等。要有这些变化是需要经过至少一代以上培育。也就是说需要时间、技术的投入。目前而言,人工培育植物历史短暂,技术也不够纯熟,尚未明显改变植物的质属性。因此,从本质上可以说,我们所查到的所有的植物及其制品基本上仍属于野生植物。当然,本着宽严相济原则,同时考虑国家对人工培育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鼓励政策,对于有证据能够证明人工来源或合法人工干预的情况,可不视为犯罪。综上所述,对于野生属性而言,依照常识、科学知识判断,是人人皆知的内容,一般情况下无须再举证。而当事人提出的非罪理由并非是植物的非野生属性,而是在法律人情之内的非罪理由,如人工干预较大,人工培植具有合法性等。这样,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当事人进行举证。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植物活体或死体而言,若能查清来源的,甚至能查明群落分布的,当然认定为野生植物,当事人也无抗辩的余地。对于未形成群落、甚至无法查明来源的,若是年代久远的植物,应当认定为野生植物。如果当事人提出异议的,理应由当事人举证,或证明人工干预的程度,或证明其人工培植的合法性等,理由成立的,可不认定为犯罪。根据这一思路,对于查处的植物制品而言,即使无法查清来源,根据判断植物的年龄,也能够认定其野生属性。对于当事人提出异议的,同样需要当事人举证,理由不成立的,应当认定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
(作者单位薛培/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一处王军/四川省成都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森林公安局)
(责任编辑刘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