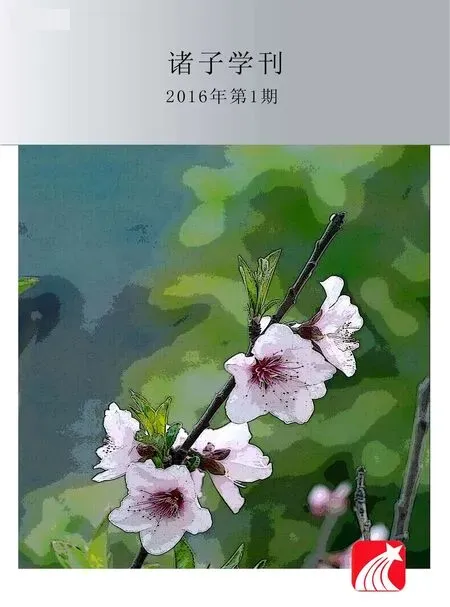關於“新子學”構建的芹獻芻議
——《〈莊子〉結構藝術研究》讀後漫筆
2016-02-01李炳海
李炳海
關於“新子學”構建的芹獻芻議
——《〈莊子〉結構藝術研究》讀後漫筆
李炳海
建立“新子學”體系,需要走出疑古思潮的陰影,細緻整理傳世諸子著作,重新發掘它們的當代價值。“新子學”研究要有開放的國際視野和圓融的思想境界,對西學重視的理念,要善於挖掘其在傳統國學中的發展流脈。“結構”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重要範疇,也是西方結構主義的重要概念,釐清二者的差異,並將結構分析法運用於諸子文章的研究中,是“新子學”創立期的有益嘗試。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要完成現代轉换和與西方文藝思想的對接,也要從如何認識早期文獻的文本入手。《莊子結構藝術研究》一書作為“新子學”的成果,通過分析文本的結構特征,不僅深入揭示了《莊子》文章的内涵,也發掘出結構本身所藴含的哲學和美學理念,可以推動諸子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關鍵詞 新子學 文本結構 文獻整理 現代視角
中圖分類號 B2
由方勇教授主編的《諸子研究叢書》,是他主持的《子藏》工程的一部分,已經陸續推出一系列諸子學研究著作。最近,由賈學鴻著、學苑出版社出版的《〈莊子〉結構藝術研究》一書,稱得上是迄今研究《莊子》結構最系統、最全面的著作,同時也提出了許多與“新子學”的構建密切相關的學術議題。
一
由“結構”一詞,人們很容易聯想到西方的結構主義以及現代和後現代派的建構和解構之争,似乎這是借鑒西方理論而確定的選題。其實,對作品結構的關注,是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傳統,並且歷史悠久,淵源極深。只是由於科舉取士制度的廢止和八股文的衰落,遂使對文學作品結構的研究在相當長一段時期處於冷清狀態,以至於今天一提起結構研究,仿佛是在推銷舶來品。類似情況在學術研究的其他領域也經常可以見到。例如,青年男女交往以鮮花相贈,《詩經·鄭風·溱洧》就有“贈之以芍藥”之語,毛傳曰:“士與女往觀,因相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别,則送女以芍藥,結恩情也。”*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72~373頁。這是青年男女以鮮花相贈最有力的證明。可是,隨着時代的推移,這種風俗逐漸淡化,只在少數地區流行,很大程度上被人們遺忘。以至於到了今天,當人們的交往以鮮花相贈,再加上用於贈送的鮮花品種有的來自域外,於是,許多人便認為贈花之禮是由域外傳入的習俗,實在是一種誤解。古代文學作品結構研究在當下的處境,與贈花習俗的歷史遭遇有相似之處,也往往受到誤解。因此,有必要對結構研究加以正名,用以消除這個領域的數祖忘典現象。
結構是作品的基本組成要素,也是區别中國古代文體的重要尺度之一。散文與駢文、古詩與新體詩,它們之間最重要的區别就體現在結構方式上。正因為如此,從作品結構切入去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並且尚有廣闊的學術空間可供開拓。近些年來,文體研究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一個學術熱點,是當代學術的新進展。文體之間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作品的結構方面。文體研究離開作品結構,是不可思議的。即以先秦《楚辭》及戰國諸子為例,許多争論不休的學術公案,如果能從作品結構方面加以審視,學術難題就比較容易破解。《天問》是一篇千古奇文,作品前一部分按照問天、問地、問人的順序加以追問;而在問人段落,又按照夏、商、周的時間順序依次展開,脈絡比較清晰。可是,“天命反側,何罰何佑”至“易之以百兩,卒無禄”一段,又錯雜多個時段的歷史故實,還有與前面重復的内容。鑒於這種情況,有些學者就認為這段文字屬於錯簡,於是就進行重新編排。如果從作品結構的角度加以考量,就會發現所謂的錯簡段落,其實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板塊,是圍繞“天命反側,何罰何佑”的追問,聯綴相關的歷史事實,帶有總結前文的性質。再如《荀子·成相》,各章雜用三言、四言、七言句,各類句子的數量有着基本的遵循。可是,也有個别章出現例外,如“請成相,道聖王”章没有四言句,總句數較之絶大多數章少一句。對此,王念孫斷定“有脱文”*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462頁。,對於“願陳辭”一章,王念孫稱“脱一三字句”*同上書,第463頁。。王念孫的説法在後代得到普遍認可,近現代的《荀子》注解基本沿襲王氏的説法。可是,如果從《成相》全篇的結構板塊加以觀照,很容易就會發現,凡是句數不合常規的章,均是各板塊的首章,起着引領後文的作用。顯然,個别章的句數不足,並非是脱文造成,而是荀子有意為之,是要把各板塊的首章與後面的章節加以區别,以突出它的特殊地位。再如《荀子·賦》所載的《佹詩》,前面主體部分結束之後,緊接着是《少歌》,共計二十句。楊倞注:“此下一章,即其反辭,故謂之《少歌》,總論前意也。”*同上書,第482頁。《佹詩》前面一個板塊,結尾兩句是“與愚以疑,願聞反辭”,故楊倞把《少歌》稱為反辭,又認為《少歌》相當於楚辭的“亂曰”。楊倞的分析不無道理,他是從結構模式的角度看待《佹詩》和《少歌》。但是,由於他對《少歌》這個術語把握得不够准確,所得出的結論還須進一步加以補充修正。先秦官職中,大與小經常對舉,大指正職,少指副職。由此看來,《少歌》指的是副歌,前面的主體部分是正歌。荀子是把樂章結構納入作品,使作品的兩個板塊有正副之分。
上述案例表明,把結構分析的方法運用於諸子文章的研究,是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有時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莊子》一書歷來是學術熱點,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種研究論著接連推出,鋪天蓋地。可是,通過檢索可以發現,專門從結構切入的論著卻是數量有限,是這個領域的薄弱環節。把《莊子》結構研究定為研究題目,並最終推出這部學術含量很高的專著,不僅是《莊》學研究的創獲,而且選題本身就富有啓示意義,可以推動諸子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也可視為“新子學”創立期的一次嘗試。
方勇教授倡導“新子學”,顧名思義,它區别於傳統的子學,與舊子學有明顯不同。但是,從總體的學術格局來看,它又是當下復興國學大潮的一個組成部分。章太炎先生的《國故論衡》把國學劃分為小學、文學、諸子學三個板塊,子學在國學中居於重要地位。子學的門類歸屬,決定了它的研究對象必然要到古代去尋找,“新子學”當然也不例外。文章層次研究是被遺落和淡忘的子學課題,把它重新找回很有必要。類似情況在子學領域還有很多,“新子學”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把那些失落或被人忘卻的子學遺産重新找回,並且發掘它在當下的價值。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可用《莊子·天地》中如下寓言作比喻:
黄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侖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414頁。
黄帝在疏忽中遺失玄珠,先後派出多批使者前去尋找。在這個寓言中,黄帝發現自己遺失玄珠,並且知道遺失的場所。而在當下的中國,許多人對於子學遺産的遺失則渾然不覺;有的雖然意識到遺失,但是不知道從何處找回;還有的雖然能够指出遺失的對象,以及遺失的原因,卻没有找到它的能力和辦法。“新子學”所要擔當的重要歷史使命之一,就是重新挖掘已經失落的子學遺産,並使它進一步發揚光大。試以賈誼為例對此作簡要説明。賈誼是漢初重要的思想家,他所著的《新書》是漢代子書經典之一。他在《陳政事疏》中提出砥礪臣節的主張,希望天子尊重大臣:“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班固撰、顔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256頁。這裏提出的是尊重人格,保持人的尊嚴的問題。對於犯罪的大臣,他列舉一系列人性化的處置方式。賈誼的上述建議,體現的是人文關懷,是文明社會所需要的因素。可是,以往對賈誼的研究,或是評論他在仕途上是幸運還是懷才不遇,他的思想屬於儒家還是法家,而他的學説中最珍貴的重視人的尊嚴的主張,無論是在記憶層面還是在現實層面,很大程度上已經被遺忘,以至於今天一提到人權、人的尊嚴,仿佛是來自域外的思想庫存。這只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各個領域,子書寶貴遺産丟失的情況大量存在,通過“新子學”研究,使它重放光芒。當然,這一任務涉及繁多、具體的操作性工作,絶非易事。然而,最重要是有追尋的自覺意識,並善於發現值得追尋的對象。
二
《〈莊子〉結構藝術研究》是以傳世的《莊子》文本為依據,這必然涉及《莊子》的成書過程,會遇到有關《莊子》文章本然狀態的追問。這部著作没有回避這個問題,而是作出了積極的正面回應。這就又涉及“新子學”的一個重要問題: 對於像《莊子》這類由幾代學者陸續編撰,經歷漫長歷史時段最後寫定的諸子著作,是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原書的作者考證、文本形態演變方面,還是對這些傳世經典的價值進行發掘,兩種選擇反映不同的治學理路,也是存在争議的問題。
漢代及其以後的子學著作,其作者、文本形態的認定和先秦時期的同類著作相比,難度較小,通常可以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因為有足够的文獻作支撐。比如桓譚的《新論》,《後漢書》本傳中明確記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961頁。據此,可以把《新論》的著作權明確地認定為桓譚和班固二人,屬於班固的只有《琴道》篇,其餘則均是桓譚所作。可是,對於多數先秦諸子著作而言,其作者究竟是一人還是多人?如果是多人,每個人的具體擔當如何?這些問題基本都是學術懸案,至今真正落到實處的並不是很多。學鴻這部著作設專節論述《莊子》文本結構的形成過程及特點,反復援引前代學者章學誠《文史通義》、余嘉錫《古書通例》中的相關論述,承認《莊子》文本所經歷的歷史演變過程,以及該書出自多人之手,在此基礎上從現代接受學視角,進行文本結構研究,從而把這部書與後世出自一人之手的著作區别開來,這種做法是可取的。
《莊子》作者和篇目考證,是難以澄清的問題。造成這種情況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章學誠和余嘉錫兩位先賢都談到的,先秦時期還没有明確的著作權觀念,還處於以言為公的時代,未曾出現抄襲剽竊之類的糾紛。學人著書相互附益,在那個時代屬於正常現象;二是那個時代的許多文獻屬於公共資源,也可稱為學人進行著述的公共素材,大家都可以利用,而不存在所謂的專有權。由以上兩個方面的原因所決定,先秦諸子著作出現彼此重復、自相矛盾等現象,也就不難理解了。對於著作權觀念尚未自覺確立時期的諸子著作,要對各篇的作者逐一加以考證,這樣做本身就不合乎邏輯。對生成於文獻、素材共享時期的諸子著作,非要對作品的文獻按學派進行嚴格劃分,這種做法同樣不合情理,是違背歷史實際的。當下學界流行歷史還原之説,體現出對歷史的尊重和求實精神。但是,諸子研究的對象,有些問題可以最大限度地進行歷史還原,力求得出的結論盡量符合歷史實際。同時,有些問題無法進行歷史還原,只能作為懸案暫時擱置。
因為《莊子》的作者及篇目無法考證清楚,據此而否認對它進行結構研究的合理性,這種看法實際上是受了疑古思潮的影響。要建立“新子學”體系,一個需要認真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走出疑古思潮的陰影,對於傳世諸子著作進行整理,重新發掘它們的當代價值。疑古思潮對諸子研究所産生的負面效應,隨着出土文獻的陸續面世,已經顯露得越來越清楚。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出土之前,許多人懷疑《老子》文本的真實性,對它的文字大加改動。帛書《老子》的面世,證明此前許多懷疑屬於主觀臆測。河北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的《文子》出土前,不少人認為《文子》抄襲了《淮南子》。這批竹簡的面世,同樣使這一懷疑不攻自破。當然,也有的諸子著作目前還未能如此幸運,繼續被視為偽書。如有人提出《列子》摻入張湛的論述,致使這部書至今還遭受冷處理的待遇,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視。也許某一天地下出土張湛所處時段之前的《列子》,這部書才有正名的機會。“新子學”的建立,不能把希望過多地寄托在考古發掘,而應該重視傳世文本的整理和研究。近些年來,隨着出土文獻的陸續面世,疑古思潮又以新的形式再度湧動,那就是重出土文獻而輕傳世文獻,甚至用出土文獻否定傳世文獻的真實性,這種做法同樣毫無道理,不足為法。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可以相互印證,但是,就同一部書而言,出土文獻未必優於傳世文獻,二者之間往往是不同版本系統之間的關係,而不能簡單地以優劣論之。如果就文獻的實際效應和價值而言,有的出土文獻在地下沉睡千年以上,它對後代所産生的影響,根本無法與傳世文獻相比。出土文獻從入土之日起,它的文本樣態就已經凝固,未再發生變化。它對文獻古本原貌的考證確實有重要價值。傳世文獻往往經過多次校勘、翻印,文本形態與開始階段難免存在差異,但是,傳世文獻的流傳在文本形態上也是一個歷史的篩選過程,總的趨勢是優勝劣汰,由粗到精。由此看來,把《莊子》的傳世文本作為結構藝術研究的依據,實際是對歷史積淀的認可,是把它作為既定的歷史遺産加以繼承、開掘和利用。同樣,對於其他早期諸子著作,也不能無限度地陷入作者和篇目的考證,而要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傳世文本的整理和開發利用。即以《孟子》一書而言,趙岐《題辭解》稱:“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孫奭則寫道:
唐林慎思續《孟子》書二卷,以為《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韓愈亦云: 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没,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中華書局2008年影印《十三經注疏》本,第2661頁。
林慎思、韓愈的説法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據此去考評哪些篇目是孟子自作,哪些出自弟子之手,或者弟子所記録的篇目,萬章、公孫丑又具體有何擔當,顯然,這種考證無法得出確切的結論。反之,即使不作這種考證,只是以師徒共撰為背景,並不會妨礙對《孟子》一書的研究。事實上,從古到今對《孟子》研究所取得的有價值的成果,並不是作者、篇目的考證,而在於對傳世《孟子》一書思想及文學等方面的研究。
“新子學”體系的建立要以諸子傳世文本為基本依據,還須遵循一個原則,就是不對傳世文本輕易改動,尊重它的歷史存在。對於那些懷疑傳世文本真實性的説法,必須慎重地加以斟酌,而不能盲從。即以《淮南子》各篇的標題為例,姚范稱:
疑“訓”字高誘自名其注解,非《淮南》篇名所有,即誘《序》中所云“深思先師之訓”也,《要略》無“訓”字。*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頁。
《淮南子》共計二十一篇,除末篇《要略》外,其餘各篇題目均綴以“訓”字。姚范認為各個篇題的“訓”字是高誘後加,而不是原文所有。姚范的説法在當代得到普遍的認可,誰如果再對篇題以三個字稱之,就會被視為孤陋寡聞,受到嘲諷。從實際情況考察,姚氏的看法並非確乎不拔的定論。《淮南子》一書末篇《要略》,相當於全書的序言,為了與其他篇目相區别,故篇題不綴以“訓”字。該書其餘各篇題目,有的去掉“訓”字可以作為標題,如《原道》《俶真》等,有的去掉“訓”字就成為《天文》《地形》,可在那個時代還見不到這樣的篇題。由此看來,不能因為篇題有“訓”字,就斷定是注釋者所加。傳世的《逸周書》,各篇標題均綴以“解”字,如《度訓解》《命訓解》,但是,並没有人懷疑“解”字是作注者所加。從著述體例考察,《淮南子》前二十篇的題目,或原本就綴以“訓”字。如果《淮南子》的篇題是高誘所增益,那麽他注《吕氏春秋》也應照此辦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這個案例再次表明,對於傳世的諸子文本,不應該輕易地懷疑,更不能妄加改動。
三
近年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者提出兩個明確的口號,一是實現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二是實現與西方文藝思想的無縫對接。這兩個口號帶有理想色彩,但也是學術研究的大勢所趨。無論是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還是對西方文藝思想的借鑒,“新子學”都可以大有作為,並且是必須確定的目標,否則,“新子學”體系就無法真正建立起來。《〈莊子〉結構藝術研究》這部著作在以上兩個方面均作了有益的嘗試,並且卓有成效。
研究《莊子》是古代的顯學,尤其是宋代起步的評點派,對於研究《莊子》的結構藝術更具有借鑒價值。如何有效地繼承這筆歷史遺産,發揮它對當下研究的推動作用,《〈莊子〉結構藝術研究》採取的處理方式頗為可取。
第一是取長補短。古人從文章學角度評論《莊子》,往往是感悟式的,所用的評語富有形象性。這些評語與古代以詩論詩有異曲同工之妙,給人以美的享受。當下是散文氣息彌漫的時代,文本閲讀已經無法産生出那些詩性的評語。對《莊子》所作點評充滿詩意,成為古人所長,把這些評語移植過來,是以古人之長,補今人之短。但是,這些充滿詩意的評點,往往恍惚矇矓、撲朔迷離,顯得不够確切和嚴密。遇到這種情況,就需要用現代的理念、範疇加以界定,作出清晰的闡述,這便是以今人之長,補古人之短。因此,所謂的取長補短是雙向的,而不是單向的。《〈莊子〉結構藝術研究》一書的有些標題,明顯是取自古人的評點。如對結構藝術類型劃分所用“登峰觀頂”、“撥雲露月”、“草蛇灰線”等詞語,就是屬於這種情況。這些富有詩意的評語源自古人,同時,書中對它們又有具體的説明,實現了古代文學命題的現代轉換。
第二是精挑細選,擇取合宜。古人對《莊子》文章所作的評點,往往連續使用多個富有詩意的評語,類似於獨立的短文,讀起來令人目不暇接,乃至於眼花繚亂。明代陸西星評論《逍遥遊》,連續運用“纊中引線,草裏蛇眠,雲破月映,藕斷絲連”*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卷一,上海愛古書店1933年石印本。,共計四個形象的比喻。這段評語確實很優美,然而,它們是否完全合乎《逍遥遊》的文本實際,則另當别論。如何對古人的評語作出取舍,使得所選擇的評語與所評論的對象相契合,確實需要謹慎地斟酌,有時甚至要忍痛割愛。盡管評語詩意盎然,但是針對性不强,或是與所評論的對象存在隔膜,還是不能作為立論的依據而加以援引。學鴻在著作中,將陸氏評價《逍遥遊》篇章結構的用語“草裏蛇眠”作了改造之後,應用到《齊物論》和《天地》篇的結構分析當中,體現出甄别的細緻入微。
第三是綜合考量,評價適中。古人對《莊子》文章所作的評語,有時還出現溢美失實的情況,所作的評價過高,已經超出《莊子》文本的實際水平。這種傾向在劉鳳苞《南華雪心編》體現得尤為明顯。而當下的子學研究,也往往出現類似情況,出於對研究對象的偏愛,自覺或不自覺地對它作出過高的評價,甚至作出理想化的處理。學鴻這部著作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在“《莊子》結構研究的缺憾”一節,明確指出評點派所存在的形式化和主觀化的偏向。對於古人評語的援引,能從《莊子》文本的實際出發綜合考量,所作的評價公允適中。
實現中國古代文學和西方理論的會通,這部書也有所嘗試。主要採用了兩種方式: 一種是借鑒西方理論,用以闡釋《莊子》的結構藝術,其中反復提到英國形式主義美學家克萊夫·貝爾關於“有意味的形式”這個著名命題。《莊子》是言道之書,道又無法直接加以顯現,而必須採用特殊的方式對它進行描述。所以,把“有意味的形式”作為研究《莊子》結構藝術的理論支撐,可謂恰如其分,切中肯綮。在運用這個命題的過程中,指出它最初是針對視覺藝術而言,因此,把它用於《莊子》的結構分析,又經歷了由視覺到語言轉換的環節,而不是直接與《莊子》挂鈎。這種會通是以他山之石而攻己之玉,收效明顯。第二種是援引西方學者有關中國古代文化的論述,如德國漢學家卜德的《中國哲學的和諧與沖突》一文,是用海外漢學家的論述印證自己的看法,也做得恰到好處。不過,閲讀全書之後會發現,對於域外學者相關論述所作的借鑒,遠遠少於中國古代的評點及相關闡述,這固然受到書的作者學術視域制約,同時也表明,“新子學”體系的建立,主要應該依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而西方的理論只能起參照作用。
對現代及域外相關理論的借鑒,有利於“新子學”成為一個開放的系統,而不是把自身封閉起來。不過,這種借鑒必須謹慎進行,要對借鑒對象加以甄别推敲,而不能原封不動地套用。學鴻在著作中多次援引臺灣學者陳滿銘有關作品中章法結構的論述,其中有如下一段:
縱向的結構,由内容義旨,也就是情、理、景、事等組成;而横向的結構,則是内容之形式,也就是篇章邏輯,亦即各種章法,如今昔、遠近、大小、本末、賓主、正反、虚實、凡目、因果、抑揚、平側……等組成。因此,舍縱向而取横向,或舍横向而取縱向,是無法分析好文章的篇章結構的。*賈學鴻《〈莊子〉結構藝術研究》,學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頁。
這裏將文章結構劃分語義和形式兩大類,確實有可取之處。這種處理方式既避免了將結構類型劃分過於繁瑣、寬泛的弊病,同時,又能防止對結構類型的關注僅限於形式而忽略内容。至於把語義系統稱為縱向結構,把形式系統稱為横向結構,則有違於作品結構的實際情況。語義結構、形式結構都是有縱有横。比較複雜的作品,不但兩種結構縱横交錯,就是同一系統的結構布局也是有横有縱,而並非單向延伸。陳氏對兩種結構所作的縱横劃分,並不完全符合它們在文章中的實在狀態,很大程度上是他本人對這兩種結構的觀照視角,是從縱向去看語義結構,從横向去審視形式結構。如果真地按照這種縱横之分去研究文章的結構,勢必會遇到許多難以逾越的障礙,無法自圓其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所要借鑒的對象,“新子學”所建立的開放系統才有可能堅牢而圓通。
四
子學是中國古代的思想寶庫,“新子學”體系的建立,必須注重思想方面的研究,對此,章太炎先生已經開風氣之先。他的《國故論衡》下卷《諸子學九篇》,題目有原儒、原道、原名、明見、辨性*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47頁。。從這些題目可以看出,先生所説的子學,指的是古代思想方面的學問。中國近現代的子學,基本是在這條道路上向前推進的,可以説是子學的正路。對於“新子學”而言,還必須繼續沿着這條路前行,並且有所創新。具體而言,就是對先哲思想的研究要有新思維、新角度、新方法。
學鴻這部以《莊子》的結構藝術為研究對象的著作,難能可貴的是,没有停留在對結構方式、類型的排列,以及對作品功能、效應的陳述,而是通過對文章結構的分析,發掘其中所藴含的思想、觀念。該書的“結語”部分,以“大道理念藴藏於結構之中”為題,具體總結了書中所涉及的一系列理念*賈學鴻《〈莊子〉結構藝術研究》,第383~389頁。。其中包括哲學理念、美學理念,涉及許多經典的命題。結構藝術的分析與思想觀念的開掘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從結構形式切入,探索它的思想承載,是把《莊》書的結構作為有意味的形式進行處理。
子書的思想是成體系的,雖然流派繁多,但是許多思想各個學派都予以關注,並且是被認可的理念,可以稱為子學的核心理念。如果能對這些理念進行系統的梳理,劃分為衆多系列,那麽,中國古代思想的精華,它所具有的普適性也就基本得以揭示。即以該書中提到的同類相從命題為例,文中列舉的材料出自《周易·乾·文言》《禮記·樂記》,還提到東方朔的《七諫·謬諫》。如果進一步加以搜索,會發現這是衆多子書反復申訴的理念。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專設《同類相動》欄目,蘇輿的義疏援引《荀子·大略》《吕氏春秋·有始覽》《新論·類感篇》的相關論述加以解説*蘇輿《春秋繁露義疏》,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358頁。。這種帶有普遍意義的命題,在子書中數量衆多,“新子學”應該成為研究這類命題的數據庫和學術平臺。
《〈莊子〉結構藝術研究》通過文章結構分析所發掘出的主要是哲學和美學理念,這是該書有較大理論深度和較高學術價值的重要原因之一。按照傳統的學科分類,美學是哲學的分支。按照傳統的説法,哲學是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概括和總結,居於各類學科的頂端。没有哲學思辨的民族是思想貧乏的民族,同樣,没有哲學作為支撐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是流於表面的浮淺學問,不可能有巨大的深度。“新子學”是受新儒學的啓發而來,綜觀新儒學幾代學者的研究,他們的著述之所以産生深遠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們良好的哲學素養,得益於他們對中西哲學的會通。他們的主要特點,是運用西方理論對中國儒家學説加以闡釋。“新子學”要形成自己的體系,同樣必須以哲學思辨為支撐,否則,面對許多子書會無所措手足,很難有效地進行發掘和利用。但是,“新子學”又不能步新儒學的後塵,而必須在强化哲學支撐方面走出自己的路數。章太炎先生在論述諸子研究時指出:“四裔誠可效,然不足一切畫以自輕鄙。何者?飴豉灑酪,其味不同,而皆可於口。今中國之不可委心遠西,猶遠西之不可委心中國也。”*章太炎《國故論衡》,第103頁。這段論述至今仍有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也是“新子學”應遵循的基本原則。“新子學”强化哲學支撐,首先應該立足本土,堅持民族本位,而不過分依賴他山之石。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是極其豐富的,而且主要見於子書。先秦時期的陰陽五行學説、精氣説、魏晉玄學、宋明理學,都有寶貴的哲學思想資源有待繼續發掘。以這些哲學思想為支撐所形成的“新子學”體系,既能體現鮮明的民族特色,又能反映歷史的邏輯,從而展現出與新儒學不同的風貌和走勢,更易於植根於中華大地,並以獨特的樣態走向世界。“新子學”强化哲學支撐的另一翼,是盡量吸收自然科學的成果,對子書中的哲學思想加以提升,顯示它的當下價值。《老子》四十五章提出一系列哲學命題,其中包括“大直若屈”。王弼注:“隨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樓宇烈《老子道德經注校釋》,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23頁。王弼是從處世的角度解釋這個哲學命題,認為它指的是隨世推移,與物婉轉。如果從現代科學的角度加以審視,老子的這個命題能够成立。在地平面所畫的直線如果不斷延伸,就會圍繞地球一周而成為曲線,正是大直若屈。《老子》四十一章也提出多個哲學命題,其中包括“大方無隅”。河上公注:“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王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65頁。這是從立身的角度解釋“大方無隅”,着眼人的行為方式。如果從古人直觀的思維方式考察,這個命題同樣具有合理性。先民認為天圓地方,稱天為大圓,地為大方,具體記載見於《管子·心術下》。從現代科學角度來看,地球是圓形的,整體上可以説是没有邊角。古人以樸素的直觀面對世界,他們雖然在想象中稱地為大方,實際上他們也無法見到大地邊緣的角。再如《莊子·逍遥遊》中説:“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這是由大鵬摶扶摇而上九萬里所産生的想象和推測,認為人在地面仰視上天其色蒼蒼,大鵬在高空俯視地面所見到的也是這種顔色。莊子為什麽會有這種想象和推測?是否有道理?對此,近人劉武的解釋最為具體:
然天之高不易寫也,特寫輕虚而居上層者,狀如野馬之雲氣也;其下,則浮空之塵埃也;又下,則生物相吹之息也。……三者原無色,厚則在色,如水原無色,深則有色,色亦蒼蒼然也。*劉武《莊子集解内篇補正》,中華書局2008年《莊子集解·莊子集解内篇補正》合刊本,第5頁。
這是從空間厚度方面解釋“天之蒼蒼”色彩感的由來,已經接觸到光學原理,但是,對於莊子的猜測是否合理並没有作出解答。隨着現代宇宙飛船的升天,莊子的猜測得到了證實。從太空俯視地球,確實“其色蒼蒼”,是和藍天相似的色彩。用現代光學理論來解釋這種現象是比較容易的,由此可以看出莊子猜想的合理性。子書中的這類案例還有許多,如果“新子學”能够自覺地借助自然科學的相關知識和研究成果,那麽,它一定會有不同於新儒學的鮮明特色,並且與當下所處的時代、與子學受衆的聯繫更加緊密,使古老的學説重新煥發生機和活力。當然,這就關涉到“新子學”的跨學科研究,學科隊伍的結構問題。需要以學科整合的方式,形成一支有别於傳統子學的研究隊伍。
五
《〈莊子〉結構藝術研究》所征引的文獻包括著作和論文兩類,其中著作140部,論文30篇。與當下的博士論文及相關學術著作相比,所列出的文獻數量不是很多。但是,作者列出的是徵引文獻,也就是説,所列文獻均是書中具體引用的對象,而不只是過目瀏覽的參考文獻而已。《莊子》一書共33篇,出現在該著作目録中的篇目計31篇,只有《説劍》篇和《盜跖》篇未被列入。從目録中可以看出,在閲讀《莊子》原典方面投入精力頗多。由此聯想到“新子學”構建與解讀原典的關聯,如何通過對原典的深入解讀,推出一批標誌性成果,是“新子學”構建的當務之急,也是長遠的任務。
在當今網絡時代,文獻資料的搜集已經是很容易的事情,一部計算機就相當於一個頗具規模的圖書館、數據庫。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對於古籍的整理和研究而言,網絡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使人提高效率,節省時間和精力;另一方面,它又導致人的惰性,助長浮泛空疏的學風。“新子學”應該擔當起匡正時弊、引領風氣的責任,通過推出系列有學術品位的成果,牢固立足於當代學術之林。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要組織一批以學術為人生歸宿的志願者、應召者,在子學著作的整理、出版方面開創新局面。舊版《諸子集成》惠及幾代學人,至今還在不斷重印。可是,這套書所收的著作畢竟數量有限,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有鑒於此,幾家有遠見的出版社都以不同的方式,擴大子書出版的種類和數量,並且已經取得良好的效果,但仍有繼續拓展的空間。中華書局擬定的“新編諸子集成”書目,收録著作四十一種,其中有些與舊版《諸子集成》重複,但相對於數千種子書而言,仍是極其有限的,用《莊子·秋水》的話加以形容,猶如“小石小木之在大山”、“礨空之在大澤”、“稊米之在大倉”。當然,這個系列的書目是精品,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由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刊印的《諸子集成補編》共十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舊版《諸子集成》收録書目偏少的缺憾,把許多比較罕見的子書分門别類地集中在一起,省去學人許多翻閲之勞,亦是功不可没。不過,這套書採用的是原版影印方式,雖然每部書前面有提要,但没有對原文重新加以點校,加之影印效果欠佳,許多地方字迹不清,造成閲讀障礙。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諸子譯注叢書”頗具特色,其《前言》對各書有全面系統的敘述,注釋簡明扼要,譯文亦准確暢達,更便於廣大學人研讀,預計會有良好的市場效應和社會效應。
上述三個子書系列的刊行,為“新子學”提供了可供參照的對象,有的做法可以借鑒,有的模式則需要加以修改完善,在此基礎上可形成“新子學”自己的品牌。根據《子藏》的編纂計劃,在出版方面是三套馬車並駕齊驅,有資料、有論文、有專著。介於資料與專著之間,似乎還應該增加子書原典注釋一個類别。從當前流行的子書來看,真正經得起推敲的注本,多出自古人及前輩學者之手,當代人的注本所占比例較低。而當前學術界、知識界迫切需要的,則是既有學術品位,又能雅俗共賞的注本。“新子學”在這方面可以大有作為,應該在子書傳播、與現實接軌方面作出自己的貢獻。到目前為止,許多重要的子書尚缺少較大讀者覆蓋面的合適注本。近些來看,雖然許多研究生的學位論文以子書為研究對象,但是,由於注釋類著作在許多專業不能作為學位論文提交,因此,由這批青年學人完成的子書注釋比較罕見,在這方面留下許多空白。就是已經出版的三個系列的子書,在子書原典中所占的份額也很小,還有廣闊的選擇餘地,而不會與它們相重複。
“新子學”的子書原典注釋,應該形成自己的特色。除了注釋和翻譯之外,還可以設立導讀及考辨欄目,這兩個欄目的文字必須簡明扼要,便於理解,而避免長篇大論和繁瑣考證。所選的子書原典,應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在歷史上有較大影響,並且與現實比較切近。子書原典的注釋是一項艱苦細緻的工作,實際操作者要有相應的資質,以深厚的學養為支撐,尤其是在語言文字方面要有較深的造詣。這類工作只能採取一人一書的承包方式,而不能層層轉包,或是多人合注一本書。這類書目的選定應該經過嚴密論證,開始階段數量不宜過多,採取穩步推進的方式,逐漸形成子書注釋系列。如果能在三、五年之内推出十部左右,也是頗為可觀的成就。總之,這個系列的工作如果能够付諸實施,那麽“新子學”的創立就有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周易·屯·彖》稱:“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當下正處於學術昌盛的時代,“新子學”是在這種形勢下應運而生。它的創立具有合理性、必然性,也可視為學界的建侯之舉。“新子學”處於初創階段,面臨艱巨的任務,有許多重要的事情要在預定的時間内完成。令人欣慰的是,“新子學”的創立經過了充分論證、長期醖釀,形成了清晰的理路,並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以上所述,是閲讀學鴻博士的新著之後的零散感思,很不成熟,也不成系統,屬於獻芹之舉。學鴻這部著作主體部分的結尾提到卡爾·雅斯貝斯的“大全”理論,提到《莊子》美學的圓通韻味。“新子學”的創立,體現的正是學術上追求大全、圓通的理想。而這種理想的實現,需要無數個圓環扣合,需要從局部做起。《老子》二十二章稱:“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這大概就是“新子學”實現大全、圓融的途徑。
[作者簡介]李炳海(1946— ),男,吉林龍井人。東北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著有《周代文藝思想概觀》《部族文化與先秦文學》《道家與道家文學》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