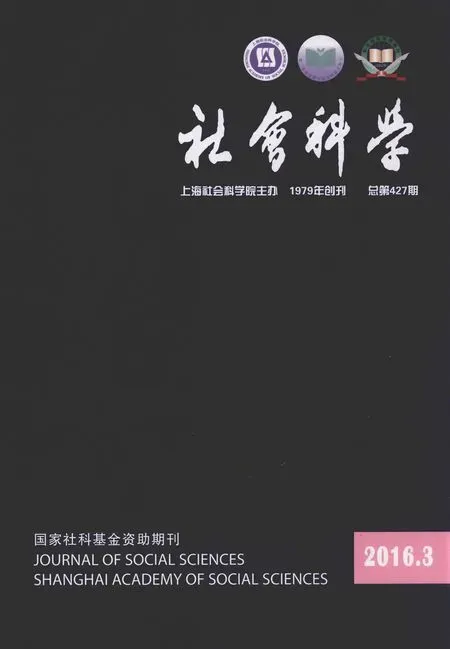当前新疆反极端主义的思考
2016-01-31戴艳梅
王 娜 戴艳梅
当前新疆反极端主义的思考
王 娜 戴艳梅
极端主义界定和理论学说的多元化并不否定极端主义本质上的统一性,应当在极端主义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视野中审视新疆“三股势力”“三位一体”、境内外勾结、危害严重的“极端化”基本态势。既有的“去极端化”建议和反极端主义模式,都没有将反极端主义作为独立的命题。极端主义和反极端主义应当有独立的价值和定位,不应当依附于宗教、民族、恐怖主义、极端分子等问题来讨论。中国新疆的“去极端化”应当置于中国反极端主义的整体战略框架中予以考虑,其先导性的意义可以超越其特殊性和区域性的特征,但是不能取代其特殊性和区域性的特征。中国的反极端主义战略应当从政策模式走向法治模式,在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的法治建设框架中,构建多元化有层次的系统化策略,形成中国的反极端主义法治体系。
“去极端化”;极端主义;反极端主义;新疆;法治
在新疆,随着暴恐态势的发展,打击“三股势力”的基调不断强化。“三股势力”就是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三股势力”之间有本质区别,又相互融合,在新疆形成“三位一体”之态。我们应当挖掘凝聚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背后的根本因素,才能比较好地应对暴恐活动,解决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笔者认为,“三股势力”背后的共同根源是极端主义,因此,新疆的“去极端化”问题更迫切更重要。基于此,本文从理论层面、事实层面予以探讨,并尝试提出应对之策。
一、 理论之辩:何为极端主义?
(一) 极端主义的多元化界定
在汉语语境中,从字面意思来看,“极”是顶端、最高点、尽头的意思;“极端”是事物顺着某方向发展到顶点;“主义”是指对事情的主张,形成系统的理论学说或思想体系。对极端主义的界定,有两种:第一,以政治内容为核心的界定,如有的学者提出,极端主义是指政治主张偏激、且采取极端手段实施具有政治目的的活动*李琪:《中亚地区安全化矩阵中的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二,排除政治因素的界定,如有的学者指出极端主义是“任何个人或者组织为实现其某种严重脱离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并排斥与之不一致的任何理念,而针对其自身或第三者采取暴力或其他非暴力的手段,从而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行为”*卢有学、吴永辉:《极端主义犯罪辨析——基础理论与立法剖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苏联大百科全书》*[苏]伏维金斯基主编:《苏联大百科全书》第48卷,莫斯科国家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27页。将极端主义界定为,通常对于激进观点和手段的极度倾向。维基百科则认为,“极端主义是一种远离社会主流态度或违反公共道德标准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或宗教)。极端主义有很多表现形式,包括政治的、宗教的和经济的”*http://en.wikipedia.org/wiki/Extremism.。
由此,极端主义主要是描述那些与现存标准不一致的观点和思想,将某些危及现存标准和社会规则的极端思想界定为极端主义,通过标签化,从而打上否定性评价的烙印。极端主义一词的适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宗教领域等。极端主义词语适用的广泛性与各领域极端主义思想的多样化相结合,催生的结果就是界定极端主义是十分困难的。就极端主义内含的核心要素“极端化”而言,通俗意义上很好理解,即与主流标准或者一般标准相去甚远,但是,如何认定主流标准或者一般标准,这是个价值判断问题,也是个主观认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
Dr. Peter T. Coleman和Dr. Andrea Bartoli明确指出,极端主义界定中存在的问题:第一,由于界定者的价值观、政治立场、道德标准以及界定者本身与极端主义者的关系等不同,同样的极端行为,有人认为是正义的、合乎道德标准的,有人认为是非正义的甚至是反社会的恐怖主义。第二,权力的差异也是界定极端主义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冲突中,与坚持维持现状的高权力群体成员相比,低权力群体成员的类似行为更容易被界定为是极端的;另外,边缘群体将参与更规范的冲突形式视为对自身的封锁和偏见,他们更倾向于极端行为;统治集团通常也使用极端行为。第三,极端行为经常采用暴力手段,尽管极端主义集团在暴力与非暴力的策略方面偏好不同,如暴力的使用水平和暴力的首选目标等方面。而且,低权力群体成员更倾向于采用直接的、偶发的暴力手段(如爆炸式自杀),统治集团更倾向于采用结构性的和体制式的暴力手段(如酷刑和警察粗暴的非正式惩罚)。第四,极端的个人和组织(如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常常被认定为是持续性的一贯邪恶,但是,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作为个体,他们可能存在冲突、可能存在心理上的矛盾,并且在群体中,包含着大量的差异性和冲突,如哈马斯的成员在与巴勒斯坦分歧谈判的意愿上有很大不同。最后,极端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在旷日持久的冲突中活动性(尽管暴力、创伤的升级是显而易见的)降低,极端主义的态度更加封闭、僵化、偏狭,以及随之而来的是抗拒改变*⑦ Andrea Bartoli and Peter T. Coleman, “Dealing with Extremists”, http://www.beyondintractability.org/essay/dealing-extremists.。
就极端主义理论而言,其多元性多面态更是显而易见。在政治领域,有左派极端主义、右派极端主义,甚至Seymour Martin Lipset提出了“中心极端主义”,认为“中心极端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根基*G. M. Tamás, “On Post-Fascism”, Boston Review, Summer, 2000.。在宗教领域,有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等。有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对极端主义进行解读,如Dr. Kathleen Taylor提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精神疾病,是可以治愈的*Simon de Bruxelles, “Science ‘May One Day Cure Islamic Radicals’”, The Times, London, 2013-05-31.。Arno Gruen指出,极端分子缺乏自我认同,这是自我毁灭自我憎恨的结果,导致对生命本身的复仇情结,并强制杀死自己的人性。因此极端主义不是战术,也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毁灭生命的病理性疾病⑦。
(二) 极端主义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那么,极端主义的统一界定是否可能?有的学者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如Ronald Wintrobe指出,很多极端主义运动,尽管秉持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但是,依然共享一系列相同的特点,并以“犹太原教旨主义者”(Jewish Fundamentalists)和“哈马斯极端分子”(The Extremists of Hamas)为例,提炼出两者的共同之处:两者都反对与对方有任何妥协;两者都非常确定自己的立场;两者都倡导并使用暴力实现目标;两者都是民族主义者;两者都无法容忍自己组织内部的不同意见;两者都妖魔化对方*Ronald Wintrobe, Rational Extrem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adic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5.。
笔者认为,尽管极端主义的理论学说繁多,界定极端主义有困难,但是,还是有必要提炼极端主义的核心要素。从一般意义上来看,被冠名为极端主义的思想或者理论,一定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思想导向或者追求目标的单极化;二是思维路径的偏狭性。这两者相结合,在行动上推崇到极端,就必然导致暴力手段的使用。所以,暴力是极端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文明世界的语境中,对“人”身体和生命的尊重和保障是最基本的价值,也是不可突破的底限。全面废止死刑和和禁止酷刑已经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就是这种价值诉求的体现。极端主义不可避免地使用暴力,突破了社会承受的底限,也是其“极端化”的表现。
从特殊性角度来看,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流派的极端主义是不同的。就中国而言,极端主义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法定范畴,《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2001年)(以下简称《上海公约》)明确规定了极端主义的概念,“极端主义是指旨在使用暴力夺取政权、执掌政权或改变国家宪法体制,通过暴力手段侵犯公共安全,包括为达到上述目的组织或参加非法武装团伙,并且依各方国内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任何行为”。从规范意义来看,中国和上合组织认定的极端主义有三个特征:第一,目标是夺取政权、执掌政权或者改变国家宪法体制;第二,使用暴力;第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简单来说,是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政权的刑事犯罪。极端主义既是意识形态也是暴力犯罪。
另外,单从极端主义本身的界定来分析其特征是不够的,《上海公约》同时明确规定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因此,要在三者相互区分的语境中理解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是指:“一、为本公约附件(以下简称“附件”)所列条约之一所认定并经其定义为犯罪的任何行为;二、致使平民或武装冲突情况下未积极参与军事行动的任何其他人员死亡或对其造成重大人身伤害、对物质目标造成重大损失的任何其它行为,以及组织、策划、共谋、教唆上述活动的行为,而此类行为因其性质或背景可认定为恐吓居民、破坏公共安全或强制政权机关或国际组织以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行为,并且是依各方国内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任何行为。”分裂主义是指:“旨在破坏国家领土完整,包括把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分裂出去或分解国家而使用暴力,以及策划、准备、共谋和教唆从事上述活动的行为,并且是依据各方国内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任何行为。”恐怖主义的特征是:第一,针对平民或者居民使用暴力进行伤害、恐吓;第二,破坏公共安全或者威胁政权机关或国际组织;第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分裂主义的特征是:第一,破坏国家领土完整;第二,包括使用暴力;第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比较《上海公约》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界定,这“三个主义”的目标不同,这是它们的本质区别,相同之处都包含“暴力”元素,都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因此,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极端主义,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极端主义具有特殊性,该特殊性获得中国认可,新疆的极端主义也是纳入该框架内予以打击,有必要进一步探究新疆极端主义的客观情状。
二、 事实探求:新疆极端主义如何?
(一) 新疆极端主义的范围
从客观事实的角度来看,新疆的极端主义如何?需要首先明确新疆极端主义的范围。广义说认为,极端主义是当今世界的一股政治浊流,有三种主要类型——民族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是超常规的政治现象……作为政治现实中的客观现象,极端主义包括非常规的观念和暴力行为两个方面。……可以把极端主义视为一种激进行动为外形,以反社会、反政府为内核的政治现象”*王嘎:《极端主义对中亚政治稳定的威胁》,《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按照这种说法,中国新疆地区的“三股势力”都属于极端主义的范围。狭义说是在新疆地区“三股势力”划分基础上的特殊指向,即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之间是有区别的,新疆的极端主义就是宗教极端主义,或者更明确一点,就是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
笔者主张应当同时兼顾广义说和狭义说,为了便于区分,对广义说的极端主义表述为“极端化”,对狭义说的极端主义表述为极端主义。一方面,新疆的“极端化”融合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抛开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全面正确认识另一个;另一方面,新疆的“三股势力”是不同的,只有在相互区分的基础上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和应对新疆的宗教极端主义。
(二) 新疆“极端化”的基本态势
1. “三股势力”“三位一体”
“新疆‘三股势力’指的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他们三位一体,打着民族、宗教的幌子,煽动民族仇视,制造宗教狂热,鼓吹对‘异教徒’进行‘圣战’,大搞暴力恐怖活动,残杀无辜,挑起暴乱骚乱。他们的目标就是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来,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吴福环:《新疆“三股势力”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光明日报》2009年7月25日。正是因为“三股势力”打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的旗号,也被称为“东突势力”。“东突”运动将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作为其两大意识形态基础,并衍生出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段志丹:《“东突”运动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的产物》,《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三股势力”密切联系、相互交融的状态,并不抹杀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区别,相反地,恰恰是这三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基础。
首先,从横向静态上来看,就理论而言,民族分裂主义是民族主义极端化的表现,民族主义的理论根基是民族自决原则,民族主义极端化体现为较强的排斥性和激烈性,在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内部,少数民族的极端势力通过暴力活动等表达独立建国的政治诉求,既是对现有政权的否定也是对国家领土的分割;宗教极端主义本质上不是宗教,而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不惜一切手段(主要是暴力),推翻现有政权统治,恢复神权统治,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恐怖主义是故意制造恐慌的暴力行为,其本质是暴力元素不可或缺。上合组织坚持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三者相互区分的立场(见前述),相对于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而言,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在外延上更广泛,打击力度更大,作为刑事犯罪来应对。
其次,从纵向动态上来看,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就深受“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萌发于19世纪70年代的“泛突厥主义”,亦称为“泛奥斯曼主义”、“土兰主义”、“乌古斯主义”,这是一种主张将土耳其、俄罗斯、伊朗、阿富汗、中国以及中亚诸国境内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为一体,建立“大突厥斯坦”的跨国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随后,“泛突厥主义”被激进的民族主义势力所利用,成为民族分裂的理论工具*《中国反恐的基本态势与战略措施》,载《第三届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国际论坛论文集》,2011年,第4页。。十九世纪中期产生于西亚的泛伊斯兰主义提出:政治上,全世界的穆斯林联合起来,强化哈里发的领导,遵循《古兰经》的教诲,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法基础上的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伊斯兰共同体,反对欧洲殖民主义;宗教上,强调“认主独一”,伊斯兰教应是适应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域*参见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426页。。由于新疆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宗教情感的历史渊源,“双泛”思想一直以不同的方式渗透至新疆发挥影响力,并成为新疆“东突”运动主要的意识形态基础。“20世纪80年代,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在原有泛伊斯兰主义的基础上接受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推崇‘圣战’,其意识形态基础明显地极端化。20世纪90年代‘东突’组织恶性膨胀,暴力恐怖事件频发,其极端行为宣告了泛伊斯兰主义中的激进主义元素已经开始并同恐怖主义理念相结合,并指导其行为模式走向极端。”*段志丹:《“东突”运动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的产物》,《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最后,从当下的结构形态来看,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者之间相互交融,其中,宗教极端主义处于枢纽地位。民族分裂主义是新疆少数人借助于“民族”权利的幌子将具有血统关系的人员聚集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从而达到分裂新疆的目的,恐怖主义是推崇暴力手段,而将这两者深度凝聚在一起的是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为民族分裂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的“正当化”有机结合提供了强大的心理基础和理念支撑。正是在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蛊惑下,三者共同达成“极端化”的总态势。在新疆,“三股势力”实施的六类主要恐怖活动案件,包括爆炸、暗杀、纵火、投毒、制造打砸抢骚乱事件、制造暴乱事件等。总之,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者分别从政治、宗教和现实等层面构筑了新疆“三位一体”的“极端化”。
2. 境内外勾结
新疆“三位一体”“极端化”的态势,与国际因素密切相连。中国新疆的“极端化”,是中亚“极端化”乃至世界“极端化”的组成部分,呈现出内外勾结的明显特征。
首先,就新疆“东突”势力的发展而言,在政治层面,新疆的“极端化”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国际势力的身影。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在英国的支持下,由泛突厥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和沙比提大毛拉等炮制建立的*王克平:《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溯源及嬗变》,《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10期。。“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等恐怖组织的成立及活动均与境外敌对势力密切相连。
其次,就中亚的整个局势来说,“极端化”的态势比较明显,已经成为世界上关注的焦点地区,“在不远的将来,中亚会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向西方文明宣战的策源地”*《独立报》,2001年9月14日。。中亚民族的多样性、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以及民族、宗教问题的跨国性,使得中亚的民族、宗教问题呈现复杂化的特征;中亚各国在苏联解体以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真空状态为“极端化”思想和势力的生长提供空间,而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经济、社会、民生等问题为“极端化”思想和势力的扩张提供机会。问题和矛盾的复杂化,是冲突频现的根本原因。另外,由于中亚地处东西方世界的交汇处,无论从历史传统还是从当下的现实状况来看,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等国际势力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比较活跃。
最后,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经济全球化推动资源、人员、资金的全球性流动和配置,使得资源效益优化的同时,也使得缓慢于全球化发展步伐的国家和地区呈现边缘化的态势。另外,冷战思维在全球化过程中仍在延续。因此,“极端化”的思潮和势力,在东西文明的交流对抗中、在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抬头复兴。国际社会对本·拉登本人的摧毁和对基地组织的打击,并没有毁灭极端势力,“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成为“后拉登时代恐怖主义的新标志”,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恐怖组织”,“‘ISIS’对世界的危险远远高于塔利班,其影响已经突破区域局限,成为全球性的威胁”*陈宪忠等:《揭秘“伊斯兰国”组织:世界“最富”的恐怖集团》,《环球时报》2014年6月16日。。2015年11月13日发生在巴黎的暴恐袭击已经证实了这种判断。
新疆“极端化”分别在区域层面上和国际层面上呈现内外极端势力勾结的特点,无论是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培植,还是恐怖主义活动的策划、实施,国内外因素相互交织。例如近几年,我国一部分新疆维吾尔族非法偷渡出境,经由土耳其前往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参加所谓的“圣战”,有的返回中国境内继续策划、实施暴恐活动*参见《10名土耳其人组织新疆渉恐人员偷渡出境被批捕》,《环球时报》2015年1月14日。。
3. “极端化”危害严重
新疆极端势力主要通过“认主独一”对抗政府、“圣战”杀人论、“殉教升天堂”论、“伊吉拉特”论、泛“清真”论、不戴面纱者“非伊斯兰法”论等方式予以运作,自2014年以来,新疆极端势力的活动呈现出新特点,包括“跳出新疆,暴恐活动外溢”、“滥杀无辜,残忍之极,无以复加”、“组织和预谋”、“视频洗脑、网络动员、小团伙作案”、“暴恐成员低龄化、且有女性参加”等*潘志平:《鼓励宗教去政治化2014极端势力活动“外溢效应”明显》,《人民论坛》2015年1月20日。,危害严重性趋强。
就“极端化”的危害性而言,在狭义语境中,主要侧重于宗教极端主义的危害性,如有论者指出,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传播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相勾结,从事煽动破坏活动,危害社会政治稳定;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宣扬宗教极端思想、危害社会秩序的活动不利于新疆的经济发展;宗教极端主义的泛滥影响团结和睦的民族关系;破坏新疆地区正常的宗教活动*施东颖:《浅析宗教极端主义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影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有的论者指出,宗教极端主义的危害表现为:危害国家安全;制造不同信教群体之间的仇视和斗争,撕裂族群与社会;危害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毒化宗教氛围,摧毁宗教形象和声誉*马品彦:《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在广义语境中,是指“三股势力”的危害性,如有的论者指出,民族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活动,对中亚国家的社会稳定产生严重影响,干扰中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对中亚地区的安全构成威胁*陈联璧:《三个“极端主义”与中亚安全》,《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5期。。有的论者认为“三股势力”的危害主要是:妄图分裂祖国、破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危害新疆和周边地区安全与稳定,肆意践踏新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民族团结、策动民族分裂,严重干扰新疆的经济发展*徐步军:《铲除危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毒瘤——“三股势力”》,《统一论坛》2015年2月23日。。
虽然论者角度不同,但是,基于“三股势力”“三位一体”的构架,宗教极端主义的危害性和“三股势力”的危害性是不可割裂的。因此,从广义的角度,立足于中亚的整体形势来看待新疆“极端化”的危害性更为合适。新疆的“极端化”对国家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公民个人的生命财产等社会各方面各领域造成全面的严重危害,并给周边地区的安全稳定甚至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带来威胁。鉴于“极端化”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因此,采取什么策略“去极端化”就尤为重要。
三、 应对之策:如何“去极端化”?
(一) 新疆“去极端化”之既有建议
就新疆“去极端化”的策略而言,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专门针对宗教极端主义提出的应对之策。如有的论者指出,新疆宗教极端主义打着伊斯兰旗号以夺取政权,其本质并不是宗教,基于神权政治论、宗教至上论、异教徒论和圣战论,其极端性表现在三个方面:思想上极端,将某些宗教观点极端化,反对世俗政权;政治上极端,主张政教合一;手段上极端,主张用各种暴力手段来实现目的*张英彪:《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策略探讨》,《才智》2014年第30期。。据此,提出“分层次有针对性的策略”,即将维吾尔穆斯林分为四种社会群体,分别为文化穆斯林、世俗穆斯林、保守穆斯林和极端穆斯林,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即培养文化穆斯林、提倡穆斯林世俗化、教育保守穆斯林、打击极端穆斯林*张英彪:《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策略探讨》,《才智》2014年第30期。。有的论者指出我国遏制宗教极端主义中存在问题,如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立法不够清晰,限制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传播的法律制度落后,宗教管理也存在一定缺陷等,从而提出应当完善我国遏制宗教极端主义的立法及相关制度,包括:落实我国的宗教政策,划定宗教自由的法律边界,加强国家意识和正确宗教观的教育,完善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相关立法,完善互联网的相关立法*⑧⑩ 胡田野:《借鉴与完善:遏制宗教极端主义的立法研究》,《政法学刊》2013年第10期。。有的论者提出,防范和遏制宗教极端主义,在新阶段要大力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针对“祸水东渐”推进“战略西进”;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基本方针,保护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发挥宗教人士的积极作用;要严厉打击那些制造、传播宗教极端主义的不法分子;要审时度势,认清祸水源头,强调宗教极端主义是一切民族、一切宗教的公敌*叶小文:《防范和遏制宗教极端主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第二,针对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提出的应对之策。如有的论者指出,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活动,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制止非法宗教活动;坚决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伊斯兰教对新疆的渗透破坏活动;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铲除宗教极端主义的土壤*施东颖:《浅析宗教极端主义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影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第三,针对恐怖主义提出的应对之策。有的论者立足于宗教“去极端化”对反恐的意义,提出打一场反暴恐、“去极端化”的人民战争,在战略上,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以先进文化引领、鼓励伊斯兰教回归文化宗教、道德宗教,推进社会世俗化进程;在战术上,发展教育、以文化人*潘志平:《鼓励宗教去政治化2014极端势力活动“外溢效应”明显》,《人民论坛》2015年1月(下)。。有的论者直接指出,新疆的反恐斗争策略是:教育上,针对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提出要国家托管、免费教育;针对宗教问题,要加强立法、规范管理;针对贫困问题,要强化对口援疆、政策扶持等,不断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刘刚、赵宇:《新疆地区宗教形势和去极端化》,《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第1期。。有的论者提出遏制极端恐怖主义的战略系统:深入暴露宗教极端恐怖主义的邪教实质;支持、鼓励开展合法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广泛开展国际间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积极开展少数民族文化知识教育;大力发展民族地区多样化经济;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和恐怖主义活动*胡东武等:《遏制极端恐怖主义的战略系统论研究》,《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前述论者的立场和角度不同,基本观点有或多或少的重合。鉴于新疆的“极端化”呈“三股势力”“三位一体”、境内外勾结的情状,新疆的“去极端化”策略设计应当统筹考虑,不可偏废。
(二) 外国“去极端化”的战略
1. 限制宗教自由战略。目前,欧洲和美国“去极端化”的思路渐趋一致,都是立足于宗教和暴力之间的联系,对宗教自由进行限制。欧洲各国出台相关法律进行规制,有的通过出台或者修订其他法律对宗教自由进行限制,包括严格审查宗教组织,直接干涉宗教信仰本身,限制宗教结社的特权等,限定宗教自由的非公共性,如法国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宗教标志的服饰等;有的直接将其作为反恐法的一部分纳入其中,如“在英国的立法中,将宗教认定为恐怖主义活动的动因”⑧。美国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暴力行为,纳入反恐法中进行规制,对于非暴力的极端主义言论及其传播,是美国司法机关的一个难题,要在宪法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和遏制极端主义之间进行艰难的取舍。目前,言论入罪过分严格的立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设定的言论入罪必须满足的三个标准:言论发布者必须有引起骚乱或者暴乱的明确意图(Intent);该骚乱或者暴乱是紧迫的,即将到来的(Imminence);该言论必须是具备导致骚乱或者暴乱的“可能性”(Likelihood)。受到批判⑩,应当对极端主义宗教言论和结社等行为进行限制的思想抬头。
2. 应对极端分子战略。该战略将“去极端化”聚焦于如何应对极端分子,沙特采纳这样的战略模式。沙特在2003年发起一个“预防、康复和善后关注”(Prevention, Rehabilition and After-Care)战略,专门针对极端主义分子,分别采取预防措施尽可能清除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改造极端分子使其尽快融入社会、并进行对极端分子监督管理和社会追踪、社会支持防止极端分子再误入歧途*胡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去极端化研究——以沙特PRAC战略为个案的分析》,《国际论坛》2012年第5期。。
3. 全面战略模式。俄罗斯采纳这样的模式。俄罗斯于2002年7月25日出台《反极端主义活动法》,该法在近年进行了大量修订与完善,对极端主义的封堵越来越严密。2014年11月20日,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在2025年之前反极端主义战略》,2014年11月28日,俄罗斯总统发布该战略,作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打击极端主义的基本文件,该战略把恐怖主义视为极端主义的极端表现。在恐怖活动得到有效控制后,目前,俄罗斯把反恐的重点放到消除恐怖主义根源上,即消除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反极端主义活动法》规定了一些概念、原则、方向、组织基础,将恐怖活动列入极端主义的组成部分。《2025年前俄联邦反极端主义战略》规定了本领域的核心概念,分析了现代俄罗斯极端主义威胁的主要来源,指出了打击极端主义的目的、任务和基本方向及战略的实现机制。该文件通过以上四个部分基本上架构了俄罗斯反极端主义的基本框架。该战略的目标与国家安全战略一致,仍然是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保持安全与稳定,实现这一目标依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实施的组织性与法律性措施。战略确定了国家在反极端主义方面的任务是:建立统一的国家监控系统;完善立法;形成全社会反极端主义的合力,尤其是在舆论宣传领域。打击极端主义的基本方向包括立法、执法、公共政策、移民政策、媒体监控、教育与青年政策、国家文化政策、国际合作八大方面。该战略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规定了实现目标,完成任务的三个阶段:2015年是在计划与组织方面完成准备工作;2016年—2024年全面执行并监控战略实施,预测极端主义发展,建立互联网等媒介防极端主义渗透的系统;2025年总结并提出新方案。《反极端主义活动法》在立法上规定了极端主义领域的违法界限;《2025年前俄联邦反极端主义战略》则旨在构建国家反极端主义的系统,涵盖了堵截极端主义的八大方向,方向之下的措施详细具体,便于联邦主体与市一级制订落实的方案。在建立了有效的反恐体系后,俄罗斯将关注重点放到清源,可以想象,俄罗斯国内反恐形势会进一步好转。
(三) 新疆“去极端化”的法治战略构想
鉴于极端主义理解和界定上多元化、一般性和特殊性兼具的特征,当代新疆“去极端化”问题的定位不能过于简单化也不能过于复杂化,不能过于宏大也不能太微观,应当立足于极端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趋势,从中国和新疆的具体情况出发,构建“去极端化”战略。因此,有必要反思既有的对策,综合国内外的战略模式,提出中国的“反极端化”战略。前述新疆“去极端化”建议和国外的反极端主义模式,立足于不同的具体情况,从不同角度来探讨,有一定的合理性,均有可取之处。但是,将极端主义问题视为宗教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甚至极端分子的问题,是不全面的,没有将反极端主义作为独立的命题。本文认为,极端主义和反极端主义的讨论,应当有独立的价值和定位,尽管与宗教问题、民族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密切相连,但是,不应当依附于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来讨论。因此,新疆的“去极端化”策略应当置于中国反极端主义战略构建视野中予以论述。
第一,“去极端化”的定位。需要先厘清两个关系,即反极端主义与“反恐”的关系、新疆“去极端化”与中国反极端主义的关系。首先,就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关系来说,作为现实问题,二者之间相互交融,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两者又有区别。在反极端主义和“反恐”的策略上,存在不同的关系模式,即反极端主义和“反恐”相互独立的模式、反极端主义包含“反恐”的模式、“反恐”包含反极端主义的模式。鉴于本文前述关于极端主义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广义层面上反极端主义包含“反恐”,在狭义层面上反极端主义和“反恐”相互区别,这是比较符合逻辑的。因此,不赞同“反恐”包含反极端主义的定位。其次,就新疆“去极端化”和中国反极端主义的关系而言,鉴于中国极端主义问题的现实情况,新疆“去极端化”问题在中国反极端主义问题中具有特殊性和不可取代的先导性。但是,无论从地域上来看还是从问题本身来看,新疆“去极端化”问题属于中国反极端主义的一部分,两者不能等同。
第二,“去极端化”的模式选择。从整体上来看,“去极端化”的模式主要有法治模式和政策模式两种类型。法治模式是通过构建完整统一的法律框架,将反极端主义纳入整个国家法治体系中。目前,俄罗斯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国内专门制定“反极端主义活动法”,并制定“去极端化”的国家战略,在该战略中,反极端主义的全面法治化是近期基本目标。政策模式是为了短期利益或者解决急迫问题的需求,将反极端主义作为其中的一个具体措施或者步骤。目前,中国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在国内的刑事立法修订中,为了满足反恐立法的需要,规定部分反极端主义的罪名*《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罪名包括: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在国际合作中,为了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提出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网络恐怖主义为重点,建议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商签“反极端主义公约”*参见2014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各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
政策模式尽管具备灵活性、即时见效的特征,但是,与法治模式的系统性、确定性特征相比,其碎片化、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去极端化”的效益大打折扣。因此,中国的反极端主义应当从政策模式走向法治模式,构建反极端主义战略,在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同步推进,融入法治建设的整体框架中,从而全面实现反极端主义的法治化。
第三,“去极端化”的策略选择。就反极端主义的策略而言,根据着眼点是聚焦于“人”还是“事”、目标是彻底“消除”还是进行“调解”转化而有所区别。一、隔离、根除的策略。该策略将极端分子和极端组织作为打击的重点,通过简单地运用信息、法律和武力来识别、定位、逮捕(或者摧毁)极端分子或者极端组织的头目,斩断极端组织的经济来源,损害极端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并竭尽全力使公共的主要群体远离极端成员,谴责他们的行为。二、渗透、分化的策略。该策略是组织一定的社会团体或者成员渗透极端组织,尽可能争取其中温和成员的支持,通过损害其最为珍视的遵从和凝聚力,达到瓦解极端组织的目标。三、“反激进化”策略。该策略将恐怖主义“激进化”简单地表述为这样的过程:个体或者群体由于种种原因怀有不满或者怨恨情绪,在接受了极端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情况下,逐渐发展成为恐怖主义者,与“激进化”相对应,以接受极端思想为界,“反激进化”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先“反”后“去”的过程*沈晓晨、杨恕:《试析“反恐怖主义激进化”的三个关键维度——基于英国“预防战略”的案例分析》,《欧洲研究》2014年第3期。。四、综合策略。该策略提出要同时综合运用不同的策略,包括彻底根除的策略和调解分化的策略等。五、和平建设的策略。该策略目的是处理培育极端主义的潜在条件,在两个层面上提出行动要求。宏观社会层面的要求:减少不公和压迫,保护人权,弱化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减少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促进政治授权、社会团体之间的宽容、合作、非暴力冲突解决方案;民主化和参与治理;强化民权社会。在微观社会层面,要求减少陈规旧习和敌对影像,提升同感、关心、文化之间的理解,为年轻人提供经济和社会支持*Andrea Bartoli and Peter T. Coleman, “Dealing with Extremists”, http://www.beyondintractability.org/essay/dealing-extremists.。
很明显,隔离、根除策略和渗透、分化策略是聚焦于“人”的策略,将极端分子与社会公众予以严格区分,并进行敌对化的界定,前者是消除极端分子,后者是争取更多的社会成员与极端分子疏远。“反激进化”策略是着眼于事态发展过程的策略,综合策略与和平建设策略是立足于解决问题的聚焦于“事”的策略。从效益上来看,隔离、根除策略可以直接去除个别组织或者人员,但是,不能解决极端主义的深层次问题,还有可能激发更激烈的反抗,甚至提升对极端主义的同情。渗透、分化策略不能排除反弹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反而被极端组织利用。“反激进化”策略以恐怖主义是可以预防的命题为基础,以是否接受极端思想为界,采取预防措施,但是,“反对什么、怎么反对、如何反对”这些涉及“反激进化”实施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沈晓晨、杨恕:《试析“反恐怖主义激进化”的三个关键维度——基于英国“预防战略”的案例分析》,《欧洲研究》2014年第3期。。综合策略与和平建设策略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雄心勃勃的计划和令人沮丧的日常工作事项,常常因为期限太长、太过于乐观而不够现实而被极端主义分子抛弃。建设和平进程的缓慢步伐也疏离了那些本身还不是极端主义分子而又倡导积极对抗的社会阶层”*Andrea Bartoli and Peter T. Coleman, “Dealing with Extremists”, http://www.beyondintractability.org/essay/dealing-extremists.。鉴于此,任何单一策略都是不够的,“去极端化”的策略选择应当立足“人”,着眼于解决“事”,兼顾思想、理念、行为、社会环境,形成有区别有层次的多元化系统策略。
综上,一方面,新疆极端主义的现实特征是中国构建反极端主义战略的事实依据;另一方面,中国新疆的“去极端化”应当置于中国反极端主义的整体战略框架中予以考虑,其先导性的意义可以超越其特殊性和区域性的特征,但是不能取代其特殊性和区域性的特征。中国的反极端主义战略应当从政策模式走向法治模式,在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的法治建设框架中,构建多元化有层次的系统化策略,形成中国的反极端主义法治体系。
(责任编辑:潇湘子)
Thinking about Anti-Extremism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Wang Na Dai Yanmei
In spite of the diversity of the definition and theory of Extremism, the nature of the Extremism should be studied. In Xinjiang, three phenomena exist including “Three Forces” (the Terrorist Force, the Ethnic Separatist Force and the Religious Extremist Force) in the Trinity, collus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forces, serious damage caused by Extremis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tremism in Xinjiang should be examin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neral and special nature of Extremism. The existing Anti-Extremism models show that Anti-Extremism is attached to the issues of religion, nationality and terrorism. In fact, the independent value and position of the issue of Anti-Extremism should be emphasized. Anti-Extremism in Xinjiang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overall strategic framework of China’s Anti-Extremism which should be built i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and the domestic level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law instead of the policy.
“Removal of Extremism”; Extremism; Anti-Extremism; Xinjiang; Rule of Law
2015-11-27
D635
A
0257-5833(2016)03-0041-10
王 娜,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上海政法学院检察制度比较研究中心负责人 ;戴艳梅,公安部研究员、博士 (上海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