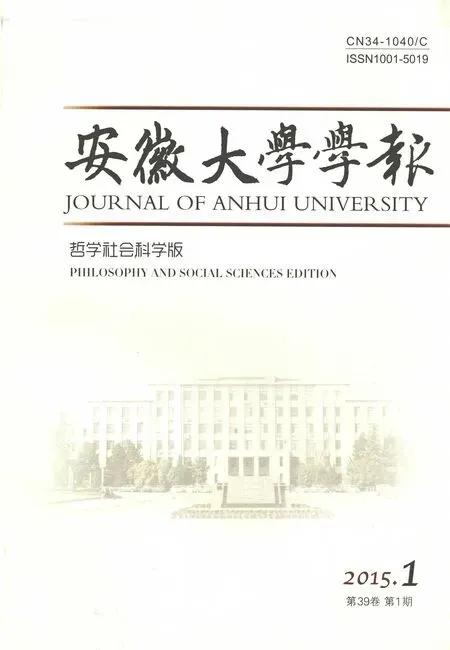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优遇传教士·浙江禁教·容教令出台——从中国天主教史角度看康熙帝政治
2016-01-31冯尔康
冯尔康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优遇传教士·浙江禁教·容教令出台
——从中国天主教史角度看康熙帝政治
冯尔康
摘要: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优遇传教士、浙江禁教与容教令出台三者是连环关系,二次南巡眷顾传教士触发浙江禁教,再导致容教令的制订与颁布,就中康熙帝眷注传教士和允许传教的态度表露无遗。从中国天主教史角度考察,众所周知的南巡主要目的之外,康熙帝为了使用西洋人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有着附加的一个目标——借机考察传教士的为人与技能。目的达到了,调查研究的施政手段亦运用得很成熟。就康熙帝个人讲,他在对天主教与反教臣民之间实行中庸之道的平衡政策,也是一种政治治理艺术。容教令颁布,宗教纠纷并未完结,地方官的反教事情终康熙之世亦未停止(康熙以后仍在继续)。究其原因,臣民反对外来的天主教是在“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观念支配下进行的;又由于君统与道统分离,君统不能支配道统,至少不能完全支配道统,体现君统的皇帝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若与道统不能协调一致,方针政策就不能贯彻到所有的领域,不能真正贯彻到基层政权的州县。
关键词:康熙帝南巡;天主教;传教士;禁教;容教令;道统;君统;华夷之辨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中优遇传教士,随后发生的浙江禁教与容教令出台,三者是循环相生现象,可谓连环关系:二次南巡优遇传教士引发浙江禁教,再导致容教令的出台。从中不难发现事物的多样性,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研讨。若从天主教史角度观察,则可深入了解康熙帝调查研究的政治作风与南巡的多种目的——为利用西洋人的科学技术、艺术而考察传教士是南巡目的之一。容教令颁布之后,在浙江及其他一些省份仍有反教现象,而且是以封疆大吏和府县官来主导,他们敢于蔑视皇帝谕旨,是以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观念为准则,是在君统与道统分离的前提下发生的行为,归根结底并不违背忠君伦理。
一、背景: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以前与西方教士的关系
康熙二十八年(1689)南巡,三十年(1691)浙江禁教,三十一年(1692)康熙帝制订容教令,三件事集中在皇帝与相当部分地方官、民间对待天主教相异的态度方面,因此有必要先交代康熙帝二次南巡以前与西方传教士的密切关系,以便明了他在第二次南巡中眷顾传教士的历史渊源。
康熙帝是在亲政之初(七年,1668)开始欣赏西士*“西士”是在朝廷、宫廷服务的传教士,他们以服务的业务为主要职责,传教作用很大,但不是将主要精力投注于此,并以此区别于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传教士。冯尔康:《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及其原因试析》,《安徽史学》2014年第5期。的,随着与西士、传教士接触频繁,认识加深,认为他们忠诚质朴,多方使用,并在二十三年(1684)首次南巡中就表现出对传教士的热情。
第二次南巡前,康熙帝招徕与多方面任用西士。传教士多系主动到中国来传教,或为此目的而为朝廷服务,康熙帝却主动招揽他们。十一年(1672),令礼部差人前往澳门迎接被说成是精通历法的徐日昇(Tomas Pereira,1645—1708)。二十四年(1685),康熙帝要求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人推荐在澳门的年轻而懂得历法、医术人员,遂有征召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之举*《熙朝定案》,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7页。《〈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含《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昭代钦崇天教至华叙略》《钦命传教约述》和《正教奉褒》五书,下文凡取材于这五书的,简单注作“韩琦校注书”。引文出处间或随文夹注。。二十七年(1688)从江宁府天主堂召苏霖(Jose Suarez,1656—1736)来京使用(韩琦校注书,170页、345页)。同年3月21日,康熙帝接见法国来的洪若翰(洪若,Jean de Fontaney,1643—1710)等五人,赐茶及一百金币,“对中国人而言,此举可谓是极高的礼遇”,并将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留在宫中,“允许其他神父到各省传播我们神圣的教义”,随后李明(Louis-Daniel Le Comte,1655—1728)、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洪若翰去各省传教*[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1卷,郑德弟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69页,下引该书简单注作“书简集”;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页。。
康熙帝招徕传教士,将他们任用于诸多领域。使用南怀仁在钦天监,制定历法,研制观天器械。八年(1669)三月,康熙帝要求南怀仁“负责并制造六个不同种类的欧式的天文仪器”,后者于十二年(1673)制造出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等六件天文观象仪器,重建京师观象台。南怀仁又根据康熙帝指令于十七年(1678)著成《康熙永年历法》(韩琦校注书,第129~137页)。继南怀仁之后,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1638—1712)、徐日昇、安多主持钦天监治历业务。康熙帝任用南怀仁铸造三类不同功能的火炮,用于平定三藩之乱,增强军队装备和对外宣示武力。二十五年(1686),运用红衣炮轰击俄国盘踞的雅克萨(今俄罗斯阿尔巴金诺),摧毁城堡,俄军投降*《清史稿》卷280《郎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4册第10134页。。康熙帝任用西士做通事,在接待外国使臣时充任翻译;尤其是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中,任用徐日昇和张诚为译员,赐参领职衔*韩琦校注书,第170页;[德]莱布尼茨编:《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梅谦立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0页,以下简注作“中国近事”。,他们对《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起到至关重要的交涉(中介)作用。二十五年(1686)派遣闵明我出使西洋(中国近事,第16页)。康熙帝本意可能有两个,一是与俄国交涉,二是在欧洲招徕西士,结果是从西欧带来一批传教士。康熙帝还使用西士参与京城建设,二十四年(1685),康熙帝就京城内城平整道路、疏浚城河之事,指令南怀仁、闵明我测量地形,以便刨挖。南怀仁、闵明我测量后提出工程建议,为康熙帝批准(韩琦校注书,第158~163页)。
对西士的信任,在于康熙帝认为他们忠诚淳朴。二十一年(1682)利类思(Lodovico Buglio,1606—1682)故世前夕,康熙帝夸奖他“老成质朴,素知文翰”,特赐银二百两、缎十匹。南怀仁在二十七年(1688)临终前后,康熙帝称赞他“综理历法,允合天度,监造炮器,有益戎行,奉职勤劳,恪恭匪懈,秉心质朴,始终不渝”,是“有体面人,毫无虚假”。康熙帝褒奖徐日昇“真实而诚悫可信”*韩琦校注书,第127~129页、168页、170页;《中国近事》,第20页。。康熙帝如此嘉许西士心地质朴、忠诚可信,与他认为汉人特别是理学名臣虚伪、言行不一有关。
在处理反教臣民与传教士双方的矛盾时,康熙帝采取中庸策略,维持原定政策中对传教的限制,又睁一眼闭一眼放任传教士传教。在八年(1669)终结历案之时,康熙帝接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议不许传教的建议:南怀仁等照常自行供奉天主外,“直隶各省或复立堂入教,仍着严行晓谕禁止”,“除伊教焚修外,其直隶各省一应人等不许入教”,不得聚会散发《天学传概》、铜像等物。二十六年(1687),南怀仁请求任从民间信仰天主教,礼部、工部会议坚持八年方针,康熙帝允准,同时指示,有的地方官禁止传教,文告中将天主教等同于谋叛的白莲教,说法不妥,应当删去(韩琦校注书,第183~184页、357~358页)。康熙帝一面依旧禁止传教士传教,一面不让地方官将天主教看作邪教,持中庸态度,以安抚反教的官民和争取合法地位的传教士双方。其实这是矛盾的,允许传教士在各省停留,就是默认他们传教。翻译《中国近事》的梅谦立在《译者的话》中说:“一方面,康熙愿意接纳传教士,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西方的知识;另一方面,他不愿意得罪汉族大臣,不肯从官方的角度承认天主教是三教之外的另一个合法的宗教。”(中国近事,第2页)
首次南巡接见传教士。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到济南,差遣侍卫赵昌到天主堂,因传教士汪儒望(汪儒旺、汪汝望,Jean Valat, 1614?—1696)去江南,未遇。十一月到金陵,又差赵昌去天主堂,问济南何以无西洋先生。随后,康熙帝传见汪儒望、毕嘉(Giandomenico Gabiani,1623—1694),传教士献方物四件,康熙帝赐他们青苎、白银,并询问他们姓名、年龄、何时来中华、在江宁几年、用度何来、知否格物穷理之学、身上带没带天主像。毕嘉、汪儒望一一回答。康熙帝离开江宁,道经天主堂前,汪儒望、毕嘉设香案跪送,呈上颂皇恩七言诗。康熙帝览后启行,赵昌让他们给皇上写详细的谢恩信,并由他带给南怀仁等人。十二月初康熙帝回到京城,南怀仁、闵明我在养心殿呈递汪儒望、毕嘉写的感恩信,康熙帝因而问他们某省、某地是否有天主堂,表示对传教士的关怀,令南怀仁感到康熙帝对待传教士“不啻家人父子”!(韩琦校注书,第155~157页、339~340页)在西士眼中,康熙帝把西士看作自家人,不是外人。
看来,康熙帝欣赏西士的为人和特殊技艺,而西士是从西洋传教士中选择的,是以对传教士也另眼看待,故而第一次南巡就主动向他们施放爱惜之意,第二次南巡眷顾他们就不是偶然的了。
二、康熙帝二次南巡优遇传教士与伤害汉臣的两件事
第二次南巡,康熙帝赓续前番施恩传教士的做法,更加公开显示对他们的优容态度,令他们感受传教事业将得到发展的鼓舞;又用传教士传播的天文知识奚落汉大臣与治罪浙江巡抚金,令汉人臣民感到压抑。康熙帝顾惜传教士的情形,不妨先看事实:
事前通知将接见传教士及进行赏赐的物质准备。康熙帝定在二十八年(1689)正月初八日启程,出发前两天,徐日昇、张诚赴内廷请安送行,康熙帝逐一询问巡行将经过地方的传教士姓名及天主堂坐落,并告诉他们会在各地召见教士。同时指示内大臣,“弗忘随带颁赐教士物件”(韩琦校注书,第346页)。徐日昇、张诚得此信息,自然会迅速通知各地传教士早做接驾准备。其实,这可能就是康熙帝向他们预告行程的目的。
南巡途中,凡有传教士的地方,康熙帝都不惜精力地接见传教士,与他们交谈、赏赐和接受贡物,并令侍卫到天主堂行礼。
在济南。康熙帝于正月十五日至济南,传教士柯若瑟(Jose de Osca,1657—1735)跪迎道左,康熙帝执其左手,询问姓名、入华几年、曾否到京。随即令侍卫赵昌、御前一等哈伍至天主堂,宣称“万岁爷命我们来拜叩天主,颁赐银两(二十两)”,柯若瑟请他们“进内厅叙话待茶”。
在杭州。二月初九日康熙帝到达杭州,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在御舟经过的黄金桥迎驾,康熙帝问他入华几年、先在何处、在杭州几年、多大年纪、认识汉字否,又问“京中徐日昇曾有书来么”?洪若翰在南京么?让他不要慌张回答,殷铎泽说“万岁爷是臣等大父母,臣不慌”。随即赐嘉果、异饼、乳酥,康熙帝并说所赐果饼“这里难得”。接谈之后,殷铎泽赶忙回到北关门内的在河道岸边的教堂,跪迎御舟,康熙帝很高兴再次见到他。十一日,赵昌、伍奉命到天主堂送赐银20两,叩拜天主像。殷铎泽随同他们朝见,献方物八种,康熙帝说:“不收他献,老人家心里不安,收玻璃彩球,余着带回。”其时殷铎泽66岁。十七日,康熙帝回銮路经天主堂,殷铎泽第四次见驾,与松江天主堂潘国良(Emanuele Laurifice,1646—1703)共同跪送。康熙帝没有见过潘国良,问是谁。潘国良回称,本来是到苏州接驾,路上遇阻,没有赶上,追到杭州迎驾。康熙帝问他何时入华、先在何处,松江有天主堂吗?同谁一起来中国的?潘国良回答来了18年,先后去过广东、松江、绛州,回到松江,现年43岁。潘国良可能一时想不起和谁同来中国的,殷铎泽代答,是与广东天主堂方济各同来的。康熙帝即赏赐潘国良银子20两。康熙帝问他们打算送驾到哪里,回称到苏州,康熙帝对殷铎泽说:“送君千里终须别,老人家好好住在这里。”接着侍卫传旨:“万岁爷命老人家好好安心住在这里。”殷铎泽就不再远送了。
在苏州。十九日,从杭州尾随御舟的潘国良到苏州,趋朝谢恩,献方物六种。康熙帝觉得人家是从大西洋带过来的物件,不收不好,让呈上过目,收小千里镜、照面镜、玻璃瓶,潘国良叩谢退出。二十二日康熙帝离开苏州,潘国良随同百官在枫桥西跪送。康熙帝将潘国良召至御舟近旁,再次问他年龄、到中国几年、曾住何处、到过北京没有,并赐乳酥、嘉果。潘国良谢恩:“蒙圣恩宠锡,臣不能仰报万一,只求天主保佑万岁爷永永荣福。”康熙帝问他是否认识汉字,是否读过汉书,会说松江话吗?得到肯定回答。康熙帝要他“回去好好住着”。
在江宁。二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到江宁。毕嘉、洪若翰在上方桥迎驾,康熙帝“仁慈地停了下来,并以世界上最客气的方式和我们交谈。皇帝骑在马上,后面跟着他的侍卫和二至三千骑兵”。康熙帝问“毕嘉你好么”?因大雨,让他们赶快回去。次日清早,二人至行宫请安,传旨问“你们都好么”?二十七日御前一等哈邬、侍卫赵昌至天主堂,先叩拜天主,次宣读上谕,赏赐银两。赵昌说:“万岁爷一路来,凡遇西洋先生,俱待得甚好。”邬、赵昌吃饭后离去。中午,毕嘉、洪若翰赴行宫献方物12种,因毕嘉说内有各省西洋人的,康熙帝本意只收两件,故多收四件;其中验气管二架,康熙帝让他们自行送至京师。毕嘉、洪若翰回堂不久,赵昌到天主堂,奉旨问:“南极老人星江宁可能见否?出广东地平几度?江宁几度?”他们回答完毕,赵昌“即飞马复旨”。毕嘉、洪若翰因匆遽回答,恐难以详悉,至晚戌初(19时)观看天象,验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数,详察明白,另具一册,于二十八日早晨送入行宫。康熙帝与毕嘉、洪若翰的频繁接触,正如洪若翰所说:“皇帝停留南京,我们每天前往行宫,他也每日派遣一到两名侍卫来看我们。”三月初一日,康熙帝临行,差赵昌、邬送三盘食物到天主堂,在天主台前摆设,并说这是蒙古王进贡的,不是平常物件。又传旨意:“不必往行宫谢恩,就在天主台谢恩罢了。”随后毕嘉、洪若翰乘船,先到扬州湾头恭候圣驾。初五日御舟到湾头,毕嘉、洪若翰迎驾。康熙帝命他们的小船靠近御舟,问江浪大,怎么渡江的,为何比御舟快,为什么要来此?回称为避开风浪,不走瓜洲闸口,从仪真(仪征)过来的,为的是感谢皇帝洪恩,特来送驾。康熙帝高兴,从御桌上撤出四样食品赐给他们。又让他们上御舟,靠近皇帝交谈。康熙帝问毕嘉,你看朕摆设的书架可好?回说好;康熙帝说毕嘉67岁了,那么洪若翰呢?毕嘉代答45岁。康熙帝说让他自己回答,是时洪若翰华语欠佳,勉强学说了,康熙帝笑着道“还说不来”。另问扬州有无天主堂,毕嘉告知扬州、镇江、淮安均有天主堂,但无传教士,由他照管。这时岸边有臣子奏事,康熙帝一一下了指示,并不在意让毕嘉等听见,还问刚才所下旨意好不好,回说都好。这样不知不觉船行15里,康熙帝乃命赵昌送二人换船回返,他们不忍离去,康熙帝说你们送得很远了,回去吧。
在济宁。三月十一日康熙帝龙舟至济宁石佛闸、天井闸,传教士利安宁(Manuel de San Juan Bautista,1656—1711)迎驾。康熙帝召见,问姓名字号、哪国人、西洋原名、来中华几年、年纪以及会否天文、医学与满语、汉语,利安宁一一作答,谓自幼习格物穷理,略知历法,在济宁无人教满语,所以不会。康熙帝当即赐御果四盘。接着,康熙帝令赵昌等人到天主堂瞻礼圣像,赐银20两。利安宁献西洋方物四种,康熙帝赏收水晶瓶一对,并且说收一件就如同全部接受了*以上康熙帝在各地与传教士的往还,俱见韩琦校注书第171~181页、346~351页;书简集第275~277页。。
毕嘉进京献宝。康熙帝在江宁留下话,毕嘉当作头等大事来做,当年(二十八年,1689)四月十五日就把验气管送到京中,故《耶稣会毕先生碑记》云“己巳,赍验气仪赴京”*韩琦校注书,第414页。《熙朝定案》《正教奉褒》则将毕嘉进京献宝的时间写作“康熙二十九年孟夏十五日”、“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韩琦校注书,第179页、353页),都说康熙帝离开江宁已经一年一个多月了,毕嘉才送宝到京,岂不太懈怠了!敢对康熙帝这样吗!是以笔者采《耶稣会毕先生碑记》“己巳”说,认定在二次南巡的当年四月,即康熙帝离开江宁一个多月,毕嘉就赶到京城。。康熙帝以他是“朕前之人”,不必像外臣那样等候引见,十七日就由赵昌、徐日昇引见。康熙帝问“一路来可辛苦么”,“江宁等处地方官何如”,今年收成如何?路上来河里有水吗?回答:水浅,坐船到济宁,“舟行最难,臣恐延迟日期,是以从济宁起旱来的”。接着问:洪若翰、殷铎泽、潘国良好吗?由于奏对时间长,特赐茶饭。到了十月,天寒,康熙帝赐毕嘉貂皮套袍、冠各一件。三十年(1691)正月上元日,召毕嘉、徐日昇等畅春园赴宴,观看杂剧烟灯*召毕嘉等畅春园赴宴、观看杂剧烟灯事,《熙朝定案》《正教奉褒》均系于康熙三十年上元日(韩琦校注书,第180页、354页)。据《耶稣会毕先生碑记》,毕嘉于“己巳”四月到京、“辛未”(康熙三十年)离京(韩琦校注书第415页),则他有可能在北京度过了康熙二十九年、三十年两个上元日。是仅三十年上元日还是两个上元日均受召赴宴,从笔者所见史料看难以确定。。三月十八日康熙帝圣诞,毕嘉、徐日昇等至畅春园贺寿。四月十一日,毕嘉请假回南养病,康熙帝关照他,要他过了炎热的夏天,秋后再走,毕嘉仍要求南行,康熙帝对他说:“尔系老年人,行止听尔自便,前去路上宜小心,保重身体要紧。”又对众臣说:“今毕嘉年纪虽老,耳目尚健,汉话通明,惜乎牙齿没有了。”又说:“尔回江南好好保养,勿负朕谆爱至意。”(韩琦校注书,第179~181页、353~355页)
由以上叙述可见,康熙帝南巡途中与各地传教士过从以及在宫中接待毕嘉,总括起来有这么几个特点:
其一,不惮其烦地会面,亲切交谈。所到处多次接见传教士,在江河舟行之中,将传教士小船召近御舟,或将传教士召进御舟,几乎是促膝交谈;在道路上勒马接谈;在行宫相见,或令侍卫传话。一个人多次会见,少则两次,多则四五次,还派遣侍卫去天主堂传话,询问事情。
其二,礼尚往来。派遣内侍教堂行礼,赏赐银两和珍稀食品,所赐银子各地标准相同,均为20两,以示一视同仁。传教士敬献方物,中国人的习惯是不能全部接受,康熙帝是依据献物人情况选受两三件,至多六件,表示赏收,给献纳者面子。
其三,公开示好。康熙帝南巡之时,所经过地方的官员、邻近省区的督抚都要到行在朝见,康熙帝频繁、亲切地会见传教士,真可以说是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的,传教士感到荣耀,倒不一定是世俗的荣誉感,而主要是从中体会到皇帝让他们好好在地方居住,是向地方官员暗示允许传教,可能会令各地官员改变对传教士不友好或冷漠的态度,对他们传教大为有利。如同徐日昇、安多在三十年(1691)十二月十六日题本所说:“皇上南巡,凡遇西洋之人,俱颁温旨教训,容留之处,众咸闻知。”(韩琦校注书,第182页)又如中途参加第三次南巡的白晋所说:康熙帝延见各地传教士,“他要以这些公开表示让人看到他至高无上的关怀以及对所有传教士的重视,并以此表明允许他们在帝国各省传教”(书简集,第148页)。他们理解,众人都知道康熙帝优遇传教士,都是尊崇皇帝的,皇帝的态度明朗,众人当然要礼遇传教士;如此,传教事务就好做了,就会顺利。
二次南巡中康熙帝对传教士热情的同时,却对汉人大臣做出两件不愉快的事情,一是突然考察汉臣天文学知识,搞得他们狼狈不堪;另一件事是问罪浙江巡抚金。
考察天文知识的事,徐海松、吴伯娅均有论述*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37~241页;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绪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6页。,拙文《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及其原因试析》亦述及。前面说到康熙帝在二月二十五日到江宁,连续面见毕嘉、洪若翰,特地派遣赵昌去教堂询问老人星的事,其实就是为对汉大臣进行突然袭击——考核天文知识。这里引出《圣祖仁皇帝实录》的记载,以明了事情的梗概:二十七日傍晚,康熙帝至观星台,“召部院诸臣,问汉臣中有知天文者否?皆奏曰臣等未能通晓。乃问掌院学士李光地,尔所识星宿几何?李光地奏曰:二十八宿臣尚不能尽识。上因令指其所知者。又问古历觜参,今为参觜,其理云何?李光地奏曰,此理臣殊未晓。上曰,以观星台仪器测之,参宿至天中,确在觜宿之先,观此足信今历之不误矣。又问尧时中星,今移几度?李光地奏曰,据先儒言,已差五十余度。上又问恒星动否?李光地奏曰,臣不能知,惟新历言恒星天亦动,但其动微耳。上曰,郭守敬仪器不可行于今,由不知恒星天动故也。自来史志历法,多不可信,质之以理,类空言无实。如荧惑退舍之说,天象垂戒,理则有之,若果退舍,后来推算者,以何积算?上又历指三垣星座,问李光地,不能尽举其名。上指示从官,历历明析,尚书张玉书、图纳等奏曰,皇上聪明天纵,观文察理,诚非愚臣等所能仰窥也。上又披小星图,按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谕诸臣曰,此老人星也。李光地奏曰,据史传,谓老人星见,天下仁寿之征。上曰,以北极度推之,江宁合见是星,此岂有隐见也!”*《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39,二月乙丑条,《清实录》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6~527页。事情中有四点值得留意,一是康熙帝专门考问汉大臣天文学知识,不问及其他民族的大臣,又是突然召见询问,应当说他的目的就是让汉臣措手不及,出乖露丑。二是汉大臣果然被考倒了,翰林院掌院学士李光地应当是最有学问者之一,对所有的问题都不能全面回答,或全无所知,或答复中有谬误,被康熙帝指斥,颜面扫地。“实录”里没有提到原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兵部尚书张玉书,其实他也被问得哑口无言*关于江宁观星台考察汉大臣学问之事的记载,实录之外有:《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43~1844页;书简集,第276页;韩琦校注书,第175~176页;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4《本朝时事》,《榕村语录 榕村续语录》,陈祖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43页。。三是康熙帝的天文学知识得自西士,在南京又临时学到一些,立即用来奚落汉大臣。四是康熙帝强调他在八年(1669)正月颁布的时宪历准确,故云“足信今历之不误”。李光地也用“新历”回答恒星是否运动的问题,可见新历——时宪历不仅皇帝看重,它的知识亦引起汉臣的留心。总之,康熙帝显示了天纵圣明,远远超过富有文化知识的汉臣,曲折反映出满人文化自卑而又试图令汉人在文化上屈服于满人的心态,其武器则是西洋科学知识。
三、浙江禁教的发生与状况
康熙三十年(1691)七月十六日,浙江巡抚张鹏翮支持临安知县禁教,发出全省禁教令。在说明其执行过程及结局之前,需要明了它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禁教发生的背景
传教士在浙江活动频繁,吸收了不少信徒,坚持宗教生活;培养出一些华人笃信者,协助其传播宗教;教徒中不少士人,影响甚大。浙江是儒学重地,历来文风很盛,反对天主教势力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儒学与天主教针锋相对,势必出现水火不容的斗争,乃有禁教的发生。
1.天主教在浙江的活动能量甚大。
(1)“圣教三柱石”反映出明清之际天主教在浙江立足与发展。
明末有“圣教三柱石”之说,“三柱石”是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71—1630)和杨廷筠(1562—1627),徐光启系南直隶松江上海人,李之藻和杨廷筠均为浙江杭州仁和人,都是江浙人,而杭州有其二。李之藻,万历进士,三十八年(1610)信教,四十一年(1613)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合作编译《同文算指》,协助徐光启修撰《崇祯历法》。撰文《读景教碑书后》,说明明代天主教与唐代景教一脉相传,不应怀疑天主教教义及其正当性(韩琦校注书,第11~13页)。杨廷筠,官苏松巡按御史,原先对佛学有兴趣,后与李之藻、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郭居静(Cattaneo,1560—1640)往还,特别是见到李之藻之父采用天主教葬礼,遂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入教,著《代疑编》《代疑续编》《圣水纪言》《天释明辨》,为天主教辩白。
三柱石均同传教士过从甚密,明末清初在江浙的传教士甚多。金尼阁万历三十九年(1611)到杭州传教,后去罗马,返回后于天启二年(1622)再度来到杭州,并于崇祯元年(1628)病逝于此*[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80~681页,下引该书简单注作“荣振华书”。参阅[比利时]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序言一(韩德力),赵殿红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3页,下引该书简单注作“鲁日满账本”。。艾儒略在去过北京、南京等地后,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到杭州传教,为250人举行洗礼(荣振华书,第12页)。接着邓玉函(Johann Terrenz,1576—1630)于天启元年(1621)到杭州进行传教活动(荣振华书,第603页)。在金尼阁到达前夕,中国广东新会人、助理修士钟鸣仁已在浙江传教,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在杭州建立教堂,并于天启元年(1621)故世此地(荣振华书,第216~217页)。他的幼弟、助理修士钟鸣礼亦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到杭州活动(荣振华书,第213页)。
传教士在浙江吸收教徒,建立教堂。在17世纪上半叶,天主教教堂散布于浙江八个府的府城、县城、村镇(表1)。
顺治十七年(1660),多年在浙江传教的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在杭州城北关门内兴建教堂*卫匡国,崇祯十六年(1643)到达杭州,随后去上海、浙江遂安,顺治三年(1646)在宁波,五年(1648)为杭州住院会长,后回欧洲,顺治十六年(1659)重返杭州,兴建教堂,十八年(1661)卒于杭州。见荣振华书第411~412页。,康熙二年(1663)在洪度贞(Humbert Augery,1616—1673)主持下竣工落成(荣振华书,第40页)。该堂建筑规模大,可以容纳众多传教士居停,有花园,特建房舍,专门储存传教士印刷天主教书籍的刻版。教堂内悬挂图画七十二帧,描绘天主教圣人和主要人物。所以白晋说它“因建筑结构和堂内绘画而被视为中国最美之教堂”(书简集,第149页)。这所教堂就是前述殷铎泽迎接康熙帝,以及赵昌进入行礼的地方。它是江浙教会中心,苏州、松江、上海、常熟、嘉兴、崇明的耶稣会院都隶属于它(鲁日满账本,第176~177页)。

表1 天主教浙江早期教堂表
注:***荣振华书第855页云“遂州于1615年”建立教堂,然浙江无遂州;而该书第411页又说卫匡国于1643年到杭州,后来去遂安县、宁波,返回杭州。由此笔者认为“遂州”系“遂安”之误。遂安,今淳安,属杭州市。**荣振华书,第855页。*荣振华书,第411页;鲁日满账本,第176页。
(2)历案透露出浙江天主教拥有巨大的潜在力量。
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教案中,仅剩下江西、杭州两个住院,而后者还在秘密地向北京、河南、陕西、湖广、南京、广州和上海传教(荣振华书,第841~842页)。康熙四年(1665)历案,或被称作“历狱”,一部分传教士被囚禁北京,甚至将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判处死刑(未执行),25名传教士禁闭在广州。而浙江传教区竟然继续活动,扩及东南、中南、西北和京城,潜在能量甚大。在禁闭广州的25人中,洪度贞、闵明我、费里白、白道明四人是在浙江传教的,张玛诺(Jorge,1621—1677)、鲁日满(Francois de Rougemont,1624—1676)、毕嘉、潘国光(Francesco Brancati,1607—1671)、刘迪我(Jacques le Favre,1613—1675)、成际理(Felicien Pacheco,1622—1686)、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七人活动于江南,其他几省一、二、三人不等*韩琦校注书,第398~399页;荣振华书,第842~843页。,江浙传教士几乎占了一半,人多,传教力量大。而且在江浙的传教士互相配合,往往一人在两省传教,如鲁日满,顺治十五年(1658)到澳门,而后在杭州住了一年,康熙二年(1663)起常驻常熟(荣振华书,第576~578页),以此为基地,不时到杭州布道(下文将说到他在杭州传教的情形)。
2.浙江士民奉教者众多而坚定。
(1)传教士与传道员、笃信者。
殷铎泽,顺治末年康熙初年(1660—1665)在江西传教,历案中先后被解送北京、广州,康熙十年(1671)回到罗马,次年撰著的《中国人的学问》在泰弗内编辑的杂志发表(中国近事,第160~161页),康熙十三年(1674)重返中国,没有根据八年(1669)规定居住江西,却居停杭州,接替已故洪度贞衣钵,为一千余人施洗。为宣讲教义,刊刻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的《七克》*《四库全书》收入天主教书籍三种,《七克》为其一。,以及其他教会书籍,绘画天主像,传播天主教日历,组织教徒在教会节日举行弥撒等活动(中国近事,第23页)。他训练出传教助手,当二十六年(1687)洪若翰等五人在暹罗乘坐中国商船到达宁波后遇到被遣返的困境,时任耶稣会在华副会长的殷铎泽特地派遣“手下的讲授者之一”(此人是天主教会法学院毕业生,同行的还有他的两位佣人)到宁波,帮助他们解决难题,殷铎泽特意指点洪若翰如何同中国官员打交道(书简集,第262页)。讲授者,即传道员,协助传教士向对天主教有兴趣的民众讲解教义,从中吸收信徒。前往宁波的传道员,更是为帮助洪若翰等人谋求进京之路,超出一般的传教业务。教会是要支付传道员生活费的,因此传道员不可能太多,但殷铎泽有数名传道员。鲁日满于康熙十四年(1675)春夏间、秋冬间两次到杭州、嘉兴活动,为一些人施洗,如在嘉兴,为Catharina施洗,她是Maurus Ch’in Chum Yu的儿媳,Fam Stanislaus的妻子是她的代母。又为Paulus举行洗礼,此人是Fam Stanislaus的父亲,Paulus的代父是Maurus Ch’in Chum Yu。另外在“著名的村庄”朱家角为Joseph Vam Cin K’im施洗,他的代父是Tai Hien K’im。鲁日满在杭州有传道员和司事,如传道员Fam Pe Kin,司事Cum(Kum) Paulus,Ho Co Fan,大相公Yam,相公(助理传道员)Yan,对不同年龄、职业教徒的团体予以辅导。鲁日满在杭州掌管教会三栋房屋,收取房租。他同排字、印刷工匠打交道,刻印教理文献和传教材料,如使用几两银子刻印《主制群证》,此书即“天主统治世界的许多证据”。鲁日满付给杭州传教员和有关人员生活费,如一次付给Ho Co Fan 一两三钱银子;Cum(Kum) Paulus为鲁日满经管房屋租赁,鲁日满定期给他一百文。诸际南是杭州有名文人、教徒,鲁日满的账本记录:“给大文人诸际南的小儿子一些钱,作为一种救济金:0.100两。”鲁日满在杭州收取信徒布施,大相公Yam的姐姐Yao大娘给四两银子礼物,Yam太太给银一两八钱,Yam老爷给六钱及一两路费,Yam大相公的妻子Maria送给许愿天主的银子十两,Maria的小妹妹Yao娘娘同样给银子,Yam大相公给银四两,Hoam赠送约一两七钱*鲁日满账本,第117页、120页、125页、148页、151页、152页、178页、189页、190页、211页、212页、214页、215页、322页、350页、352页、364页。。由鲁日满施洗的教徒和布施的人群来看,他(她)们往往是一家人或者是姻亲,或者是一个家族的成员,朱家角大约是教徒聚居地。此外江西建昌人万其渊(1631—1700)神父,康熙二十七年(1688)在南京领受神父神品,并在浙江传教(荣振华书,第51~52页)。他可能是殷铎泽或鲁日满下属的神职人员。
由布施情形可知,教徒中有一批虔诚者。他们不仅仅是自家信仰,还宣传、捍卫天主教及其教义。教徒Hum Cie min(Hung Chi-Min)在二十六年(1687)前后写作《辟妄》,与反对天主教的常熟人、佛教和尚Chieh辩论。杭州教徒冯研祥(冯文昌),别号吴越遗民,是藏书家,修订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65—1655)的《圣约瑟夫行实》、南怀仁的《温计图说》(鲁日满账本,第212页、253~254页)。
从“三柱石”起,到冯研祥、Hum Cie min,或为进士,或普通人,但在教徒中有一批各种层级的文士,他们对天主教信仰弥笃,能够为捍卫天主教出力,因为社会地位较高,颇能左右民众对天主教的态度,追随他们信教,就连杨廷筠都是受李之藻父子的影响,更不必说一般平民了。他们是浙江天主教的中坚力量。
(2)信徒宗教生活。
教徒的宗教生活离不开教堂,杭州不仅有北关门内的教堂,城外还有一些小教堂,另有一座小圣母堂。
杭州教会内部有善会组织——教徒的协会,是小群体,有几种类型,如儒会,是文人教徒团体,可能也吸收非教徒参加活动。聚会时,教堂有点心供应;教堂购买书籍,供文人共同使用。又如天神会,由教会付钱给工匠制作一些念珠,提供其成员使用。女信徒由女传道员带领在小圣母堂进行宗教庆祝,每年会有几次集会*鲁日满账本,第118页、125页、134页、177页。。
教徒按照传教士制定的教会年历和瞻礼单过宗教生活。在江南的传教士柏应理、鲁日满分别制作中国教会礼仪年历和瞻礼单,开列教会节日,供教友使用。此种年历在江南流通,商人得知某日为天主教某节,因应做生意牟利。教堂据以组织宗教活动,从圣诞节开始,而后是天主教的其他重要节日,届时信徒到教堂做弥撒,做告解。传教士则忙于听告解,会客,送圣像(鲁日满账本,第299~304页)。
3.儒家文化重镇浙江反对天主教的力量雄厚。
标题所示,笔者限于条件未曾为撰写本文阅览浙江地方志和有关人物的文集*应该阅读浙江省通志及有关府州县镇志,以及当事人张鹏翮文集,虽有客观原因未能如愿,然亦不能消释笔者愧疚感。,没有多少史料支持,因而有想当然的成分。而还要这么说,乃因浙江是人文荟萃大省,系儒家文化重镇*清朝科举鼎甲,尤其是状元,多出在苏松常杭嘉湖。,儒士中尽管有笃信天主教者,但反对者亦必众多,反对势力亦必强大,否则就不会有张鹏翮的禁教。而在执行雍正朝驱逐传教士政策中,浙江巡抚李卫又是一位强有力者。他说西洋人传教,以金钱引诱中国人,许多人暗中入教,现在虽无大害,但应禁革。他将传教士马德诺遣送澳门,把杭州天主堂改为天后宫*《朱批御制·李卫奏折》,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八日折、八年五月初二日折,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缩印本;参阅拙作《雍正传》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一目“驱逐传教士于澳门、广州”,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4页。。应当说两位浙抚的行为反映了反教者的强烈愿望。
在张鹏翮禁教之前,浙江有不满传教士传教的士人,出现过反教活动,张鹏翮的前任金亦为反教者。康熙十四年(1675)冬天,嘉兴地区发生对教徒不利行为,情况还较为严重,所以教徒Fam tie跑到常熟报告鲁日满,希望得到救援(鲁日满账本,第177~178页)。事情表明当地有信教与反教两种力量进行针锋相对的争斗。杭州士人陆次云对天主教抱持欣赏与厌恶交织态度,他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撰著《八纮译史》的《例言》中,一面说西洋人为“西域奇人,梯航异国”,一面说他们的《职方外史》一书“令人闻所未闻”,但“处处阐明彼教,听倦言繁”*陆次云:《八纮译史·例言》,“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陆次云谓传教士为奇人,是惊异他们的数万里远航和科学技术,而讨厌他们传教,厌弃他们宣扬的教义。杭州仁和人应谦,是很有名气的大学者,又有汉民族气节,拒绝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宏词之征,浙抚赵士麟为他刻印《性理》,他是反对天主教的*参阅肖清河《辟佛老,知真儒:张星曜与〈历代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天学总函:汉语基督教文献集成”,http://site.douban.com/178384/widget/forum/10128950/discussion/48360590/。。而到康熙三十年代,另一位杭州人郁永和在所著《稗海纪游》的《海上纪略·西洋国》里,则视天主教为“邪说”,“诱人入其教中,中国人士被惑,多皈其教者”*转引自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第204页。,深为痛心。他的写作在张鹏翮禁教、容教令颁布之后,这里不必多说。前面说过洪若翰等人到宁波,要求进京,殷铎泽派遣传道员去救助,事情是洪若翰等人向宁波地方官提出申请,地方官表示同情,允许他们在当地置买房屋,报告到省城,巡抚金持反对态度,责备宁波官员允许买房,并报礼部,要求禁止中国商船从邻国携带西洋人到中国,倘若到来就应遣返。所以西士苏霖说他是“憎恨天主教”者;当事人洪若翰说此人“对我们的宗教深恶痛绝”*《中国近事》,第20页;书简集,第262页。。另一个当事人白晋同样说,“浙江总督强烈声称反对天主教,千方百计地想把我们撵走”(中国近事,第65页)。西士异口同声地指责金憎恨传教士,倒说明他强烈反对天主教传入中国,不允许传教士在浙江停留的态度。当然,最后是康熙帝允许他们进京。看来,在浙江官民中不满、反对天主教的不乏其人。
(二)张鹏翮禁教
康熙三十年(1691),杭州府临安县知县发布告示,以天主教为邪教,予以禁止。县令的布告是用木刻版印刷的*《中国近事》第22页:“通告刻于木板,公开示众。”,必是多处张贴,令众人知晓,显示事情的严肃性,必须认真执行。殷铎泽认为这个知县对天主教完全无知,而且违反康熙帝的有关诏令。显然他是通过某种途径表示反对知县行为,知县感到压力,向巡抚张鹏翮报告,张鹏翮支持这位属员,于七月十六日发出全省禁教的通告,并将告示张贴在教堂门上。张鹏翮的告示宣布,禁止传教士在全省传教和民人信教,特别指出殷铎泽违反皇帝诏令传播邪教,应受严厉惩罚,信教者必须改邪归正,勉力遵循儒家之道和按照皇帝颁布的上谕十六条做人行事。具体地说:(1)张鹏翮使用康熙八年诏令指斥殷铎泽抗旨传教。张鹏翮引述本文第一节说到的康熙帝允许在华西洋人信教,但不得传教的谕旨——“直隶各省或复立堂入教,仍着严行晓谕禁止。”“除伊教焚修外,其直隶各省一应人等不许入教。”文告说禁止传教法令早已公布,载在礼部法规中。按照规定,传教士在历案以前居停何处,仍回原地,可是殷铎泽原先是住在江西的,违法来到浙江,又违抗圣旨制造与散播天主教读物,招揽信徒一千多名,如此罪行,不得不对他进行惩治。(2)禁教是给愚民信徒一个改邪归正的机会。文告对选择信教的士民表示惋惜,张鹏翮深知天主教在士民中的影响力,跟着一个外来宗教走,由来已久,有鉴于此给他们一个改正的机会,为此各州县清查教徒,教育他们脱离天主教,严格惩治不听劝告的信徒。(3)倡扬儒家之道,比较佛道与天主教,以天主教为邪教,说明禁教的正当性,令百姓摆脱天主教的影响。张鹏翮强调儒家伦理是治国之本,臣民必须恪守仁义孝悌之道,尽忠尽孝,士农工商各行各业都要铭记、践履皇帝在九年(1670)颁布的上谕十六条,教导无知者顺应天理,服从天命,做讲究伦常的正人。张鹏翮还将道教、佛教与儒学比较,认为佛道不过是小火炬,哪里能像儒学照亮人生前进道路;又进一步比较天主教与佛道,认为天主教还不如佛道,是邪教,意图让人从思想上摆脱天主教的影响*张鹏翮文告,见《中国近事》第22~24页,书简集第281页,《洋教士看中国朝廷》第42页。。张鹏翮文告没有对十六条展开说明,其中第七条“黜异端以崇正学”*见《圣祖仁皇帝实录》卷34,十月癸巳条,《清实录》第4册,第461页;又见《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2《敕谕·谕礼部》,《四库全书》本。正是张鹏翮所应用的思想武器。
发布告示,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禁教具体行动。(1)针对天主教和传教士。将告示贴在教堂门上,封闭教堂,没收作为官府的公用建筑,或者用作中国人信仰的祭祀场所,甚而意欲拆毁教堂;将殷铎泽传到衙门,质问他原先居住江西,“是如何获准在(杭州)城内居住的”?(书简集,第281页)这当然使殷铎泽感到非常难堪,是对他的羞辱和折磨;同时官方对其他传教士也进行质问,甚至要驱逐出省;教堂里的许多天主教书籍和各种圣像被焚毁。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官方虽然传问殷铎泽,但是并没有控制他,他仍然有行动自由,能够给京城西士写信求助,所以对他做法上是有分寸的,有节制的。(2)针对教徒。据殷铎泽给洪若翰的信中说,禁教中,“最让我悲痛的是……人们对我的可怜的基督徒施行的暴力;人们抢劫他们的钱财,进入他们的住宅,虐待他们,扔掉他们的圣像,使他们整日不得安宁”(书简集,第281页)。苏霖得知的信息是:教徒“有的被关押,有的被抢掠”(中国近事,第24页)。无疑,浙江官方强令教徒退教,殴打信徒,甚至把一些人逮捕关押,毁坏他们的宗教信仰用品,如十字架、书籍、画像等物。在这个过程中,不法差役和地方不良分子抢夺教徒的财物。
浙江禁教,随着容教令的出台而结束。但在容教令制订过程中,礼部于三十一年(1692)正月二十日上题本,建议下令停止浙江禁教,二十三日康熙帝批准。至此,浙江禁教已是不了了之。
四、容教令的制订
容教令的产生,有着三部曲的过程,首先是朝内西士、朝外传教士的活动与意图私下解决;第二部是礼部坚持不许传教的旧章与西士希图借机达到全面开禁;第三部为康熙帝撇开汉臣、使用满臣制订容教令。
浙江禁教,殷铎泽当即写信给徐日昇、安多求助,差人送到北京,信中说浙江巡抚以天主教为邪教,欲将教堂拆毁,驱逐西洋人。徐日昇等于九月见信,同时期,南京的毕嘉亦将浙江之事通知张诚。徐日昇、张诚因在《尼布楚条约》签订过程中与清朝首席代表、康熙帝叔舅公索额图(?—1703)建立了友情,后者表示过以后会帮助他们,这时徐日昇找到索额图,索额图即写信给张鹏翮,希望他停止禁教。可能是张鹏翮不买他的账,没有给他答复,致使西士希望私下了结的愿望落空,转而直接请求康熙帝出面制止张鹏翮禁教。
康熙帝为使事情赶快解决,开始设想让人私下游说张鹏翮撤回文告,绕过礼部,免得公文往还,耗费时日。但是,这时徐日昇等人改变主意,以为这样做的话,浙江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以后再出现类似的事情怎么办?不如一劳永逸,请求皇帝通过礼部的公文手续,撤销原先禁止传教的法令,改为允许传教,中国人自由信教*一些教士认为:“应当对簿公堂,因为,除非禁教诏令被撤销,否则迫害会天天发生,我们哪里好意思常常麻烦皇上。”《中国近事》,第26页。。徐日昇、安多遂于十二月十六日以“钦天监治理历法臣”的名义给康熙帝上题本,讲述西士治历、造炮、出使诸方面劳绩,而遭到攻击,使得殷铎泽无容身之地,“臣等孤子无可依之人”,唯愿皇上“将臣等无私可矜之处,察明施行”。走正常程序,题本经由通政司上呈,康熙帝也因徐日昇等人的私下当面求情,将题本发交礼部议奏。立即有御史弹劾徐日昇、安多,指责传教士不当给皇帝上这样的题本,反对允许传教。礼部于三十一年(1692)正月二十日议复,搬出康熙八年、二十六年禁止传教的条文,坚持不许传教的旧章,唯因二十六年诏令中有地方官不得将天主教与白莲教谋叛相提并论的内容,以此通知浙江巡抚。在此之前,西士预计到走正式程序,题本“会回到汉族文官的手上”,“再次为礼部公布禁教法令提供可乘之机”(中国近事,第26页)。事情果然如此。
康熙帝立意允许传教,二十三日召见内阁成员,对礼部坚持禁教大为不满。恰在此时,康熙帝意欲从澳门招徕医生庐依道(Isodoro Lucci,1661—1719),令一位西士与官员共同迎接。但是西士表示不能应命,因为浙江的事使他们感到羞辱,无脸到澳门去见西人。此事刺激康熙帝加速解决允许传教的事务,二十六日召见大学士,告诫他们不得禁止天主教。康熙帝说,“在他们的宗教里,我们找不到什么不好。我们应让其自由传播”。正月三十日,康熙帝令撤销原先的禁止传教诏令。二月初二日上谕,说明西洋人有三个劳绩,将他们信奉的天主教视为邪教予以禁止是无辜的。特派索额图到内阁说明皇帝态度,并指示只命满大臣、满学士与议,即排除汉大臣参议资格,免得他们反对。索额图乃说他认为天主教是“圣善”的宗教,“崇拜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服从皇上与长上,孝敬父母,不发虚誓,毋杀人,毋贪求他人之妻。这就是他们所信奉的。我的部下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对其信条恪守不渝”。有的官员提出疑问,“在如此历史悠久的光辉帝国,接受一种外来的宗教乃是一种羞辱”。索额图辩解说,“为什么全帝国乐意吸收历法、火炮与其他艺术品?智慧就是求事实,不管是从外面或其他什么国家来的”。又有人担心,“如果容许天主教,天下百姓很快就会归附它”。索额图回应说,若都信教,“那盗窃、淫乱、反叛都会停止”。初三日各衙门会议,则有汉人参与。与满人礼部尚书顾八代共同会议的有:尚书熊赐履、左侍郎席尔达、左侍郎王飏昌、右侍郎多奇、右侍郎王泽弘、大学士吏部尚书伊桑阿、大学士吏部尚书阿兰泰、大学士礼部尚书王熙、大学士户部尚书张玉书、礼部侍郎满丕和思格则等人。当天礼部正式写出遵旨会题呈文,允许西人传教和百姓信教。初五日奉旨批准,容教令产生*容教令产生过程的史料,见《中国近事》第24~36页,韩琦校注书第183~186页、356~359页,书简集第281~284页,《洋教士看中国朝廷》第42~44页。。随后礼部通告各省施行。
关于容教令的内容,时彦多有论述,拙文《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文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亦有涉及,本文仅交代徐日昇、安多题本与容教令两者在内容上的雷同,至于它的贯彻、在中国天主教史上的意义诸事,则不再着墨。题本云:“(南怀仁)西洋所习各项书籍,历法本源、算法律吕之本、格物等书,在内廷纂修二十余年,至今尚未告竣。……若以为邪教,不足以取信,何以自顺治初年以至今日,命先臣制造军器,臣闵明我持兵部印文,泛海差往俄罗斯,臣徐日昇、张诚赐参领职衔,差往俄罗斯二次乎?”*韩琦校注书,182页;中国近事,第28~29页。容教令实际上包括康熙帝谕旨和礼部文书两部分,康熙帝上谕:“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器,效力勤劳,近随征阿罗素,亦有劳绩,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将伊等之教目为邪教禁止,殊属无辜,尔内阁会同礼部议奏。”礼部等衙门会议得:“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阿罗素,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有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作乱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抄写得西洋堂内康熙三十一年碑文》,原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引文见冯明珠主编《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第128~129页;另见冯明珠《坚持与容忍——档案中所见康熙皇帝对中梵关系生变的因应》,收入辅仁大学历史系编《中梵外交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第167页。其他多种文献记录了容教令内容,不再一一列出。西士题本与朝廷容教令共同肯定西士的治历、铸炮、出使三种业绩,都说不应当视天主教为叛逆邪教。题本出现在先,容教令在后,笔者的意思倒不是将题本视作容教令的蓝本,而是说朝廷和西士对西士的功绩及天主教不是叛逆的见解完全一致。
康熙帝解决浙江禁教事端,不是就事论事,也不为指斥张鹏翮及浙江官员,强令他们撤回禁教布告,而是首先撤除八年、二十六年禁止传教、信教的诏令,又顺理成章地在全国范围允许传教,允许信教。
五、余论:从中国天主教史看康熙帝政治
本文主要内容大致陈述如此,意犹未尽,思索天主教传教何以如此波折,皇帝诏令究竟对其传播有多大价值:皇帝优待传教士,地方臣民禁止传教,皇帝干脆允许传教,地方臣民又有新的反教活动,如此环环相扣,怎么都与各自愿望相左?难道皇帝的政令就不能全面彻底地贯彻?与此相联系,反教官民所信奉的思想武器——道统与君统是何关系,君统能够完全支配道统吗?康熙帝六次南巡,究其原因,都没有说到与传教士的关系,难道没有任何瓜葛吗?因此,笔者拟从天主教史的角度,从道统与君统关系的角度,探讨康熙帝的政治。
(一)康熙帝南巡目的之一是考察传教士,反映其调查研究的政治作风
康熙帝为什么一再南巡?评论大体上是三条原因,首先是治理黄淮两河与保证漕运,关注国计民生,这是官方经常宣示的,无疑是主因;设若将南巡与北狩对照来看,北边是为武备及与蒙古联盟,南面是为解决国计民生,互相配合,真是“全国一盘棋”。其次是笼络汉人,协调满汉关系,在平定三藩之后,更需要安抚汉人,所以祭祀大禹陵、明孝陵,蠲免逋赋,接见致仕官员,钦赐士子举人。复次,关注地方吏治,召见各地督抚。笔者以为需要增加一条,即为利用西洋人科技知识而了解其人,以至于派人深入教堂察视。
康熙帝六次南巡,次次花费精力与传教士周旋,如同杭州教徒何文豪、张星曜等人在《昭代钦崇天教至华叙略》所云:“凡巡幸之处,必顾问天主堂所在,引见西儒,温旨劳问,或赐白金,或赐御膳,或赐袍缎,或赐克食,或赐果饼,从无虚日。”(韩琦校注书,第206页)康熙帝亲自及派遣侍卫对传教士进行半公开半隐蔽的察访。他对所见教士,总要问他姓名(甚至字号)、年龄,来中国几年、到过什么地方,哪一国人,有何特长,用度来源,同京城的徐日昇、张诚等人有无通信或见面等等问题。他在出发前就得知沿途教堂和传教士的一些情况,南巡中认识不少人,获得的信息更多,然而为坐实对传教士的了解,时或对同一个人提出同一的问题。如对潘国良,二次南巡在杭州与在苏州问了同样的一些问题,仅隔一天的重复询问,相信不是忘了在杭州的谈话,而还要纠缠老问题,不过是作进一步的查实。三十八年(1699)第三次南巡,潘国良已经从松江移住杭州,到无锡迎驾,康熙帝问他哪国人,与闵明我一国吗,多少年纪,何时到中国,有天球吗,南京、苏州北极几度?及到杭州,潘国良送呈浑天仪,其实康熙帝问的是浑天星球。康熙帝回銮,经过天主堂,“差内臣进堂细看”,内臣奏报杭州天主堂遭火灾,正在修建。康熙帝到苏州,召见潘国良,赐银助建教堂(韩琦校注书,第188~189页、361~362页)。康熙帝真是有心人,既查察了潘国良及其教堂,又显示了他的关切,令人感激。他问在地方的传教士与在京城的徐日昇等往来情形,更有深意,是了解徐日昇们是专心为他服务还是从事教务活动。派遣侍卫赵昌、伍(邬、吴、伍应为同一满人)去教堂,传教士请他们到内庭饮茶吃饭,时间不会很短,侍卫有公务在身,怎么敢在外逍遥,想必是康熙帝命令他们在教堂逗留,以便深入了解情况。尤其是赵昌,具有照管西士的职责,更另有使命,就是陈国栋在《养心殿总监造赵昌——为康熙皇帝照顾西洋人的内务府成员之一》文中说的兼有监视的任务,是康熙帝的耳目和代言人,并引出徐日昇一封信中的话:赵昌是皇帝的“眼睛、耳朵和嘴巴”*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343期,第47页。。服务内廷并随从第三次南巡的白晋就说,康熙帝“派官员赴南京教堂和浙江省会杭州的教堂祭拜上帝,了解两教堂情况”(书简集,第148页)。他更明了康熙帝善于秘密调查:“皇帝的习惯是:对所有值得调查的事情,都要搜集大量的有关情报;与六部的公开调查相反,他委派各种身份的人秘密进行调查。”(中国近事,第57页)显见康熙帝南巡途中是在考察传教士,这也是他南巡的一个次要目的,是在公开目的(治河与考察吏治民生)之外的不宣布的目标。
康熙帝信任西士和传教士不是盲目的,是通过各种方式、渠道考察他们,观察他们是否实心实意为清朝效力,以便决定对他们的态度。后来发现在礼仪之争中张诚偏袒教皇使节铎罗,就对他冷淡了,再发现传教士对他隐瞒教皇格勒门得十一世禁约令,就非常生气,而后宣布驱逐科技艺术人员之外的传教士。南巡途次的考察传教士,显示出康熙帝的政治作风和考核臣工的方法。尤可注意的是,康熙帝对传教士的这种细密考察,比考察中国臣工的含义更深刻,因为他们是外国人、传播外国宗教,就更其需要严格察究和监视。
(二)从南巡途中颁发印票看康熙帝在教会内部斗争中争取传教士留在中国的努力
南巡与传教士的关系,尚有一件事情不容忽视,即四十六年(1707)的第六次南巡接见领票传教士。格勒门得十一世于1704年决策,改变利玛窦在华传教方式,禁止中国教徒偶像崇拜,次年派遣铎罗来华执行其教令。康熙帝接见铎罗,但并不知其真正目的,不过已经知道教会内部有派别之争,误以为能够调停,于是采取两项措施,一项是对在华传教士实行发放印票制度:对使用利玛窦方式的传教士,发给印票,作为证明,可以继续在地方上行教。此票由内务府印制和发放,领票者要到京城领取,并且保证不回故国,永远居留中国。康熙帝第六次南巡,四月二十六日回銮驻跸扬州,举行集体发票仪式。这一天,传教江西的庞克修(Jean Testard,1663—1718)及各省传教士共22人,齐集行宫陛见,由皇长子直郡王允褆亲自一一发给他们印票。康熙帝特意指出,“(向)尔等颁敕文之后,与朕犹如一家之人矣”,接着向所有领票的传教士“赐宴,并赐缎纱”。此次颁发印票,非常郑重,说明康熙帝看重其事。这既是表示继续实行允许传教政策,又是对忠诚于利玛窦方式的传教士的嘉奖。消息传到杭州,教徒何文豪、张星曜等人欢欣鼓舞,讴歌康熙帝:“备闻圣谕,举手加额,叩谢我皇上钦崇天主、陶淑万民之圣德,可谓至矣尽矣。”(韩琦校注书,第206~207页、366页)康熙帝另一项措施是于四十六年(1706)、四十七年(1708)先后派遣传教士龙安国(Antoine de Barros,1664—1708)、艾逊爵(艾若瑟,Joseph-Antoine Provana,1662—1720)出使教廷,表达康熙帝对在华天主教的态度。遗憾的是龙安国死于海难,艾勋爵到达罗马,开始被教皇控制不许重赴中国,后来放行,病逝于路途。康熙帝两次派遣使节,均告失败*在派遣龙安国出使之前,派遣白晋出使,由于铎罗设置障碍,白晋未能成行。。
康熙帝晚年禁教,改变三十年代的初衷,是回应教皇对华传教方针,当然不是福建宗座代牧麦格罗特(阎当)等在华传教士导致的。但若从中国天主教兴衰史角度看康熙帝政治,康熙帝的热情对待与驱逐传教士的截然相反态度的变化,是维护清朝敬天法祖的治国纲领。教廷不允许中国教徒敬天尊孔祭祖,违背康熙帝的政纲,超出了允许传教的底线,理所当然遭到禁止。
(三)容教令颁布后康熙朝反教势力仍在不断地表达其态度
容教令颁布,一方面是传教士、教徒兴高采烈,歌颂康熙帝圣明;另一方面,反教的势力依然存在,他们的声音也没有消失。终康熙朝,奉教与反教的斗争始终不断,当然康熙朝以后亦复如此。下面从浙江天主教、反教双方态度说起,次及各省反教事件,以及朝臣的反教上疏。
(1)殷铎泽进京谢恩和严州建立教堂。就浙江禁教而言,容教令的颁布,是张鹏翮及浙江官员的失败,殷铎泽是大赢家,教徒也扬眉吐气。殷铎泽在容教令颁布一个多月后的四月三十日赶到京城,向康熙帝谢恩,赵昌传旨:“你老人家远来,身体都安康么?但今日你来乏了,且回去歇息,过几日再来陛见。”五月初三日殷铎泽趋朝,进呈天学穷理各书及方物12种,康熙帝全部收受。初九日,乾清宫朝见,康熙帝问:“你老人年寿几何?那一年到中国?在江西住了几多年?在杭州住了几多年?”到了六月,殷铎泽要回杭州,因安多和内务府李煦要去广东迎接奉命出使俄罗斯的闵明我,康熙帝让他们同行,以便照顾。十七日到畅春园辞谢,赏赐琼玉膏,“路上用补力”(韩琦校注书,第186~187页、359~360页)。康熙帝对他真可谓眷顾甚殷,殷铎泽风光地返回杭州。
大约是在容教令发布七八年之后,经过礼部批准,罗萨里主教德·里奥纳(梁弘仁)在严州建立教堂(书简集,第314页)。
(2)在地方官反对中宁波建堂的周折。
利圣学(Jean-Charles de Broissia,1660—1704)、郭中传(Jean-Alexis de Gollet,1664—1741)于四十年(1701)夏天到达宁波,开始取得地方官同意,购买地皮,兴建教堂。不久,新任地方官不认可,查问利圣学是什么人,从何处来,到此有什么打算。回答后,仍禁止建房,并将事情报告巡抚,巡抚持同样态度。传教士搬出容教令及新近礼部批准严州建立教堂的例子,述说兴建教堂合于康熙帝旨意。巡抚声称“皇帝的诏书未禁止建造新的教堂,但是,它也没有允许建造新的教堂。礼部已批准了严州的教堂,但是这一批准并未涉及到宁波”,予以拒绝。后因张诚找到礼部尚书说情,礼部批准宁波建堂。郭中传乃重新开工修造教堂,他雇用的偶像崇拜者厨师下毒药害他,幸免于死(书简集,第204页、313~317页)。事情明摆着,浙江巡抚、宁波地方官及民人中有人对容教令不认同,不乐于执行。
(3)衢州、严州反教活动与奉教者的著述。
约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第六次南巡前夕,浙江衢州、严州同时出现反教活动。当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五次南巡时,严州府天主堂孟(Francois de Montighy,?—1742)与杭州府天主堂艾思玎(Agostino Barelli,1656—1711)、湖州府天主堂隆盛(Guillaume Melon,1666—1710)远至淮安迎驾,随后在杭州献方物。及至康熙帝驻跸西湖行宫,衢州府天主堂艾毓翰(Juan Astudillo,1670—1714)与绍兴府萧山县天主堂何纳笃(Giovanni Donato Mezzafalce,1661—1720)陛见,献方物16种。康熙帝回銮,孟、艾毓翰等五人送驾(韩琦校注书,第191~192页)。事隔一年,衢州、严州都出现反教事情。地方官追究天主堂神父,封闭教堂,不许教徒出入;差役到教徒家中搜查,看是否藏匿传教士,如同搜捕叛逆一般;毁坏宗教器物、书籍;衢州教徒余多默被县官杖责锁押,县官说“朝廷已禁天教,驱逐西洋人,尔等何得管守堂内?”衢州、严州之外,金华、兰溪、嘉兴、萧山等处教徒“俱各受累,人人自危”*韩琦:《张星曜与〈钦命传教约述〉》,韩琦校注书,第425页。。
反教者激烈活动,奉教者也不甘示弱,何文豪、张星曜、杨达等人著述《昭代钦崇天教至华叙略》,张星曜增补为《钦命传教约述》,宣传康熙帝对天主教和传教士的仁慈,证明信教合法,不应遭到迫害*韩琦:《张星曜与〈钦命传教约述〉》,韩琦校注书,第416~432页。。康熙末年,传教士仍然在浙江活动,六十一年(1722),西洋人德神父到海宁县传教,高廷显及子入教;到了乾隆十一年(1746),他们的后人高维学、高天升家尚存有天主画像、经书*浙江巡抚常安奏(乾隆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22页。。
(4)其他省份的反教活动。
福建反教。在衢州、严州反教之时,有福建教徒朱玛窦到杭州,告诉杭州同教者:“福建八府神父尽回西洋,地方光棍联络衙门,将堂白占,议改义学公馆,不容一人进堂瞻礼。”(韩琦校注书,第425~426页)所述显然有很大夸张成分,不过,四十六年(1707)闽浙总督梁鼐确有“驱逐西士,阻止行教”之事(韩琦校注书,第364页)。四十八年,福建巡抚张伯行(1651—1725)有《拟请废天主教堂疏》,请求禁止天主教,以正人心,以维风俗*张伯行:《正谊堂文集附续集》之《续集》卷1《拟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75~176页。。表明福建长吏多有强烈反对天主教者。
湖广黄州逮捕教徒。四十一年(1702)赫苍壁(Julie-Placidi Hervieu,1671—1746)、孟正气(Jean Domebge,1666—1735)到黄州准备建立教堂,地方官与巡抚都不允许,说省城已有教堂,为何还要在黄州建立。传教士报告张诚,后者找到巡抚儿子、国子监官员说情,巡抚遂行允准,给知府行文云,容教令宣称“欧洲人的教义表明其绝非是一种没有根据和迷信的教派。他们也不是骚扰国家之人,反而是在为国家效劳”。知府也顺水推舟地同意了*书简集,第323~327页;荣振华书,第189页、309页。。孟正气在黄州买了房子,僧侣与百姓反对,告到官府,孟正气怕出大事不得不让出房屋(书简集,第205页)。黄州官员查检到在当地的江西赣州朱姓教徒,因他公开信教,摘除其圣像,押解至九江,辗转解送回籍(书简集,第323页)。
江西府县官反教。约在三十九年(1700),利圣学、孟正气在抚州、饶州、九江三处买房建堂,饶州、九江地方官反对,藩司持通融态度,才在那里立足传教*书简集,第203~204页;荣振华书,第189页。。
河南南阳、鹿邑反教。南阳教堂是西士冯秉正(Joseph Marie 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1663—1738)利用测绘地图时机,用银子买的。五十三年(1714)新任知府以禁止所有教派为名查禁天主教,教堂门前不许放置十字架,强令信徒退教,于是有人退出。后因知府奉派出差,禁教不了了之。约在五十八年(1719),鹿邑知县厉行禁教,拘捕教徒弗朗索瓦·吴,抄家,在公堂焚烧基督、圣母像,三次打他,致其死亡*[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2卷,郑德弟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179~183页、221页。。
(5)御史樊绍祚疏请禁教。
康熙五十年(1711),御史樊绍祚奏疏请求禁教,疏称:“今有西洋人等造为异说,名曰天主教,臣访闻近今京畿直隶各省人民,多有信服其教者,恐流衍日久,渐染滋深,害及中国人心,则廓清不易,伏祈敕下该部,严行禁止。”礼部根据容教令、给予传教士印票事,认为传教士并无妄作非为,不应禁止,得到康熙帝认可(韩琦校注书,第217页)。
容教令颁布之后,各省之禁教屡有发生,且多由督抚大吏、府县官出令,衙门执行。疆臣、地方官何以敢于违背皇帝旨意,而且并未因此受到惩处?因为容教令事涉外国人、外国宗教,这就关乎意识形态中的两种观念,即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道统与君统的分离。本来汉人以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反对满人统治,但是西洋人和天主教从外部进来了,满汉的华夷之辨因而隐退,中华之满汉共同对付外夷,这是大义,高于忠君伦理。当君主在这个方面出现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康熙帝的容教令,臣子是可以据理力争的,内心是可以不满的*康熙帝因为容教令在文人中降低了威望。雍正帝召见巴多明、白晋、戴进贤说:“有一段时间,父皇糊涂了,他只听了你们的话,其他人的话都听不进了。……朕的先父皇迁就了你们,他在文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就降低了许多。”见《洋教士看中国朝廷》冯秉正1724年10月16日信,第106页。。官员的禁教,正是遵循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不但不违背君权,且是最大的忠君,与反抗谕旨完全无涉。华夷之辨观念属于道统范畴,是儒家伦理在民族问题上的最高准则。道统是与君统分离的,君主不能违背道统中的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的伦理法则,可以解释它、利用它,不能使用君权改变它。在这里,君主的权威是受道统制约、限制的,是不能无往而通行的。所以,张鹏翮将殷铎泽传到衙门,质问他原先居住江西,“是如何获准在(杭州)城内居住的”?张鹏翮当然知道,康熙帝两年前在杭州见过他四次,显示出他们之间某种密切关系。他还应当知道康熙帝要殷铎泽好好住在杭州——当面对殷铎泽说“老人家好好住在这里”,侍卫接着传旨:“万岁爷命老人家好好安心住在这里。”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问殷铎泽是怎样获准居住杭州的,显然是明知故问,是公然对着康熙帝旨意了!而张鹏翮之后的浙江巡抚及宁波、衢州、严州、南阳、鹿邑、黄州等等地方官,以及闽浙总督、福建巡抚,仍然对容教令持保留态度,也可以视为不买账,以己意解释它,因为他们思想上反对洋人的天主教,是以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为行为依据的。正因为官员依仗这个准则,以及君统与道统的分离,有点“有恃无恐”了。康熙帝也遵守这个准则,容忍禁教官员的“抗旨”,没有进行处罚。如果再继续论述至高无上的君主行驶君权有某种难以克服的障碍、君权是有限度的,就超出本文范围,就此搁笔吧。
责任编校:张朝胜
作者简介:冯尔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安徽 合肥230039),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071)。
中图分类号:K249;B9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5)01-0001-14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