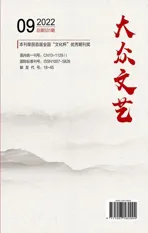“五四”新文学时期的中国民俗学:属于精英的民俗学
2016-01-28袁曼琳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610000
袁曼琳 (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610000)
“五四”新文学时期的中国民俗学:属于精英的民俗学
袁曼琳 (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610000)
“民俗”,本应是来源于民间草根的最淳朴原始的文化事象,一旦上升为一门学问、一门学科之后,便呈现出“精英化”的特征。“民俗”与“民俗学”之间,便产生了一道鸿沟。本文试图以中国民俗学发生期——五四运动的“歌谣学”运动为分析对象,分析“民俗”的“民众化”与当民俗上升到民俗学之后的“精英化”倾向,并试图探讨在这样的情境下,如何让民俗真正地回归到大众的范围内。
歌谣学运动;民俗;精英化;官方化
“民俗”这个词语,最早是由日本人翻译过来的,它的英文单词是Folklore,其提出,则是来自于英国的民俗学家威廉·汤姆斯的一篇文章。汤姆斯试图用这个词语去代替当时惯用的“民间的古俗”,意指“民众的知识”、“民众的智慧”或“民众的学问”。后来这个词语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步演变成为含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指民俗本身,就是民俗志的资料,如风俗、习惯、歌谣、故事等;二指研究民俗的理论,就是民俗学。”1
如果我们只看第一个定义,把民俗理解为民间风俗,而不是一门学问,那么它所指的就是“一个民族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方面长期形成的传统”。2它就是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之一。从而与官方、与意识形态、与上层的思维无关。民众的思维意识应该是淳朴的,感性的,它是“与科学思维、官方意识相对应而存在”3,也就是说,“科学思维要求理性和客观,官方意识重视统一和谨严,而民间思想表现信仰和情感。”4而这个特点,应该是“民俗”最为珍贵且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不同于“官方”和“上层社会”的最大特点。
不过,一旦民俗上升一门学问,成为民俗学之后,或多或少地,受到官方和文化精英的刻意营造,民俗的最本真特点并不能完全地保留下来,甚至变成“文化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华东师大的田兆元就认为,“传统的民俗学研究实际上有偏向文化精华的倾向。”5同时他认为,“把民俗视为文化精华,视为非日常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一种民俗学的传统。”
“民俗”丧失其本真淳朴的特质,加入精英文化的元素,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态势。接下来笔者将试图以“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即民俗学在中国的发轫期,以期间最具有代表性的“歌谣学”运动为例,简单对比民俗的“民众化”与民俗学的“精英化”“官方化”现象。
一、民俗与歌谣·民俗学与歌谣学
本文试图探讨的中国的民俗学运动,为什么却要以“歌谣学”运动为例呢?歌谣与民俗学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钟敬文先生曾经明确地指出:“民间文学作品及民间文学理论,是民俗志和民俗学的重要构成部分。”6直到今天,在民俗学的研究工作中,歌谣都是十分重要的材料。歌谣和民俗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从一个方面来说,各民族特定的风俗习惯往往会影响到该民族歌谣的产生和发展,并影响这些歌谣的内容和形式;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丰富深厚的民俗事象,给歌谣创作提供了大量民族性、地域性的素材,是歌谣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而当我们追溯历史,中国的民俗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起源应该是北大歌谣研究会的成立及《歌谣》周刊的创刊。作为我国民俗学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歌谣》周刊第一号的发刊词曾明确地指出,“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一九二四年的一月份,歌谣研究会曾提出改名为民俗学会,后来虽然并没有改名,但实际上也是民俗研究的学会。可以说,中国的民俗学就是以歌谣学运动为其发端的。所以我们理应这样认为,歌谣与民俗的关系密不可分,中国民俗学的发生发展也是跟“歌谣学”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
二、“精英化”“官方化”的中国歌谣学运动
(一)歌谣学运动的开展带有其政治化的目的
中国的歌谣学运动从一开始就并不纯粹单纯是以调查研究民俗本身为出发点的,它始终是带有着一些“功利主义”的倾向。其实质就是文化界以及官方企图通过“目光向下”,调查研究民俗,从而在文化上实现“再造国族”。歌谣学运动无疑与时代背景、国家背景息息相关。
当时的中国社会风起云涌,辛亥革命之后,清王朝虽然被推翻了,并建立了共和体制,但是国内依然是处于动荡的状态。于是,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两大旗帜的召唤下,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势不可挡的文学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希望人们能够做到真正地关注民众,从中国传统的羁绊中逃脱出来,为新时期的中国“再造国族”贡献出文化上的一份力量。
受这样的时代背景的影响,歌谣学运动就注定了它不可能单纯是一项为民俗而学问的运动。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学者们对歌谣学运动所期盼的从文化上“构建国族”的期望。国族,作为一个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概念,指的是“在知识精英利用原有文化资源进行建构的基础上,在政权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共同体。”“现代国家,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构建产生的,美其名曰‘nationbuilding’。”7国族可以被建构,而国族的建构需要人们的族群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来自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等。中国民间文学运动时期的文学家们所做的正是从文化认同上推动国族建构的过程。
可以这样说,当时中国的民俗学研究是带有其政治化的目的的里面的。这种带有政治化目的的研究,势必会掩盖掉很多不利于其政治目的的元素,从而无法完全还原民俗的本来面目,以及呈现出它原始淳朴与感性的本质特征。实质上,中国的民俗研究向来如此。
(二)受当时时代条件的局限,知识分子无法真正做到“目光向下”
“再造国族”是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拯救这个民族所抱有的美好的期望,它们通过“目光向下”,重新关注普通大众的文化事象,试图从文化上达到这一目的。但是“目光向下”的目的并为达成,时代条件的不成熟,使得的歌谣学研究更多的只是在书斋中的研究,脱离了民众,加入了更多的学者的阐释,从而或多或少失掉了民俗文化事象本来的面目。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曾经这样说道:
“五四透过运动的方式被定义的文化有三个限定词:城市背景、大众传媒和知识分子。在安德森的印刷资本主义理论中,文化也是在这三个范围内才得以成型。而当今的问题是,中国绝大多数国民恰恰不在印刷资本主义的覆盖之内。直到抗战时,那套文化壁垒才真正被打破。一个重要的标志是瓦窑堡会议提出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人们这才真正注意到口传文化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民”是什么意思。”8
当时的学者迫于拯救国家,重振民族,从西方、从日本那里引进了许多新式的概念,其中就有“民”的概念。对“民”的重视似乎是建构新的国族所必备的要素。但是,鉴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整个学界对于“民”的思考程度的局限性,并不能够真正的思考出何为“民”,以及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把“民”当作主体。实际上,当时的学者也没有把“民”当作主体,而只是将其作为了一种认识上的功利性工具。
(三)当时的民俗学的调查,受到官方的制约
学者们在进行对民间歌谣的田野调查,从事歌谣研究的时候,都会受到官方力量的牵绊与制约。官方与学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用若即若离来形容。历来中国官、学两界的区分就不是特别明显,“学而优则仕”,一个人很可能同时是政府官员也是文化学者。这两种角色无法割裂的关系,使得五四时期对于歌谣的研究,也参杂着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意味。
实际上,中国社会中“官、士、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显得十分微妙的。领导中国“歌谣运动”的实际上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或者可以称作“士”。在过去中国语言里,阶层一般是指阶级内部不同等级的群体或处于不同阶级之间的群体。后来我们概念中的“士”一般指的就是“读书人”。但是这样的定论放到“歌谣运动”当中似乎就并不见得准确了。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个难以确定的对象,徐新建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所谓的群体——无论称之为‘知识阶级’‘新知识界’还是‘学术部落’,作为一个统一完整的阶层,其实并不存在,而不过是当事人为了利益需要和论述者为了阐释方便的说法而已。”9我想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否有这样的几点原因:1.“歌谣运动”中的“士”不同于我国古代的“士”,这样的“知识阶级”在形成年代上是在晚清之后。2.当时从事“歌谣运动”的研究者们并不是专职的。3.“士”的立场并不坚定,他们夹杂在“官”与“民”之间,与“官”的关系暧昧不清,对“民”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
政府与文化精英们保持着联系,其实是试图通过文化,通过道德说教来维持其自身的统治。“中国也有人能够摆脱国家认可的正统思想,但他们的信仰很少被人们认真看待,从而也很少成为官方信仰的威胁。”如果说,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前,民俗文化不被官方认真看待,是因为它在文化精英眼中是粗鄙的,在政府官方那里不被视为威胁其统治的事物,那么到了五四时期,民俗的“重见天日”是同时受到学者的重视,另外也是政府官方带有功利目的的推动。可以说,——主动权、话语权、发言权从来未曾真正掌握在发明、拥有、传承民俗事象的普通老百姓的手上。
当时的中国知识界研究歌谣,关注民俗,这里面固然有着文化上、学术上的目的,但是同样也是交互着政治上的目的的。学者在对歌谣进行研究的时候,由于始终无法摆脱政治上的目的,所以真正还原歌谣的本来面目,只是一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譬如说,当时的官方机构对于学界的歌谣调查的计划方案,曾指出:
“民俗调查为社会行政之重要依据,亟宜举办。”同时需要对“民众教育、礼俗改良、新生活运动、经济建设运动等,均特加注意……今日民众教育之推行及礼俗制服等方案之拟定亦需此种实际材料,更有进者,民族复兴以民族团结为前提,任何破除民族间之隔阂,以沟通民族文化,自亦当以民族研究为基础工作,而民俗调查为不可缓也。”
可见,对于民俗的调查始终摆脱不了官方的目的。
(四)某些学者自身对于民俗文化的不屑
从主观意愿上来讲,除了政治上的功利性目的,新文学革命时期的学者们期望能够与民众相结合也有出于对于民间文学的本身的喜爱,对于过去官方的那种酸涩文学的鄙视。容肇祖曾经就在《忆<歌谣>和<民俗>》为题,说道:
“五四以后,我进北京大学,一些老师们提倡搜集或的新文学,编辑‘新国风’的问题。这是搜集现代歌谣的起源。……“新国风”是五四以后提倡新文学、新诗歌而开发的一个新园地。它提出了创作新诗要和民间歌谣结合,使新诗接近人民。”
不过实质上,当时虽然是把“民”挂在嘴边上,但是不少学者的骨子里面却不大瞧得起老百姓,“五四”时期不少知识者觉得老百姓是很封建的,需要被启蒙的。于是,当民俗上升为“民俗学”之后,为了摆脱那种所谓的“田野的”“粗鄙的”东西,从而不可避免地会趋于一种“精英化”的态势,从而或多或少脱离民俗其本真的、淳朴的、原始的风貌。田兆元认为我们对于民俗的解释,其实是出于阶级立场的一种解释,即是“把民俗定位为劳动人民和底层社会的生活传统”10,从而“刻意与精英文化区别开来,以表现学科的革命性及其对于大众的亲善性”11,它的主旨依旧还是在“政治方面”。
三、让民俗真正回归大众是否可能
上观历史,其实中国自古就有民俗,只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是发生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无可厚非地,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它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了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源远流长的中国民俗,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宝贵贡献。在古代社会,我国的民俗文化实际上作为“礼”文化的对应和补充而存在下来的。在古代典籍中,对于民俗就有过诸多的解释。譬如《周礼》上就说:“礼,屡也。因人所践履,定其法式,大而婚冠丧祭,小而视听言动,皆有其节文也。……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化曰俗。”12也就是说,礼是古代社会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俗则是普通民众的习惯和风气。诸如此类的解释还有很多,但无非都是强调了民俗与“礼”之间的关系,以及民俗对政治伦理倾向。
再到当下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列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实际上是我们所谓的民俗文化的代表作品。作为这些名录上的东西,其实都是精华的东西,是经过筛选,甚至是加工之后的东西。而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更都是文化精英了,他们掌握民俗文化的水准,是普通的民众所无法达到的。在这样的状况下,民俗也呈现出了一种文化精华的形态。
笔者认为,对于民俗事象的关注,从来都不是单纯地以保护传承某种民俗文化为目的开展的。同时,当它上升并具有某种官方政治化的目的之后,民俗最本真的淳朴感性的风貌便遭到损坏。让民俗真正回归到大众是否可能?这是笔者在文章最后提出的一个问题。破而不立,笔者在这里无法解答这种靠实践才能真正解答的问题。只是想要说明的是,民俗属于民众,只有当民俗完全服务于大众,才能发挥民俗的最大作用,才能让民俗发挥其本真的光彩。
注释:
1.钟敬文.《钟敬文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第231页.
2.赵晓兰.《歌谣学概要》.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272页.
3.谢国先.《新世纪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9月第23卷第5期.
4.同上.
5.田兆元.《民俗本质的重估与民俗学家的责任——一种立足于文化精华立场的表述》.载《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五期.
6.钟敬文.《钟敬文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第244页.
7.张永红,刘德一.《试论国族认同和族群认同》.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1月第27卷第1期.
8.胡子林.《国族问题的话语谜踪》.载《书城》,2008年12期.
9.徐新建.《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 四川出版集团 2006年版 第38页
10.田兆元.《民俗本质的重估与民俗学家的责任——一种立足于文化精华立场的表述》.载《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五期.
11.同上.
12.杨树喆.《中外民俗学发展述略》.载《百色学院学报》, 2006年10月第19卷第5期.
[1]钟敬文.《钟敬文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第231页.
[2]赵晓兰.《歌谣学概要》.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272页.
[3]谢国先.《新世纪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9月第23卷第5期.
[4]田兆元.《民俗本质的重估与民俗学家的责任——一种立足于文化精华立场的表述》.载《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五期.
[5]张永红,刘德一.《试论国族认同和族群认同》,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5年1月第27卷第1期.
[6]胡子林.《国族问题的话语谜踪》.载《书城》2008年12期.
[7]徐新建.《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 四川出版集团 2006年版 第38页.
[8]杨树喆.《中外民俗学发展述略》,载《百色学院学报》 2006年10月第19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