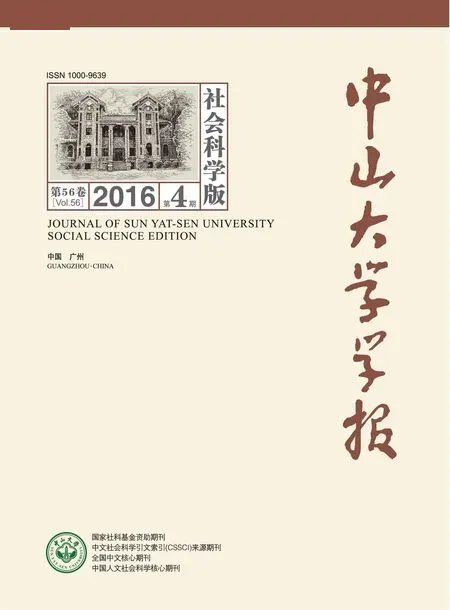国民外交协会与近代国民外交“对内”趋向*
2016-01-27曾荣
曾 荣
国民外交协会与近代国民外交“对内”趋向*
曾荣
摘要:巴黎和会前后,外交风潮迭起,国民外交与北京政府外交走向极不明朗,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为其中重要关节。国内舆论界对中日谈判前后北京政府“秘密外交”的批评,孕育了国民外交的“对内”趋向;留日学生的罢学归国行动,强化了国民外交对政府外交的“监督之责”;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及其活动,使得国民外交“对内”趋向得以形成,这不但深刻地影响了巴黎和会时期北京政府的外交走向,还对其后的“国民外交”乃至民国外交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国民外交协会; 国民外交; 北京政府; “对内”趋向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不仅是“国民外交”与“政府外交”相互纠葛的重要结果,还促使国民外交“监督政府外交”,使国民外交“对内”趋向得以形成,由此深刻影响了巴黎和会期间北京政府的外交走向,堪称近代中国“国民外交”史上的“里程碑”。
学界既往关于国民外交协会的研究,多聚集于其外交主张、活动与影响,意在阐释“国民外交”的定义,缺乏协会成立背景与原因的深入探讨,尤其是关于国民外交协会对北京政府外交走向影响的动态过程,以及对“国民外交”乃至民国外交的深远影响,往往语焉不详①郭秋香:《国民外交协会之始末——兼论五四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复旦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许冠亭:《“五四”前后国民外交协会活动述论》,《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印少云:《民初国民外交运动的对内转向分析》,《江汉论坛》2006年第11期。。唐启华、邓野关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的新著,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②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台湾学者廖敏淑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文则注意到巴黎和会前后“国民外交”截然不同的历史状况,进而指陈“国民外交”定义依时流变的事实③廖敏淑:《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台湾中兴大学1998年硕士学位论文。。问题在于,上述关于“国民外交”的定义是当时人的定义,还是后人对历史事实的自我界定?显然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追溯国民外交协会成立的历史渊源,动态展现国民外交“对内”趋向的历史过程,进而揭示国民外交协会与北京政府外交走向的密切联系。
一、中日秘密谈判与国内舆论界
1918年前后,欧战的硝烟虽未散去,但是国际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并对远东时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及其退出欧战后,日本借机谋划与中国缔结“中日军事协定”,以此扩大在中国满蒙地区的势力*《日支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実施ニ要スル詳細ノ協定ニ関スル件》,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復製,No. 57。。1918年2月5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会见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要求中国为应对欧战新局势而配合日本采取“共同行动”*《中日军事协定共同防敌案》(1918年2月6日),《外交文牍》第2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2页。。对于日方建议,北京政府内部起初意见不一,但在主战派段祺瑞的赞同下,中日双方进行了一系列交涉和磋商,并于3月25日就共同防敌问题进行换文,其内容包括中日两国在海、陆军方面协同合作的办法及条件。随后两国政府分别派员,就具体条款进行商议,从而为达成最后协定做好铺垫。
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方的要求下,中日双方商议“共同防敌条款”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然而,由于国内外媒体对交涉内容及经过的曝光,到1918年4月,国人展开了对中日交涉的激烈讨论。4月12日,《晨报》刊载题为《生死关头之中日交涉》的新闻,推断此次中日交涉内容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第五项,呼吁“国人速醒”,共同反对中日秘密交涉。由于中日谈判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相关消息主要从《泰晤士报》等外国报纸得来,为此该文批评北京政府外交当局是“为人守秘密”,而于“国民外交四字固未曾有丝毫影响于脑筋”*《生死关头之中日交涉》,《晨报》1918年4月12日。。16日,益世报社社长刘俊卿也以《政府其速猛省》为题刊文,劝告北京政府勿签条约,否则我国“军警、外交之权失,而中国亡矣”,并强烈要求立即停止谈判*《政府其速猛省》,《益世报》1918年4月16日。。当天,《晨报》再度刊文,敦促北京政府外交当局以国家主权为重,将交涉内容及日方要求条款公之于众,“宜稍明国民外交之意义,不可徒为人守秘密”*《中日交涉大事件》,《晨报》1918年4月16日。。与此同时,《中华新报》主笔汪馥泉更是以《外交罪言》为题,严厉指责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涉是“断送国脉”之举,呼吁北京政府外交宜“以国民实力为后援”,而不要“以秘密对付为能事者也”*《外交罪言》,《中华新报》1918年4月16日。。19日,《益世报》一篇署名“梦幻”的评论,严厉谴责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将“我国所有财政权、外交权、军警权、路矿权、教育实业权,已于秘密中断送殆尽”,呼吁“全国上下乘此亡国条约尚未签押之际,联合团体,拼死力争”*《民国一线生机》,《益世报》1918年4月19日。。
在国内舆论界的推动下,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团体纷纷响应。4月中旬,全国商会联合会、顺直省议会、直隶商会联合会共同致电北京政府,声称当前“中日新交涉案,报纸喧传,人言啧啧,其中真相不得而知”,故强烈要求政府将中日交涉内容从速宣布*《全国商会联合会等质问中日交涉电》,《益世报》1918年4月19日。。
诚然,民国初年,时人将国会视为对下代表国民意愿、对上监督政府的重要机构。然而,第一届国会于1913年底解散后,因政局动荡而一直未能重建。第二届国会的筹备工作虽在1917年段祺瑞组阁后即开始进行,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18年3月6日,北京政府才颁布国会选举日期令。因此,在国人反对中日共同出兵交涉之时,各省正在进行选民统计工作,距离第二届国会的正式成立为时尚早。在此情形下,4月20日《益世报》刊发题为《今后之国民外交》的评论,称国会为代表民意的机关,“即为监督政府机关,国会存则监督之权在国会,国会亡则监督之权在人民,人民不能直接监督,省会、商会皆为代表民意之正式机关,则以法理而言,亦可代行国会职权,以尽监督之责”。故在当时国会尚未恢复之时,全国商会联合会、顺直省议会、直隶总商会这种质问政府、监督政府外交的行为是“国民代表应尽之天职”,而全国商会、学会等团体则是今后国民表达外交意愿与发动国民外交运动的重要力量*《今后之国民外交》,《益世报》1918年4月20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国人对北京政府秘密外交政策的批评,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外交对内“监督之责”的产生和萌发。
如前所述,中日关于“共同防敌”的谈判一直处于秘密状态。自3月25日中日双方换文之日起至4月底,北京政府仍未就谈判内容向公众表态。然而,随着国内外舆论对中日谈判条款内容的不断揭发,举国上下掀起一股谴责北京政府“秘密外交”的巨大声浪。4月22日,《晨报》社论从实行“国民外交”的角度立言,称“方今为国民外交时代,凡国际交涉皆须得国民最后之同意”,绝非政府数人可以“率尔擅行”。就当前外交局势而言,我国欲实行国民外交,则“不容外交秘密存在”,为此呼吁国民应当督促政府,“将此事件真相与政府所怀抱方针明示中外,以释国人之疑惑”*《国民对于中日交涉之疑问》,《晨报》1918年4月22日。。与此同时,中华学界联合会也加入到反对中日秘密谈判之列。在联合会主任程苌碧、汪馥沅等人的带领下,该会与上海商界、工界等团体密切沟通,各界团体就“反对中日密约”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发给上海各界团体的函电中,中华学界联合会痛斥北京政府与日方缔约,声称此约“名为中日共同防御,实无异举全国之海陆军授与外人”。呼吁上海工、商、学等各界人士,“明国民外交之意义”,共同反对此约*《上海各界反对中日密约之函电》,《益世报》1918年4月23日。。《时报》主笔包天笑则认为,民国肇建以来,国会被解散,约法被蹂躏,外交屡屡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没有“强有力之国民”,故而提出今后我国欲实行国民外交、有效监督政府外交,则必须先培养“强有力之国民”*《强有力之国民》,《时报》1918年4月24日。。
需要强调的是,在各界人士对政府秘密外交的批评中,《新闻报》主笔李浩然连续刊发的时评尖锐且富有针对性,目标直指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中日关于共同出兵问题的交涉开始后,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不是外交总长陆征祥,而是时任北京政府参战督办事务参谋处处长靳云鹏。对此李浩然认为,陆氏身为外交总长,于关系中国主权利益的外交大事,当“尽外交总长之责”,不仅应将中日交涉内容“及早宣布”,还要以国家主权和利益为重,对此案“酌夺利害”,与各方“审慎磋商”*《勗外交总长》,《新闻报》1918年4月22日。。而在题为《外交当局之责任》的时评中,李氏敦促北京政府外交当局拒绝日方无理要求,称:“国民为外部争权限者甚力,外交当局其毋负国民而甘为武人之奴役也。”*《外交当局之责任》,《新闻报》1918年4月27日。此外,李氏《外交之秘密》一文进一步批评北京政府秘密外交政策之失当,认为“国民所以要求宣布条件者,非为博与闻外交之虚名,实欲详察利害,作政府后盾”,然而北京政府置国民要求于不顾,以“军事委员会”操纵此案,其“违法侵权之罪,已无可辞”*《外交之秘密》,《新闻报》1918年5月3日。。为了唤起广大国民监督北京政府外交,在题为《对外欤?对内欤?》的时评中,李浩然进而提出关乎“国民外交”历史走向的时代命题:“以对外为主体?抑以对内为主体也?”*《对外欤?对内欤?》,《新闻报》1918年5月6日。
显然,当时北京政府的秘密外交政策与国人要求大相径庭,两者的矛盾日益尖锐。在此背景下,如何对政府外交实行有效监督,成为当时十分紧迫的任务。而以国内舆论界为代表的中国知识阶层,通过对中日谈判前后北京政府“秘密外交”的批评,孕育了国民外交的“对内”趋向,诠释了“国民外交之意义”。
二、留日学生罢学归国风潮与对内“监督之责”
随着中日交涉日益向纵深发展,到1918年5月,国人反对中日秘密交涉的行动出现新动向: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国民外交行动主要表现为舆论界的声诉和抗议,那么从5月初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留日学生罢学归国风潮蓄势待发。
留日学生罢学归国风潮的最初发起地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时人称之为“东京一高”),主要发起者为该校留学生王希天等人*吉林省档案馆编:《王希天档案史料选编》,长春:长春出版社,1996年,第2页。。早在1918年初,王希天就与周恩来等人往来密切。中日密约交涉开启后,在两人的积极联络和大力推动下,广大留日学生逐渐加入到反对中日交涉的队伍中来。1918年5月5日,留日学生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救国团”,大家以“一致对外、决不干涉内政”为宗旨,为组织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做出具体安排和部署*《旅日日记》(1918年5月5日),周恩来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编著:《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1912.10—1924.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9—361页。。7日,王希天率先归国,周恩来等人“送之至横滨”,从而正式拉开了留日学生罢学归国风潮的序幕*《旅日日记》(1918年5月7日),周恩来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编著:《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1912.10—1924.6),第361页。。
值得注意的是,留日学生在发起罢学归国运动之时,不约而同地宣称以监督政府外交为主要目的,而决不干涉内政。除“中华民国救国团”外,留日学生救国团也公开宣称,专门致力于监督政府,“不涉及内政”*《留日学生议决救国团之组织法》,《益世报》1918年5月14日。。“东京一高”学生则在布告中声称,为督促政府外交当局拒绝日方要求,当前“惟有一致归国,协力鼓吹国民全体反对,并共筹种种积极办法,誓不达到政府拒绝要求条件之目的不止”*《留日学生议决全体归国之现状》,《益世报》1918年5月11日。。
留日学生的言论和举动引起国内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时报》主笔戈公振认为,留日学生之所以倡议全体归国,其直接原因是政府不将对外交涉情形“开诚布公、一切宣示”,以致留日学生均表“疑虑”,其根本原因则是北京政府无“国会”的监督。“使今日而国会存在,则代表有人,又何劳留日学生之辍业”,以全体罢学归国的巨大牺牲来警示政府*《留日学生回国》,《时报》1918年5月13日。。梁家义也发表题为《时局解决问题》的社论,急切提出“对内之万不容缓”的口号,称当前外交日亟,欲使政府与国民“一致对外”,则一方面政府各党派、各政团“急宜止息争讧”,另一方面在第二届国会尚未成立之际,全体国民宜起来监督政府外交*梁家义:《时局解决问题》,《微言》第1期,1918年5月16日。。
5月16日,中日双方签署《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支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調節》,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復製,No. 54。。19日,双方又签署《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支海軍軍事協約調印ノ件》,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復製,No. 54。。协定签订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发国内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由留日学生发起成立的“中华民国救国团”,在《警告全国四万万同胞书》中将矛头直指北京政府,称国家权益为全体国民之“公产”,非政府之“私产”,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是全体国民的“天职”,国民“一方面当发挥公意,造成强有力之舆论,为外交后盾,一方面捐弃嫌隙,举国一致,合力对外”*《国民救国团警告全国四万万同胞书》,《益世报》1918年5月19日。。而在《救国团宣言书》中,留日学生亦宣称学生对于“政治非所敢闻”,而专门致力于发动国民“一致对外”,以及敦促“政府严拒要求,国民为之后盾,惩日人之妄”*《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宣言书》(1918年5月20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5、46页。。这一情况再次表明,留日学生虽然公开批评北京政府外交失当,但对其合法性予以认同,故而宣称以政府外交为主体,强调国民外交的“监督之责”与“后盾”作用。
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运动正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北京学界反对中日协定的行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从5月20日至24日,北京大学、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两千余人,“齐集总统府请愿挽救外交之事,其态度之诚挚,秩序之整齐,均足代表吾国民之朝气”,而于“精神上影响于全国民者,实将垂之于永久”*《北京学界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赴总统府请愿》(1918年5月20—24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46、47页。。与此同时,上海各学校学生一面向北京政府联名致函,一面与归国留日学生加强沟通联络,表达对中日协定的强烈反对。此外,全国商会联合会亦上书总统冯国璋,称“若不经国会同意,无论与何国缔结条约,不发生何等效力”,为此要求政府拒绝批准中日秘密条约,“以维国法而保主权”*《全国商会呈大总统文》,《时报》1918年5月30日。。
随着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运动的持续开展,至1918年5月底,归国学生已达三千余人,此外还有一千多人也准备归国*《留学界风潮未已》,《学生杂志》第5卷第7号,1918年7月5日。。大规模的留学生罢学归国行动,无疑给北京政府当局造成触动。北京政府教育部屡发布告,要求留日学生返回原校,同时国务总理段祺瑞、留日学生监督江翊云等人也与留日学生代表面谈,劝说学生早日返校,但均遭到爱国学生的拒绝*《教育部催促留学生返校之布告》,《时报》1918年6月8日。。
6月19日,《大中华报》率先刊登《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全文。随后,各界民众无不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与谴责,归国留日学生的言论与行动亦进入新阶段。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首先发难,在其发布的《泣告全国父老昆弟书》中,急切呼吁国人一面督促政府取消协定,“一面组织救国团,合筹抵制方策”*《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泣告全国父老昆弟书》,《益世报》1918年6月20日。。而为唤起国人挽救国家利权,留日学生救国团还发布《救国团丛刊》。在该刊第2辑中,留日学生以“独吞中国论”为标题,全文翻译并刊载日本黑龙会代表内田良平的《解决中国问题意见书》,以揭露日人欲吞并中国的计划和野心*《排日問題一件/2救国団叢刊第2輯》,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復製,Reel No.1—0063。。7月14日,归国的广东籍留日学生联合广东各校学生及社会人士,组织召开国民大会。与会者发言踊跃、群情激愤。会议宣言更是直接表示,“人民为外交之后盾,外交视人民为转移,大凡国亡,不亡于政府,实亡于人民”,此次政府与日方签订协约,其原因在于国民对政府外交监督不力,国家兴亡,在此一举,愿全体国民急起而图之*《粤省开拒约国民大会之状况》,《益世报》1918年7月25日。。8月3日,邵飘萍亦刊发社论,指责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协定,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对外交不加以研究,另一方面则在于国民“对于外交问题亦盲从而依附之”,国民与政府“两者皆失监督指导之道,蹈内政外交不分之弊”。为此提出“全国人所当一致监视政府之方针,以勿使轶出范围之外”的建议*《出兵问题与国防问题》,《益世报》1918年8月3日。。
时至1918年底,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在国内,是年10月10日,徐世昌“与前代办总统冯国璋交接”,就任北京政府总统,主战派段祺瑞被免去国务总理职务,由钱能训重新组阁*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存稿,戊午年九月初六日条,未刊。。而在美国方面的劝说下,北京政府与南方军政府开启“和议”事宜*The Minister in China(Reinsch)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Paper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11,1919, p.294.。23日,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和平期成会”,其后国内政局南北对峙的紧张态势得以初步缓解*《致京省通电》(1918年10月23日),熊希龄:《熊希龄先生遗稿》电稿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3299、3300页。。国际上,随着1918年11月11日德国被迫签订停战协定,持续四年多的欧战以同盟国的战败而告终,旨在解决战后和平问题的巴黎和会即将召开。
在国内外形势趋于好转之际,以舆论界为代表的中国知识人士也敏锐地观察到外交新动向,呼吁国民积极参与外交。11月17日,《时报》社论表示,欧战结束后,国际局势日趋明朗,此为“可喜”之事,然而我国“国民对于外交漠然不甚注意,一听政府措置”,此又为“可忧”之事*《可喜可忧之外交》,《时报》1918年11月17日。。戈公振所撰时评进一步指出,巴黎和会是我国能否收回所失利权的“一大关键”,虽然此事“有政府之主持,然所关甚巨,国民岂能置之不问?”*《和议研究会》,《时报》1918年11月26日。商逵则在《欧战后学生之觉悟》一文中,号召包括归国留日学生在内的广大学生,在巴黎和会召开之际,共同督促政府外交,担当挽回国家利权的重任,并勉励广大学生,“其责任之重,重于千钧,时期之急,急于燃眉,地位之苦,苦于尝胆”*商逵:《欧战后学生之觉悟》,《学生杂志》第5卷第12号,1918年12月5日。。留日学生救国团更是直接提出,当此巴黎和会召开前夕,全体国人应当“群起共相讨议,造成舆论,以供当局之采择,而备外人考察,或联络团体,选举代表赴欧陈诉于平和大会,以收国民运动之效”*《救国团之通电》,《时报》1918年12月7日。。
与此同时,以梁启超、汤化龙、汪大燮、林长民、张君劢等为代表的研究系,因在新国会选举中仅得二十余席,败给了由段祺瑞扶植的安福系,建立一个“研究系国会”的政治愿望遂遭重创*谢彬:《民国政党史》,(上海)学术研究会总会,1925年发行,第78页。。研究系在政治上失势后,欲借欧战后的外交之机,重新建立其在国内政坛上的影响力。为此,梁启超数次赴北京与徐世昌商谈,准备“以私人名义赴欧观察”*《梁任公将赴欧洲》,长沙《大公报》1918年11月23日。。1918年12月18日,徐世昌决定设立外交委员会,以研究和制定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外交委员会成员包括汪大燮、孙宝琦、熊希龄、林长民、张国淦、周自齐、王宠惠等人。显然,这是一个由研究系所掌握的机构,其重要宗旨是借外交参与之机影响政局*李新:《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2卷(1916—1920),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89页。。
在国内各界纷纷提出参与外交要求的推动下,全国各大媒体、各界人士谈论“国民外交”的现象亦屡见不鲜。12月12日,《益世报》刊载题为《今后之国民外交》的社论,称“外交之所凭藉者民气耳,有民气为之后盾,则政府之气壮,既不至受外人挟制,外人亦不敢遽肆欺凌”,故在巴黎和会即将召开之际,全体国民当发起“国民外交”,通过“联合团体,万众一心,再接再厉,以为政府奥援”*《今后之国民外交》,《益世报》1918年12月12日。。24日,蔡元培在国民外交后援会的演讲大会上表示,巴黎和会“关系国际外交异常重大”,不仅打破过去严守秘密外交政策的状况,而且为实行国民外交提供了重要基础,堪称“外交革命”*《在外交后援会的演说》(1918年12月24日),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88页。。需要强调的是,蔡元培在当天的演讲中指出,当前“各国均标榜国民外交,此后外交无秘密之必要,无论何国国民均须注意”*《昨日之外交演讲会》,天津《大公报》1918年12月24日。《外交讲演会再志》,天津《大公报》1918年12月24日。。31日,邵力子亦在《民国七年之上海》一文中,称赞“国民对外交及公益,皆有长足之进步”,尤其是在欧战结束后,国内各团体“皆能表示国民外交之成绩”,大家关心时局,积极参与对外交涉*傅学文编:《邵力子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5页。。
值得注意的是,时人论及“国民外交”时,不但呼吁国民为政府外交后盾,还强调国民外交对政府外交的“监督之责”。《中华新报》主笔汪馥泉撰写题为《国民外交》的社论称,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各国国民“无不树立团体,畅发舆论,同心努力,作外交之后援”,反观我国国民却无动于衷,为此呼吁国民结成强有力之团体,“对外固为国民之外交”,对内监督政府外交,此即“国民外交之道也”*《国民外交》,《中华新报》1918年12月23日。。梁启超亦在“国际税法平等会”的招待会上,称赞该会成员是中国“实业界之有力人物”;提出“现世界之新潮流是曰国民外交”;认为“所谓国民外交者,非多数国民自办外交之谓也,乃一国外交方针,必以国民之利害为前提”;勉励大家“当此国民外交时代”,一面积极参与外交,“为国民外交之先河”,一面“督促政府”,“审察内外形势”,借巴黎和会召开之机,维护国家主权与利益*《公宴梁任公纪略》,《时报》1918年12月28日。。杨昌济则从学生立场出发,宣称“今日大多数之国民,毫无智识,无思想,故无舆论,无清议,无组织政治之能,无监督官僚之势”。巴黎和会为中国挽回已失利权之良机,广大学生有“独立之思想”,应当以实际行动,“唤起国民之自觉”,积极参与外交,监督政府外交*杨昌济:《告学生》,《国民》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0日。。
综上可见,围绕中日交涉,包括国内学界、商界、舆论界等在内的广大人士掀起了反对中日协定的热潮。诚然,各界人士对政府秘密外交的批评十分尖锐,留日学生大规模的罢学归国行动更是造成了北京政府当局的触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国人始终宣称以政府外交为主体,国民外交为之“后援”(或“后盾”)。而与以往所不同的是,时人更加强调国民外交在对外交涉中的对内“监督之责”。这一动向和趋势随着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的召开而表现得更为突出,并且最终推动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国民外交协会的出现。
三、国民外交协会与北京政府外交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参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包括驻法公使胡惟德、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以及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3页。。北京政府指派代表团的任务是:(一)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省的一切利益,不得将这些利益让日本继承;(二)取消“民四条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三)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等特殊权益;(四)断绝德、奥等同盟国在华经济利益。
然而,日本政府却强行要求中国代表,非经日本同意,所有主张不能在和会提出,尤其是中日密约,坚决不许中国在和会召开期间公布*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重光葵外交回忆录》,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年,第24页。。显然,日本政府欲借巴黎和会之机,强行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颜惠庆著,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第1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第818页。。
在此情形下,国内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外交诉求。2月5日,熊希龄分别密电南、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和朱桂莘,称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虽有挽回主权重任,但是北京政府恐“无能力对付日本,或致受胁承诺”,为此呼吁南北双方“目前将内政暂缓商议,速以此次外交为第一问题,赶开临时紧急会议,联电政府”,要求立即收回山东权益,“以救国危”*《致上海唐总代表南京朱总代表等电》(1919年2月5日),《熊希龄先生遗稿》电稿四,第3492、3493页。。收到函电的当天,唐绍仪急电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吁请严厉拒绝日本无理要求,请求北京政府将中日密约公之于众,并称“总统对于此事不能置若罔闻,以违人民之意”,否则“人民因之应行表示其对于总统之态度”,予以坚决地反对。与此同时,全国和平联合会、商业公会、出口公会、各省议会、教育会等函电交驰,纷纷电请北京政府与巴黎和会中方代表,呼吁对日本无理要求“严词拒绝,以保主权”*《国民对于外交之声援》,《晨报》1919年2月7日。。
诚然,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初,国人为挽救国家主权和利益奔走呼号、函电飞驰,但是对于“国民宜如何厚其舆论之力以为后盾,我政府宜如何利赖之、信任之,使得专力肆意自由发言,勿失此千载一时之会”,仅凭个别在野人士大声疾呼,抑或由数个团体发几通电报等举措,似乎难以办到*《祸吾国者谁乎》,《益世报》1919年2月8日。。为了切实敦促政府外交,借巴黎和会召开之机,“伸张民意于国际间”,2月11日,熊希龄以在野人士身份致电张謇,建议“联络全国各界合组国民外交协会”*《致南通张季直电》(1919年2月11日),《熊希龄先生遗稿》电稿四,第3052页。。在熊氏多方联络下,16日,北京的国民外交后援会、和平期成会、京师商会、政治学社、国际研究社、兰社、战后外交研究会等团体联合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国民外交协会。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众人推举熊希龄、张謇、林长民、王宠惠、严修、范源濂、庄蕴宽7人为理事,并公布协会的宣言称:当前“国势陵夷,儳焉不可终日,吾人追原祸始,误于政府之无外交政策者半,误于国民不解国民外交作用者亦半,假令政府而有外交政策,国民亦解国民外交作用,上下一心……爰设斯会,一方表示公正民意,一方力为政府后援,有志之士,曷兴乎来云云”*《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会纪事》,《晨报》1919年2月17日。。
显然,上述宣言旨在呼吁国民参与外交,负起监督政府外交之责,充分发挥“国民外交作用”。而为广泛吸纳社会各界人士入会,扩大国民外交协会的组织规模和社会影响,协会《简章》明确规定:“凡中华民国人民年满二十以上者,经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得为本会会员。”*外交协会著:《国民外交协会简章》,民国八年油印本,第11页,见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普通古籍阅览室。
国民外交协会一经成立,便立即投入到国民外交运动之中。17日,该会联合北京总商会、国际联盟同志会等团体,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表示国民对于国际联盟之热望及声援,并希望全国一致发电赞助”*《国内专电》,《时报》1919年2月17日。。21日,国民外交协会通电全国各省议会、农工商会、教育会及各报馆,宣布该会对外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各项工作;(二)撤销势力范围并制定实行方法;(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四)撤销领事裁判权;(五)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借*《国民外交协会声明主张通电》,《益世报》1919年2月23日。。
与当时国内众多团体所不同的是,国民外交协会不但发布明确的宣言、制定详细的外交主张,而且将上述主张“制成议案”,以期影响和敦促北京政府外交当局*《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发表对外主张电》,长沙《大公报》1919年2月24日。。21日,为了向广大民众宣传国民外交协会的宗旨和对外主张,该会在北京中央公园召开演说大会。会上蔡元培、梁秋水、林长民、梁士诒等人相继发言,演说实行“国民外交”的意义和作用*《国民外交协会讲演会纪事》,《晨报》1919年2月24日。。蔡元培在做题为《自他均利的外交》的演说时称:过去“我国外交之所以失败,由一切委诸少数当局之手,常以秘密行之”,故自今以后,全体国民应当联合团体,以强有力的国民外交声势,一方面作为政府“外交当局之后援”,另一方面要监督和敦促政府,在巴黎和会中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此即国民外交协会之所由发起,而今日到会诸君所不可不注意者也”*《自他均利的外交——在国民外交协会讲演会上的演说》(1919年2月21日),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59页。。
不仅如此,为了促使北京政府将中日密约早日公布,以及催促中国代表将山东问题提交巴黎和会讨论,国民外交协会还指派梁秋水等人为代表,赴北京政府总统府申诉。梁秋水向代为接见的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说,“山东问题实为此次外交一大关键”,英美等国欲将山东权益转让日本,我国“最要之对待方法,惟有请政府电训专使,勿予署名”。面对国民外交协会代表的强烈要求,吴氏表示总统徐世昌收回山东利权的态度“极坚决”,将采取行动,“电训专使,极力坚持”*《国民外交协会代表与府秘书长谈话》,《晨报》1919年3月5日。。随后国民外交协会代表拜见代理外交总长陈箓,向其详细了解巴黎和会召开以来的外交动向。代表们不仅要求政府外交“以民意为根据”,严厉拒绝日本无理要求,而且宣称国民于重要外交问题,监督政府,赞助政府,“实为人民之天职”*《日本新要求之经过》,《学生杂志》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5日。。鉴于日益严峻的外交态势,在各方的催促下,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在与外交部商议后,决定自3月14日起,将中日密约向全国公布*《为中日密约提出欧会请力与主持》(1919年3月10日),《(民国)南北议和会议卷宗集成》,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2916—2924页。。毋庸置疑,中日密约的公布,固然是北京政府对国内外局势综合判断后的重要举措,同时与国人的“国民外交”行动影响政府外交不无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国民外交协会代表通过访谒总统府和外交部,初步了解到和会召开后的国际局势,但由于远隔重洋,协会同人无法及时了解巴黎和会各方的外交动向,影响对时局的判断与行动。对此,国民外交协会在各大报刊及北京各学校发布召开第二次演讲大会的通告*《国民外交协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3分册第344期,1919年3月28日。。4月8日,国民外交协会理事张謇、熊希龄、林长民等人,利用其与研究系的特殊关系,致电正在欧洲考察的梁启超,邀请其作为国民外交协会的代表,将巴黎和会各国外交动向及时电告协会*《请允为国民外交协会代表并主持巴黎和会事与张謇等致梁启超函》(1919年4月8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7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7页。。
对于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梁启超欣然应允。随着巴黎和会各国磋商的持续进行,中国代表日益被置于不利境地。4月16日,英、法、美、日、意五国开会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居然被排斥在外,未能参会。由于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强硬态度,美国总统威尔逊为避免和会破产,决定牺牲中国利益,满足日本要求*《外交報告筆記》,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復製,No.1。。梁启超察觉到这一动向后,立即函电国民外交协会,称“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山东问题的形势十分严峻,“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80页。。国民外交协会接到梁氏电报后,于5月3日紧急召开全体大会,决定阻止代表在山东问题上签字,并议决办法四项:(一)于5月7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以及英、法等国将山东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三)若我国对外主张不能在和会上得到实现,则请政府立即撤回专使;(四)向英、美、法、意四国使馆致电,陈述国人的对外意见*《北京国民外交协会为青岛问题定五七召开国民大会电》(1919年5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36页。。
中国在山东问题上交涉的失败,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索。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群情激愤,一场规模空前的“五四”爱国运动随即引发。很快,国民外交协会成为这一运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该会通过广泛发动国人参与外交活动,引导国人督促政府外交,使得中国国民外交“对内”态势日益增强。7日,在国民外交协会的召集下,北大、清华等校学生齐集中央公园,共同商讨应对之策*《七日国民大会最后一幕》,《国民公报》1919年5月9日。。会上,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熊希龄极力呼吁国人对政府“非严重鞭策不可”,表现出对北京政府外交的强烈不满*《国耻纪念日之国民大会》,《晨报》1919年5月8日。。
诚然,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国民的“外交觉悟”,进一步激发了国人参与外交的热情,尤其是英美法日意五国操纵巴黎和会,商议制定损害中国国家主权与利益之条约,“国民誓不承认而必力起抗拒”*达人:《国民运动之价值》,《爱国》第2号,1919年。。与此同时,在国民外交协会的引导下,各界民众对北京政府外交的声诉与谴责,使得中国国民外交行动愈加强调对内“监督之责”。对此,张庭英在《国际联盟与中国今后之外交后援》一文中指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之所以拒绝签字,其原因是国民一致反对,政府“外交借重于国民”,然后才能拒签和约。这充分表明,今后“外交之得失,其关键不在政府之能力若何,而在国民之能力若何”*张庭英:《国际联盟与中国今后之外交后援》,《北京大学月刊》第5期,1919年。。《世界大势》也刊载题为《国民外交为今日之新趋势》的社论,表示“外交仅赖政府之时代已为过去之事实,今后之外交乃须国民之自觉”,监督与敦促政府,使其以国家利益为重,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国民外交为今日之新趋势》,《世界大势》第10号,1919年。。《盛京时报》一篇题为《对外与对内》的社论,则对国民外交走向问题加以分析,认为“中国之危险,不在对外之不振,而在对内之不能统一”,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及其活动,说明今日“民气”可用,“国民外交”的对内“监督之责”,势在必行*《对外与对内》,《盛京时报》1919年5月13日。。
由此可见,巴黎和会前后,国民外交协会通过大力发动和引导各界人士,一面监督政府外交,一面阻止中方代表签字,成为影响民国外交走向的重要因素。而国民外交的“对内”趋向的形成,无疑给北京政府当局造成震动。山东问题交涉失败后,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被相继罢免,6月13日,国务总理钱能训亦被迫离职,北京政府国务院面临再度组阁的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近代国民外交“对内”趋向形成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党争和政争因素。尤其是以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研究系,在政治失利后欲借外交之机,重新建立其在国内政坛的地位。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会上,梁氏以《外交欤内政欤》为题坦言道,五四前后的国民外交运动,“与其说是纯外交的,毋宁说是半内政的,因为他进行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外交欤内政欤》(1921年),《梁启超全集》第11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01页。。而在钱能训内阁遭到弹劾后,北京政府内部皖系与研究系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激化。皖系指责林长民、熊希龄等人煽动五四运动,造成了政府内部“党争”的局面。对此,熊希龄致函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为自己申辩称,国民外交协会的组织成立,最初由汪大燮提出,然后禀告总统徐世昌,并得其同意。该会的发起成立,“均非弟之主动,弟不过因人成事而已。当时弟等之意,重在与政府一致,为政府之后盾”,不料“五月四日之变,出诸意外”,国民外交行动趋于“对内”,大家纷纷起而监督与敦促政府外交,进而影响到国内政局*《复吴秘书长函》(1919年),《熊希龄先生遗稿》电稿五,第4573、4574页。。尽管熊氏此函意在为自己申辩,但毋庸讳言,国民外交协会的出现及其活动,进一步推动国民外交的“对内”趋向,坐实了对政府外交的“监督之责”。
四、结语
总之,巴黎和会前后,国民外交言论声势浩大,国民外交活动此起彼伏,近代中国可谓是步入“国民外交时代”。其中,国内舆论界对中日秘密谈判的揭露与批评,孕育了国民外交“对内”趋向,诠释了“国民外交之意义”;留日学生的罢学归国行动,强化了“国民外交”对政府外交的“监督之责”,阐发了“国民外交之道”;政、商、学、舆论界等联合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则以实际行动影响政府外交,实现“国民外交作用”。对此,钱基博在《国民外交常识》一书中指出,在欧战行将告终之际,中国外交的首要“善后方策”,是“我国民宜监督政府,力持公开外交”*钱基博:《国民外交常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68页。。此语可谓是道出了巴黎和会召开前夕中国国民外交的新动向,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国民外交协会发起成立的历史动因。但是,时任江苏省无锡县图书馆馆长的钱基博,于1919年间撰写出版该书之时,难免以一种“后来者”的视角,来反观欧战结束前后的这段历史,其中或多或少地掺杂了主观色彩。
诚然,当前学界关于近代“国民外交”概念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其对内监督政府外交或“为政府外交之后盾”的内涵,这与初入中国的日本国民外交理念表面上较为吻合,但却与清末国人“外交之本体实在国民”、“国民自为外交上之主体”等口号差异甚大。
事实上,清末“国民外交”经由日本进入中国,时人因应于内忧外患的时局,对其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和改造。尤其是当时国人认为“既然国家本来就不仅仅属于政府,而是全体国民,再加上清政府对外交涉招招失败,丧权辱国,在国民眼中失去日益代表国家的资格”,“民国以后则逐渐演化为政府外交的后援和补充”*桑兵:《华洋变形的不同世界》,《学术研究》2011年第3期。。总体而言,清末至民初,“国民外交”经历了由对外转向对内的调适,其表现是国民从外交“主体”地位向“后援”的转换,其实质则是国民对政府能否代表国家的认同与考量。
换言之,如果说“国民外交”思想的天秤,同时包括对外与对内两个砝码,那么这两个砝码的分量,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并非等同。而要深入考察国民外交的对外抑或对内趋向,把握近代中国国民外交的历史走向,则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以时间为径,对国民外交协会这座近代国民外交史上的“里程碑”,所成立的时空背景和历史动因进行客观地探讨。就此而言,作为“国民外交”乃至北京政府外交走向的重要关节,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及其活动,为近代“国民外交”的历史走向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杨海文】
*收稿日期:2015—11—08
作者简介:曾荣,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北京10023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