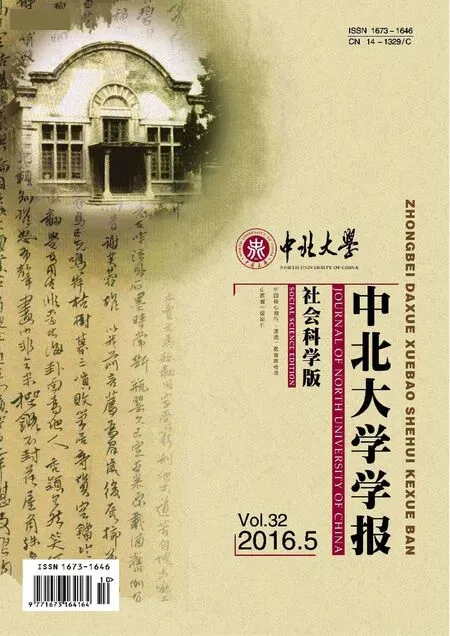都市异乡客的幸福追寻
——论《嘉莉妹妹》对移民的价值取向书写
2016-01-24秦丹丹
秦丹丹
(金陵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6)
都市异乡客的幸福追寻
——论《嘉莉妹妹》对移民的价值取向书写
秦丹丹
(金陵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6)
本文结合嘉莉妹妹的三点移民特质,探究嘉莉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价值取向以及为之付出的代价。对移民家庭的创伤记忆、传统意义上家园感的缺失以及道德监督的缺位共同铸就了嘉莉的幸福定位,使他在人生抉择的重大关头做出不问手段但求成功的价值选择。为了生存、快乐和自我实现,嘉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她异化了的幸福方向标指引下,嘉莉越界了社会传统道德,丧失了自己的本真,最终导致生命意义的虚无感。对移民价值取向的探究表明了德莱塞对美国社会转型期人文危机的深层忧患。
《嘉莉妹妹》; 城市移民; 20世纪初; 价值取向
作为德国移民的第九个孩子,美国大作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 )在多舛坎坷的创作岁月中以自己经历的人和事为主要素材,独辟蹊径,真实而细致地书写出芸芸众生在20世纪之交美国社会转型期所经历的心灵阵痛和信仰危机。对德莱塞小说的品读,不应简单化地将其界定为对自然主义生物学理论的演绎,他对自然主义是抱有矛盾态度的,《嘉莉妹妹》 《金融家》等有一定自然主义倾向的小说更多代表的是“违心的自然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两者的融合”[1]292;也不应笼统地将其所有作品贴上批判资本主义的标签,晚年的德莱塞锋芒不再,直言自己揭露社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发生革命”[4],他的晚期小说创作与宣传秩序、稳定和驯服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有着微妙的共谋关系的。[2]作为美国现代小说的先驱,德莱塞的伟大,在于“他的洞察力,他的同情心和他对生活的悲剧性的观点”[3]。研究德莱塞,我们必须结合催生文本的时代语境和作者的创作理念,对具体文本做具体分析。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当今时代背景下,再读反映20世纪美国相似时代语境的小说《嘉莉妹妹》,对身处社会转型期、面临价值观多元化选择的我们来说,在价值取向上必然受到一种人生启迪。
1 内因: 嘉莉的移民特质
内战之后,美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迅猛发展,为了获得更充足的劳动力,美国政府制定了宽松的移民政策。1863年,林肯政府通过了《鼓励外来移民法》。这一法令的出台,意味着美国政府公开奉行积极接纳外来移民、来者不拒的移民政策。移民数量呈几何级数快速攀升,庞杂的移民队伍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对洋洋自满地信奉新教的美国主流社会形成冲击。[5]作为移民的儿女,德莱塞深谙他们这一段独特的文化体验,他取材于生活,写下了一篇篇外乡移民到达美国大都市后所经历的悲欢离合。《嘉莉妹妹》讲述的是移民的第三代——嘉莉的都市化过程。乍别家乡,十八岁的嘉莉固然有些伤感,但在她心灵深处,“绝对不是因为家园有什么好处值得留恋”[6]1,一笔带过的离愁别绪只是转瞬即逝的多情,很快她的思绪就转到即将开启的都市生活上。嘉莉初来繁华的芝加哥,满怀年轻人对未来的种种幻想,却很快因失业、贫病交加几近流落街头。但她不愿回到她的家乡,因为与她朝夕相伴的是村庄和田野,父亲在面粉厂干活,父辈的贫穷在她心灵深处留下了永恒的伤痛。冬日的枯枝唤起了她对老家的回忆:“以前在家时,每年十二月份从家里的窗前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景色。她不禁呆住了,痛苦地扭着一双小手。”[6]72多年后安居下来的她看到窗前掠过的面孔,“想起自己的老父亲穿着沾满面粉的工作服,在磨坊里干活……她感到很悲哀,只是很少说出来”[6]135。贫困的家不能给远行的她提供像样的行囊,她能带出的全部行李“不过是一只小箱子,一个廉价的仿鳄鱼皮小背包,一份装在纸盒里权当午饭的点心,一只黄色小皮夹……至于现金,只有四美元”[6]1。对家庭和父辈的创伤记忆坚定了农家子女嘉莉留在繁华大都市的决心,充满梦想和希望的她抱着改变自己命运的幻想来城市谋求发展。在她看来,不管以什么方式,只要能生存下来,就有可能抓住机会,就有可能获得金钱和财富。而一旦回老家,面对的只有可怕的贫穷和单调乏味的生活。在杜鲁埃那里,她可以获得老家得不到的一切。因此,她宁可选择偷偷离开姐姐家、仰陌生男人的鼻息、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也不愿再回老家。小说这样描写走投无路的她仍坚定地选择都市而不是农村:“回哥伦比亚城,她能干什么呢?那里单调狭隘的生活她烦透了。而芝加哥这个神秘的大城市,还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她,她所见的一切,才刚刚向她展示了无限可能的机会。一想到要她离开这里,回到那闭塞的地方过那种乏味至极的生活,她就气愤得要叫起来……汉生夫妇盼着她回老家,她则想着要离开他们,但不是回老家。”[6]59这里还需要提起的是,小说中的移民——无论是嘉莉,还是嘉莉的姐夫汉生——都不是第一代移民。嘉莉是第三代移民,汉生是第二代,“生在美国,父亲是瑞典人”[6]10,他们已经没有第一代移民浓厚的根的情结,对生养自己的家乡感情淡漠,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发家致富,实现自己的美国梦——汉生的雄心是在芝加哥西区盖起自己的房子,而嘉莉“很快就领会到人生中还有更多的快乐,开始狂热地追求物质享受”[6]2。可以说,嘉莉这批移民的后代“对任何地方都没有很深的依恋”[7]30。当嘉莉被赫斯特乌德挟持到蒙特利尔又到纽约,她对度过平生第一段不凡岁月的芝加哥也没有多少留恋,小说是这样描绘嘉莉“旅行”时的感受:
(嘉莉)以惊奇的目光望着窗外不断掠过的村庄,那些简朴的农舍和舒适的小屋。对她而言,这是一个新奇有趣的世界,她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被击败了,她依然满怀希望。大城市里有的是机会,说不定她会摆脱束缚,获得自由——谁知道呢?说不定她会幸福快乐的。[6]260
而到了纽约,嘉莉的感受由惊奇进一步上升为欣喜:
火车沿着哈德森河行驶,圆圆的青山就像一排排哨兵,耸立在辽阔的河谷两边。她被这美丽的风光吸引了。以前只是听说过哈德森河,纽约大都市,现在就在眼前,她望着车窗外的风光,心里充满了惊叹……看到哈莱姆河上的几只船以及东河河面上更多的船,她一颗年轻的心不禁充满了喜悦。这是第一个迹象,说明大海就在前面。[6]271
在十八岁的嘉莉看来,祖辈父辈从异域他乡移居到美国,却只能给她一个贫穷得令她不愿想起的家,如今她已跻身都市,并不断地向更大的都市迁移。对她而言,家不过是任何能给她提供舒适和体面生活的住所。因而她能很快接受一个又一个更好的家。在这个都市异乡客心里,传统意义上的家的意识已经淡漠,更谈不上任何家庭观念,嘉莉不断离开自己曾经的家,而且“任何家从来也没有在她心里留下任何印象;另外一个家或家庭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经济安排而已”[8]。同样,当赫斯特伍德每况愈下、穷困潦倒之际,嘉莉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他,朝着自己愈来愈辉煌的百老汇明星宝座进发。这种四海为家、随遇而安的性格特征,加上嘉莉与生俱来的利己心,使她得以轻装上阵、无牵无挂地在都市冒险征途上勇往直前。
除了上述两点,嘉莉之所以做出这些在传统清教伦理意义上伤风败俗的价值抉择,还与另外一个移民特质分不开,那就是道德监督力度在年轻移民子女身上的弱化。小说开篇就暗示了嘉莉的“涉世未深”[6]2以及她的道德监督人的缺位。“要是身边没人给你谨慎的劝导,有多少谎言会吹进你没有设防的耳朵里呀!”[6]2嘉莉的父亲和母亲——传统意义上道德施教者和监督者——在小说中是缺位的。“这部小说的各种手稿中几乎都未曾提到嘉莉的母亲,她的父亲也只是在嘉莉所乘坐的火车经过他工作的面粉厂的时候,出现在她的脑海里”[9];嘉莉的姐夫姐姐,觉察到了嘉莉不合规范的要求和表现——想看戏、站在楼下看街景、搬出去与别人同居——却只是旁观,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制止。对于杜鲁埃来说,嘉莉是轻而易举就落网了的猎物,因为“嘉莉在家时就没有多么严格的家规束缚过她。假如有,她此刻一定会深受良心的折磨而痛苦”[6]74。她甚至连“一成不变的习惯”或者规矩也没有,“倘若她以前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习惯,此刻就该发生作用”[6]73。在这里,德莱塞将嘉莉家庭观的弱化和她道德监督力度的缺失都与她的移民家庭背景联系到了一起。缺失传统家规督管的嘉莉虽偶尔也能感到良心的责问,可它“只是一颗平常渺小的良心,代表着一种世俗的见解”[6]86。嘉莉总能找出各种托辞,身处呼啸的寒风中,“贫困代她做出了回答”[6]86。由此可见,当嘉莉在沉浮的关键时刻被迫进行价值抉择时,对父辈的创伤记忆催生了她在都市风尘中继续冒险的意志,家园情结的丧失默许了她一次次反常的迁居,道德监督的缺失姑息了她在伦常规范层面的不断滑坡。在光怪陆离的都市引力下,嘉莉开始了她的幸福追寻。
2 外因: 嘉莉的无尽所求
在嘉莉到达芝加哥之前,作者德莱塞就点明了这个农家女儿去大都市的初衷:“她很看重自己的魅力,很快就领会到人生中还有更多的快乐,开始狂热地追求物质享受。她犹如一个装备尚不齐全的小骑士,去冒险勘察这个神秘的都市,狂野地梦想自己从遥远的地方获得某种未知的至高无上的力量,来征服这个城市,把它踏在脚下——让他像那诚心忏悔的浪子,伏在一个女人的脚下。”[6]2这段话阐明了两点: 嘉莉的首要追求是物质享受,而她憧憬中获得享受的途径是靠投机取巧。嘉莉对物质的推崇不仅表现在她对穿着的在意、对外在的看中、对玩乐的追求,更体现在她为了生存,选择的是求利务实的价值取向。在是非取舍的关键时刻,嘉莉首肯的是物质,背弃的是情感、承诺和道德。初遇杜鲁埃,嘉莉立刻身不由己地被他光鲜的外表所吸引,只言片语的交谈便感觉两人情分不同一般。在站台见到久违的姐姐,她感受不到任何亲情的温暖,相反,“看到他(杜鲁埃)离开,她感到怅然若失……虽然和姐姐在一起,她却感到非常孤单,孤单地一个人漂泊在波涛汹涌、冷酷无情的大海里”[6]9。开往芝加哥的旅途初步奠定了嘉莉城市逐梦的目标: 富裕的生活、华美的服饰与享乐的生活。然而,下火车的那一刻,生活的艰辛和劳苦不期而至,打破了嘉莉的黄粱美梦。十八年的亲情在巨大的反差面前变得一钱不值,和亲人在一起,她感到的却只有失落和孤独。进城后的嘉莉在物质的强大磁力面前,将承诺抛诸脑后。火车上的她尚且 “明白自己不是来享乐的”[6]5,“自己是孤身一人远离家乡的,跑到这茫茫人海中挣扎谋生”[6]8的,寄居姐姐家,心照不宣她明白自己要付食宿费。然而,嘉莉已经狂热地迷上了这个商业化都市。刚找到工作——工作还没开始,工资还没拿到,食宿费还需交出来——嘉莉就将承诺抛诸脑后。任何事都可以不管不顾,自己的无限膨胀的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新伞、新帽子不合时宜地被她一一买回来。对于钱用光了怎么办,承诺不能兑现怎么办,嘉莉是从来不去想的。嘉莉不是未雨绸缪的人,更不是勤劳实干的人。对嘉莉的拜物欲最具说明性的例子,当然是嘉莉在人生重要关头所做的两次抉择。第一次是她穷困潦倒之际不顾伦理道德,与杜鲁埃同居。第二次是私情暴露、生存再次堪忧之际,她半推半就,与赫斯特伍德私奔到纽约。无论在芝加哥还是在纽约,身无分文的嘉莉首先要满足她的物质需求,因为这是生存的根本,因而,嘉莉在她同杜鲁埃和赫斯特伍德的关系中不得不充分权衡道德成本与经济受益之间的关系。[11]奢望轻轻松松获得物质享乐,嘉莉只能“重复她与这座城市的道德遭遇”[12],将自己推到社会道德的边缘。
安顿下来的嘉莉,摆脱了一度威胁她的衣食之忧,刚进城时逛街、看戏、玩乐等精神需求现在成为了她第二阶段的幸福定位。她不仅热衷于看展览、赏宅邸,也不仅追求优雅的步态、精致的发式,一次偶然的演出,让她具备了索要婚姻名分和情感回应的资本。这次演出对嘉莉的人生具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演出激起了她心灵深处的共鸣,排演丰富了她单调的幽居生活。“那非凡的舞台魅力,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华丽的服装,如潮的掌声,所有这一切,都那样地吸引着她,使她觉得自己也可以登台表演,自己也有征服观众的本领。”[6]148排练给她带来了她从不曾体验过的快乐。其次,演出给嘉莉的天分提供了绽放的机会,嘉莉收获了自信和骄傲,一扫她作为都市异乡来客的自卑情结,令她魅力倍增。杜鲁埃发现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孤苦无依、向他乞怜的嘉莉了。她的声音变得轻快活泼,这也是以前没有的。她不再用充满依赖的目光看他”[6]183。而赫斯特伍德“从未见过这位姑娘如此兴奋。她说话的时候,脸颊绯红,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往日的忧伤也不见了踪影,浑身都洋溢着演出带来的喜悦”[6]152。更重要的是,嘉莉敏锐地意识到,她的生活出现转机,她可以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她头一遭尝到受宠的滋味,头一遭成为受人仰慕、被人追求的人物。成功所带来的独立人格此刻初现锋芒。她和情人的关系完全改变过来了。她不再从低处仰望她的情人,而是站在高处俯视他了……她正初次体现到那种微妙的变化,她从乞求者变成了布施者。”[6]178-183于是,她拒绝了杜鲁埃的求婚,却要求能给她“体面生活”[6]124的赫斯特伍德定下明确的婚期。《嘉莉妹妹》“最深刻犀利地刻画了性的魅力和经济依赖之间的关系”[13]。演出的成功为这个穷困的移民女儿带来焕然一新的精神气质,也为她在小说后半部再次遭遇困顿之际,选择演艺人生、走向自立提供了资本。
按照露西·伊利格瑞的理论,女性只有通过接受父权社会赋予她们的角色才能够“将自己的隶属地位转化为肯定因素并最终消解这种隶属身份”[14]。嘉莉在与两个男人相处的时候,曾多次要求婚姻的名分,她试图借助婚姻,最大程度地屈从于女性的被动角色,依赖男性获得理想生活。然而,当这个愿望一次次化为泡影,当她发现梦寐以求的婚姻并不能帮自己实现梦想的时候,她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另谋生路。“倘若他(赫斯特伍德)还不能尽快找到工作,自己就必须要采取行动了。也许她不得不出门,再次孤身奋斗。”[6]345追求女性隶属身份的消解,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通过自我实现方能达到。认准了第三阶段的幸福定位,嘉莉立即行动起来,这次的求职,她表现出初来芝加哥所没有的耐力和坚韧,她百折不挠,屡败屡战,而赫斯特伍德却在家整日枯坐,坐吃山空。几周后,嘉莉挤进了百老汇一家剧院的歌舞队,从最卑微的合唱队员干起。很快,她的美貌、天分和气质让她脱颖而出,日益走红,终于成为轰动纽约的名角。商业化都市的残酷竞争,让嘉莉逐渐成熟,惨痛的经历让她认识到自己必须强大起来,必须实现自我的价值。
嘉莉虽然胆怯,可能力很强。别人的信赖使她觉得自己好像肯定能走红,既然如此,她胆子也就大了起来。她经历过人世沧桑,这对她很有帮助。她再也不会为男人一句轻飘飘的话而晕头转向了,她已经懂得,男人也会变,也会失败。过于露骨的吹捧已经对她不起作用。必须具备优秀品质——善意的优秀品质,如阿姆斯那般才华横溢的人物所具备的优秀品质,才可能打动她。[6]404
这段话确立了嘉莉的“新女性”形象。她走出了男权的藩篱,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我,获得了独立的人格,也获得了掌管钱袋子的女性在家中享有的“特权”: 她学会质疑,“既然她在几周内就找到工作,他几个月来懒惰闲散、一事无成是没有道理的”[6]356; 她萌生反抗,“现在(赫斯特伍德回来后)她只得停止练习,准备晚饭。心中的怨气也由此而生。她既要工作又要做饭。难道她在演出的同时还得操持家务吗”[6]359; 她开始不满,“她如今有了实实在在的收入……看样子他(赫斯特伍德)还想依靠她那可怜的十二块钱生活呢”[6]359-360; 慢慢地,她开始逆反,“她经济上的日益独立增强了她冷眼旁观的勇气”[6]360。可见,现在的嘉莉不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社会行为,得到了全凭自己掌控的经济权利,她还获得了真正的女性自我意识,她不再迷信男性权威,开始了独立的思考和行动,而这一切,都是工作和经济收入带来的。正如玛丽·瑞安所指出的,“不是教室,也不是公寓,而是工作,为培养年轻女性所显示的独立精神提供了最广泛和最合意的环境”[15],最终,为了“获得自由”[6]405,嘉莉离开了颓废不堪的赫斯特伍德,选择了一条靠自己打拼走向成功的道路。嘉莉的移民背景和特质决定了她在都市的幸福定位,她从一个渴求温饱的都市异乡客成长为一个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摆脱了男权桎梏、敢于并成功地谋求自我价值的时代新女性。
3 代价: 人性感知的失落
现代化大潮浩浩荡荡,嘉莉就像灵巧的弄潮儿,在她的都市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不断调整自己的幸福定位,谋求更好的价值取舍。然而,评论界普遍注意到,幸福的实现没有给嘉莉带来切实的快乐。汤姆斯·P·里吉奥以“嘉莉的忧伤”为主题论述道:“直到最后,嘉莉始终是忧郁的,当她看到她希望企及的一切——包括名望——都不能满足她的需要。”[7]25有论者指出:“她的每一次成功都反衬出了她的梦想的一次次幻灭。”[16]嘉莉少有欢颜、倍感失落的情怀,正反映了都市移民在价值观迷失后遭遇的异质化生存状态。
嘉莉到达芝加哥不久,很快贫病交加,几近流落街头。杜鲁埃为她提供了一个安乐窝,摆脱了一度威胁她的生存危机。然而,内心的责问却让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倍受煎熬。从最初收下杜鲁埃的钱,到跟着他买这买那,到最终搬进杜鲁埃为她租下的小公寓,小说中随处可见嘉莉的踌躇和不决。“她揽镜自照,从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比以前漂亮的嘉莉;她审视自己的内心,内心的那面镜子代表的是自己的看法和世俗的观念,从这面镜子中看到的却是一个变坏的嘉莉。她在这两个嘉莉之间摇摆不定,布置哪个嘉莉才是真正的她。”[6]85嘉莉清楚地知道,她这次得以成功地逃避贫困和流离,付出的是童真。然而在物质诱惑和监督缺失的双重影响下,嘉莉对物质无尽的欲求占了上风,最终,“她干脆就把它(对同居一事的道德纠结)抛到脑后,压根儿不去想它”[6]87。伦常的僭越带来了良心的不安,而当她不再纠结于此事时,就意味着道德观的迷失。
在嘉莉的第二个幸福定位阶段,她努力学习并融入“新的生活状态”[6]98,每天她都“忙着调整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以适应新的环境”[6]102,她学习有关风度的知识,学会区分人的等级,学会融入新的社交圈,学会新阶层的潜规则,一时间,“各种琐碎的小事,对财富的推崇,还有那些传统的道德观念,都从这位浅薄的女人口里说出来,灌输给嘉莉,使嘉莉的思想一时混乱起来”[6]97。在杜鲁埃和海尔太太的双重影响下,嘉莉的欲望越来越强,欲壑难填,她很快发现自己虽然锦衣玉食,精神却越来越忧郁。
童年时关于神仙居所及帝王宫殿的幻想现在又浮现在眼前。她想象着,穿过那雕刻华丽的门廊,在那明亮的球形水晶灯的光辉下,走进嵌着雕花玻璃的大门,那里面一定是个快乐无忧的世界。她敢肯定,幸福就在那里。啊,倘若她能走过门前宽敞的路面,走进那宝石般华贵的大门,身穿华丽的服饰,高贵优雅地发号施令——一切的忧伤肯定就会一扫而光,一切痛苦肯定就会消失殆尽……她渴望着,渴望着,渴望着。思绪转得很快。一会儿思念起哥伦比亚老家的小屋,一会儿渴望能住进湖滨路边的豪宅里,一会儿妒羡某位女士的漂亮衣服,一会儿又渴望能置身于一个高雅的环境中。她感到无限的忧伤,一颗心在彷徨着、希冀着、幻想着。想到后来,她甚至觉得自己的处境似乎尤为孤苦无依。[6]108-109
这是一种可悲的异质化生存状态,曾经因可望拿到四块半的周薪“而兴奋得满脸通红”[6]26的嘉莉不见了,只剩下裹着绫罗绸缎却因欲壑难填而颦眉哀伤的嘉莉。嘉莉渴望通过消费活动和消费能力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品味和地位,她的生活价值观趋于感性和浅薄,她对中产阶级精神享受的盲从带来的是虚荣心、消费欲望和享乐欲望的无限膨胀,带来的是消费时代审美的迷失和困境。
在纽约靠自己的才艺和运气走向成功的明星嘉莉,早已摆脱了衣食劳顿之忧,在貌似富足的精神生活中她慢慢变得麻木不仁,梦寐以求的登报愿望实现了,可这并不能给她带来多大的欢乐。“她在这地方根本就没什么熟人可送……大都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嘉莉不久就体会到了。她发现……许多人接近她,都纯粹是为了寻欢作乐,毫无温暖的友谊和同情心可言。”[6]415她开始感到孤单,感到厌倦。她早已不再是她的移民父母生就的“嘉罗琳·米勃” 了; 和杜鲁埃同居时,她是杜鲁埃太太,名叫嘉莉·查尔斯; 在爱弗莱礼堂演出时,她是玛登达小姐,名叫嘉莉·玛登达; 和赫斯特伍德私奔到蒙特利尔时,她是乔·赫·嘉莉; 和赫斯特伍德结婚后,她成了韦勒太太,名叫嘉莉·韦勒; 登上百老汇舞台时,她又重新用起了嘉莉·玛登达的名字。姓名的不断更迭暗示着嘉莉在光怪陆离的都市漩涡中身份观念的丧失。“嘉莉在她的演艺生涯中日臻专业娴熟,然而她的观众与她在情感上却日趋疏离。”[17]45如今在百老汇正大红大紫的她,再也找不到她在芝加哥初演时那批观众的忠诚与激情,也永远无力重温当年的她演出成功后收获的欣喜和骄傲。“掌声和名气——这些以前在她的心目中遥不可及而又不可或缺的东西——如今已经微不足道了。”[6]472
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畸形发展带来了人的精神异化。《嘉莉妹妹》展示了主人公进城后的异质化生存状态,嘉莉以移民后代的身份进入都市,移民特殊的家庭背景和对生活的感悟主导着她的价值抉择,她从都市边缘人最终跻身都市名流,她为了生存、快乐和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她异化了的幸福方向标的指引下,嘉莉越界了社会传统道德,丧失了自己的本真,最终造成生命意义的虚无感。德莱塞在世纪之交书写移民对移民价值的寻求,充分体现了作家对美国社会转型期人文道德危机的深层忧患。
[1][美]爱德华兹·霍顿. 美国文学思想背景[M]. 房炜,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蒋道超. 难以超越文化的假定——20世纪中美德莱塞研究述评[G]∥德莱塞研究.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3]Walcutt, Charles Child. American literary naturalism: a divided stream[M]. Minneap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6.
[4]Matthieseen F O. Theodore dreiser[M].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1951.
[5]Pizer, Donal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merican realism and naturalism[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6][美]西奥多·德莱塞. 嘉莉妹妹[M]. 徐菊, 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2014.
[7]瑞科,烫姆斯. 忧伤的嘉莉[G]∥皮泽尔,剑桥美国小说新论·《嘉丽妹妹》新论. 英文影印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方成,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传统的文化建构与价值传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9][美]利罕,理查德. 城市,自我和叙事语篇[G]∥皮泽尔. 剑桥美国小说新论·《嘉丽妹妹》新论. 英文影印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美]理查德·利罕. 文学中的城市: 知识与文化的历史[M]. 吴子枫,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1]Lewis,Charles R. Desire and indifference in sister carrie: neoclassical economic anticipation[J]. Dreiser Studies, 1998(1-2): 18-32.
[12]Michaels. Walter Benn. Sister carrie’s popular E- economy[J]. Critical Inquiry, 1980(2): 373.
[13][美]拉泽尔·齐夫. 一八九〇年代的美国——迷惘的一代[M]. 夏平,嘉彤,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14]Irigaray, Luce.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15]Mary P. Ryan. Womanhood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M]. New York: Franklin Watts,1983.
[16]黄开红. 社会转型期的“美国梦”——试论嘉莉妹妹的道德倾向[J]. 外国文学研究,2006(3): 143-148.
[17]霍夫曼,芭芭拉. 一个青年女演员的画像: 《嘉莉妹妹》中展现的回报[G]∥皮泽尔,剑桥美国小说新论·《嘉丽妹妹》新论. 英文影印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The Quest of Happiness by a City Immigrant in the Metropolis——Dreiser’s Writing of Immigrant’s Value Orientation inSisterCarrie
QIN Dandan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 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0016, China)
Starting from an analysis of sister Carrie’s three distinctive immigrant traits which prove to be decisive in her subsequent value choice, the paper traces her pursuit of happiness and the prices she paid for them. At every critical turning point of Carrie’s adventure, it is the traumatic memory of the poor immigrant life, combined with the absence of a traditional sense of family as well as moral supervision that has pushed her resolutely to an“end for end’s sake”value orientation and she continued on her road from a city outsider to an urban celebrity. Carrie paid dearly for material acquisition, spiritual fulfillment and self-actualization, she went beyond the border of conventional moralities, lost her true self and only got a sense of nihility in return. The exploration of immigrants’ value orientation demonstrates Dreiser’s humanistic concern for American society at the turn of 20thcentury.
SisterCarrie; city immigrants; the turn of 20thcentury; value orientation
1673-1646(2016)05-0086-06
2016-05-12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美国社会转型期小说人物价值取向研究(15YJC752026)
秦丹丹(1983-),女,讲师,硕士,从事专业: 美国文学。
I712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6.05.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