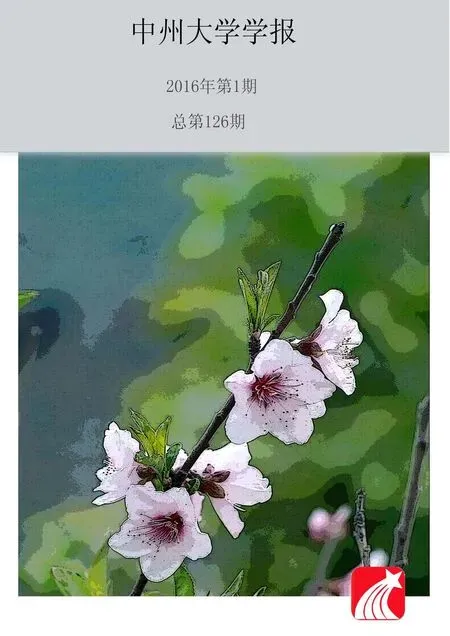社会学理论叙事的基础
2016-01-23张月
张 月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社会学理论叙事的基础
张月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摘要:社会学理论的目标在于客观地展现社会事实,揭示社会复杂结构与演进规律。可从事实上看,任何社会学理论皆为理论家根据自己的认知对社会所做的叙事,是围绕其观点所进行的系统符号建构。由于理论家的观点、立场、视域、观看方式、观察视角不同,自在世界在其眼中呈现的形态各具特征,而其观看世界的方式、认知能力、精神活动机制、衡量存在的尺度以及判断事实的标准,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终造就了理论的千差万别。本文从观看与想象、对象世界与选择、事实与叙事、同质性与异质性、观念与形态、地图与疆域等方面,对社会学理论叙事的基础加以分析,为理解传统社会学、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学理论提供一种新的维度。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传统社会学;现代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叙事基础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社会学理论呈现出越来越错综复杂的趋势,学派林立,理论形态千变万化,传统理论、现代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相互盘绕交织在一起,要想精确地区划彼此的疆域、明晰标示出它们的边界已相当困难。传统的理论看似昨日黄花,但其基本假设与基本原理仍是现代理论大厦的奠基石,一些重要概念和思路依然现身于现代理论体系之中。现代社会学理论常以与传统理论迥然相异的面相示人,可其内里与传统理论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理论的参天大树依然深深地扎根于传统理论丰沃的土壤之中。后现代理论以现代理论为靶子,激烈地反对现代社会学近乎偏执的本质主义主张和狂热的科学至上的原则,全面解构其宏大叙事,可其所涉及的论题始终未能脱离现代社会学理论的论域,只是变换了讨论和分析的视角;而且后现代理论无意之间以模仿对手的方式,在解构现代社会学理论宏大叙事的同时,不由自主地进行另一种叙事的建构,而这另一种叙事仿佛距宏大叙事的路途并不遥远——在人们看来,其绝对的相对主义、绝对的异质论、多元主义与折中主义,仿佛是另一种类型的宏大叙事。
几乎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立意都在于,展示世界的真相,再现存在的事实与真理。然而,任何一种理论事实上都只是理论家关于世界的认识的一种描述和呈现,是有关世界、存在、事实与真理的叙说。由于理论家的观点、立场、视域、观看方式、观察视角不同,自在世界在他们眼中呈现为异样的形态,他们根据自己看到的世界来认识世界,并根据自己的认识来建构有关世界的理论;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理论家本人观看世界的方式、认知能力、精神活动机制、衡量存在的尺度以及判断事实的标准,都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所有这一切最终造就了理论的千差万别。本文拟从观看与想象、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同质性与异质性、观念与形态、地图与疆域等方面,对社会学理论叙事的基础加以分析,为理解传统社会学、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学理论提供一种新的维度。
一、观看与想象
在有关社会的理论中,理论家的观点居中心地位,观点体现着理论家观察世界与社会时所处的位置抑或采取的态度,其重要性不言自明。理论家通过观念实践所希望展示的,就是其观点本身,而理论是理论家围绕其观点所进行的符号系统建构。就理论观点的界定而言,法兰西杰出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给出过相当简明的界说,国内学者引用了这一简明定义:“观点即立足点之观”(point of view as a view taken from a point)[1]16。若对观点一词加以分析,即可看出造就观点的诸种要素分别是:观看者、观看对象、观看方位、观看时间、观看行动、观看过程与观看结果等。而在这些要素之中,人们最应该给予关注的,是观看者与观看方位,“立足者之观”是观看者在一定的观看方位上,通过观看行动而获取的观看结果。假定观看对象同一,观看方位相同,观者不同,观看结果就会呈现差异。若观者同一,观看方位不同,观看者看到的景观也会不一样。事实上,即使是同一个观者,若在不同时刻观看,观看结果亦不相同。人们的日常经验足以证明这种假设的合理性,大量的社会学例证同样也能证明其正确性。
人们通常相信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忽略研究者的主体性及主体之间的差异,认定社会学理论是对于社会事实系统的客观表述与释义,社会学观点是对社会真理的客观展现。然而,这种所谓的客观性相当可疑。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头脑中,存在着两种有关社会事实的客观性的幻觉:第一个幻觉是,社会学的理论表现社会的客观事实;第二个幻觉是,社会学理论表现的世界即客观世界本身。事实上,理论表达的社会事实只是意向性事实,而非所谓的客观事实。任何研究都是人做出的,人之间的差异必然体现在其观点与理论的建构上,而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其观看上。同为社会研究者,因观者不一,同一被观看对象呈现为不同的形态。在埃米尔·迪尔凯姆看来,社会存在先于个体,由先在的社会事实构成,社会事实的存在并不取决于个人,且比个体生命存在更持久;而在马克斯·韦伯眼中,社会却是另一种景观——社会只是用来指称一群人的名称,离开构成群体的个人及其行动,社会根本就不存在。两种不同的社会观带来了两种对社会的理解与阐释,两者根据自己的主张,分别建立了唯实论的社会学理论与唯名论的社会学理论,并随后演化成为两种迥异的社会学流派。然而,即使是同一宗属的社会学家面对同一对象,因观看视角不同,也会持有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赖特·米尔斯与路易斯·科塞同为冲突学派的社会学家,但由于他们看待冲突的方式不一,对于冲突的认识也不一样。米尔斯看到的是绝对的冲突与利益的对立,科塞则看到了冲突与合作的并存,基于不同的观点,两者分别创立了各自独具个性的冲突学说。
显然,在社会研究与探索过程之中,社会学家的主体性始终存在,并始终在发挥着意向性但并非任意性的作用。无论人们怎样否认,主体性都会顽强地显现自身,并渗透进研究者的研究过程与研究成果之中。假如用心去看,我们即会发现,每一位社会学家的理论,皆为带有其个性特征的社会学理论;即使是同一学派的理论家,其理论同样也会显示出各自的差异,而理论上的这种差异,恰恰就是理论家主体性存在的证据。因此,将社会学理论看作是社会事实的客观表述,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认定,是一种想象出来的抑或认定的客观性。这种想象凭借的是建立在简单的、机械论基础上的主客两分法判断标准,把认识主体视之为客观反映者,根据刺激—反应模式,反映者一丝不差地再现对象本身。事实上,研究者永远不可能成为映现客观世界的完美机器。主体永远不可能从人的活动之中抽身而去,米歇尔·福柯宣告的“人之死”(主体之亡),不过是一种夸大其辞。福柯创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其理论既是主体活动的产物,也是主体存身于世的明证。福柯的理论不可能是拉康、德里达、列奥塔、鲍德里亚、德鲁兹等人的理论,而只能是他本人的理论。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都试图抹煞主体的存在,但二者抹煞主体性的过程,其实就是其主体进行活动的过程。让-保罗·萨特有关选择的绝对自由的主体论、浪漫主义者的任意专断、唯意志主义者夸大主体作用的主张本身是有问题的,它们造就了一种主体无所不能的虚妄,但人们不应在反对此类有问题的主张的同时,造就主体已死的另外一种幻觉。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即可发现结构对主体虽具有强烈的制约、限定作用,但结构永远不可能扼杀其存在。
当我们发现,将研究主体看作映现客观世界的完美机器是一种幻觉时,我们还有必要审视第二种所谓的客观性。通常人们认为,社会学理论表现社会的客观事实,社会学理论表现的社会事实,即社会事实本身。其实这只是另外一种有关客观性的幻觉。任何理论表现的世界只是观者眼中的世界,是世界的一种映象。而这一映象,依据黑格尔的理解,绝非客观世界之本体,而是一个他物,“映象是从有之范围里还剩下来的全部余留。……是本质的一个他物”[2]10。理论展现的世界,在观看的意义上对应于外在世界,这一外在世界是大卫·休谟那种通过经验与感官所触知的世界,也是伊曼努尔·康德所言的人们感知的现象世界,而非世界本体(物自体)。人认识到的世界,始终都只是也只能是被人感知到的世界,是人在认识世界过程之中的一个新的生成物,它介于人与本体世界之间,既非纯粹的主观构造,亦非纯粹的客观对象。实际上,依据人的认识建构的理论所表现的世界,并非是人们认定的客观世界,而只是人与世界的一种关系体现。
人们把理论表现的世界当成世界本身,是双重置换造成的结果。人们最初将观看世界获得的映象,看作是(take it as)世界本身,然后又把依据世界映象建构的理论呈现的世界视同为(identify it with)世界本身。其过程如同假设A=B,B=C,所以A=C。事实上,假设就是假设,而非真实本身。从真实性上考量,A就是A,A不是B,B也不是C,所以A根本就不可能等于C。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曾言:“人是——人。”[3]189马丁·海德格尔也曾经写道:“语言是语言。”[3]190洪堡和海德格尔的表述看上去像是赘述(tautology),抑或是逻辑学上的同义反复,但实际上它恰恰是在强调本位回归,反对替代,反对用其他的语义来取代或置换原有的语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防止看似真实的虚假置换。世界本体与人对于世界的呈现,原本是两种类型的存在,一种是实在域的存在,一种是符号域的存在。人们所以将其混同,乃是误认和误识,这非常类似雅克·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展示的那种状况:将镜中自我看作是实存自我本身。完成这一过程的,是人们的一种精神机制,即想象性视同机制(mechanism of identification),这一机制让人将其看到的世界(世界在人视觉上的映象)看作是世界本体,随之又用言语将其看到的世界(世界的映象)呈现出来,并最终将言语呈现的世界视同为世界本体。其实,世界本体、世界的映象、映象的呈现,原本是三种不同的存在,分别隶属于实在域、知觉域与符号域。
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想象性视同这一精神机制会无意识地发挥作用,人们对此习以为常,错把看到的世界当作世界本身而不自知,进而相信自己眼中的世界就是世界本体。实际上,人对世界的认识,不过是对世界的经验与感知,与世界本体在经验及感官的层面上仅存在一种对应关系,但绝非客观世界本身。而人根据对世界的认识创立的理论,从根本上说,原本就是人无法从其中抽身的符号性系统建构。强调客观中立、价值无涉的人,可能会竭尽全力想要从其理论建构之中抽身而去,但是实际上他们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H.詹姆斯曾明白无疑地告诉世人说:“作者试图从其书写的著述之中隐遁,可他却现身于其所书写的每一页之中。”[4]37在人类的活动中,主体始终在场。
二、对象世界与选择
理论建构的依据,是人对世界与社会的感知和认识,而感知和认识始于人对世界和社会的观看。观看影响着人对世界与社会的感知与理解,进而影响理论的系统建构。柏拉图很早就已认识到观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博学的沃尔弗干格·冯·歌德也发现,眼睛有着自己的生活。人的观看并非单纯机械的目视活动,而是观者将目光投诸于对象世界的视觉选择活动,观看意味着选择,意味着对世界的整理。巴尔曾在《看》一文中引述了歌德表述其主张的原话:“我们在投向世界的每一瞥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在整理着世界。”[5]282观看是意蕴丰富的精神—视觉活动,其中涉及与观看主体相关的观看视角、观看方式、观看意图与态度等。观看视角、方式、意图与态度不一,人们所看到的世界与社会也各不相同,它们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于对象世界的感知、认识、把握与判断,影响着人们对世界与社会形成的看法与主张。
众所周知,在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有着多种多样的观点与主张,进而形成了多种不同理论流派。实证主义社会学、社会进化论、知识社会学、形式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理解社会学、功能主义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本土方法论、批判社会学、新功能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互动仪式链理论、结构化理论、反思社会学等,所有这一切,只是诸多社会学理论中的主要理论和学说,不过仅就这些理论与学说显示出的彼此之间的差异与分歧,足已说明问题的关键所在。同样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但在对社会的认知、分析与解释上,研究者采取了彼此不同的路径,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选择不同的解释方式。这些理论与学说相互之间观点各异,甚至彼此之间互相冲突。对于这种状况,我们无法做出那种所谓的对与错的判断,因为每一种理论与学说皆有其合理的解释逻辑与立论依据。然而,差异的确存在。要理解这些差异,我们只能运用回溯的方法,回到理论与学说的提出者那里,回到其初始的观点与观看活动上去。
理论与学说是研究者依据其观点所进行的符号建构,而观点的获得与研究者的观看活动、尤其与其观看视角及观看方式相关。观看视角由观看者选定的位置限定,在何处观看,意味着从那一位置给定的角度观看。这里所说的位置,并不只限于物质世界的空间限定的视角,还包括意向性的、学科性的视角,譬如本体的、认知的、价值的、审美的视角,政治的、伦理的、科学的、法律的视角等。从不同视角观看,被看对象会呈现出殊异的形态,被看对象的属性也会因此在观者眼中发生变化。同一个被看对象,从政治的视角观看可以接纳的,而从伦理的视角上观看则可能必须拒纳。甚至即使是运用同一学科的观看视角来观看同一对象,因角度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观看结果。如在马克斯·韦伯眼中,科层制基本上是一种具有正面功能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在米歇尔·克罗齐耶看来,却是极具负面价值的恶性循环现象。
观看视角框定了观看的视域与观看对象,观看方式决定观看活动的属性与观看结果的性质。
三、事实与叙事
在社会学研究之中,人最重视的是社会事实,它是研究者从事研究的基础。社会学所要做的事,用埃米尔·杜尔凯姆的话说,就是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在他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集体性、外在性与强制性特征。然而,社会事实并不是纯客观的,并不等于外在于人的存在,抑或发生在人之外的事件。纯粹客观的存在抑或本体世界是否存在,人无法确定,用康德和休谟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是不得而知。可一旦人要认识这种存在,判断它存在,就必须使用其感官,而此时人业已与被认识的对象建立起联系,他本人已成为其认识活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所认识的世界是将其自身包含在其中的世界。也就是说,他所认识的并不是纯粹客观的存在,而只是他所认识的存在,他无法将其自身从中剥离出来。
关于这一点,发生认识论的代表人物J.皮亚杰、R.加西亚在其《心理发生与科学史》中做出了明确说明,他们认为,研究者所指的社会事实,归根到底“也始终是由客体提供的一个部分和由主体构成的另一个部分之间组合的产物”[6]11。与之相似,量子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卡尔·海森堡也做出过同类的说明,他指出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意外地与自我邂逅,人作为观测者始终是观测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观测者总是作为被观测过程中的一部分,那么人们长久以来所领会的客观性就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概念”[7]196。也正因为如此,他提出了测不准原理。涉及同类现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提出了著名的论断:“理论决定观测结果。”[7]196换一种方式来表述,我们亦可用此来对这类现象进行诠释。理论原本是观点的系统表述,因此我们可以将爱因斯坦的论断改写为“观点决定观测结果”。而观点是观者在其立足之位上所看到的景观。
若将这一主张运用于社会学,即可发现,社会事实是社会学家根据其观察所做的一种建构,其中在这一围绕着外部世界的建构过程里,社会学家自身的主体起着重要作用,他始终在场,始终在其建构的社会事实之中。仍以埃米尔·迪尔凯姆与马克斯·韦伯为例,即可说明问题所在。他们同为现代社会学的创立者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代宗师,但在二人眼中社会却呈现为不同的形态。
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由先在的社会事实造就而成。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并作用于人,对人的意识进行塑造。埃米尔·迪尔凯姆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社会现象——具有客观性、集体性及强制性的社会事实,并提出一整套的研究方法,建立起了自己的唯实论学说。他写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并以此为基础,从事社会现象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代表作《自杀论》《社会分工论》,无疑是体现他的观察视角与研究方法的经典之作。
然而,在韦伯看来,唯有个人以及其行动才是真切的实在。离开了构成群体的个人及其行动,社会根本就不存在。真正重要的,不是那种超越于人之上的社会结构,而是包含着人的主观意义的人的社会行动。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得以构成的人本身有意义的行动,而要研究人的行动,就必须使用他所倡导的“投入理解”的方法,这样才能发现主导行动者行动的内在逻辑,并对其做出合理解释。他以此为本确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他所撰写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即是其方法论的系统表述。他按照自己限定的方式从事研究,提出了大量具有原创性的几乎涉及到社会学每一个领域的系统学说,创立了具有社会唯名论特征的理解社会学。其学说成为现代与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另一源头。
由此可见,所谓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只是人们的一种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的认定。因此在讨论社会事实时,必须要将人的在场性考虑在内。
社会事实并非客观性存在,而是人对外部世界与自身关系的一种判断与认定。理论是对这并非是客观性的存在的表述,因此也就更不能称之为客观性的存在。事实上,人的理论表述只是一种言说,一种叙事,亦即对自己所感知、判断和认识的存在的一种系统表述。
假如纯粹的客观世界存在,我们在此所面对的就是三重存在:纯客观世界、社会事实与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的社会学理论。我们无法确保理论的言说能够与客观世界完全重合。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尽可能让社会学理论与其要解释的社会事实相契合。
即使要让社会学理论与所言说的社会事实完全契合,也只是一种理想,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事。首先,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对等性。社会事实是一种存在,语言是另外一种存在。社会事实是主体融入其中的高度复杂的存在,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两者之间所能够达到的最多是一种对应性。语言作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形式,自身本非是一种完美的结合体,能指与所指之间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而且一个能指可以有多个所指,同样一个所指也会有多个能指,甚至从最为极端的意义上讲,能指会不断地滑动,因而语言的歧义性、含混性是显在的;而且语言的意义本非只是其词典意义,其真义在使用中被使用方式所决定。因此,要使其自身结合并不完美的符号与社会事实相对应极为困难。
所以,人们在看待理论的过程中,应注意到这种复杂关系,要注意到其间存在着的诸多缝隙,注意到它们隶属不同性质的存在,一方并不代表另一方,甚至一方与另一方并不完全对应。人不能完全通过理论来认识社会事实。
然而,理论作为一种叙事,必须以社会事实为基础,没有这一基础,理论就无法言说,尽管其言说通常不够充分。即使其言说充分,人们也应该注意到其言说与社会事实相对应的程度,要知道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性存在,本身也具有建构功能,它能够建构另外一种存在,代替社会事实出场,抑或先于社会事实到场。假如人们过份相信理论,就会因理论与社会事实具有良好的对应性而接近社会事实,因理论与社会事实错位而远离社会事实。
即使理论的叙事与社会事实之间具有良好的对应性,理论对社会事实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人们也应注意到,由于社会事实并不完全是客观性的存在,而是主体参与其间的存在,理论如何叙事与对社会事实如何认定的人的主体活动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人们不仅应注意理论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更应关注确认社会事实的主体与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的关系,而如何认定社会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从何处观看,以何种方式观看。
四、同质与异质
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学之争表现在很多方面,然而,这些表现从某种意义上可归结为观看方式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他们对社会事实做出不同的认定,并造成了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方面的殊异。在现代社会学家看来,社会事实是具有同质性的存在,因此可对其进行化约,可使用还原、高度简化、高度演绎的方式,进行量化分析,进行规范性的研究;而后现代社会学家则认为,社会事实是具有高度异质性的存在,具有不可通约性,因此不能进行简化,不能使用还原论的、高度简化、高度演绎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反对将定量分析作为主要的分析方法,而主张重视复杂性、多元性、相对性,采用描述的逐一对待的定性分析的方法,尊重社会事实的本原状态。
事实上,社会事实的同质性与异质性之争,归根结底是观看之争。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社会中并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更不会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发生一模一样的事。强调异质性即强调差异性。因此从绝对意义上说,这种强调能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事实本身的真实性。当谈论社会中的人时,应具体化。如乞丐绝不可能与总统一样享有同等权利和权力;当谈论居住条件时,应将富人的居住面积、穷人的居住面积及大量中间群体的住房面积分别进行具体描述,而不应将所有被研究的人群的居住面积加以平均,用平均值来说事儿,不然就会掩盖具体的真实性;在讨论女权时,应厘清是什么人的女权,是白种女人的女权?黄种女人的女权?黑种女人的女权?是哪个地区哪个阶层的女人的女权?在后现代社会学家看来,根本就不存在那种同一的标准的权利,也不存在普适性的原理与准则,对一个人适用的对另一个人可能完全不适用。如同意大利谚语所言,“一个人的面包对另一个人是毒药”。
然而,假如从宏观层面上看,社会事实仿佛又具有同质性。悬置了个体差异后,以其他物种作为对象进行比较,即可发现,人作为一个类属,具有大量的同质性。社会学家也发现,人类有着共同的目标。至少一些总体目标为人们普遍所接受,譬如解放、自由、民主、平等、和平、发展等。这些目标虽并未实现,但其作为社会前进的目标,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世界上的人们,起码是大多数人仿佛一直在朝着这些观念指向的目标做着不懈的努力。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是一种未竟的事业。人类共同的目标之所以未能实现,在于人们没有采取正当的方式,假如人们之间的交往不是采用权力的媒介、金钱的媒介,而是运用本真的话语作为媒介,那么走向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目标的道路就会变得通畅。因此,继续从事现代性的建设,完成未竟的事业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显而易见,现代性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双向性的交替性的涌现,有着合理性与必然性。现代社会学家与后现代社会学家看到了社会事实存在的两极性,看到了人们矛盾而又真切的双重需要,而正是他们的发现造就了他们各自的理论。只是他们各执一端。他们注意到,人希望保全自己的个性、自由和个性化的需要,但同时也希望整个社会朝着平等、自由、民主、和平、富强的方向发展。将两种需要推至极端,就会造成两种需要的对立。无疑,现代性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对立也正是对人的矛盾性需要的一端的执守造成的,而无论执着于哪一方,都有可能使真正存在的需要得不到合理的满足,问题得不到充分的解决。若注重同质性而排斥异质性,就有可能忽视人们的差异性需要,忽视人的个性,用形式上的真实掩盖实际上的虚假,用抽象的公正来抹煞实际存在的不公正,用一元化的标准来压制人的多元化的需求,将富有活力的有着创造力的人变成机器化的数字化的便于操控的异化对象;相反,假如固守异质性而否定同质性,一味地强调对现代性理论的解构,向一切同一性、统一性开战,一味地否定一切现代性的规范,而自身毫无建树,那么最终就会造成研究范式的完全失效。这样,理论不复为理论,缺乏概括性,不具有任何规模性的解释效力,人们之间因强调异质性,排除一切同质性,最终将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沟通,最低限度的组织难于形成,最为基本的合作也无法进行。毋庸讳言,这将把社会与人置于一种艰难的境地。
现代性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论争,源于对不同的社会事实的把握,源于对社会存在的不同形式的观看。假如执守于现代性理论的理论家与热衷于后现代理论的理论家都能够换一种视角来重新看待社会与社会中的人,他们就有可能看到以往自己看不到的存在,两种之间的对立就有望变成对话,就有可能进行沟通与交流,形成对社会事实的新的认定,对社会事实做出不同以往的解释,建构有关社会的新型的理论。
关键在于要从多元的丰富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固守于一点的观看视域那里形成对社会事实的认定。社会性的存在是错综复杂的,人的需要是多样的和矛盾的,研究者与理论家应该让人的多元性的需要以其原有的方式存在,不对其进行人为的干预,其中包括认知上理论上的和观念性的干预。以复杂的方式来看待复杂的社会,以矛盾的眼光来看待矛盾的需要,让矛盾以矛盾的方式存在着。据此,从多维的视角来进行观看,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社会事实,并运用理论的方式对其进行叙说,而那时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理论的叙事将会是多元化形态的叙事。
五、观念与形态
事实上,无论是否强调多元,社会学理论始终都是以多元的形式存在着。尽管从孔德和斯宾塞开始,就有着建构一元化的将所有的内容皆囊括其中的宏大社会学理论的构想与努力,但这种理论始终也无法取代其他的理论。翻看社会学理论的历史,我们发现,即使是同属一派的理论家,也同样显示出其理论的个性差异,这种个性差异正是其在观察时所具有的观看视域、观察视角、观看方式的不同造成的。影响人观看事物的方式既受知识与信仰的影响,也受传统、地缘文化、教育模式、习俗时尚、性格、偏好、社会地位、出身、性别等的影响。
理论的叙事始于观看,而观看是一种意识活动。意识犹如烛光,它只能照亮意识领域之内的世界,而烛光之外,是黑暗的领域,其间的存在人们不得而知。那种试图建立包罗万象的理论的努力不言而喻是徒劳的。一个人的意识只能是他自身的意识,不可能是别人的意识。而人与人的意识之间皆存在差异,这就注定了人的观看活动的多样性,注定了对社会事实的认识的多样性,从而形成理论叙事的多元化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的多元是一种必然,而多元理论的共生也就不可避免。在每一个时代,总会有某种理论占据优势地位,但它并不能扼杀其他理论的存在,并发挥其影响力。
应该说,理论的多元与共生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我们应该关注构成理论多元的要素。除了以上所言的那些元素之外,我们尤其应该注意观念的作用,观念在观看与理论叙事方面具有很强的塑造功能。当相信自己能够找到存在的深度模式的时候,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去寻找这种结构,在所有的被研究的对象之中,研究者仿佛都能够看到这种模式的结构,并且运用最为简洁的概念工具来进行分析与描述。结构主义理论家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他们运用两分法与二元对立的概念工具,在所有研究对象内部都观测到了隐含着的深层结构,通过数比关系的分析与符号矩阵的建立,他们将隐含在其中的深层结构复制出来,并运用最为简约的语言对其进行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主义理论家是最强调同质性的人,他们在所有的被研究对象之中,都发现了大致相同的结构。特里·伊格尔顿曾经以嘲讽的口吻谈论结构主义理论家,说他们凭借自身的方法一下子就到达了理论的制高点,可下一步该怎么办就不知道了。的确,他们确实有本领在几乎所有的对象中都能找到那类深层结构,他们能够说清楚对象本身的同质性与同类结构,但是他们无法说清这类对象之间存在的差别,使一个对象区别于另一个对象的差异性。结构主义看上去像是一种发掘与复制,实际上是一种拆解与重组,它将原本有机的整体拆散,根据自身理论观念的需要,重新组合,塑造成与其理论叙事要求相对应的那种模样。
结构主义理论家是这样,那些盲目地信奉数理工具的人同样也是这种观念的牺牲品。在当代,尤其是在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不少人对数字、图表、公式与模型极度迷恋,几乎达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似乎不使用这些工具就显示不出水平。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在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中,大量使用数字、图表、公式和模型,似乎只有这样才够科学、严谨,才有真正的份量。事实上,数字统计分析和概率分析只有在说明总体趋势时,才是真正有用的;其他时刻,尤其是在针对具体的对象时,他们几乎不具备任何真正有效的有针对性的解释力。统计与概率分析的真正价值在于寻求一种总体上的趋近值,确定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进而做出预测。作为工具,使用起来相当便利与经济,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因而,使用统计与概率分析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但统计分析中所谓的平均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对这些工具的使用极为在行,然而他却声称,在文字能够说清楚时,尽量不用数字,在数字能够说明问题时,尽量不用公式、图表与模型。他认为,在数字、图表、公式与模型之中隐藏着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这更多像是在玩游戏。其实,数字、图表、公式与模型的虚假一点也不亚于文字,甚至比文字有过之而无不及。使用者特别容易用这些工具蒙骗那些不会使用这些工具的人。就有关社会事实的叙说方面而言,这种方式不仅缺乏直接的对应性,而且很有可能错位,将社会事实扭曲成为另外一种模样,并依照数字、图表、公式与模型将社会事实按自己的需要进行重新塑造。
因此,如若缺少必要的反省,人很容易成为其观念的囚徒,为自己所建造的观念世界所囚禁,这不仅会毁掉他自己所经验的世界,而且也会最终毁掉自己真实的存在本身。
六、地图与疆域
即使我们能够摆脱观念的束缚与限制,从观念的囚禁中解放出来,尽可能地按照实际经验来进行判断和认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存在本身具有多域性、多态性,其间有着多重复杂的关系。我们置身其间的物性世界存在于实在域,我们对物性世界的感知空间属于心理域,而我们用于表现我们对实在域认知的文字、图像属于符号域。
实在域的世界,从其物性来看,不因人的意志与愿望而改变属性,但在不同条件下会呈现为多样态。不仅如此,当人与这一世界相遇时,在作为主体的人的眼中和心中,它亦会呈现为多样化形态。而有关这一世界的认知也样态各异。关于世界本源,仅西方哲人就说法各异,远至古希腊的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普罗泰戈拉、柏拉图,近至康德、黑格尔、叔本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皆有自己的学说,他们的主张彼此殊异,个性独具。每一学说所具特性,皆为其主体在场的标志。
人的主体,在具有自主性、能动性、选择性的同时,亦有个异性。这种个异性即“人差”,它与生俱来,根植于身体(生理构造、神经系统)基底,它决定着人只能是他自己,它是一人区别于他人的决定性要素。主体的这种个异性,注定了一个人在感知世界、接受外界刺激时异于他人,它影响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作用于人的知觉导向、意识选择、对文化的顺应或拒纳等。具体到社会学家,他们的学说之所以具有独到之处,在于其主体性的作用,这种主体性令其在感知社会时异于他人,社会在其观看中显出不同外观,而其用言语描述的社会亦呈现出与其观看对应的多态性的面相。
人虽因原生的个异性在主体活动中注定会显示出其区别于他人的的特质,但若搁置这种差异,从宏观层面上看,人作为同类,在身体的总体构造上和感知世界的总体方式上又存在着类的相同性。这种类同性是人们彼此认识、理解对方的基础,是相互间达成共识的根基;也是人可使用语言这一公共符号系统来表述彼此能理解的意义的前提。类同性使人的集体行动成为可能——人相互协作,朝向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共建理想社会。
共建理想社会,异议虽存,但总体目标一致,即和平与发展。在此进程中,社会学家肩负着重要使命,为让人认识社会,社会学家须完整再现出社会全貌。为此,他们需找到如实描述社会本相、社会运行与发展趋势的语言,进而描绘社会发展的未来蓝图,为创造理想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然而,社会学家必须时刻保持清醒意识,有关社会的未来设计或蓝图只是愿景规划,其功能最多能够媲美地图,令人通过符号性的存在与实存社会建立起联系。
地图不是疆域,它只是根据数学法则,使用点、线、色块、文字、数字等来表达疆域上各种事物的空间分布、联系及时间中的发展变化状态而绘制的图形。其首要功能是工具作用,能最为简明地让人认识实存的疆域。从其构成上看,地图最显著的特征是高度的缩与略,这意味着空间压缩与细节省略。疆域上的大量实体存在,到了地图上踪迹全无,成了空白,要想令其充实,惟有借助想象的力量。地图对应但不对等于疆域,且这种对应只是部分的对应,简略对应,有时对应的二者间会发生错位。
理论叙事与地图相似。理论再现的社会如地图标示的疆域,始终是概略的。构成理论的语言,无论其描述多么详尽,都终归是框架式的抽象性的描述,人们必须运用想象,才能将省略掉内容的空白填充起来,以便得到比较具体化的社会的图像。
毋庸讳言,找到一种完备的叙说社会事实的语言是困难的,即使能够找到一种理想的语言,也不应忘记叙说中的社会与现实的社会,仅为符号与现实的一种对应关系,而且在作为叙述者的主体在场的情况下,其间的关系极有可能发生偏移、甚至错位。
词语本非事物,宛若地图并非疆域,有关社会的理论远非社会本身。社会学理论是关于社会的叙事,现实社会是社会学理论叙事的基础,理想状态下的社会学理论叙事,能够带领人们认识社会真相;而社会蓝图则是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叙事,其功能犹如地图,将为人们建构未来社会指明方向,提供路径。
参考文献:
[1]朱国华.权力的文化逻辑[M].上海:三联书店,2004.
[2]〔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德〕马丁·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
[4]Leon Edel.Stuff of Sleep and Dreams[M].Avon Books,1983.
[5]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C].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6]〔瑞士〕J·皮亚杰,R·加西亚.心理发生与科学史[C].李其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美〕洛兰·格伦农,等编.20世纪人类全记录[C].余吉孝,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
(责任编辑刘海燕)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Narration in Sociology
ZHANG Yue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Sociological theories aim at displaying the social facts objectively, and revealing the complicated structures and the evolutionary laws of the society.However, every sociological theory is in fact a narrative about society by a sociologist based on his or her social cognition, and is no more than the systemic construction in symbol concerning his or her speculation.The world in itself manifests with different shapes in their eyes owing to their varied viewpoints, positions, horizons, ways of observation and perspectives.Their ways of looking at the world, their cognitive capabilities, their mental mechanisms, their measurements of the being and their criteria for judgment of facts, play an essential part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theories, and determine the differences from one to another in theory.The text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 in sociological theory from the aspects of observation and imagination, objective world and selection, fact and narrative, homogeneity and heterogeneity, concept and form, map and territory, and opens up a new dimens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aditional sociology, the modern sociology and the post-modern sociology.
Key words:sociological theory; traditional sociology; modern sociology; post-modern sociology; basis of narration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1-0090-08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1.019
作者简介:张月(1959—),男,河南开封人,社会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艺术学、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艺术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并从事西方经典作品和人文思想的翻译工作。
收稿日期:2015-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