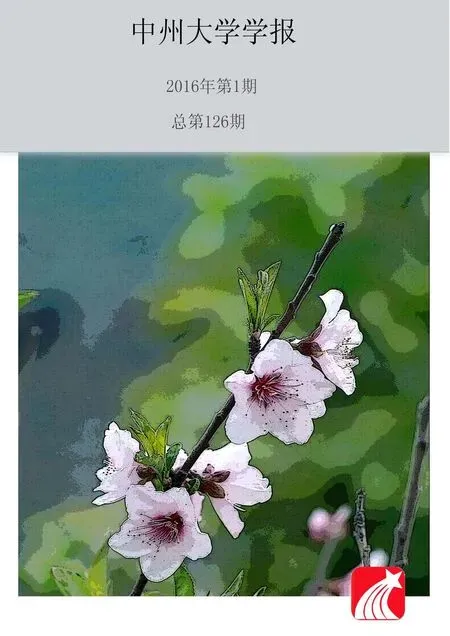韵外之致:一种汉语诗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轨迹
2016-01-23泓峻
泓 峻
(山东大学威海校区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韵外之致:一种汉语诗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轨迹
泓峻
(山东大学威海校区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易传》“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这一命题经过魏晋玄学家的发挥,在唐代文论家司空图那里进一步发酵,衍生出推崇文学作品的“韵外之致”这一审美理想。唐代关于诗歌境界的理论,则与这一思想形成呼应,它们都是儒家哲学、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佛教哲学杂揉整合之后的产物,经由有形的现象界而进入自由的审美世界,是其真谛所在。这是一条与《诗经》《离骚》开创的两大传统有很大区别的新的诗学传统。而且,作为重要的美学指标,它除了深刻影响到后世汉语诗歌的创作与评价之外,还延及词、曲、文乃至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成为汉语文学最具标志性的特征之一。
关键词:韵外之致;诗境理论;内涵;影响
一
在先秦时期,有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命题,对后世的汉语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两个命题,一个是出自《易传》的“言不尽意”,一个是出自《孟子》的“言近而旨远”。它们一个从悲观的角度,强调了面对无限的意义世界,语言的局限性;另一个则从乐观的角度,强调了语言可以越过自身有限的形式,指向无限的意义世界。
实际上,用有限的语言形式去表达无限的意义世界,既是语言表达行为面对的困境,也是语言表达行为的乐趣所在。人类绝对不会因为语言表达的艰难而放弃表达的努力,而总是要直面挑战,不断去寻找以有限切入无限的可能性。乐观如孟子,认为好的表达,可以做到“不下带而道存焉”[1],即让极为平常的事情,蕴含深刻的道理;悲观如孔子,也提出了“立象以尽意”的方式,认为可以通过“象”去象征性地呈现隐秘的“圣人之意”。
这两个命题以及与之有关的言说策略,在后世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与充分的发挥。唐代史学家刘知己正是借用了孟子的说法,对《左传》的叙事效果进行了总结,认为《左传》的许多文字达到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2]225的境界,并认为“春秋笔法”的运用,是形成这种叙事效果的重要原因。这种叙事学思想由史学进入文学,成为后世汉语文学叙事追求的最高境界。
而《易传》“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这一命题,则经过魏晋玄学家的发挥,首先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哲学命题,进而由哲学入文学,在唐代文论家那里不断发酵,不仅由此衍生出“言外之意”“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类似的说法,而且还直接启发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意象”“意境”“境象”“境界”等诗学概念的产生。这些新的诗学概念,经由唐人的提倡,逐渐成为后世中国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文学追求的至高境界,对文学家审美体验的表达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整体上讲,汉代是正统的儒家文学观念得以正式确立并大发扬的时代。东汉以后,随着名教式微,“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的发生,文学表达也开始试图淡化教化功能,去言说主体个性化、深层次的生命体验。对于当时的文学家而言,这种生命体验是新鲜而动人的,但也往往是稍纵即逝,难以把捉的。在这种新的体验面前,许多文学家开始感受到了言说的困难。陆机在《文赋》中就曾感叹写作中“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也讲,创作时常常会出现“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的情况。
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经历的新的语言烦恼。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说‘言不尽意’,在庄子那里,其困难是一般性的语言无法接近他所追寻的神秘的、飘渺的、‘莫见其性’‘莫见其功’的‘道’的话,那么,在诗人作家这里,‘言不尽意’的尴尬困境,是关联到如何用一般性的语言,来表现诗人作家的审美体验问题。”[3]正是基于这一语言表达的焦虑,从魏晋开始,一些文学家就一方面试图对那稍纵即逝的个性化生命体验进行命名,另一方面又在执着地寻找着将这种体验表达出来的途径。
在为新的审美体验进行命名时,在刘勰的时代,比较典型的做法是用通感的方式,把通过文学作品体会到的颇为神秘的个性化审美体验称作“味”“滋味”。陆机《文赋》中有“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的说法。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也有“张衡《怨篇》,诗典可味”的说法。最著名的是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的“滋味”说。他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并认为诗作将赋、比、兴三者“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便可“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4]2。
把在优秀文学作品面前获得的精神体验与不可言说的味觉体验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直接启发了唐代著名的文论家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这篇文章中,司空图正是从“滋味”说入手,去阐发自己的诗学主张的。他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又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然后,他又将这个比喻进一步延伸,说那种“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5]97的调味品,真正懂得辨味的中原人是不用的,因为它们除酸、咸之外,缺乏醇美之味。而食物的醇美之味,是超越于咸酸之外的。同样道理,真正的文学体验,其动人之处,也不在有形的语言之内,而在于其“韵外之致”[5]97。
司空图“韵外之致”之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在解释诗歌的审美意蕴时,既立足于文学语言,又试图超越文学语言的辨证态度。他说,诗的“韵外之致”是“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因为“远而不尽”,所以是开放的,虚化的。在这一点上,它与老子、庄子等人所讲的“惟恍惟惚”“不可言传”的道十分近似。然而,像道一样虚无飘渺的审美体验,又是通过“近而不浮”的文学语言传达出来的,因为“近而不浮”,所以它是有形的,可以把捉的。在这里,“‘韵内’与‘韵外’是有密切联系的,只有‘韵内’有真美,‘韵外’才可能有意味”[3]。
司空图在另外一些地方讲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等等,作为一种审美效果,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司空图的“韵外之致”这一总结,其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将《易传》提出的“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这一哲学命题,转换成了一个诗学命题,既突出强调了文学体验超越语言的一面,又强调了这种超越语言的审美体验,就蕴含在有形的文学语言所创造出来的具体可感的物象与情境之中。
三
在唐代,与司空图的这一诗学思想相呼应的,还有关于诗歌境界的理论。
在汉语文学史上,以“境”论诗,衍生出境界、境象、意境、情境、妙境、绝境、甘境、能境、取境等等一系列概念。诗境理论,也有一个从古代到近代直至当代的复杂的演变过程,形成了一条极具民族特色的诗学传统与美学传统,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艺术史与审美心理史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比较早地明确提出相关概念并加以分析的文献,当属成书于唐代、署名王昌龄的《诗格》,其中写道: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6]39
中国文论十分重要的“意境”这一概念,就首见于这段文字,尽管这里所说的“意境”与后来许多人讲的“意境”在涵义上有明显区别。
唐代另一个论及“诗境”话题的是皎然。在《诗议》中,皎然讲:
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定质,色也。凡此等可以偶虚,亦可以偶实。[6]51
《诗格》中虽也有“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一说,但对“境象”的具体状态没有说明。在《诗议》的这段话里,皎然把论述的重点放在了对“境象”的分析之上,指出了其亦虚亦实,“可睹而不可取”“可闻而不可见”“义贯众象,而无定质”的特点。
到后来,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中,又进一步对“境”与“象”的关系进行了发挥,“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7]172。
在“境象”这一概念下,“诗境理论”与此前的“意象理论”融而为一。刘禹锡的“境生于象外”之说,实际上是在之前司空图、皎然等人“言外之意”“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之后,又增加了一种类似的说法。
四
关于“境”和“象”、“意境”与“意象”这些概念应该怎样区分开来,是近代以来学者才开始认真追问的问题。在试图对它们进行明确区分的时候,学者们多从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一角度切入,如认为:“境比象一般来说要广阔得多,丰富得多,生动得多。然而境又是离不开象的,没有象就不能生成境。”[8]
在这种流行的看法之外,有学者还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作为一个艺术理论概念,“象”与“境”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与绘画联在一起的,而后者的原始意义则出自音乐。正因为如此,“境”是一个比“象”更能体现抒情文学“韵外之致”的概念,因为“音乐的特征,可意味而不可言传,可感可爱而不可度量。它的界域不是具体的,而是从演奏、歌唱至停止时所表现的一切”,因此,“以情境来标示抒情文学的构造,它恰好反映了抒情文学和音乐一样,具有模糊、激荡、婉转而无具形的特征”[9]95-96。
这种看法很有启发性,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把握唐代诗境理论最为核心的内核,那就是强调诗歌的“韵外之致”。但因此认为在谈论抒情文学时“象不如境”,则未必妥当。因为在唐代及以后的诗论家那里,这两个概念既不用来标示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的不同特征,也并非用来标示两种不同文学的历史渊源。一方面,它们都在论诗的过程中使用,另一方面,在美学指向上,它们也是高度统一的。它们强调的都是诗歌的实与虚的结合,既包含感性的言、象、境、韵、味,同时又指向无形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美学特征。
两个概念在美学指向上的这种统一,大概跟佛教理论对这两个汉语中原有的概念的借用与改造有关。在佛学的概念里,这两个概念都有虚实结合,由实入虚的涵义。
“境”“境界”是佛学中极其常用的概念。有学者分析指出,佛学的“境界”有三重意指,一方面“它接近于外物,可称为‘外境’”,另一方面指“根——识——境三缘和合之‘幻相’境界,以区别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外境’”;同时,“佛学对心识极度推崇,而心识在禅定修持时又有一个不断提升层次的过程。因此,境界在佛典中又自然地引申出第三种涵义,用于指称心识修养的层次,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精神境界、心灵境界”[10]。佛家所讲的这种境界,显然与唐代诗论家所讲的境界在内涵上有更多的相通之处。《诗格》将诗的境界分为物境、情境、意境,很可能是受到佛家“三界”“六境”等说法的影响。
“象”这一中国哲学与文论中固有的概念,也很早就被佛教所借用。晋代僧人僧肇在他所著的《不真空论》中就说:
是以圣人乘真心而理顺,则无滞而不通;审一气以观化,故所遇而顺适。无滞而不通,故能混杂致淳;所遇而顺适,故则触物而一。如此,则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不能自异,故知象非真象;象非真象,故则虽象而非象。[11]36
这种似真非真,“象而非象”的“象”,与司空图“象外之象”,以及宋代严羽论诗时所讲的“空中音,相中色,水中月,镜中象”在理路上是十分近似的。诗学中的“境界学”“意象说”,实际上都是儒家哲学、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佛教哲学杂揉整合之后的产物,经由有形的现象世界而进入自由的审美世界,追求空灵、玄远的“韵外之致”,是其美学理想的真谛所在。
五
在唐代开始形成的追求空灵、玄远的“韵外之致”的诗学理想,对后世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一方面,由它生发开来,形成了一条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及由屈原开创的那种慷慨悲歌的诗学传统有很大区别的新的诗学传统。另一方面,这种审美理想又具有普遍的意义,它不仅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标准影响到所有的诗歌创作,并延及词、曲、文乃至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
现代作家周作人在文章中多次引用日本诗人大沼枕山的一句诗,“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与初唐和盛唐相比,中晚唐的文人生活受到佛教思想影响,情趣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人希望过一种“仕隐兼顾”的“中隐”生活,“以隐为高,脱离尘世的超越性和心灵上的自适无碍”[12]。与此同时,诗风也发生了明显的转移,这种转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量“诗僧”在诗坛涌现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应该讲,随着佛教尤其是本土化佛教“禅宗”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其影响所及开始深入到中国文化最为核心的领地——诗歌。唐代的诗坛上,自始至终都有僧人的身影存在。中晚唐以后,诗僧更是大量出现并形成诗坛的一支重要力量。有学者根据周勋初主编的《唐诗大辞典》统计,本书所涉及的唐代诗僧有288人,其中初唐35人,盛唐19人,中唐70人,晚唐164人。[13]对于中晚唐诗僧大量出现这一现象及其对当时诗坛的影响,唐以后的历代研究者多有提及。如叶梦得的《石林诗话》讲:
唐诗僧,自中叶以后,其名字班班为当时所称者甚多,然诗皆不传,如“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数联,仅见文士所录而已。陵迟至贯休、齐己之徒,其诗虽存,然无足言矣。中间惟皎然最为杰出,故其诗十卷独全,亦无甚过人者。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气,往往反拾掇摹效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僧体,格律尤凡俗,世谓之酸馅气。[6]424
叶梦得是从否定的角度谈论僧人诗的,但从其话语中仍然流露出从晚唐到南宋僧人学诗的盛况。至于并非僧人身份,但却经常与僧人交游,受到佛教影响或具有隐逸思想的诗人,则为数更多,难以准确统计。其结果就是,中晚唐以后,在中国诗坛出现了大量反映僧人和文人修行悟道生活的山居诗、佛寺诗和游方诗。这些诗歌多以佛寺山居生活为依托,描写曲径通幽、空寂无人的山林风景,表现僧人或文人空诸所有、万虑全消、淡泊宁静的心境。这类诗人,唐代有王维、司空图、寒山、拾得、皎然、灵澈、贯休等人,宋代有苏东坡、严羽、道潜、释觉范、慧洪等人,逐渐形成中国诗歌史上前后相承、颇具声势、理论与创作相互支撑、大家辈出的一条脉络。追求空灵、玄远的“韵外之致”,是这一脉诗歌最为突出的美学特征。
然而,司空图当初提倡“言外之意”“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这种诗学理想时,却并非把它仅仅当成某一种诗歌风格或诗歌流派应具有的特征来提倡的。我们发现,在他的《二十四诗品》所列的二十四种风格中,“冲淡”“洗炼”“自然”“含蓄”等风格类型自然贯穿了这种诗学理想,即便是一些从名字上看应当与这种诗学理想没有太直接关系的风格类型,在司空图“以诗论诗”地对其风格加以描述时,也几乎都带上了这种诗学理想的痕迹。比如,关于“雄浑”,他这样叙述: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
关于“高古”,他这样叙述: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踪。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黄唐在独,落落玄宗。
关于“劲健”,他这样叙述:
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
就是“纤秾”“典雅”这种风格,也被他叙述为: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纤秾)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典雅)(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因此可以说,在司空图那里,“韵外之致”是对所有诗歌的要求,是优秀诗歌都应当具有的品质。司空图的这种诗学观念,被后世的许多诗人与诗论家所接受,成为诗人创作的一种自觉追求,也成为诗论家论诗的一条重要标准。
宋人在诗歌上主张学唐诗,推崇的主要是盛唐诗人,特别是杜甫。对于晚唐诗人及其诗作,则颇多微词。但他们反对的,只是晚唐那些过于瘦硬、酸涩的僧人诗。如果认真分析他们的诗学立场,就会发现其推崇的风格不仅与司空图等人不相冲突,甚至深受他们的影响。《石林诗话》中,叶梦得虽认为僧人诗大多是无足道之作,但仍然极力推崇其自然、含蓄、意在言外的的诗风,他赞谢灵运的诗“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6]426;“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6]424;称赞杜甫的诗“出奇不穷,殆不可以形迹捕”,“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意与境会,言中其节”[6]424。
翻开宋代及以后各朝代的诗话,到处可见“有余味”“意在言外”“淡远”“有野意”“有余韵”“意味悠长”“有不传之妙”“平夷恬淡”这样的说法。对陶渊明其人与陶诗的重新发现与定位,是宋人对文学史的一大贡献,而他们最倾慕的,是陶渊明隐士的身份与田园生活的自然、闲适。他们评论陶诗时,能够想到的语汇,也多是“境与意会”“字少意多”“体合自然”“趣向不群”等等。而许多人对苏东坡的称赞,则常常说他“语意高妙”,“如参禅悟道之人”,“深得渊明遗意”。从中,我们不难见出庄、禅思想影响的踪迹,而这正是晚唐司空图等人诗学精神的核心所在。
当一种文学风格成为一种文学观念与价值标准时,它甚至会介入文学史的建构。《诗人玉屑》称引宋人诗话《漫斋语录》的一段话云:
诗文要含蓄,便是好处。古人说雄深雅健,此便是含蓄不露也。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可见风雅;下语六分,可追李杜;下语十分,晚唐之作也。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易,此诗人之难。[6]987
说古人“雄深雅健”的意思就是“含蓄不露”,显然是用自己的诗歌观念对古人诗歌观念的改造。非要把这种诗歌观念套进文学复古论的框子里,也暴露出时代的偏见对作者文学观念的深刻影响。然而,如果不是仅仅把晚唐以后受庄、禅思想影响形成的新的文学观念与特定的文学内容相联系的话,用“用意十分、下语三分”,或者是“意在言外”“造化天成”“有余韵”“意与境会”等后起的文学观念去指称《诗经》、谢诗、陶诗、杜诗,却并非没有道理。汉语的语言特性决定了这种风格在汉语诗歌中不可能只属于某一时期或者是某一流派。
当然,这一诗学理想的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后世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中。而且,与之相关的词汇,不仅出现在宋以后的诗歌评论中,在人们谈论词曲、戏剧乃至小说、文章的时候,其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如“境界”一词,有用于评论诗歌的,如“晨钟云外湿”句,妙语天开,从至理实事中领悟,乃得此境界也。有用于评论戏剧的,如:“若刘晖吉奇情幻想,欲补从来梨园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宫……境界神奇,忘其为戏也。”[14]45也有用于评论文章的,如:“文之出奇怪,唯功深以待其自至,却又须常将太史公、韩公境悬置胸中,则笔端与常境界渐远也。”[15]13
近代学者王国维则在他的《人间词话》中,以“境界”这一概念作为支撑,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诗学范畴,用来观照、评价前人的创作。从中可以见出这些概念极大的衍生能力,同时也可以看出其所包含的文学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可以说,对“韵外之致”的追求,已经成为汉语文学最具标志性的特征。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338.
[2]张振珮.史通笺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3]童庆炳.司空图“韵外之致”说新解[J].文艺理论研究,2001(6).
[4]钟嵘.诗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5]王济亨,高仲章.司空图选集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6]王大鹏,张宝坤,田树生,等.中国历代诗话选[C].长沙:岳麓书社,1985.
[7]刘禹锡.刘禹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8]张少康.论意境的美学特征[J].北京大学学报,1983(4).
[9]王文生.论情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10]程相占.佛学境界论与中国古代文艺境界论[J].东方丛刊,2002(3).
[11]石俊,主编.中国哲学名著选读:上卷[C]//僧肇.不真空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12]晏晨.中隐:中唐时期的一个美学范畴[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13]李乃龙.中晚唐诗僧与道教上清派[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0(4).
[14]张岱.陶庵梦忆[M].上海:上海书店,1982.
[15]姚鼐.惜抱轩尺牍:卷六[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刘海燕)
本刊声明
《中州大学学报》一贯提倡并引领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原创性研究,对追求深邃的理论思想、高端的学术品位、扎实的原创成果和严格的学术规范的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始终保持敬意。本刊坚持以开放的胸怀,着力于学科专业层面,强化文章的学理性、栏目的稳定性和编辑的规范性,以服务于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为办刊宗旨。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国家七部委关于《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的通知精神,坚持以论文的学术质量作为录用的唯一标准。近期本刊发现社会上有不法分子冒充编辑部收取作者钱物的现象,敬请广大作者和读者注意,谨防上当受骗。本刊不收取作者论文发表的任何费用,质量上佳者还有优质稿酬见寄。本刊保留依法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Aesthetic Charm: One Kind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rack of Chinese Poetic Theory
HONG Jun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Weihai Campus of Shandong University,Weihai Shandong 264209, China)
Abstract:Metaphysics of Wei and Jin Dynasty has deepened one proposition in Yi Zhuan, this proposition is “Word fail to convey the meaning, artistic images created to convey their meanings”.Then this proposition has been further researched by a famous Tang dynasty literary theorist Si Kongtu.In his research, aesthetic charm has become one kind of aesthetics ideal of literary composition in China.All of this proposition and theories of poetic imagery of Tang Dynasty are rooted in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and Metaphysics of Wei and Jin Dynasty.The key idea of this proposition is that aesthetic charm comes to an aesthetic world through concrete images.As an important standard, this proposition has not only produced a profound effect upon the later poem creation and evaluation, but also influenced Song Ci, Yuan Qu and other literary genres.This proposition has become a symbolic character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aesthetic charm; theories of poetic imagery;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connotation; influence
中图分类号:J02;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1-0048-06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1.011
作者简介:泓峻(1966—),男,河南郑州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学文本理论研究”(12JJD750020)
收稿日期:2015-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