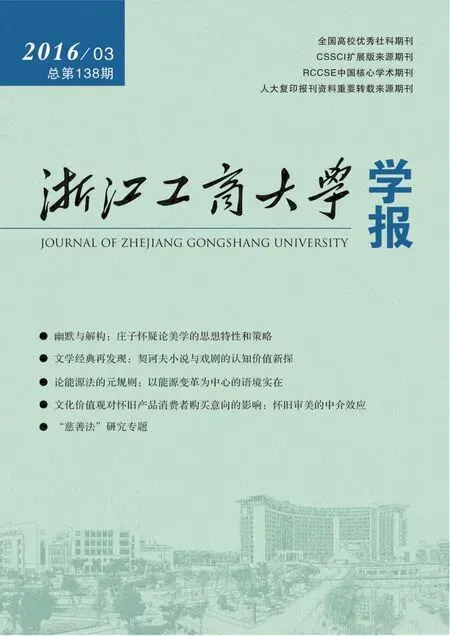疯狂纪事抑或19世纪末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
——评契诃夫小说《第六病室》
2016-01-23维诺格拉多娃
奥·维诺格拉多娃
(1.俄罗斯新大学,莫斯科 101135; 2.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杭州 310058)
疯狂纪事抑或19世纪末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
——评契诃夫小说《第六病室》
奥·维诺格拉多娃1,2
(1.俄罗斯新大学,莫斯科 101135; 2.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杭州 310058)
摘要:本文以《第六病室》为例,概述了契诃夫小说研究的可能视角、其文本解读多样性的原因,以及当时一些关于《第六病室》的最具特色的国内外文学评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医学、心理学、精神病理学为切入视角,同时结合契诃夫本人的创作兴趣,论述了《第六病室》中的三重叙事结构,及其在表现主人公病态心理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心理学研究方法;意识流;叙事角度
一、 对契诃夫作品的诠释:现实而可能
契诃夫被认为是19世纪俄罗斯最后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同时也是20世纪俄罗斯第一位现代派散文家,这为我们研究他的作品增加了难度。尤其是对于他的一些戏剧,很难界定其戏剧类型(喜剧或悲剧)、演员的表现力(人物性格)、作者相对于读者所处的位置等等。而契诃夫的作品中这种双重性和多面性的交织,加上其创作风格的矛盾性,使得文学评论家们可以从不同视角对他的文本进行一些解读:自然主义(社会学角度)、心理现实主义(文化历史角度)以及解构传统文本的(后)现代主义(采用心理学、结构学方法等)等。
英国学者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在20世纪初评论1915年的契诃夫作品英译本时写道:“契诃夫给人一种不做作的印象,(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残渣’——连故事与故事的联结本身都动人心弦,带着天然的诗意。如果一定要为契诃夫贴上一些标签的话,那么他既是现实主义者,也是个诗人。”[1]
众所周知,贯穿契诃夫作品始终的主题包括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对人生矛盾的展现、存在主义的崩塌、孤独、对日常生活的恐惧失望以及精神叛逃,这种叛逃又往往最终将主人公带向疯癫、灾难和死亡。这些主题在契诃夫1890年之后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890年的萨哈林岛之行和1891—1892年的大饥荒都给契诃夫带来了极大的心灵触动。其之后作品的主人公形象变得更为贴近现实,作品中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精神错乱的主题。如果说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精神错乱》(1888年)和中篇小说《决斗》(1891年)中主人公还可以对自己和社会妥协,那么这样的妥协在《第六病室》(1892年)中变得绝无可能。
契诃夫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是精神衰弱者(伊万诺夫、拉耶夫斯基、瓦西里耶夫、万尼亚舅舅等),他们在心理层面都是不正常的。契诃夫曾多次谈到他对人心理活动的方方面面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在与亚辛斯基的一次交谈中契诃夫说到,他对这类人的所有心理倾向都颇有兴趣[2]。契诃夫通过专门的钻研和对精神病人的观察而掌握了精神病学领域的知识。在19世纪90年代,契诃夫还经常去精神病院观察精神病人。那家精神病院就坐落在他莫斯科郊外的梅里霍沃庄园不远处,然而契诃夫对精神病人的兴趣并不在他们的病情本身,而是他们的性格特质。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有所证明,我们在契诃夫的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到自然主义的影子,可以看到精神病人外在形象和内在性格的双重写照。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中医生、市民和作家描述的所谓精神病人们对自我的认知,取决于作者的态度,取决于他们是否是名副其实的“疯子”。作为一个作家兼医生,契诃夫试图解开这些精神问题的谜团。
当契诃夫发掘到一个鲜明的性格特质并决定描写它时,他会对这一特质的不同层面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在契诃夫最受争议的作品《第六病室》中就直接表现了疯狂与理智这一主题。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病人伊凡·德米特利奇——这个简直和自己一模一样却又截然不同的前法警时,拉京医生就对女房东交待说:不该妨碍人们发疯。从语言的表达色彩上来看,这样的态度是同作者本人的立场相一致的。或许,契诃夫本人对于精神病人的一些观点趋同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欧洲精神病学家的观点——缺乏一个标准来准确无异地将精神障碍界定为一种疾病。文中一些简短对话也佐证了这一点。拉京医生与伊凡第一次对话中他就提到:“这跟道德方面和道理全不相干。一切都要看机会。谁要是关在这儿,谁就只好待在这儿,谁就到处溜达,就是这么回事。讲到我为什么是医师,而您是精神病人,这既与道德无关,也讲不出道理来,纯粹是由于简单的偶然性而已”[3]37。另有文中两位精神病人的对话提到,“社会在防范犯罪、精神病人以及一般不稳当的人方面是不会善罢甘休的”[3]37,“……我们软弱啊,我们不中用。……您也是这样,我亲爱的。您聪明,高尚,从母亲的奶里吸取了美好的激情,可是刚刚走进生活就疲乏了,害病了。……我们软弱啊,软弱啊”[3]78。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众多“看似简单却含义多样”的作品之一。“这个故事很无趣,因为故事中完全没有出现女人和爱情元素。……像是谁不经意间随随便便写出的”[4],契诃夫在给作家阿维洛娃的信中写道。如果暂且忽略小说自身的风格和结构,在拉京医生这个形象身上和文中他与多种社会思潮的论战中,我们可以看到契诃夫同时代人的影子(例如对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主义和不以暴力抗恶论的反对,对叔本华和尼采学说追随者的反对),而没有特意关注小说的风格和结构。许多人在这部作品中首先看到的就是对社会的批判。“在《第六病室》中展现了我们和社会秩序的缩影。第六病室到处都是。”[5]作家列斯科夫在谈及这一作品的艺术价值时说道。
许多评论家认为,1892年对契诃夫的人生及其创作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搬到梅里霍沃庄园后,契诃夫投入于社交生活,与自由杂志《俄罗斯思想》的主编们走得很近。在契诃夫梅里霍沃时期的中篇和短篇小说选题中,社会问题和对现有社会环境的不满变得越来越重要。几乎所有这一时期的作品都在探讨尖锐的社会问题,都涉及社会基础阶层——资本家(《出诊》《女人的王国》)、农民(《农民》《在峡谷里》《新别墅》)、知识分子(《我的一生》《妻子》《文学教师》)等。一些评论家认为,在这些作品中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处世之道和社会政治观点,作者也变得越来越独立和矛盾。
至20世纪中期,随着语言学和人文学科的发展,人们对契诃夫作品的形式和语言投入了更多关注。美国学者托马斯·维纳是首批强调“意识流”的学者之一,他指出契诃夫作品中主人公内心对白与外部世界间存在着模糊的界线。维纳详细分析了一些例子,他认为如果从主人公、作者和次要人物这几个叙事角度综合来看文本,就会发现他们往往揭示了作者的评价。[6]
那么,在作家这一身份之外的契诃夫,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和医生,又想告诉读者们些什么呢?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论述契诃夫如何在《第六病室》中呈现主人公不断发展的心理疾病(纠结状态和谵妄的发展)。契诃夫不仅以第三视角客观地从外部论述,并且还以患者的视角从内部揭示病人的内心世界。这种双重叙事角度的存在,是契诃夫有意为之的艺术表现手法,还是恰恰在无意中揭示出作者潜意识里对角色内心世界的沉迷?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但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主人公畸形、病态的意识世界并非常态,正如之后卡夫卡的作品中呈现的那样(尤其可对比《第六病室》与卡夫卡的《审判》,本文受篇幅限制,暂不展开对比)。对契诃夫来说,这并非是其惯用的艺术手法,只是众多作品中的一个案例而已。
同时,众所周知,契诃夫是竭力抗拒自己创作风格中介入荒诞元素的,他不喜欢被称作印象派或革新派作家,也不刻意追求革新。
随着20世纪经典文学体系的变更,文学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跨学科等多样的方式,这为分析文本提供了新的可能,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病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被借鉴使用。心理分析流派在文艺学领域有几个分支:艺术心理学、心理诗学、弗洛伊德主义及其后续的新精神分析批评。这些与语言内在形式密切相关的研究方法在这里十分重要,这类研究方法首先被运用在20世纪乌克兰语言学家波铁布尼亚的著作中。心理学方法着意于主导观点及其展示形式、与作品体裁密切相关的感知主体、意识与潜意识(梦境、幻想、纠结状态等)。在俄罗斯文艺学发展过程中,完善了这种研究方法的还有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文艺学家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和文艺学家高尔恩·费里特。[7]
依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精神分析视角下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人的潜意识、无意识、心理症群、神经症,与作者童年所经历的创伤关系密切。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法分析了莎士比亚、歌德、托马斯·曼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这一观点。
文艺学家斯米尔诺夫、埃特金特运用心理分析法详细研究了本国的文学作品,弗里德曼运用唯心主义心理分析方法分析了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卡希娜·叶夫列伊诺娃在自己的研究著作《天才的地下室》中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性欲之源,叶尔马科夫对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中的心理学现象也有所研究。
斯米尔诺夫在其著作《心理学历时年表:俄罗斯文学中自浪漫主义时期至今的心理学史》[8]中展现了自19世纪至20世纪的心理学演进图景,指出了不同时期作品中的心理类型及逻辑活动,这些不同的心理类型和逻辑活动共同组成了完整的系统。他对心理类型的分析始于普希金和果戈里的浪漫主义作品。当谈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分析时,文学评论家们普遍将其现实主义风格与俄狄浦斯情结相联系起来。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主人公与其他主体并无不同,他们与世界的普遍联系更为紧密。白银时代(更多出现象征主义)的文化是疯狂的、歇斯底里的。因为常常出现即使主体努力寻找,也找不到情绪宣泄对象这种情况,所以施虐受虐倾向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在斯米尔诺夫看来,后现代主义其实是自恋和精神分裂这两种心理类型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在后现代主义中,主体与客体之间完全可以划等号。
由于契诃夫一生都是临床医师,在研究契诃夫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借鉴医学临床和理论研究结果的方式,这样所得的结论是具备说服力的。契诃夫曾明确地说过,医学就像他的妻子,而文学则是他的情人[9]。很多俄罗斯国内和国际上的学者在研究契诃夫的作品时都会将他视作一位医生,相关专题著作有盖泽尔的《契诃夫与医学》(1954年)、梅维的《契诃夫创作与生活中的医学》(1961年)等。许多当代的对契诃夫作品的研究也是从医学这一角度切入的*参见Березина А:Тема болезни и безумия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А.П. Чехова//Остров Горн, 2013, № 8; Белякова М. М.:Парадокс душевной болезни в рассказе А. П. Чехова Черный монах//Филология и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материалы IIмеждунар. науч. конф. (г. Москва, февраль 2014 г.).М.:Буки-Веди, 2014,pp.42-50.。
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我们对从“医学”视角诠释契诃夫的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目前我们还没看到研究契诃夫作品中描写医学或病理心理学现象的艺术价值的相关成果。为什么契诃夫经常描写病人和死亡?——在契诃夫的不同作品中多次出现的不稳定的精神状态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作品中每个病人的故事在整个小说情节结构中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于这些问题,研究契诃夫的文学家们和医学家们都没有给出答案。那么,我们就以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为例来尝试寻找一下这个答案。
二、 故事的情节、感受主体和叙述主体
在分析《第六病室》这一文本时,如果从主观感知和叙事角度出发,在普遍语义和象征主义视域下来考虑这些独特的角色,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某种临床表现,其次可以发现一种多层次的艺术关系。让我们一起来看它们之间有何关联。
故事由第三人称开始讲述,文中还包含着与读者的交流“如果您不怕被蓖麻扎伤,那您就顺着通到小屋的羊肠小道走过去,看一看里面在干些什么吧。推开头一道门,我们就走到了前堂……[3]1。”叙述者对所有人都给予如亲密熟人般的描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叙述者就像是亲历事件本身的参与者一样。叙述者在描写伊凡·德米特利奇·格罗莫夫时写道:“……我喜欢他那张颧骨突出的宽脸,它老是苍白,愁苦,像镜子那样映出他被挣扎和不断的惧怕所折磨着的灵魂。他的悲苦的脸相是奇特的、病态的,然而清秀的面容虽则印着深刻真诚的痛苦,却聪明,显出文化修养,他的眼睛射出热情而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他本人,殷勤,乐于帮助人,对一切人,除了尼基达以外,都异常体贴。不管谁掉了一个扣子或者一把调羹,他总是赶紧从床上跳下来,拾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总是跟同伴们道早安,临到躺下睡觉,又向他们道晚安[3]4。”然而故事起初明确出现的叙述者,在随后的文中仅仅出现两次,甚至到最后完全消失。这样的处理方式把隐含作者和主人公的声音巧妙地揉为一体。
第二章由第三人称展开。在第三章我们开始得知伊凡·德米特利奇究竟有怎样的感受,就好像叙述者走入了他的意识:“……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走过窗前:这不会平白无故。喏,有两个人在房子附近站着不动,也不说话,为什么他们不说话呢[3]10?”随后,在第四章描述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生时,“叙述者”承认,并非所有人都知道他——这意味着他并非故事的作者,是这样的吗?还是说这种独特的不确定性并不是为了叙述者,而是为了将故事继续讲下去的隐含作者?具有情态色彩的短语出现在了这一章和接下来的一章中,譬如“这次谈话又持续了近一个钟头,显然给安德烈·叶菲梅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50
而与此同时隐含作者从某处得知了拉京医生的感受:多年以来主动疏远人群,却又免不了要与他们接触,当听见小孩的啼哭或者看到血时,便会有耳鸣、心悸的感觉。这些叙述者站在“故事之外”所给予的描述和评价,其实在与世界的关系、沟通方式,甚至是祈使情态色彩:“达留希卡,最好开饭吧。……”[3]24*达留希卡为“达利亚”的爱称。这些方面,已经掺杂了拉京医生的内心感受。在第六章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对于拉京医生病情日渐严重的暗示。“‘多么可惜啊,’他缓慢地轻声说,一面摇着头,眼睛不看对方的脸(他从来也不直视他人的脸),‘真是可惜极了,尊敬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我们城里根本就没有一个能够聪明而有趣地谈谈天的人,他们也不喜欢谈天。这在我们就成了很大的苦事。甚至知识分子也不免于庸俗,我可以断言,他们的智力水平丝毫也不比下层人高。’[3]25”类似主题的对话在这一章多次出现,只是描述时的语言稍有不同。这对白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故事的高潮做出铺垫。一方面,在描写格罗莫夫的精神错乱时,反复强调他作为小市民的庸俗和卑微,以及城市中智慧与知识兼备的人群的缺失;另一方面,这对白还透露出萦绕在拉京医生心头的那个念头:精神上的快乐和满足才是生活的唯一。
在后面的章节中,尽管只有无所不知的隐含作者在讲述,但有关拉京医生的痛苦的描述却越来越多。对拉京医生精神混乱的描写常常围绕在对一些典型话题的叙述展开——孤独,过多的抽象阅读,生活的创伤。因为人们对他来说变得难以容忍,他如今甚至也有了格罗莫夫曾经有过的姿势。为什么这样的变化会反复出现呢?
拉京医生似乎从伊凡·德米特利奇那传染上了懒散之气,还沉溺在自我的世界中,他甚至开始长时间地躺在沙发上,脸对着靠背。这姿势和生病的警察在第一天忽然中断和他的谈话时的姿势一模一样。“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照例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墙,咬紧了牙听他讲话。他的心上压着一层层的沉垢,他的朋友每来拜访一次,那些沉垢就长高一层,好像就要涌到他的喉头了。”[3]67他们的相识是医生疾病的诱因。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很喜欢格罗莫夫,并因此不再喜欢其余所有那些让他觉得压抑的东西。由于与伊凡·德米特利奇相识,拉京在他那里发现了超价值观念,同时也固执地对周围世界失去了兴趣。甚至他唯一的朋友都开始令他觉得无比沉重。“我的病只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二十年来我在全城只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他却是个疯子。我根本没有生什么病,无非是落在一个魔圈里,出不来了。”[3]72
在性情和意识形态的独特性方面,拉京和伊凡·德米特利奇可以说是一样的:一个孤僻冷漠,一个时常激愤而不满,二人对社交活动和提升周围人生活品质这些事都很不擅长。似乎作者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任何个体,如果渴望拥有深邃而复杂的思想,就注定会陷入疯狂的状态。“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好像关在一个牢笼里,逃不出去似的。——拉京说道。”[3]27在契诃夫的作品中,知识分子和疯子是相互开放统一的,作者似乎想要指出这些有头脑的俄罗斯人可以无限“变坏”,这一类人就属于“危险群体。”
如果说在小说的开头我们看到的是一对明显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是快要发疯的病人,一个是医生。那么到了小说的最后,他们之间已经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医生和病人的关系。相比于拉京医生,伊凡·德米特利奇反而显得更加稳重睿智,其人生哲学中也表现出“保守”这一特点。这也许是契诃夫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模糊健康心理和病态心理之间的界线(尽管伊凡·德米特利奇是个病人,但他却有着健全的思维能力——而直至最后一刻,健康的拉京医生却坚持着不那么现实的世界观),这与契诃夫对上流社会(尤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好逸恶劳、思想空洞的怀疑态度相互呼应。契诃夫的这种态度在当时就已经广为人知,在众多评论中人们对此也积极讨论。
文中隐隐显露出的作者的角色很有趣。在为格罗莫夫体检这一情节中,契诃夫就像是“扮演了一个医生”,而在第六病室内医生和格罗莫夫的对话中,契诃夫又开始站在伊凡·德米特利奇背后,在小说中,有时他还会借“叙述者”之口发声。这种三面性或许可以证明契诃夫创作过程中的内心矛盾,而这种矛盾在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得到释放和解决——随着主人公拉京被带入第六病室以及格罗莫夫复仇般的“喜悦”而烟消云散,三面性也由此消失。叙述者再次置身事外,变回一个不表态的观察者,与作者合而为一。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人的故事即世界观:病人(格罗莫夫)、医生(拉京)和作者。其中作者尽量表现得客观公正(相对健康),而从心理病理学角度来看,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作者身上似乎也出现了精神障碍的迹象(纠结状态)。譬如,我们看到的次要人物形象从开头到结尾渐渐变得苍白干瘪、单一而没有深度——作者让他们无一例外地与主人公产生冲突——就好像是作者本人仅痴迷于主人公的人格似的,似乎除了主人公,其他一切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作者对描写主人公之外的人们毫无兴趣,他带我们一起深入拉京医生的意识之中,次要人物在医生的意识中只是充当着病人这一元素。
一直存在于拉京脑海里的念头——注定要全部覆灭——在作品中成为了现实。这就是为什么他最后被迫害致死——拉京的念头已经走出了主人公的脑海,成为了作者构思的一部分,读者也被拉入这样的意识中。“为了扑灭这些卑俗的思想,他赶紧思忖:他自己也罢,霍包托夫也罢,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也罢,迟早都要死的,在自然界连一点痕迹也不会留下。”[3]67
对契诃夫而言,这样的结尾像是一场内科手术(或者说是心理完形的闭合),因为它使主人公的有关外部世界的极度焦虑状态得以解脱。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医生的死亡并没有那么必要——在他最后被带到第六病室的时候,他的路就已经到头了。格罗莫夫的脸露出恶毒而讥诮的神情,对拉京说道:“啊哈,把您也关到这儿来啦,亲爱的!”他眯细一只眼睛,用带着睡意的沙哑声调说,“我很高兴。您本来吸别人的血,现在人家却要吸您的血了。好得很!”[3]76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作者、叙述者和故事人物三者之间的矛盾,使我们无法对作品塑造的艺术形象给出一个明确的评价。然而从艺术角度出发,三方争论这一设计恰恰在宣泄情绪方面造成了独特的效果。假如在小说《决斗》里动物学家没有杀死道德败坏的拉耶夫斯基,拉耶夫斯基随后成了“对社会的危险性不下于霍乱细菌”的人,假如契诃夫为拉耶夫斯基安排了之后改过自新之路,那么所有读者可以想象到的可能性都将不复存在。只有死亡,才能将医生从过于沉重的使命、薄弱的意志、注定走向病态的天性以及作者对他的特别关注中解救出来。拉京医生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才恍然大悟:他曾给了别人怎样的冷漠和残酷,又是如何亲手把自己送入深渊。
受文章篇幅限制,很遗憾我们无法进一步详细阐述契诃夫作品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理智”“疯狂”“工作”“哲思”等,来使得上述分析论述更加充实有力。
参考文献:
[1]ШЕРЕШЕВСКАЯ М А,ЛИТАВРИНА М Г. Чехов и мир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н.1[M]// ПОЛОЦКАЯ Э А. Чехов в английской критик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и. М.:Наука,1997:406-453.
[2]ШУБИН Б М. Доктор А. П. Чехов[M]. М.:Знание,1997:113.
[3]契诃夫.第六病室[M].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ЧЕХОВ А П. А. П. Чехо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в тридцати томах[M]// ЧЕХОВ А П. Письмо к Л. А. Авиловой. 29 апреля 1892 г.М.:Наука,1974:64-66.
[5]ЛЕСКОВ Н С. А. П.Чех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M].М.:Гослитиздат,1947:187.
[6]WINNER T G. Chekhov and his Prose[M].N.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66.
[7]ДМИТРИЙ С М. Пути и вехи pусско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в двадцатом веке[M]. М.: Водолей,2011:79.
[8]СМИТНОВ И П, ПРОХОРОВА И Д. Психодиахронологика: Психо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от романтизма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M].М.: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1994:66-67.
[9]ГЕЙЗЕР И М. Чехов и медицина[M].М.:Медгиз,1954:134.
(责任编辑杨文欢)
The Chronicle of Madness or an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Life in the Late XIX Century?——OnWardNo.6 by A. P. Chekhov
O.VINOGRADOVA1,2
(1.RussianNewUniversity,Moscow101135,Russia; 2.SchoolofInternationalStudies,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58,China)
Abstract:TakenWardNo.6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possible perspectives of Chekhov’s works, the reason of the diversity of interpretation of Chekhov’s texts, and a number of the most uniqu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onWardNo.6.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of other schola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ipl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A. P. Chekhov’sWardNo.6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cine, psychology and psychopathology in combination with Chekhov’s own creative interest, and explore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s effect on the display of the protagonist’s morbid psychology development.
Key words:research methods of psychology;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arrative perspective
收稿日期:2016-03-15
作者简介:奥·维诺格拉多娃,女,俄罗斯新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外籍教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民俗学研究。 李培,女,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6)03-0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