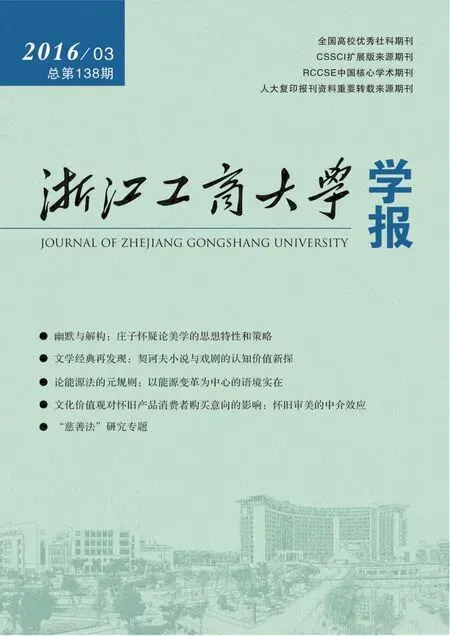由亲缘性到互嵌性: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发展关系
2016-01-23冯元
冯 元
(1.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管理学院,南京 210038;2.台湾东海大学 社会工作学系,台中 40704)
由亲缘性到互嵌性: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发展关系
冯元1,2
(1.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管理学院,南京 210038;2.台湾东海大学 社会工作学系,台中 40704)
摘要: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近年来逐步被视为我国社会福利体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参与力量。西方社会工作起源于英美慈善事业,在民国时期经由西方传教士及教会组织传入国内,并吸纳本土慈善文化滋养而生长出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在当前政策制定、理论研究与实务推进过程中都对两者的互动性关系关注不足的情境下,重新梳理和审视社会工作在西方起源及在我国起源时与慈善事业的亲缘性发展关系,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借鉴意义。在当下和未来,都不应疏离或切割两者的密切联系,而应积极在政策、理论、实务层面构建互嵌性发展关系,充分整合两者的优势与资源,促进优势互补,互动共赢,共同助推中国特色的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建设。
关键词:社会工作;慈善事业;社会福利体系;互嵌性;社会治理
2005年民政部向全国人大提出慈善法起草建议,2009年民政部向国务院提交立法草案,标志着慈善法立法工作正式进入立法程序[1]。经过“十年怀胎”,我国首部《慈善法》于2016年面世,在国家以“开门立法”与“民主立法”为精神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过程中,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和密切关注。从《慈善法(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来看,只分别在一审稿第六十四条处和二审稿的第五十九条处的“开展医疗康复、照料护理、教育培训、社会工作等具有专门技能的慈善服务,应当执行国家或者行业协会制定的标准和规程”规定中提到社会工作,而最终颁布的《慈善法》中却并未出现“社会工作”一词。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此次立法过程中对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定位与功能以及两者的关系的关注和考量明显不足。不论学界还是实务界不容忽视的是,社会工作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慈善事业发展风潮中,此后两者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从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两者的历史缘起中的亲缘性关系和现实及未来发展中的互嵌性关系加以论述,以期引起决策者、研究者与实务者对两者内在联系的注意和重视,加强对它们的整合利用。
一、 英美慈善事业历史视野中的社会工作生长与分野
社会工作的生长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它的生长与西方英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作为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长达一百年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所遵循的是亚当·斯密的放任自由主义思想,信奉个人对自己的贫困负责,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实行最小干预,由此导致社会问题丛生,在国家无力应对的情况下,宗教慈善与民间慈善也迅速发展起来,充任弥补国家在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上供给不足的主要力量。随着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科学性与专业性议题也应运而生,专业社会工作也就在这种背景和土壤中得到生长,并由科学慈善之身走向专业独立发展之路。
(一) 英国工业化社会催长的慈善事业
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英国兴起一场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浪潮,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发生重要变革。机器大规模的使用导致大量手工业劳动者失业,席卷农村的圈地运动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但政府未能开展与经济与社会结构急速变迁状况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导致大面积出现失业、流浪乞讨、居住环境恶劣、疾病流行等为特征的城市病[2]。如英国手工织布工数量在1820年时为24万人,但到1840年时已减至12.3万人,到1856年已只剩2.3万;又如英国棉纺织工人在1806年每周平均工资为200便士,到1830年已降至90便士[3]。这种由少数人掌控财富的工业经济发展形态导致贫困化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量人口长期处于严重的贫困之中。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工业革命时期有近三分之一的英国工人家庭始终处于贫困状态,到1834年英国贫困人口达到12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8%[4]。纵然英国1601年所颁布的具有现代济贫制度奠基意义的《济贫法》,在工业革命时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面对工业化所带来日趋严重的贫困和失业问题却作用失灵,反而致使财政救济支出不堪重负,如1802—1833年间,英国济贫税增长了62%,这使得《济贫法》招致大量社会批评和改革的激烈争论[5]。
在此背景下,各种改革声音催生了1834年的《新济贫法》颁布,该法最大的影响之处在于将以往兼施院内和院外救助的模式全面收缩为院内救助;其次该法建立更加紧密的济贫管理体系,在全国建立了济贫委员会,由济贫委员和济贫监督官管理教区济贫事务。在新的济贫制度中,对贫民的资格审查和管理更加严苛,大量需要救助的贫民被排除在济贫制度之外。这一问题显见于未同步取缔院外救济的教区的救济数据,1841—1842年英国590个联合教区之中有132个保留了院外救助职能,184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院内救济量为23.1万人,而院外救济量为124.7万人,1848年院内救济量增至30.6万人,院外救济量增至157.1万人[3]。在这种新济贫制度之下,社会贫困化未被有效遏制反而不断加剧,以及损伤受助者尊严和权利的强制性救济方式,引起了基督教会和慈善人士的关注和重视。新济贫制度的核心思想是个人应该对自己的贫困负责,而不能依赖国家的福利救济,因而其采用“劣等处置”和“济贫院检验”原则,要求受助者必须进入济贫院,将救济视为对穷人的一种惩罚,其目的在于提供最低限度的救济,治理穷人懒惰和道德缺陷,促使他们去工作[6]。在这种形势下,并未消减的大量贫困人口转而从教会、慈善人士、慈善机构那里获得救济。旺盛的济贫需求恰恰刺激了民间慈善组织和民间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据桑普森统计,1972年伦敦有700个慈善机构,其中1850年至1972年间增加了204个,增幅为29%[7]。到19世纪后期,英国的慈善事业得到更加蓬勃的发展。
(二) 英美慈善事业中衍生的社会工作
19世纪末期英美慈善组织会社运动为社会工作起源提供了肥沃土壤,个案工作方法正是在此过程中初步形成。早在1814年,查默斯牧师就在Glasgow教区进行了尝试,将教区划分为25个责任区,每个教会执事负责一个责任区,对区内求助者进行家访,评估其家庭情况和求助需要,这些执事便是最早的友好访问员[8]。1869年,由索里牧师推动全英各大城市成立慈善组织会社,其服务组织模式的重要特点是分区责任制,他们将城市分区,每区设置一个志愿者委员会负责求助者的申请登记,资料核查及提供济贫委员会问询和慈善组织与慈善人士查询等工作[9]。慈善友好访问员在他们进入社区和家庭广泛开展访贫问苦的过程,发展出一种个别化的工作原则与方法,这正是个案社会工作所坚持的核心原则和方法。从社会工作缘起的角度而言,慈善友好访问员正是早期个案工作者雏形,而查默斯牧师作为慈善组织会社运动的重要直接发起者与推动者,自然而然被视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史中的第一位个案工作者。1877年,慈善组织会社运动由布法罗圣公会引入美国,随后美国各大城市慈善组织会社运动迅速扩展。在此背景下,随着慈善组织会社数量的迅速增长和慈善活动的不断扩展,重复慈善救济增多,慈善信息管理难度增大,慈善组织协调更为复杂,慈善人员工作能力不足,慈善资源配置不合理,慈善救济效率偏低等现象浮现,成为一个必须应对的现实问题,因而以加强慈善人员专业训练与教育,聘请专职人员从事慈善救济等为特征的“科学慈善”运动命题应运而生。1893年美国水牛城慈善组织会社提出应该让接受过特殊训练的专职人员从事慈善救济工作,被视为“科学慈善”运动的开端,其也被视为慈善事业衍生与裂变专业社会工作首要动力源泉和主要历史事件[10]。1912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开设社会工作课程,随后社会工作教育迅速发展,成为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知识化与科学化的重要力量[11]。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不同于慈善组织会社形态的睦邻组织运动也在英美风行,两者被视为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方法形成的先导。1844年乔治·威廉在伦敦成立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1851年基督教青年会传入北美,他们针对工业化时期青年失业、失范与道德惰化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诸如研读经书,开设讲坛,创置会所与阅览室等社会服务活动[9]。1864年丹尼斯在伦敦东区开创贫民区驻入式服务模式,其与知识青年一同住进贫民社区,提供贫民教育。1875年圣裘蒂教会的巴涅特开创大学生入驻贫民社区的贫民服务模式,并于1884年在伦敦设立汤恩比馆,为老人、儿童、劳工与移民等教育、娱乐、法律等服务[12]。1889年经由汤恩比馆的神学生简·亚当斯在芝加哥设立赫尔馆,从面向社区儿童提供托管、课后照顾、夏令营服务扩展到面向社区居民提供教育、艺术、文化活动与创办图书馆、餐馆、合作社等社区服务[13]。这种以社区为介入系统,充分运用社区资源和社区居民力量,注重工作者与社区居民建立良好的合作参与关系,以发展社区服务、解决社区问题与提升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睦邻组织运动正是社区工作方法的核心要素所在。
(三) 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分野独立
社会工作专业由“科学慈善”运动演进而来,其与慈善事业保持短暂的伴生关系后走向了独立的专业化道路。1915年弗莱克斯提出著名一问“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吗?”,他提出批判的首要理由是社会工作缺乏自己的理论,玛丽·里士满在此情势下于1917年出版标志社会工作专业正式形成的《社会诊断》,并与其他人员积极引入精神分析学派理论,以提升社会工作的理论性与专业性[14]。专业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分野与独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1929—1933年美国遭遇经济大萧条,罗斯福于1933年开始实施救济、复兴与改革为三要素的新政,《社会保障法》等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为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制度空间。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时期及战后英美等国出现了大量诸如贫困、青少年犯罪、家庭解组与功能缺失、疾病流行、战争心理创伤等社会问题,为社会工作实务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因而也造就了美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实务首先在医务、精神治疗、儿童与家庭、学校社会工作四大领域展开[15]。二战后,英国采用《贝弗里其报告》,建立起典型的福利国家制度,为公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普遍性福利。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利的资源传递者,在福利国家制度框架下获得了快速的制度性发展。如1948年英国《儿童法》要求地方政府设立儿童部门,促使儿童社会工作成为当时英国社会工作最重要的领域[16]。
社会工作从慈善事业中分离与独立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工作从理论与实务上追寻专业化的过程。社会工作在1950年代前的半个多世纪中,主要处于专业理论与实务方法的早期孕育与初步形成阶段。美国大概是在1950年代初确立了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地位,1955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基本奠定了美国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地位[15]。相比于美国,英国的专业发展环境也十分良好。英国于1945—1979年实施的是典型福利国家制度,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丰沛的滋养和条件,特别是1968年西蒙委员会所提出的于1971年正式设立的统一社会服务部门后,当时多数社会工作者被政府聘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案与服务受到广泛认可,从而确立了社会工作在英国的专业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社会工作最早孕育于英国,但是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道路一直由美国主导[16]。社会工作在专业发展的过程中深受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环境影响而呈现不同的特点。如社会工作在其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发展出反身性—治疗性,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改良主义三种理论类型,在三种理论类型中,又可以看到由心理动力、危机干预等微观型理论到系统与生态,社会心理等宏观型理论,再发展到人本主义,批判主义,女性主义,反歧视,文化与民族敏感等理论的社会工作理论演进脉络[17]。而这些专业理论的发展与影响变迁与相应阶段的主流社会思潮是相呼应的,如实证主义思潮下社会工作服务要求重视服务结果和成效,因而社会工作实务非常关注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收集证据;如20世纪兴起的反压迫思潮要求社会工作者注意专业权威的慎用和反思,注重和服务对象建立平等互动的关系,而女性主义的出现则引导社会工作服务要考虑性别和性别差异[18]。
社会工作百年发展历程中,其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慈善事业是广为共识的。但社会工作走向专业化后,实务工作者与学者们对两者关注的声音有严重弱化趋势。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国内学术界对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关联性研究非常薄弱,对两者关系的关注也严重不足。而有关社会工作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民国时期的研究却不多[19]13。首先,此次《慈善法》未提及“社会工作”就是重要明证。其次,通过中国知网搜索,截止到2016年2月底,篇名同时包含“慈善”和“社会工作”的核心期刊仅有2篇,篇名同时包含“宗教”和“社会工作”的核心期刊论文为3篇;篇名包含“慈善”而全文包含“社会工作”的期刊论文为105篇,篇名包含“社会工作”而全文包含“慈善”的核心期刊论文385篇。仅有的少量文献,主要探讨的是西方社会工作起源与慈善事业的关系,而少有文献就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与社会工作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 民国时期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的关系渊源
社会工作在我国的生长受历史因素的影响而被分割为两个时期,分别为民国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至今。前一时期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战乱频仍,灾害频发,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引起一系列的诸如贫困加剧、流民增多、疾病流行、家庭破裂、孤儿成群等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一情形,国民政府,民间慈善组织与慈善人士,外来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纷纷参与到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中,促进了当时的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发展。可以说,我国的专业社会工作是伴随西方传教士传教与慈善活动及西方社会学引入过程而产生的[20]。后一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社会学恢复重建过程中,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也得到缓慢发展,而其在实务上,人们较多关注其与民政工作的关联性,而较少关注其与慈善事业的关联性。因此,在探讨我国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关系时,就不得不检视民国时期两者之间的关联和意义。
(一) 民国时期慈善事业的发展
中国有着悠久的慈善传统和思想基础,民为邦本思想,儒家仁义学说,道家行善积德思想和佛家慈悲为怀与因果报应学说,以及传统的宗法族规都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思想营养来源[21]。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我国被迫对外开放,由此至民国时期成为西方教会慈善进入和成长的重要阶段,这在客观上也催生了我国传统慈善事业向近代慈善事业转型。而近代慈善事业又是民国时期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源头,为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方法基础[19]41。西方教会在我国的慈善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医疗慈善事业,它是西方教会在我国最先开展的慈善活动,截至1877年西方教会在华创办的教会医院达到16所,而到20世纪初比较有名的教会医院已经达到30多所,据1937年《基督教差会世界统计》显示,美国基督教会和法国天主教会在华兴办的医院分别达到300所和70所。其二是儿童慈善事业,1901—1920年各国天主教会在华兴办了150多所孤儿院,收养孤儿多达1.5万名,相比而言,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也创办了大批规模相对较小些的孤儿院。此外,循道会、信义会、宣圣公会、浸信会、路德会和北美长老会等教会组织还创办了盲校、聋哑学校、残疾儿童特殊教育学校等,提出并践行“教养结合”的慈善救济原则。其三是赈济慈善事业,我国在1876—1879年经历“丁戊奇荒”,西方教会组织将西方成熟而严密的慈善物资和资金募捐、管理、输送和分派技术和经验带到我国,并刺激了我国民间慈善组织对慈善效率与成本的反思和改革。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成为常态,促使传教士与我国民间慈善人士建立了一定的合作关系,在一些城市成立华洋义赈会。在民国后期,传教士大都与我国民间慈善组织和慈善人士联合成立各类慈善组织,如国际统一救灾会等,这些慈善组织在抗日战争期间参与了大量赈济兵灾、救护与遣送难民、掩埋尸体等慈善活动[22]。
相比于教会慈善,我国民国时期应对灾害救济等慈善事业主要有政府,民间慈善人士及其组织,本土宗教组织三股力量。首先,政府发展了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事业。一是出台了大量诸如《社会救济法》等慈善与救济相关政策法规,促进了慈善事业的规范性发展;二是设置了大量社会救济设施,各级政府直接设置了大量诸如救济院、慈幼院、习艺所等救济与福利设施,同时对私人与民间的救济设施进行监管;三是设施了专项救济资金,如国民政府颁布《救灾准备金法》,中央与地方将每年的救灾准备金纳入预算,用以保障救灾与救济经费;四是实施多元化救济,政府开辟工赈、农赈、赈灾公券发行等救济方法,同时非常注重整合民间慈善力量[23]。其次,民国时期的民间慈善处于转型与快速发展中。在维新运动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许多新的慈善理念和民间公益团体[24]。到民国时期慈善事业比历史上任何一时期都要发达,表现在其拥有大量的正式慈善机构和慈善服务项目,出现了大批慈善家和慈善人士,对社会关系调节和社会问题治理产生了巨大作用[25]。这一时期,大批下野军政要员,前朝遗老,实业家等投入慈善事业中,他们遵循“教养结合”的原则积极开展慈善救济与慈善教育。如熊希龄于1920年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就是典型的“教养结合”的慈善机构,对收养的孤贫儿童实施文化教育和技术学习,至1949年香山慈幼院共教养儿童超过6000人[26]。这些慈善家作为当时的慈善家群体,以其特殊的社会阶层地位聚集了强大的民间慈善力量,并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在社会救济事务上依赖于他们,如民国时期湖南多次遭遇灾害时,时任省长赵恒惕都求援于湖南乡党熊希龄,通过其召集在京湖南人组成旅京筹赈会对湖南灾民进行赈济[24]。再次,诸如中华佛学会、中华佛教总会、佛化新青年会、世界佛教居士林等佛教组织纷纷积极参与当时的灾民、难民、失业者、残疾者、乞丐、失养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救济中[27]。
民国时期,外来教会慈善和我国本土慈善构成了当时慈善事业的主体内容,尽管外来教会慈善具有一定的民族与文化侵略性的消极作用,而本土慈善也存在诸多贪污腐败等负面影响,但我们应该正视他们所产生的诸多积极作用和意义。从社会工作角度而言,当时的慈善事业中既通过西方传教士将一些具有社会工作元素的理念、方法和技术引入到我国;而本土慈善也在中西文化的共同影响下,生长了具有本土性的社会工作服务元素。这些特定的因素和环境为民国时期我国社会工作的孕育、萌芽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二) 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发展路径主要有两条,传统社会工作的本土性生长和西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引入。如与西方社会工作缘起于慈善事业一样,我国社会工作的主体也是从慈善事业中演进而来[28]。首先,民国时期社会工作教育发展在西方教会推动下得到快速发展。民国时期,大批高校由教会所创立和运营,为社会工作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平台和强劲动力。步济时作为缉基督教青年会的关键性人物,筹划和创建了大量的社会服务项目与组织,1917年其在燕京大学创立社会学系,积极推动社会工作研究、实务和教育发展,其本人也被称为“中国的社会工作之父”[19]17。1925年燕京大学将社会学系改名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雷洁琼受时任系主任的许仕谦邀请在该校从事社会工作教育[29]。此外,沪江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岭南大学等教会学校都开设了社会学、社会服务、社会工作相关课程,积极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其次,社会工作实务在专业教育的推动下得到发展。以上列举的教会学校在教育过程中十分注重学生实务能力培养和社会服务参与,通过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让学生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精神。如时任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就社会学教育目标提出“首要任务不在社会学理论而是在社会工作者训练上”,该系在抗战时期与上海市儿童保护部、国际红十字协会、全国儿童福利协会等组织有紧密合作,积极参与了当时的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服务。再次,社会工作研究有快速发展。1902年至1948年间,我国共有316部社会学著作,其中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方面的为25本,且其中21本在1941—1948年间出版;1944年《社会工作通讯》创刊,成为民国时期首本专业社会工作期刊[19]17。
(三) 行政推动下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的互动
孙中山所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思想对民国时期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将社会福利事业放在重要位置,并从多方面予以管理和规范。首先,设立专门机构统筹管理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1912年孙中山的临时国民政府设立内务部,其职能之一就是管理社会事业;1929年行政院下设赈灾委员会,1930年该委员会与赈务处合并为中央振务委员会,并设立各省市下属机构;1937年为应对战时需要设立社会部,负责战时伤员救护、儿童救助、难民救济等各种福利与慈善事业[19]13。其次,通过立法促进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规范发展。国民政府积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发展经验。1928年起,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监督慈善团体法》《各地方慈善团体立案办法》《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等有关慈善事业的管理规范[30]。1936年陈凌云在考察英、美、德、日等国家后在其《现代各国社会救济》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救济仍然立基于慈善的“恩惠”与“施舍”思想,而西方却是将社会救济视为政府的责任[31]。此后,国民政府扩大了自身的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责任,1940年国民政府在其社会部下设总务司、组织训练司、社会福利司、合作事业管理局四大机构来管理包括教会组织、民间组织在内的全国社会行政事务,而地方也设立了相应的行政机构,并由地方政府直接设立了大量救济院、育婴院等社会福利与服务机构,这标志着传统社会救济转向现代社会服务,也表明国民政府的社会福利行政由此走向专业化[32]。1943年国民政府进一步颁布了《社会救济法》,开创社会救济立法先河,促进了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在制度性环境下的融合发展,也为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互动性发展提供了制度性路径。再次,中共在其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等区域内广泛开展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的诸多群众工作和社会服务,也是具有历史特色的社会工作。1934年毛泽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提出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的一切问题,就蕴含了非常重要的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思想[19]41。
三、 社会工作与现代慈善事业的“互嵌性”发展
发展现代慈善事业,与发展现代社会工作事业一样,已经成为我国政府与社会的重要共识。从西方社会工作起源到我国民国时期社会工作起源看来,其起源都与慈善事业有着亲缘性的关系,或者说西方和我国的社会工作都是借慈善事业之胎孕育而生。在国内,社会保障一般涵盖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优抚安置四个方面,而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却涵盖了社会保障,如英国《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社会福利条目下设置两个子条目为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33]。2005年我国将慈善事业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34],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从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经验来看,慈善事业是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补充力量。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建设[35],并将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内容。依据西方经验和我国实际发展状况,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都可以视为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力量。“嵌入”一词源于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意指某事物卡入另一事物的过程和结果,该词由王思斌引入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的讨论中[36]。本文沿用这一概念,并认为我国现代社会工作与现代慈善事业应该在社会福利体系框架下保持“互嵌性”发展关系,才能有效地整合彼此的优势和力量,并为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体系而提供更好的支持。
(一) 政策层面的互嵌性发展
我国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复苏,继2005年慈善事业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后,社会工作也于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纳入国家政策议题。此后,两者获得了快速发展,社会工作于2014年被纳入《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而慈善事业也于2015年进入立法程序的关键节点。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强调“支持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发展”。这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重要政策地位,也论述了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已有相关政策来看,社会工作政策与慈善事业政策都考虑了彼此的联系和优势。通过政策梳理与分析(见表1),可以发现两者在政策定位上有三个特点:一是社会工作可以为慈善服务提供专业人才、方法、技术与服务;二是慈善事业是社会工作的重要作用领域;三是慈善组织和个人可以为社会工作服务与社会工作机构提供资源支持。本文认为现有政策已然认识到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之间的“互嵌性”发展关系,但是这种认识不够深入和系统,相关政策条款过于笼统和形式化,缺乏操作性和实践性。今后,相关政策制定和调整过程中应该充分认识到两者早期起源的亲缘性关系与未来发展的互嵌性关系,充分考虑两者的互嵌性发展路径、程序、角色、功能以及监督、评估等议题,从政策上提出更多更具有操作性与引导性的规定和规范。比如,在慈善法制定过程中,非常值得考虑社会工作在慈善对象需求评估,服务介入,服务控制以及慈善项目方案规划与实施,慈善资源输送与整合方面的优势,通过引导性政策来拓宽社会工作参与慈善事业的路径和合法性身份。事实上,我国在制定面向儿童、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弱势群体的福利政策时,已开始注意到整合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力量与资源。如2016年由国务院制定的关爱保护流浪留守儿童的政策,以及2015年中央有关精准扶贫政策,就注意到从政策层面引导各级政府整合两者的优势与资源。
(二) 理论层面的互嵌性发展
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困境突出表现在缺乏理论基础,法制保障滞后,慈善组织规范性发展不足几大问题,国内学者对我国慈善事业的理论研究也十分薄弱[37]。从中国知网文献搜索结果来看,仅有少量文献是探讨慈善事业理论问题的,且多是针对企业捐赠进行理论探讨的。我国慈善组织的许多工作人员来源于民政机构,如各省市的慈善总会组织,他们缺乏必要的专业理论背景,专业服务能力不足[38]。因而,在现代慈善事业构建的过程中,如何发展慈善事业自身的理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社会工作发展近百年来,一直注重通过理论研究来发展自身的理论,这些理论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科学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我国慈善事业可以借助社会工作的理论优势,加强慈善组织与社会工作学术机构的沟通与合作。一方面将已有的适合慈善事业的社会工作理论引入并进行内化性整合,另一方面,可以邀请社会工作学者和其他学科的学者针对慈善事业进行理论研究,发展慈善事业自身的理论体系。近年来,诸如“郭美美”等事件对慈善组织外部形象和公众慈善热情造成严重损伤,也一定程度折射出慈善组织所面临的内部治理结构松散和失效问题。如果能够引入或参考社会工作职业伦理,组织行为学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对慈善组织内部治理是必然有益的。慈善事业具有救急不救穷的特点,它往往是利用慈善捐赠帮助慈善对象解决临时性困难,如医疗、教育、生活贫困方面的救助最为常见,但这些救助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慈善对象的问题。而社会工作却是以“助人自助”为原则,具有“授人以渔”的激发服务对象潜能,恢复与发展社会功能的功能。如果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能够两者相结合,既能弥补慈善事业理论不足的现实困境,又能为社会工作理论应用和创新提供新的土壤,而慈善事业大量的实务经验也能丰富社会工作的实务理论。
(三) 实务层面的互嵌性发展
据民政部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4底年我国有基金会4117个,社会团体30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9.2万个;2014年全国共接收社会捐赠款物604.4亿,福利彩票年销售额2059.7亿元;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16万[39]。截至2015年底我国有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4686家,社会工作行业组织455家[40]。从数据来看,一是慈善组织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都具有一定的规模了;二是公益慈善组织能够募集大量慈善资源;三是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数量可观,且呈逐年大幅增长之势。如果将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置于我国现代社会福利体系下,慈善组织扮演的是政府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资源”,而社会工作扮演的是政府和慈善组织的“资源传送带”。因此,在实务层面,要充分注意整合利用这两者的角色功能和优势,并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两者的互嵌性发展。其一,专业人才队伍的互嵌,在专业人才教育过程中,社会工作专业和慈善专业都应当共同设置两者的核心课程;社会工作组织与慈善组织可以互引对方的优质人才,促进慈善组织的专业化水平及社会工作机构的资源整合能力。其二,服务输送的互嵌,社会工作者及组织可以根据服务需求协助慈善人员及组织设计慈善项目或将慈善项目进行专业服务转化。如李嘉诚基金会2014年的“大爱之行—全国贫困人群社工服务及能力建设项目”正是通过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进行服务转化的。慈善人员及组织可以依托社会工作者及组织挖掘和评估慈善服务需求,设计和创新慈善项目与方案,塑造和提升慈善服务品牌,督导和评估慈善服务过程,训练和管理慈善人员与志愿者等。如近两年来,随着“互联网+”概念的风行,微信圈与微信平台成为社会工作与慈善组织合作的重要路径和平台。时常可以看到,不少个体急病医药费筹款的求助信息是通过专业社会工作者及机构核实与制作,经由“腾讯公益网”“乐捐”“轻松筹”等公益慈善网络平台面向公众和微信用户发布的。再如国际救助儿童会于2014年与民政部建立合作关系后,以项目化运作方式,采用设施捐赠、社会工作者培训等方式积极参与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有效探索了国际慈善组织与中国政府部门在实务上的合作经验。其三,服务理念的互嵌,“扶贫济困”是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共同坚守的服务理念和时代责任。2014年所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不仅更加明确了政府兼有社会救助与救济的主要职责,而且明确了社会工作参与灾害救助、基本生活救助、临时性救助等社会救助的合法身份和基本职责。2015年国家《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同样非常重视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中的关键作用。某种程度上而言,国家已在制度层面将“扶贫济困”视为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共同的使命和职责。如2016年《慈善法》中将“扶贫济困”列为慈善的首要任务。而民政部却将“扶贫济困”列为2016年度我国第十个国际社工日的主题。可见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在核心理念上高度重合,而这种理念上的重合与互嵌关系得到制度性的维系。其四,服务理论的互嵌,慈善事业是基于宗教、道德、情感为基础的施舍和救济活动,具有朴素的自愿性与随意性,具有非常丰富的实务经验和实务理论,而社会工作是基于社会正义与社会福祉使命的专业助人活动,具有严格的专业性与规范性,同时通过外借和内生积累许多专业理论。加强两者理论上的相融互通,既有助于规范慈善人员的职业行为和慈善服务,又有助于防范社会工作的过度专业化与专业服务过程中的专业权威过度使用。从具体实践来看,如爱德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十分注重引进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注重与高校社会工作院系和学者建立课题研究,学术研讨,实务培训等合作关系。既优化了他们内部的组织结构和服务能力,也促进了高校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也提升了社会公众对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的认知和了解。
四、 结语
我国的近现代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发展都与西方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我们也有不容忽视的自身传统和特色。在今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工作体系和慈善事业体系时,应该在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下,考量两者的角色、功能与关系。本文梳理社会工作在西方缘起时与慈善事业的历程和关系,以及我国民国时期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发展的历程与关系,其意图在于引起决策者、研究者和实务者注意审视两者互动发展的历史传统,从而在当下和未来发展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时,注意挖掘两者的内在联系,注意采用更加开放、包容、吸纳、互补的理念来整合利用两者的优势与资源。总而言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也是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的频发期,在当前社会福利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还十分薄弱且难以全面应对社会问题与满足社会需要的情境下,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有着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社会治理与社会润滑功能。因而,珍视两者的亲缘性关系传统,加强构建和整合当下和未来两者的互嵌与互动关系对我国的社会治理、民生建设与社会福利发展都是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维炜.慈善法草案诞生记[J].中国人大,2015(11):26-27.
[2]高德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病”及其初步治理[J].学术研究,2001(1):103-110.
[3]丁建定.英国新济贫法的出现及反新济贫法运动[J].东岳论丛,2011(5):20-25.
[4]MICHAEL E ROSE. The Relief of Poverty,1834—1914[M].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2:17.
[5]郭家宏.工业革命与英国贫困观念的变化[J].史学月刊,2009(7):52-60.
[6]MURRAY P. Poverty and Welfare 1815—1950[M].London:Hodder Murray,2006:75.
[7]HARRIS B.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ocial Welfare in England and Wales , 1800—1945[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65.
[8]YOUNG A F,ASHTON E T. British Social Work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6:69-71.
[9]卢成仁.社会工作的源起与基督教公益慈善—以方法和视角的形成为中心[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2-53.
[10]刘继同.英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结构性特征[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5-15.
[11]王婴.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与启示[J].江苏社会科学,2002(3):48-52.
[12]MCCRONE K. Standish Meacham—Toynbee Hall and Social Reform 1880—1914: The Search for Community[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187-188.
[13]GILCHRIST R,JEFFS T. Settlements,Social change and Community Action:Good Neighbours[M].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2001:19-33.
[14]HAYNES K S. The One Hundred-Year Debate: Social Reform versus Individual Treatment[J].Social Work,1999,15(4):501-509.
[15]刘继同.英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历史、类型与实务模式演变的历史规律[J].社会工作,2013(3):3-30.
[16]侯建州,黄源协.专业主义VS管理主义:英国社会工作历史的检视[J].台湾社会工作学刊,2012(10):1-46.
[17]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M].冯亚丽,叶鹏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15.
[18]何雪松,陈蓓丽.当代西方社会工作的十大发展趋势[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19-24.
[19]孙志丽.民国时期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研究[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2011.
[20]董根明.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轫[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5-20.
[21]王卫平.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及其启示[J].史学月刊,2013(3):16-17.
[22]周秋光,曾桂林.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述论[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6-12.
[23]毕素华.民国时期赈济慈善业运作机制述论[J].江苏社会科学,2003(6):152-157.
[24]朱英.戊戌时期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J].江汉论坛,1999(1):66-69.
[25]周秋光.民国时期社会慈善事业研究自议[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3):103-107.
[26]佟梅依.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J].北京档案,2000(9):36-37.
[27]李湖江.民国初期的佛教组织与慈善思想[J].法音,2015(2):39-43.
[28]卢谋华.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问题[J].理论月刊,1985(1):39-43.
[29]王思斌.雷洁琼的社会工作思想与实践[J].社会工作,2004(9):9-14.
[30]曾桂林.民国时期的慈善法制建设及其经验教训[J].史学月刊,2013(3):16-19.
[31]陈凌.现代各国社会救济[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5-21.
[32]林顺利.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引入和发展的路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34-38.
[33]尚晓援.“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J].中国社会科学,2001(1):113-121.
[34]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需要努力的方向——背景、意识、法制、机制[J].学海,2007(3):62-67.
[35]彭华民.论需要为本的中国社会福利转型的目标定位[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52-60.
[36]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J].社会科学战线,2011(2):206-222.
[37]郑功成.现代慈善事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学海,2005(2):36-43.
[38]陈涛,武琪.慈善与社会工作: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J].学习与实践,2007(3):106-112.
[39]民政部.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5-06-10)[2016-03-10].http:// 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506/201506008324399.shtml.
[40]王勇.第七届(2016)中国社工年会即将召开[EB/OL].(2016-03-11)[2016-03-10].http:// www.gongyishibao.com/html/xinwen/9428.html.
(责任编辑彭何芬)
From Affinity to Embedment: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Wor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y
FENG Yuan
(1.SchoolofManagement,NanjingNormalUniversityofSpecialEducation,Nanjing210038,China;2.DepartmentofSocialWork,TunghaiUniversity,Taichung40704,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social work and charity have been gradually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part in developing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The social work in western countries originated in the English and American charity, and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by missionaries and church organiz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giving birth to localized social work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local charity at that time. Currently, given the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ir relations in policy making, theory studies and practices, it is crucial to review and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relations in affinity between the social work and charity when originated in the West and in China. Either in the present or in the future, their close relations should not be alienated but built into embedment relations in terms of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s. An integration of their strengths and resources is needed for a win-win promotion of building the general social welfare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Social work; Charity; Social welfare system; Embedment; Social governance
收稿日期:2016-02-25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适度普惠社会福利理论与制度研究”(10JZD0033);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生态系统视角下流动儿童权利保护与社会工作干预研究”(13CSH100);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目“抗逆力视域下流浪儿童救助模式创新研究”(2014SJD270)
作者简介:冯元,男,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博士研究生,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社会福利、社会工作、儿童保护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6)03-01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