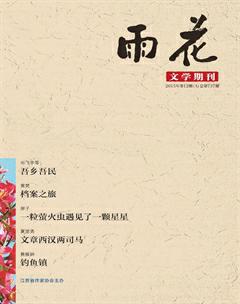在微茫的街灯下
——毕飞宇工作室小说沙龙第三期活动实录
2016-01-18郭亚群
在微茫的街灯下
——毕飞宇工作室小说沙龙第三期活动实录
直到有一天,她的肚子竟然跟“通情达理”旗鼓相当起来。这当然首先得益于鞋匠的努力。同时,家里无处不在的鞋楦也给了艳红破阵杀敌的启示。艳红在肚子上垫了一层棉花。这样的处理让艳红暂时稳住了阵脚。她从容地站在鞋店门口,隆起的肚子像一面骄傲的小鼓。李耳的女人站在报刊亭门口,哗哗地翻着《故事会》,左眼的余光准确地找到了艳红的肚子。隔了片刻,忽然很大声地对报刊亭主人说:“走啦,走啦,我们家李耳炖了鸽子汤,说是下奶。都腻了,吃吐了。”说完,挺着肚子,像个鸭子一样摇摆着走了。
当艳红再不需要借助棉花虚张声势的时候,李耳的女人生了一个女孩。这个消息是报刊亭主人告诉艳红的。报刊亭主人说:“李耳跟我关系不错,平时也照应我的生意,本来是要早点把人情出了的,可是人家生的是个丫头,怎么说呢?还是等通知吧!”听到这个消息,艳红的心里忽然就高兴起来。不管如何,在生孩子这件事上,自己最起码可以保持不败。生个女孩,与她打个平手,如果有幸生个小伙,就大获全胜了。
一个明艳艳的晴天,艳红顺利生下一个儿子。看着那个眉目像极了自己的婴儿,艳红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哺乳期的艳红成了一个骄傲的母亲,她抱着儿子,坐在鞋店的门口晒着太阳。儿子饿了,闹了起来,艳红稍稍避过身将乳头塞进孩子嘴里,孩子不哭了,小嘴一拱一拱,吧嗒吧嗒地吸着乳汁。她看到以往“通情达理”站的地方,蹲着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流浪汉,正专注地看着一张肮脏的广告纸。
艳红已经很少想到李耳了,有一次,她看到李耳戴着一顶绿色的帽子,骑着绿色的自行车。那车已经过时了,就像李耳的面貌一样,结婚之后,早早现出了中年的疲态,很荒凉的样子。艳红的心里空荡荡的,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涌上心头。在生孩子这件事上,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可是她却高兴不起来。相反,她的情绪很低落,有跌入谷底的危险。尽管她相信像“通情达理”这样的女人肯定会卷土重来,可是,她一点也打不起精神了。
(作者 汪夕禄)
庞余亮:毕飞宇工作室小说沙龙活动已是第三期了,活动影响也越来越大。目前有好几个作协先后学习和借鉴了我们的这种模式进行小说研讨,这是小说沙龙的另外一个收获。上次小说沙龙结束的时候说会给大家带来惊喜。今天的惊喜之一就是著名作家、省作协副主席储福金先生的到来。与此同时,还有第二个惊喜,沙龙迎来了慕名而来的无锡朋友,第三个惊喜是泰州青年小说创作方面走在前面的周新天和何雨生的出席;当然还有三次小说沙龙活动都没有缺席过的李风宇老师和毕飞宇老师。李风宇老师特地还为第一期的小说沙龙活动写了一篇文章《接地气的福扣》,又名《微茫的街灯引领》。文学其实就是街灯,现在我们围绕这盏微茫而坚定的灯光,开始小说沙龙的第三次研讨。
这次研讨的题目是《邮差与艳红》,我之所以选择这篇小说是因为这篇小说里面存在着我们兴化小说创作者的另一种缺点。初看这个小说的时候,第一印象特别好,超过了前面两期沙龙讨论过的小说,接着我发现了它的弱点,这弱点也许在我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周新天:这篇小说还是比较成熟的,它有典型的环境、典型的人物。它的不足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题目不准确,艳红与邮差并不能包容整篇小说,其实小说讲了艳红与邮差以及小鞋匠之间的感情纠葛,还有艳红与邮差老婆之间的较量。而且邮差在小说里面并不十分出彩。如果我写的话,题目我就会直接写《艳红》或者《八字桥镇的艳红》;第二点我觉得小说的现代性和传统性不能兼容,比如“李卫军分检邮件就像吃饭,拿起筷子,张开嘴,一划拉,米饭就跟牙齿激烈斗争了。这是一边倒的战争,没有难度,水到渠成,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这种语言是标准的现代语言,这种写法比较独特,本来不该算作毛病,但是后面邮差未婚妻对艳红说:“你不要再找他了,不要脸的事情做多了,你就没脸了。记住,你已经没脸了。”这样的语言让我想起了《红楼梦》《边城》,这样的语言配着八字桥镇的环境倒是挺好。但是文章中有很多现代性的语言,让我觉得不相容。这样的文字会冲淡艳红带给读者的鲜活形象以及水乡古镇带给读者的画面感。如果是我写,我会花几百字写八字桥镇的地理环境,用那样闭塞的环境描写来凸显邮差的地位。
高翔:我是觉得小说名字其实挺好的,它表现了一种张力。结尾艳红生了个儿子但还是很失落,我们可以发现,小说当中的有些人物虽然不在场,但你是能感受到他在场的那种力量的。小说后半段的主角是艳红,前半段邮差出场,这样的题目反而可以让读者拥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作者为什么取这样的名字。但是我觉得按照这样的题目来写的话,小说后半段的张力还不够明显。小说传统现实的语言和现代主义的语言都运用在文本中,会显得有些混杂。但我不认为同一个文本就不能兼容这两种语言,但是我们应该把它打磨得更地道一些,短篇小说每一个字都应该把它打磨得光滑、经典、精确。小说中的语言还有逐字推敲的余地,比如“李卫军分检邮件就像吃饭,拿起筷子,张开嘴,一划拉,米饭就跟牙齿激烈斗争了。这是一边倒的战争,没有难度,水到渠成,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一个没有难度、没有技术含量、一边倒的战争怎么能说是激烈呢?还有,一些现实主义的有些琐碎的语言是否让它更有意味一些?就如前面的环境描写是不是能和主人公产生某种联系。另外,如何把现代的语言和现实的语言结合起来?小说里面的两种语言太近了会有点出戏,就如本来含情脉脉的语言忽然来了很戏谑的语言,我们就会觉得不搭。
庞余亮:这篇小说开头很不好,可以有多种方式,唯独不可以这样开头,小说很多出彩的地方被作者忽视掉了,不出彩的地方反而被作者反复在写。比如小说就应该从艳红的鞋子开始,白色的塑料凉鞋,中间是红色的皮鞋,到最后生了孩子之后的鞋子又有变化,有一条这样的线就会相当好了。小说中还有很多的毛病,比如说一开始说邮包很轻,后来又说李卫军在拖邮包,甚至邮包的颜色后来也变掉了。这说明作者写作时是非常粗心的。
易康:我觉得小说的故事没有讲出来,人物也没有立起来。就感觉一个人在巷口徘徊,我们期待他走过来说些什么时,他却走开了,然后走到另一个巷口,又走开,如此循环。另外他冗杂的描述冲淡了故事,特别是后半段,我觉得小说的很多部分是可以删去的。前面六段可以打散了渗入到小说的其他部分。我觉得舅舅这个人物完全就可以把他删掉。写小说就像陈列一个货架,在货架里我们可以塞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首先要把架子给搭好。如果我写,我会在“艳红从水泥板上跳了下来,一只手拦住李卫军,一只手死劲地摁着车铃,‘当当’的铃声快速地响了起来”这里开头。小说还有个问题就是叙述的顺序上,我觉得可以按照时间的顺序分成三个板块:第一个艳红与邮差修成正果的过程,第二个详写李卫军的婚事略写艳红的婚事,第三个就是艳红与邮差妻子的暗斗。但是最后我觉得邮差还是需要出现一下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围绕售报亭来写故事。一两个女人的对峙开始,把之前的故事穿插在其中,最后以邮差妻子的退出结束。我想说一些关于阅读与写作的关系,毕先生说“写作是阅读的儿子”,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处理好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不光要进入名著还要从名著中出来。
庞余亮:我倒觉得舅舅这个人物不可以删,艳红其实并不是游离于两个男人之间而是三个男人之间,包括舅舅。这里面应该是有故事的,艳红在舅舅那里是有话语权的,如果把这个处理好,应该会是一个有深度的好小说。
沈光宇:我觉得小说的背景有点乱,前面绿色的自行车、李卫军这个名字等是带有很浓郁的文革色彩的。后面艳红穿红色的鞋子抹鲜艳的口红又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事情。背景的跨度太大,由此带来,艳红为什么就和邮差干柴烈火,后面为什么就破罐子破摔嫁了个武大郎。邮差与艳红之间的故事应该具有合理性,比如可以说艳红和在北京当兵的铁道兵有书信往来,通过邮差传递,后来铁道兵落户北京了,就抛弃她了。后来邮差不要她了,她就想着能够到小城镇上,就嫁给了鞋匠,这样就有合理的理由。
刘春龙:刚刚说到舅舅这个人物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删去的。校长40岁没有找对象,性格或者说人格肯定是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小学的校长去和小鞋匠说亲,他的身份还是可以的,而小鞋匠地位是很低的,这个性格的转变有点不真实。另外依着艳红泼辣的性格,完全不需要舅舅去说亲,可以自己直接跟小鞋匠说要嫁给他。看这篇小说的感觉,一开始的确有点意思,心里有些期待,越到后面越替作者觉得惋惜,觉得一个好的故事他没有写好。从一些细节上看这个故事可能是个真实的故事,但是故事和小说是有区别的。故事推进的合理性,人物塑造的真实性,谋篇布局的技巧性可能都需要努力一下。
庞余亮:其实我觉得作者打造他心目中的小镇,各个时代的特征糅杂在一起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逻辑性的缺失。邮差、艳红、鞋匠的内心都是有问题的。刚刚易康老师讲到的在巷口徘徊的问题,我是觉得小说中很多地方是可以出戏的,可惜都没有出戏。比如一开始邮差与艳红一次次见面最后滚在了一起,没有展开;第二个胖女人来找艳红的时候没有展开;第三个胖姑娘和邮差举行婚礼的时候没有展开;第四个艳红不死心要嫁给鞋匠,这个心理过程是逻辑性的推动,也应该展开;第五个艳红从鞋匠那把鞋子取走的时候应该是有戏的,可以留下一个铺垫;还有结婚时的那双红皮鞋是个非常出戏的地方,也忽略了。另外我还是觉得舅舅这个人物应该保留,因为这样才有迂回,不然整个故事太平庸了,没有延展性。小说的最后李卫军、艳红等所有人物都还在镇上,那就还有发生其他故事的可能性,小说要保持这个可能性,才有味道。
何雨生:如果我写,我会在舅舅这个人物上多一些笔墨,写他们三个男人与艳红的故事,因为舅舅是个光棍,可能对自己的外甥女也产生了一些好感,这个好感又让舅舅感到后怕,可能这样故事会更有意思。
董景云:我觉得题目可以就直接用艳红两个字。如果我开头也是从第七段开头。我觉得小说里的几个人物都很不负责,邮差不负责,自己有未婚妻还和艳红在一起;舅舅不负责,怎么就舍得把自己那么漂亮的外甥女嫁给一个残疾人?艳红对自己也不负责,怎么就破罐子破摔了呢?另外几个人物也太冷静了,邮差冷静,艳红那么美,勾引了他几次才动心;胖女人面对未婚夫被抢走后的表现太冷静;艳红明明追到自己的心上人,最后她又退让了,也太冷静,这些应该有东西的地方都没有展开。还有艳红和邮差第一次滚在一起应该展开,应该有动作和心理的描写。情节的推动需要一股力量,要炫势。比如说艳红在将请帖给李卫军的时候应该有一段描写,如何邀请的,最后李卫军没有来,艳红的心理活动都应该有一些笔墨
高翔:这个地方作者用了一个词“干柴烈火”,这个词语太俗气,包括形容鞋匠的漂亮,还说鞋子洋气得不行,这些词语都不应该出现。
庞余亮:这就说明小说的作者很懒惰,小说里面千万不能随意,一篇小说一万字,你随意一个词,就最起码减掉5分。
毕飞宇:我同意刚才的这个观点,小说写得不太负责任。小说的情节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写两个女人的斗法,她们为什么斗法,好多人提出了质疑。胖女人和李卫军结婚的时候,文章中写道:“李卫军和姑娘结婚,艳红并没有那么伤心,她清楚自己的劣势,也清楚对方的优势。艳红伤心的是李卫军的转变太迅速太彻底了。”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艳红未来拧巴和纠结的那个点不应该在胖女人身上,而应该是在李卫军的身上。这是一个点。第二点她为什么要嫁给鞋匠,我们沿着刚才说的李卫军结婚时艳红的心理状态,其实作者已经为艳红嫁给鞋匠铺垫了一个逻辑了。但是因为他不负责任,他铺好的路他没走,却走了其他的路。这个地方小说已经到门口了,他没有进去。小说中最不合理的地方,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处理得非常合理,不仅仅合理,而且可以非常精彩。比方说,艳红心里想:“老娘我这辈子不要了,你不是和我做过爱吗?你不是跟我做爱的时候对我的身体显示出无限的热情吗?好,我糟践它。”这样这个地方就会变得非常漂亮,人性的深度也就往下走了,但是作者都不要了。所以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不负责任。第三点,我特别奇怪,艳红已经通过舅舅的说媒嫁给了鞋匠,但是整篇小说里看不到半点艳红对于鞋匠的感受——好或不好,什么都没有。如果她就是为了恶心李卫军,她嫁给了一个一无是处唯独有一张漂亮脸蛋的鞋匠,小孩生出来不管男女,有了一张漂亮的脸蛋。当艳红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孩子非常漂亮的时候,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出现了:这个孩子的漂亮让这个母亲感到非常自豪,可是这个小孩的脸像谁,又让她非常地恶心。所以本来不合理的东西其实完全是可以往下走的,问题是你怎么做。我记得之前就说过,小说中不存在合理不合理,所有的合理要靠作家去赋予。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写得慢,你写过的句子,留的每一个点,脑子里都要记住,然后小说的人物、性格、情节往下推的时候,它跟前面都是有关系的,这叫才华,这还叫责任心。你一边写一边忘,本来写的艳红是对男人不满意,写到最后跑到女人那去了,跟男人都没关系了,这太拧巴了。
顾开华:我觉得小说里面的心理描写太少,小说能否打动人,不是作者写出来,而是让读者读出来的。
毕飞宇:任何一个小说最重要的首先是成立,现代主义小说理念要成立,古典主义或写实主义小说故事要成立,还有一种所谓的风味小说语言要成立。这个小说的语言确实不错,但是他把故事弄成这样,还不如不要这个语言呢。在这个小说里,语言妨碍了故事。就如一个种地的大爷,到了70岁满嘴没有一颗牙,背是驼的,身高只有160,你一定要给他一件燕尾服,还不如不给。因为故事不成立,所以语言也不成立,他的语言相对这个小说来讲好得不配套了。鞋匠为什么有女人喜欢他?我们换个思维,就因他一个特殊的职业,每天身边围着一群女人,他成为了一个女人心理大全,他说话能够搔到女人心里痒痒的这样一个男人。其实这个小说中一些零碎的点特别好。比如艳红去按自行车的铃铛。艳红未必爱这个鞋匠,但是这个鞋匠就是能打动他。比如一个点,艳红拿鞋过来,鞋匠斜着眼睛看了艳红的脚,转身拿了个鞋楦子往鞋子里一钉。艳红说你把我的鞋弄大了,鞋匠说,鞋子要大一点,你看你大拇脚指那都磨出个老茧了,多难看啊。他一定要搔到女人的痒处,小说就合理了。没有天然的合理性,合理性一定是作家赋予的。李卫军和别的女人结婚了,她去小鞋匠那挑逗他,每一次挑逗小鞋匠都能应对自如。艳红心想,这个男人不错啊。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问自己是不是喜欢她,事情已经办了。而小说里艳红和小鞋匠的关系并没有出现。小说最重要的两点一个是人物,一个是关系,某种意义上讲关系比人物更重要。
董景云:我觉得艳红在与小鞋匠结婚的那天,没有等到李卫军很失望,然后和小鞋匠在新房里应该有一段描写。
王锐:我写小说经常会到达一个点就展不开,不是不想负责任,而是没有这个能力负责任。
毕飞宇:我写小说的一个体会,这个小说9000字,顺利的话,我两天就可以写完,不顺利的话,可能要写一年。比如《家事》《相爱的日子》。如果到了某个点,走不过去,怎么办,四个字“设身处地”,你就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一方,你跟他过日子,你一定能找到,问题是你是否舍得这个时间。不是能力不够,而是耐心不够。
高翔:我觉得小说的结尾到“可是她却高兴不起来”就已经很饱满了。后面的不需要。作者用了中篇小说的手法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很多叙述有些累赘了。短篇小说中,一个字的多余都会影响到其他东西的交代。一个不成熟的小说,越是有更多合理性的处理方法。
庞余亮:小说沙龙的目的是慢慢在欠缺的体系中完善起来,要建立起自己的知识构架和小说构架。我们汲取每一个发言中精彩的部分来弥补我们小说写作中的弱点。
毕飞宇:我觉得舅舅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如果有,应该是来拆台的,这样艳红还能做出很多戏来。比如舅舅说,你看他又不行。艳红回他,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啊。一句话能把他噎死。我们写小说的时候还要注意语言的速度,一个字都不能多,利索、麻利。
李风宇:小说沙龙的活动对我们的选稿用稿也提供了很多的借鉴。现在我们的读者俱乐部有40多家,这一次我将讨论稿发给俱乐部,大家都进行了探讨。小说的语言很好,情节设置上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是一篇有韵味的短篇小说,其韵味充分体现在小说的语言和故事结尾上,作者更善于做情景细节的铺陈与刻画,但细节超过了情节,感觉比例失调,有些拖沓,柔性足,刚性少,有些情节韵味不足,趣味不够,不够饱满。”
储福金:我参加过很多次的作品研讨会,大多数都是讲好话,而今天听到的都是提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模式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其实每个人的作品都有长处短处,我们提出这些短处能够便于作者修改。意见多了,作者也可能会无所适从。有的意见是可以修改的,有的变动了他的构思就不太好办。创作的功力是需要耐心与磨练的,功力还不仅仅是写作方面的,还有可能是对生活的感受程度没有达到,没有生活,就没有办法很生动地把它表现出来。才华很重要,生活也很重要。功力还包括想象的能力。写诗歌的时候要有诗眼,写小说的时候同样要有这样的点。有了这个点,就要花功夫,花耐心。说到合理性,其实生活中的真实性和艺术中的真实性不是一回事,小说是自己造了一个天地,只要在自己造的艺术天地里合理就行了。好的作品中要有形而上的东西,文本的背后要有一些东西,不一定就是哲学的,也可以是情感的丰富性,人物的深刻性。文章的结尾大家都说不错,就是因为这样的结尾背后有一点形而上的东西,但是这样的结尾应该要与整个文本的结构结合起来,让这点味道显得更浓郁一些。
庞余亮:小说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能否射到靶心,第二个就是箭射出去能不能虚空。这两个方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很难达到的,但是我们既然爱上了文学爱上了写作,我们就向这个目标走。每个人写作的嗓音是不可能变的,但是尽量把它修得完善一点,把自己的气息调整得更均匀一些,怎样把自己的力量送到自己的嗓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最近的《文学报》采访张承志,有一句话非常好,“紧握手中的笔”,希望我们作者手中的笔握得更紧,写得更有力。
(整理:郭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