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育效果差
2016-01-15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文 / 李 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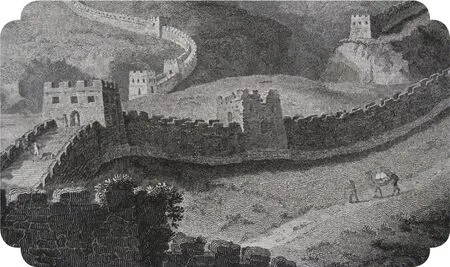
在传承和发展人类文明方面,历史教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往往是由家庭、社会、学校(如村塾、社学、书院等)共同承担。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末民初以来,随着效仿西方的新学制的出现与逐渐完善,各级各类学校更多地在历史教育中唱起了主角,换句话说,历史教育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学校的课程上。
本文选取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先后数次颁布的《历史课程标准》,通过分析它的基本内容与要求,折射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育的嬗变历程,展现当时基础历史教育的面貌。
一
中国新式学制的建立,始于1903年,即癸卯学制的施行。清廷在这一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中学五个年级均开设历史课,并对讲授内容和次序都提出了较具体的要求。从此,中国的学校历史教育走上了近代的轨道。
1912年初,民国刚一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便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明确以“课程标准”作为教育的指导性文件。从此,“课程标准”一词沿用了四十年(时而也用“课程纲要”一词),直至1953年学习苏联做法着手制订《教学大纲》为止。
就历史教育而言,尽管有了“课程标准”,但因民国初创,百废待兴,还来不及细细规划,所以大的方面基本沿袭了清末的《学堂章程》,未做根本性的变革。而且民国初年的历史教科书也未更张,基本是对清末所编教科书略加修订而用之。当然,也非所有东西皆一成不变,课程目标上便有所差异。不过总体而言,民初的中学历史教育还未形成自己的特色。
民国时期的中学历史教育真正走上自己的轨道是在1922年学制改革之后。在1919年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教育界出现一股学习西方教育的热潮,学习的重心,也从日本转向美国。这一转变,基于多方面因素,最关键的是,在新文化运动反对专制、培养共和国民的思想氛围下,中国知识分子更倾向于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为主体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教育。与强调纪律、服从和无条件忠诚的日本教育相比,美国教育更具备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精神,而且以美国方式为主的多层次、多系统、多渠道办学的灵活的学校制度,也更适合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多种需要。所以,经过教育界和社会各界较充分的讨论与论证,以及美国教育家孟禄等人的参与推动,1922年北京政府颁布施行了新学制——壬戌学制。
为适应这一变化,中学历史教育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从以往注重历史知识全面性和系统性的通史教学,转为关注人类生活状况变迁和文化演进的专史教学。此时,中学历史课程的设置完全遵循学制改革的精神,一方面向注重教育实用性的美式课程靠拢,另一方面则力求有所创新,打破清末以来历史课中外分编、通史讲授的固有格局。
1922年学制改革前后,正是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白话文开始深入人心,这也带动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更新。此前的历史教科书皆为文言,如清末时使用的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等。民国初建时也仍采用,基本没有大的变化。直到量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吕思勉所编《自修适用本国史》,才开启白话文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先河。1923年,傅运森按照北京政府新颁布的《课程纲要》,编写出将中外历史合为一体的教材,该书打破“朝代”“国界”的旧习,“从人类文化上讲述变迁的情形”,推进了中学历史教育的发展。
盈利企业净利润通常为正值,当扣除投入资本成本后,EVA结果为正,表明企业价值持续增加;而EVA结果为负,则表明企业价值被损毁。
1922年的学制改革,是北京政府在教育上的重大举措,大体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从而使民国学制基本定型,但同时亦存在某些缺陷,所以才有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所做的调整。
二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学校系统方面承袭了1922年新学制的规定。1928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重新制定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相应地,中学历史课程随后也做了调整。
与1922年的新学制相较,南京国民政府此次颁布的《中华民国学校系统》可谓萧规曹随,只是局部微调。不仅如此,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部陆续订立的各级学校组织法及学制系统,也是在1922年学制大框架不动的前提下,对其具体实施做一些变通而已。
1929年,南京政府教育部宣布废除高级中学普通科文理分组办法。1932年又颁布《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学校法》,将三种不同类别的中等学校分别单独设立,在普通中学初中、高中两段全部取消学分制,实行学时制,在高中阶段取消选修课,加强基础课。此后,教育部又对中学学制有过几次局部修改。可以说,中学学制在1930年代已大体稳定下来。
学制的调整与改变,必然带来各科课程的变化。所以,自1929年起,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曾几经修订,以适应学制的更新和时代的需求。
1929年,教育部颁布了《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普通科外国史暂行课程标准》,以回应1928年《中华民国学校系统》的有关新规定和1929年废除高级中学普通科文理分组的决定。与北京政府1923年颁布的量《课程纲要》相比,此次颁布的《暂行课程标准》有相当大的变动,某种程度上是向清末民初课程设置的回归,即仍要求学生系统地学习中外通史,只是在课程编排上加大了学习强度。
以往是在五年或四年的中学学段内,本着先中后外的原则,直线式学完中外通史;此次则是循环式设课,初中阶段先学习一遍中外通史,高中阶段再深入系统学习一遍,以此强化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这样做,自然是与南京政府提高教育效果和学科标准的办学原则相吻合。不仅如此,在课程目标上也有了更全面的规定,如初中阶段的目标共有七条,涵盖了让学生了解中外历史上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科学等方面变迁概况的基本要求,以及在了解史实基础上激励学生进步向上的基本目的,尤其强调:“研求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概况,说明近世中国民族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以激发学生的民族精神,并唤醒其在中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研求重要各国政治经济变迁的概况,说明今日国际形势的由来,以培植学生国际的常识,并养成其远大的眼光与适当的国际同情心。但同时仍注重国际现势下的中国地位,使学生不以高远的理想,而忽忘中国民族自振自卫的必要。”高中阶段的课程目标共有十条,对学生基本知识的掌握、历史意识的培养等方方面面,在初中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需了解“民族的分合,政治制度的沿革,民生经济的利病”,“养成‘无征不信’的态度,随时提出历史上未解决或可疑的问题,讨论其真伪或其影响,以培养学生自由研究的习惯”。与1923年的《课程纲要》相较,这一课程目标要全面、宽泛得多,既有当年那种注重教育实用性的色彩,又增加了大量新的对学生基本知识、基本理念、基本能力的要求,符合历史学科的特性,是一个进步。
1932年,伴随着《中学法》等教育法令的施行,教育部颁布了正式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这两个“标准”是对1929年的《暂行课程标准》予以修订后颁布的,其中高级中学部分是把原有的本国史课程标准和外国史课程标准做了合并。与暂行标准相比,这个正式标准并无根本性的变化,只是相对有所简化。
1932年之后,教育部又对各科课程标准做了几次修订。首先是1936年再颁《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这两个“标准”与1932年的量“标准”几乎完全一致,仅在个别字句和极微小的内容上有调整。接着,1940年又出台《修正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修正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这两个“标准”是在抗日战争的危亡时期颁布的,所以带有浓重的战时色彩,如在初中增加了一些“抗战建国”的内容。1948年,教育部对《历史课程标准》再度修订,颁布《修订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修订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
纵观1929年以来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的几番修订与颁布情况,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
府时期的中学历史教育,在课程编排、课程内容、课程目标等方面均有不同于北洋时期的独到之处,各个阶段里也有些各自的特色,但奠基性的课程标准,还应属1929年公布的三个量《暂行课程标准》,后来的几个“标准”皆是对其进一步完善。也就是说,1929年的量《暂行课程标准》确立了中学历史课程的基本原则,后来者只是对此原则修修补补。
三
从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的《历史课程标准》的几经修订,带来中学历史教育的几度嬗变。就课程内容而言,是从通史到专史再到通史,表面上看似乎画了个圆圈,实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内中所涉及的知识体系、知识要素和知识点,都伴随时代的前进和学术研究的进展,出现一系列变化;就课程目标而言,除了基本的对知识、能力方面的要求外,每个时期还结合时代特色做出了特殊要求,尽管这些要求大都流于泛泛而谈,但在某些时候,如抗战时期课程目标对“抗战建国”的强调,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所以,无论北京政府,还是南京政府,所颁布的《历史课程标准》,若从总体内容上考察,皆是值得肯定的。
问题在于《历史课程标准》实施的效果如何,即中学历史教育在民国年间的教育成效怎样,这恐怕是更值得关注的方面。量有一个事实大概是人所共知的,即中学生的数量在民国时期一直不多,如在校生人数最多的1946年,全国中学生共1495874人,仅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千分之三。对于普通教育而言,教育对象如此稀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如此低下,量自然无形中限制了其功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具体到历史教育的效果问题,也必须把这一事实作为前提和出发点来谈。
应该说,从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在《历史课程标准》的编订、实施等各个环节上大都是认真负责的,常乃德、何炳松等专家学者也为此付出了极大心力,使历史课程日趋完善。不过教育毕竟不是纸上谈兵,它是要在实践中取得成效的。教育对象的稀少,已使历史教育的功能打了折扣,而教学效果的不理想,更表明《历史课程标准》在具体实施中是不成功的。
1924年,章太炎在《救学弊论》中说:“近在上海闻有中学教员问其弟子者,初云孟子何代人,答言汉人,或言唐宋明清人者殆半。”1934年,吴晗发表《中学历史教育》一文,对当年大学入学考试的4000份中国史试卷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这些试卷没有一份是完全正确的,及格以上的大约只有四分之一,“题目全部是极简易的常识测验”,但考生能答出“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哪一年的不到一半,尽管离事变发生还不到三年;二十四史能说出八种的也不到一半。所以他感觉到“具有本国通俗历史常识的高中毕业生寥寥可数”,并由此慨叹“中学历史教学的失败”。1948年,李洁非发表《现阶段的历史教育》一文,指出:“抗战以来,转徙流离之余,师未安教、士不悦学的结果,历史教育虽不时被强调着,可是匪但不见有所改进,抑更有江河日下的趋势。作者近被邀阅浙省普通考试历史试卷,其中能辨朱陆异同者,百不得一二,二程且多指为程潜量……毫无历史知识者,比比皆是。”从这三篇先后发表在20、30、40年代的文章所反映出的情况看,中学历史教育的效果显然不佳,无论是北京政府时期,还是南京政府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