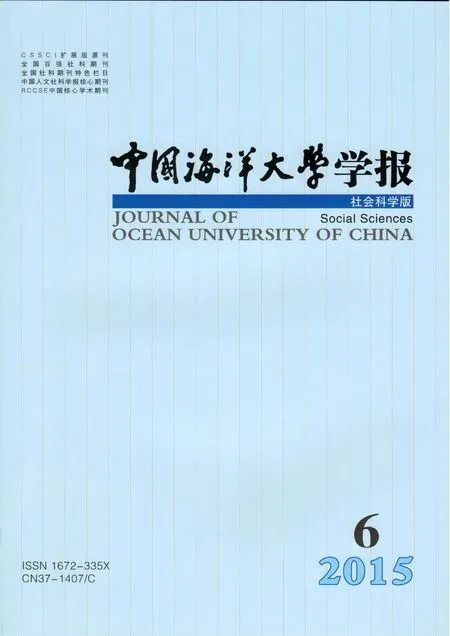清代朝贡贸易中的贡使身份问题探析——以18世纪初苏禄国贡使案为例
2016-01-15吕俊昌
清代朝贡贸易中的贡使身份问题探析
——以18世纪初苏禄国贡使案为例*
吕俊昌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从鱼贩、水手到通事、贡使,福建人马光明往来于苏禄与中国之间。朝贡贸易中华人贡使的身份是否成为“问题”取决于是否发生不法行为,马光明一案反映了华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与朝贡贸易的关系,也集中展示了清帝国在执行海洋政策中的偏差,以及对内与对外造成的差异。东南海域流动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以及所谓“朝贡体制”下的特殊秩序,促使了华人与贡使之间身份的“流动”与转化。
关键词:苏禄;贡使身份;清代海洋政策;朝贡贸易
收稿日期:2015-06-11
作者简介:吕俊昌(1986-),男,山东莱芜人,厦门大学南洋学院博士研究生, 专业方向为中外关系史和海洋史。
中图分类号:K901.6文献标识码:A
在明清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朝贡贸易始终是无法绕开的话题。而其中来华贡使身份问题学界已有关注,但是主要集中于明代*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19页;陈学霖:《记明代外番入贡中国之华籍使事》,《大陆杂志》卷24,第4期,1962年;陈尚胜:《"夷官"与"逃民":明朝对海外国家华人使节的反应》,《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55-575页。,清代还未有专文研究。因此本文以18世纪初南洋岛国苏禄(今属菲律宾)与清朝之间发生的一起朝贡案件为例,探讨贡使身份问题以及事件背后的社会历史机制,并对中国东南海域的社会秩序略陈己见,以求教于大方。
一、案件始末
目前已有的关于苏禄与中国关系史的研究基本都与朝贡贸易有关,其中或多或少地提到马光明充当贡使诈骗的案例。*钱江:《清代中国与苏禄的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88年第1期;高伟浓:《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3页;余定邦:《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3-296页;夏春江编:《苏禄王和苏禄王墓》,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4页;郗玲芝:《清代苏禄国朝贡史研究》,《德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苏禄国,位于菲律宾群岛南部,信奉伊斯兰教,它与中国官方的关系在苏禄国王亲自来华朝贡,病逝于德州,被明王朝厚葬之后就渐渐销声匿迹。直到康熙十三年(1674)苏禄苏丹遣使受封,朝贡贸易才再度复兴,[1]但是直到雍正四年(1726)冬才确定了每五年一贡的贡期。并规定届时苏禄国可派遣正、副贡使各1员,通事1名等,从福建厦门入贡。[2](卷39,P372)
乾隆五年(1740)九月,苏禄苏丹派遣鸟人皆色爹(人名)与汉人火长(又名伙长,掌观指南针盘及船中更漏,辨认针路)马灿等将遭海难的福建晋江、海澄县商船送回内地,并奏请朝贡。[3](P119-124)在得到允许朝贡的请求后,乾隆七年(1742)九月二十日,苏禄贡使劳独喊敏、甲必丹马光明等赍送本国方物附搭黄万金洋船进入厦门。经厦门口岸的文武官员查验、造册通报后,福建督抚遴选专员伴送使团至京。在京期间,苏禄使团收到了极高的礼遇。天气炎热,乾隆皇帝还特意嘱咐礼部派官员加意照看,多给冰水及解暑药物。[4](P197)六月,在正大光明殿接见了苏禄贡使。[5](P173)
然而乾隆十一年(1746)八月十三日,苏禄贡使送来的“谢恩表文”中称,乾隆九年(1744)马光明一行回国途中遭遇风暴,船只漂至邦仔丝兰(即今菲律宾吕宋岛中西部Pangasinan省)时被吕宋(即西属菲律宾)一方扣留,诏书及所赐之物被损毁。通事陈朝盛更加指出马光明等人财物被名为黄占的“番目”劫掠,参与其事的黄占胞弟黄令、黄罕已回厦门,请求福建地方当局提讯。福州知府听后,立即传集相关人等逐一究讯:关于“吕宋番目”黄占是否参与搬抢、扣留银物之事,马光明、陈朝盛、武厨安力、马金成4人言之凿凿。至于黄令、黄罕是否皆在抢夺现场,武厨安力和马金成予以否认,马光明和陈朝盛却又称“只见黄令,未见黄罕”;被告黄令、黄罕则供称,两人出生在福建,其兄黄占是父亲黄紫在吕宋所生,并在吕宋生活,从未回家。黄罕从未出洋贸易,黄令只往天津贸易,从未到吕宋。而且当年八月陈朝盛曾让陈梧等以黄占搬抢之事索诈,未遂,方加仇害。陈朝盛则辩解是黄令畏罪,托陈梧请求照应。[3](P137)
显然黄罕并未参与劫掠,而黄令也声明从未到过菲律宾,并极力撇清自己与同胞兄长的关系,所谓劫掠之事即使发生也只与生活在菲律宾的黄占有关,根本与己无关,马光明等此举纯属诬赖。……与此同时,在纠纷之外,福建当局也发现苏禄国的朝贡表文存在问题。顺治元年清廷规定“外国朝贡以表及方物为凭,该督抚查验的实,方准具题入贡。”[6](卷503,P39)然而苏禄此次遣使赍送谢恩表文中只有使臣,并无方物。再者,按照雍正九年(1731)南掌国(老挝)的先例,苏禄只需呈递苏禄文的表文,到中国后“率由督抚令通事译录具题”,[6](卷514,P175)但是这次苏禄国却早已备好汉文、番文两种版本。更让人起疑的是来自苏禄之人竟不认识表文内“番文”。谨慎的福建巡抚保守起见,便以“种种不合,不宜具题”为由令苏禄贡使将表文带回。
实际上从福建石浔司巡检处查知,马光明、陈朝盛本就是内地人,前者即乾隆五年(1740)时送船户蔡长发等遇难船只回国的马灿;通事陈朝盛原名陈荣,也是内地人。[3](P138-139)黄令的确只是在乾隆七年(1742)、九年(1744)往返天津。最后,厦门海防同知与同安知县的调查结果,揭开了马光明的庐山真面目[3](P141):
马灿,原挑卖小鱼营生,后充船稍,在吕宋逋欠番商之债,又充洋船大缭往来苏禄,苏禄番人皆称为‘马大缭’,又负欠厦门行账千余金,控审有案,马光明负欠无偿,遂在苏禄夤充贡使,来至内地不特可以避债兼得择殷索诈。至吕宋之法,凡有逋欠番商之债,即著番目赔偿,黄占系吕宋甲必丹,马光明所逋曾累黄占代赔,迨至乾隆九年内苏禄贡船回国阻风湾泊吕宋所辖邦仔丝兰地方,马光明在船演唱番戏作乐,黄占闻知回明吕宋国王,将船押入大港扣留,货物抵还宿逋。此搬抢一事之原委。*首先,吕宋并无国王,这里是指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其次,关于"吕宋甲必丹"问题。西班牙殖民者统治菲律宾期间,在华人社区设立监督(Governor)一职,由华人担任。负责对华人家庭或生意的纠纷进行初审,然后上报西班牙人长官(Alcalde-mayor)。黄占对马光明财物的扣留也体现了甲必丹处理商业纠纷的职责。学界一般认为甲必丹制设立于19世纪初,实际上从该案来看,甲必丹早在19世纪之前即存在,也可以说甲必丹不过是监督制的进一步延伸而已。相关研究参见Alfonso Felix Jr.,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1570-1770,Vol 1.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66,p.83;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ed.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 Ohio, Cleveland: Arthur H. Clark Company.1903-1909,Vol.16.p.197;Vol.36, p.205.
三个月后,福建按察使禀告巡抚陈大受,“缘马光明系内地同安县民,自幼卖鱼为业,后充洋船水手,往来吕宋,倚恃外番名目赊取厦门行保李鼎丰、郑宁远、林琅观等货物银九百两,尽行侵吞,迨李鼎丰等控追,光明狡骗不偿,复往吕宋又骗用番商货本,于乾隆四年间逃往苏禄,营求国王之弟收为通事。”[3](P143)
乾隆九年(1744)二月马光明在从福建回苏禄之际,还收养了一个义子马成带在身边,并在到达邦仔丝兰时将义子当作礼物送给了“吕宋国王之弟”,原想借此弥补其在吕宋的债务,然而黄占对此并不知情,于是马光明一行的财物仍落入黄占之手。马光明对黄占怀恨在心,便捏造黄占在漳州的兄弟黄令、黄罕等参与搬抢事宜,并将之告知苏禄国王,凭借苏禄国书以及贡使身份,马光明等便开始了“索诈”的活动,陈朝盛也亦步亦趋。陈梧则借着“番王世子”的身份,恐吓他人,并将“番人”所带置货银300两花费殆尽,无奈之际,唆使“番目”假称与洋行邱诗观等赌博输掉,逼迫洋行“屈认代赔”。[3](P141-144)而马光明的罪行还不止一桩:据称乾隆七年(1742),劳独喊敏与马光明进京朝贡路过浙江,在浙江巡抚那里曾状告宁波人邵士奇欠苏禄3000多两银子,浙江巡抚立时追缴给他,甚至是先从司库程费银中动支银两。[3](P129)针对马光明的种种不法行为,巡抚陈大受量刑奏道:
马光明、陈梧、陈朝盛……私越外番,献媚结营,充贡使、通事,复往来苏禄、吕宋两国,藉端构衅,且先后回至内地假借番国名目,三人狼狈为奸,择殷而噬、诈骗商民,讦讼扰累,动以国王咨奏恐吓,凡闻其名者无不震惧,子弟仆从,横行乡曲,种种不法,诚属奸徒之尤,实难轻纵。查例载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诓骗引见,惹边衅,贻患地方者,问发边远充军等语。马光明、陈梧俱应照例边远充军,各佥妻发遣,陈朝盛附和为从,照例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徇不为枉。各名下所欠洋行番人银两著追给主,仍咨提马成回籍,同伊等家属一体严加管束,不许出境。[3](P144)
再后来经黄令、黄罕以及房族人等证实,黄占实为已故之父黄紫的继妻在内地所生之子,在吕宋居住多年未回。面对马光明借苏禄声势“百端吓诈”,黄令为免得拖累,才供为吕宋所生,后来见马光明罪行暴露,这才将实情吐露。[3](P156,159)
二、苏禄与清朝的关系及华人的角色
马光明固然借所谓“外番名目”借债,但是他能先后从福建和菲律宾商人(实际主要是华人)等多处借债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时华商之间借贷关系的普遍性和可接受度。已有学者在探讨海外华商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中经常提到华人信用与虚拟亲属关系对华商贸易成长的重要性,[7]马光明收养义子就是建立虚拟的亲属关系的体现,而这也是历史上闽南地区比较盛行的拓展海外贸易的方式之一。“闽人多养子,即有子者,亦必抱养数子,长则令其贩洋赚钱者。”[8](卷15,P327)在该案中义子马成甚至被送给菲律宾国王之弟,作为弥补债务的交易,表明身为华人的马光明也想要缓和与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是马光明等人的行径破坏了华商之间的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与此同时,原本是华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因为朝贡贸易演变为“国际”官司。对比中外交往中的战争、贸易等宏大叙事,马光明一案可能微不足道,但是细细梳理,管中窥豹,仍然存在值得思考的价值。
对于朝贡制度本身,学界已多有探讨,但从朝贡国方面来说无非是为了政治或经济利益。苏禄方面对该案件并没有相关记载,因此学者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苏禄之间关系史的研究都是借助中文史料。[9](P150-152)马光明一案背后反映出苏禄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双方各自试图借助外力巩固自身地位的尝试。西班牙殖民者虽然从16世纪开始就征服了菲律宾群岛的大部,但是唯独难以攻克南部穆斯林统治的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等地区,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将这些地区的穆斯林称为“摩尔人”,双方引发的冲突——即摩洛战争——延续整个西属菲律宾时期(1521-1898),直到当下都是菲律宾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过也不能将宗教冲突对双方战争的影响绝对化,相关研究表明至少在19世纪后期以前,穆斯林政权经常奉行世俗的实用主义策略,[10](P237-248)统治者会根据内、外局势做出权衡。1737年,苏禄新任苏丹阿里木丁(Alimud Din)一世上台之初削弱地方拿督(Datu)权力的举动引起了后者的反弹,为了巩固其政权,阿里木丁一世便采取亲西班牙政策,在1744年允许耶稣会在苏禄传播天主教,建立教堂以及西班牙人的堡垒。阿里木丁一世此举引发传统穆斯林势力的反对,1749年其兄弟班第兰(Bantilan)夺取苏丹之位,高举伊斯兰旗帜,悬赏阿里木丁人头,迫使阿里木丁一世逃至马尼拉,在那里他受到西班牙殖民者的欢迎。[11](P315-316)
与此同时,原穆斯林派也寄希望于清朝,试图通过清朝的认可和贸易增强其权威和财富,扩大在这个政治分裂的地区的影响力。[12](P5)案件中提到黄占曾向菲律宾总督(吕宋国王)报告马光明的行踪,可知西班牙一方也清楚苏禄的意图,所以可能才授意黄占拦截马光明一行,打破苏禄与清朝的联系。事实上早在雍正末年(1735)第二次朝贡过后,苏禄苏丹就请求清廷修复其祖上在山东德州的陵墓,获得清廷的赞同。[4](P196-197)乾隆十八年(1753),苏禄还请求“内附”,“请以户口、人丁编入中国图籍”,“则三宝颜、千丝仔等闻风远避”(此时三宝颜已被西班牙占据),尽管清廷未予同意。[4](P194,205)至乾隆十九年(1754),苏禄又上表文请求乾隆帝赏赐铜、铁、硝磺以及4名能造枪炮的工匠,以此防御西班牙殖民者。[5](P731)不过,面对苏禄的请求,清廷主张岛夷争端“听其自办,不必自有所袒护”[3](P192-193)的不干涉政策,所以清廷亦未遂其愿。

表1 清代苏禄与中国朝贡关系史简表 [3](P119-190) [4](P192-211)
值得一提的是清苏之间的关系并未因上述朝贡关系的结束(1763年)而结束,恰恰相反,由于1764年后西班牙殖民当局对菲律宾华人实行大规模的驱逐政策,许多华人便转到苏禄地区,由此促进了苏禄与中国的贸易。所以自1760年始双方的私人贸易规模呈双倍的增长,到19世纪的前十年达到顶峰。[13](P9)
从表1来看,苏禄每次朝贡几乎都是搭载中国船只,特别是福建漳州、泉州商船,表明所谓官方的朝贡贸易几乎是在由民间贸易的推动之下完成的,其中往返都离不开华人的参与。雍正四年(1726)苏禄致清朝的表文中曾专门提到华人在其中的重要性,“缘沧溟实阻,指南无车道,必经吕宋地方,彼与臣世为敌国,且思必得熟海之人,方能上达愚诚”。[14](卷269,P5120-5122)马灿之前的身份为火长,其地位相当于领航员,“司针路者”,正因为他们熟悉航路,所以“波路壮阔,悉听指挥”。[15](卷9,P170)按照朝贡例行规定,苏禄需要先遣使请贡,再正式派使团来朝贡,然后次年再来谢恩。苏禄距厦门水程120更左右,[16](卷2,P118)帆船时代航行靠季风,一般是夏秋时节来中国内地,再等至来年东北季风时返回,所以实际每次遣使来中国的周期都较长。从表中也可以看出,从1726年至1763年的30多年,实际正式的朝贡行为只有1726年、1743年、1754年、1763年的四次,其他几次都是请贡,期间好几次都是卷入了马光明的案件而朝贡不成。但正式的几次几乎都有华人参与。马光明一案后,清廷也曾行文告知苏禄国“商民、船户良歹不一,其中竟有无籍之徒惯于蛊惑赚骗,嗣后该国贸易货财须谨慎择人,毋得轻事信托”。[3](P147)但是事实表明华人仍未缺席,这恰恰说明在苏禄与清朝的朝贡贸易中,华人参与的重要性。但问题是华人是否可充当贡使?
清代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明代的朝贡贸易制度,到乾隆年间与清朝维持这种关系的国家主要有朝鲜、琉球、安南、暹罗、苏禄、南掌和缅甸七国。其中对朝鲜和琉球两国的来使资格曾经做过某些限定,比如朝鲜,正副使各一员,以本国大臣或同姓亲贵称君者充任。琉球,正副使也是各一员,以本国王舅或耳目官即正议大夫、紫金大夫充任。但对于其他几国便只是规定了贡使的人数以及称谓等,比如南掌,贡使称大头目、次头目,其下有先目、通事、夷目、后生。对苏禄则仅规定“正、副使各一人,通事一人,从人无定额”。[2](卷39,P372)同时清朝没有沿袭明朝向海外朝贡国颁发勘合的制度,作为其遣使朝贡的凭证,以杜绝非官方的贸易和欺诈行为。毫无疑问,对于苏禄来说,贡使身份的无限制实际上也为华人充当贡使提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有雍正时期的先例。
雍正十年(1732)贡使龚廷彩再次回到福州上表以谢“天恩”。清廷赏赐的物品中,分别规定了对苏禄国王、正副使以及通事和从人、留边从人的赏赐。其中却特别规定,“正、副使彩缎6匹、里4匹、罗4匹、纺丝2匹、绢2匹,如来使系内地人,彩缎3匹、里2匹、绢1匹、毛青布6匹。”这表明清廷对于苏禄国朝廷选用华人作为贡使是认可的。
由此上溯至明代,正德五年(1510),满剌加国遣使亚刘者,本江西万安人,“以罪叛入其国为通事,至是与国人端亚智等来朝,并受厚赏”。[17](P78)爪哇国派遣到明朝的使臣通事洪茂、马用良、文旦等皆为福建龙溪人。[18](P212)著名的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后裔,担任中琉朝贡通事的比比皆是,有些还担任资金大夫和正议大夫等。*参见杨国桢:《跨越海洋的传奇:琉球久米陈氏家族史研究》,载杨国桢:《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第306-329页;孙清玲:《论"闽人三十六姓"在中国海外移民史的特殊性:东亚朝贡体制下的海外移民个案分析》,《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等。再如暹罗,暹罗华人在中暹朝贡贸易与民间贸易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P68)从1688年到19世纪中期,华人实际上是暹罗国王对外贸易的主要合作对象。[20](P165-188)明朝初期,官方还未将这些出国之人视为罪民,正统以后才开始因为华人使节的不法行为而不满,[21](P555-575)并对华人贡使产生了不良印象:“四夷使臣多非本国之人,皆我华无耻之士,易名窜身,窃其禄位”。[22](P281)
所以,此次以马光明为贡使原本也是可以接受的,可以设想如果马光明没有“索诈”行为,或者“索诈”行为未被发现,马光明等人或许会成为中外交流的友好使者。但是从官方角度来看,马光明的确是犯了“尤有关国体”的罪名。借贡使之名,招摇撞骗、滋扰内地,借王朝之权力以满足其私欲,自然要付出代价。其后苏禄再来进贡时,福建地方官府在查验时就谨慎了许多。乾隆十九年(1754)查出副使杨大成实即内地武举杨廷魁,于是便被发到黑龙江充当苦差。马光明案后,清廷也申明再三“嗣后凡内地在洋贸易之人,不得令承充正、副使。”[23](P97)是以,马光明一案的结果在于基本终结了以后华人充当苏禄国贡使的可能性。而苏禄与清朝之间的朝贡与五年一贡的期限并不吻合,期间因为贡使资格问题、国书程式问题双方进行了多次的交涉,而马光明一案或许是一次集中的展现,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朝贡贸易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变数,以及实现过程的复杂性。
三、“明严暗疏、内外有别”的清王朝海洋管理政策
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皇帝发布上谕道:“定例商人往外洋诸番贸易,迟至三年以外始归者,将商人、舵水人等勒还原籍,永远不许复出外洋,例禁甚严。今马灿等乃僭往苏禄往来内地,不但如陈大受所称影射滋事等弊,且以内地民人为外番,充作贡使,尤有关于国体,可传谕陈大受令旗知情事之轻重,留心筹办”。[3](P140)按说马光明的贡使身份是不成立的,可是从清初以来苏禄的朝贡贸易史来看,内地人充当苏禄贡使又是苏禄国王认可,曾经一度也被清廷所接受,所以马光明又可以具有贡使的身份。那么,如何看待这种事实上的矛盾?
乾隆十九年(1754)清廷允许领照出洋贸易之人无论年份久远,本人及亲属概准回籍,在此之前规定的出洋期限最长仅三年,对偷渡之人则是毫不留情的指责:“至无赖之人,原系偷渡番国,潜在多年,充当甲必丹,供番人役使,及本无资本流落番地,哄诱外洋妇女,娶妻生子,迨至无以为生,复图就食于内地,以肆招摇诱骗之计者,仍照例严行稽查。”[12](卷270,P14-15)
与明代的海洋政策“重防其入”相比,清代的海洋政策是“重防其出”[24](P29)。清廷对出海之人与海外反清或海盗势力勾结一直心存余悸,并将沿海的“以海为生”的商人和渔民视为“海贼之薮”,乾隆皇帝对马光明的劣行也归结为“私越外洋,勾结滋事”。[4](P201)与此同时,清帝国在东南海疆地区建立了保甲、汛防与稽查三者结为一体的保甲防御体系。在这种防御体系之下,是对出洋船只管理上的极其严格,手续极为繁琐。对出洋人员均采取具结、保结、连环互结等管制手段,[25](P331-376)凡是出洋之人姓名、籍贯、年貌、箕斗、职业等等都要由文、武汛口细细巡查,[8](卷4,P80)唯恐内地民人外出勾结番人作案。按照大清律例,“交结外国及私通土苗,互相买卖借贷,诓骗财物,引惹边衅或潜住苗寨,教诱为乱,贻患地方者,除实犯死罪外,俱问发边远充军。”[26](卷20,P331)马光明得此结果也是显然。
可是严格的规定并未获得严格的执行。各种合法和非法的出洋贸易或移民都在或盛或衰地进行。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守口员弁私纵偷渡成风”,“进出口各船不拘内地外洋,每船勒取番银陋规多寡不等,文武各衙门朋分收受”。[27](卷706,P884)马光明等一直往来于苏禄与内地之间“索诈”,或许也是利用了这种稽查不严的情况。所以,马光明案之后,乾隆十三年(1748)福建督抚才联名上奏,针对稽查不力问题提出了“绥靖海疆”的三条对策:其一,地方有司严格保甲制度。责令保甲房族在编查保甲门牌时注明户内人员去向,不明之人及时举报。其二,“贩洋船户、客商人等应分别责成稽查、验放,以杜顶替也”。其三,“沿海荒僻口岸应令讯弁及时巡查,以杜偷越也”。[3](P164-165)
一方面是清廷对沿海进出口人员稽查的明严实松,另一方面是地方官府对待本国人与外人的内外有别。[28]清廷在议定南洋禁航令时,曾明示“禁出允入”,“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商船概不许前去,其外国夹板船听其前来贸易。”[6](卷510,P91)“天朝怀柔远人,凡由番国来告的事情,必然加以体恤。”且看苏禄来华朝贡时福建地方官府的例行举动:乾隆五年苏禄来华请贡,遭风漂至台湾凤山,巡查御史立即“饬凤山县备办粮米食物,星往接济抚恤,又购给帆布”,并拨官兵防护,毋许地棍赴船骚扰,一遇顺风即派人护送至厦门。以后苏禄每次派遣使臣来厦门,厦门地方官总要加以抚恤,安顿夷馆,选派行商保证公平交易,[3](P119,122,204)即使在处理马光明一案期间也是,继而择定回国时间,选定往苏禄船户,保证安全回国。当然,这其中也有力图避免“番民”与内地人勾结的想法,但是对外“怀柔远人”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
四、结语
通过以上案例的探讨,可以看出朝贡贸易中华人贡使的身份是否成为“问题”取决于是否发生不法行为。由此也不难得出明清统治者贡使政策的相对延续性。著名学者王赓武先生指出海外华人是“没有帝国保护的海商”,[29](P91-118)马光明的案例表明起码部分华人试图在这方面寻求突破。该案件的发生也有其内在的根源。苏禄国试图借助华人的力量建立与清朝的联系。清廷一方面防范、限制内地人出洋,另一方面“怀柔远人”,优待来客。这种海洋管理上对内与对外的差异,无疑给沿海百姓带来心理上的不平衡,让人看到了贡使名目的价值所在。正如马光明所说,“总是他仗着天朝自然加恩于他”。[3](P159)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前,边界模糊,人员往来频繁,以苏禄为代表的所谓朝贡国实际与清廷又仅保持着较为松散的联系。与此同时,清朝地方官员在进出口管理上疏于防范,为某些人钻体制空隙创造了机会,使得海商在可能的情况下选择改变身份;并且这种贡使的名目还可以成为炫耀和诈骗的工具,以及民众畏惧的根源。海洋世界的生计模式塑造了流动的身份,王朝政策与个人紧密相连。正是在这片海洋世界里,内地人(华人)与“番人”可以游动其中,并互相往来,使得个人游离于体制内外的可能性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 钱江. 清代中国与苏禄的贸易[J].南洋问题研究,1988,(1).
[2] 钦定大清会典(光绪版)[Z].续修四库全书,第79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菲律宾卷)[Z].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4]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中研院”史语所编. 明清史料(庚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7.
[6]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版)[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7] Joshua Kueh, Adaptive Strategies of Parián Chinese: Fictive Kinship and Credit in Seventeenth-Century Manila[J].PhilippineStudies, Vol. 61, No. 3, 2013.
[8] 周凯等撰.厦门志[Z].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9] Cesar Adib Majul, Chine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ltanate of Sulu[A], in Alfonso Felix JR.,TheChineseinthePhilippines,1550-1770,Vol.1,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66.
[10] 彭慧.西班牙殖民时期菲律宾摩洛人的认同[A].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编.亚太研究论丛(第7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 Gregorio F. Zaide,PhilippinePoliticalandCulturalHistory[M],Vol.1, Manila: Philippine Education Company,1957.
[12] James F. Warren,TheSuluZone,1768-1898.Thedynamicsofexternaltrade,slavery,andethnicityinthetransformationofaSoutheastAsianmaritimestate[M].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1981.
[13] James F. Warren, Sino-Sulu Trade in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J].PhilippineStudies, Vol.25,1997.
[14] 陈寿祺等.福建通志[M].台北:华文书局,1968.
[15] 张燮.东西洋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6] 徐继畬.瀛环志略[M].台北:华文书局,1968.
[17] 余定邦,黄重宽.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8] 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19] 钱平桃,程显泗主编.东南亚历史舞台上的华人与华侨[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
[20] (澳)J·W·库什曼.暹罗的国家贸易与华人掮客(1767-1855年)[A].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三辑)[C].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1] 陈尚胜. “夷官”与“逃民”:明朝对海外国家华人使节的反应[A].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四)[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2] 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3] 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4] 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5] 刘序枫.清政府对出洋船只的管理政策(1684-1842)[A].刘序枫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九辑)[C].台北:“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5.
[26] 郑泰、田涛点校.大清律例[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7] 清高宗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6.
[28] 陈尚胜.论清前期国际贸易政策中内外商待遇的不公平问题:对清朝对外政策具有排外性观点的质疑[J].文史哲,2009,(2).
[29]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
The Envoy Identity in Tributary Trade System in Qing Dynasty——A
Case Study of Saltanah Sulu in the 18thcentury
Lv Junchang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Ma Guangming, once a fishmonger, then a sailor, interpreter and envoy, was always sailing on the sea between China and Saltanah Sulu. It all depends on the law whether envoy's identity became a problem in tributary trade system. Ma Guangming case not only reflects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dispute and the tributary trade system,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ba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mpire Qing's maritime policy,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Benefiting from the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Southeast Sea, and the borderless tributary system, a Chinese often changed his identity and became a Sulu envoy.
Key words: Saltanah Sulu; envoy identity; maritime policy of Qing Dynasty; tributary trade system.
责任编辑:高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