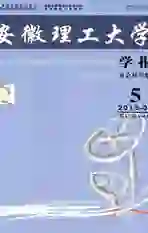《诗经》及其注解文献中草字部假借字研究
2016-01-12张道升张捷
张道升+张捷
摘 要:由于问世时间久远,《诗经》原本当中所使用的汉字有相当一部分字义发生了转变,以至于今人无法解读这些名篇佳句。假借就是《诗经》里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类字义转变的情况,有很多学者都为《诗经》做过注解,其中包括对假借字的使用情况所进行的说明。但是百家争鸣,莫衷一是。将《诗经》及其注解文献中草字部假借字提炼出来,对比各家的说法,查阅资料,审慎分析,弄清它们的假借情况,这对规范它们在古代汉语中的使用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诗经》;假借字;通假字
中图分类号:H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5-0031-05
《诗经》问世已有2500多年,无数文人学者对其进行研究。近代以来,文学方面的研究著作灿若繁星,汗牛充栋;与文学类的繁荣相比,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通过参考一部分学者的研究文献,发现文字方面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诗经》中假借字的使用非常频繁。当然,不少研究《诗经》的前辈早就发现了这个现象并且编写了专著加以阐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寻找一个突破点——对“草字部”这个有代表性的部首进行研究,希望可以填补学术研究上的一个小空白。这也避免了把《诗经》中所有的假借字都找出来研究的繁复局面。
一、假借字的学术定义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假借字”的概念。这就不得不从“假借”讲起,什么是假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指出“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1]。翻译成白话,就是本来没有这个字,但为了表达的需要,借用旧字来充当新义,这就是假借,其中的这个旧字就是一个假借字。比如,“长”本义是指物体的长度长,形容词性,后来指长官,变成了名词性,此处的“长”也就是一个假借字。确切地说,许慎率先提出了“假借”的概念,这一点,在学术界基本上没有异议,但是后世的学者们对于“假借”的所属范畴有较大异议。许慎本人认为“假借”是一种造字法,故而和“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并列为“六书”。清代语言学家戴震分析汉字“六书”得出“四体二用”的结论,他认为汉字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为造字法,转注和假借两种为用字法[2]。这一结论冲击了许慎的“六书说”,大体上是经得住考证推敲的,故而后世学者基本上都认为“假借”就是一种用字法。
其次,我们要弄清“假借字”产生的原因。我们知道,表意字是古代意音文字的基础。但是靠表意字来记录语言有很多困难:有些现象很难表意,造不出字来;而且如果事事表意,就得一物一字,给记忆造成极大的负担。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人们想出了借字表音的办法,就出现了假借字。清代学者孙诒让曾说:“天下之事无穷,造字之初,苟无假借一例,则逐事而为之字,而字有不可胜造之数,此必穷之数也,故依声而托以事焉。视之不必是其字,而言之则其声也,闻之足以相喻,用之可以不尽;是假借可救造字之穷而通其变。”[3]这话的大致意思是,天下的事物很多,造字的初期,如果没有假借的介入,为每一个事物单独去造字,那么造出的字就数不清了,根本造不完全,所以才借助同音词来指代事物。看上去不一定是指代本物的字,但是说出来是那个事物的音,听上去也算明白,使用起来就不受限制了,假借字可以解决造字不全的问题而使文字的使用变通。
二、假借字和通假字的关系
假借字到底和通假字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陈梦家先生在1956年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的“文字”章里,把汉字分为“象形”、“假借”、“形声”三种基本类型,是为“三书说”[4]。陈氏认为汉字从象形开始,在发展与应用过程中变作了声符,就成了假借字。裘锡圭先生在1988年出版的《文字学概要》中认为陈氏“三书说”基本合理,但是不应该把假借限制在本无其字的假借范围里,应该把通假也包括进去[5]。裘锡圭先生将通假引入到假借的概念里,究竟有无道理呢?让我们先将通假和假借分开来解释。
通假字自产生之日起就和“六书”纠缠不清,学者们见仁见智,难成定论。康晓玲在《试论通假字》中认为,通假字和六书中的假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6]。通假字是训诂学上的问题,六书中的假借是文字学上的问题。前者和正字相对应,后者和本字相对应;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遵循音同音近的原则。康晓玲的观点未免过于笼统,失于宽泛。马晓琴认为通假和假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假借是六书中的一种,是一种造字的方法,造字的原因是:“本无其字”,造字的方法是借用现成的字来“依声托事”。而通假则是一种用字的方法,一般地说,通假是本有其字的,但由于一时疏忽忘了写本字,或由于传抄底本不同,或由于师承不同,而借用了另外的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示本字。马晓琴割裂了通假和假借之间的关系,完全站在《说文》的角度片面的来看待假借字和通假字。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认为“所谓古音通假,就是指古代书面语言里同音或音近的字的通用或者假借”[7]546。周秉钧在《古汉语纲要》中提出“通假,指的是古书上音同音近的字互相通用和假借的现象。凡是两个读音相同或者相近,意义也相同的词,古代可以写成这个或者那个,叫做通用。凡是两个读音相同或相近而意义不同的词,古代有时可以借代,叫做假借”[8]。两位大家都看出了假借与通假之间的联系,但是在论述上不是很严谨。
本有其字,因音通假,是为通假字。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是为假借字。两者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字音必须相同或相近,都是用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去代替另一个字。
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也曾说过:“假借字的产生,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有其字,而人们在书写的时候,写了一个同音字;第二种是本无其字,从一开始就借用一个同音字来表示。”[7]547于是乎,现代学界把假借字的定义分述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假借字既包括本无其字的假借又包括本有其字的通假;狭义的假借字单指本无其字的假借。由此可见,王力先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看出了假借和通假同属于用字法领域,并且理清了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为降低撰写难度,本文将从广义的假借字角度展开论述。
三、列举《诗经》及其注解文献中的例字进行分析
为何选取《诗经》中草字部首来进行假借字研究呢?李圣楠先生在《从<诗经>通假字看声母在通假关系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诗经》全部2 826个用字中通假字就达到了521个[9],比例超过六分之一,而通假字只是假借字的一种情况,所以《诗经》中假借字的使用是非常频繁的,以《诗经》作为研究底本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在《诗经》篇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就是草字头部首的字,共使用155个,说它们是《诗经》里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部类,当之无愧。由于《诗经》中出现的绝大部分草字部首字都是植物类专有名词,这其中的绝大多数又都是非常用字,研究意义不大,现主要对其中的常用字进行探究。同时为了减轻调研难度,只对实词义项进行研究,不研究虚词义项。
初步筛查后,确定了“莫、芮、芼、薄、藏”这五个字为假借字的研究对象,确定依据是“同声而定”。这些字和本字具有相同的声符而在意义上有联系。其中只有“芼”是非常用字,其余四个字都是直到今天都通用的常用字。选取这几个字进行研究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一)莫
《说文·茻部》:“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莫的本义是日落的时候,此处特指黄昏。现在这个义项一般写作“暮”。而在《诗经》及其注解文献中,“莫”至少有以下几类义项:
1.mù,《诗·齐风·东方未明》:“不夙则莫”;《唐风·蟋蟀》:“岁聿其莫”;《小雅·采薇》:“岁亦莫止”;《大雅·抑》:“谁夙知而莫成”。在以上各例句中,莫都是“晚”的意思。基本上都是从本义直接引申而来的,无论是毛亨、郑玄还是朱熹,都没有把这几个“莫”当作假借字,应当是无误的(该释义见于《汉语大字典》(第2版)3 430页)。
2.mù,《诗·大雅·板》:“民之莫矣”。马瑞辰《传笺通释》解释为“莫,读为瘼,训病”[10]。就是一种疾病。马氏认为这里的“莫”是“瘼”的假借。而李富孙《诗经异文释》卷十三:“民之莫矣。荀悦《汉纪》引作慕。”[11]荀悦和李氏都认为这里的“莫”是“慕”的假借。虽然假借字的本字在学术界有异议,但是此处的“莫”为假借字当是确定无疑的。
3.mò,《诗·小雅·巧言》:“圣人莫之”。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成“莫,又作漠同,一本作谟”[12]。李富孙解释成“圣人莫之,《汉书叙传》师古注作‘谟”。而何楷在《古义》中写道“莫通作谟,徐铉云:泛议将定其谋曰谟”。综上所述,此处的“莫”应是“谟”的假借字确定无疑,而谟就是谋划的意思(该释义见于《汉语大字典》(第2版)3 430页)。
4.mò,《诗·大雅·皇矣》:“求民之莫”。王先谦《三家义集疏》:“鲁齐莫作瘼”。又李富孙《异文释》:“《潜夫论》班禄引作之瘼”。王氏引用得当,他认为此处的“莫”是假借字,并且通过调研得出鲁齐这个地方存在“莫”通“瘼”的情况。李富孙也引用班禄的说法,认为“莫”是“瘼”的假借字,从而侧面印证王氏的说法。而“瘼”是病痛苦难的意思,“求民之莫”就可以解释成“了解民间的疾苦”,故而也是词通句顺。该词条《汉语大字典》(第2版)3 430页:“安定。《诗·大雅·皇矣》:‘监观四方,求民之莫。毛传:‘莫,定也。”我们认为此释义不合语境,当改。
以上义项中,例1与假借字无关,而例2、3、4都是确定下来的假借字。由此可见,“莫”字在《诗经》中作为假借字使用的情况很复杂,从而应当成为注解《诗经》相关篇目的一个关键字。
(二)芮
《说文·艸部》:“芮,芮芮,艸生貌。从艸,内声。读若汭”。《广韵·祭韵》:“芮,草生状”。《玉篇·艸部》:“芮,草生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芮”的本义是小草生长的样子,形容词性。而在《诗经》原文中,只有一处出现了“芮”,但历史上的注解可谓是众说纷纭。
ruì,《诗·大雅·公刘》:“芮鞫之即”。毛亨解释成“芮,水厓也”。郑玄解释为“芮之言内也”;孔颖达解释成“芮,水内也”;朱熹解释为“《周礼·职方》作汭”;陆德明认为“芮,本作汭”。乍一看,毛亨、郑玄、孔颖达、朱熹、陆德明对于此处的“芮”说法不尽相同,但是我们细细分析一下,发现他们几乎都把这个“芮”看作和水有关,基本上解释成河流弯曲的地方。而且,郑玄、朱熹和陆德明都认为此处的“芮”是假借字,郑玄认为是“内”的假借,朱熹和陆德明认为是“汭”的假借,实际上,“内”和“汭”是一回事,都指“河流弯曲或汇合的地方”,只是在郑玄的年代,“汭”字还未造出或者还未广泛使用。在这里,“芮”字作为“汭”的假借字来使用是可以确证的,否则本例句将无法正确翻译出来(该释义见于《汉语大字典》(第2版)3 389-3 390页)。
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至少罗列出“芮”的三类假借用法[13]。第一类就是《诗经》中出现的“汭”;第二类是假借为“纳”,吸收的意思;第三类是假借为“蜹”,一种略像苍蝇的昆虫。
借助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芮”在《诗经》中的假借情况比较明确,只有“汭”这一种。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避免注解上的失误。
(三)芼
《说文·艸部》:“芼,艸覆蔓。从艸,毛声。诗曰:左右芼之”。芼的本义应该是植物的草叶覆盖茎蔓,指植物生长茂盛,形容词性。在《诗经》中,“芼”出现了这样几种义项:
1.mào,《诗·召南·采蘋》:“有齐季女”。毛传:“芼之以蘋藻”。陈奂《传疏》:“芼,菜也”。这里的“芼”被解释成菜,这里的菜应该是广义的说法,不是单独指某一种蔬菜,而是指某一类蔬菜。这是一类以浮萍水藻为主的蔬菜,浮萍水藻都是很茂盛的样子,我们可以看成是“芼”字本义的引申,那么形容词性的“芼”在这里就变成了名词性的“菜”了。这里的“芼”并非假借。
2.mào,《诗·周南·关雎》:“左右芼之”。《关雎》是《诗》的开篇之作,也是最为脍炙人口的一篇。但是例句中出现的“芼”,在《诗经》的传诵过程中,始终有着不同的注解。毛亨注解为“芼,择也”;许慎解释为“芼,艸覆蔓”;孔颖达解为“芼,训为拔”;朱熹解释为“芼,熟而薦之也”。让我们把这几种解释带入原句中去翻译一下。毛亨和孔颖达的注解同义,故而合并。“参差荇菜,左右芼之”,毛注为“荇菜有短有长,向左向右去采摘它”;许注为“荇菜有短有长,左边的右边的都很茂密”;朱注为“荇菜有短有长,左右之人把它做熟了置于草席上(来祭祀)”。以此观之,朱熹的注释有些牵强,完全站在维护封建礼仪的角度。而毛亨和许慎的解释都有可取之处,出于对仗的考虑,学者们大都采取毛亨的说法。但是后世学者很尊重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许慎给“芼”字下的本义界定是准确无误的,那怎么理解《关雎》中的“芼”呢?马瑞辰在《传笺通释》中给出一个解释“芼者,覒之假借”。李富孙在《诗经异文释》里呼应道“左右芼之,《玉篇·见部》引作覒之”。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里也记录着“芼,假借为覒”。综三家所述,“芼”当是“覒”的假借字,这样一解释,真是让人豁然开朗,“覒”的意思就是拔取。故而得出一个结论,“芼”本身只有茂盛或者菜的意思,只有在假借时才有采摘的意思(该释义见于《汉语大字典》(第2版)3 390页)。
以上义项,例1是词义引申,例2却是名副其实的假借。“芼”虽为非常用字,但由于它在《诗经》篇章中的特殊位置,使得文字学者们偏爱于它,弄清它的假借用法,才能揭开它身上的神秘面纱。
(四)薄
《说文·艸部》:“薄,林薄也。一曰蠶薄。从艸,溥声”。按照许慎的说法,薄的本义是“林”,林就是草木丛生之义;另外一种,薄指蚕丝的厚度。两个义项都是形容词性,前者是形容草木的,在先秦使用的频率较高;后者是形容一般物体的,这个义项在现代使用较多。《诗经》中出现的“薄”有以下几类义项:
1.bó,《诗·周南·葛覃》:“薄污我私,薄澣我衣”。朱熹解释道“薄,犹少也”。朱熹的解释好像是没有问题的,他认为此处的“薄”虽然不是宽度上的范畴,但是可以看作是量上的反映,和“厚薄”当中的“薄”属于相似语义场,故而可以看作是“薄”本义的引申。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薄,发声也”。王氏认为此处的“薄”是个发语词,词性是虚词。王氏看的更透彻一些,此诗是写女主人公以葛覃起兴来抒发自己的喜悦之情,“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就是洗衣服的意思,前后两句是并列关系。按照朱熹的解释,这二句翻译过来逻辑上是不通的。故而可见,此处的“薄”无论是虚词义项还是实词义项都没有假借的可能。
2.bó,《诗·周颂·时迈》:“薄言震之”。郑玄的解释为“薄,犹甫也;甫,始也”。陈奂传疏引《后汉书》注引《韩诗章句》云“薄,辞也”。陈奂和郑玄的注解并无出入。“始”是副词,副词属于虚词,虚词指的就是“辞”。郑氏对《诗经》做的注解是很有见地的,被业内学者高度称赞,此处的注解就是非常精辟的。郑玄把此处的“薄”准确地解释为“开始”,和后面的“言”合用构成一个发语词。作为一位语言学家,做到这一步并不是什么难事,难能可贵的是郑玄还看出了“薄”的假借。长久以来,不少学者都为一个现象所困扰,“薄”明明是一个实词,为何能作虚词当中的发语词来使用呢?殊不知郑玄在两千年前就给出了一个很有力的回答。在郑玄的时代或者更早的时代,汉语声母中是没有轻唇音“非、敷、奉、微”的,这就是被清代学者钱大昕及后来语言学家证实的“古无轻唇音”现象。那么轻唇音到哪里去了呢?轻唇音被重唇音“帮、滂、并、明”合并了。在郑玄的时代里,“甫”的读音很接近“薄”的读音,故而有了假借的先决条件。而“甫”有着副词“开始”的含义,后世的学者们或不注意或懒得改正,就一直用“薄”去代替“甫”的虚词义项。终于,在岁月的积淀下,“薄”出现了固定的虚词用法。在《诗经》两千多年的注解史上,郑氏在此处的精妙一解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他从源头上解释了“薄”出现虚词义项的原因。就凭借这一点,后世学者们望尘莫及(该释义见于《汉语大字典》(第2版)3 526页)。
3.bó,《诗·小雅·蓼萧序》:“泽及四海也”。郑玄《笺》:“外薄四海也”[14]。陆德明《经典释文》:“诸本作外敷”。又孔颖达《疏》:“检郑尚书经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敷”。郑玄固然是没有把此处的“薄”看作假借字。原因很简单,当时“敷”字没有问世,或者是郑玄抄错了字,金无足赤,再智慧的学者也会有出错的时候。陆德明很明确的指出了假借字,“薄”通“敷”,覆盖的意思。通用的原因就是音近替换,原理是“古无轻唇音”。而孔颖达进行了总结性的注解,基本上确定了“薄”的假借用法。
例2、3义项都是很明确的假借用法,几位大师的研究成果让后人受益匪浅。
(五)藏
《说文新附·艸部》:“藏,匿也”。徐铉等按“汉书通用‘臧字,从艸后人所加”。藏的本义就是躲藏,本来的写法是“臧”。而“臧”的本义在《说文·臣部》中的解释是“臧,善也。从臣,戕声”。臧的本义是“美好”。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藏匿”,《楚辞·九怀·尊嘉》:“辛夷兮挤臧”。洪兴祖补注“臧,匿也”。更有明确指出“臧”字假借的情况——《易·师》:“否臧凶”。《焦循章句》:“臧,古藏字”。《汉书·礼乐志》:“臧於理宫”。颜师古注“古书怀藏之字本皆作臧”。由此可见,“臧”字与“藏”字有着密不可分的假借关系。在《诗经》中“藏”就有这么几种义项:
1.cáng,《诗·小雅·十月之交》:“亶侯多藏”。朱熹解释为“藏,蓄也”。朱熹在此处的解释基本上是准确无误的。该诗是周幽王时期的一位小官作的政治怨刺诗,该句译为“确实应该多多蓄养”,与前句“择三有事(三有司,三卿)”衔接紧密,逻辑通顺。此处的“藏”是动词性的,有保护保养的意思,与“藏”的本义收藏有一定的联系,故而是引申无误。
2.
cáng,《诗·小雅·隰桑》:“中心藏之”。马瑞辰的《传笺通释》明确解释为“藏者,臧之假借”。李富孙《诗经异文释》也写道“中心藏之。表记释文:藏,郑解诗作臧”。马氏很明确的认为此处的“藏”是“臧”的假借字,郑玄最早也是这么认为的,李富孙对此也表示支持。其实“臧”才是本字,动词性的收藏、躲藏、隐藏,全部都是以“臧”为本字的。后来,“臧”还被活用为“收藏的东西”,就成了名词性的了。可能是这个时候的某些学者觉得“臧”表示名词有些突兀,就加了一个艸字头,于是就有了“藏”,但应该明确,“藏”最初仅仅是表示名词性的义项,随着使用的广泛化,才逐渐的取代了“臧”的动词义项(该释义见于《汉语大字典》(第2版)3 531页)。
例2是假借,而且是汉字演化史上比较特殊的一种。汉字的演化大体上遵从着由繁化简的趋势,但是“藏”取代“臧”却是逆其道而行,真是很有特色。
“莫、芮、芼、薄、藏”每个字至少都有两个义项,在这么多义项中有些是假借的,有些是引申的,鉴别这些义项有时候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研究过程中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其实,《诗经》中草字部首的假借字实际上还有很多,但是因论文篇幅和时间的限制,本文只列举这样五例,希望致力于《诗经》或假借字研究的学者能够关注此事。
参考文献:
[1]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3-4.
[2] 孙雍长.转注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20.
[3] 孙诒让.籀庼述林[M].成都:巴蜀书社,2002:118.
[4]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98:25.
[5]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20-122.
[6] 康晓玲.试论通假字[M].太原:山西大学出版社,2005:1.
[7] 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62:546、547.
[8] 周秉钧.古汉语纲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263.
[9] 李圣楠.从《诗经》通假字看声母在通假关系中的作用[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
[10] 马瑞辰.诗经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232-233.
[11] 李富孙.诗经异文释[M].上海:上海书店,1988:157.
[12] 陆德明.经典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07.
[13]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M].北京:中华书局,1984:522-531.
[14] 郑玄.毛诗传笺[M].上海:上海书店,1988:52.
[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