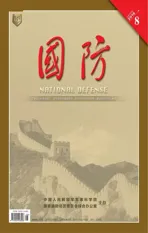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伟大的长征之八 喜极而泣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川达维
2016-01-05王树增王树增著名军旅作家专业技术3级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
王树增王树增,著名军旅作家,专业技术3级。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等,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伟大的长征之八喜极而泣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川达维
王树增**王树增,著名军旅作家,专业技术3级。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等,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
1935年5月20日,中央红军先遣队到达泸沽城。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认为,如果川军死守横在大路上的富林,中央红军要从大树堡渡口渡过大渡河将十分困难,因此建议中革军委改变行军路线,选择小路从安顺场方向渡过大渡河。关于必经彝区的问题,刘伯承说:彝族分黑彝和白彝,黑彝是纯粹的彝族血统,是彝族的上层;白彝是彝汉混血,属彝族的下层。他们之间有矛盾,主要起因是彝人对汉人的猜疑和敌对,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奉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后果。但是,只要红军工作得当,是有可能通过的。
晚上,刘伯承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到达冕宁县城。这座县城里没有任何川军防守。为了不打扰居民,先遣队司令部设在城内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红军进驻的时候,刘伯承把教堂里的神职人员集合起来,向他们宣传了红军的宗教政策。教堂里的几个法国修女对面前这个被传说为“土匪首领”的红军将领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感到万分惊讶。
在遭遇巨大损失的湘江战役之后,进入大渡河地区的中央红军又没有退路了:后面,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和周浑元的追击部队;西面,有滇军孙渡部沿着雅砻江的布防;东面,有川军杨森的第二十军和郭勋祺、陈万仞等部的联合阻截;前面,大渡河上的主要渡口已经布满川军刘文辉的部队——中央红军进入了一个狭窄封闭的地域里,如果一旦被大渡河所阻挡,挣脱被围歼的命运就等于是一场血战死拼。
在与共产党人的多年对立中,毛泽东给了蒋介石太多的意外,以致现在无论红军有什么举动,蒋介石都会首先感到其中有诈。但是,等了几天之后,蒋介石发现毛泽东并没有什么惊人之举,而是沿着当年石达开走的路线北上了。蒋介石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毛泽东是懂得历史的,中国版图如此之大,毛泽东为什么非要走石达开的死路?
蒋介石旋即任命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拨二十一军、川康军一部约4个旅归其调遣。他并没有把防守的重点放在从冕宁向北的安顺场,这说明,他依旧不相信精通历史的毛泽东会选择与石达开完全一样的旧路。
对于川军杨森,毛泽东并不熟悉。朱德说,蒋介石的这个任命是“一石两鸟”,既考验了杨森对他的忠诚,也可借此机会拉拢杨森,促使杨森率川军与红军血拼一场。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用意十分清楚,但是他认为,石达开之所以被围困在安顺场而不能渡河,根本的原因是他收买的那个彝族土司背叛和出卖了他,不然清军也无法顺利通过彝区来到大渡河边。毛泽东说:“顺利渡过大渡河的关键是和彝人关系的处理。”在为刘伯承率领的先遣队送行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嘱咐,先遣队的任务与其说是打仗开路,不如说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如果红军模范执行民族纪律,取得彝人的信任,抢渡大渡河的行动就能取得胜利。为此,毛泽东特别命令19岁的萧华带领一支红军宣传队跟随先遣队一起行动。
虽然走的是同一条路,但是中国工农红军绝不是石达开的太平军。读过《庸庵文续编》的毛泽东深知这一点。但同样读过《庸庵文续编》的蒋介石却绝不会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毛泽东让部队准备了一些酒、绸缎和枪支,请来当地的彝族头人小叶丹。彝族头人对红军将领能够平等对待他们很感动,因为平时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官员很看不起他们。从彝族头人那里,毛泽东了解了这一带彝人族系的情况,并且指示刘伯承尽快和彝人首领达成协议,以免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通过的时候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见到刘伯承,小叶丹首先解释说,在这个地区,彝人基本上分成3个族系,即沽基、罗洪和洛伍。经过三方代表的交谈,罗洪家族由于抢了红军,人都已经跑了,其头人不肯再露面;洛伍家族表示出中立的立场,而沽基家族的小叶丹愿意和红军继续谈判。刘伯承从解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到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一直到满足彝人的各项要求和红军过路的种种细节,耐心地与小叶丹商谈,最后以结为兄弟为条件结盟。
这是共产党人少有的举动,仪式按照彝族沽基家族的传统进行。结盟仪式后,刘伯承邀请小叶丹和他的小头人们一起吃饭。红军把附近一个小集镇上的酒全部买了下来。酒席中,小叶丹表示,如果罗洪家族的人再袭击红军,他就带人把罗洪家族的村寨烧了。刘伯承劝解道:“彝人之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欺压彝人的国民党军阀。”这个观点让小叶丹很是折服。最后,刘伯承送给小叶丹十几支步枪。
红军将领和沽基家族的结盟,对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至关重要。在以后的行军中,不但袭击红军队伍的事件很少发生,粮食的筹集也相对顺利。小叶丹还专门派出彝人武装护送红军先遣队赶往大渡河渡口。
为了加深共产党人在彝人中的影响,红军专门留下一名负伤的红军团政委,帮助小叶丹组织与国民党军对抗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后来联合了包括罗洪、洛伍家族在内的1000多人,几乎相当于一支红色游击队。当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追击而来时,虽然也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给彝人准备了大量的礼物,但是薛岳发现共产党在这里的影响已经很深,于是他立即命令给每一个彝人紧急“消毒”。国民党任命的“彝务指挥官”邓秀廷把红军留下的那位团政委逮捕了,小叶丹家族倾尽家财,用1500块大洋把人赎了出来。后来,小叶丹被邓秀廷以“通共有据”的名义杀害于大桥镇。被害之前,小叶丹对弟弟沽基尼尔说:“红军把咱们彝人当人看。刘伯承这样的大人物是守信用的。我死了之后,你要告诉刘司令,咱们彝人相信的是共产党和红军。”
5月25日,红军的突击队终于占领了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北岸。26日,大雨倾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在大雨中向安顺场急促前进。部队必须迅速渡河,一刻也不能耽搁。但是,当毛泽东到达大渡河边的时候,他担心的情况到底出现了。
在渡口,红军一共只找到4条船,而且只有1条是好的,其余3条都需要修。刘伯承计算了一下:一条船的最大容量是30人,往返一次最少要1个小时。占领北岸之后,一天一夜仅仅渡过去1个团。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需要整整1个月的时间。可是,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已经越过德昌正向大渡河急促挺进,川军杨森的部队距离安顺场也只有三四天的路程。中央红军根本没有1个月的渡河时间。
于是,一个新的渡河方案形成了:兵分两路。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继续从这里渡河,渡河后组成右纵队,由刘伯承和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北岸向上游的泸定方向前进,以接应从那里夺桥渡河的红军大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沿大渡河南岸奔袭至上游的泸定桥,在那里夺桥渡过大渡河。其他部队和中央纵队随后,一律立即改变行军路线向泸定桥前进。
这是一个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作出的冒险决定。
首先,此刻红军无法确定位于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是否还在,即使那座桥还没被川军破坏,红军也无法确定那里有多少守桥部队。其次,命令所有的部队改变行进路线,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160公里的路程,沿途的情况未知。其三,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继续在安顺场渡河,其他部队改由泸定桥渡河,这就意味着中央红军将被大渡河分隔成两部分。一旦从泸定桥渡河失败,中央红军将成为分散的两支部队,而会合将会使红军再次付出代价。最后,中革军委决定:从最坏的情况打算,如果泸定夺桥渡河失败,两支红军不能会合,则由刘伯承和聂荣臻单独率领部队“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中央红军各军团再次面临极大的困难:沿着大渡河南北两岸向上游泸定桥前进的部队,必须在两天半的时间里奔袭万分崎岖而又敌情未知的山路,而160公里的路程还意味着必须以每天50公里以上的速度急行军。同时,位于安顺场下游的红三军团必须立即向西靠拢,不然就无法追上突然转向的主力。尤其是由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他们顺着大路到达大树堡佯装主力后,必须不顾一切地追上在小路上的主力;但是现在主力部队改变了行动路线,从大树堡到泸定桥比到安顺场远了整整一倍,且他们被命令坚持到28日才能动身,其追赶路途的遥远和艰辛可想而知。
5月26日,中央红军兵分两路夺取泸定桥的决定,当天就被国民党军的情报部门截获。
蒋介石紧急由重庆飞往成都,重新部署对中央红军的“围剿”行动。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不敢怠慢,立即命令第四旅袁国瑞部火速向泸定方向增援。袁国瑞命令其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沿大渡河南岸阻击向泸定桥前进的红军,第十一团团长杨开诚沿大渡河北岸阻击向泸定桥方向接应的红军,第十团团长谢洪康率领部队为总预备队,第四旅旅部进驻龙八部。
这是敌对两军的赛跑,目标是泸定县城西面那座吊桥。
南岸,中央红军的前锋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29日清晨,四团已经向泸定桥守军川军李全山部发起进攻。
泸定桥是一座由铁索支撑起来的空中吊桥,由13根碗口粗的铁索连接两岸,其中9根为桥面,4根为扶手,桥长101.67米。然而桥面铁索上铺的木板已被拆去,北岸桥头的桥楼已被沙袋紧围,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垒,从堡垒的射击孔中伸出的机枪正对铁索。泸定城一半在山腰,一半紧贴河边,城墙高约两丈,上面的堡垒所配置的火力在桥面上形成了一张火网。
在北岸防守的是川军李全山的第三十八团,其先头部队三营曾与红军隔河举着火把齐头并进。三营的先头连比红一军团四团早两个小时到达泸定桥后,即开始拆除桥板,并构筑阻击工事。天亮的时候,团长李全山率李昭营到达北岸桥头堡,此时,南岸红军的四团也到了,双方即刻交火。在交火中,川军李全山团有50多人受伤。
在川军团看来,万丈深渊之间,仅凭几根铁索就想突击到河这边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们一边向河对岸射击,一边不断地向红军高喊:“有种的你们飞过来!”
下午,红军第四团确定了夺桥的作战方案:二营和三营火力掩护,并特别注意用火力阻击两侧的增援之敌;一营分3个梯队正面强攻。
首先发动进攻的是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带领的22人突击队,他们必须强行攀索到达北岸;三连在他们的身后,任务是跟在后面铺桥板;三连的后面是一连,任务是在铺好的桥板上发起最后的冲锋。
下午4时,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打响了。
没有任何别的可以选择的出路,只有迎着枪林弹雨强行冲过13根寒光凛冽的铁索。
22个年轻的红军勇士向铁索冲去。
川军开始疯狂射击,红军的掩护火力也猛烈压制。炮弹呼啸,大河两岸皆成一片火海。川军的子弹打在铁索上,火星迸溅。红军勇士一手持枪,一手抓索,毫无畏惧地一点点向北岸靠近。
三连连长王友才带领的官兵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们人人抱着木板,只要前面的突击队队员前进一步,他们就在铁索上铺上一寸。
南岸红军的军号声连续不断地怒号,红军所有的掩护火力也愤怒地喷射。22名红军勇士冒着川军的弹雨和炮火攀索前进,并接近了泸定桥北岸的桥头堡。
与其说这是一场战斗,不如说是意志和勇气的较量。看着攀着光溜溜的铁索冲过来的红军勇士,川军目瞪口呆,惊恐万分。他们平生从未见过这样舍生忘死的场面。
时任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当事先准备的全团数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司号队同时吹响冲锋号时,我方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弹像旋风般刮向敌人阵地,一片喊杀之声犹如惊涛裂岸,山摇地动。22名经过精选的突击队队员,包括从三连抽调来的支部书记刘金山、刘梓华……他们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在队长廖大珠同志的率领下,如飞箭离弦,冒着对岸射来的枪弹,扶着桥边的栏索……向敌人冲去。激越嘹亮的军号声震荡着千年峡谷。
就在红军勇士即将接近北岸的时候,北岸桥头突然燃起了大火——川军把拆下来的桥板堆在桥头,泼上煤油点燃了。大火封住了桥头。火势凶猛,映红了渐渐暗下来的黄昏天色。
攀在最前面的廖大珠连长喊了一声:“同志们,跟我前进!”然后他站起身,第一个冲进了火海。第二个迎着火海冲进去的,是一个苗族小战士。接着,突击队队员一个跟着一个冲进了大火之中。
头发、眉毛和衣服都被烧焦的红军勇士冲过了火焰,冲上了泸定桥桥头堡阵地。后续梯队踩着桥板,不顾一切地过了桥,冲进泸定县城。
泸定县城里的巷战进行了2个小时。最后时刻,川军团长李全山得知自己的身后也出现了红军,立即命令周桂的三营掩护团主力撤退。而周桂则把掩护的任务交给了饶杰连长。但是,饶杰没等红军到跟前就先逃跑了。周桂只好一边撤退一边收容自己的官兵,最后发现他的三营只剩下十几个人。
傍晚时分,刘伯承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沿大渡河北岸也到达泸定桥边。
两军在桥头会合了。
1935年5月29日晚10时,大渡河谷夜风强劲,刘伯承和聂荣臻提着马灯,在四团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的引导下,走上了泸定铁索桥。刘伯承从桥的这头走到那一头,然后又从那头走回来。在桥中心,他停下了,用脚跺了几下桥板,铁索桥剧烈地晃动起来。刘伯承自语道:“泸定桥,泸定桥,我们胜利了,胜利了!”
第二天,由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主力和由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主力,以及中央纵队先后到达泸定桥。
毛泽东走上泸定铁索桥,扶着冰冷的铁索说:“应该在这里立一块碑。”
多年后,聂荣臻也这样评述了红军突破大渡河的壮举:“这是全体红军集体作战的结果。没有红四团英勇无畏,川军不会如此就放弃了抵抗。没有红五团去大树堡吸引敌人,红一团在安顺场能否抢渡成功还是个疑问。如果不是红一师从安顺场渡了河,威胁了泸定守敌的背后,泸定桥能否顺利得手也很难预料。如果我们不能夺取泸定桥,我军将是个什么处境?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是任何敌人不能比的。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够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刚刚摆脱了危机的中共中央派陈云去上海白区恢复党的组织,同时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这一决定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事先没有向共产国际请示,事后也没有汇报,这在中国共产党以往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遵义会议不但更换了中共中央的领导,还剥夺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权力,这样重大的事件如果不能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将关系到目前的中共中央是否“合法”的问题。特别是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内部,一些干部已经习惯了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对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遵义会议决议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
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王明和康生。派一个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人去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一直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一个愿望。陈云正是一个合适的人选。陈云辗转到了上海,设法与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联系后,决定分别启程去苏联。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试图恢复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并派出张浩同志去上海。张浩是位老资格共产党员,原名林育英,是中央红军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堂兄。林育英是带着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回到中国的。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对中国共产党现状毫不知情的共产国际依旧选举了王明、毛泽东、朱德和张国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当陈云一行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张浩已经在去上海的路上了。
到达莫斯科的陈云和潘汉年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遵义会议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领导人的变动,还有目前正在进行的军事转移的情况。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决议,肯定了张闻天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讲,至关重要。
在泸定县城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军路线。红军将领的心中都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从泸定向北有3条路可以选择:走西面,要从大雪山的西麓绕过去,是一条马帮走的小路,通往川北的阿坝地区,由于绕路,这条路的路程较长。走东面,是一条大路,沿途都是人口稠密的城镇,可以直通成都,但是这条路上肯定有敌人重兵把守。还有一条路,在东西两条路的中间,由于需要翻越险峻的雪山,连马帮都很少通过。
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走中间这条路。
当时,中央红军并不知道红四方面军的确切位置。但事后证明,这条中间的路恰恰是两军会合距离最近的一条路——此时此刻,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中间仅仅隔着一座雪山。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翻过二郎山后,迅速突破川军在天全、芦山的阻击线,接近了大雪山夹金山。
中革军委收到红四方面军的电报,电报称已派出部队去懋功方向迎接中央红军。1935年6月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为达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给各军团的指示》,首次以命令的形式明确了中央红军要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会合的地点确定为懋功。
夹金山主峰海拔4260米。当地的一位老者说:这座雪山是一座神山,如果事先不向神祷告,贸然上山是会受到惩罚的。红军官兵们说:红军就是神仙。
年轻的红军官兵坚定而乐观地相信,在雪山前面不远的地方,他们一定能见到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两支红军部队一旦会合,革命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中央红军离开天全、芦山的那一天,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再次脱离队伍,向东佯装主力行军。而蒋介石接着就认定这支行进的部队就是中央红军的主力,他无法想象中央红军会选择翻越大雪山。
由于要翻越雪山,红军必须把一些伤员和病号留下来。在政治工作人员与这些伤员和病号谈话的时候,他们都流下了热泪。
对于大部分官兵都是南方人的中央红军来讲,即将翻越雪山比面临一场战斗更令他们心情紧张。在与当地老乡们的交谈中,红军官兵对有关雪山的一切譬如雪崩、寒冷、缺氧有了初步的了解。年长的老乡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过的话,早晨和黄昏是一定不行的。要过,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气,最好手里再拄根拐棍。”
部队开始着手准备粮食、御寒的衣服和辣椒。但是,大雪山下人烟稀少,烈酒和辣椒无法买到,御寒的衣服更是无从找寻。之前抢渡金沙江时闷热难挨,红军官兵大多是单衣单裤,有的还穿着短裤;后来为了奔袭泸定桥,官兵们把多余的衣物全丢掉了。因此,杨成武政委说:“看来,我们只能穿着单衣去翻那座雪山了。”
1935年6月12日一早,前卫部队红一军团四团将仅有的两串辣椒煮成了两大锅辣椒水,全团官兵一人一碗。上午9时,部队便向夹金山大雪山出发。
对于经过漫长征途的红军官兵来说,翻越夹金山大雪山是比任何残酷的战斗更为艰难的过程。远远地看,雪山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来自平原的他们对高海拔的威胁显然没有准备。他们预先想到了路滑、寒冷、疲惫和剧烈的喘息,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过死亡。
中央纵队中的女红军们也是一身单衣。贺子珍和刘群先一起拉着马尾巴爬山。无论刘群先如何劝说,贺子珍都不肯骑在马上。她认为红军要走的路还很远,如果把马累死了,困难就更大了。但减员最多的是担架员和炊事员。担架员的负重太大,他们因为不愿丢下那些在作战中负了伤的红军战友而将自己累死。炊事员们死亡的原因大多是因为违反了轻装的规定,他们在登山时的负重甚至超过了担架员。他们无从估计雪山对自己有限体能的巨大消耗,总是想多带些食物,以免让让官兵受饿。
翻过雪山的四团下到山脚的时候,一条深沟挡在了路上,红军官兵沿沟寻找继续北进的路。就在这时,沟口方向传来了一声枪响。
前卫二营营长曾庆林报告说:弄不清是什么队伍,喊话也听不清楚。二营立即展开了战斗队形,四连做好了出击准备。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在望远镜里观察,发现前面竟然出现了一个小村庄,村庄的四周影影绰绰地有不少人在走动,这些人都背着枪,头上戴着大檐帽。这样的装扮黄开湘和杨成武以前从未见过。
司号员用号声联络,对方用号声回答了,但是双方都没听懂是什么意思。
四团派出3个侦察员摸了上去。然后主力部队以战斗队形缓慢前进,一点点地向对方靠近。
对面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了:“我们是红军……”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的3个侦察员一边飞奔而来,一边高喊:“是红四方面军!是红四方面军!”
这一刻,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官兵永生难忘。
那一刻,阳光下的雪山一片金黄,木城沟里的高山杜鹃迎风怒放!
还在中央红军通过彝区向大渡河靠近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命令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第九军军长何畏,率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和第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日夜兼程西进,前往懋功地区接应中央红军。由于双方的电台联络并不通畅,红四方面军接应中央红军的路线只能保证大方向正确。
从理番到懋功150多公里,必须翻越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红四方面军官兵与翻越夹金山的中央红军一样为此历尽艰辛。直取懋功的先头部队是韩东山率领的二十五师。出发前徐向前找韩东山谈了近两个小时,谈话的中心意思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接应中央红军。两军的会合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徐向前说:“你韩东山是四方面军派去迎接毛主席的代表,说不定将来你的名字还能进入史册呢。”徐向前的一番鼓励令韩东山十分兴奋。回来向师里的官兵一传达,官兵们也很激动,有的连队甚至加了餐喝了酒。在向懋功前进的路上,二十五师不断遇到川军的阻击,大小战斗打了20多场,但是为了完成接应中央红军的任务,全师官兵无心恋战,每一次都是把伤员匆忙留下之后就继续赶路。在两河口附近,二十五师拼尽全力击溃了川军邓锡侯部2个营的阻击,然后一路直取懋功。根据行动计划,韩东山命令2个营据守懋功,其余部队向达维方向疾进。二十五师准备翻越夹金山,到宝兴、芦山和天全一带去寻找中央红军。到达达维之后,寒风呼啸大雪漫天,韩东山只好决定大部队暂时休息,命令七十四团团长杨树华带领三营向夹金山接近。三营在到达巴郎地区时与川军遭遇。由于红军兵力少,遭遇战打得十分残酷。三营官兵抱着一定要尽快找到中央红军的决心,奋不顾身地向数倍于己的敌人冲了上去。阻击的川军在被消灭了大半后溃逃,三营营长陈玉清也由于伤势过重停止了呼吸,全营牺牲的官兵多达64人。
6月14日下午,韩东山的二十五师在达维列队欢迎从雪山上下来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稼祥……
在离开达维北去懋功的路上,毛泽东接到了红四方面军发来的贺电:
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政委,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懋功会合的捷电传来,全军欢跃,你们胜利地转战千余里,横扫西南,为反帝的苏维埃运动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历尽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造成了今日主力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础的条件。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
及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启
六月十五日
6月16日,中央红军给红四方面军发出了回复贺电:
张主席、徐总指挥、陈政委并转红四方面军全体红色指战员亲爱的弟兄们:
来电欣悉。中国苏维埃运动二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慌战栗。我们久已耳闻你们的光荣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特此电复。
朱、毛、周、张及中央
野战军全体指战员
十六日
同一天的第二封电报,第一次向红四方面军首长明确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总方针,即“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6月17日,中革军委收到了张国焘、陈昌浩的电报。电报对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总方针表示了疑义,不但不同意红军向东或向北发展,反而提出了向西南更荒凉之地发展的设想。电报档案原文错漏极多,大致的内容是:向东进入四川腹地,北川一带水深流急,敌人已有准备,不容易通过。而沿着岷江北打松潘,地形和粮食等条件也不具备。如果向北发展,那么就要集中主力打青海和新疆。
第二天,由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联合签署的回电发出。电报坚持红军主力必须先控制向北转移的枢纽地带,占领从川北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松潘,“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因此,需要“即下决心”,“立攻平武,松潘”。
两天后,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联名致电张国焘,重申“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实施向陕甘方向的突破,哪怕“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因此请张国焘“再过细考虑”。“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但是如果“认为绝无办法”,那么对向川西南发展的方案可以商量执行。电报最后希望张国焘前来懋功:“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时在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已经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对立。张国焘与中央和军委之间的分歧仅局限于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上。但是,无论从当时的角度还是现在的角度看,张国焘的主张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从懋功往西,是中国最荒僻的雪域高原,大军进入那里前途将是什么?事后,张国焘在行动时,也没有选择这条几乎等于自杀的道路。
6月25日,在抚边村,红军官兵搭起了会场。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土墙上用石灰水书写了“欢迎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万岁!”和“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标语,房屋上挂上红旗,红旗上也写有标语。草地上搭起的讲台四周用松枝镶起了一道绿色的边缘。一切令这个小村庄顿时充满了生气。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从会场步行了3里路,到达一条小路的路口。几千名红军官兵在他们的身后列队完毕。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难以形容的重要时刻。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终于会面了!
(责任编辑:何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