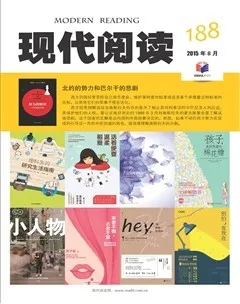父母的婚事
2015-12-29马鼎盛
马鼎盛,中山大学台湾研究所顾问、中外知名军事时事评论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客席研究员、广东省政协委员,著名粤剧演员马师曾、红线女之子。
天下最无奈的事,莫过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其实爹要娶人才是古今中外更无奈的事。在小民百姓家,有了后娘,就有后爹。我爹娶后娘的时候,我大概11岁。为什么大概?因为父母离异,我才六七岁已经跟母亲过了,那位王姓后娘同我总共没有见过几面,从来没说过话。父亲请我吃饭,丰盛的西餐,还教我用银勺喝汤不要碰出声音。我问父亲,王同志(父亲不让我们叫后娘王阿姨)怎么不吃饭。父亲说我爷俩谈天,叫她干啥。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会上,新华社照相,有关人士请我站在王同志旁边,我死活不干。事后一些亲戚朋友提起这件事,还说我小小年纪挺有个性。现在拿起我在父亲遗体旁的照片,看着50年前自己的一脸黑气,才懂得什么是不识大体。这种事在香港媒体的娱乐版报道,触目的标题少不了是“名伶马师曾幼子大闹灵堂”、“马师曾遗体前,幼子与晚娘分庭抗礼”等等,总之是“亲者痛,仇者快”的社会效果。放到今天,一个59岁的盛年男子,事业有成,离婚多年,迎娶一个三十大几的女人,家里念中学的儿子应该没有什么社会压力吧。
“娘要嫁人”的问题对我的刺激极大。当年一副愤怒青年的架势,相信惊动了母亲的领导方面。不记得是北京文化部什么头面人物,找我认真地个别谈话,说你妈妈年纪很轻,应该找个终身伴侣。一番义正词严我听而不闻,不是白眼相向,就是拂袖而去。当年在我眼中,接近母亲的除了油头粉面,就是人面兽心。有的前来搭讪,我肯定叫他下不来台。在那无法无天的岁月,根本不知道自己违犯了《婚姻法》——干预他人婚姻。后来在十年浩劫中,母亲好不容易结了婚,我也算同吃同住了三年。当时那种敌视的立场,有几件事印象很深。外婆同母亲相依为命一辈子,我妈是她的全部希望、荣耀和奉献的祭坛。老太太亲手奉上燕窝、人参、虫草、三蛇这些滋补品炖汤,如今不但要同别人分享,有时我妈还把大部分喂给“那个人”吃。外婆同我们提起“那个人”都愤愤不平又无可奈何。“那个人”从内地调来广东一个文化单位担任副职,该单位一个朋友成了我们的热线小广播。说“那个人”本来提出要做大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长,以为他在华北抗日战争、东北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都是有名的军事记者,殊不知这些老资本都被后来不利的档案记录所抵消。“那个人”屈就的广东某文化单位有不少老红军时代的文人大家,七级八级高干济济一堂。“那个人”只是区区十一级的“三八式”中年干部。热线小广播说“那个人”长期不上班,连工资也不去拿。最损的一句话是反正有你妈养活。年少气盛的我能够忍住,不把话传给外婆听,算是怕气煞她老人家。中越边境战争磨磨蹭蹭那些年,“那个人”跑了几趟广西前线。母亲偶尔给我看了“那个人”写的内参稿子,提到解放军用高射炮打越南人的地下掩体,说是创造性发明,让我对资深军事名记者的最后一点敬意烟消云散。
母亲夹在两个势同水火的男人中间有多么难过,我当时只顾自己的感受,并不懂得为人子的道理。直到1996年,外婆以103岁寿终正寝,母亲孤身一人住在华侨新村的大屋,窃贼多次穿房入户洗劫,母亲被强盗打成重伤。我才醒悟到,妈妈身边没有一个老伴,在情在理都是我们的不孝。所谓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最难;母亲前前后后难了整整48年。
74岁的男子结婚是司空见惯,换成女性又另当别论。40年前妈妈择偶可算艰苦卓绝,如今更是渺茫之极。做儿子的虽然开通,总不方便开口去找后爹,所以谈到“理解”二字,实际作用也就是礼貌层面的。
我们是单亲家庭,没有严父慈母,只有严母。例如我哥哥,当时小三十的人了,娶媳妇还得老娘批准。轮到我谈婚论嫁的时候,能够婚姻自主,对象父母都是“臭老九”,还有海外关系,不过已经是改革开放第三个年头,大不了分开住。此后的大环境、小环境都利于我们母子比较平等对话。1989年我回到香港定居,老婆孩子陆续跟着来。十年后我作为记者采访母亲,这种同事关系一直持续了14年,直到母亲最后的时光。
(摘自花城出版社《马鼎盛自述:我的母亲红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