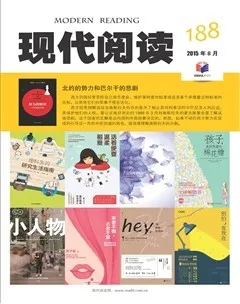南极之行
2015-12-29王静
现在,我站到了南极的土地上。这是2010年底,而2011年就是人类到达南极点100周年。
自从进入南极圈之后,我们就一直住在文森峰大本营,等待机会冲顶。可天公不作美,我们被接连几天的大风雪阻挡,困在了大本营。
因为没有预料到会在文森峰困这么久,组织方预备的卫星电话的电池快没电了,所以打电话需要申请并得到批准才行。这几天我也很少见队友打电话,好像大家已经彻底放下了一切,在这辽阔无边的冰天雪地里尽情享受寂寥和无所事事的乐趣。而我却在为不能回京、不能通过电话处理一些事情而纠结。我心中突然觉得非常迷茫:“我为什么要在这冰天雪地里等待攀登那没有意思的顶峰?”
我们于2010年12月13日下午从北京出发飞往巴黎,然后转机到智利再到蓬塔,一路上大家气势高昂。一队装备精良、衣服上又佩戴着南极标志的队员,每到一处都备受瞩目。
17日离开蓬塔飞往联合冰川的时候,那种匆忙赶飞机的感觉还真像是执行任务中的特种部队。我们乘坐的美国大力神飞机,样子很特别,机舱内到处都是裸露的管道和零件,粗糙得就像没装配完的半成品似的。飞机的前半部是近百人的座位,后半部是敞开的行李舱。飞行时,机舱内声音震耳欲聋,大家都戴着耳塞,彼此用肢体比划着交流。
经过3个半小时的飞行,我们到达了南纬80°海拔710米的联合冰川。吃过晚饭稍作休息就直飞文森峰大本营。因为大飞机无法在文森峰大本营降落,中途还换乘了一架小飞机。几经周折,当我们终于到达文森峰大本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近12点了。这里是南纬78°,早已进入了南极圈,所以是极昼。即使晚上12点太阳依然高悬,光线亮得刺眼。从此我们的生活里就没有了黑夜,到了睡觉的时候,人人都需要戴上眼罩,慢慢习惯在“白天”里睡觉。
初到大本营的第一个晚上,可能是真累坏了,我睡得特别香。第二天早上醒来,看到天空依然还和昨天一样艳阳高照,似乎有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19日,我们就赶到低营地了。按计划我们应该在4天时间内完成登顶并重新回到这里。从大本营前往低营地,海拔从2100米上升到2700米。尽管都是雪坡,但是比较平缓,坡度只有10°~20°。我把大部分装备都放在雪橇里拉着,背上只背了一个登山包,里面放上随时需要的物品。这段距离我们走了5个小时,中午的路餐是一块冰冷的三明治,晚上是煮方便面,在冰冷的环境吃上热乎乎的方便面,感觉还不错。
低营地旁边有山,太阳照射的时间很短。而南极太阳直射与不直射之间,温度能瞬息变化摄氏30度。在太阳直射的状态下行走,不仅衣服很容易被汗水湿透,还要频繁地往脸上和胳膊上涂防晒霜,再捂上头巾,不然可能很快就会被晒伤。而一旦停下来休息,或者没有太阳直射时,则必须快速穿上羽绒服,否则很容易被冻伤。在耀眼的阳光下,冰雪极其刺眼。从进入南极圈的头一天开始,我的眼睛就有些痛。四周全是白雪,又没有黑天,必须24小时戴着墨镜,时刻提防可能出现的雪盲。
到达低营地之后,我们原计划去高营地进行适应性训练,结果被向导告知,未来两天的天气都不好,不适合往高营地攀登。
接下来的两天,天气依然不好。大家在向导的带动下,开始锯雪砖搭建防风雪墙。雪墙砌好后,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这时从高营地撒下了4个人,一位父亲带着他的一双儿女和一个向导。一聊才知道,他们居然是1924年攀登珠峰的传奇人物英国人马洛里的后代。这一家3口曾经在2008年一起由珠峰南坡登顶,现居住在加拿大,女儿23岁,是加拿大最年轻的登顶珠峰的女性。
一直期待好天气等待登顶,只是如今这样的等待和无所事事,的确比真正的攀登还难熬。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无聊的等待加剧了对家人的思念。想念家里那张温暖的床,想念和亲人、孩子们相拥的感觉。越是这样,越是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的孤寂感,就像整个世界都停滞在这冰冷的南极大陆冰盖,而我却被冻成了千年冰人。
时间又过去了一天,到了22日,天气依然很糟糕。大家起得更晚了,现在营地每天只吃两顿饭,一次在中午12点,一次在晚上7点左右,每顿饭都是袋装的方便食品。每天在极冷的环境下,即使不运动,能量消耗也很大,饿的时候就吃些自带的零食充饥。
这天我们下午4点才吃到中午饭。是牛肉米饭,这是进山的第一顿米饭,中国人都喜欢米饭,大家吃得很香。晚上8点多,大家又吃了一顿。尽管是非常简单的方便面汤,为了保证体能,再喝点儿汤还是很有必要,饭后回到帐篷继续看书。在帐篷里戴着薄手套拿着书,不一会儿手就被冻痛了,脚也冻得麻木起来。我赶紧爬起来,穿上羽绒袜套和厚厚的羽绒上衣,然后钻进睡袋里就着热水吃了一块巧克力,这才慢慢暖和过来,然后逐渐在书的催眠中睡去。
再次醒来,已经是23日早上。早饭时,每个人只有少量的鸡蛋,是用方便食品袋包装好的没有蛋壳的鸡蛋,然后再用开水冲一些袋装的麦片或者奶粉,吃完依然是回帐篷看书、写日记。今天是被困在低营地的第六天,如果接下来天气依然不够好的话,我们的食物供给也会出现严重问题。
24日下午,同行的意大利一家3口用雪创作了一棵圣诞树,上面除了有一顶帽子,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大家倒了一些红酒,庆祝即将到来的平安夜。不过向导显得忧心忡忡,因为得知第二天天气依然很糟。他决定去运输一些必需的食物,他告诉我们,估计26日会往高营地攀登。如果这样的话,28日可回到联合冰川。我没有太多的期待,只希望不要再次推迟,因为这样整天闷在帐篷里哪儿也去不了,太熬人了。
外面的风声很大,温度很低,起床时已是中午1点。我穿好衣服去雪墙边小便。突然狂风大作,雪花吹到屁股上,就像无数针刺,小便飞一般呼呼洒在羽绒靴上。我的第一反应是:“坏了,靴子肯定全湿透了。”此时,风雪扑打在脸上,眼睛都无法睁开。我急忙提上冰冷的裤子,低头一看却发现,刚才我的担心实属多余,被风吹洒在靴子上的小便居然全部结成了冰粒。我一手捂着脸,一手捂着羽绒服,快速跑回帐篷,整理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
昨晚狂风,我们的炊事帐篷被狂风吹塌了,今天没法再做饭。今天已经是被困在低营地的第八天,比计划的攀登时间超出了太多,食物供应紧缺,长时间吃不到一点新鲜蔬菜。再这样下去,一定会缺乏维生素,体能也是个问题。
导游说,明天天气应该转好,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整队将前往高营地,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在27日登顶,28日可下撤到大本营,煎熬的日子终将过去了。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欣喜若狂,好久没有这么强烈的开心感觉了。
终于,26日凌晨12点多,我们出发了。
早晨6点,到达了高营地。高营地在一个相对的凹地,前面是直壁悬崖。站在悬崖边望着远方,给人无限遐想。南极的雪山和云雾缭绕相接在一起,蓝天和白云之间还夹着彩云,不断变幻,已经分辨不清天空云海和南极冰盖,天地似乎连在了一起,向四周无限延伸,仿佛可以穿越时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和心境下,才能感悟到南极的冷艳与俊美。
我们在高营地准备第二天冲顶的时候,遇到一位尼泊尔向导带着一位70岁的英国人登顶后下来,他们往返用了12小时,完全可以想象,攀登这座山并没有多大难度。果然,我所在的第一队登顶只用了5个半小时,下山只用了2小时10分钟,而且攀登过程中一点风也没有,一直都是太阳高照。酷热的行进过程中可以脱衣服,可是脚上穿的御寒鞋袜却没有办法脱卸。由于脚热,下撤过程中袜子变潮湿,脚长时间浸在潮湿的环境里,行走起来很容易磨出泡。下午回到营地,每个人的脚都有不同程度的磨伤,我脚上被磨起了3个泡。
我们简单收拾了一下,在高营地就开始商量徒步滑雪到南极点的事。
因为在低营地等了8天,接下来徒步南极点的时间就显得非常紧张。在4天的时间内,如果按以前的计划行走1纬度(113公里)的距离,几乎是很难完成的任务。由于队员对徒步距离的意见不统一,有人建议改为徒步七八十公里,最后干脆说徒步50公里,四舍五入就当100公里,也就是大家说的1纬度了。在讨论的过程中,组织方介绍,事实上,之前国内很多人也没有完成真正的1纬度,能完成100公里已经非常不错了。我和肖远一直坚持徒步走满1纬度,也就是113公里,到南极点,而不是仅仅走一小段路程敷衍了事、自欺欺人。我们为这事讨论了好久也没达成一致的结论,决定一边下撤一边再做安排。
次日早上,我们从海拔3800米的高营地下撒到大本营,在那里乘坐飞机,于当晚7点顺利到达了联合冰川大本营。回到联合冰川之后,我们接着讨论徒步南极点的方案。我们最后决定,29日起程,计划用4天半的时间徒步75公里到达南极点,这样的决定并不是我满意的结果。
(摘自北京出版社《静静的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