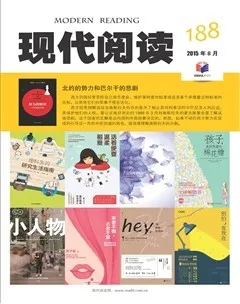晚清:天朝对媒体的态度
2015-12-29汤传福等
不管天朝的体制上下多么嫉视报纸,媒体时代还是在他们不情不愿中无可阻挡地来了,在不期而至的媒体浪潮面前,当权者左支右绌,应对无方。
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来了基督教,也带来了报纸。但天朝对这个舶来品的威力并不清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天朝对报纸的认识仅限于《邸报》。尽管新闻史家说《邸报》是中国最早的报纸,但它只与官阅不与民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就像不能把高俅擅长的蹴鞠说成是足球一样。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遥远的南洋出生,被偷偷运往内地,散发给不特定的大众,而高高在上的《邸报》,只有统治阶层才有资格阅读。当第一批《察世俗》在天朝的土地上被散发,意味着天朝的媒体生态进入了近现代,从小众传播进入大众传播,但这个巨大的象征意义在当时无人知晓。
在天朝的统治逻辑里,一切都必须在可以掌控之中,包括信息的发布与流通。咸丰三年,江西巡抚张芾奏请内阁“刊刻邸抄增加发行量”,方便底层民众深入学习、深刻领悟中央精神,可惜在朝廷眼里这道奏章纯粹是找抽,皇帝批示:“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在天朝统治者眼里,官办报纸给官员阅读是无可置疑的,何必刊刻出版让一般小民也能预知政事呢?忙于剿灭太平军的天朝还没有政务透明的概念,但天威莫测的好处他们很清楚。
天朝对自己完全掌控的《邸报》没有扩大发行的兴趣,文网森严的结果是自己对大众报纸毫无概念,忽略了在开放口岸出版的洋报纸。直到报纸的威力让他们浑身不适时,他们才清楚报纸对他们的危害不亚于鸦片,鸦片戕害了臣民的身体,而报纸“毒害”了臣民的大脑,撼动了帝国的意识形态。
天朝对报纸的漠视和无知并非特例,人类对新事物的认知总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在18世纪的西方,人们同样认为报纸是微不足道的事物,即使睿智者如卢梭,对刚刚出现的报纸也是一脸不屑,1755年他曾以鄙夷的口吻说:“一本周期性出版的书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一本既无价值又无益处的昙花一现的著作。文人们以轻率的态度诵读这些东西,仅仅是给未受教育的女人们和为虚荣心所驱使的蠢人们听的。”与大哲卢梭比起来,天朝的懵懂并不过分——你不能要求任何人对头脑中没有概念的事物有着透彻的认识。
因为对近代报纸概念的懵懂,天朝不能清晰地将办报界定在一个国家的主权范围内。而另一方面,报纸进入中国搭载的是传教权的顺风车,颇有瞒天过海的意味。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允许美国人和法国人在通商口岸设立教堂。订约后,法国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两年后,道光帝批准弛禁天主教,按照与英美两国约定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基督教(新教)随之照行。教会报刊因允许传教而合法进入中国,但刊载的内容并不限于宗教。一开始教会报刊只是附载一些新闻和西学,但这部分内容因为受到欢迎,比例逐渐增大,成为报刊的主要内容,宣教的内容反而隐而不彰。
在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是传教士伍德等在1861年创办的《上海新报》,这是一份典型的商业报纸,对太平军和清军的战事多有报道,很受读者欢迎。在此前后十年,上海的中文新闻纸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直到1872年才遇到了竞争对手《申报》。《申报》报道的主要内容是商业和政治,该报每天在头版头条发表“论说”,开创了报纸论政的先河。至此,报纸在天朝走过了一条由外文到中文,由传教到商业进而到新闻到论政的道路,成长为严格意义上的大众中文媒体。
大清政府对越来越多的中文报纸的出现反应迟钝,和邻邦日本比较起来,让人唏嘘。在美查创办《申报》的同一年,他的同胞布莱克在东京开办了一份日文报纸,四年后,此人又办了一份《万国新闻》。这份报纸刚出版,就遭到日本同行的强烈抗议,认为这是对日本主权的侵犯,危及他们日文报纸的销售,江户警察也立即禁止日本人销售该报。在外交上,日本外务大臣与英国全权大臣巴夏礼交涉,要求关闭布莱克的报馆。巴夏礼为此制定了一个法规,规定“凡是在明治天皇陛下领土之内印刷或出版报纸的英国人都将被认为是有罪或者犯法”,这使得外国人在日本办报的行为立即终止,日本成功狙击了洋人在本国创办日文报纸。
反观清政府,一直没有反对洋人在中国办外文报纸,对外商办华文报纸听之任之。在清廷眼里,报纸不过是传教的工具,报馆不过是洋人经营的一个企业。直到中外发生争端,洋人办的报纸偏袒本国,曲直混淆,少数人才意识到办报应是一国主权之内的事,“此事不载通商之约,本属中国自主之权。”
报馆不同于一般企业,关注政治是其发展的必然道路,政治红线迟早要踩上。《申报》创办之后,尽管馆主美查公开声明宗旨在营业牟利,但语涉政治引起清廷抗议还是不可避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曾发给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一封照会,其内容值得解读。照会引用了一段上海道台给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公文:
查上海英国租界有英商美查于上年创设申报馆,所刊之报,皆系汉文,并无洋字。其初原为贸易起见,迨后将无关贸易之事逐渐列入,妄论是非,谬加毁誉,甚至捏造谣言,煽惑人心,又复纵谈官事,横加谤议,即经职道函致英领事饬禁,未允照办。
照会要求威妥玛饬令英国驻上海领事:“凡不关贸易之事,不准列入《申报》。”奕虽然对《申报》用中文出版并不高兴,但也未表示抗议,其具体要求仅仅是不准报道“不关贸易之事”。奕的态度代表了清廷对报纸的看法,只要洋报纸不关心政治,不去触及天朝的统治,天朝与洋报纸井水不犯河水。
HaKx8ybmZ/8e1x7q/g09gFPkzhcC4VoVNMiMHYJgArg=像这样通过外交途径抗议报纸报道政治的举动并不常见,更多的反应体现在朝廷的谕旨和大臣的奏折上。《中国教会新报》和《汇报》曾因转载香港报纸上的朝廷密旨而让清廷大为恼火,清廷为此下旨严查:“军机处封发寄信谕旨,各省奉到后,自应加意慎密,况系中外交涉事件,岂容稍有漏泄?乃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密寄沈葆桢等谕旨,上海新闻纸内竟行刊刻,究系何人泄露,著李宗羲严密确查,据实复奏,毋得稍涉含混。”但这条谕旨要求查办的不是报纸,而是为报纸提供信息的泄密者。
清廷对租界里的报纸无可奈何,而地方官员的反应则是千奇百怪,甚至让后人啼笑皆非。1882年1月,上海会审公廨接江苏学政黄体芳的命令,在《申报》馆门前张贴了一张告示,告示严厉谴责《申报》发表《论院试提复》的论说,以及批评一些地方乡试弊端。黄学政认定这篇论说是针对自己,是童试被黜之家散布流言,希图泄忿,而报馆受其委托,“为之推波助澜”。他还威胁说要移文咨本省各大宪转饬地方官,按律严办。此外,《申报》曾经有个《时人行踪》的小栏目,在报纸上并不重要,因为非常重要人物的行踪都会在重要版面详细报道,不会放在这个小栏目里。《申报》在创办不久刊登有江南提督谭碧礼来沪的消息,结果谭碧礼遣人前来交涉,禁止刊载他的消息,又行文总督,大肆诋毁。
学政登门问罪虽然过分,但还可以理解。报道谭大人正常的公务活动,内容并非负面,谭大人为何也要来交涉一番呢?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官场人物漠视甚至鄙视报纸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谭大人看来,名字见报简直是一种羞辱。
清廷管不了洋报纸,但管得了自己的子民。黄体芳严谴《申报》,却让上海前任道台办的《新报》躺着中枪。朝廷以《申报》捏造事端、眩惑视听为由,下旨查办上海报纸,新任上海道邵友濂不敢碰洋报,却将《新报》封了。在广州,《广报》因登载某大员被参一折的消息,结果被粤督所封,报馆被迫迁入租界,改名《中西日报》,挂名英商继续出版,品评时事反而更为大胆。
不管天朝的体制上下多么嫉视报纸,媒体时代还是在他们不情不愿中无可阻挡地来了,在不期而至的媒体浪潮面前他们左支右绌,应对无方。直到甲午战争之后,媒体言说政治已成为常态,天朝才有极少数人去思考报纸也可以为我所用,舆论阵地你不去占领就会被别人占领。郑观应和陈炽都提出中国人要自己办报馆,洋人在中国办报只能用洋文,而王韬则更进一步,不仅要办中文报纸,还要办洋文报纸,这样当中外发生争端时就有舆论阵地去影响洋人。
然而,天朝对这些先知先觉的建言听不进去。开放报禁,意味着朝廷承认报纸所代表的公众舆论权的存在,而这项公权力与专制皇权是不可能兼容的,大一统的皇权体系是不可能允许舆论权节外生枝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