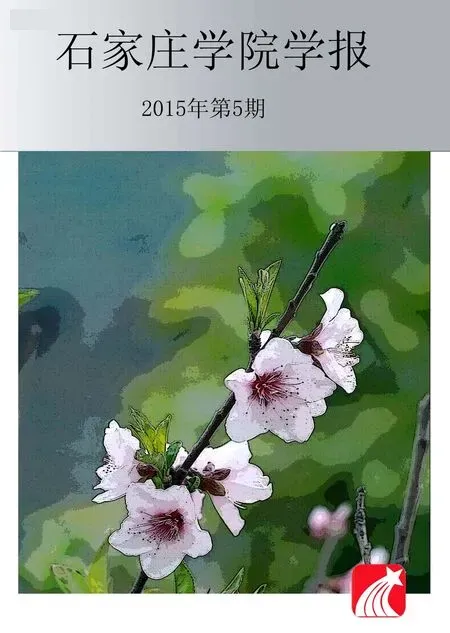试论《穷达以时》思想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演变
2015-12-29陈鸿超
陈鸿超
(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100084)
试论《穷达以时》思想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演变
陈鸿超
(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100084)
郭店简《穷达以时》的成文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代表了战国时人对人生穷达的新思考。自战国入秦汉以来,学人在继承《穷达以时》理性思想的同时,在应对方式上逐渐分化为入世与出世两种思想倾向。二者处世态度虽有不同,但均承认外在机遇的客观随机性,强调以内在自省来应对人生之境遇。
穷达;理性;历史背景;时代演变
对于人生穷达,古人很早就有过深入思考。郭店简《穷达以时》作为地下出土的此类文献,在文句与思想上均能与诸多传世典籍关联。它们之间的联系实则反映了先哲在该问题上的传承与发展。本文即抓住“穷达”这一核心命题,比较《穷达以时》与各类文献的异同,以期对穷达观念的历史背景与时代脉络作一简要的梳理。以下不揣谫陋,望求教于方家。
一、与相关文献的时代关系
《穷达以时》自公布以来,学者对于释文、简序多有激烈讨论,现以整理者整理为基础,[1]145-146结合各家意见,将该篇文献通行释文胪列如下:
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无其(简1)
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舜耕于历山,陶埏(简2)
于河浦,立而为天子,遇尧也。咎繇衣枲褐,冒紩蒙巾,(简3)
释板筑而佐天子,遇武丁也。吕望为臧棘津,守监门、(简4)
棘地,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尊而为天子师,遇周文也。(简5)
管夷吾拘囚梏缚,释械柙而为诸侯相,遇齐桓也。(简6)
百里转鬻五羊,为伯牧牛,释鞭棰而为命卿,遇秦穆。(简7)
孙叔三舍期思小司马,出而为令尹,遇楚庄也。(简8)
善否,己也。穷达以时,德行一也。誉毁在旁,圣之贼之。梅伯(简14)①陈剑、陈伟等先生将简14同简9编联,于义见长。参见陈剑《郭店简〈穷达以时〉〈语丛四〉的几处简序调整》,载《国际简帛研究通讯》第二卷第五期;艾兰、邢文主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317页;陈伟《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180页。
初醓醢②“醓醢”的释读参见赵平安《〈穷达以时〉第9号简考论——兼及先秦两汉文献中比干故事的衍变》,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2期。,后名扬,非其德加;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简9)
衰也。骥厄张山,骐入于驿棘,非无体状也,穷四海,致千(简10)
里,遇造故也。遇不遇,天也。动非为达也,故穷而不(简11)
□□□为名也,故莫之知而不吝。芷□□□□□(简12)
□□□□嗅而不芳;璑珞瑾瑜包山石,不为□□□□(简13)
不埋。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敦于反己。(简15)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了其大量文句能与《荀子·宥坐》《韩诗外传》《说苑·杂言》《吕氏春秋·慎人》等诸多传世文献对应。故此,一些学者通过《穷达以时》诸如“天人之分”的线索,探求这些文献的成书先后①如李学勤先生认为包括《穷达以时》在内的各类文献以时代编排为:《穷达以时》→《庄子·让王》→《荀子·宥坐》→《吕氏春秋·慎人》→《风俗通义·穷通》→《孔子家语·在厄》。参见李学勤《天人之分》,载郑万耕主编《中国传统哲学新论》,九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而池田知久先生则认为《穷达以时间》成书偏晚,当在《荀子·天论》与《吕氏春秋》编撰年代之间。参见池田知久《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研究》,曹峰译,《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4-168页。。这种思想论证暗含一个假定,即假定古代社会思潮呈线性的进化发展。然而,思想的发展脉络具有复杂性和多向性,并非只具有单一的直线性。以直线型思维建立在假设、推理和考据之上,认为现象与现象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通过周密的推导论证,最终得出唯一性结论的研究范式虽有很大启示,但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2]尤其值得怀疑的是,用这套方法考证某一较短历史时间内的文献成书先后是否行之有效。所以,《荀子》《吕氏春秋》等这些战国中晚期文献是难以单纯通过某些词句来界定其时代先后的。然而,倘若我们反向思考,在已经明确的时代前提下,不去计较小范围的时间段,以此去探求文献本身的价值及其所处的时代脉络似乎更具意义。基于这一想法,我们把与《穷达以时》有直接关联的文献分为战国、西汉、东汉三组,见表1。

表1 《穷达以时》相关文献成书时代表
这三组文献时代明确,组内的文献虽无法确定其准确的成书年代,但大体可认定为同一时期。
需要提及的是,虽然书中的相关语句可能抄撮自更早的材料,但通过词句的改写与重新编排实质上代表了编撰者的主旨思想及其反映的时代特征。所以,通过对《穷达以时》内在思想的讨论,我们将纵向、横向分析和阐释穷达观念的历时发展与共时联系。
二、对成因探求的理性发展
自原始社会阶层分化以来,古人可能很早就对“穷达”产生思考。商代之前无文献可考,而我们知道,商代尚鬼神上帝,甲骨卜辞反映的是由神灵主宰祸福。以此推测,商人或许把个人的荣辱得失也视做神灵的安排。但可以肯定的是,将个人穷达取决于“天”的理论应溯源自周初之观念②商代甲骨卜辞中的“天”没有作“上天”之义,“天”之观念是周人提出来的。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81页。。周人以天命观作为国家基础,如不论是西周铜器铭文,还是传世文献,均不断提及文王膺受天命③如大盂鼎铭文即有“……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二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0页。又《诗·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参见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8页。《诗·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参见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83-584页。。其旨在说明,文王得获天命主要是依靠德行。若从个体而言,这也成为了文王得以发“达”的理据。穷达取决于“天”,“天”又依德而行,这大概逐渐成为了周人的主流观念。然而,随着西周的崩解,时人开始怀疑“天”是否公正地依照德行标准评判,如《诗经·大雅·瞻卬》:“天何以剌?何神不富?舍尔介狄,维予胥忌。”[3]578又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襄仲杀死了太子恶和公子视,夫人姜氏怨天不惩④《左传》文公十八年:“夫人姜氏夫人,大归也。将行,哭而过市曰:‘天乎,仲为不道,杀嫡立庶。’”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32页。。即便在一些文献中,“天”的绝对权威性依旧存在,也很难清晰看到“德”所起的决定作用。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中载: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
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4]396
虽然“天”还在依旧主宰人事,但“天”为何不让兴宋,大司马固只简单地归结为“天之弃商已久”的神秘附会,并未从现实的德行进行解释。当然,如果我们把《左传》视为战国的作品,至少可以说“天”的神学信仰至战国仍盛不衰,甚至传统的天德观念还在继续延续⑤例如在《国语》等这类说教式文献中仍不乏其例,如《国语·周语中》单襄公所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国,无从非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参见韦昭《国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4页。。但这里要说明的是,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对天德观念的怀疑实则展现了传统观念与现实社会的矛盾,这种社会心理的纠结在乱世动荡中变得日益激烈。正在此背景下,当孔子厄于陈蔡时,子路才有“君子亦有穷乎?”的有感而问,以及后来诸子对此事件富以自身思想的加工⑥《论语·卫灵公》提供的原始故事情节是:“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参见阮元校刻《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 516页。子路所问实质上代表了当时社会相当一部分人对“有德者必达”传统观念的怀疑。。
就《穷达以时》而言,开篇中心句“有天有人,天人相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中“天”的概念显然承袭自周初以来的思想观念。对于“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之思想关系,学者多有详尽论述,兹不复赘述。而我们需看到,对比先前,这里“天”的内涵开始有着超越道德属性且更为现实的界定。
整体来看,《穷达以时》中主宰“穷、达”的“天”被分解为“世”“时”。这两个概念,作者也许无意作形式上的区分,但事实上,它形成了两个逻辑层次,从而把征引的历史典故分为两组。从简2到简8用排比方式引述的历史故事无一不是围绕“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展开的。“世”的概念似乎等同于我们今日宏观的社会环境,即当世有无明主。如简文所言,正因有尧,“耕于历山,陶埏于河浦”的舜才得以“立为天子”;正因有武丁,“衣枲褐,冒紩蒙巾,释板筑”的傅说才得以“佐天子”;正因有文王,“臧棘津,守监门、棘地,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的吕望才得以“尊而为天子师”;正因有齐桓公,“拘囚梏缚,释械柙”的管仲才得以为“诸侯相”;正因有秦穆公,“转鬻五羊,为伯牧牛”的百里奚才得以为“命卿”;正因有楚庄王,“三舍期思小司马”的孙叔敖才得以“为令尹”。可以说,这些贤才之前的“穷”得以逆转为日后的“达”,遇“世”是前提。
而从简14开始,简文在正式提出“穷达以时”观点之后又引述了“梅伯”与“伍子胥”两个典故:“梅伯初醓醢,后名扬,非其德加;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衰也。”与之前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梅伯“初”与“后”、伍子胥“前”与“后”境遇的差别更强调的是“穷达”遇“时”的转化,因而这里的“时”更多层面的是一种时局的指代。
总之,自周以来盛行的“天”,经过了《穷达以时》的修正,内涵变得十分明晰。“天”不再完全依“德”来评判命运,但亦非悲观无法捉摸,而是有了理性的探究与思考。即在“天”“人”相分之“天”的层面里,把“天”视为唯物的外在。而同期有直接关联的战国文献虽没有这么系统的表述,甚至有不同的主旨倾向,但它们均去除了“德”性之天和“神”性之天,如《荀子·宥坐》是借孔子厄于陈蔡表述了对“为善者报之以福,为不善者报之以祸”之“天”的怀疑与反思:
孔子南适楚,厄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弟子皆有饥色。子路进而问之曰:“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孔子曰:“由不识,吾语女。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吴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孔子曰:“由!居!吾语女。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句践霸心生于会稽,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5]621-622
《庄子》对孔子厄于陈蔡的典故有多处记述,其中,只有《庄子·让王》涉及了“穷达”本身问题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甚至未涉及到“天”: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犹弦歌于室。颜回择菜于外。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应,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人也。召而来,吾语之。”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娱于颍阳,而共伯得志乎共首。[6]973-975
而颇受道家影响的《吕氏春秋·慎人》重新加入了“天”,但此处决定“功名大立”的“天”狭义地被等同于概念清晰的“时”:
功名大立,天也。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夫舜遇尧,天也。舜耕於历山,陶於河滨,钓於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贤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泽之湛滞壅塞可通者,禹尽为之,人也。夫汤遇桀,武遇纣,天也。汤、武修身积善为义,以忧苦於民,人也。
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堀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於冻馁之患。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舜自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见尽有之也。尽有之,贤非加也;尽无之,贤非损也。时使然也。
百里奚之未遇时也,亡虢而虏晋,饭牛於秦,传鬻以五羊之皮。公孙枝得而说之,献诸缪公,三日,请属事焉。缪公曰:“买之五羊之皮而属事焉,无乃天下笑乎?”公孙枝对曰:“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忠也。君为明君,臣为忠臣。彼信贤,境内将服,敌国且畏,夫谁暇笑哉?”缪公遂用之。谋无不当,举必有功,非加贤也。使百里奚虽贤,无得缪公,必无此名矣。今焉知世之无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务博也……[7]336-338
总之,这三类文献折射的不管是天人相分,还是天人合一,对穷达的探索均摒弃了天的“善恶”评判,其代表着对“天”认知的理性化历程。同时,除了《穷达以时》有明确强调“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天人关系的总纲外,这些文献在开头均没有这样的总论。如果我们再把汉代的文献加进来详查,会发现儒家在穷达的认知上,天的概念在逐渐淡化。如《穷达以时》中“遇不遇,天也”,甚至被直接替换成了“时”。如:
《荀子·宥坐》:“夫遇不遇者,时也。”[5]622《韩诗外传》卷七:“遇不遇,时也。”[8]244《说苑·杂言》:“遇不遇,时也。”[9]422-423
《孔子家语·在厄》:“夫遇不遇,时也。”[10]138并且,这些文献除了“时”“世”外,还引入其他如“材”“人”“命”来客观解释穷达的成因,如:
《荀子·宥座》:“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5]622
《说苑·杂言》:“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9]422-423
《孔子家语·在厄》:“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
肖者,才也……为之者,人也。死生者,命也。”[10]138
实际上,池田知久先生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与《穷达以时》相比,四种文献使用‘天人’关系思考世界之思维方式已经稀薄化。”[23]99但可惜他没有进一步细究其原因。而从上述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解释穷达产生的根本原因上,周初以来德性与神性的“天”被扬弃。战国时出现了一批学人,他们或改造“天”的含义,或淡化天人的思考方式。到了汉代,儒家文献甚至逐渐不再借用“天”这样的词汇,即便在道家影响下的文献中,“天”也成为无意志控制的存在而始终没有回归到拟人化的神性主宰。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共时与历时的脉络来看,从西周到东汉,对穷达成因的思考,是有一条理性线索可循的。
三、应对方式的演化
在《穷达以时》中,决定穷达的终究原因在于理性的天,其表现为“遇不遇”。如何得“遇”?在之前传统的天人观念里,或不加解释,或在解释中隐射各类“神异”思维。如新出清华简三《说命》记载傅说得遇武丁:“惟殷王赐说于天。”今遗存的《书序》云:“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得求诸野。”[12]122又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晋公子重耳逃难至楚,楚成王云:“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4]409在这些文献中,知遇全然不为人控,它们把“遇”解释为颇具宿命观念的“天”。
而在《穷达以时》里,“天”主导下的“时”“世”“遇”均无涉及神性,它的发生似乎具有客观的随机性。所以作者认为在明晓“穷达以时,幽明不在”①幽明在原简中作“”,“”字从子幽声,读为“幽”当无误。幽明于此是为何意诸家解释未明,其实幽明一词,传世典籍习见,常与阴阳、鬼神并称,如《周易·系辞传》:“仰以观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周易》这条李锐先生即已指出,参见李锐《郭店楚墓竹简补释(二)》,《古墓新知》,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又《史记·五帝本纪》:“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张守节正义:“幽,阴;明,阳也。”在后代的典籍中,“幽明”更常等同于“鬼神”,如李白《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皇唐叶有六圣,再造八极,镜照万方,幽明咸熙。”王安石《全椒张公有诗在北山西庵僧者墁之怅然有感》:“幽明永隔休炊黍,真俗相妨久绝弦。”蒲松龄《聊斋志异·神女》:“家君感大德,无以相报,欲以妹子附为婚姻,恐以幽明见嫌也。”根据这些文献释义,再结合上文的论述,“幽明”一词于简文可泛指阴阳鬼神一类的事物,故“穷达以时,幽明不再”即表达造成穷达的原因是以客观的“时”,而不是以“鬼神幽明”,这样的解释似更为通顺。的情况下,需要“敦于反己”,即在否定神明宿命论同时,强调人为的努力:
善否,己也……遇不遇,天也。动非为达也,故穷而不□□□为名也,故莫之知而不吝。
原本善恶精神意义上的“天”被剥离出来后,客观物质性“天”的随机意向便无法捉摸,所以人当及力所能及之事,做好自己的修为,不在意不为人意左右的外在。不过如此一来,在天人相分的背后,便存在一个潜在的纠结,即个人德行与穷达无法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
梅伯初醓醢,后名扬,非其德加;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衰也。
这导致了《穷达以时》在“敦于反己”的目的上存在着“动非为达也,非为名也”的出世思想。于是,在《穷达以时》作者的世界观里,探清穷达动因的同时,由此伴随而来的纠结似乎未得到完全解决。不过,在另外一些文献里,对穷达的处理方式则更为彻底,从而分为两种思路,如穷达不为功德名利的出世精神,在《庄子·让王》中更被得到推崇,并把它作为一种心安理得之“乐”:
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娱于颍阳,而共伯得志乎共首。[6]975
并且,《庄子》甚至借儒家的孔子之言改变之前人们对于“穷达”的衡量标准: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6]974
上述思想去除了“穷达”的社会物质化差异,使得“达”不再受外在因素的限制,完全可依人主观精神达到。这一人生观在后来道家影响下的文献中得到进一步延续,如《吕氏春秋·慎人》《风俗通义·穷通》多采《庄子·让王》之言,其中便有与上几近相同的句子。不过,“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实际上是在概念上作了巧妙的规避,从根本上逃避了社会层面上的“穷达”议题。然而,面对同样的问题,在《荀子·宥座》中却显得积极入世:
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5]622
《荀子》明确提出了“博学深谋,修身端行”是为了“以俟其时”。其暗含的话语是:君子不仅要做好自己,也要以立足社会为目的,等待时机,随时准备机遇的来临。到汉代,大多数的儒家文献积极应对穷境的做法变得愈加具体,如:
《韩诗外传》卷七:“为穷而不困,忧而志不衰,先知祸福之始,而心无惑焉。故圣人隐居深念,独闻独见。”[8]245
《说苑·杂言》:“为穷而不困,忧而志不衰,先知祸福之始,而心而惑焉。故圣人之深念,独知独见。”[9]423
二者均倡导学习圣人“不困、志不衰、知祸福、心无惑”的乐观精神,而东汉《孔子家语·在厄》所记述的孔子与子贡的言论更从侧面表现出入世之倾向:
子路出,召子贡,告如子路。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子曰:“赐,良农能稼,不必能穑;良工能巧,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赐,尔志不广矣,思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问亦如之。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后见君子。”
孔子欣然叹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10]135
从这段孔子对子贡的言论来看,要求儒士即便身处穷地,志要广、思要远。而子贡所言“夫子推而行之”,更具有不畏困境、积极进取之意。
综上,在穷达应对方式上,到了战国时期产生一种思潮,均强调做好属于“人”范围内的事。但是,道家讲求心不为穷达所动以规避无法控制的外在因素,而儒家中的一脉开始淡化“天”的作用,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加强为积极进取的精神,以达到志不衰、心无惑、俟时而出的精神状态。
四、余论
作为堙没千年的地下文献,郭店简《穷达以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与传世文献对照的战国文本。通过上文对它们思想关系的梳理,我们更可清晰地了解到“穷达”观念演变的时代脉络,由此推测其思想成因及影响。
首先,东周以来,社会发生重大动荡与转型,任何个人的命运都可能在历史瞬息的变化中沉浮不定,社会心理随即进入了对前途穷达的忧虑。当原始的天人宗教道德论无法说服现实时,至少社会精英中有一部分人开始对此产生怀疑与反思,如可从上博简《鬼神之明》中窥见:
今夫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则以其赏善罚暴也……[13]310
学者指出,无论年代还是出土地点,上博简与郭店楚简都很相近。以《鬼神之明》作为一种思想背景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穷达以时》中的天人关系。《穷达以时》虽还沿用“天”的概念,但已转化为理性的“天人相分”。它摒弃“天”的宗教人格属性和道德属性,将其作为客观随机的外在因素。这种思潮不限于儒家,还存在于道家等诸家文献中。而“天人”关系之思维方式在后代如《荀子》《说苑》《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在厄》已日趋稀薄化。故从整体上看,“天”在“穷达”思考中从神学概念上剥离,再到消亡,正是一条理性化的道路。
其次,在应对穷达的方式上,《穷达以时》最后提出“敦于反己”,即讲求内在的自省,这符合儒家的一贯作风,如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14]1513即是如此。这种做法被后代儒者延续发扬,并且愈加具体与积极。从“天人相分”“敦于反己”到“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再到“推而行之”,人的主体作用在不断加强。而另一方面,《穷达以时》也包含一些出世思想,这在道家文献中展现得更为深刻彻底,其讲求“穷达”皆乐,规避了社会层面上的“穷达”认定,以求得精神上的洒脱。
综上,战国至秦汉,对穷达的思考从历史的纵轴来看是一条理性的发展道路,西周“天人”观念到战国时得到一些学人的改造与扬弃,至汉代进一步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理性高度。而从历史横轴来看,对穷达成因的理性认知产生了两种应对方式,道家或受道家思想影响下的文献,追求穷达如一,超然世外,以此达到在精神上的自由逍遥;而儒家这一脉秉持孔子以来的乐观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加强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更具有积极进取的入世倾向。
[1]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2]曹峰.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刍议[J].社会科学,2012,(11):122-127.
[3]阮元.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许维遹.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
[8]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0]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M].上海:上海书店,1987.
[11][日]池田知久.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研究[M]//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M].上海:中西书局,2012.
[13]马辰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4]阮元.论语注疏[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责任编辑 程铁标)
An Analysis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Evolution of Thought from Qiong Da Yi Shi in Guo-dian Tablet
CHEN Hong-chao
(Department of Histor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84,China)
The writing of Qiong Da Yi Shi(《穷达以时》)in Guo-dian Tablet has its unique historical background,which shows people’s new thinking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predecessors’rational ideas,scholars’thoughts had differentiated into active and passive attitudes.Although they were different,both admitted objective of randomness in outward chance,and emphasized importance of inner introspection to face life’s challenges.
consensus;rationality;historical background;evolvement of times
K207
:A
:1673-1972(2015)05-0011-06
2015-05-10
陈鸿超(1987-),男,浙江温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