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运用经方治疗内伤杂病验案举隅
2015-12-22陈国宁,王健
王健运用经方治疗内伤杂病验案举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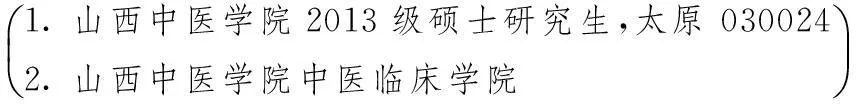
【关键词】王健;内伤杂病;经方;验案
通讯作者:陈国宁1王健2
收稿日期(2014-12-11)
王健,临床医学博士,山西中医学院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第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工作继承人。从事中医内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18年。在临床工作中遵经方之义,运用经方治疗各种内伤杂病效如桴鼓,兹举例如下。
嗳气
患者某,男,58岁,2014年9月25日初诊。自诉:嗳气 1年余,无论空腹及餐后未有缓解之势,餐后尤甚,伴烧心、反酸,纳差,近1年消瘦10余斤,胃脘部如有气阻,偶有疼痛,精神欠佳,寐可,大便干硬,1~2日一行,小便可,舌淡红,苔薄白,脉沉弦。1年前省会某医院胃镜检查示:反流性食管炎。中医诊断为嗳气;证属肝胃不和,胃气上逆;治以疏肝和胃,理气降逆。方用四逆散加味。药用:柴胡10 g,白芍12 g,枳实15 g,乌贼骨30 g,浙贝母15 g,苏梗10 g,黄连6 g,吴茱萸3 g,瓜蒌20 g,砂仁(后下)6 g,甘草6 g,生姜6 g。6剂,水煎服,日1剂,早晚2次,空腹温服。
2014年10月2日二诊:诸症减,纳稍增,大便日2次,舌质红,苔微黄,脉沉。药用柴胡10 g,党参15 g,生白芍12 g,枳实15 g,陈皮10 g,半夏9 g,黄连6 g,生白术15 g,麦冬15 g,百合30 g,乌药10 g,丹参15 g。2剂,水煎服。服药方法同上。
2014年10月4日三诊:晨起嗳气,餐后反酸,烧心,症状又同首诊之前,纳一般,寐可,大便正常,舌质红,苔薄微黄腻,脉沉滑。拟用降逆化痰,理气和胃之品。药用柴胡10 g,姜半夏9 g,黄芩10 g,太子参15 g,旋覆花(包煎)12 g,代赭石(先煎)24 g,浙贝母(捣)15 g,乌贼骨30 g,陈皮10 g,茯苓15 g,瓜蒌20 g,郁金15 g,蒲公英30 g,甘草6 g,生姜6 g。6剂,水煎服。服药方法同上。
2014年10月11日四诊:诸症减,大便偏干,舌红苔薄,脉沉滑。上方加苏梗10 g。6剂,水煎服。
2014年10月18日五诊:症大减,患者心情畅快,纳增,寐可,二便调,舌边红苔白,脉沉滑。继用上法,5剂,水煎服,以巩固疗效。
按:嗳气是指胃中之浊气上逆,出于咽喉而发出的声音,又名“噫气”,正如《灵枢·口问》所注:“寒气客于胃,厥逆从下上散,复出于胃,故为噫”[1]。多见于反流性食管炎、慢性胃炎和功能性消化不良。病者初来,王健教授详询病情后得知患者曾多方求医,却久治未愈,故思虑重重,苦恼至极,就诊时面容愁苦,言语中恐重疾加身,故辨为肝胃不和证。肝主疏泄,若肝气郁结,气的升降开合不利,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致胃气失和,浊气不降,气机阻滞,故嗳气、反酸且上腹部时有疼痛。肝气疏泄失职,影响脾之运化,故出现纳差,消瘦。亦为肝胃不和之象。王健教授拟用疏肝和胃、理气降逆之法,方用四逆散疏肝和胃,佐以乌贝散以制酸止痛;合用左金丸清肝解郁制酸;佐苏梗理气宽中止痛;砂仁行气温中;瓜蒌润肠通便。
患者二诊时症状有所缓解,故继用四逆散加味,但三诊时患者诉嗳气症状复如从前,王健教授静心思考,认为病人嗳气时久,由最初的病及肝胃已渐渐影响至脾,致土虚木乘,痰饮中阻,升降失和,乃胃虚气逆所致,故改用补虚降逆之法。方用旋覆代赭汤加减治之,用旋覆花下气降逆,代赭石降肝气、降胃气功效甚捷。正如《医学衷中参西录》云:“而降胃之药,实以赭石为最效”[2]。加陈皮、半夏调和肝脾,疏理气机。患者嗳气不单是肝气、胃气上逆,同时胃气已虚,故用太子参、甘草、生姜甘温益气。诸药合用,补气健脾,镇肝降逆,扶正祛邪,嗳气自止。
郁证
患者某,女,57岁。2013年5月23日初诊。主诉餐前上腹部不适数月,胃脘喜暖,喜按,伴心悸,头晕,精神欠佳,眠差,纳食不消,时有嗳气,心烦汗出,口苦,偶有乏力,大便干稀不定,舌质暗红,苔薄,脉沉弦。证属阴阳失和,气机紊乱,治以调和阴阳为法,方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药用:柴胡10 g,党参15 g,黄芩9 g,姜半夏9 g,生龙骨15 g,生牡蛎15 g,桂枝10 g,生白芍12 g,百合30 g,乌药10 g,郁金15 g,蒲公英30 g,甘草6 g。7剂,水煎服。
2013年5月30日二诊:药后诸症明显缓解,上方加麦冬15 g,7剂,水煎服。
2013年6月18日三诊:诸症平稳,带药返回老家。后陪其爱人看病时告知诸症已无,精神、睡眠尚好,停药。
按:《伤寒论》第107条云:“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3]。其病机是邪气弥漫,三焦失畅,但病机关键是枢机不利。主要表现为气机升降出入紊乱,其根源在于阴阳失调。本案患者症状繁多杂乱,上、中、下三焦症状皆出现,王健教授认为该病寒热虚实互见,气血阴阳紊乱。遇到这种情况,王健教授常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本方可以看做是小柴胡汤加味而成,用小柴胡汤调畅气机,滋阴和阳,调气和血;桂枝、白芍合用,一出一入,燮理阴阳;加龙骨、牡蛎重镇安神除烦;百合、乌药梳理上下诸气;蒲公英、郁金清热理气,疏肝利胆。用本方不在于大补大泻,而在巧妙调和,调阴阳,调升降,和肝胆,调脾胃,顺应脾胃肝胆升降之性。
讨论
经方以其组方严谨,功效卓著,配伍巧妙而被历代医家所推崇。经方在内伤杂病中有着广泛的运用,若辨证准确疗效甚佳,故有必要对这些经验进行总结。
在病案一中,嗳气临证以肝气犯胃多见,但久病致虚,气虚痰阻,影响脾胃气机,故对于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辨证尤须用心体会和感悟。病案二中患者症状可谓纷繁复杂。面对此类病证,唯以小柴胡汤通达三焦,上下表里既畅,气机升降出入正常,诸症自解,当得益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之结果。合用桂枝汤调和气血,燮理阴阳,正如《伤寒论本旨》所云:“桂枝汤立法,从脾胃以达营卫,周行一身。营表里,调阴阳,和气血,通经脉,非攻伐,非补助,而能使窒者通,逆者顺,格者和。是故无论内伤外感,皆可取法以治之”。加龙骨、牡蛎镇静安神。上述之例,皆遵张仲景之意,实践证明确有良好疗效。
参考文献
[1]谢华.黄帝内经[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576.
[2]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册)[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49.
[3]熊曼琪,王庆国,关庆增,等.伤寒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