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其帕鲁》的作者之谜及其与波斯文化的渊源
——访旅藏澳大利亚翻译家杰夫·贝利先生
2015-12-18罗爱军边珍
罗爱军 边珍
(①西藏大学旅游与外语学院 ②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西藏拉萨850000)
《卡其帕鲁》的作者之谜及其与波斯文化的渊源
——访旅藏澳大利亚翻译家杰夫·贝利先生
罗爱军①边珍②
(①西藏大学旅游与外语学院 ②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西藏拉萨850000)
澳大利亚翻译家杰夫·贝利先生旅藏二十年,精通英、藏、日等多种语言文字,近年来出版了近十部藏英双语翻译作品。本刊在他与合作者白玛嘉措即将推出最新译作《卡其帕鲁》之时对其进行了采访。杰夫·贝利先生通过文献考证和实地走访,尤其是对“Khoda”一词进行了详细考察,提出《卡其帕鲁》一书作者即为卡其帕鲁本人的观点,同时指出《卡其帕鲁》与古代波斯诗人萨迪著作《古洛斯坦》与《布斯坦》的渊源联系。杰夫·贝利先生认为《卡其帕鲁》是跨文化交流的结晶,里面蕴含的智慧有益于世事人心,读者应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领悟和实践这些智慧。
杰夫·贝利;《卡其帕鲁》;萨迪;《古洛斯坦》;《布斯坦》
笔者:杰夫·贝利先生,今天我很荣幸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委托,对您进行专题采访。您初次来西藏是1995年,当时我在西藏大学工作,和您相识并结下了深厚友谊。今年是您来西藏二十周年,这些年来您在西藏大学和西藏社科院学习、工作,翻译出版的著作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在我们采访的开始,您能不能简单地介绍一下您的生长经历、教育背景和学术兴趣等方面的情况?
杰夫·贝利先生:我是澳大利亚人,本科就读于阿德莱德大学历史和英文专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研究生学习期间我的学术兴趣转向了教育。此外,我还攻读了跨文化学方面的研究生课程以及语言学和人类学方向的一些专业课程。我个人对史学和语言学非常感兴趣,还曾经在澳大利亚高级中学教过英文、历史和日文。从1996年开始,我和妻子在西藏大学进修藏文,学习西藏文化,度过了愉快而充实的三年,顺利完成了这里的藏文学习课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做过英语教师、翻译以及学术研究工作。截止今年,我受聘在西藏社会科学院担任常驻研究员已经有十四个年头了。
笔者:贝利先生,谢谢您上面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您和西藏社科院的翻译合作项目成果累累,能不能给我们的读者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杰夫·贝利先生:好的。从2000年起,因为担任英语教学工作的原因,我结识了西藏社科院的一些科研人员,从此开启了藏文作品的英译工作之路。十几年来,我们合作出版了八本书:《藏英合璧藏语拉萨口语动词注释》、《六青年的故事》英译本、《圣常啼传》英译本以及《语言之路》藏英学习丛书5册。这些书上市之后都广受好评,在西藏自治区甚至国内被不少藏语读者选用来学习英语,在国外也有读者通过这些书籍学习藏文。据我所知,西藏大学的对外藏语教学项目就采用了其中一些书籍作为教材。国际藏学界对《藏英合璧藏语拉萨口语动词注释》以及《六青年的故事》和《圣常啼传》等藏文经典的英译本反响热烈,相关著作在英国牛津和美国弗吉尼亚召开的藏学会议上受到高度评价,一些国际知名学者,如尼古拉斯·奥斯特勒(Nicholas Tounardre)、马克·图林(Mark Turin)和大卫·哲尔马诺(David Germano)为相关著作撰写了书评并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多次引用。整体而言,我对这些翻译作品是比较满意的。当然,这些成绩只是一次长途旅行中的驿站,面对浩瀚精深的西藏文化,还有许多翻译工作等待我和同仁们一道努力去完成。
笔者:看到您对西藏文化的热爱和为传播西藏文化所做的工作,我们十分感动。贝利先生,据我们了解,您和西藏社科院的翻译合作项目即将结束,之后您还有什么工作计划?
杰夫·贝利先生:我和西藏社科院的合作项目还有一部书籍待出版,现在已经进入到排版、校对阶段了,预计2016年初就能与读者见面。这部书就是藏族传统教育名著《卡其帕鲁》。我对此非常期待。因为在翻译《卡其帕鲁》的过程中,我倾注了很多心血,为弄清楚书中一些细节问题走访了拉萨、日喀则等地的学者和相关人员,发现了一些前人没有注意到的线索,尤其是西藏文化与波斯文化的一些联系。现在译作就要问世,我的心情就像一个怀胎十月的母亲,等待自己的孩子呱呱落地,非常盼望也非常激动。
笔者:那要预先祝贺您啦!您说自己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西藏文化与波斯文化之间联系的新线索,这听上去十分有趣,可以提前给我们透露一点儿内容吗?
杰夫·贝利先生:非常乐意!《西藏大学学报》在自治区内外尤其是藏学界享有很高声誉,能在这个平台上和相关研究人员探讨学术问题,我深感荣幸。首先我想申明的是,我没有在藏文化语境下成长的经历,藏语不是我的母语,因此面对浩如烟海的藏语文学典籍,我做任何判断都是小心翼翼,十分谨慎。关于《卡其帕鲁》一书的些许思考来自我这些年对藏文化不断学习、积累的过程,在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
不久前我有幸翻译《卡其帕鲁》这部藏文教育与文学名著,在参阅相关研究文献过程中一些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尤其是这部著作的作者和题材来源。通过文献考证和实地走访,我发现《卡其帕鲁》一书很有可能受到古代波斯诗人萨迪(1194-1291)著作的影响。如果将《卡其帕鲁》与萨迪作品的内容进行比较,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至于《卡其帕鲁》的作者,我认为就是书名所示的卡其帕鲁——一个真实的人而非笔名,并且与六世或七世班禅喇嘛过往甚密。我的研究认为,卡其帕鲁是与七世班禅喇嘛丹白尼玛或者七世班禅喇嘛的老师仲则·洛桑次臣共同完成了《卡其帕鲁》的写作。



《卡其帕鲁》一书体现了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一些思想内容,文体优美,表达自然,这些都表明作品是跨文化合作的结晶。
笔者:您的这些提法很新颖,与学术界对《卡其帕鲁》的传统看法有很大差异。您和其他学者有过交流吗?他们是否认可您的这些观点?
杰夫·贝利先生:在翻译《卡其帕鲁》期间,我就有关问题和许多学者进行了讨论,同时还追根溯源,对拉萨和日喀则地区的藏回(早期来自克什米尔地区,长期居住在西藏并信仰伊斯兰教,日常生活中使用藏语的穆斯林群体。在本文中为行文方便,一律采用“藏回”的称谓)进行采访,充分了解了他们对《卡其帕鲁》这部著作的想法和意见。我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代表了一些相关学者的看法,如果在表述过程中,我没有能够完整、准确地传达出这些藏学专家和藏回采访对象的观点,责任完全由我自己承担。我希望这些学术观点能够激发读者的阅读和研究兴趣,引起进一步的学术探讨,为相关研究带来些许新鲜气息。
笔者:我想您的愿望会实现的,这些观点一定会在学术界引起争鸣,也期待更多研究者加入到对传统文化经典的研究队伍里来。让我们回到《卡其帕鲁》,是什么原因让您对这一文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杰夫·贝利先生:《卡其帕鲁》在藏语文学里是一枝奇葩,文本中隐藏了很多不解之谜。即使只对书籍内容大致阅读一下,心头也会产生不少疑问:一部明显有伊斯兰教影响的书籍为什么会在佛苯盛行的雪域高原广为流传?这位自称“卡其帕鲁”的神秘作者究竟是谁?这本书是怎样在藏区流传起来的?为什么今天它依然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如果对文本进一步细读,还会发现更多问题有待探究:《卡其帕鲁》没有采用传统书面语,行文里有不少日喀则方言,这样一部作品三百年前如何能被当时的精英阶层接受?作者在文中大量使用了口语词汇和日常习惯用语,而传统藏文诗歌有严格的诗律要求,这两者又是如何做到和谐统一的?
《卡其帕鲁》尽管只有六百一十三个诗行,内容却十分丰富,值得讨论的话题更是不胜枚举——最重要的当然是文本主题与文体风格——不过,这里我还是想先谈谈作者究竟是谁以及文本最终如何成稿的问题。
笔者:那您能不能先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主要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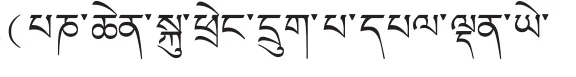
传统上认为《卡其帕鲁》由藏族作者撰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文本在语言运用和宗教内容上表现出来的本土特色。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卡其帕鲁》如果不是由藏族学者撰写而成,文字不可能如此优美、地道并且富有表现力。当这一观点遇到质疑,这些学者通常会反问:“一个外族人怎么可能创作出这么优美动听的藏文诗歌?”事实上,确实存在着一种可能性,也就是作者是来自克什米尔的藏回二代或三代——出生在卫藏并且从小熟谙藏语,也可称作“归化”了的藏人。到《卡其帕鲁》成书时期,从拉达克和勃律等地迁徙而来的藏回在卫藏地区已有几代定居。[4]帕鲁世家生活在日喀则,此时也是家族发达,事业蒸蒸日上。根据阿布·巴卡尔——日喀则清真寺的管家,同时也是日喀则穆斯林墓地的管理者——的讲述,今天在日喀则生活的藏回,有十三个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这些早期定居者,并且自称是源自克什米尔的穆斯林。

对于《卡其帕鲁》作者是藏族的进一步论证来自文本本身。《卡其帕鲁》里经常会使用一些佛教语汇,例如佛法(——尽管这个词本身可以泛指宗教或宗教教义,在勃律它通常指代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对藏回而言也指伊斯兰教)和喇嘛(),在涉及圣地时也只提圣地天竺而非麦加,尤其是整本书的主题“业报”看上去都明白无误地体现了佛教思想。例如文中有一处要求读者观想上师(第十一章第43行),另外一处请求上师以慈悲护念众生(第十一章第83行)。这些描述显而易见与伊斯兰文化格格不入。然而,我采访的藏回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们强调这正显示了卡其帕鲁高超的写作技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伊斯兰文化中的谆谆教诲有机融入藏语文化的语境里。“业”或者说“命运”也是理解伊斯兰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对此我的藏回采访对象再三强调:“我们此生的行为当然对来世会有影响。”

笔者:贝利先生,您对传统观点的这两点质疑有其道理,不过只能算作间接驳论,并不能直接证明《卡其帕鲁》的作者就一定是一位穆斯林。您有什么直接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吗?




事实上,卡其帕鲁还不是作者的全名。作者在诗歌序言部分明确提到了自己的全名“卡其帕鲁居”。我的一些采访对象证实这一家族曾长期在日喀则生活,不过阿布·巴卡尔提供的资料最为详实。他说卡其帕鲁家族的姓氏是“祖”(Zu,音译进藏文后发音变成“居(Ju)”,后来发音再变为“玉(Yu)”),而帕鲁的名字实际上是法祖拉(Fazullah)。我采访的其他克什米尔回商后裔也持相同看法。
阿布·巴卡尔还说卡其帕鲁家族曾经住过的宅邸被称之为“玉拉(Yula)”。我认为“玉拉”之所以得名,一种可能是卡其帕鲁家族姓氏“祖”的转音加上藏语敬辞“拉(la)”,另一种可能是直接来自“Fazullah”的缩略形式。尽管卡其帕鲁家族在阿布·巴卡尔小时候就已经断了后嗣,他本人并没有见过这一家族的后人,但街坊邻里都知道“玉拉”曾是卡其帕鲁家族的宅邸。今天这处宅院已难觅踪影,也没有人知道帕鲁家族是什么时候断的香火。按照阿布·巴卡尔对儿时的记忆,卡其帕鲁家宅所在的地点,现在已经成了日喀则市里一条繁华的充满现代化气息的街道。
在日喀则穆斯林墓地,一排排墓穴按所属家族排列,很多墓碑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沧桑。阿布·巴卡尔告诉我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些墓碑到底是属于哪个家族了,因为镌刻上去的铭文很久之前就已磨蚀殆尽。不过,他确信卡其帕鲁家族就葬在这里,而且卡其帕鲁本人的墓穴也在其中。
笔者:这些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物没有得到妥善维护和传承,真是一件可惜的事。您对“Khoda”一词和卡其帕鲁全名的语源考据很有新意,也很有说服力,对解开《卡其帕鲁》一书的作者之谜肯定会有帮助。您在前面还提到《卡其帕鲁》与波斯诗人萨迪作品的联系,能不能在这里做一些说明?
杰夫·贝利先生:尽管表面看上去《卡其帕鲁》一书自始至终贯穿着佛教思想,但其中的伊斯兰文化印记却很难被完全抹去。一些藏回学者认为,这部著作在创作过程中借鉴吸收了波斯古典诗歌作品的内容,尤其是波斯著名诗人谢赫·穆斯利赫丁·萨迪(Sheikh Muslih-ud-din Sa'di,名字一般缩略为Sa'di,有时也拼写为Saadi)的代表作《古洛斯坦》与《布斯坦》。
萨迪出生在波斯西南部的设拉子城,前半生游历广泛,后来回到设拉子城定居后创作颇丰,影响也很深远,被誉为波斯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9]他于1258年发表了《古洛斯坦》,意译即为《蔷薇园》。[10]这部作品是一部诗歌和故事集,大部分内容取材于他的旅行经历,中间穿插了不少寓意深刻的格言警句,问世之后大受欢迎,而且多次被译成英文,在西方世界广为人知。
《古洛斯坦》一书中讨论的主题与《卡其帕鲁》十分吻合,萨迪教诲劝导的写作风格以及对日常伦理实践的关注在《卡其帕鲁》一书中也得到了充分反映。例如《古洛斯坦》卷目中的“记帝王言行”、“论知足常乐”、“论教育的功效”和“论交往之道”等,与《卡其帕鲁》中的内容都有对应之处。[11]而且不可逆的命运这一主题贯穿《古洛斯坦》全书,因此萨迪不断恳请自己的读者,要慎重对待尘世里的一言一行。与此对应的是,这一思想也贯穿《卡其帕鲁》始终,不过改换了语境,采用了藏语文化中“业”或“果报”的叙述框架。尽管“命运(fate)”与“业(karma)”一般情况下内涵有别,但在《卡其帕鲁》中的一些诗行里可以将“业”译成“命运”,对文中思想内涵不会产生影响。
如,在《古洛斯坦》第一卷第九个故事中,萨迪悲叹道:
终于如愿以偿,但又有何益?既然
逝去的青春一去不返。
命运之手已敲起离别的鼓声。[12]
同样,关于生命得失的思索,关于命运无情的慨叹,也是《卡其帕鲁》想要传达的主题之一。帕鲁在第四章中写道:
如果不接受命中前定因果,
只会让自己白白遭受苦痛。[13]
笔者:我之前读过萨迪的这两部著作的中译本,不过从没有把它们同《卡其帕鲁》联系起来。从您刚才所说的内容来看,《古洛斯坦》与《卡其帕鲁》确实在主题内容上有不少相同之处。不过,世界文明史上经常会出现一些主题类似的作品,尤其在社会生活、伦理实践方面大多数民族都会有所共鸣,例如在《萨迦格言》里就能找到不少词句与《论语》里的章句相呼应,这很难说两者之间就有渊源关系。您能否就此做进一步的论述?
杰夫·贝利先生:当然没问题。《卡其帕鲁》的主题在《古洛斯坦》一书中大致都有所反映,不过如您所说,具体内容之间的对应还不十分明显。当我们转向萨迪的另一部代表作《布斯坦》(意译为《果园》),对它进行仔细研读,就会发现《卡其帕鲁》与其有更加清晰可辨的联系。《布斯坦》写作于1257年,比《古洛斯坦》早一年发表。[14]与后者同时采用散文和诗体写作不同,《布斯坦》正文以诗体撰成,这一点与《卡其帕鲁》完全一致。波斯诗歌同藏文诗歌写作十分类似,有严格的诗律要求,对修辞表达和辞藻提出了很高要求,有时甚至会牺牲诗歌内容的明晰性。[15]比如《卡其帕鲁》中就有一些表面看上去语义含混的诗行,读者只能凭个人理解去揣测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
根据现在可考的文献资料,萨迪六十多岁时完成了《布斯坦》的写作,内容包括十个主题,即:正义、善行、爱情、谦逊、乐天知命、知足常乐、教育、感恩、忏悔和祈祷。[16]如果对照两本书的内容,会发现《布斯坦》与《卡其帕鲁》的结构和内容非常契合,我个人认为《卡其帕鲁》与萨迪的这部作品存在很深的渊源。
下面我举一些实际的例子说明两者的联系。在“论知足常乐”这一章,萨迪在第三段对话中写道:
穷人因缺衣少食苦恼,国王因国事繁忙操劳。
国王统治穷人效劳,国王权势倾天而穷人常在牢狱哀号,有朝一日魂归尘土,两者区别再难找到。[17]
帕鲁对相同主题的描述则是:
国王端坐黄金宝座,
乞丐只能破布裹身,
面对无常死亡并无两样。
……
乞丐虽苦也过一生,
国王享福终究成空。[18]
在“善行”一章,萨迪对自己的读者晓之以理:
拿出你的金银财宝,因为终有一天你不再拥有;现在就打开财富之门,因为明天钥匙就不在你手。[19]
与此十分相似,帕鲁对藏文读者也有相同的吁请:
当财富之钥易手,你只会悔恨无穷。[20]
……要趁早教会宝马疾驰的步法。[21]
《布斯坦》中有这样的诗句:
如果你不想在末日审判之时苦痛,就不要忘了今日烦恼不已的众生。[22]
帕鲁在藏文化语境中对此则这样表达:
如果企望来世有财富与安逸,
最好先想想此间乞丐的模样。[23]
《布斯坦》中“论知足常乐”一章里有一行诗句,几乎意思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卡其帕鲁》相应的章节。
《布斯坦》:
只顾吃睡是动物的信条,人若遵从就如同傻子一般生活。[24]
《卡其帕鲁》里则是:
吃吃睡睡是驴牛之业,
我的孩子,这样生活难道就是幸福?[25]
《布斯坦》与《卡其帕鲁》之间的联系和相似之处比比皆是,以后如果有机会,我想可以撰写专文进行详细论述。在这里我仅再举几例加以说明,例如《布斯坦》中专门论述了保密的重要性:
把珠宝交给司库,不过把秘密留给自己。在话儿没出口前你是主子,一旦说出去你就成了奴仆。[26]
帕鲁的藏文表达则是:
可以把金银托付他人。
一旦需要还能够取回。
若把秘密与他人分享,
总有一天会自噬其手。[27]
……
秘密没出口逍遥自在,
秘密一说出丧失自由。[28]
对于这个话题《布斯坦》中还写道:
言语是禁锢在思想之井中的魔鬼——切莫让它从你的舌头和唇腭之间溜出来。当精灵从神灯里获得自由,再无良策把它召回。[29]
与此对应,《卡其帕鲁》里写道:
把言辞这个魔鬼关在心灵深处,
再锁上嘴巴和舌头。
如果魔鬼逃脱有人就要遭殃,
那时悔恨哀叹也是于事无补。[30]
《布斯坦》与《卡其帕鲁》两书的相似之处还反映在一些文体特征方面,比如风趣幽默的语言表达,丰富多彩的比喻修辞以及章节结尾时常常以第三人称出现的总括性文字。在《布斯坦》序言部分结尾的地方,萨迪带着一丝揶揄自夸道:
毫无疑问,我的文字在波斯受到尊崇,犹如无价的东方麝香一般。萨迪把蔷薇和欢乐带到花园,他的诗句恰如蜜渍椰枣——一旦打开,里面的宝石自然会熠熠生光。[31]
《卡其帕鲁》在每章结尾也采用了类似的叙述手法,例如第三章结尾:
卡其帕鲁将自己的点滴心得,
串在一起如同珍珠,
呈献给您三界王者。
说到价值理应不差。[32]
帕鲁在第四章结束时的陈述同萨迪的写作手法也十分相近:
卡其帕鲁的肺腑之言从口中吐露,
亲爱的孩子,要用心听着。
你们要明白的道理,这儿都已写下,
尽管篇幅不长,却能给心灵可口滋养。[33]
这样的例子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一一道来。不过从上面提供的例证来看,基本可以认定《卡其帕鲁》的写作受到波斯诗人萨迪作品的影响,尤其是《布斯坦》。卡其帕鲁应该对这两部作品非常熟悉,尽管《卡其帕鲁》一书不是对这两部作品的直接翻译,但在撰写过程中作者应该参考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和写作风格。帕鲁在这项工作中展现出来的翻译技巧和文化交流意识让人赞叹——他把波斯两部古典作品的主题和叙事有机地溶入藏语文化当中,创作出的文字不但流传至今,而且在藏区深受喜爱,广为传颂。用现在的学术语言来讲,帕鲁是一位跨文化交流的先行者,熟谙文本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传播时要考虑的要素和要传达的思想精髓。
笔者:听了您这番论证,我也要赞叹卡其帕鲁超前的文化传播意识和精湛的文学造诣了!
杰夫·贝利先生:我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在《卡其帕鲁》一书的写作过程中,帕鲁极有可能得到了西藏本土学者的帮助,比如七世班禅喇嘛的老师洛桑次臣,对文字进行了加工和润色,使行文更符合藏文文法和表达习惯。但我个人更倾向认为《卡其帕鲁》的初稿无论是口述还是以书面形式,应该是由帕鲁自己完成的。
笔者:那有没有可能卡其帕鲁曾经向七世班禅喇嘛或者他的经师谈起过萨迪其人其事,尤其是向他们介绍过萨迪这两部作品《古洛斯坦》和《布斯坦》的内容,在充分酝酿之后七世班禅喇嘛或者他的经师撰写了《卡其帕鲁》初稿?
杰夫·贝利先生:当然,我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可能性。不过,尽管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一定道理,有一些学者现在也依然坚持这个观点,但在我看来它很难解释我在上面提到的那行诗句:“在我们的语言中,我们尊崇其为‘Khoda’。”我是这样考虑这个问题的——既然传统上很多学者认为帕鲁与六世或者七世班禅喇嘛及其老师有过密切交往,那他们之间对彼此信仰的讨论自然就十分可能,一些学者可能据此推断出《卡其帕鲁》是帕鲁同七世班禅喇嘛或其经师洛桑次臣合作的成果。我个人不太赞同这些看法,不过无论这些观点成不成立,《卡其帕鲁》一书深受波斯诗人萨迪作品的影响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
笔者:谢谢您把自己研究《卡其帕鲁》的心得和我们读者一起分享,尤其是为有志研究西藏文化的青年学子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西藏文化自古以来与波斯文化就有交流,通过对《卡其帕鲁》文本的研读,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民族交往和文化融合的理解,对中国当下构建和谐社会和新型民族关系都会有所启发。贝利先生,我们知道《卡其帕鲁》藏英对照本的出版工作已经进入到排版校对阶段,即将由西藏人民出版社推出上市,您的相关工作也要告一段落。在这里能不能结合您的研究心得,谈谈您对这部著作的个人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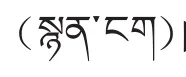
我在这里也简单介绍一下《卡其帕鲁》的诗律。《卡其帕鲁》包括十一章正文和一篇简短的前言。包含教诲劝诫内容的十一章由六百一十三个诗行组成,其中除了两个诗行是十一个音节,其余均为九音节诗行,前言部分则采用了散文体。藏文诗歌属于音节格律,易于唱诵和记忆。诗律对每行音节的数目和格律都有严格要求:一般而言,每个诗行的音节数目为奇数,但偶尔也会出现偶数音节的诗行。作者在《卡其帕鲁》中使用的九音节诗行就很典型,属于前六后三的格律形式。对于读者而言,这意味着朗诵的节奏应该是2-2-2-3。作者对这一诗律得心应手,口语词汇运用自如,很多诗行都是单独成句,内容常常是一句简短的格言隽语或者对读者发出的直接吁请。当然,作者有时也会使用两个、四个或更多诗行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最后,我想说说《卡其帕鲁》的修辞和作者的“微言大义”。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卡其帕鲁》的作者有时会从一个话题突然转到另外一个话题。进一步细读就会发现,作者实际上是在一个更大的写作和思想框架下安排这些讨论。文本中使用了很多祈使用法,作者想以此表明,他所关注的并非只是教授读者一些格言警句,而是希望读者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领悟和实践这些智慧。
那么,卡其帕鲁对我们这些后来的读者到底有什么期望呢?《卡其帕鲁》文字后面的未尽之言是什么?我觉得作者是一个文明忧患意识很深的人,对人生和社会有很多思考。简而言之,作者希望无论尘世的境遇如何,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珍惜和善度此生,因为这不仅事关此生幸福与否,更与个体和文明的未来息息相关。用书中教诲的话来讲,就是孩子必须尊重父母和长辈,君主治理国家要体恤民情,父母应该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们此刻所有活着的人都要扪心自问——面对无常的命运和终归要来的死亡,我们应该如何有意义地度过一生?
人类很早就对生命意义和我们生活其中的宇宙万物开始探究,世界主要文明对此也有共识,那就是个体生命的所作所为并非无关紧要,人类未来的命运和我们此时此刻的抉择息息相关。用当下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一个人必须负责任地活着,无论是做父母还是子女,是做公务员还是个体创业……我想这也许就是卡其帕鲁及其先驱萨迪通过写作想要后世读者思索和践行的微言大义吧。
笔者:贝利先生,《卡其帕鲁》出版后您就完成了与西藏社科院的翻译合作项目。据我所知,您现在已经开始了与西藏大学的相关科研项目工作,能不能在我们访谈最后谈谈您现在的工作?
杰夫·贝利先生:我一直以来盼望着和西藏大学的科研人员合作,因为西藏大学是我的母校,我和妻子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多的时光,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这里也有我的很多老师和朋友,有一起朝夕相处建立的友情。我很感谢这里的老师和朋友曾经给予我的帮助,所以很高兴能回来工作。
我现在手头的工作是和同事一起翻译一部藏语民间故事集——《尸语故事》。这本书非常有名,在西方也出了几种英译本,但很可惜大多是改译或缩略本,一直没有全译本,我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弥补这个缺憾。另外,我自己觉得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民间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因为这些故事通俗易懂,把深奥的道理用浅显的方式表达出来,很有趣也很生动,所以老少皆宜。民间故事的文字也很活泼,有很多方言俗语和格言警句,特别适合语言初学者。我认为西藏文化融汇了青藏高原四面文明的精华,通过民间故事这个渠道也可以找到一些文化交流的脉络,对当今的学术研究也会有借鉴意义。
笔者:谢谢您,贝利先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接受我们敬献给您的这条哈达。祝您在即将到来的2016年里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扎西德勒!希望您的译作早日与读者见面!
附录:下面三行藏文是杰夫·贝利先生重点分析的一个例子(见杰夫·贝利和白玛嘉措译著《卡其帕鲁》第44-45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15版),兹附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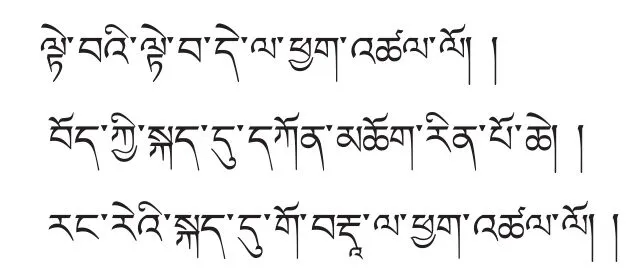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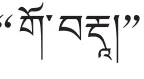
(《霍康·索朗边巴文集》藏文版)[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503-504.
[4][5][6]Cabezon,Jose Igancio.Islam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世界屋脊之上的伊斯兰教》英文版)[J].Saudi Ar⁃amco World,1998(1-2)同时参考了其他相关文章。
[7]卡其帕鲁关于生活艺术的忠告.[Khache Phalu’s Advice on the Art of Living,(Ka-che Pha-lu’i rNamthar)][M].达瓦罗布,译.1986:xv(笔者采访的藏回对象有一些也认为现行《卡其帕鲁》文本有所改动)。
[8]在此我要感谢著名语言学家Nicolas Tournadre教授的帮助。他就职于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Aix-Marseille Uni⁃versity),精通波斯文,对“Khoda”一词进行了详细考察。
[9]Edwards,A.Hart(1911).萨迪的布斯坦或果园(The Bustan Or Orchard of Sa’di)[M].Omphaloskepsis Books.2010:ix.参看:Rehatsek,Edward(1888).萨迪的古洛斯坦或蔷薇园(The
Gulistan Or Rose Garden of Sa’di)[M].Omphaloskepsis Books.2010:xiv.
[10][12][14]Rehatsek,Edward(1888).萨迪的古洛斯坦或蔷薇园(The Gulistan Or Rose Garden of Sa’di)[M].Omphalo⁃skepsis Books.2010:xvi,34,xvi.
[11]因为杰夫·贝利先生提供的英文版与之文字有出入,除《古洛斯坦》目录内容采用水建馥译本外(《蔷薇园》,商务印书馆北京2013年版),本文作者根据文意对其他相关内容进行了翻译。
[13][18][20][21][24][26][28][29][31][33]杰夫·贝利,白玛嘉措.卡其帕鲁教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5:109,63,65, 67,67,143,117,119,73,99,111.
[15][19][22][23][25][27][30][32]Edwards,A.Hart(1911).萨迪的布斯坦或果园(The Bustan Or Orchard of Sa’di)[M]. Omphaloskepsis Books.2010:ix-x,19,19,67,63,73,73,5-6.
[16][17]Edwards,A.Hart(1911).萨迪的布斯坦或果园(The Bustan Or Orchard of Sa’di)[M].Omphaloskepsis Books. 2010:目录页,16.因为与杰夫·贝利先生提供的英文版有文字出入,除《布斯坦》目录内容采用张晖编译本外(《果园》,宁夏人民出版社银川2007年版),其他相关内容由本文作者根据文意进行翻译。
Khache Phalu——Its Author and the Persian Influence -An Interview with the Australian Translator Mr.Geoff Bailey
Luo Ai-jun①Bian Zhen②
(①School of Tourism and Languages,Tibet University②Lhasa Normal College,Lhasa,Tibet,850000)
The Australian translator Mr.Geoff Bailey has been living and working in Tibet for twenty years.As a master of English and Tibetan,he has published quite a few books in recent years,which cover a wide range of themes.The journal made an interview with Mr.Geoff Bailey while his new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work Kh⁃ache Phalu is in the press.Mr.Geoff Bailey puts forward in the interview that the content of Khache Phalu seems heavily influenced by an ancient Persian poet named Sa'di,whose famous works include The Gulistan and The Bustan.In terms of the authorship,Mr.Geoff Bailey regards that there undoubtably does seem to have been a person called Khache Phalu,who more than likely would have made the initial Tibetan rendering,either orally or in writing.He also points out the hidden message of Khache Phalu-which is,imploring the readers to conduct themselves well in this life,for it surely impacts their lives now and most importantly,in the hereafter.
Geoff Bailey;Khache Phalu;Sa'di;The Gulistan;The Bustan
10.16249/j.cnki.1005-5738.2015.04.010
H214
A
1005-5738(2015)04-058-010
[责任编辑:拉巴次仁]
2015-10-23
罗爱军,男,汉族,陕西旬邑人,西藏大学旅游与外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文化研究和高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