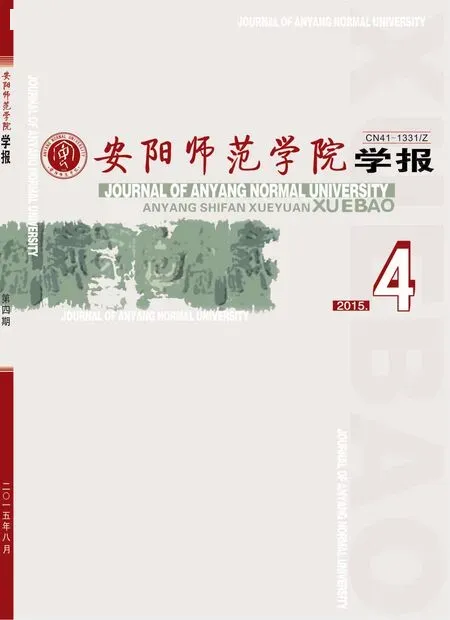战时逃难知识分子的世俗生存——以《潘先生在难中》《马伯乐》《围城》为例
2015-12-18刘丹
战时逃难知识分子的世俗生存——以《潘先生在难中》《马伯乐》《围城》为例
刘丹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战争的爆发,对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知识分子这个阶级本身就存在着双重性。所以在动荡徘徊之中,知识分子渐渐分化成不同的类型,很多人参加了抗战,很多人观望犹疑,很多人堕落反动,还有很多人选择了逃亡:潘先生、马伯乐、方鸿渐。他们逃难的背景和原因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失去了道德操守和精神追求,没有承担历史使命。我们也许可以理解这种人性中的弱点,但却不是我们提倡和赞扬的。
[关键词]知识分子;逃难;潘先生;马伯乐;围城
[收稿日期]2015-05-11
[作者简介]刘丹(1991—),女,河北省秦皇岛市人,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收稿日期]2015-05-23
一、知识分子身份的丧失
“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来源。一是来源于俄文,受西方现代性的冲击,19世纪的俄国出现了一个揭露黑暗统治、反对不合理秩序的群体,他们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二是来源于法国,1894年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这引起了左拉、雨果等文人的正义感和社会良知,他们发表了一篇名为《知识分子宣言》的辩护文章。无论是俄国还是法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并不只是仅仅局限于狭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是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人类良知。
中国的文人,作为“四民”之首,从小就树立了孔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地理想抱负,自觉地承担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则是出现在清朝科举制废除之后,文人没有了“学而优则仕”的升迁,渐渐选择了出版商、教书先生、留学生、撰稿人等不同的道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逐渐成为了具备现代意识和科学知识的进步知识分子,自然而然的成为了社会改革的启蒙者和急先锋。
战争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不能再“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由于他们的出身、角色以及职业原因,他们渐渐在动荡的年代中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资本。知识这种“无形资本”,必须通过转化才能成为“硬资本”,这就决定了他们要依附统治阶级。这种依附性和软弱性,就常常将他们置身于尴尬境地:一面追求精神理想和自觉的伦理担当,另一面,又不得不在“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现实处境中谋求生存。这样,就造就了知识分子的孤独苦闷,软弱动摇。在徘徊衡量中,知识分子渐渐的选择、分化、淘汰、整合成了不同的群体。有的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如觉慧、杜大心;有的软弱痛苦、不得不留守,如祁瑞宣、觉新;有的走入了反动阵营,如祁瑞丰、戴渝;还有的在不停的奔走、逃难、流浪,如潘先生、马伯乐、方鸿渐。他们已然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只是以一个难民的身份,在世俗社会中艰难的生存。
二、不欲偷生而终得苟活
在逃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也想有尊严的生活,但是却最终苟活,斯文扫地,根本无暇顾及国家的利益。作为“灰色人物”的典型代表,潘先生的那种“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的小市民性格,是五千年来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处世哲学。战争爆发,他惊慌逃跑;平安到达上海,他松了口气;怕失去工作重返故里,担惊受怕;平安无事后,写匾庆功。他的所作所为,都只是为了自己和家人能够平安的生存下去。在逃难中挤火车时,阿大、阿二就是他所有的财产,当身后没有了小手时,“家破人亡之感立时袭进他的心,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望出去电灯人形都有点模糊了。”[1]在入住上海旅馆之后,他边喝酒边欣赏自己的儿子;在向红十字会要徽章时,也多要出了远在上海的妻子和儿子的那份,这其实就是为了能够保存潘氏血统的延续下去。
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一书中用一个同心圆展示了个我、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圆心是个我,圆心外第一圈是核心利益家庭中的我,第二圈是大家庭利益的我……最后一圈才是天下利益的我。潘先生为了保全自己孩子的性命而逃难,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生存,他只能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小学校长,是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否则没有薪水就难以维持家庭的开销,就难以维持这种血缘的延续。无论是逃走还是逃回,对于他来说,都是一种赌注,所以他不断的在衡量,在斤斤计较,最终目的都是苟且偷安。对于这种小知识分子来说,他没有教育局长的那种职权,所以只能巴结取巧、委屈求全,这种卑微和劳苦,恰恰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中国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封闭的农耕文化注定了“小国寡民”的性格,他们与世无争、中庸、懦弱、内敛、自私。潘先生重返战场,既有害怕失去工作的原因,也有怕别人瞧不起的原因,确实能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教师的良知,“回去终是天经地义”,等他到了红房子,“那里早已住满了人,大都是十天前就搬来的。连教育局长和其他同仁也早就在那里占据了一个不错的位置。”[2]在战争胜利后,他给军阀写匾时,眼前浮现的是“拉夫,开炮,焚烧房屋,奸淫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3]他并没有丧失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只是不得已的苟且偷安,这种贪生怕死,正是由于“夫”与“父”的传统责任的召唤,终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造成了不欲偷生而终得苟活的结局。
同样的,马伯乐和方鸿渐,在逃亡中关注的只是自己的生存和生计,他们也不愿意以一个难民的身份,如此窝窝囊囊的生活,可是终究摆脱不了小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对于这种萎顿和痛苦,自然是值得同情的。
三、“去势”状态下的逃离责任
萧红笔下的马伯乐,是个“万事总要留个退步”的人,这所谓的退步就是“逃跑”。无论发生任何事,马伯乐总是想着逃走:小时候发大水别人都泡在水里,唯独马伯乐爬到烟囱上,更是把馒头用小绳穿一串挂在脖子上;小女儿雅格生病,他太太让他去找医生,可他总是推脱要去看朋友,这一去就是一夜;每次和妻子吵完架,他就逃到大街上去,完全听不见哭声和骂声……在逃难的过程中,他更是将国民性中的这种“逃离”,表现得淋漓尽致:卢沟桥事件一发生,马伯乐就从青岛的家逃到了上海;在储存干粮的时候,他总是想着省钱第一,所以原来一顿吃五个鸡蛋的蛋炒饭现在也是能省则省,他认为逃难过程中挨饿总是难免的,现在吃不饱正好是在做训练;在挤火车的过程中,他太太拉着大卫、拖着约瑟、抱着雅格,还要拿着好几只箱子、一只网篮、还有行李,而马伯乐早就在前面挤得没了踪影;甚至在到了汉口,和王小姐谈恋爱时他也是给不出任何承诺的跑掉了……
马伯乐完全承担不了责任,也无法在马家树立起大少爷的权威,这是因为他自小就是胆小悲观的,成年后也没有稳定的工作供养家庭,他完全就是一个“多余人”。“二三十岁的人了,张口就是父亲,伸手就是钱”[4]每一次向父亲要一点零用钱总要气得面红耳热,可是过不了几天钱花完了,还是得乖乖的再低声下气的去要钱。尤其是在去上海开书店失败回家后,在吃饭时没有人开口和他讲话,父亲吃完饭离开后,他也只得不饱不饿的吃上一碗就退出客厅,甚至父亲漱口的声音都会对他造成威胁。身为家里的长子,马伯乐却无法树立自己在封建大家庭中的地位和尊严。
马太太是一个要强的女人,但是遇见这样软弱的丈夫,她只能接管家里的一切大权,做了事实上的下一代接班人。马伯乐手里没有一点钱时,就只能去借太太的体己钱,就只能看太太不大好看的脸色:他出门不小心踢倒了铁壶吵醒了太太,就赶紧去道歉,想不到弄巧成拙惹怒了妻子,“马伯乐就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恭顺也不对,强硬也不对,于是满脸笑容,而内心却充满了无限的痛苦。”[5]在上海逃难的过程中,由于他钱财短缺,生活困难,只能给妻子一封封的拍电报,想让妻子带着钱财来,可是用什么方法使妻子来呢:要去投军吧,可是上海还没有开火;要去当共产党吧,可是太太最多寄张回家的船票钱;就说在上海交了个女朋友吧……当太太终于到了上海后,他不能确定到底带了多少钱,只能处处忍让,生怕失去这个资本。在“出嫁从夫”的传统社会中,男性本该占着主导地位,可是马伯乐丝毫掌握不了自己的人生,又何谈控制女性呢?
在这样压抑的家庭中,马伯乐还要看孩子和下人的脸色,他从不打孩子,也不敢打,一动手,他太太就在后面打他,所以他的孩子都是不怕他的,尤其是二儿子约瑟,就像小酒疯子似的抱住父亲大腿不放,使得马伯乐想走却迈不开步,马伯乐讨厌极了,推又推不下去,打又不敢打;马伯乐偷着跳上了父亲的车子,可是车夫却不侍候他……无论家里的老少尊卑,对他完全是不放在心上的,所以他渐渐形成了女性气质:走路都溜溜的,甚至哭泣也是轻轻的,安静的,一边思量一边哭,把腿弯着,把腰弓着,悲哀的哭。
经济状态的困窘,正是马伯乐丧失男权的象征。“这是什么世界,没有钱,父不父,子不子,妻不妻,夫不夫。人是比什么动物都残酷的呀!”[6]被“阉割”了的马伯乐,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逃跑者。隐藏在国民性中的男性性别认同危机,恰恰是知识分子在逃难过程中不能承担责任的潜在原因。潘先生对教育局长的谄媚,方鸿渐的寄生生活,这些“去势”或者“缺席”状态下的人,不仅丧失了男性的话语权,最终旁落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领导地位,“全汉口的人都在幻想着重庆”,那么到了重庆之后又怎么样呢?
四、社会转型中的迷茫
《围城》中,赵辛楣对方鸿渐的评价是“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7]这正可以看出上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状态。抗日战争爆发使得大量的知识分子逃往内陆,在逃难的路程中,他们经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失业、饥饿、勾心斗角、甚至还有妓女的嘲弄“教书的?教书的没有钱,为什么不走私做买卖?”[8]钱钟书以方鸿渐为基点引出苏文纨、唐晓芙、曹元朗、赵辛楣、高松年、李梅亭、汪处厚、韩学愈、孙柔嘉等三十多位知识分子,展现了新旧社会转型中的知识分子的迷茫和焦虑。
在逃难过程中,五个人各怀鬼胎,各显神通。赵辛楣仗着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自然充当了领导;李梅亭仗着自己的老谋深算,在如此坎坷的路途中也算滋润:有烟抽,有地瓜吃,有鱼肝油补充营养,还可以挑逗一下孙小姐和王美玉;顾尔谦为了把钱补给给家庭,自己坐三等舱却以把好位置让给年轻人为名,一路都是一副胁肩谄笑的丑态;孙柔嘉看似一个楚楚可人的小女生,但“刁滑的很”、“就像那条鲸鱼,张开了口”;唯有方鸿渐一人,无所事事,他真正关注的只是自己如何谋得生计、又如何谈好自己的恋爱。逃难的旅途中,他似乎很快的就忘记了失恋的痛苦;买汽车票时一点忙帮不上,只能留在旅馆“好好陪着孙小姐”;走没有栏杆的桥时,还要孙小姐在前面引路……尽管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依旧是一个独立能力和解决能力很差的人,所以他一事无成,这种生活、事业、爱情上的“围城”,恰恰是由于世俗化的生活使他丧失了人生意义的追求,他已然习惯了“被安排”:留学依靠岳父,谋事依靠赵辛楣,婚后依靠孙柔嘉,他空虚、迷茫、流浪……
社会转型时期的新型知识分子,自小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如道家的“无为而治”,所以往往安之若命,甚至随波逐流;成长过程中又接触西方的众多现代观念,所以往往在接受过程中需要选择消化;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一个思想迷茫和文化选择的过程:是接受还是舍弃?是继承还是革新?这个受过新旧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慢慢分化成了不同的类型:有浑浑噩噩的方鸿渐、有官僚式的高松年、有腐朽的李梅亭、还有出走的赵辛楣……相比之下的方鸿渐的父亲,尽管迂腐陈旧,但却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人生寄托,这种传统知识分子恰恰代表的是一种社会良知。
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学说,正是突出了新型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功能。可是在潘先生、马伯乐、方鸿渐的价值观中,向来没有什么主义的负担,也没有血性男儿的追求,他们随俗沉浮,精神没有寄托,灵魂没有归属,迷茫之中的“新式文人”,如何能承担起这种责任呢?甚至于,他们愿不愿意承担呢?
五、结论
在大起大落的年代里,战争毁灭了知识分子的书斋,打击了他们的自尊,更是考验了他们的人格。中共一大代表全是知识分子,十大元帅九人出身知识分子。废名在《莫须有先生传》中曾写到“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而言,衣食住的问题与他的灵魂全不相干。”[9]探究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还是“苟全性命于乱世”,是融入抗争的洪流还是逃入个人的小我世界,都是一种选择。潘先生、马伯乐、方鸿渐的逃亡,仅仅是代表着众多逃难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只要没有伤害任何人,就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中国消极避世是一种“活命价值”。只不过,我们提倡的是知识分子,乃至一个普通人的,道德操守、历史使命和精神追求。
[参考文献]
[1]裴毅然.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和探索[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2]许纪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3]汪凤炎,郑红.中国文化心理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
[4]陶东风.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5]王江松.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M].北京:线装书局,2012.
[6]沙莲香.中国民族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7]英 迈克·彭 著 邹海燕 译.中国人的心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
[8]林语堂.中国人[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4.
[9]欧阳仑.中国人的性格[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