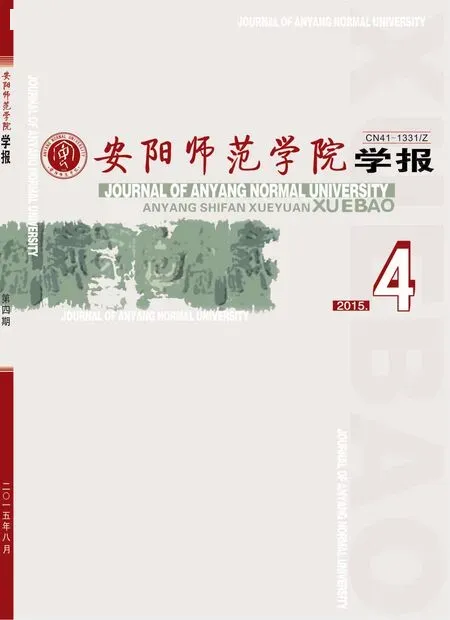景物风俗描写与“寻根乡土小说”
2015-12-18李超
景物风俗描写与“寻根乡土小说”
李超
(湖北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摘要]“寻根乡土小说”是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寻根乡土小说”中有色彩丰富奇异,又各具特色的景物、风俗描写,它们与“寻根乡土小说”相融合,形成了浓郁的特色和持久的生命力。和其他时期的乡土小说相比较,“寻根乡土小说”既有传承又有创新。
[关键词]景物风俗;寻根;乡土小说
[收稿日期]2015-05-11
[作者简介]李超(1988-),山东莱芜人,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与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一、“寻根”与“乡土”之间的融合与分析
“寻根文学”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主要体裁呈现形式是小说,“寻根文学”的作家认为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寻根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表现出对传统风情、风俗的偏好。
“乡土小说”是指以回忆重组的形式来描写故乡农村生活带有浓厚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 ,它的题材主要涵盖三个范围:一是以乡村、乡镇为题材,书写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生活;二是以流寓者的留寓生活为题材,书写工业文明进击下的传统文明逐渐淡出历史走向边缘的过程;三是以“生态”为题材,书写现代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表现出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特征。如果从地域角度来分析,可以把"寻根文学"划分为"城市文化寻根"和"乡野文化寻根"两个大范围。[1]
由于“寻根文学“和乡土小说两者特征的自然契合,“乡野文化寻根”体现于“寻根文学”中就自然形成了”寻根乡土小说“,它是整个“寻根文学”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也是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寻根乡土小说”的抒写中,作家们非常注重“异域情调”和“地方色彩”的挖掘[1],这一无意识挖掘的直接效应是“寻根乡土小说”在艺术特色上明显区别于“新时期”以来其他题材的小说创作。这种区别得益于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创作自身具备的两种特征:一是着力于恬静、安适的“农家乐园”的描绘;二是描写苍凉蛮荒充满悲剧氛围的洪荒时代古老先民的生活形态。[1]无论是“农家乐园”的描绘,还是“蛮荒生活”的抒写,它们都与“寻根乡土小说”所要表现的文化思想内涵和新鲜的审美感受一并融合,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生命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以来的各种文学体裁中,上述两个形态都不乏展现并精彩纷呈。但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十七年”文学中,这种展现几乎消失殆尽,为数不多的保留也深深的刻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新时期”文学以来,以“寻根乡土小说”为主要代表的“寻根文学”真正睁开了沉睡的眼睛,无论是作品本身的艺术特点还是内在的精神力量都回归到文学本身,在这种回归中,“寻根乡土小说”中的景物风俗描写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作用的产生既得益于“寻根乡土小说”传承了传统乡土小说创作中的明显特征,同时,它在传承的过程中又体现出来了文学乡土意义上的新变。
二、乡土风情、风俗抒写的承续和新变
(一)“寻根乡土小说”的对传统乡土小说的传承
乡土小说从20世纪初中期开始,一直延续的是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三画特征”[1],着重体现的是“风景”和“民俗”。从鲁迅最早期的乡土小说创作如《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开始,鲁迅笔下的“鲁镇”、“未庄”等乡村野镇都体现出浓郁的地域风俗画特征,此后的以废名、沈从文及“京派”为代表的乡土浪漫派小说更是透露出浓郁的田园归隐情节。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多个作家群落和流派的乡土小说创作,主要包括“革命+恋爱”式的乡土小说、“社会剖析派”、“东北作家群”和“七月派”的乡土小说创作,这些不同派别的小说创作是特殊时代背景或流寓在外的特殊身份的作者进行的乡土抒写,这种乡土抒写带有了意识形态成分和浓重的乡愁气息。随后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乡土小说逐渐发生变调,不管是“土改”时期,“合作化”时期,还是“文革”时期的乡土小说创作,浓烈的政治意识压缩了文学作品其他特征的表现空间,但是,即使如此,这些时期的乡土小说创作中仍然保留了颇多的乡村风情和风俗的描写,这也显示了乡村风情、风俗作为乡土小说的基本特征。
作为“新时期文学”以来重要的文学阶段,“寻根文学”时期的乡土小说创作自然应该延续这种抒写传统,从现实看,“寻根乡土小说”在“风景”和“民俗”两个特征上也确实得以延续,并表现出了可贵的创新性,体现出了新的特征和内涵。这两种特征之间并非完全趋同,它们又略有差异,与“风景”有关的特征化抒写更多的体现为传承性,而“寻根文学”探求民族文化之根的使命更容易承载于“风俗”的描写上,“寻根乡土小说”的创新性更多体现于“民俗”描写。
以鲁迅《故乡》、《祝福》等乡土小说作品为例,作者对故乡的刻画典型性的突出一种浓重的氛围,这种氛围在鲁迅笔下往往几笔即可勾勒:“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2]。聊聊数语,就展示给我们了一个沉闷压抑的乡村世界。由景物描写塑造某种氛围的描写手法深深的影响了以后的乡土小说创作,每个时期的乡土小说创作中都能找到这种影子。作为“寻根文学”的开山之作,韩少功的《爸爸爸》传承了这种乡土创作的传统,同时在凸显浓重的氛围之外,还出现了更为精细化的楚山、楚水的地域特色描写,楚地山水在他的选取和拼接下有效融合,形成了独特韵味,山水和鸟兽鱼虫出现在他的笔下,更多了一层魔幻色彩:“寨子落在大山里和白云上,人们常常出门就一脚踏进云里,你一走,前面的云就退,后面的云就跟,白茫茫云海总是不远不近的团团围着你,留给你脚下永远也走不完的小孤岛,托你浮游。”[3]“寨子”形成的是大环境,大环境的描写显得虚幻而神秘;“有时可见树上一些铁甲子鸟,黑如焦炭,小如拇指,叫的特别焦脆和洪亮,有金属的共鸣声。”[3]这是大环境中具体元素的描绘,衬托于整个环境下更具古怪奇异色彩。这样类似的元素在整个作品中有很多,富有奇异色彩的元素融合于整个陌生环境中,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风格,构成了楚地特有的气场和力量。相比于《故乡》中浓郁的灰色调景色描写带给人的压抑感,这种饱含异域色彩的景色抒写带给人的是陌生化的力量和原始的冲击力。
如果说《爸爸爸》在乡土风景的刻画上凸显的是原始的冲击力,那么莫言的《红高粱》在展现异于南国风景的同时,则蕴含着野蛮的生命力。抛开莫言本身创作风格不论,单就讨论《红高粱》在地域化景物描写所体现的北国特点上,这仍旧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范本:“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无边无际的血海”[4]。“高粱”挺拔,高耸,坚韧,“高粱”的“血海”构成的是一幅北国独有的壮阔景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空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的影子”[4]小说用粗线条勾勒出的画面,对生长在北方,或是见过大片高粱田的人而言会深感熟悉,能够从文字中嗅出大地的腥气,体会到作者笔下的根植于“高密东北乡”这块土地上的人有高粱一样不屈不挠,敢爱敢恨的秉性,红的像火,烈的像酒。有了这样一幅画面,就让人不难明白,作者为什么选取“高粱”这个意向,为什么人物和故事的发生与这片高粱地有这么紧密的关系,与之相关的影视作品又为何那样去体现。
不管是《爸爸爸》,还是《红高粱》,它们并非“寻根乡土小说”中着意特意挑取的作品,“寻根乡土小说”的其他代表性作品如阿城的《棋王》,张承志的《黑骏马》等,它们或有对祖国西南边境景物的描写,或活生生的把草原风景抛在了我们面前,展现一幅陌生而又奇幻的画面,它们自己的地域抒写都传承了传统乡土小说的抒写特征,体现“寻根乡土小说”与传统小说创作的一脉传承性。
(二)“寻根乡土小说”文学乡土意义上的新变
韩少功曾在《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5]这篇纲领性的文章其实透漏出了“寻根乡土小说”相比于其他时期乡土小说创作而言不仅有传承,更应体现乡土意义上的新变。从“寻根乡土小说”本身的特点来分析,这种新变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民俗风情所体现的载体价值,就是说创作者在叙述民俗风情时不再只是展现一域的特点,而是以此为载体去挖掘民族之根的力量。二是在挖掘深植于民族文化之根的同时所体现出来的立意上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不在于实际解决问题的结果,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探索的形式和勇气。
在其他时期的乡土小说作品中,对于自己家乡风俗的描写比比皆是,这种风俗的刻画多为婚丧嫁娶、祭祀、节日等传统风俗,从鲁迅的《祝福》,到沈从文的《边城》,再到孙犁的《荷花淀》,甚至以赵树理为代表的的“山药蛋派”的小说创作,这些乡土小说作品中的风情风俗的描写多是如实刻画,基本“中规中矩”,而《爸爸爸》在风俗描写方面,则更多的抒写了当地奇异传说和神幻风俗:“山中多蛇,据说蛇好淫,即便装在笼子中见到妖娆妇女还会在笼中上下顿跌,躁动不已,几近气绝。”[3]“人一旦染上虫毒,就会眼珠青黄,十指发黑,嚼生豆不腥,含黄连不苦,吃鱼会腹生活鱼,吃鸡会腹生活鸡,在这种情况下,解毒办法就是赶快杀一头白牛,让患者喝下生牛血,对满盆牛血学三声公鸡叫。”[3]我们无从考证作者在依据传统的基础上加入了多少想象的成分,但是作品中荒诞怪异的内容还是很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在这种猜测和想象中,一个地域的文化特色得到了最大发酵,与作者所要追寻的这种依托于民族之“根”的,或丑陋,或美丽,或神圣,或荒诞的奇特力量紧紧契合,而显得毫不生离。这就验证了“民族的、本土的民间文化形态,既能使本土文学获得再生的资源,又成为与世界文化对话的一条重要途径”[7]。它使“寻根文学”的“河流”注入了最具活力的活水,使得它瞬间力量倍增,携泥沙、巨石而下,拐角山隘均不能阻挡,“寻根文学”所追寻的生命力变得不只是设想,成了实实在在摆在众人眼前的活物。这种生命力通过民俗得以体现,作者并试图探索民俗表象背后的根植于民族文化之根的力量。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寻根乡土小说”体现出立意上超越性的力量。《祝福》、《阿Q正传》的等乡土小说在立意的深层次上偏向于揭示国民的弱根性,批判国民不肯苏醒的灵魂,即便像《社戏》这样稍感轻松明快的作品也多半是因为有回忆孩童时期的成分,而“寻根乡土小说”则是渴望探求深藏于民族文化之根的力量,在民族文化之根上寻求出路,以拯救民族灵魂。这两者之间在立意上无法判别孰优孰劣,鲁迅的立意更为深层,但是“寻根乡土小说”的创作也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尝试办法。一个是深切的反省和解剖,另外一个是热切的希望。这种对比在《祝福》与《红高粱》之间显得特别明显。
《祝福》一开场就有这样的描写:“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6],这是一片灰色的景象,充满了沉重压抑感,这是对故土的热爱之上的沉重。再联想一下《故乡》开头的描写,这种沉重氛围的凸显就更为明显。在《故乡》中,鲁迅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萧条毫无生气的“故乡”:“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隐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2]。
与之相对比,莫言口口生生说“高密东北乡”是“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我爷爷”“我奶奶”是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杂种”,但很显然是以赞美的态度去写“我爷爷”、“我奶奶”,去写“高密东北乡”的故事的,这样浓烈的感情需要浓烈的环境作衬托,浓烈的环境下简述的“绚丽的故事背后又隐藏着作家深刻的理性精神和文化忧患意识”。[7]这一感情基调的确立就让叙述者在写民俗、写人物的过程中都无意流露出赞美的态度:“轿夫抬轿从街上走,迈的是八字步,号称‘踩街’。踩街时,步履不齐的不是好汉,手扶轿杆的不是好汉,够格的轿夫都是双手卡腰,步调一致,轿子颠动的节奏要和上吹鼓手们吹出的凄美音乐,让所有人都能体会到任何幸福背后都隐藏着等量的痛苦”[7]这与其说描写的是风俗,不如说是在“显摆”,显摆的是力量,是生命的原始的活力,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不知为何但就是要这样去做的“带劲的事情”。同样的富有渲染力的画面还出现在酒坊出酒的祭拜仪式上,红红的高粱酒举过头顶,从他们那虔诚的表情中,我们感觉到这些生于斯、长于斯,天不怕、地不怕的“混不吝”也有敬重和敬畏的力量。从另一个层面讲,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生命的野性与强力,不是漂浮于历史的天空,而是也有一段“根”的力量紧紧扎于土地之上。与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相比,“寻根乡土小说”因为与其立意的差别,少了些许悲情,多了一丝悲壮,淡化的是失望,饱含的却是希望。
三、景物风俗与“寻根乡土”结合产生独特生命力的原因分析
小说创作中,景物风俗的抒写并不应该拿“独特的存在”来称呼,它应该是小说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及组成部分,但是,“寻根乡土小说”所产生的影响和生命力,就得益于“寻根乡土小说”中的独特地域景物风俗抒写,也就是说,不同的景物风俗抒写与“寻根乡土小说”相结合,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这种效果产生了坚硬、持久的生命力。如若从文学史的纵向和文学艺术本身的横向两个维度来分析,这种现象的产生就不难理解。
从纵向看,中国文学创作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小说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摆脱不了“类型化”写作的局限。即便是文学作品中的景物风俗描写也好像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红绸”,这块“红绸”随着作者基于意识形态的创作意图的需要,随之增减。无论是土改时期的作品,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作品如《创业史》、《三里湾》,创作者在景物风俗描写这一点上,一是压缩了作品本应该自然存在的景物风俗描写内容,二是在景物风俗抒写过程中类似于人物表现一样突出了“正反”两极对比。这不是偶然的存在与一部作品,而是成为这一时期作品创作的无意识现象与规律。从文学创作角度的科学性来说,这种“正反”两极的对比,本身就违背了作品本身该有的艺术性及穿透力、感染力。有趣的是,原先的“国统区”作家张爱玲创作的反应“土改”的作品如《秧歌》、《赤地之恋》反倒有许多涉及农村风景风俗的描写,但是作家有意“揭露”和“唱反调”的意图过于迫切和明显,这种描写因此也未能摆脱为作家倡导的意识形态服务的窠臼,只不过又换了个立场而已。
“文革”结束后出现在文坛上的“伤痕”、“反思”文学,如同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这个“病人”深深陷入对刚刚经历过的这场劫难的扼腕、追思,还来不及顾及并寻找文学本身所需求的,也是必不可少的诸多元素中来,在这其中,景物风俗描写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创作者一味回忆苦难,慨叹时代对个人带来的浩劫,忽略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深度,造成作品整体格调不高,艺术性不强。试想今天我们在读到“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作品《班主任》、《伤痕》等作品时,很难想象中国现代文学在经历过那么多的大家和那样的辉煌后,竟如同小儿学步一样,在文学艺术性上如此陌生,这样艺术性的重新开启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终于,到了“寻根文学”阶段我们嗅到了真正文学的气息,这也就是文学回归的由来。在这种回归中,文学作品中丰富的景物风俗描绘贡献出了自己独特的力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从横向看,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必定是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结合。艺术性侧重技巧和元素,精神性侧重情感和人性。小说本身作为艺术的种类,需要具备这两种元素,这是艺术对文学作品的自然要求,同时,也是文学作品赋予小说的生命力的所在。从艺术性的角度看,“寻根乡土小说”传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新时期”文学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景物风俗描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丰富了作品的语言元素,为作品感染力的激发支起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框架;从思想性的角度看,“寻根乡土小说”构架起的“寻根文学”作品,本身的精神力量和追求的终极价值又寄托在景物风俗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的“根”之上,二者相结合最大限度的发挥出了景物风俗描绘的力量,使其与作品和时代本身,构成了不朽的精神存在。
称之为不朽的文学作品必然有它独立于世的特别之处,“寻根乡土小说”在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历程中集中性的出现了优秀,甚至称之为不朽的文学作品,这其中,除了“寻根乡土小说”是构筑于民族之根之上,并由此向深处去溯源和分析这种精神性思想性力量之外,这些作品中共同具有的丰富的景物风俗描写的内容,与这种精神性、思考力之间的衬托和融合所形成的独特效果,也许能为我们提供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思考,这对任何企图创造有生命力的作品的作家都是一种启发和指导。
[参考文献]
[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鲁迅.呐喊.北京:燕山出版社[M].2011.
[3]韩少功.爸爸爸[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4]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5]韩少功.文学的根[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1.
[6]鲁迅.彷徨[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M].2013.
[7]王光东.民间文化形态与八十年代小说[J].文学评论,2002,(4).
[责任编辑: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