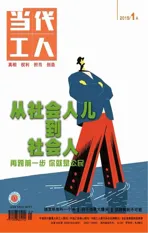路徽:那时的身份证
2015-12-17老杨头子
文|老杨头子
路徽:那时的身份证
文|老杨头子

徽:标志、符号。如国徽、校徽、帽徽、徽章、徽记、徽帜。徽是宣示,也是凝聚,更是图腾。有图腾就会有精神、有意志。社会转型期,当崇高、尊严等被一一解构和嘲弄后,因徽而信仰,在徽里找到自我,便是我们最该重拾的希望。
奖品是800斤小米
1990年中秋刚过,我们这些临近复员的老兵没事就聚在一起探讨,将来的就业问题。七嘴八舌中,战友老蔫慢吞吞地说:“我哪都不去,就上铁路。”老兵们诧异,“你是哪路神仙?你说进铁路就进铁路?咱得听民政局安置。”“我爸在铁路上班。”
能进铁路,那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我也想。我喜欢那衣服,那徽章,那气势。老蔫送我一枚胸章,红色圆形的,上面是白色路徽。我细细打量,中国铁路路徽整体就像一台迎面驶来的机车。上面是象形人字,下面是工字,像铁路钢轨的横截面。从上往下看,喻意人民铁路;由下往上看,喻意铁路工人。我感叹这设计用心,老蔫说,“路徽要表达的就是人民铁路属人民,人民铁路为人民。”看看每年春运一票难求便知,铁路对人民多么重要。
典典滴滴
新中国成立前,一条铁路线一个管理局,各有各的路徽标志;新中国诞生前后,铁路陆续回到人民怀抱,路徽甄选而出,成为新中国工业系统中最早统一使用并沿用至今的标志。据说某些艺术院校还会将路徽作为创意设计的经典范例来评述赏析。
多年后,我曾上网查阅新中国铁路路徽的设计者,介绍寥寥:陈玉昶,满族,出生于1912年,辽宁省沈阳市人,自幼爱好美术,曾在日本的高等商业学校就读,在交通部业务处任职期间应征参加铁道路徽设计,作品最终当选。1969年,57岁的陈玉昶在长春病逝。
至于甄选过程,今日叙述起来并无太多“台前幕后”。当时的军委铁道部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路徽式样,一共收到3200多种图案,每个应征作品都编上号,在铁道部举行了展览,向职工征求意见。民主后的集中便是铁道部专门成立了路徽图式审查委员会,反复审查后,呈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财经委员会批准,确定了现在这个“人”“工”合成的式样。据说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审阅入围作品时,没多加思索就选了这件。
这件事最大亮点在于第一名的奖品是800斤小米,这相当于从事繁重体力的劳动者个人全年足额口粮。我好奇,陈玉昶是怎样保存这么多小米的?穿越到现在,小米手机异军突起,iphone6供不应求,万能的网友们调侃:幸亏不是800斤苹果啊!
这胸章是老蔫的心爱之物,转送到我手里更是视若珍宝。那时路徽的配发、使用和管理很严格。铁路职工出入厂区、值班、公差或集体活动都要佩戴。一旦丢失,要到人事部门备案,将编号记录下来,在铁路局内发行的报纸上登声明作废。作用和重要性不亚于身份证。
然而,我们对胸章的感情远不及老蔫父亲。老蔫说父亲那代人以铁路为家。每当父亲要出门接发列车时,都会照镜子端正一下胸章的位置,然后从挂钩上摘下帽子,对着帽徽吹两下。小小习惯在老蔫眼里显得极其神圣,那代表父亲将要去为人民服务。有一次,父亲把帽子戴在老蔫头上,老蔫站得笔直,生怕自己的小脑袋把帽徽戴歪。
名字只一个
复员后,老蔫顺理成章进了铁路,而我被分到一家企业。那家工厂的烟囱在我当兵前就不冒烟了,我铁了心没去报到。民政局二次分配,把我分到了铁路。我狠狠亲吻了胸章上的路徽,它将成为我身份的象征——铁路人。
报到那天人挺多,铁路广场上黑压压全是脑袋。一个穿铁路服的老者,在二楼平台举着麦克风组织站队。我记不起他的模样,但他帽子上的路徽在阳光下格外显眼,让我印象深刻。
接收人员不关心每个人在部队的职务、表现,就问一句父母是铁路哪个站段的。我说我爸妈都是地方厂矿的。话音刚落,我名字前就被打了个挑儿。
隔天,各站段来领人。我跟着队伍进了火车站后面一个青砖瓦房的四合院。领队的大个子介绍:我姓严,欢迎大家来到工务段。不管以前各位在哪个部队从事什么职务,以后咱们的番号就一个,1435,咱们的名字也只有一个,工务线路工。今日回忆,这情节像极了周星驰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的片段,进了华府,唐伯虎的编号是9527。他为秋香来,我是被那衣服、那徽章、那气势所吸引。
培训我们的教员是来自养路一线的老顾。他向我们展示了锹、镐、耙子、铁棍一类的家伙,然后画了个路徽,“记着,路徽下这个工就代表着我们——每天和道轨亲密接触的工务人。”刚才情绪还有点低落的新人被老顾忽悠得挺兴奋,“咱们就是支撑铁路的脊梁呗!”
铁路特点可以概括为“高大半”——高运量、大动脉、半军事化。以前工务段招人,能扛动枕木就行。随着铁路发展建设,养路一线不光要体力,也拼智力、讲文化。老顾说铁路是个大联动机,工种繁多,每天为旅客货主服务的不仅仅是路服笔挺的车站服务人员和列车员,也有咱们,头上的路徽都是一样的。你们好好干,埋没不了。
我相信老顾的话,那路徽就像一种信仰,证章、帽徽、纽扣、机车、建筑物上,路徽无处不在,也烙印在心中。很难想象,那是怎样一种自豪感和归属感。
理想很美丽,现实很残酷。1997年4月1日至今,铁路先后进行了6次大规模提速。每一次提速,工务人都挥洒了无尽的汗水。相对付出,工务人得到的回报却是微不足道的。
提速后,客货运量陡增,工务段任务量逐日加大,除了常规的维修保养,还要参加无休止的道岔大修、转线施工等大规模施工会战。很多工友常年吃住在沿线现场,一年到头休不到几个完整的星期天。荣光下,工务人默默隐身,我们的衣服油脂麻花,我们的活计苦脏累,我们的月薪勉强糊口。社会上称呼我们“铁道驴子”,还有一套顺口溜: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逃难的,仔细一瞅,工务段的。某些领导也不待见“素质偏低”的工务职工。
何以激励我们?路徽,路徽看得见。
当各级部门成立了不同规模的监察大队,每日拿着高清摄像机、高倍望远镜辗转各地,现场“围猎”一线干活的工务职工时,我心就好痛。倘若真的违章违纪就罢了,偏偏这些人为了完成上头规定的硬指标,鸡蛋里挑骨头,每月都有冤假错案发生。

路徽设计者,陈玉昶(1912-1969),满族,辽宁沈阳人。1938年毕业于日本山口高等商业专门学校。1949年10月,在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任职。1961年调吉林省交通厅工作,1966年调省汽车修配厂工作。这是他当年荣登媒体。
那段日子,我许愿稳稳当当,不出问题。轻则扣钱,重则下岗啊!入路之初,路徽映衬下发光的理想,在这种高压氛围下,消磨成了只是养家糊口。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体制运行的悲哀。
幸而今天一切都在好转。
老情结新变化
在道轨上敲敲打打的我,有一个爱好——写作。2010年,路局宣传部派我去采写温泉寺桥梁工区当年学大庆的事,他们是1960年代铁道部命名的百面红旗之一。现任工区工长领我来到了曾经的荣誉室,门把手早已烂掉,工长找来一根撬棍,别开了门;房子漏了,地板塌了,满地都是剥落的墙皮,只有英模的脸在布满灰吊和蜘蛛网的墙上笑容灿烂。
那天很巧,当年学大庆的老工长,80多岁的于明远老人也来到工区。老人指着一些老照片告诉我:“那时他们想出了冬防洪,夏防寒的思路,但维修费不够,他们就到河里筛沙子,到山上捡石头,割条子编土筐,爆破废旧圬工梁当钢铁料用。”
看老人讲述往事时的神情,我感受到那个年代铁路人的激情。他们创造的不平凡对应着今日的沧桑,曾经的铁路人这一身份证明,或许是一生最大的安慰。路徽的设计者肯定不曾想到,这简单的一人一工,由多少血汗泪铸就啊!
2013年,铁道部撤销,挂了6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的牌子被送到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牌子悄然换上。多年后,或许铁路和航空一样,出现多家公司,至今已有66个年头的路徽也可能发生变化,许多带有铁路路徽的老旧物件会成为收藏界的抢手货。于我,那是职业生涯的最难割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