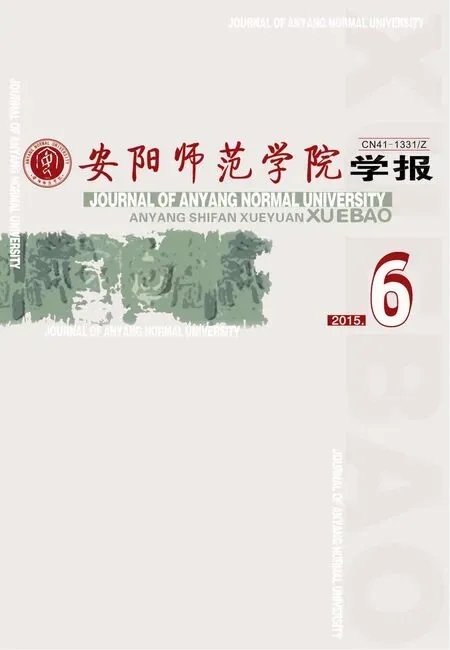佛教对“悼祭”文学的影响
——以“自悼”为例
2015-12-17韩林
韩 林
(大连大学 人文学部,辽宁 大连 116622)
佛教对“悼祭”文学的影响
——以“自悼”为例
韩 林
(大连大学 人文学部,辽宁 大连 116622)
佛教的传入,对悼祭文学中的“自挽自悼”类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说中出现了悟前生类、入冥类及超度类三种故事。与此前的作品相比,体裁上从主要活跃于抒情文学转向叙事文学;内容上从着重情感的抒发转向现身说法;作品的终极指向从面对死亡转向延长生命。这些故事以劫后重生的遭遇拉开了与死亡的距离,淡化了此类题材原本哀伤的情调和悲剧的氛围。宣佛小说过多地承担了宣传宗教的社会作用,无形之中流失了文学的情感表达及审美功能。
自悼;佛教;小说;
悼祭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指一个生命个体在面临死亡时,所产生的对生命的眷恋、对死亡的恐惧、对存在的意义及人生价值的思考,常通过祭奠、悼念、缅怀、回想等一系列相关的现实活动表现出来。“丧悼文化是个体生命意识、伦理关怀和血缘情感等面临死亡的洗礼,而形成的一系列特定情感表现、仪式、风习等,构成的复杂民俗事象。”[1]王立教授在《永恒的眷恋——悼祭文学的主题史研究》一书中,按照悼祭对象把悼祭文学分为悼亡(妻)、悼友、悼子女、悼兄弟姐妹、悼妓姬及自挽自悼六种类型。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六道轮回”、“阿鼻地狱”、“因果报应”等观念随之而入,使自挽自悼类作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早期主要活跃于抒情文学中转向占有叙事文学阵地,从抒情文学中的情感表达转变到叙事文学中的现身说法。
抒情文学中的自挽自悼类故事大多是活着的人对未来将要面对的死亡所发出的感叹,可能是从挽歌发展而来。表现为女性在爱情受挫、男性在前途受阻时的顾影自悼,还有一大批绝命诗及挽歌挽词。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对这一主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产生了一大批相关的宣佛小说,从自悼的方式来看,大约可以分为三大类型。
一、悟前生类故事
轮回观念是悟前生类故事产生的基本前提。轮回(Samsara),又译“沦回”、“生死轮回”、“轮回转生”、“流转”、“轮转”等,音译“僧娑洛”。取车轮回旋不停,众生在三界六道内循环流转,生生不息之意。《心地观经》:“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2]佛教把人世间一切生灵归纳为六种:天(天神)、人(人类)、阿修罗(魔神)、畜生(各种动物)、饿鬼(永受饥渴折磨的生命体)、地狱(生活在地狱里的生命体)。佛教认为,只要时空还存在,所有的生命体都会按照一定的规律在六道中循回流转,独运而不变,周行而不殆,肉体泯灭而灵魂不死。轮回的最终去处是“六道”和“涅槃”两途。所以一个人可能出现前生、今世。前世是人,今生有可能是畜生,前世是畜生,今生有可能是人,如《朝野佥载·榼头师》中梁武帝的前生是一只曲蟮;《异杂篇·唐绍》中唐绍的前生是一只狗。《北梦琐言·刘三复》中的刘三复,知道自己的前生是一匹马,所以他知道马的疾苦,处处为马考虑,受到人们的赞扬。
一个正常人是不清楚自己的前世今生的,这些悟前生的人,是指知道自己前生今世具体轮回的人,这类人属于一个特殊群体,事实上不大可能存在。由于轮回往往与报应联系在一起,所以佛教往往借他人之口来浇自己之块垒。悟前生类故事从功能上看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歌颂人间情感的至高无上,包括亲情、友情、爱情等。故事中的人物大多是在某一世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面对死亡时仍恋恋不舍,发誓来生再续今生缘,转世投胎之后,有的就以悟前生的方式来使人明白前生的因缘。《酉阳杂俎·顾非熊》载,著名诗人顾况之子顾非熊,在七岁时与兄长玩耍的时候,挨了打,他忽然声称自己是哥哥,能叫出弟弟、妹妹的小名,能详细地说出顾况已故儿子的生活细节,每一件事都丝毫不差,一家人都很惊诧。原来他是顾况死去的儿子托生的,因为留恋顾况的父爱不忍离开,转世又回来了。此则故事是儿子感谢父亲恩德而再次托生到顾家,《冥祥记·向靖女》则是因为女儿感恩于母亲的爱而再次托生。这些人有的是生下来就知道前生的事情,有的是忽然之间醒悟过来,与禅宗中的“顿悟”很相似。
另一种恰好相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申冤复仇的。如《逸史·卢叔伦女》记载,有一个云游僧人,到了中午想吃些斋饭,便向正在采桑的卢叔伦女询问,卢女指点他去王家。僧人到了王家一看,他家正在为一群僧人设斋。王家夫妇便请他入内用斋,吃完饭后,王氏夫妇奇怪地询问僧人为什么来得这么及时,僧人如实相告。王氏夫妇觉得很奇怪,便请求僧人带路去寻找采桑女。没想到此女看到他们转头就走,夫妇二人一直追到卢家。卢氏女关门闭户坚决不肯出来,惹得卢氏母亲非常生气,责怪她不应该对邻居如此无礼。忽然听到此女道出某年某日王氏夫妇曾害过人的往事,吓走二人。原来,此女前生父子三人贩卖胡羊,曾借宿于王家,三人全被王氏夫妇所害,尽劫资货。此则故事中卢叔伦女通过说出前生被害之事,揭发了这对老夫妇曾经犯下的罪行。故事通过这样的叙述,说明因果报应,在劫难逃的道理,从而劝人改过。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传入中国后,六朝僧人慧远作了详细的阐发,把报应分为“现报”、“生报”和“后报”三种。前世所种下的因果在二世、三世……受到报应,悟前生类故事大多都属于“后报”。这些故事中的悼祭对象大多是那些冤死之人,他们的死因无人知晓,如果没有悟前生类故事,这些冤情就会石沉大海。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申冤报仇,顾影自怜。在此类故事中,丧悼文化与中国古代的复仇文学主题联系到了一起,内容变得更加复杂。
二、入冥故事
这类故事描述已经死了的人来到阴间之后,由于某种机缘而使他们获得了重生。这种“魂游地狱型情节模式”的设置就是想通过世人之口将地狱报应之事广泛传播,来劝导世人,宣扬佛理。如《报应记·赵文若》、《酉阳杂俎·王氏》、《定命录·陈昭》、《酉阳杂俎·王翰》、《冥报记·李山龙》、《广异记·李昕》、《法苑珠林·陈安居》、《报应录·李质》等,故事中的人物大多都数都经历了冥界之旅,他们重返阳世之后,在惊魂未定之时,说出自己在冥界的所见所闻。《报应记·沈嘉会》载,沈嘉会的虔诚感动了太山府君,被请到太山府君的宫殿生活了二十八天。人们通过沈嘉会返阳的叙述了解到死后世界。《冥祥记·赵泰》以赵泰在冥间所见所闻将地狱中的不同类型的人所要经过的历程做了详细的描述,使人从感性角度来认识死后世界。小说中的人物通过对“死”这一过程的追忆和描述向人们展现“死亡”,表达伤悼情怀。从阴间返回阳间的途径有很多种,最主要的是三种:
第一种是死者因为生前诵读佛经而被放回阳间。如《广异记·孙明》中,孙明每天记诵《金刚经》二十遍,坚持了二十年。他进了阴司之后,冥王因此将其寿命延长二十年,又放了回来。《报应记·王陁》、《广异记·卢氏》等写的都是通过诵读佛经而自救的故事。写经、诵经不仅可以自救,而且还能够帮助他人。《冥报记·大业客僧》写一僧人通过写经的方式把自己已经入冥的两位同学救回阳间。《报应记·李丘一》写唐代李丘一喜好打猎,遭到报应而横死。因为他生前曾经造《金刚经》一卷,阎王即招来死于他手的生灵,令他一一请罪,并要他答应替这些生灵建立功德,即抄写《金刚经》一百卷。这里造功德不仅可以使人入冥返阳,还可以偿还杀生的罪孽,这就为那些犯过错的人提供了改过的机会,扩大了佛教的受众范围。其它如《法苑珠林·刘公信妻》、《酉阳杂俎·僧智灯》、《报应记·袁志通》、《法苑珠林·赵文昌》、《报应记·勾龙义》及《太平广记》中的“金刚经条”、“法华经条”、“观音经”等多是此类。写经、译经一直都被认为是无量功德,历代的高僧传记都少不了这一笔。
另外有一类故事描写主人公曾无意当中施恩于来追索其命的追命鬼,鬼非常感激,于是想办法帮助此人,教他通过念经传法之术来延长其寿命。如《广异记·张御史》写张某为朝廷命官,在渡淮河时,有黄衫人说有急事请求搭船。御船者要殴打他,被张某制止并亲自把多余的饭菜给他吃。当张某到驿所时,却发现黄衫人已在门口等候多时。原来黄衫人并不是人,而是鬼。他奉命取张某性命,本应该在淮水中将其溺死,因感激张某渡船和给饭之恩而不忍下手,使张某在人间多停留一日。张某向他请求延长寿命之法,黄衫鬼告诉他,如果能在一日之内诵千遍《金刚经》,就可以躲过此劫。于是,张某急寻数人帮诵经一千遍,结果,阴司给他延长了十年寿命。《广异记·李洽》的故事也与此类似。佛教十分重视经文,无论从学识上还是从时间上,一般的普通百姓都很少有接触经文的条件,故宣佛小说把佛经与人类情感最脆弱的死亡连在一起,希冀由此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第二种是通过铸造佛像而使冥途中的人或鬼得以返回。佛教造像的规模及种类居于世界各宗教之冠。早期佛教着重伦理教诲,不拜偶像,不允许描绘雕刻人形的佛陀像,凡需要表现佛陀事迹的地方,多用其它事物来代替。如在佛祖生前行动过的地方刻一个脚印,在佛祖说法的地方设法轮或菩提树。公元一世纪时,佛教受印度婆罗门教影响,开始主张佛有许多化身,造出各种菩萨,佛陀雕像。键陀罗(Gandhara)的造像运动,在佛教内部几乎是同大乘教派的崛起并兴的,至贵霜王朝(约公元1一3世纪)时,希腊人的神明观念和造像意识,打破了次大陆避造佛像的禁忌,键陀罗、秣菟罗与阿默拉沃蒂鼎足而三,成为当时的三大雕刻中心。雕像崇拜并不是印度所独有,原始人类的图腾崇拜可以看作是其早期形式,它开始于实物崇拜。在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对原始实物产生敬畏,希望通过自己对其崇敬能够得到它们的庇佑。在表达这种崇敬感情的同时,产生了画像、雕像,并在不知不觉中对其进行艺术加工。
佛教传入后,雕铸佛像的潮流在原有基础上广泛蔓延,小说中也有相应的表现。《纪闻·刘子贡》载刘子贡卒后进入冥司,遇到生前的一个邻居。此邻人请他传话给自己的儿子,自己由于生前有过,在冥司受罪,让儿子替自己造观世音菩萨像,写《妙法莲花经》一部,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升天了。后来子贡返阳又活了七日。由此可见,造菩萨像可以消罪免灾,解脱罪孽。为了突出信仰的虔诚内涵,佛教并不强调亲手造像,只要心向往之,像由谁造,要求并不是很严格。如《法苑珠林》卷三十四感应缘载:
唐坊州人上柱国王怀智,至显庆初亡殁,其母孙氏及弟怀善、怀表并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失其姓名,死经七日,背上已烂而苏,云:“在地下见怀智,见任泰山录事。”遣此人执笔口授为书,谓之曰:“汝虽合死,今方便放汝归家,宜为我持此书至坊州。访我家通人,兼白我娘:‘怀智今为太山录事参军,幸蒙安泰。但家中曾贷寺家木作门,此既功德物,请早酬偿之。怀善即死,不合久住。速作经像救助,不然,恐无济理。’”此人既苏之后,即赍书故送其舍。所论家事,无不暗合。至经三日,怀善遂即暴死。合州道俗闻者,莫不增修功德。[3]
第三种是指在黄泉路上遇到了僧侣,由于他们的帮助而使人免死。如《广异记·刘鸿渐》记载有一个僧人劝刘鸿渐诵《金刚经》,他就照做了。后来,他被阴间鬼使追入冥界,遇到了劝他诵经的僧人,此僧向阎王列数其诵经功绩,使其得以生还。《报应记·张政》载,唐代邛州人张政,暴亡后看见四个鬼来捉他,路上遇到一胡僧,胡僧训斥诸鬼乱捉人,并随之共见阎王。胡僧与阎王理论,说张政是被误捉,阎王本欲检册核实,不想胡僧大怒,阎王不得不马上放了张政。从这则故事中可见僧人不仅可以出入阴阳,而且在阎王面前还颇有地位。这样突出僧人的作用,是佛家宣扬其“三宝(佛、法、僧)”灵异的手段之一。无论这些人在阴间经历了什么,最终结果都是返回阳间。阴间死的悲惨,恰是阳间作恶的结果;阴间的飞黄腾达,恰是阳间行善积德的功劳。赵杏根先生的《佛教因果说与中国文学》把报应分为“现世报”、“现世地狱报”、“地狱报”、“交叉报”、“异世报”五类,其中,“现世地狱报”与“地狱报”基本上在入冥故事中体现出来。*参见赵杏根:《教因果说与中国文学》,《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1期。
“释氏辅教之书”所表现出来的自挽自悼是指个体生命通过冥界之旅,返回阳间之后对生命的肯定,对永生的向往及对死亡的哀挽。此类小说的主人公大多经历了一个生——死——生的过程。这个由生到死,由死再生的过程,是主人公检讨一生功过是非的过程,也是一个教导现世民众的契机。
三、超度类故事
佛教传入之后,人们在面临死亡时多了一个程序,即请僧人做法事、道场,念经超度。如果深入考察可以发现,这种形式是民间习俗、宗教信仰包括道教影响等多方面作用的结果。超度形式总体看来分三种:
首先,为将死之人超度,希望能够借此除病消灾。这种形式在佛教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表现方式不完全相同。早期的此类活动表面上看来表现为巫术,是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多种因素促成的。古代医术不发达,人得了重病在无药可治的情况下,只好寄希望于鬼神。佛教传入后,请僧人念经更加普遍,人们希望由此能够得到佛祖及菩萨的眷顾,使病人能够尽快的好起来。如《冥祥记·董吉》中载:“董吉,于潜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进,恒斋戒诵首楞严经。村中有病,辄请吉诵经,所救多愈。”[4]《广古今五行记·并州人》载:并州人由于对佛不敬而鼻中生肉,大如桃,疼痛难忍,于是请来一个和尚替他忏悔。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把请僧人忏悔当作普通的消灾方法。
其次,为亡者念经是要安慰已死的灵魂,希望他们能够入土为安。《报应记·崔义起妻》记载唐代崔义起的妻子萧氏死后,崔家请了许多僧人来为萧氏修了初七的斋日。《稽神录·高安村小儿》中载,高安村一个小孩死后,每年的祭日,家里都设斋祭奠他。这种祭奠方式的具体程序,文学作品中记录得不够详细,但请僧人超度却常被提起,反映了在佛教影响之下,民间悼祭方式的新变。
再次,为亡者超度,是为他们减轻生前的罪孽,为来生投胎转世做准备,寄托了人们死而复生的愿望。从上文宣佛小说中的返阳故事可以看出来,能够入于阴间又返阳的大多是遇到了僧人、念经或礼拜佛像。这些都离不开佛教的因素。这是一种美好愿望,同时也是一种求得永生的信仰。“人类捉到了灵的观念,乃得慰安的信仰,相信灵的一贯继续,相信死后的生命。然而这种信仰不是没有困难的,因为人与死在面对面的时候,永远有复杂的二重心理,有希望与恐惧交错综着。一面固然有希望在慰安我们,有强烈的欲求在要求长生,而且轮到自己又绝不肯相信一了百了;然而同时在另一面又有强有力的极端相反的可怖畏的征兆。”[5]正是这复杂的二重心理,导致人们的悼祭行为越来越复杂。
宣佛小说中的这类故事是伴随着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小说这种文体出现得比较晚,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小说发展的一个高峰。佛教传入不久就经历了这一时期,佛教的自我宣扬与小说的发展结合到一起,使这类作品大行其道。
丧悼意识起源于人类的自发情感,是个体面对肉体毁灭时所流露出的伤感,是生命在特定时期都会经历的一种体验。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具有原发性。佛教传入之前的自悼作品,把死亡作为终点,指涉的对象是死亡;受佛教影响所产生的宣佛小说中的自悼作品,把死亡作为一个中转站,指涉的对象经过死亡的中转,指向了人生。前者大多表现出哀伤的情调,悲剧的氛围;后者则通过重返阳间的体验,拉开了与死亡的距离,淡化了这种情绪。宣佛小说说教色彩十分浓厚,过多地承担了宣传宗教的社会作用,无形之中流失了文学的情感表达及审美功能,艺术性不强。
[1]王立.永恒的眷恋――悼祭文学的主题史研究[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291.
[2][唐]般若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M].[日]高楠顺次郎等.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三.大藏经刊行会1924-1935:302.
[3][唐]释道世.法苑珠林校注[M].周叔迦、苏晋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1070.
[4][宋]李昉等.太平广记[C].北京:中华书局,1961:772-773.
[5][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33.
[责任编辑:王守雪]
2015-09-17
大连大学青年博士专项基金(2014YW11);大连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
韩林(1978-),女,文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与文化。
I206.2
A
1671-5330(2015)06-006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