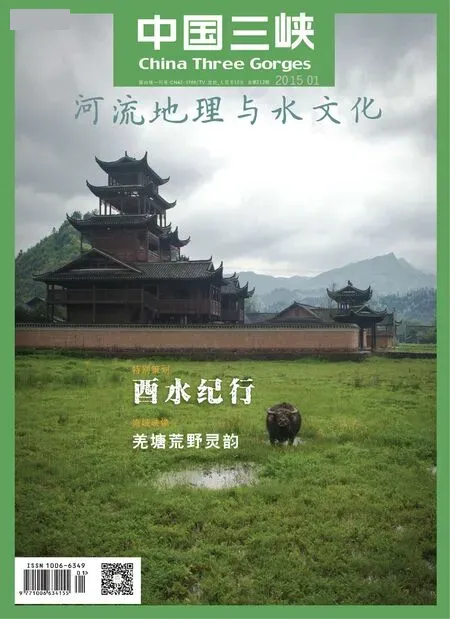宝岛与海
2015-12-16鲁博林编辑李颜岐
文、图/鲁博林 编辑/李颜岐
宝岛与海
文、图/鲁博林 编辑/李颜岐

垦丁海边的夕阳。在变化万千的夕晖中,浅海与滩涂呈现出绚烂的魔幻之姿。
2012年的整个下半年,我都待在台北一所维多利亚式红砖建筑与大王椰子装饰的大学里。台北是一座很繁华的城市,大学却是安静的,大部分的时间,我往返于学校本部和分校的一座图书馆,颇有些肆无忌惮地把时间挥霍在众多竖排繁体书本上。然而在这座临近海洋的岛屿上,每天只是与“古物”为伴,多少有些遗憾。幸得与友人为伴,寻得契机畅游环岛,在岛屿最南端望见太平洋,在小镇信步寻踪,在港口流连追忆,再回到台北去忠孝东路走过几遍,凭此见证了一个时刻呼吸着的、活着的宝岛。

澎湖西屿岛上的草海。天风习习,草海翻腾,骄阳之下渺小的身躯无处遁形,却自由得如登极乐。
大概是从那时起,台湾真正地成为我心底里一个美丽的烙印。平生所见过最美的海浪,拂过最呜咽的天风,听过最动人的笑语,触动过最深的乡思,无不在这一次的旅途中。
行走垦丁
行走在台湾,无论是走马观花的几日行旅,或是年深日久的漫长跋涉,几乎都离不开海。作为岛屿的台湾并不小,然而在浩渺的太平洋中,便是沧海一粟了。岛与岛民的命运,都为海所环抱,在台湾的任何一个角落,即使是白云围绕的大山深处,似乎都能听到惊涛拍岸的大浪淘沙之声,可知每每拂过面颊的暖风,都来自那蔚蓝色的大洋。
与其说是“看海”,不如说是“听海”。在台湾听海,便不得不提垦丁。因为一部《海角七号》而闻名遐迩的垦丁,的确拥有全岛最美的海岸线。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早已游人盈门,其中不少是欧美的背包客。《海角七号》讲的是爱情,以一个卖座却虚构的当代故事做噱头,来为自家吸引眼球,可以说是台湾特色。而许多处交通的不便,也看出这里的旅游产业“初上新妆”的生涩。醉心于人文历史或不愿多费气力的游客,估计会有小小的失望。只是这却并不妨碍垦丁的美。当那出尘拔俗、澎湃深郁的蓝与我们甫一会面,所有的烦恼与此前的不满,几乎都在屏气凝神中融化。
垦丁的海让我想起川端康成在讲述他凝视坂本繁二郎的画时那种触动,“在荒原寂寞村庄的黄昏天空上,泛起破碎而蓬乱的十字型云彩。这的确是日本黄昏的天色,它渗入我的心。”也理解了电影《超时空接触》中,女主角穿越虫洞之际,目睹了整个壮阔宇宙如云烟过眼、惊呼“太美”的极乐之境。在鹅銮鼻的灯塔下面,或在猫鼻头的高台上,当迎着沉雄浑厚的海声远眺蓝色洋面,当强劲却温柔的海风使我融于天地之时,本无一点悲哀的心里,骤然泛起了不可言说的回响,充塞着我的整个灵魂,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几欲落泪;同时又感到那之前萦绕于眼角眉梢的喜怒哀乐,渺小得如同蝼蚁。我想,自然的伟力,也许正是这样给予从古到今的人以震撼、以启迪,恰如醍醐灌顶。
在垦丁行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来回都以十公里为单位,离开了机车便万万不能了。驾着机车,可以方便地穿梭于散布各处的景点——恒春小镇、垦丁水族馆、垦丁森林公园、垦丁大街等,都自有特色,而倘若要靠当地公交系统乃至徒步,恐怕大部分时间就要在等待与休息中度过了。对于游人而言,机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一道难得的风景。卞之琳《断章》云:“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没错,机车上的风景,便是游人自己。所谓“碧海共长天一色,机车与星月齐飞”,沿着海岸笔直空旷的公路,在机车背上飞驰,一边听海风呼啸,一面看天色渐微。在变化万千的夕晖中,浅海与滩涂呈现出绚烂的魔幻之姿,在宝石蓝与玫瑰紫的衬映中迎接初升之月。人生快意,莫过于此。
寻路离岛
垦丁之外,以澎湖为首的离岛也是看海的上佳去处。这就是那个歌里唱过的澎湖湾,有七美的双心石沪、盛产瓜果的白沙岛和号称“台湾堆”的吉贝沙滩。可惜在澎湖的几日,风浪掀天,多数时候只能在马公市内以及临近的本岛徘徊,不想由此却着实领略了一番旅行的真味。

印象最深是那趟漫无目的的西屿之行,这趟歪打正着的旅途也许真正说明了何谓“旅行”。原本计划已提前一天做好,于是早早便起来去车站赶车。这里的巴士是每一小时一班,赶到的时候刚刚错过上一班,延误颇久才得以出发。中途经过澎湖水族馆时贪心地一番流连,转眼日头就过了正午,结果十分不巧地再次错过了下一班继续进发的班车,只好就地再等一个小时。这时已将近傍晚,我和友人似乎都有些倦怠,预备乘车往传说中西屿尽头的灯塔瞅一眼就打道回府。然而车却并未停在灯塔附近,下车处离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眼看四周人烟稀少,无奈只能朝着一个大概的方位步行。不久之后,我们就发现自己迷路了。所幸的是,Google Map还能导航。于是一边靠着电量不多的iPhone寻路,一边探险般往前小心试探,竟不知不觉走到一片高山上的草原。

澎湖岛。从高处观海,一只羊漫步于草间,远处是广袤无垠的海水。
天风习习,草海翻腾,骄阳之下渺小的身躯无处遁形,却自由得如登极乐。两个人在一段柳暗花明的旅途中迷路,再找到路,再迷路,又再次找到,有趣得如童年在后山上的一次神秘远行。我们迎着狂风,兴奋得大喊大叫,张开双臂朝着无人的四野挥舞,在草的海洋中踏出一条道路,像孩子一样飞驰过去。随时端起相机,自由地按下快门,而每一张照片都是自由的。泪水在自由的奔突中悄悄地流出来,却倏地被风吹干,嘴角也在风里微微扬起,风亦慈悲。
我们途经了一座荒废的石头祭坛,一湾美丽的白墙砌成的爱琴海式的渔港,最终找到了一直向往的灯塔。在灯塔下眺望遥远的太平洋,满身疲惫,却也满心充实。飘摇翻飞的海风和广袤无垠的海水再次给了我启迪,使我反悟真正的旅行,就是无惧无怨,心有所向,永远在路上。
闲逛九份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1983年,后来成为台湾音乐教父的罗大佑,在他的第二张专辑里推出了《亚细亚的孤儿》这首歌。台湾的命运便像这歌词所叙说的那样,如同被放逐到茫茫太平洋上的飘萍,交杂着各种颜色、各种方向的风,却惟独失去了根。在台湾的“中国人”——这对他们来说,多少是一个辛酸的称谓。
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是演绎这份离散之情的经典之作。基隆林家兄弟在乱世的悲剧境遇,以及在台湾人心中抹不去的“二·二八事件”的伤痛,都在其中呈现,而作为电影外景拍摄地的九份也由此驰名。九份位于新北市瑞芳区,日治时期因为盛产金矿而鼎盛一时,大批淘金者涌入,将这里的坑道挖得如蛛网般密不透风,曾有“小香港”和“亚洲金都”之称。时移世易,我们到达九份的时候,这里早已脱去了旧日繁华的外衣。登上金瓜石的黄金神社,只见荒废的基座和孤独的石头鸟居,它们曾经见证日本的统治与“黄金山城”的繁荣。可惜天风猎猎,世事沧桑,吹散了历史再也无法聚拢,这人来人往之地,喧嚣终究归于平静。财富与欲望枯竭之后的九份,得以恢复生活的本来面目。
当然,闻名而至的旅人仍是不少的。在九份的盘山公路上,随处下车,便能钻进一条熙熙攘攘的巷子里,领略昔日山城繁华的余音。台湾小吃甚多,这里的巷子便是明证,芋圆、肉干、蚵仔煎一应俱全,不仅如此,上上下下的坡道两边,也遍布许多颇有韵致的创意铺子,贩卖些古早的“台湾特色”,一瞬间将人带回到那个传说中的年代。于是好玩的,好看的,莫不齐全,在城中小巷游荡的过程本身也成为一种眼福。偶尔撞见老戏院的院墙上民国风的壁画,或是电影镜头里熟悉的酒家之时,则似时空易位,乍现一丝错愕。

俯瞰“双心石沪”。澎湖有许多捕鱼用的石沪,规模有大有小,却没有一处石沪比得上七美岛的“双心石沪”。
在九份闲逛,也可以有别样的味道。比如偏离人群走上一条清静的小巷,在一草一木间寻访生活的辙印。九份民居亦是沿山而建,远眺近观景色俱佳。狭窄的小道两旁各是风格不一的小楼房,一路走下去,好像穿行在另一重天地。在一处简陋的别墅之处,我邂逅了一只白猫。暖暖的午后,她本来趴在石梯上晒太阳,另一只小伙伴也在附近张开手脚,躺在高处的阳台酣睡。淘气的“弟弟”、“妹妹”则与经过的游人们嬉耍,摆出各式或慵懒或高贵的姿势和镜头捉迷藏。我们路过时,猫咪方才懒洋洋地伸了下胳膊腿,回头一瞥,清澈的眼神里尽是捉摸不透的心事——恰似九份这座美丽的山城。
基隆记忆
有人把基隆与北美的New York Harbor相比,然而对于台湾的外省人而言,基隆却并不完全是新大陆的开端——毕竟,相对于扬起自由旌旗的雄心勃勃的美国人,许多老一辈台湾人却是以逃亡者的身份赶赴基隆的。对他们来说,这里是暴风骤雨的短暂终结,也是漂泊旅途的漫长开端。齐邦媛先生在她的回忆录《巨流河》一书中,曾记载她们一家迁台之后,自己屡次去基隆港接船的经历。“我最后一次去基隆接船是一九四九年农历除夕前,去接《时与潮》社的总编辑邓莲溪叔叔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一家六口。我们一大早坐火车去等到九点,却不见太平轮进港,去航运社问,他们吞吞吐吐地说,昨晚两船相撞,电讯全断,恐怕已经沉没。”太平轮由此被誉为东方的泰坦尼克号,而基隆港,作为国共内战后期用于国军眷属撤退的接站港口,来到了聚光灯下历史舞台的中央。

基隆街景。
如今的基隆依然是一座人口众多的热闹港口,不乏令游客心驰的景点,譬如让吃货垂涎三尺的庙口夜市和西北方15公里左右的野柳地质公园。然而要一睹其人文意蕴,却不得不亲自走入这座城市的街巷里弄探索。漫步于基隆的大街,会发现它和临近的台北迥异的地方。市中心耸立着诸多西式风格的建筑,构成了一条带着浓郁怀旧气息的长廊景观。作为开放的港口,这里似乎与西方人的关系更密切。最初在此地殖民的西班牙人,早在1626年便在今日基隆的和平岛(那时称社寮岛)修筑了“圣萨尔瓦多城”,后来基隆则历经荷兰人、郑氏王朝、清王朝、日本人的统治。可以说,在台湾的历次易主中,基隆都首当其冲,这也使得港口以片瓦之地承载着数百年朝代更替的腥风血雨,同时也留下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强烈印迹。夏日午后,任意徜徉在一字排开的小洋楼之间,颇有一种离了宝岛,重回天津卫的感受,想到1900年的八国联军,正是从天津港登陆,一路烧杀劫掠,攻陷北京。近代中国的港口城市,在表面的繁荣背后,颇有同样不可告人的心酸郁结。
台北故事
从基隆往内陆几个小时的车程,便重回台湾的心脏城市台北。如今的现代化和繁华景象早已掩盖了当年这里作为“化外之地”的偏僻与荒芜,在以铜钱为图腾的台北101大厦附近,你会以为自己其实身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腹地。车水马龙的罗斯福大街与热带树木相互掩映,灯红酒绿的夜店文化也使游人迷醉,在没有限行的台北街头,机车的咆哮声激发着市民雄心勃勃的荷尔蒙。可以说,台湾再无一座城市拥有如台北这般的自信与强力,就算在仅次于它的第二大城市高雄,也决计找不出台北东区一样的“花柳繁华地”。

九份夜景。在宫崎骏的《千与千寻》里,似乎也有类似的场景,这也是这座山海小镇吸引游人的原因之一。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台湾人在创造了亚洲四小龙的奇迹之后,在一系列的经济腾飞中,多少已经淡忘当年留下的历史疮疤。然而物质的富足却始终填不满灵魂的虚空,命运离散的残缺无法用摩天大楼来补齐,于是对当代的台湾人而言,“传统”一词对他们反更显得弥足珍贵,这就使得即便在台北这最为富庶的都市里,也还保留着足以令人抚今追昔的凭证——譬如台北故宫博物院。

僻静的九份小巷,一只猫回头漫不经心地一瞥。
说起“故宫”,若从这两个熟悉的字眼里,我们只能想到紫禁城那朱红高墙围成的故地,那必定是不完整的。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也顺手牵走了北京故宫中大量的无价之宝,譬如被誉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三宝”的“翠玉白菜”、“肉形石”和“毛公鼎”,以及曾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引起我们无限遐想的“核舟”。可以说,正是这些被赋予了强烈历史印痕的古物,让尝尽离散之苦的台湾人始终不忘自己的文化身份,决绝地挺过了一系列风云变幻,执着地坚持着身为炎黄子孙的那份骄傲感。“故宫”之于台湾的中国人,便如同“约柜”之于漂泊四方的犹太人,只要还有一息尚存,便绝不肯放弃自己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黄公望名作《富春山居图》,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断作大小两段,又在近代的历史风云中各自纷飞,前段《剩山图》陈于浙江,后段《无用师卷》藏于台北。2011年6月,两幅传世画卷在多年隔绝一水之间后,于台北“山水合璧”,当时的总理温家宝这样形容这一文化之盛事:“画是如此,人何以堪。”对于依旧天涯漂泊的中国人而言,不知听闻此语,又将是怎样一番感慨了。
这并非一趟面面俱到的旅程,我所看见的台湾不够丰满,可渗透着我的记忆,鲜活可感。而今离开宝岛近两年,不时想起当时一路的行走感悟,仿佛仍能感到风从那里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