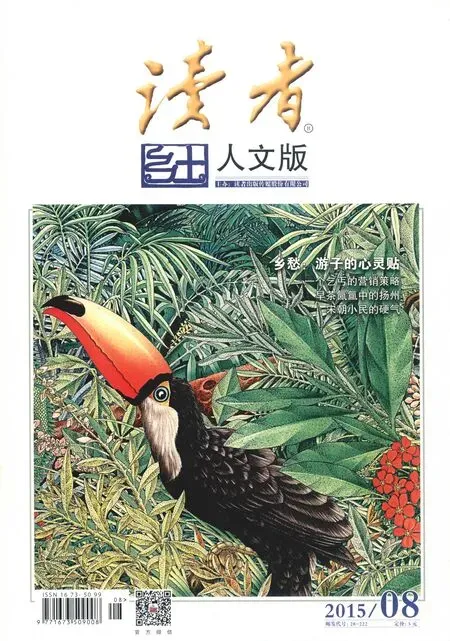旧的城
2015-12-13文/周冲
文/周 冲
旧的城
文/周冲

戏、旗袍、人力车。
写下这三个词汇的时候,旧上海洋场的风尘味扑面而来—20世纪30年代的女子,抹着厚厚的胭脂,盘着爱司头,带着形销骨立的命运,由年轻或不再年轻的三轮车夫拉着,赶赴一个秘密约会。上海大剧院的廊柱下立着一个男人,吸着烟,眼睛看着她,递过来一包微热的糖炒栗子。
然而在这个夏天,我得知了这三个词的另外一种解读方式—武宁。运西瓜的小货车一辆辆地驶过,花伞在膨胀的阳光和雨水中盛开,水豆腐、裁缝店的老皮尺、渡口的风、竹椅和杨梅果,积铢累寸地设计着葳蕤的小城生活,风情万种,流光无限。
最早的光明,由一辆人力三轮车载来。
穿着白汗衫的车夫,摇摆在车蹬上,响着长铃,在大叶女贞的阴影里一闪而过。灰色斗篷里坐着面目模糊的女子,寂静地看着可看可不看的风景,想着可想可不想的心事。时间轻轻游移,戾气尽消,“吱吱嘎嘎”的转轮声中,一只手从斗篷中探出来,掠过雨后的紫荆花。
黎明被车铃唤醒,小贩张檐支摊,出售微笑与好生活。银行的男职员带着两只热艾果,在上班途中边走边吃,滚烫的甜汁流出来,他撮圆了嘴,倒吸气,咂咂舌头。孩子念着“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谁不忆江南”,跑过水门汀的小巷,小书包像雏翅般在身后扑闪……细节活色生香,乘坐着人力车一一经过,就像经过一篇散文或者一首诗。
成年以后,途经许多城市,它们姓名各异、经纬不同,但都被科技与速度锤炼成孪生子。没有哪一座城如武宁这般念旧,宽待历史,宽待记忆。人力车是无声的证明。它们带着旧风尘,在小城的街道拐角揽生意。只要三四块钱,你便可以坐在起伏的背影上,去往想去的地方。
风在下坡处恣意地越过,像老中医的手安慰着皮肤,人的眼睛舒适得眯起来。上坡的时候,车夫跳下车,一手持车把,一手拽车后的椅柱,人弓成45度,奋力爬行,如负轭劳作的牛。
到达目的地,人们下了车,离去了。车夫转道而行,载上新的活计。他们低着顺命的眉眼,在风里咬嚼一只白地瓜,车子横梁上系着的钱罐子叮当作响,斗篷的荷叶流苏一漾一漾,他们觉得知足。正午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车斗里打着盹,白烟卷在指间幽幽燃着,积灰一截截断落,落在车子的踏脚上。
人力车—旧上海与小城在这个词里达成某种默契,内部风起云涌,算尽机关,表面却不动声色。就像悲喜无常的夜里,人力车急速而过,都看到了,看透了,表面却像什么也不知。
就这样蹬着蹬着,车轱辘一转,五月过去了。广玉兰俯下身来的时候,旗袍开始在街巷间熙来攘往。白丝缎的底子上绘着小花,边缘咬着蓝丝线,绳络结扣,风情昭然。低眉顺眼的姑娘,披着浓郁的长发,在古艾湖的边缘走过。

北方是穿不得旗袍的,太粗糙了,太苍茫了,丝绸单薄的料子一落地,就要被糟蹋。都市也成不了旗袍的背景,灯红酒绿、明枪暗箭的世界,一切都在进攻,在索取,矜持成为不懂风情的代名词,旗袍的韵致风干了,像狼狈的绢花。
唯有武宁这样的小城,像屏风一般,提供古典的底色。安分的、多情的、有故事的、入世又出世的,脾气相近,像是天作之合。
青砖围墙的小门打开,穿粉色旗袍的姑娘走出来,发髻微坠,她叫住卖菜人,在板车里翻拣,红番茄、绿辣椒、黄萱花、白米糕,质地素净,色彩缭绕。她想到晚餐的清爽餍足,抿嘴一笑。
也有不再年轻的女子,在黄昏的葡萄架下,翻看一只苍老的红箱子。隔年的旗袍已经皱了,时光这张大网,没有因为它的精致而心生恻隐。她捧着它,想着多年前的千回百转,那轮月,那个人,那些沉默与灼烧。此时的墙外,有人吹起响亮的口哨,骑自行车的男孩,像白鸟一样飞过。
如同人力车,旗袍在这里也出奇地兴盛。曾在古艾河边坐着,打量过往行人,计算这种服饰的穿着率,发现十有二三。她们回家,约会,穿过长长曲径去看一折戏,听传说如何落到人间。
来历不明的花鼓戏班,在这个六月,在午后和夜间,咿呀唱响。古艾河边的青砖白瓦、长藤野蔓,一下子加上了柔光,然后,眠在一片轻盈的宋词里。
我不知道戏班子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也不知他们将在这里停留多久。我只知道在来到这座城市之后,他们就一直在这里,拈袖拂巾,横波媚眼,兰花指在空中游来游去。
旦角穿红,花满鬓,云满裳,珠粒巍巍摇,眉心点朱砂;生角着青,戴着大沿檐,更像水上讨生活的渔家。两个人在台上互相抬举,用牛郎织女作譬喻:“我把你,比牛郎……”“我把你,比织女……”充满暗示的挑逗,在空气中来来去去。唱着唱着,水到渠成了,互喊夫或妻。“胡大姐,你是我的妻哇哈罗”,“刘大哥,你是我的夫哇哈呀”,终身已定,以后生死都要相依。传说里的爱情,总是简单、不费事,轻松得令人不敢相信,但大家喜欢,喜欢这种花团锦簇,祥光普照。
“你带路往前行啊,我的妻你随我来行啊,得儿来得儿来……”台词时顿时起,锣钹响声阵阵,填满唱词的间隙,三两个换戏服的戏子站在没有幕布遮拦的后台,毫无顾忌地解扣宽衣,赤裸的胸膛露出,隐约在观众的视线之内。他们的脸与身体形成鲜明对比,一边白得刺眼,一边黑得醒目,像谢必安与范无救。红色道具箱里挤着算盘、折扇、长髯、须鞭、珠花、胭脂,长铁杆上吊着戏服,花花绿绿一大堆,取尽了人间最鲜艳的色泽。
螟蛾般的人们,被灯光吸引着,簇拥在四周。小孩钻来钻去,姑娘顾盼生姿。老人坐在自家的小板凳上,摇着蒲扇,盯着戏台,一边交换对剧情的意见:“哎呀,真可怜哪!”“宁拆一座庙,不拆一门婚,你捣什么乱呢?”“这婆娘也真狠心!”卖玉米、凉粉、咸水花生的带着小马灯,在角落里守株待兔。他们的篮子上半掩着白包袱,白包袱上倚着一只长长的木勺子。
我忽然非常感动。这样的戏,这样的人,这样的水波与夜晚,彼此融合着、呼应着,成为小城的外部的光彩,内部的柔情。除了它,还有什么能成为小城的胭脂与花钿?除了它,还有什么能成为寂寞夜光的羽衣?除了它,还有什么能成为当地最好的柴火与药引,给予它绽放和疗救?
看戏回来的时候,穿过这些日常欢喜,对身边人说:“生活这么好,我们要相爱。”
(马 钟摘自豆瓣网)